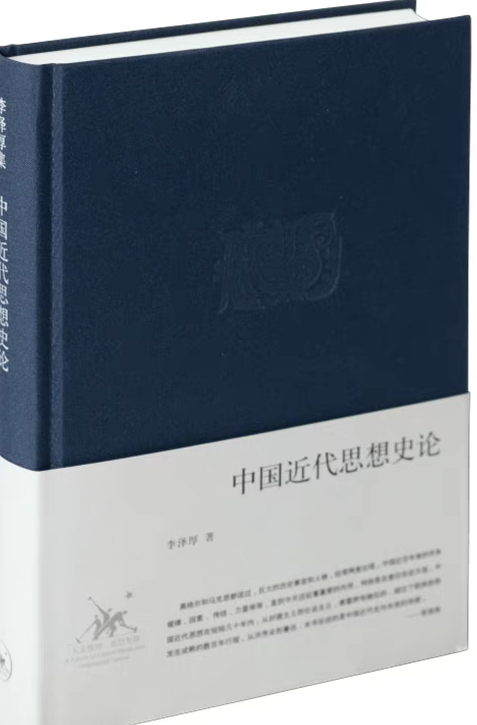我們的“大學”——寫在畢業季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1小时前
這一篇談一談我的、或者説我們的“大學”。
畢業季,QQ上收到了不少即將離校的同學的留言。大部分當然是禮貌性的,或者是為了處理畢業論文相關問題,但也有幾段涉及到師生之間的思想交流的。
其中一段是來自思政專業的C同學:
“非常感謝您對我畢業論文的指導和建議。我從您西哲和演講與口才的課程中也學習到了很多,從您在觀網發的文章也受到了啓發,指導我解決了一些問題,給我看事情提供了新的視角,對我的幫助很大。特別感謝您一直以來的啓發,真的讓我受益終身。”
還有一段是來自其它專業的Y同學:
“老師,我是之前在西方哲學史課後跟您散步聊天的學生。我聽了老師您的意見去看了李澤厚先生的書。《美的歷程》寫的實在是太好了。我最近在圖書館看完了李澤厚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感覺填補了初高中歷史課本上幾頁紙匆匆帶過的極大空缺。書中提到的幾句話讓我醍醐灌頂,説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進程在近代發展並不徹底,封建主義依舊沒有被根除,以致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反覆出現,甚至滲透到傳播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裏面,仔細想來真的是振聾發聵。要是沒有老師您的推薦,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接觸到這樣的書籍和這些敏鋭的思想。還有好多好多話想跟老師分享,不知道能否在畢業前跟老師再見一面。能夠跟老師面對面聊十分鐘二十分鐘對我來説都會是莫大的榮幸,也還想讓老師再推薦一些書籍。”
看到這兩段留言,我努力回憶C同學和Y同學是誰,卻只想得起C同學是女生,而Y同學是男生。Y同學有一次來旁聽我的西方哲學課,下課後對我説他對藝術與美學感興趣,好像還在讀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我隨口説李澤厚的《美學三書》(包括《美的歷程》《美學四講》《華夏美學》)很好,我大學時非常喜歡,曾被同班一位同學借去,良久不還,擔心他要賴賬,遂強硬索回,所以也推薦Y同學看一看。至於C同學,我參加了她的論文答辯(但我不是她的指導教師),評了幾句,似乎再無別的什麼交往了。但她説我給了她很大啓發,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上過她們的專業課,要是一丁點兒啓發都給不了她,那我這個老師不如不當了,畢竟,“無論怎麼講,我和她是博士生對本科生,優勢在我”。她那麼認真地聽我那些講得並不好的課,還來我在觀網的空間吸收她所需要的東西,説明她對自我成長有追求,有想法。這非常好——其實,聽課也好,與老師交流也好,你能收穫什麼,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你對自己的態度。只是C同學才20出頭,“真的讓我受益終身”未免説得太早,加一個“會”字,改成“真的會讓我受益終身”,才真的讓老師既開心,又放心。可見要駕馭好語言文字並不那麼容易,説話作文,不但要有內容、有邏輯,還要措辭得體。
所以後來我去上課,順便又與Y同學見面聊了一次。
在討論他説的李澤厚對“中國沒有根除封建主義”的批評之前,我先講了自己的經歷。
我上本科以及讀研、讀博的年代(上世紀90年代末——本世紀初),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裏(至少就我感受到的那部分而言),“考編”“考公”“上岸”還遠遠不是學生們關心的唯一主題。各種思想還在高校裏進行着認真而激烈的交鋒,也會引起許多同學的關注和參予。
比如我讀研是在某985大學的外國哲學專業,我們的政治公共課則是由公共管理學院開的,而我們同學至少三次在課堂上當面“嗆”過給我們上政治課的公管院老師。
有一次,公管院W老師上課講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時説:“有些人開講座説中國人沒有信仰,真是奇談怪論。中國人怎麼沒有信仰呢?沒有信仰,怎麼會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呢?又怎麼會拋頭顱灑熱血地鬧革命呢?”
這時我站起來表示不同意:“您批評的是我們哲學院G老師的觀點。但您恐怕誤解了他。G老師認為信仰和信念是有區別的。信仰是形而上的,是超現實的;信念則不一定,只要確信現實生活中什麼事情一定會發生,一定是好的,一定值得追求,那就是信念。G老師當然不否認中國人可以拋頭顱灑熱血,但那不是出於真正超越現實的形而上的‘信仰’,而是出於信念,即對現實目的的追求比如‘讓國家繁榮昌盛’‘讓子孫後代生活幸福’。中國人只有信念,沒有信仰,並不會導致沒有犧牲精神,但它會導致個體缺乏精神上的獨立性,因為當你的信念僅僅指向國家、民族、人民的現實利益時,那麼這種信念的最終解釋權就不在你自己手裏,而在國家、人民特別是自稱代表了國家與人民的某種政治力量比如君主、領袖、黨派等的手裏,你就需要這些外在於你的現實政治力量來定義你,評價你,最終為你裁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值得你犧牲一切包括犧牲你的自由去追求的。這樣你就很容易失去獨立思考能力。而有了超越性的形而上的信仰,你的思想就指向一個無限高於現實的精神世界(比如康德的三懸設:意志自由、靈魂不朽、上帝存在),也就擁有了一個完全獨立於任何羣體、任何現實政治力量的視角,從而以你自己的理性對現實中的一切進行批判性的審視。有了這種超越性,你當然還是可以為了國家和人民而奉獻犧牲,但這將是你自主選擇而不是被別人灌輸的結果。而有了這種信仰的支撐,你加入任何集體去共同奮鬥,或者服從任何人的領導,本質上也是建立一種自願委託與合作的契約,而不是完全喪失個體獨立性的依附與盲從。您當然可以批評G老師的這些觀點,但一定要建立在正確理解他的基礎上,而不能無的放矢,打稻草人。”
W老師回應:“哈哈,你一定就是G老師的學生吧?你別誤會,我和你們G老師認識,我説這些也不是要針對他個人,而是學術爭鳴。你説的‘信仰’與‘信念’的區別,的確是G老師的觀點,你解釋得也非常到位,不愧是你們老師的好學生。這個區別,我們姑且承認吧,但你也要想一想:它們有區別,是不是就代表它們可以割裂開來呢?所謂超越性的信仰就不從現實中來嗎?就不會被某種力量所操控嗎?歐洲中世紀的教會不就壟斷了對上帝信仰的解釋權嗎?反過來説,現實性的信念就沒有超越現實的層面嗎?中國人的確講忠君愛國,但真的就沒有獨立思考,就不去批判君主和朝廷嗎?孟子云:‘聞誅一夫紂矣,不聞弒君’‘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又説:‘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請問這不是個體的獨立精神又是什麼?而且中國人連老天爺都不迷信,都要‘人定勝天’,治水的治水,移山的移山,真的會那麼迷信皇帝佬兒?你説我誤解了你們G老師,有沒有想過可能是你們G老師誤解了中國文化呢?”
我對Y同學説:當時我當然信服我們G老師的觀點,但又感到W老師講的也不無道理。今天想來:的確,區分不等於割裂,而一套聽上去邏輯完全自洽乃至自洽得“過了頭”的話語,往往是“割裂”的產物,尤其是對一個五千年曆史十多億人口的共同體的文化下一個簡單論斷,往往割裂了許多背景關聯與有機結構。
我們那一代很多大學生總是這樣積極地參予思想碰撞。哪怕對方是老師,手裏掌握着評價我們的權力,該碰撞時我們也碰撞。在這種積極主動的交互中,書上的觀點、不同老師的觀點,經過辨析、提煉與重構,都成為了我們自己的思想的各個環節。
一個人的大學有沒有白上,或者説你上的那個能不能叫做“大”學,或許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你有沒有自覺地思考過一些“大”問題、閲讀過一些“大”師,並由此而“大大”地開闊了視野,“大大”地提升了心智,並讓“心智的持續成長”成為你的一種內在渴求。回想起來,我做一件事情,或者與一個人打交道,本能地首先會考慮這件事、這個人會令我“升智”還是“降智”以及“升智”的點在哪裏。所以我不但在課堂上經常講起我被這些人和事“升智”的經歷,也經常把這些寫出來分享,這是我在盡一個“大”學老師的責任(當然我盡任何責任都是首先出於自身興趣),大概也是令C、Y兩同學感到有啓發的地方。
因而也就是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思想激盪中,我上大學時讀了相當數量的思想史著作,也包括李澤厚的思想史論三部曲:《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與《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Y同學之前説的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令他感到“醍醐灌頂”的幾段話,應該是如下幾段:
“……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主義,在近代中國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宣傳普及,啓蒙工作對於一個以極為廣大的農民小生產者為基礎的社會來説,進行得很差。無論是改良派的自由主義,或鄒容吶喊的平等博愛,或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都遠遠沒有在中國廣大人民的意識形態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愛國義憤壓倒了一切,此外,從洪秀全到章太炎的種種小生產者的空想和民粹主義,具有深厚的社會土壤,享有廣泛市場和長久影響。康有為基於大工業生產的《大同書》雄大理想倒如同他這本收藏起來不讓人知道的書一樣,淡漠地消失在數千年農業小生產的封建社會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一規律對近代中國作了無情的諷刺。農民革命的道路可以通向新的封建剝削和統治,章太炎的半宗法半牧歌式的主張可變而為梁漱溟‘以鄉村為本位’之類的民粹主義實踐,併為毛澤東所注意。經濟基礎不改變,自由民主將成為空談;而要改變小生產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民主又正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在這方面,只有魯迅是偉大的,他開闢了不斷向前行進的反封建啓蒙道路,在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芒。
如前所指出,中國近代舊民主主義時期的思想在純粹理論部門(哲學或社會、政治、文化的理論學説上)內是缺乏深度的,沒能提出一個比較系統、深刻、完整的哲學體系。中國近代哲學思想的特點是內部藴藏着十分錯綜複雜的矛盾,一方面具有豐富的辯證法的因素和貫徹着一種講求實際、主張科學的唯物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卻又包含着十分濃厚的誇張主觀心知和精神力量的唯心主義。其中由經驗論走向主觀唯心論和主觀地運用辯證法,是最值得注意的哲學迷途。與此同時,缺乏與近代科學的內在必然聯繫,低估、輕視理論思辨,帶來了日後實用主義大舉入侵和主觀主義與權力意志惡性氾濫的嚴重後果。
從洪秀全到魯迅,本書論述的是中國近代走向未來的浪潮。與這浪潮相對抗的,是同樣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國近代正統派的思想。它們佔據社會統治地位,其現實根源是建立在小農生產基礎上的封建生產關係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意志、利益和要求,其思淵源是以程朱理學為正宗的中國封建儒家思想。這個陳舊不堪的意識形態在近代條件下,卻極為頑強地通過變換各種方式阻撓着歷史行程的前進。它或者以封建生產方式這樣一個共同體作為基礎,從而滲進農民階級的思想觀念中,使農民革命創造出一個異化的實體,從精神和物質上統治、奴役壓迫和剝削自己,平均主義、禁慾主義反而創造出無所顧惜和無所不為的特權集團和階級。它或者隨着近代氣候而轉換衣裳,穿一件‘中體西用’的新裝來抵擋資本主義;它最終則以素有傳統極為發達的中國帝王的統治權術,來破壞不可阻擋的近代民主潮流。雖然心勞力拙,每況愈下,但近代中國這種種封建主義的妖魔鬼怪卻並不可輕估,詳盡研究它的來龍去脈,是件很重要的工作。
……
……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竟至如此地捉弄人,野心、陰謀和權術居然又附在‘新’一代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身上出現了。剛剛批過‘竊國大盜’的人,自己又想做做竊國大盜了。‘稱天才’、‘設國家主席’、‘當女皇’、‘按既定方針辦’,不斷上演的竟仍是這樣一幕幕令人作嘔的封建醜劇,一百年前的先進中國人已經在要求開議院重民權,一百年後的今天,封建主義的陰魂卻仍然如此不散,並且還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而似乎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這不正是值得深思和總結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嚴重教訓麼?”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三聯書店2008年,489—491、498頁)
李澤厚此書初版於1979年。不難看出,李澤厚在此書中對中國近代“反封建不徹底”的批判是一直延伸到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身上的。而這位被“醍醐灌頂”的Y同學所不知道的是:李澤厚這種“中國近代反封建不徹底”説,就是他後來提出的“救亡壓倒啓蒙”説以及“告別革命”説的雛形。換言之,李澤厚之後沿着這條思路一徑到底,實際上否定了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歷史,也同樣會否定馬克思主義。在這裏他還打着“馬克思主義”旗號,但到了2011年,他就認為“馬克思講按勞分配,按需分配。這是個烏托邦理想,實現不了”,毛澤東“是以農民革命的民粹主義來接受和實踐馬列上述烏托邦。”(《中國哲學如何登場——李澤厚2011年談話錄》,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56—57頁)我還讀過李澤厚的一本藉着談馬克思主義而更露骨地否定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的書(現在恐怕已經不能再版了)。
所以我在談話中提醒Y同學:讀李澤厚的書,不要看到幾段話就“醍醐灌頂”“拍案叫絕”,最好將他前前後後的書和文章都看一看,並且要有一個批判的頭腦,多問幾個“真是這樣嗎?”“為什麼?”
李澤厚作為“中國近代反封建不徹底”的證據而大張撻伐的“特權集團和階級”等現象,本質上是一切私有制社會共有的剝削與壓迫的體現,而並不是封建社會更不是中國傳統社會所獨有的。資產階級在它向封建主階級舉行革命的時期,當然會衝擊和粉碎封建地主權貴的“特權”,這個時候,“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當然十分動人。但一旦政權到手大局已定,資產階級很快就會形成自己的比封建貴族強大得多的“特權集團”,即那些屬於億萬富翁及其豪富家族的特權集團——看看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難道不正是如此嗎?
至於中國,中國近代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包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這樣的反動權貴集團,並不是被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推翻的,而是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鐵拳砸碎的。這一革命是比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得多的反封建革命,因為它是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要消滅一切剝削與特權的根源——私有制。資產階級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喊出什麼樣的口號,都沒有也不可能徹底反封建。例如哈利·沃勒普(Harry Wallop)(其祖父是第九代Portsmouth伯爵)2013年出版的《購物如何定義英國階級》一書中提到:“目前英國還有1000名左右的世襲貴族,真正仍然有錢有地的貴族已寥寥無幾。”但貴族仍然是英國的大地主。據2010年Country Life Magazine發佈的數據,英國仍有超過1/3的土地掌握在極少數貴族手中(轉引自北京新東方雅思2018年3月13日譯載的《金融時報》文章《英國尚存的一千多名貴族,過着怎樣的生活?》)。不同的剝削階級之間總是同病相憐兔死狐悲的,因為資產階級不能不擔心徹底反封建的邏輯延伸下去會威脅到私有制本身的存在。
今天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友善”,但這與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有本質區別,也決不是為了什麼“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貫徹到底”。今天中國己經是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反對特權並掃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最佳武器,而事實證明資本主義那一套意識形態即使在今天的西方也反不了特權了,用在中國更是隻能造成混亂與倒退。今天的中國如果像李澤厚等人所鼓吹或暗示的那樣“全盤西化”把資本主義的“課”再補一遍,那麼不但資本主義要復辟,封建主義也會復辟,而且國家的獨立和主權也將無法保證。
中國跨越了資本主義階段而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是一個空前偉大的創舉。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我在之前的文幸幾次提到,馬克思認為東方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如果一定要搞資本主義反而會是畸形病態的,首先毀滅的不是封建貴族,而是村社等仍有生命力的前資本主義公有制共同體,而這些共同體本來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的——但必然要經歷艱難曲折的歷程包括這樣那樣的失誤。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寫於改革開放的起始時期。那時剛剛打開國門,看到西方國家如此發達而我們還相當清貧拮据,一部分中國人會產生一種“我們事事不如人”的感覺並懷疑我們幾十年社會主義是不是“搞早了”甚至“搞錯了”。一部分“精英”(其中有不少是建國以前的剝削階級的後代)就將我們國家凡是與西方不同的地方——其中很多東西比如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帶來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與文化體系,等等,其實正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都叫做“封建殘餘”“反封建不徹底”,鼓吹要把我們“跳過去”的資本主義階段按照西方的樣子老老實實原原本本地再走一遍。聯繫這一背景,李澤厚等人寫出這樣的書,從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一直到將共產主義説成“烏托邦”,可以説是一部分人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失敗主義心理的集中體現。
談話結尾,我向Y同學推薦了幾本德國古典哲學書,並建議他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在上大學時面臨那麼多思潮但仍然保持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對它們進行辯證的、歷史的考察,就是因為我從中學開始就相當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嘗試以之分析各種問題。
我的大學時代就是這樣過來的。而且如果獨立思考這些大問題並不斷在互動中打開新的認知就是“上大學”,那我現在也仍然在“上大學”。
畢業不是離開“大學”,而是走向新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