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早就開始“靈活就業”了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昨天 22:39
看理想
2025年07月18日 13:01:41 來自安徽省

《東京奏鳴曲》
“靈活就業”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的職業選擇。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超過2億人。餐飲服務、生產製造、騎手/配送、超市零售、市場推廣的崗位數量位居前列。
鄰國日本近年也興起零工熱。作為發達國家,日本影視作品中所呈現的零工時薪,常常達到幾十到一百多人民幣。主角們不僅可以靠打零工維持生活,還有餘裕發展個人興趣。
打零工真的可以實現財務自由嗎?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到底有沒有窮人?如果有,這些窮人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講述 | 潘妮妮
01.
發達國家有窮人嗎?
世界銀行2022年制定的貧困標準為日消費2.15美元,用於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低於這個標準線,就是一般概念中的“窮人”。
這裏的“窮人”一般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原本的生活狀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遭到了破壞,但是沒有或還未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比如印度、巴西的貧民窟,普通自耕農的土地被工廠徵用,或者被外國資本支持的大農場拿走。
這些失地農民來到大城市,從事零散的底層工作,在城市的邊緣自發搭建住所,形成聚居的貧民窟。他們收入低,居住環境狹小,衞生狀況惡劣,治安環境也通常由黑幫組織而不是國家來維護。這是我們更熟悉的“窮人”的狀況。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日本的確不存在“窮人”。日本人均GDP有三萬多美元,按照目前的匯率,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為300多日元,無法負擔在日本一天的衣食住行。
在上個世紀,日本的城鎮化水平就達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即使是山裏的農村,給人的感覺也是環境清潔,交通發達,居民安居樂業。
哪怕是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後,中國遊客來到東京、大阪等城市,還是會感嘆日本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線下商業繁榮興旺,一副井然有序的樣子。“失去的三十年”彷彿沒有改變日本的發達狀況,日本沒有“窮人”。
然而,事實沒有那麼簡單。如果説發展中國家窮人的關鍵問題,是“還沒有充分享受到發展成果”,發達國家的“窮人”則是完全融入了發達國家的發展體系中,既享受了發達帶來的成果,也遵守體系裏的規則,承擔體系裏的義務。
但是,當國家發展停滯甚至衰退以後,一些人漸漸享受不到成果,卻仍然要遵守規則、承擔義務,於是生活就陷入窘迫,成為了既不被社會關心,又要受社會規則約束的“窮人”。

《東京奏鳴曲》
“網吧難民”是其中的代表,這個羣體在全體人口中佔比不算大,但是他們身上反映的問題特別有典型性,引發了很強的社會共鳴。
日本的“網吧”,字面上通常叫網絡咖啡館或者漫畫咖啡館,通常分成若干個帶電腦的單人小隔間。價格是一個小時300-500日元,通宵的價位在1000到4000日元。網吧附帶提供免費的飲料、簡餐和淋浴間,隔間談不上隔音,躺卧的時候身體不能完全伸直,免費飲料餐食的水平也可想而知。
2007年,也就是日本遭遇“失去的十五年”的時候,出現了一羣長期居住在“網吧”的人。無論男女老少,他們的共同特徵是無法穩定地租房。
日本人的房租,和日本人的收入數據相比,似乎不算高,而這些人大多數是“非正式僱傭勞動者”。日本政治家和民眾固定的思維方式,還有僵化的社會體系,都沒能適應泡沫經濟崩潰之後的巨大變化。
在曾經繁榮發展的日子裏,日本的房屋出租形成了很多“規矩”。除了需要預付訂金和提前繳納數個月的房租,房東和中介也會通過各種方式審查租房者的背景,如果沒有明確的工作單位,或者曾經有多次搬家的記錄,都可能會被婉言謝絕。
在泡沫經濟崩潰前,日本社會似乎默認,一個日本人“有穩定工作”是正常的,應該終身在同一家企業穩定地熬年資升遷,對同一家企業不離不棄。“終身僱傭”既是一種權利,又是一種義務。
不過實際上,即使在日本經濟最好的時候,也只有大企業和部分中型企業才有實力搞“終身僱傭”制度。只不過經濟發展得好,失業比較少,在很多小企業也能幹一輩子。
總之,經濟發展繁榮時期,穩定的僱傭狀態讓社會產生了一種文化自豪感,認為終身僱傭是日本人自帶的出廠設置,員工忠於企業,企業保護員工,一輩子安心工作。在這種社會自豪感下,日本人的品格和穩定工作掛鈎,沒有穩定工作的人會在人格上受到質疑。
而具體到租房問題上,各種對職業和收入的嚴格審查,既是為了確認租房者的經濟實力,也是在審視租房者的人格。接納沒有穩定工作的人入住,可能會讓其他居民感到“不安”,影響公寓的評價。
這些在日本就業狀況穩定的時代定下來的規矩,本意也許是維護日本社會的穩定,但在“失去的三十年”裏,卻成為了很多勞動者的枷鎖。
泡沫經濟崩潰之後,企業難以維持龐大的用人成本,很多中小企業破產或選擇裁員,而大企業雖然礙於終身僱傭制度無法直接裁員,但是可以採用內部調動的方式,逼迫員工主動選擇辭職。

《東京奏鳴曲》
於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日本的企業越來越多地放棄終身僱傭正式員工,選擇“勞務派遣”的非正式員工。
所謂“勞務派遣”制度,是勞務中介公司一邊和勞動者簽約,一邊再和用人單位簽約,向對方派遣勞務人員。勞務人員與中介公司和用人單位之間是三角關係,會同時受到兩者的影響。
勞務派遣的直接好處是提升用人效率和就業的靈活度,潛在弊端是中介和企業為了節約成本,在涉及派遣員工福利的時候推卸責任。這就需要政府或者公共機構出面進行有效地監管。
日本國內對這方面問題的批評很多,在很多情況下,用人單位會認為派遣員工並非“自己人”,中介公司經常和派遣員工籤短期合同,導致派遣員工經濟和福利待遇顯著低於正式員工,在用人單位裏的地位也比較低。
在“網吧難民”一詞流行的同時期,日本還拍了電視劇《派遣的品格》,主角是一位能力超羣的女性勞務派遣員工。
該劇主要有三種爽點,第一是看勞務派遣超人解決正式員工解決不了的問題;第二是看主角整頓職場,幫助下層員工反擊上層員工的霸凌和性騷擾,痛擊職場等級制度;第三是看女主角和其他派遣員工痛快反擊來自正式員工的歧視,為派遣員工正名。
電視劇的收視率非常高,媒體討論熱烈,卻不夠針砭時弊。一邊替觀眾批評日本的職場文化落後,另一邊鼓勵派遣員工要有自信。
歸根到底,還是希望社會擺脱對“終身僱傭”的追求,接受勞務派遣越來越多、就業不穩定的事實。
02.
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進入21世紀,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政治家都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想通過降低企業成本的方式來活躍市場經濟,國家政策也進一步支持勞務派遣和打零工的工作方式。這類勞動者被統稱為“非正式僱傭勞動者”。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歷年數據,非正式僱傭勞動者佔全體僱傭勞動者的比例,從1989年的19.1%,到2015年突破40%,之後就在這個數字上下徘徊。此外,非正式僱傭勞動者和正式僱傭的勞動者之間存在着顯著的同工不同酬問題。
以2020年為例,正式僱傭勞動者收入中位數為32.42萬日元/月,非正式僱傭只有21.48萬日元/月,其中女性更是隻有19.33萬日元/月。對於上班族來説,這個收入水平必須努力節儉才能勉強有所盈餘。

《東京難民》
2008年,日本媒體採訪了“網吧難民”。受訪者大多數是年輕人,出生在東京之外的小地方,本身學歷普通,只能從事零工或者派遣。除去交通費、吃飯和社交,剩下的錢用來付房租和必須的水電、網絡、公共設施使用費,就有點捉襟見肘了。
何況房子也不好租。居住條件和環境好一點的地方,需要預付的現金多,對租户的工作狀況審查比較嚴格,而且一般要求長租,但是非正式僱傭經常換工作地點,如果一直住在同一個地方,萬一換的工作地點太遠,交通費吃不消。
條件不苛刻的地方又不夠方便和安全,不如干脆在網吧裏將就,反正年輕熬得起。結果網吧住久了,有長期無固定住房的記錄,再想租房就更難租了,陷入了惡性循環。
除了年輕人,媒體還採訪到了一些中年人。有一個從事IT相關工作的男性,先後經歷了公司不景氣、裁員和離婚,隨後就一直從事勞務派遣工作。雖然他收入尚可,但要付離婚後的贍養費,加上工作場所不穩定,就在網吧裏住下了。
白天,這位男士穿着乾淨的襯衣和西褲,拿着公文包出門,輕易地融入了清晨的人流中,看起來就是普通的上班族,體面的“中流”。但在網吧生活,意味着他已經失去了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成為了社會無視的“下流”人羣。這個社會的物質生活也許仍然很發達,但是和他沒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發達國家的“窮人”,他出生在發達的城市,也成長在發達的城市,沒有離開城市的選項,那就需要一直遵守發達國家的城市生存規則。但是這些生存規則,是“一億總中流”的時代設計的。
在經濟繁榮的時代,市場經濟把很多原本是“享受”的東西變成每個人必須消費的必需品。而當一個人的工作狀態和收入不再屬於“中流”時,卻還是要遵守發達國家的城市規則,繼續為體面的中流生活買單,就會和發展中國家的窮人產生同樣艱難的感覺。他們都在努力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
日本媒體現在大力宣傳“地方移住”,就是搬到小城鎮或者農村去住,類似於中國的“逃離北上廣”。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説,能夠“逃離北上廣”有幾個條件。

《日落日出》
首先,中國有大量的城市環境建設得不錯,和北上廣生活的落差不是太大。其次,很多年輕人本身在北上廣打拼,逃離其實是回家。最後,國家政策還是在追求平衡發展,希望就業的資源不要過於集中在北上廣。這個過程雖然不可能一帆風順,但是我們還在努力。
而日本的情況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資源已經高度集中在東京和大阪兩個巨大都市圈,和這兩個地方公共設施建設水平接近的城市非常少。日常生活便利性的差距,讓很多習慣了東京生活的人望而卻步。更何況很多家庭就是幾代人生在東京長在東京,無法逃離。
發達國家窮人的特徵不止於此。“網吧難民”租不到房,説明經濟上的弱勢羣體,不但得不到社會和政府的關心,反而被邊緣化了。實際上,日本“終身僱傭”觀念的背後,也有法律的因素。
1947年日本製定《職業安定法》,其中第44條就明確禁止有償的職業中介,也就是今天的“勞務派遣”。這個法律在當時是合理的,因為戰後初期社會混亂,黑社會勢力很大,勞動力中介市場被黑社會控制,需要維護社會穩定。
在1986年日本正式制定《勞務派遣法》之前,“勞動派遣”在理論上都是非法的。這就導致民眾對“勞務派遣”和其它的非正規僱傭形式,產生了一種無意識的排斥和歧視心理。
而且,由於經濟繁榮時期“勞務派遣”沒有得到國家的充分承認,國家在制定針對勞動者的福利政策時,基本也是針對“企業員工”或者“行業工會”這類有明確身份的正規僱傭勞動者羣體。
而到了“失去的三十年”,國家大力鼓勵非正式僱傭,目的是削減企業成本,緩解國家的財政負擔。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和社會會認真思考非正式僱傭勞動者的福利嗎?
很多非正式僱傭勞動者享受不到企業內部的福利,健康保險和退休金保險也需要自行繳納。收入越低越不穩定的人越是如此,保險負擔比正式員工高,未來能領到多少退休金卻很難説。
在我們的刻板印象裏,日本老年人都拿着很高的退休金,過着悠閒的生活,日本也經常有網民罵老年人把國家的錢吸走了,沒有錢給年輕人用。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日本媒體採訪過許多退休金非常微薄、必須省吃儉用的老年人,不少人還在租房子住,擔心因為年紀太大被房東趕走,退休金租不起別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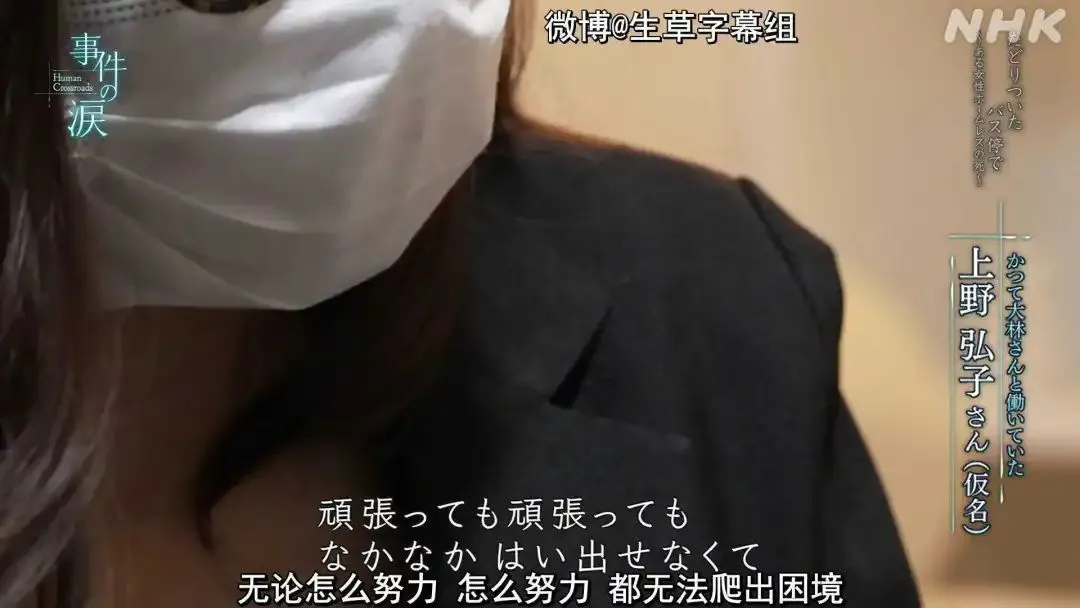
《事件之淚》
這樣的老人,大多數過去也是“非正式僱傭勞動者”。看着他們,現在的中年非正式僱傭勞動者,也會擔憂自己的未來。
很少有人會樂觀地相信日本政府能夠積極增加國民福利,畢竟幫助弱勢羣體這種事情,既要靠良心,更要看實力。而現在日本的狀況令人懷疑。
尾聲.
被拋棄的“中流”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38個成員國,基本算是被認證的“發達國家”或者被認為有潛力的“準發達國家”。
據該組織2022年的“相對貧困率”調查,日本在38個國家中排在第八位,達到15.7%,前面的是哥斯達黎加、羅馬尼亞、以色列、墨西哥、拉脱維亞、愛沙尼亞和保加利亞,都是著名的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
這個排名讓日本非常挫敗,畢竟在過去,日本一直相信自己的社會是非常平等的,併為此感到驕傲。日本國內因此更加地關注貧困問題,並定位了三個容易陷入貧困的羣體。
除了前面提到的非正式僱傭勞動者和領退休金的老人,還有一個羣體是單親母子家庭。這些羣體的共同點,就是在日本經濟繁榮的時代,他們不是主流社會和政府關心的對象。
那時候人們認為日本會一直終身僱傭,也沒有出現這麼多老人,主流社會和政府默認日本人的家庭關係很穩定,很單純,男性上班,女性在家帶小孩。所以福利直接給到有穩定工作的户主男性,很少去考慮女性一個人帶孩子且女性自己很可能是非正式僱傭勞動者的情況。
到了“失去的三十年”,這些問題都浮現了出來,但是國家已經沒有能力可能也缺乏意願去關心他們了。
這就是發達國家的“窮人”。他們是曾經的“一億總中流”,又從“一億總中流”裏面被扔出來,但是已經沒有別的生活選擇。他們繼續生活在昂貴的大城市裏,沒有逃離的選項,也無法期待政府會突然有錢有精力來關心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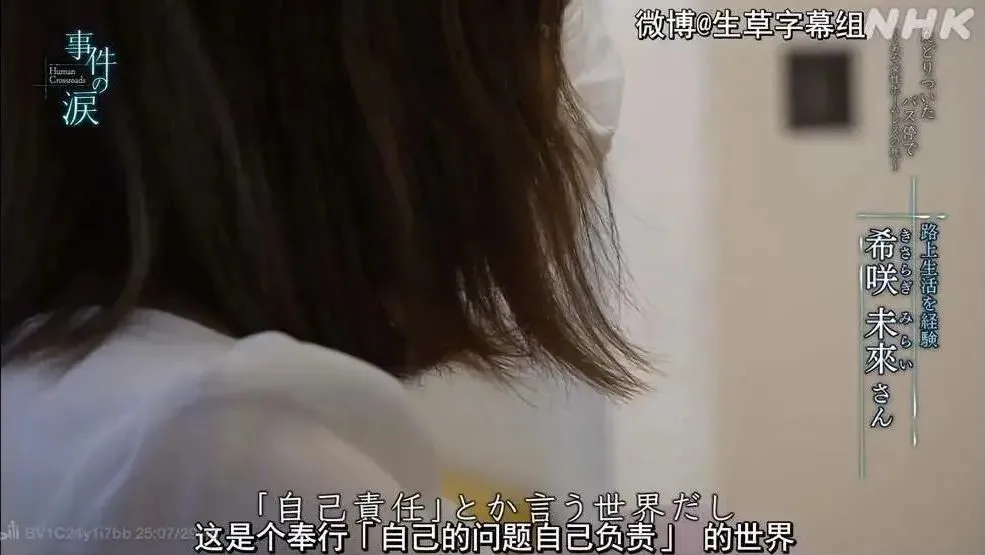
《事件之淚》
因為教育、金錢和精力的限制,他們也沒有什麼表達自己意願的渠道。他們走出家門,外表可能仍然是乾淨,漂亮的。因為這是發達國家大都市的生存規則,即使手頭沒什麼錢也必須這麼做。
發達地區的“貧窮”問題和發展中地區的“貧窮”問題截然不同。
發展中地區的貧困是缺乏發展,因此對發展中地區的“扶貧”,是找到一條合適的發展道路。對發展中地區的扶貧,其實也是一場對未來的投資,只是必須要找到合適的方法。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日本,也是通過國家主導的發展,逐漸縮小了農村和城市、小地方和東京之間的差距。
而對發達地區的“扶貧”是另一種挑戰,因為發達地區民眾的基本生存需求,遠高於發展中地區。
這不是説發達地區民眾好高騖遠,而是發達地區往往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商業,所有的基本需求都需要付出金錢去購買。而為了獲得金錢,又必須提升和打扮自己,付出學習和社交的成本。
發達城市裏的需求太多,收入和消費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從而陷入“貧困”。這也是很多學術研究會反思“過度城市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