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撤檔,直麪票房崩盤,但是好可惜_風聞
电影杂志-电影杂志官方账号-电影杂志——为你发现好片29分钟前
作者 | 我是影小妹
當張子楓飾演的花滑運動員江寧舉起冰刀,在深夜的滑冰館劃開對手鍾靈脖頸的瞬間,鮮血噴濺在潔白的冰面上,映照着她嘴角那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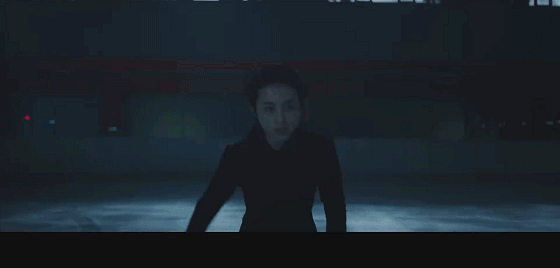
這就是新片《花漾少女殺人事件》的血腥開場。

5月戛納首映,7月18號上映。
雖然一度傳出撤檔的消息,但電影還是在最後一刻,在眾多商業大片的廝殺之下,艱難按照原定的檔期上映。
不出意外,票房非常慘烈。

這部由陳正道監製、哈佛背景新人導演周璟豪執導,張子楓、馬伊琍、丁湘源主演的作品。
借花樣滑冰的冰刃為喻體,剖開了青春期的焦灼掙扎與東亞家庭代際關係的沉重枷鎖。
影片核心圍繞花樣滑冰運動員江寧展開。
她正面臨職業生涯的背水一戰,而她的教練,正是母親王霜。

王霜年輕時亦是花滑選手,未能實現的夢想化作對女兒近乎嚴苛的掌控,她常有意無意地傳遞着一種信息:
若非生育女兒,自己本可成就更高。
這種高壓環境,使江寧如同一根緊繃欲斷的弦。

更致命的是,發育關帶來的身體變化與舊傷困擾,讓她的競技狀態大不如前,賽場上的接連失利不斷侵蝕着她的自信。
此時,染着紅髮、性格張揚的鐘靈意外闖入江寧的世界。
作為滑冰館的臨時工,鍾靈展現出驚人的花滑天賦——
她身材完美,未經系統訓練卻能在冰上輕鬆完成高難動作,其自由鬆弛的姿態與江寧的緊繃壓抑形成刺眼對比。

王霜迅速被鍾靈的天賦吸引,不僅力邀她加入訓練,甚至為她購置裝備,最終讓鍾靈住進了江寧的家。
鍾靈的挑釁直戳江寧痛處:“你媽説了,我才是她的希望,而你,已經是棄卒。”
這句話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一個深夜訓練的場合,積壓的嫉妒、憤怒與對自身存在價值的徹底否定,驅使江寧舉起象徵過往榮耀的冰刀,狠狠划向鍾靈的脖頸。
目睹全過程的王霜異常冷靜,一句“我來處理,你好好準備比賽”,將母女二人共同拖入罪惡的深淵。
電影敍事並未止步於這起“殺人事件”。
導演採用了冒險的“開門見山”策略,開場即揭示結果,隨後層層回剝悲劇成因。

觀眾很快發現,最初的“真相”僅是冰山一角。
影片巧妙織入多條暗線:江寧日常訓練中隱藏的家庭裂痕,冰場維修細節、賽事安排變動等看似無關的情節,都成為推動更大謎團的關鍵伏筆。
臨近結尾,一個顛覆性的反轉徹底重塑了觀眾對“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認知——鍾靈並未真正死亡。
那個血濺冰場的駭人場景,實則是江寧在巨大精神壓力下產生的幻覺與臆想。

真正的“殺戮”,指向了母女二人扭曲關係中對彼此靈魂的長期扼殺。
這個反轉深刻揭示了影片的核心命題:
在扭曲的代際關係中,簡單的善惡二分法已然失效。
王霜的控制慾源於自身未竟的運動員夢想與人生失落,她將對自我的不滿投射到女兒身上,以“愛”之名實施壓迫。

江寧則深陷對母愛的極度渴望與對母親壓迫的憤恨之中,她的偏執與掙扎,同樣包裹着對這項運動複雜難言的情感。
當王霜最終向女兒坦承,自己當年生涯終結並非因生育,而是能力所限,並希望女兒放下包袱時,江寧的回應卻直指本質:“我滑冰,是因為,我真的很想贏。
我和你,是一樣的人。”沒有俗套的和解,她在坦然接受自我慾望的同時,也完成了精神上的“弒母”與“釋我”。
影片結尾,她獨自走向冰面,即使失敗,卻在那一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喘息。

《花漾少女殺人事件》的鋒利,在於它精準地刺中了東亞社會兩代人的共同病灶。
王霜的形象是無數“雞娃”家長的縮影——他們將自我價值的實現捆綁在子女的成功上,以“為你好”之名行控制之實,卻模糊了孩子作為獨立個體的生命邊界。
江寧的掙扎則映射了在高壓期待下成長的年輕一代:如何在追求卓越與保有自我之間尋找平衡?
當外界的肯定成為存在的唯一證明,靈魂的代價又該如何計算?

電影借花滑之美與競技之痛,具象化了這種無處不在的拉扯。
那些優雅旋轉背後是日復一日的血淚傷痛,光鮮的賽場實則是沒有硝煙的殘酷戰場。正如江寧對鍾靈的回答:“這麼多年,我已經習慣了。
無論是鮮花掌聲,還是傷痛病患,滑冰已經成了我的血和肉,我們不能分開。”這何嘗不是對當代人困境的隱喻?
我們投身的事業、揹負的責任、乃至賴以生存的社會角色,早已與血肉交融,愛恨交織,難以剝離。

影片結尾,江寧那句“我真的很想贏”的坦誠,撕開了長久以來籠罩在“奉獻”“犧牲”等宏大敍事下的個體慾望真相。
它不提供和解的童話,只確認存在的真實——承認野心,直面慾望,與痛苦共存,或許才是掙脱無形枷鎖的第一步。
當冰刀劃開的不僅是冰面,更是虛偽的平靜表象時,《花漾少女殺人事件》便完成了它最犀利的表達:
青春的突圍與生命的重量,終究需要每個靈魂獨自在冰刃上,跳出屬於自己的舞步,哪怕帶着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