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搞副業,不用偷偷摸摸了?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昨天 22:23
在人間
2025年07月22日 18:00:22 來自內蒙古自治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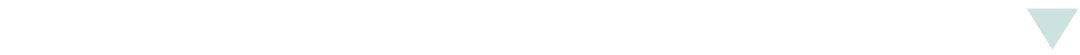
7月8日,重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微信號上發佈的一篇文章,在各大社交媒體上不脛而走,裏面明確指出:在不違反紀律、不泄露信息、不影響主業的情況下,機關事業單位幹部可以從事自媒體、健身教練、跑滴滴、送外賣等合規副業。
該內容在互聯網上發酵,民間猜測,莫非重慶打響了“第一槍”,正式宣告公務員可以搞副業?——在此之前的多年,對“公務員兼職”一事,全國性法律仍持原則性禁止的態度。
其後,成都日報、湘潭市人民政府網、福建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河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官方媒體也先後轉發了這條信息,範圍覆蓋中國大江南北。
相關內容的留言區裏,置頂的多是叫好聲:“這個政策好”“重慶是個包容性很強的城市”“通過吃苦努力正當收入應該支持”……
也有不少自稱是公務員的ID,表達出一種“不敢信”的態度,“什麼時候公務員被允許做副業了”,還有人説“連賣自己的快遞箱紙板都會被保潔阿姨舉報”,何談做副業。
網友熱議的另一面,是現實中公務員的集體沉默。當聽到可能的新風向,鳳凰網接觸到的8名公務員都覺得,儘管對同事業餘搞兼職已司空見慣,但真把“做副業擺上枱面”是“不可能的”。他們更傾向擁抱一直以來的信條:做副業的前提是“要隱蔽”。“因為一報備就是一個不允許”,“做副業等於和晉升無緣”。
弔詭的是,眾人將信將疑其時,作為“開了口子”的重慶,卻已把上述“允許公務員副業”一文刪除。當鳳凰網7月17日致電重慶人社局,對方回應“從未發佈過類似通告”,“可能是工作人員轉發了其他公眾號的內容”。
所以此次“新規”,到底是公務員系統革新的宣言,還是一樁無人認領的社交媒體烏龍事件?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李宏勃認為,地方釋放的可能是一種“正向的信號”,他告訴鳳凰網,或許應該樂觀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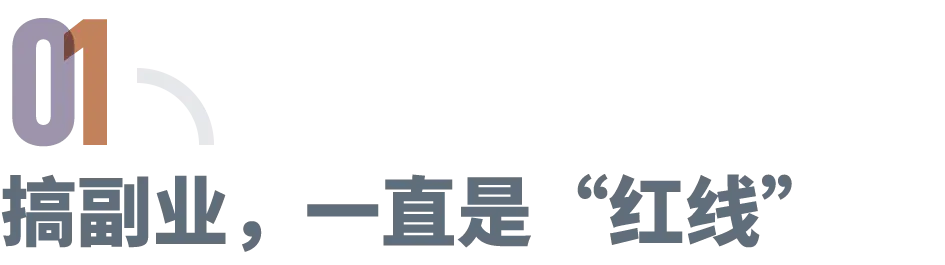
上海公務員付易泉常在小紅書上刷到討論“公務員做哪些副業合法”的帖子,他對跟帖裏的一條評論印象深刻,大致意思是“不敢評論,默默收藏”。
但他並沒有刷到此次“新規”事件,被告知的第一時間,他反應淡淡的:“哦,是嗎?”
社交媒體上盛傳重慶率先鬆了口,但四位重慶在編公務員也都表示“不知道”這個情況,而且認為“話題太敏感”,實在不方便多説什麼”。
此外,儘管河南疾控也轉發了“允許做副業”的文章,該省某地級市體制內人員李貝貝也表示沒聽説“明確公開説鼓勵副業”,反而感受到的是單位“越來越謹慎”,她説同事們普遍的態度是“生怕一個不留神就查到你”,“八項規定工作組、駐派紀檢組、違規吃喝……好像(公務員的)一個很小的動作就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更別提做副業了。

她自己就被查怕了。在上大學時,大學生創業有優惠政策,李貝貝的親戚就利用這種便利,用她的身份證辦過營業執照做雜貨鋪的小生意,商店的法人是親戚。“那時候我沒有入編,對這個事情完全不在意,辦就辦了。”李貝貝説,不久後親戚不開店了,可營業執照一直沒有註銷,等到入編做公務員以後,一次統一排查公務員是否註冊營業執照的行動查到了她。
李貝貝先跑到區裏註銷營業執照,隨後寫了多份情況説明,包括實際經營人和她是什麼關係、銀行流水明細、為什麼要借自己的名字給實際經營人辦理營業執照、有沒有實際參與經營等內容。“直到前年,我還在因為這個事情寫檢查,原因是我沒有政治敏感性,怎麼能隨隨便便借給人家。”
嚴防利用職務撈錢、“權錢交易”成了最嚴格的紅線。機關單位甚至也拿“不能辦營業執照”來嚴格要求編外人員。李貝貝單位有個女生邊考教師資格證邊做公益崗,有天她突然不來單位了,詢問相關領導才知道,因為她家裏人也用她的身份證辦了營業執照,上面查到了這張營業執照,直接取消了她的公益崗,“因為她違規經營”。
四川某地級市退休公務員胡昭告訴鳳凰網,從來沒聽過政策“鬆口”的説法。他表示據他三十年公務員生涯所知,所有的“副業”都是“悄悄地進行”,而按照過去機關單位的處事方式,“有關係的就不會被舉報、被查,沒有安排好領導的(公務員)就要遭”。這種説法也得到了曾經在南方某地級市組織部工作的宋琪的印證。
一些公務員在離職以後做副業,也會被前單位“追殺”,哪怕是此次新規明確允許的兼職:自媒體博主。宋琪2024年離職以後成為自媒體博主,走的是“體制內科普類”賽道。後來因為被人認出並且打電話給原單位確認身份,前同事特地電聯他“讓注意不要亂説話……叫我最好不要做(自媒體)了”。“實際上在三四線城市,公務員很容易被監控到。”宋琪後來搬家去了更大的城市,他説在大城市裏自媒體人多、各種聲音也多,淹沒在這些聲音裏,相關部門就不太會注意自己。
“現在還有倒查十年、二十年的機制,也就是説你在職期間如果有‘違規行為’,只要有人舉報、檢舉,即使你退休也會抓。”胡昭表示,倒查機制牽連了許多已經退休公務員。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倒查20年”是中央紀委2020年的反腐十大關鍵詞之一。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解讀,大量退休官員被查處,體現出執紀執法政策的改變。

在日趨嚴謹的背景之下,明面上做副業有一個必要條件:向組織“報備”。但是否批准,具體到地方或是單位,又有不同的態度。
“每年單位都會統計一次,有兼職情況都要向組織報告。”付易泉説。不過,他到現在沒有看見不允許或者被調查的同事,因為“實際上大家都不會真的報備”。
前公務員、主播“繁繁”也傾向認為,一般情況下,報備做副業,相當於允許別人把你在工作中出現的任何一點小錯誤都歸結在“你做副業”這件事上。“報備”成了一種“把柄”,落人口舌,“誰願意給自己招惹這樣的麻煩呢”。
因此大部分公務員都不會選擇報備,“除非(副業)做到一個非常大體量”,比如郝雨或者當年明月。如果是小公務員,繁繁表示:“有哪個單位領導會説行,同意你做副業呢?對於領導來説,同意就意味着風險極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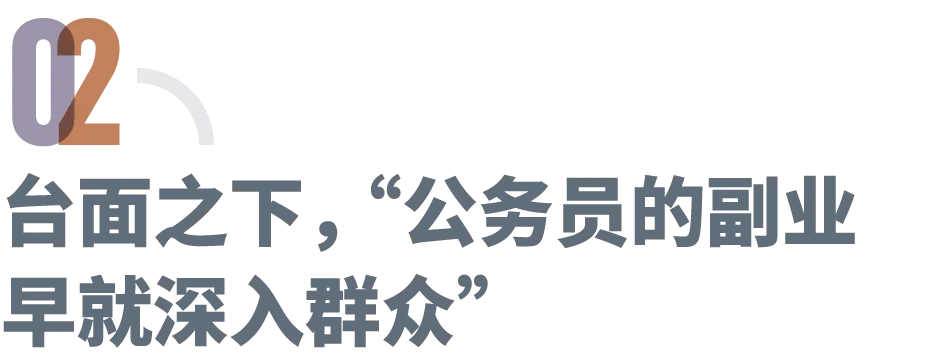
即便可能面臨的阻礙重重,“做副業”早已成為公務員私下最關心的話題之一。
繁繁曾經做過十年的公務員,辭職以後成為播客“體制內”的主理人,她有超過15萬個聽友,大部分是體制內在編人員,她説與“做副業”相關的幾期節目流量高於平均數,收聽量都在1.5萬人左右。
具體到公務員個人,“隱蔽性強”變成了做副業的必要前提。“你會發現做自媒體賽道的博主,很多都用了變臉和變聲器。”繁繁説,她在職的時候有同事炒股,但自從單位開會強調上班時間不許炒股,她視線範圍內就沒人在辦公室打開過炒股軟件。
上海公務員付易泉的觀察也類似,“都在台面下進行(副業),同事不會和你説,你看見了也不舉報,這是基本道德”。工作十年,見到過不少同事突然辭職後無縫做起其他職業,比如一個女同事去年辭職以後搖身一變成了瑜伽教練,私下打聽才知道,“她其實在職的時候已經做一些代課的兼職”。

除此之外,他還見過下班以後收費給小學生輔導語文作文的檢察官,在大學兼職講課的辦案法官,“公務員的副業早就深入羣眾”,他説。也有剛進單位的年輕公務員或者家裏比較困難的同事跑滴滴,“嚴格來説跑滴滴也很難不違規,因為這需要你辦下網約車運營證,不然就是黑車了”。付易泉聽同事詳細拆解過開網約車的經驗,下班以後6點開始一直到晚上11點,1公里能掙2塊錢到5塊錢不等,一天能掙200到300塊錢,“還要看運氣”。
至於繁繁本人,過去也在在職期間做過一些“副業”,比如在辭職前的幾個月就已經開始做播客,2017年也做過民宿。
“我當時根本沒有去想過能不能做播客、能不能做民宿這種問題”,她只知道在職期間做播客嚴格不接任何廣告,沒有得到任何收入,而民宿房子主要是母親在管理,她下班後有時搭手幫忙。她沒有跟房客透露過自己是公務員,房子也是自己家的,“相當於我自己拿來交朋友的一個工具,和一些房客聊天是很有趣的”。辭職以後,她才意識到這或許還是不太妥當。
李貝貝也曾在辦公室裏看到過學廣播電視編導的同事幫別人剪視頻,那是一條護膚品的廣告。“他應該有一個接廣告的渠道……這兩年短視頻風起,所以他的生意還行,接單接得還挺頻繁的,一個月多收入幾千塊錢應該沒問題。”李貝貝不敢太近看,只是遠遠看見同事把剪好的視頻發進一個羣,對方給他發了一個200元的紅包,一單就算完結。
還有學播音主持的同事下班會去輔導班做兼職老師,機構公開宣傳的頁面從來不提及這個老師,也就不涉及公務員“拋頭露面”的問題,“沒有留痕跡,看不出來是誰在做副業”。

就繁繁瞭解,公務員做副業中賺得最多的還是“知識付費類”的,例如有位聽友幫人分析“個人優勢”,幫助他們在職場當中站穩腳跟,靠這種諮詢服務一年增加的收入會有六位數。也有播客聽友分享過一些體制內很火的小成本“副業”,例如在閒魚上給出“鏈接”賣各種文書材料,或者發佈文章代寫的鏈接,“資料包1塊錢一個系列,積少成多。”
李貝貝就幫人撰過稿,她主要的“客户”是其他機關單位有私交的公務員,“體制內組織會機關公文寫作比賽,有的單位內部系統會有提交文稿的KPI,如果完不成,會被通報批評”,有不想寫的人,就會找寫手來代筆。她有段時間每個月交兩篇類似的文章給“客户”,內容是“廉政作風的感悟”。
做副業更“卷”的是機關單位裏的編外人員,白天幫人打遊戲練號,晚上跑滴滴、做遊戲直播,空閒時間“刷有聲讀物”賺平台的虛擬金幣兑現真錢。李貝貝説單位裏的後勤保障人員日常工作是維持設備正常運行,只要設備不出問題就屬於“大閒人”,“所以大把時間等着幹副業”,再者他們是“臨聘人員”,不怕被舉報,真被開除損失也沒那麼大。李貝貝説,“單位是幫他們交社保的地方,他的孩子兩歲,結婚也沒多久,做副業也是出於養家餬口的壓力”。

增加收入,是越來越多公務員想搞副業的原因之一。
“有些財政吃緊的地方已經發不出公務員的績效。”宋琪説,績效一年多則二三十萬,少則幾萬,“那些要靠薪水吃飯的人是很難受的。”
李貝貝的單位就已經兩個月沒發績效工資了,所在地區的區級單位甚至三個多月沒發工資了,“他們的口號叫‘保六爭九’,就是保證一年發6個月的工資,爭取發夠9個月工資”。她説,同事們做副業的態度就是“我想賺錢”。同事此前當着領導的面算孩子上輔導班、特長班的開銷,父母看病的開銷,以及房貸,“確實壓力很大,如果私下不做什麼(副業),真的是挺難的。放眼望去,我身邊這些做副業比較卷的基本上都是有孩子的。”李貝貝説,再不讓機關單位的人去幹點別的活計,“真的沒有辦法了”,她推測可能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各地鬆口“公務員做副業”的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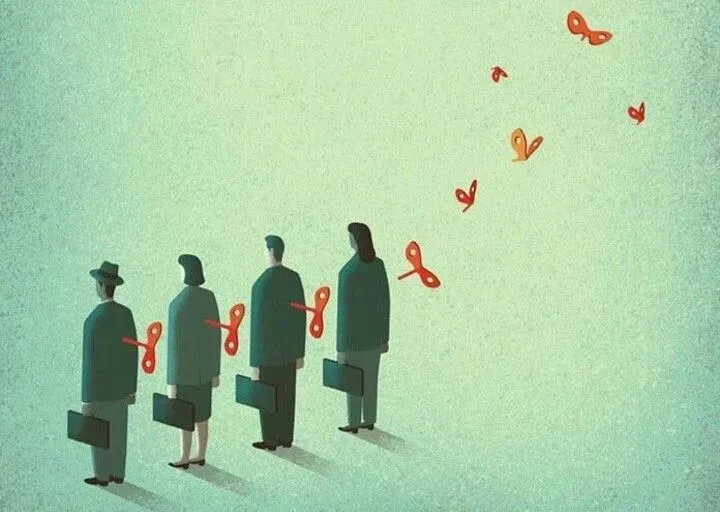
付易泉自己沒有幹過副業,倒不是他擔驚受怕,只是覺得實在當不了“卷王”。他撓着自己的頭髮説:“為啥我忙得沒空開展副業?你看我頭髮都要掉光了。剩下一點頭髮要留着,還有兩個娃要帶。”
説起近幾年的收入,“總體薪資降了20%”,他稱要不是實在太忙也想找點事情來補貼家用,因為養兩個孩子實在太花錢,“比如現在小學進去英語都不會從字母開始教,那父母工作忙怎麼辦,只有去上幼小銜接的補習班,兩個小孩就是兩份錢。”
“老實説,正常下班後憑自己的勞動獲取報酬,真的有錯嗎?”
體制內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卷副業不如踏實工作,“搏晉升”。付易泉説,“公務員每升一級都會加工資,雖然少,但現在我們最快一年半可以升一級,努力工作,可以比別人爬得更快,意味着退休以後的待遇更好。”
在這種背景下,公務員羣體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工作態度。“想往上卷,就卷職級,躺平的推都推不動。”李貝貝説,大家活得挺通透。付易泉的下屬有20%是想往上卷的,“説要加班從來不打回票,這樣領導提拔都會想到他們”,80%是躺平的,“無論你説有什麼事找他們,他們都説有別的事情要忙,要加班就説家裏有事,長時間這樣,領導也開不掉他們,就會邊緣化他們”。
宋琪總結,做副業的重點羣體是被邊緣化的“40歲以上的基層公務員”。就他觀察,這羣人的特徵是“上升空間不大”,40歲了做到副科級,成了“被領導放棄的人”,而“這樣的人在體制內佔絕大多數”,他們工資相對較低,但工作穩定,“人到四十,家裏可能正是需要花錢的時候,因為上有老下有小”。
宋琪認為,有一官半職的領導之所以對列出的副業不感興趣,一是因為本職工作非常忙碌,二是因為公務員隊伍裏有一句話是“只有指着工資花錢的那羣人缺錢”,意思是那些處於領導崗位的高層公務員生活各方面的開支都不花自己的工資,總有人給你安排好。“住房有單位分,車有單位配,現在是不允許開單位的公車,但説實在的我所接觸到的很多的領導都還是用單位的加油卡,只是他不會自己去加,司機會開着車去加油,單位會以請工勤人員的名義去僱傭司機。”

業餘副業與否,也與所處部門相關。宋琪觀察到,公務員羣體中忙到基本沒時間做副業的部門包括黨委組織部、紀委、政法委、宣傳部這樣的核心部門。具體到“局”,各個地方的重視程度不同,邊緣化一點的“局”相對來説比較“閒”。除此之外,每個單位當中也有被邊緣化的“閒人”、“懶事的領導”。宋琪過去認識的某地旅遊發展局的副局長愛好書法,但無心管工作上的事,教人寫書法,個人收了幾十名學生。
“體制不會因為你管的事兒少而開除你,工作就像分蛋糕,你願意少吃點,自然有人願意多吃一點,領導老搶分工,即便忙、累也要搶,那是因為權力是讓人上癮的。”宋琪説,換種角度思考,如果上述副局長真的沉迷教書法,只收取和市場價格一致的正常教書費用,反而是沒那麼渴望權力的一種表現。

對於“公務員搞副業”如何評判,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馬亮、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李宏勃都認為,官方從未確認過哪些副業允許公務員從事,只是劃了“紅線”和禁區。
鳳凰網查閲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官方網站上的通報,並未發現“允許公務員做哪些副業”的相關規定,但近年來有不少相關案例,詳細闡明瞭不被許可的副業,和曾經被許可的副業。

不少傳統副業形態屬於高危領域,一不小心就擦邊違規。最典型的是公職人員違規經商辦企業、違規從事營利性活動,在通報中被稱為“一邊當官、一邊發財”。在過往典型案例中,公務員自己或與他人合辦、以他人名義開辦旅行社、賓館、電影院、採砂場、洗車店等,都受到了開除黨籍、政務撤職處分,並收繳違紀所得。
還有一些特殊“兼職”被通報批評,例如2018年重慶一村幹部兼職“風水先生”被通報批評。據重慶市委黨委通報,該地涪陵區同樂鄉蓮池村黨支部書記胡澤明,從2001年任蓮池村村委會委員起,先後多次為蓮池村村民建房、安葬看風水,選擇陽宅陰地並收取費用,每次150至500元不等。2004年起,他開始在村裏兼職做“風水先生”。通報指出,胡澤明涉及黨員幹部參加迷信活動,同樂鄉紀委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還有不辦實事、只搞副業的“躺平幹部”被免職的案例。2015年湖南省保靖縣4名紀檢監察干部因熱衷“副業”,十八大以來沒有主辦或協辦過一件紀律審查或信訪件調查,而被調整出紀檢監察干部隊伍。
雖無紅頭文件規定,中紀委網站上也曾公佈一些公務員做副業的案例,明確表明“不違規”,其中包括“擺地攤”和“跑滴滴”的情形。

最典型的“做副業”被許可的案例,是2016年安徽歙縣王村鎮一名副鎮長被舉報跑網約車。他因腿部風濕疾病治療費用花掉超過1.5萬元(其中大部分為借款),跑網約車是為了還錢。他在前往縣委黨校參加早上9點半會議的路途中順道拉了趟“專車”,被熟人舉報,那時他已經總共跑了359單,淨收入近3000元。
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2019年1月,一名自稱屬於揚州市寶應縣的網友“樂樂”在揚州市人民政府網站“寄語市長”頻道留言詢問:由於生活壓力較大,諮詢下公務員利用週末時間送外賣是否違紀?隨後寶應縣紀委回覆稱,“公務員如因生活困難,利用週末時間送外賣,原則上不構成違反黨的紀律,但作為公務人員應當向組織上報告有關情況,並不得影響本職工作的開展。”
鳳凰網查詢安徽歙縣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發現,十年前被舉報跑網約車的副鎮長,已於2025年6月得到提拔,被晉升為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鳳凰網溯源發現,2025年7月這則所謂發佈“允許公務員從事六大副業”的通告,實則是一樁體制內無單位認領的“烏龍事件”。自媒體頻頻引用的消息來源——重慶人社局,在7月17日電話中回應鳳凰網,“未曾發佈過相關通告”,工作人員表示“可能是轉載了其他公眾號的文章”,且人社局官方微信號已刪除該轉載文章。稿件源頭為湖南日報旗下的“湘伴”微信公眾號綜合整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等內容而成,截至發稿時,該稿件被福建、河南、貴州等省政府機構廣泛轉發。
但“公務員能做副業”的消息已然一石激起千層浪。包括“粉筆”在內的考公培訓機構已經迅速將“如何看待公務員做副業”的話題更新進入2025年題庫,分析利弊。
“我是覺得憑勞動但不憑任何跟職級、職務相關的內容,來獲取合理的報酬,都還是OK的。”繁繁認為,公務員也是人,總會希望生活過得好一點,多一點收入。她始終忘不了前同事因為對烘培熱情滿滿,在朋友圈面向所有同事低價售賣自己做的蛋撻,用好幾個月掙到的2600塊錢給自己添置廚師機的快樂,“其實公務員需要這樣的活力,來疏解心理壓力,倒不是説真的能掙多少錢,而是給自己一種積極暗示,我生活工作可以平衡得很好”。

宋琪認為,考公的年輕人一方面選擇的是“穩定”,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創新力不足”、“拒絕接受新事物”的特徵,而做副業是一種真正深入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實踐方式,“幫助這些今後可能需要做決策、影響規則的年輕人,對普通人的生活有更深的體會,是一件好事”。
“當然,不可避免地,一小部分人會利用職權違規謀取利益,形成腐敗,影響社會穩定。”宋琪補充道,也正是因為這樣,如果能有明確“紅線”的同時,給基層公務員羣體指出能夠做具體哪些副業,把事情放在明面上,並且單位執行透明的標準,“才可能不會出亂子”。
但也有網友指出,“允許公務員從事的六大類副業”可能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公務員不得違反有關規定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
李宏勃認為,法律對公務員做出相關規定,本意有二,一是避免公務員利用手裏的權力謀取不當的利益,杜絕一切形式的“權錢交易”,二是考慮到公務員代表國家形象,是給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所以要求這個羣體有敬業精神,要把全部的精力拿來為國家的公共利益服務,不負社會的期待。

但是隨着新經濟的發展,新業態的出現,存在不違背這兩個本意的前提下,讓公務員羣體既能有一份合理的額外收入,又有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這對社會是有利的。應該抱着樂觀積極的心態看待這種信號。”李宏勃表示,原有的法律規定需要像《立法法》所説的,要跟上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保持科學性,如果簡單一刀切,不允許公務員從事所有的副業,或許沒有什麼特殊的好處,反倒壓制和阻礙了一些新事物。
“如果公務員做副業沒有違反立法的目的和法律關切的公平正義時,沒有影響本職工作,我更傾向於鼓勵人的個性和自由,這對社會有利、對自己有利的一種行為,應該鼓勵。”
他表示,地方嘗試之後發現有利於社會發展,甚至可以推動立法的修訂。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