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村:一個“三農”樣本半個世紀的樂與痛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1小时前


背景
中國的改革,以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中國的現代化,也必將以“三農”的現代化為終點。
1949年,中國總人口為5.4億,農村人口為4.8億;1978年,中國總人口為9.58億,農村人口為8.38億;2024年,中國總人口為14.08億,農村常住人口為4.65億。1978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2.83億,佔全部就業人口的70.5%,即務農者佔就業的大頭;2024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1.63億,佔全部就業人口的22.2%,即從事二產三產的佔大頭。
中國有“大國小農”的國情,很難像發達經濟體那樣只有1%~3%的人口務農。但中國振興“三農”的大方向一直也是——從農村到城鎮,從農業到非農產業,從農民到市民,在遷徙、轉型和升級中實現協調發展。
説來不復雜,真要實現這種跨越並不容易。
就我在各地所見,一畝農地的流轉價格大致在七八百元到一千五百元,這代表了中國大多數地方農地產出的價值。如果只是種地,加上政策扶持,温飽當無憂,要想富裕極難,所以必須發展非農產業,但這往往意味着風險和不確定性。
不過,人民羣眾的韌性和創造力也在於,他們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富裕路、振興路,儘管這中間有太多的困難和挑戰。

感受振興村
在目前中國47萬多個行政村裏,有一個叫振興村的地方,位於山西省長治市上黨區,版圖面積6.6平方公里,有2300多名村民,也被叫作振興小鎮,曾榮獲“全國文明村鎮”“國家4A級旅遊景區”等諸多榮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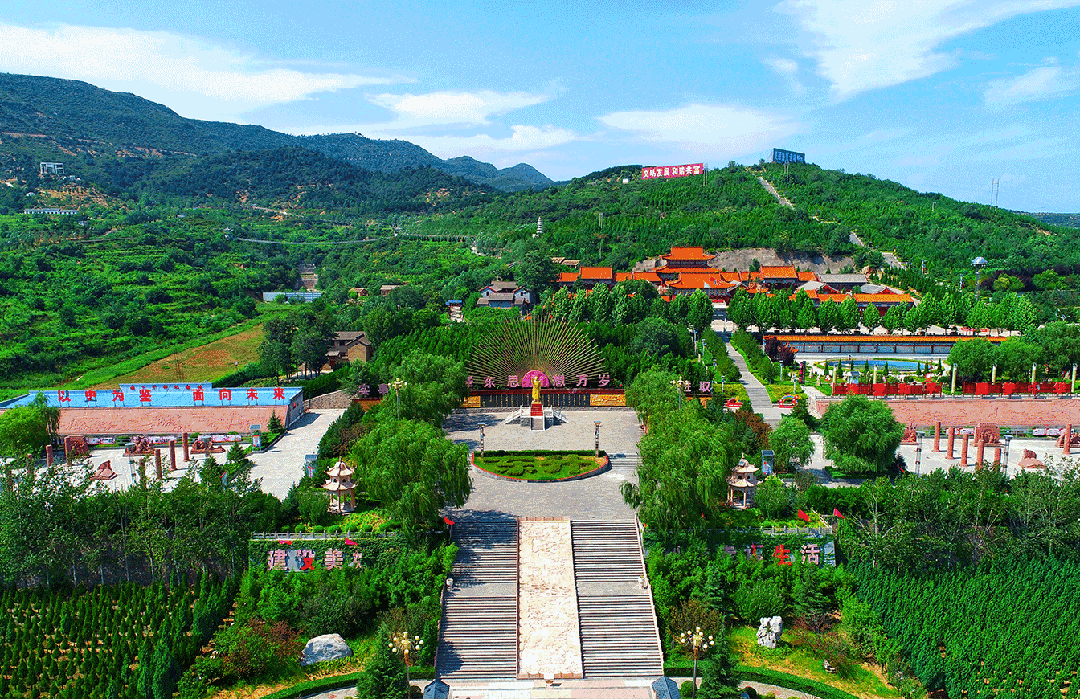
7月21日、22日,我應新華網山西頻道之邀到這裏調研。上海正是酷暑,而在羣山環抱、翠綠掩映的振興村,最高温度為攝氏27度左右,最低温度為20度,真是個避暑的好去處。
走進別墅住宅區的一户村民小院,兩層別墅,建築面積300多平方米,已經住了十幾年,但感覺還挺新。屋內外井井有條,房子的質量和屋內的環境,一點不亞於發達地區富裕農民建房的水平。院子靠牆的幾處圍欄裏,種着茄子、西紅柿、香菜等。
在和村民的交流中,我得知振興村多年前就有了五大保障機制。
一是就業均等。村裏的青壯年勞動力全部就業,因病、因殘不能就業的納入社保;
二是醫療保障。在國家的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外,村裏推出了就醫補助項目“福村寶”,村民及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外來工每年出資100元即可參保,享受大病補助,“兩塊加在一起,住院做手術,自己出的錢只有一點點”;
三是教育免費。凡在振興學校就讀的學生免校服費和住宿費,補伙食費(幼兒園每人每天補2元,小學補3元,中學補5元),考上本科的村民子女一次性發放5000元助學金,考上研究生的發放1萬元;
四是養老保障。在國家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外,村裏給60歲以上老人每年發放1200元養老金,70歲以上老人每年發放1500元養老金,並有兩次免費體檢(相當於1500元/人),“五保户”老人入住振興村養老院;
五是社會福利。對村民用水、用電和供暖進行補助,每月免3度電、2噸水,供暖從每年10月底到次年3月底給予補助;每人每年發福利金1500元;村裏還開通了振興村至上黨區、長治市區的免費公交車。逢年過節,免費發放米、面、油等物資。
村裏的道路,都以“仁、義、禮、智、信、賢、德、文、明”等命名,家家户户門上都寫着家訓。我在崇德路一户家庭門上看到,其家訓是“盡孝敬祖,盡忠報國,盡情交友,盡職創業”。
走進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圖書室裏有近萬冊圖書,有健身室、舞蹈室、科技室,孩子們有的在堆積木,有的在玩飛機航模。一位志願者介紹説,村裏有200多名志願者,有4支固定志願服務隊和兩支流動服務隊,涉及維修、環衞、文藝、導遊、紅色文化宣講等。服務最多的志願者一年服務近200小時。服務有積分,可憑積分領取生活物品作為獎勵。
這位志願者是大學畢業生,因為“村裏環境很好,福利保障也很完善”,就回鄉就業,每月工資為三四千元。
夜幕降臨,我來到1公里長的振興不夜街。大舞台上,請來的演員和村民在K歌。廣場上,婦女們在跳民間舞蹈。街兩邊,一邊是50多家餐飲、文創等商户,臨着廣場的那家正和遊客做“丟繡球招親”的互動遊戲,表演得惟妙惟肖,演完就從二樓往下面撒喜糖;街的另一邊,是各種公共服務、金融服務等網點;街中間,有很多遊戲項目。
振興旅遊公司負責人説,每年正月初一到十六是振興村的“春節嘉年華”,已經辦了8年,每年方圓幾百裏有50多萬人到這裏體驗過年的味道。從春節、元宵燈會、根祖文化旅遊節、端午健步行、避暑文化旅遊節、重陽文化旅遊節等等,“季季有看頭、長年不斷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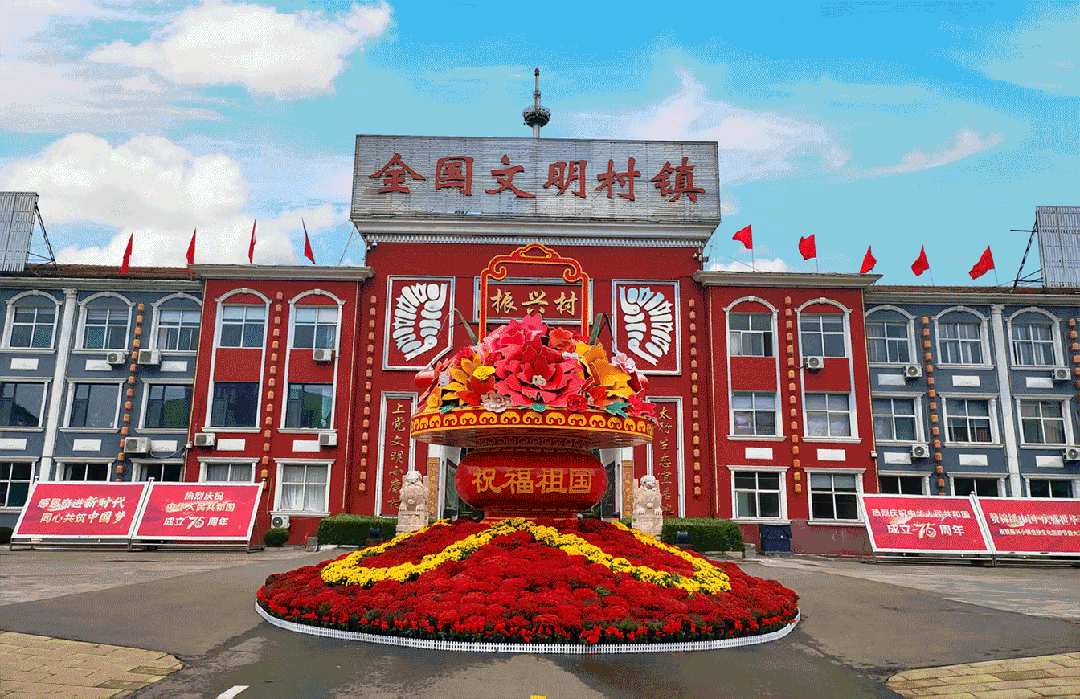
我還去看了民宿、紅色文化廣場、可容納1000人同時培訓住宿就餐的鄉村振興人才學院等。學院已累計培訓500多期,培訓人數達6萬餘人次。
我在振興村的所見,是“就地入城,就地就業,就地入學,就地就醫,就地養老”的就地城鎮化,是宜居、宜業、宜遊、宜學、宜養的和美鄉村。它不再是簡單的“三農”,而是以煤炭產業為基礎,以農文旅商等多業態為載體,融自然風光、民俗展演、休閒康養、農藝體驗、教育培訓等為一體的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示範區。
內地山西有這樣一個地方,讓我大開眼界。

振興之路:一個人和一個村
振興村發展到今天,和一個領路人有關。他叫牛紮根,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出生於1955年,今年70歲。2019年國慶70週年時,他曾作為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代表,被中組部邀請乘坐“從嚴治黨”方陣的彩車,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閲。

沒有牛紮根這頭老黃牛、開荒牛,就沒有振興村的今天。
振興村前身叫關家村,改革開放前是個“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住在山坡坡,啃着糠窩窩”的地方,100多户、五六百名村民住在落差100多米的大雄山半山腰上。村裏的路是河沙灘、土泥路,吃水要到1公里外的山溝裏挑,孩子們上學是幾個年級一起擠在破舊的關帝廟裏。
牛紮根上小學四年級時,關帝廟漏雨,他代表同學找村大隊長,希望修一下。大隊長指着他訓斥:“我們大隊窮,沒錢修。你有本事,就等你長大當幹部時吧!”這句話刻到了他心裏。

1973年牛紮根當上村大隊會計,1979年當生產隊隊長,1984年經海選成為第一屆村委會主任,同年入黨,1985年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
牛紮根當上村幹部後,動員並帶領大家一起修路、打井、建學校,資金不足就東借西湊,男女老少齊上陣,缺技術就三顧茅廬請高手。經過幾年艱苦努力,昔日的河沙灘建成了平坦的砂石路,孩子們從關帝廟搬進了新學校;打機井、鋪水管,在全縣農村第一個用上了自來水。他還發動村民改土造田種莊稼,讓家家户户都養三到五頭生豬和幾十只雞,靠勞動致富。
解決基本生活難題後,就是“讓大家富起來”的新命題。1986年,牛紮根在全體村民大會上説,要通過三個五年計劃,力爭用15年時間,把關家村從山溝溝裏搬出來,把舊村徹底改造成新村。
沒想到,這個願望直到2008年才實現。這有如何統一村民思想的問題,更是受村裏財力不足的制約。
上世紀90年代末,煤炭市場蕭條,銷不出去。2001年,鎮政府決定將位於關家村的鎮辦振興煤礦改制。時任村支書和煤礦書記、礦長的牛紮根意識到關家村的機會來了。
當時全鎮的有錢人都來爭,而關家村沒有什麼集體資產,他就動員村裏羣策羣力,由69名幹部職工湊了516萬元,向鎮政府買下了煤礦經營權,牛紮根出資20萬元,成為第一負責人。
2004年,縣裏對煤礦進行第二次改制,角逐範圍由全鎮擴大至全國。牛紮根再次得到了村民擁護,全村每家每户和礦上的員工都拿錢出來,與他站在一起,4500萬元買斷了經營權,護礦成功。牛紮根佔股40%(後增加到60%),之後,他逐漸將從村民處借來的錢以本金3倍的價格返還,或按村民意願轉為股份。
作為煤礦的實控人,他和當時的其他8位股東商定——現在煤炭形勢正在轉好,應該利用煤礦的收益,重新佈局村莊,讓村民們住上別墅,過上城裏人的生活。
“走出大山搬到平地”的新村建設再次提上議程。以新建的兩層別墅住宅為例,規劃總造價為35萬元,還包含院牆、街門、照壁和簡裝修,村民每户需要支付12萬元(保底價),原來舊房子的估價款可以抵扣一部分,不足部分由村民現金支付。剩餘23萬元和村內所有公共設施和道路建設,均由振興煤業有限公司負責投資。據統計,入住別墅的村民平均每户出資為4.6萬元左右。
2008年10月18日,關家村實現了整體搬遷,最終投資了3.6億元,興建了別墅式住宅136套,標準化村民新居95套,以及一批配套設施。很多村民沒想到有生之年能住進這樣的“小洋樓”——“不見磚、不見梁,做飯不燒煤,解手不出房,住房裝修像賓館,一户兩台大彩電,家裏有了電影院”。他們到鎮裏的集市買酒買菜,請親朋好友來慶賀。

2009年6月18日,經全體村民表決通過,關家村更名為振興村。
從當年事事艱辛的關家村到如今萬象更新的振興村,振興煤礦發揮了重要作用。2007年,在煤礦基礎上,成立了振興集團,牛紮根任集團黨委書記。
為充分發揮振興集團對新農村建設的帶動作用,長治縣(2019年改為上黨區)將原振興村、郜則掌村、向陽村3個村黨支部從西火鎮黨委中剝離,併入振興集團黨委,實現企業與村黨組織領導的合併,“三村並一村”,形成一箇中心村,即新的振興村。振興集團為三村村民一共蓋了521套新房子,加上48套人才公寓,總計569套。
2010年7月,長治縣城鄉統籌振興試驗區成立,簡稱“振興新區”。它是長治以“中心村”示範區模式推動城鄉一體化、建立新型城鎮化農村社區的一次試驗。牛紮根任振興新區黨委書記。
振興新區成立後,組建了專業合作社,共流轉振興村和西火鎮西村的土地6331畝,村民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流轉後,不適合種植的2000畝荒地退耕還林,剩餘土地按照農業觀光、農事體驗、蔬果採摘、農藝博覽等功能分區進行建設。振興現代農業公司則以“公司+農户+農莊”的模式,對流轉土地統一規劃、分片承包、自主經營,讓農民變成現代農業的產業工人。
以上是振興村的基本脈絡,其模式就是以企帶村,以工帶農,走共同富裕道路。
這裏的關鍵人物是牛紮根。2020年7月,他在振興村支部擴大會議上宣佈,將山西上黨振興集團60%的股份歸振興村集體所有,40%作為村民的股份和福利基金。以學校為例,除十多名老師是領取國家工資外,其他幾十名民辦聘用制性質老師的工資,除國家給予的補貼外都由振興集團補齊。
歷年來,振興集團累計投資13.5億元,先後完成文旅轉型和民生實事百萬元以上項目115個。在牛紮根看來,煤炭是“現在離不開,將來靠不住”,所以振興村向綠色經濟、文旅經濟轉型是必然選擇。


真的不容易
22日清晨,我坐擺渡車去吃早餐的路上,看到牛紮根一個人在路上走着。他住的房子和村民的別墅完全一樣。
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從一個關家村到和向陽村、郜則掌村“三村並一村”,合併為新的振興村;再到“一村帶兩村”(新振興村再帶動周圍另外兩個村的發展),從黑(煤炭)到綠……他有太多創造的快樂,同時,無數壓力最終也都在這個想做事、能做事、為人做事的人的肩上。
他染上了失眠的毛病,身體的零部件也有不少問題,人非常清瘦,戴一副眼鏡,像一位長期伏案工作卻營養不良的老教授。
想當年,如果不是他站出來贏得煤礦的控制權,在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大致在2002年至2012年),振興煤礦照樣會賺錢,但就像山西很多煤礦一樣,老闆自己賺了大把錢,盡情享受,最終留下的是礦山掏空、環境污染、山體塌陷的爛攤子,對所在區域的集體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並無太大關係。
我感嘆,振興村幸好有牛紮根這個主心骨,他集能人、仁者和具有奉獻精神的共產黨基層幹部三重角色於一身。
牛紮根善經營,熱心為大家辦事,村民們信任他,支持他。無論是最初建學校還是後來守護煤礦,村民都慷慨解囊。但也有一些事情,村民一開始並不認可。比如關家村的遷建,從1986年第一次提出搬村計劃,到2006年10月組織全體村民開動員會獲得認可,前後整整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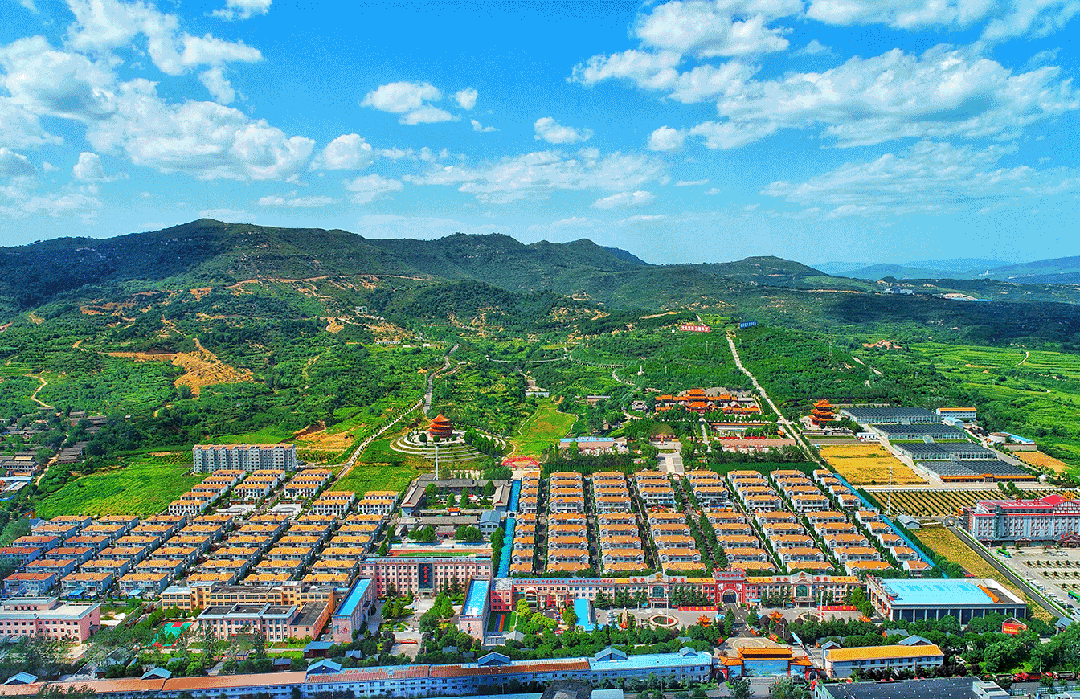
2006年遷村開始啓動後,最難做的是397個墳頭和19座廟都要遷走,僅牛紮根的家族就有53個墳頭。雖然做了大量工作,還是有少數村民説不通,有人説:“我家這個墳的風水好,如果遷墳後出現了問題怎麼辦?”牛紮根與村“兩委”幹部反覆商量後,採取了一個辦法:由村民推舉5位羣眾代表,村幹部不參與,村民代表聘請3位風水先生勘察地形,他們後來在村莊西北角挑選了一塊都比較滿意的地方,作為安置地。村集體安排人把墳坑挖好,誰家遷走一個墳,補助3000元。
最大的阻力還不是村民,而是牛紮根的本家兄弟。和牛紮根同一祖爺的有6個本家,4家同意遷,2家不同意。一位本家兄弟認為,牛紮根作為村裏和企業的帶頭人,不想着兄弟利益,把好處都給了別人。這位兄弟有個出嫁女兒,離婚回村後也想要一套房,但一分錢都不想出。
為維護一視同仁的規則,牛紮根和村幹部多次給他做工作,都不行。最後經村委會研究,上報上級政府,通過政府支持才説通了他。
為什麼本家兄弟最不理解自己?牛紮根説:“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不能否認人們對錢財的熱衷。還有就是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很濃厚的家族意識和宗族思想,在家庭和家族裏,集權力於一身的男性家長容易濫用權力來獲得更大利益,滋生特權和裙帶思想。以前的宗族間需要抱團發展,所以本家兄弟存在這種思想是有歷史根源的。但我們在分配上人人平等的村規民約不能打破,我想隨着時間推移,他們的思想觀和價值觀總會轉變。”


振興村需要更多支持
在和牛紮根的交流中,我被他一輩子獻身“三農”建設的精神深深感染。同時,我也能感受到一個70歲老人仍在奔波操心的不易。
最近這一兩年,煤價低迷,今年上半年振興煤礦的景氣遠不如以前。他要花大量時間在礦上,進行精細化管理,降本增效。雖然幾十年的行業起伏讓他相信,低谷之後就是上升,但如果徘徊時間太長,就是很大壓力。
文旅產業雖然不錯,但目前主要還是在春節、五一、國慶等節假日比較火爆,如何形成常態化效應,也是挑戰。
振興村的鄉村幹部培訓,去年服務了2萬多人次。今年由於不少地方對中央《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到風景名勝區開會的通知》的片面理解,把通知中列明的21個風景名勝區泛化到所有景區,而振興村剛好在2018年被評為4A級景區,導致培訓業務受到嚴重影響。其實,振興村這樣的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樣本,和自然風景區的內涵完全不同。
“幾十年的經歷告訴我,這些都會過去的,我相信黨和政府,地方政府也在幫我們一起想辦法。”牛紮根平靜地説。
而我則想到,我們的鄉村振興可能正處在一個很關鍵的時刻。我們需要更好地提振內需,激發活力,併為鄉村振興導入活水。
“擔任村書記不會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村書記。”牛紮根有這個覺悟,一輩子也是這麼走過來的。但當他為更多人的共同富裕默默承受壓力之時,我們也理應為他做點什麼。

最後我想説的是,鄉村振興也需要在體制機制上有更多創新。
純粹從個人立場,我對“以企帶村”有一定保留看法。把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責任都讓企業來擔,在產業上升週期是可行的,但是不是長期可行,我存疑。我認為即使像牛紮根這樣具備企業家精神和高度責任感的人,也不可能保證。
而對於適當擴大行政村規模、小村併入大村、通過中心村帶動周邊發展的探索,我則高度認同。經濟學上有所謂“市場規模決定分工效率”的道理,如果行政村規模太小,實際上支撐不起優良的公共品供給。像振興新區這樣的模式,實際是在建設一個新型農村社區,有一定規模,功能齊全,設施完備,村民不出村就可享受到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行政服務。
這種體制還避免了管與幹兩張皮的問題。新區既是制定規劃的管理機構,又是謀劃經濟發展、促進村莊建設、統籌各類服務的辦事機構。在這種模式下,一個好班子也能發揮更大作用,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望着牛紮根有些孤獨的身影,我想到他過去對媒體説過的話:“我這幾十年風雨兼程、摸爬滾打,始終沒有離開過家鄉,離開過羣眾。因為,在最艱難的時候,是羣眾支持了我,是黨肯定了我。政府給我一碗水,我還政府一桶油。我寧可累死,也不退坡。只要還幹一天,就盡全力讓羣眾滿意。”
痛並快樂着。這就是牛紮根在“三農”振興中無悔無怨的人生。
—— · END · ——
No.6465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