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蕭山的印象只有機場,那你還沒有抵達過美食荒漠的綠洲_風聞
食味艺文志-食味艺文志官方账号-人间至味,莫过碳水。公众号foodoor22分钟前

2018年,高曉松在杭州開設了公益閲讀機構“曉書館”。
落成儀式上,高不吝對杭州的讚美。他説:“我的母親是杭州人,從小家裏吃飯,習慣了梅乾菜捂肉、燴三鮮、肉餅蒸鯗、江米魚這些本地家常菜。”
實際上,高曉松的“杭州血統”來自他的外婆、著名物理學家陸士嘉,她是蕭山望族旱橋頭陸氏的千金小姐。雖然今天的蕭山已經是杭州行政上的一個區,杭州最大的機場所在地,但從人文的角度解構,蕭山卻有着與“美食荒漠”完全不同的歷史傳承。
高曉鬆口中那些“杭州家常菜”,則與臭名昭著的西湖醋魚、龍井蝦仁沒啥關係,它們代表的,是風情曼妙的蕭山餐桌,和水袖長衫的蕭紹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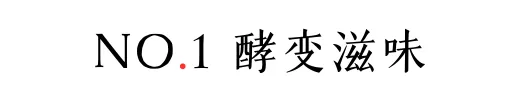
和很多江浙地區的城市一樣,蕭山,有一個晦澀難懂、無法用漢語釋讀的故地名——餘暨縣。
和餘姚、餘杭一樣,這個以“餘”作為詞根的地名,描繪的是上古時代的這片土地的地理地貌:餘暨,百越語意為“鹽鄉”。
從宏觀地理來看,蕭山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是杭嘉湖平原的南端,寧紹平原的起點;背靠連綿起伏的浙西丘陵,面朝開闊的杭州灣——山海相遇之地。
《漢書·地理志》記載,餘暨縣始建於漢初,是當時江南地區重要的鹽產地。海潮退卻,灘塗裸露,鹽霜白茫,風起時,如綾似雪,鋪天蓋地。

鹽,不僅提供鹹味,還為是發酵過程中最重要的抑菌劑,它是蕭山風味的元點和底色。
以臭豆腐、臭菜梗、臭千張、梅乾菜為代表的臭味,就是此中代表。它們的材料大豆、芥菜梗,都是農耕時代重要的植物蛋白來源。但也有同樣的,不易保存的缺點。作為抑菌劑的鹽在此時粉墨登場,在豆腐、菜梗、千張發酵黴變的同時,阻止有害菌滋生。
代表鮮味的氨基酸也在這一過程中誕生出來。

夏天,蕭山人用梅乾菜煮出淡紅色的清亮的湯,以之汆當季的小河蝦,鮮上加鮮;秋天,蕭山人以臭千張蒸肉餅,肉汁的濃香稀釋了千張的臭味,而千張的鮮則為多汁的肉餅妝點得分外妖嬈;冬天,蕭山人以臭菜梗和鹹肉、老豆腐燴出濃郁的湯煲,汁水鹹鮮,是濕冷天氣裏的暖身下飯神器;春天,蕭山人以油炸後的臭豆腐搭配新剪的韭菜,一清新一濃郁,彰顯了一體兩面的江浙精神。

鹹肉,則是蕭山味道中的核心底色。
《越絕書》裏記載了越王勾踐命士兵以海鹽醃製肉乾,在蕭山囤積以備長途征戰。傳説雖然不足信,但歷史照進今天的習慣,卻能從蕭山人的日常飲食中得以解構。
對蕭山人來説,鹹肉是一種被歲月醃過的鄉愁。它不喧譁,也不炫技,只以一身雪白油脂和赤紅瘦肉,卧於竹篾編成的風櫃裏,任風霜將它雕刻成時間的美味。春天的時候,取一塊刀口温潤的鹹肉,切作薄如蟬翼的片,隨青蒜、春筍同入砂鍋,文火慢煨。其油脂在熱氣中漸漸融化,宛若雪融春水,滲入每一寸筍節的纖維,使清鮮之中多了一抹柔腴的厚重。

或者更簡樸些,只以嫩豆腐為伴,鍋中不放一滴生油,讓鹹肉本身去演繹香氣的層次。其鹹不奪味,其香如遠山暮色,不濃不烈,卻裹挾着過年燉菜的温存和母親手勢的安詳。
鹹肉在蕭山菜裏從不是主角,它像一個深知分寸的老者,把風味交給應時的蔬果,只在餘韻中低聲提醒你——人間至味,不過一方柴米油鹽的靜好。
最妙的,莫過於鹹肉燒芥菜。芥菜須選頭茬霜後者,翠綠中透着一點苦骨。清水煮過,再入鍋中與鹹肉同煨。那鹹肉的油脂緩緩滲透,苦澀的菜葉便柔順起來,滋味也由清冽轉為沉靜,彷彿一個人的性情,在歲月中漸漸沉穩。這一鍋菜,初嘗微澀,再嘗是甘,回味竟帶點蜜意,是舊時光教人懂得的滋味。

在蕭山人的餐桌上,鹹肉從不張揚,卻也從不缺席。它不是風味的高音,而是那低沉持久的和絃。哪怕一碟清炒青菜,只需片片鹹肉相佐,便覺菜有了魂、飯有了香,日子,也因此有了細水長流的意義。鹹肉之於蕭山菜,如同一位知己,不必日日相見,卻總在寒來暑往中,穩穩立於心頭最温柔的處所。
從某種角度説,黴爛醃臭貫穿了蕭山滋味的四季,而它的底色,則是由鹹肉所代表的,來自發酵的迷人的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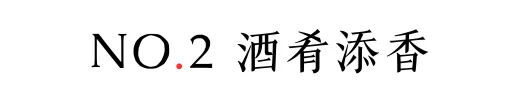
同樣源自發酵的黃酒,也是蕭山味道的另一個靈魂。
相傳東晉大將桓温平定淮南後,曾在餘暨縣大宴將士,舉杯黃酒,暢飲而歌,留下了“江南酒香,英雄意氣”的美談。《南齊書》中記載,當時的江南士族常以黃酒相賀,甚至在宗廟祭祀時也用黃酒代替美酒,以示謙遜。
與紹興同屬稻米產區,同為黃酒聖地鑑湖的流域,蕭山一直以來就有釀造黃酒的傳統。除了文人士大夫、師爺階層熱愛飲用黃酒之外,它還是重要的烹飪輔料與調味料——黃酒的黃色,來自經由糯米和麥曲中的蛋白質和澱粉化學反應得來的棕化物質,它所呈現的核心風味,也叫做“鮮”。
所以,以黃酒作為調味的底層邏輯,是蕭山美食的不傳之奧。

梅乾菜燒肉裏的黃酒,是融合甜鹹、山水密織的長卷;鹽水蝦裏的黃酒,是水秀長衫、隔簾顧盼的摺扇;清蒸魚裏的黃酒,則是去腥增香、淡妝素服的脂粉。
糟菜,則更體現了蕭山人對食物的理解和利用。
糟是黃酒釀造中,榨酒後剩餘的渣滓。過去,平民階層用它作為蒸餾原料,獲得濃烈上口的糟燒白酒;而文人士大夫們則在加入一定量的黃酒、香料後,配置成酒香濃郁的糟滷,這是蕭山糟菜的風味靈魂,加入豬手、毛豆、五花肉、豬肚等等口感脆嫩、滋味豐腴的食材浸漬,能呈現出温柔雋永的風情。
一派江南書生的氣質。

東晉六朝的江南大開發,為蕭山的味蕾世界注入了更多清新柔婉的元素。太康元年(280年)以後,隨着中原士族大規模南遷,江南成為文化交匯之地。山川氤氲,水澤渺茫,百花齊放,百鳥爭鳴。隨着吳越文化的融合,蕭山飲食逐漸呈現出清鮮本味的特點。正如《山海經》所云:“其風也,清而柔;其味也,淡而長。”
這份清淡,不是貧瘠中的簡陋,而是富足後的剋制。蕭山的清蒸魚、白斬雞、蕭三鮮,講究的便是這一份清純本味。清蒸魚,不多加佐料,黃酒去腥,保留魚肉的原始甘美;白斬雞,黃酒焯水、滾水一燙,冷卻切塊,只以葱油相佐,入口爽滑;蕭三鮮,則是將河蝦、草魚片、筍片一同清炒,鍋邊黃酒激發滋味,淡淡的鹹味與食材本身的鮮香交織,彷彿一首三重奏,簡約而不失層次。

吳越國時期,這些樸實卻風雅的食物,不僅是百姓日常的口腹之慾,更是文人墨客詩詞中的靈感之源。錢鏐(852-932年)建立吳越國後,曾在錢塘江畔設宴,親嘗清蒸魚和白斬雞,並稱贊其“清而不寡,淡而有味”,此後,這些菜餚便成為吳越宮廷中的常客。
同樣,這些清淡之味,也常常需要黃酒作為殺腥、增香、提味的利器——它是原汁原味的鋪墊,也是清新雅正的和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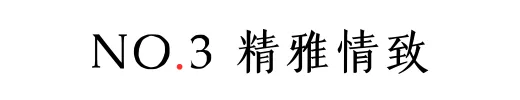
1127年,宋室南渡,臨安(今杭州)成為新都,江南地區的飲食格局再次發生鉅變。北方士人攜帶着麪食技藝和醃製手法,沿運河南下,帶來了更加豐富的味覺層次。這一變遷,也影響了蕭山的飲食結構。
在蕭山的街頭巷尾,漸漸出現了麪條的身影。手擀麪、刀削麪、餛飩麪,乃至後來的陽春麪,皆成為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北方面食的筋道與南方食材的清香交織,成為一種全新的滋味。蕭山人的麪條,大多搭配清淡的湯底或簡單的醬油拌料,強調的是麪粉本身的韌性與麥香。這種簡潔而純粹的味道,與當地的清蒸魚、白斬雞相得益彰,形成了獨特的蕭山味譜。

元末錢塘江改道,浙東運河逐漸淤塞,蕭山從商旅樞紐退守為農耕腹地。這場地理變故,卻讓飲食文化在封閉中淬鍊出別樣光華。明代《蕭山縣誌》記載,百姓宴客必呈"十碗頭":土燒酒配八葷二素,油豆腐嵌肉需用豬前腿七分瘦三分肥,紅燒大腸須保留三分脂膏,醬油河蝦定要帶籽抱卵。這些看似粗獷的鄉土菜,實則是困頓歲月裏的生存智慧——將廉價食材經數十道工序點化成宴席主角。
再比如,五花肉先以黃酒糟醃製三日,蒸透後浸入梅滷,再經竹匾晾曬,九蒸九曬後方成"梅香肉"。油亮如琥珀的肉片鹹香中暗藏梅子清酸,曾是清光緒年間蕭山商人走南闖北的"活體銀票",在異鄉切兩片佐酒,便是家鄉滋味。而南門江畔的"醬園詩社",每逢立秋開缸取醬,文人們以醬香濃淡為題鬥詩,留下"黑雲壓城醬香烈,玉箸點破琥珀光"的奇句,將庖廚之事昇華為風雅。
蕭山人對風土的執着近乎偏執。浦陽江畔的紫皮茄子必種在鹽鹼灘塗邊緣,果實才能兼具綿軟與筋道;製作黴菜梗必用沙地莧菜,因其莖稈中空利於黴菌穿透發酵。道光舉人王端履在《重論文齋筆錄》中詳述"黴千張"製法:“黃豆磨漿如絹帛,層層疊疊藏幽香,三伏天裏看雲捲雲舒,待其生出金絲方成。“這種需要觀察黴菌生長節奏的食物,被士大夫視為"格物致知"的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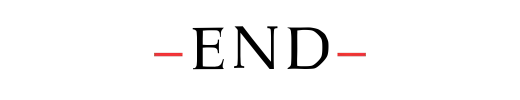
1909年,一位名叫蔡東藩的蕭山讀書人,考上了科舉,去福建擔任知府,但僅僅幾個月之後,他就棄官回家。
原因很“天真”——蔡東藩不喜歡官場,寧願回家寫書賺錢。
正是因為這一因由,中國第一套通史小説《《歷朝通俗演義》誕生:這是蕭山百姓不強求功名利祿性格的生動體現、也蕭山士子富庶精神宇宙的婉轉表達。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00多年後,蕭山第一家米其林摘星飯店,被陳曉卿評價“好吃到耳鳴”的傳奇餐館“南豐飯店”,就誕生在蔡東藩出生地不遠。


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千百年來,江南水鄉的煙波碧影在這裏聚攏。淤積的泥沙,沉澱的鹽鹼,裹挾着古老的故事,也浸潤着一方百姓的味蕾。從春秋戰國的越地遺民,到吳越一統的江南望族,再到宋室南渡的避難士人,蕭山的滋味,像一卷密織的山水長卷,層層鋪展,至今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