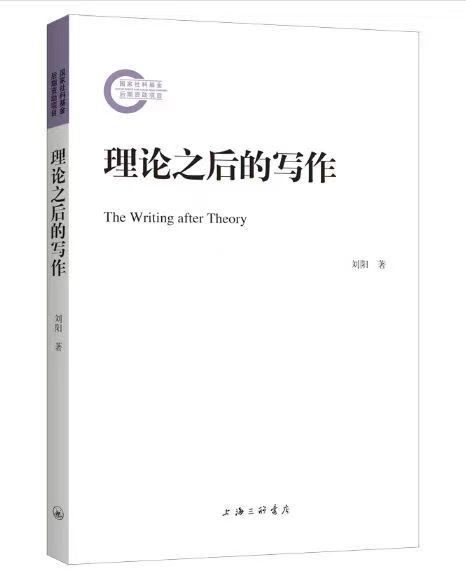金新:文體豈能有等級?_風聞
虎落平阳-25分钟前
文體豈能有等級?
金 新

華師大長江學者劉陽編寫的大學文科教材裏收錄了很多雜文案例,有鄢烈山的,有吳非的,有趙健雄的……老夫也有幸被選中多篇進行學理性分析。出過雜文集《推敲人文》的劉教授深知雜文在辯證思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想到一件有關雜文的往事。

《南京日報》曾有消息:《鐘山》雜誌社發起了新生代作家小説創作學術研討會,與會的南京新生代作家吳晨駿公開宣稱,“我的小説代表當前最高水平”,“魯迅的小説絕對比不上郁達夫,他的雜文誰都可以寫”。

不論吳先生其人的小説是否代表了當今最高水平,名不見經傳,沒有拜讀,遑論是非;亦不評迅翁與達夫先生之小説孰優孰劣,此文壇自有公論,不必贅言。欲渾點迷津的倒是有關文體的等級問題。聽話聽音,鑼鼓聽聲,從吳先生所説的“雜文誰都可以寫”來看,似為一種寄人籬下的劣等文體,順手牽羊,乃下里巴人之技耳,哪裏像小説,陽春白雪之道也。
查一查《中國文學史》,平心而言,吳先生的話確有一定的道理,文體自古有等級,只不過顯而易見者恰恰是其溺愛之小説罷了。“小説”一詞始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説以幹縣令,其於大達儀遠矣。“指的是一些卑瑣無價值的言談,還不成文體。嗣後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説者之所造也。”這才有了文體的概念,儘管不登大雅直堂。其魏晉南北朝時期發跡,有了志怪小説於軼事小説,而唐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吳先生鄙薄的、小説上不了台階的魯迅先生對小説倒頗有研究,著有《中國小説史略》,認為:“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神記逸,然敍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説。”對於小説,歷代正統文人往往不屑一顧,漢人班固縱然摒之於九流之外,唐人也“每訾其下”,就像吳先生堂而皇之唾棄雜文一般。可當時參加名為傳奇的小説創作的人,卻有不少名家。李肇説:“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這説明,吳先生引以為豪的文體,直到唐代才日臻改變人們的傳統思維定勢,正式形成了規模與特點,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走向社會。適得其反的是,被吳先生搶白的雜文,則“春風得意馬蹄疾”,先秦歷史散文與哲學散文裏獨佔鰲頭,經久不衰,與詩於某種意義上秋色平分,各各江山半壁風騷領。
每一種文體的發展,離不開其他文體的影響。唐傳奇之所以能攜小説步入文學殿堂,蓋因受詩和散文等的薰陶,形成了以詩歌與散文結秦晉之好、抒情與敍事綴同心並蒂的獨特風格。看一看白居易的《長恨歌》、陳鴻的《長恨歌傳》,元稹的《鶯鶯傳》與《李娃行傳》之類,便見一斑。在小説早已走出古之困境,眼下再造現代輝煌之際,吳先生石破驚天之高論未免讓人想起《山貓與老虎》的故事,置小説於不仁不義之地哉!
其實,文體的等級是由演變過程而造就的暫時性距離,一旦形成,豈有優劣之分?關鍵是看掌握在何人手裏,優則優,劣則劣,楚河漢界生焉。試將劉禹錫之百字雜文《陋室銘》較之吳先生之洋洋萬言小説,公論向誰?愚大膽妄想,除卻字數懸殊,佔絕對優勢外,其小説不要説千年之後,恐數載面世也即不復存在!
孔子之斷語“不知詩無以言”,有誇大詩之嫌,唯因其為聖人;吳先生之斷語,也有誇大小説之疑,則何許人也?記得當時嘗擬《詩經·小雅·巧言》句羞辱這廝:“巧言如‘狂’,言之厚也。”儘管迅翁有語:“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

據有關資料顯示, 吳晨駿1989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動力系,一個理工男能著有小説集《明朝書生》(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我的妹妹》(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柔軟的心》(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詩集《棉花小球》(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長篇小説《筋疲力盡》(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版),平心而論,比北大中文系才子陸步軒賣肉的“改行”強多了,但吳氏的“自大”的近乎狂妄的舉動除了證明中國語文界的恥辱,其實並不能證明其他什麼!
吳先生因1999年海天出版社的《《明朝書生》紅火了一陣,沒幾年好像就“泯然眾人也”,2004年之後好像就動靜不大亦或沒了。他1966年出生,而今亦奔六也,不復“新生代”,隨着年齡的增長,不知狂妄氣焰是否消退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