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當代安頓之道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10分钟前


處處是他的河
據澎湃新聞8月4日消息,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美國去世,享年95歲。6月23日,他還在直播,讀者羣裏有人傳着他的話,“大家互相擔起彼此的包袱……大家可以一起流淚”,紛紛稱老先生慈悲。
雖然95歲,很高壽了,但聽到消息,還是覺得突然。他在生命的最後日子,還在傳道,讓人覺得,生命應該直取核心,不浪費任何一點,任何時候都是寶貴的。他的往生日跟去年走的李政道還是同一天,網絡上很不平靜。
筆者的日記裏也躺着好多關於他的筆記,他的書曾是我的牀頭書。2022年6月9日的日記説,“昨天睡不着的時候,一直在看《許倬雲十日談》,看到兩點終於有了睏意。學者的視野真是寬啊。特別是他談到,蒙古時代的大瘟疫,從十五世紀延續到十六世紀,充滿了黑死病、瘧疾、天花、傷寒……都沒有斷過。一直到明朝初年,黑死病的影響都沒有消除。黑死病,其實就是沙漠裏的老鼠攜帶病菌傳播到商隊人員身上,然後一路傳染。明末的瘟疫也是從歐洲傳過來的黑死病,沿海地區黑死病鬧得很兇,沒有辦法控制,方法只有燒感染的屍體,所以還有內亂,而滿族人沒有病,故而能長驅直入腹地。感慨啊!居然還有這一層因素”。
許倬雲獨特的大歷史觀,讓他總能發現獨特的觀察點。他擅長從主流敍事之外的邊緣地帶切入,發現那些被忽略的社會力量與文化基因。
他始終強調文明是一個動態系統,內部有自我調節、自我修復的機制,所以他永存希望;他的觀察往往打破學科邊界,體現為強烈的交叉學科能力。這種觀察,不是為觀點而觀點,而是一種悲憫、通透與結構性覺察力交織的文化使命感。
在王小波的《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中,也能找到他的影子,“在匹茲堡大學的老師許倬雲教授曾説,中國人先把科學當做洪水猛獸,後把它當做呼風喚雨的巫術,直到現在,多數學習科學的人還把它看成宗教來頂禮膜拜,而他自己終於體會到,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但是,這種體會過於深奧,對大多數中國人不適用。”
1982年,李銀河和王小波作為國家公派訪問學者赴美,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和哲學系訪學,此時,許倬雲已是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據説王小波經常在課後與許倬雲辯論自由、歷史的意義、人的命運等問題。許倬雲曾説他“像一團火”。王小波對“人是為了自由和思維而生”的理念,可能部分受到了許倬雲強調“個體文明成長”理念的影響。嗯,一團火遇到一條河。萬古江河就是不停留,永遠在流轉。
而對李銀河,許倬雲公開評價過,“她敏感而理性,是罕見的能打通西方學術與中國現實的女學者”。

|許倬雲當時為台大歷史系主任(攝於1965年)
網上有讀書大V説了些胡適對許倬雲能夠留學巨大幫助的段子,其實這些可能沒有考證過。但確實,他説過年輕時就讀胡適,佩服他敢於在時代潮流中説出真話。他説過,當下需要胡適。兩人在精神層面是具有傳承性的——“文化要關照民眾”“歷史要服務當下”,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啊!
對於影響他思維的師長,筆者認為,他是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芝加哥學派的“文明互動”和“社會科學方法”,尤其是威廉·麥克尼爾等人讓他學會以“文化結構”解釋歷史,以“非中心視角”觀察中國,這些可能才是他學術底層邏輯的重要建構部分。
許倬雲在年輕人心目中,好像是疫情後火起來的,其實他火了一輩子,這些火種都在影響力同樣很大的作家、學者、思想家的心裏面。翻開好多書,不是他的書,卻處處是他的河,他的雲。
我特別喜歡的現代哲學家陳嘉映的書《何為良好生活:行之於途而應於心》裏,也看到他的痕跡:“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荀子曰:‘知之不若行之。’許倬雲總括説:‘由孔子以下,所討論知識者均着重力行,即身體力行。’”
為什麼他能引起年輕人關注,可能是他用另一種方式在講國學,講人生。我們中國文化其實就是安頓心的文化。他認為,中國古代思想不像西方那樣偏重邏輯系統或哲學觀念的抽象,而是重視道德修為、實踐經驗、社會參與。這讓他主張“國學不只是書齋之學”,而是“生存之學”“為人之學”“社會行動之學”。
所以,他在《萬古江河》《説中國》等著作中系統梳理了:中華文化的生成邏輯(農業社會、宗法家族結構);儒道互補的制度張力;“文化型社會”的動態平衡。
他認為“國學”的未來,不在故紙堆中,而在新一代人的心力與行動之中。“往裏走”是他的法寶,那是情和理交融匯合,埋在身體裏面,變成性格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能夠生出很多新視角,新維度,去解讀學問,經典,以及看似很多平常的東西。
他説,“我不是一個聰明人,也不是一個濫情的人,但是因為長期堅持這種訓練,我能發覺更深層次的東西,甚至發現原作者或許都沒想到的地方”。
當這位史學巨擘的生命軌跡終與他畢生鑽研的時空長河相融,那些散落在58種中文專著、212個版本的其他著作中的思想星火,仍在文明原野上閃爍。
其中最明亮的一束,是他反覆提及的“每個人都有抓不到的雲”,而云影之下,藏着他留給世人最珍貴的精神遺產——“往裏走,安頓自己”。在波瀾壯闊又細膩入微的學術生涯裏,他對歷史與人類文明的深刻洞見,更如亙古星辰,指引着我們在時代浪潮中找尋方向。

殘疾的觀雲者:安頓的智慧
先天性肌肉萎縮讓許倬雲的手腳永遠保持着彎曲的弧度,卻也讓他早早學會了與自身侷限共處的哲學。
抗戰時被擺在石磨上看難民潮的孩童,無法奔跑嬉戲,只能靜靜觀察挑夫的喘息、農婦的勞作、士兵的決絕——這種被迫的“靜止”,反而成了他“往裏走”的起點。
他曾説,因為一輩子不能動,不能和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這跟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的關係,因為歷史學家可能也是旁觀者。

這種旁觀不是疏離,而是向內沉澱的契機。當別的孩子用雙腳丈量大地時,他用心靈丈量人性的深度。在重慶南山躲避轟炸的夜晚,他躺在山坡上聽松濤與炮聲交織,忽然懂得“恐懼之上還有對生命的敬畏”;
在芝加哥大學,他走上街頭參加民權運動時,他看着黑人與白人並肩抗議,悟到“平等不在街頭的喧囂裏,而在每個人心底的標尺上”。
身體的禁錮反而打開了精神的自由,這正是“往裏走”最生動的註腳:當外部世界無法掌控時,轉向內心的探索,反而能找到更堅實的立足點。
許倬雲深知,“人生是為感情而生的,也揹着感情而去”,那些在困境中收穫的陌生人的善意,如同點點燭光,照亮了他內心的角落,也讓他明白,在苦難中尋得的温暖與力量,是安頓自我的基石。
他曾講,歷史的知識,即是治療集體健忘症的藥方,在自身經歷的苦難與成長裏,他也正用對歷史的深刻理解,治癒着時代的迷茫與遺忘,為自我與他人的心靈尋得棲息之所。
在對人類文明的思考中,他意識到不同文明間那些共通的人性光輝,恰是跨越種族與時空隔閡的橋樑,能讓每一個在時代洪流中漂泊的靈魂找到歸依。

| 許倬雲在芝加哥大學

歷史的織雲人:安頓的密碼
許倬雲的史學研究從來不是冰冷的考據,而是為現代人尋找安頓座標的旅程。
他秉持着“歷史不只是外在知識的整合,歷史是大羣知識叢之中最貼近人的部分”的理念,在《萬古江河》裏計算漢代糧倉容積與人口增長率的關係,不是為了復原數字,而是想告訴讀者:“兩千年前的農夫也會為收成焦慮,我們的煩惱從未真正新鮮過”;
他在《西周史》裏跳過周公的政績,專注於井田制下農夫的勞動節奏,是想揭示:“文明的根基不在朝堂,而在每個普通人如何安頓日常的柴米油鹽”。
他治史着重於社會史與文化史,關注一般人的生活與想法,在英雄與時勢之間,偏向觀察時勢的演變與推移,因為他明白歷史的根不在帝王將相,而在斗升小民。
這種“從歷史找安頓”的智慧,在《往裏走,安頓自己》中達到極致——
他用商周占卜龜甲的裂紋解讀現代焦慮:“古人灼燒龜甲問吉凶,今人刷手機看運勢,本質都是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
以明代家訓中“鄰里糾紛”的處理方式對照當代社交困境:“五百年前的人就懂得‘讓三尺巷’,今天的我們卻在網絡上爭得面紅耳赤”;
甚至將考古地層學轉化為情緒梳理指南:“洛陽城地下疊壓着十三朝遺址,就像我們心裏堆着祖輩未化解的嘆息,清理不是否定,而是理解”。
他教會我們:歷史不是故紙堆裏的往事,而是安頓當下的鏡子。
當我們為“內卷”焦慮時,看看漢代農民如何在精耕細作中找到生存智慧;
當我們因“社交隔離”迷茫時,想想蘇軾在黃州“竹杖芒鞋輕勝馬”的豁達——往歷史深處走,也是往內心深處走。
正如他所言,“天下沒有一個東西不是你的功課”,從古老文明中汲取養分,能讓我們更好地應對生活的考題,實現內心的安頓。
他認為歷史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因果的交織和演變的邏輯,這也啓示我們在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時,需以包容、辯證的眼光去看待,不片面評判,而是汲取其中推動自我成長與社會進步的力量。
許倬雲一生反對線性、進步主義的歷史觀,強調“多元”“共生”,強調歷史的“多元起點”與“長時段演變”,使得中華文明不再只是中央王朝的更迭,而成為草根羣體的生存技術、信仰實踐與文化適應的過程。
他關注草根邊陲,以觀察邊緣反觀中心,就是他的“反者道之動”,他關注文明的流動,所以才能返身自省。
説歷史,就是説人如何走過命運!
許倬雲這一代人,是“留下來,為你們説話”的最後一代儒者,他真的説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不怕世界亂,而怕你心中沒了秩序”;當我們已經快放棄人文科學的時候,他説過,“人文學不是為了考據,而是為了讓人更像人”。
疫情後,社交網絡上他很火,充滿了B站,紀錄片等等。因為時代的不安感呼喚長時段的慰藉,需要這樣一個精神人物壓得住場。這時候的“緣分卡點”是,真的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告訴我們——“不要恐慌,一切終將過去”,告訴我們千年文明有韌性,文化有深流。
他説,“人類從來都在災難中掙扎,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需要彼此成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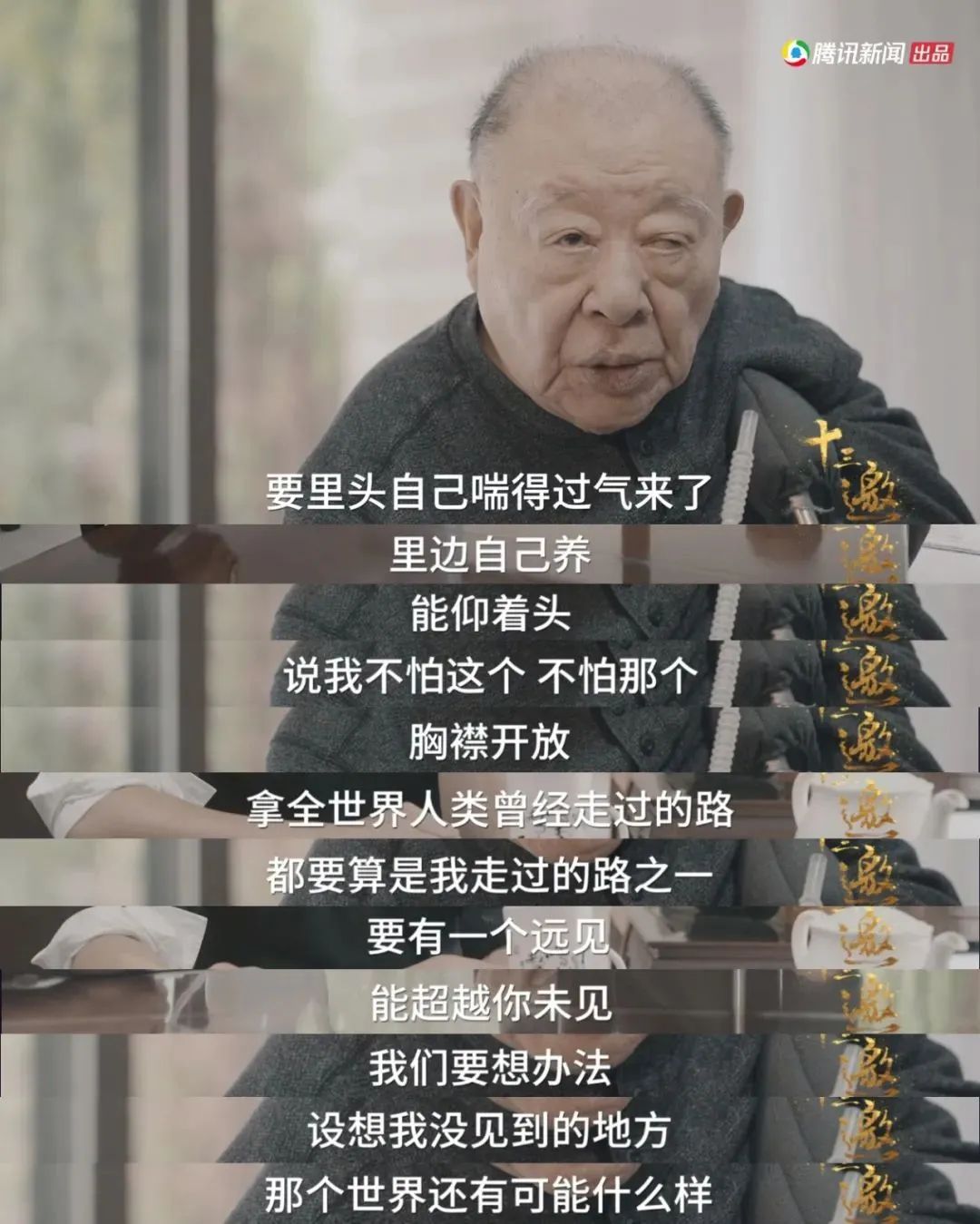

精神的種雲人:三重修行
許倬雲的“往裏走”從來不是消極避世,而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修行體系,藏在他散落的言談與著作中。
**第一重,直面遺憾的勇氣。**他説“每個人都有抓不到的雲,都有做不到的夢”,這不是妥協,而是清醒。抗戰時目睹同伴倒在日軍槍口下的創傷,中年時因身體不便錯過的田野調查,晚年“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憾——他從未掩飾生命中的“未完成”,反而將其轉化為理解他人的共情力。
“做不到的事,有機會再做也好,沒機會再做,你還可以做別的夢”,這句話背後是歷經滄桑後的通透:安頓不是強求圓滿,而是與缺憾共生。
他清楚歷史永遠只討論特殊性,不討論普遍性,個體生命中的遺憾與特殊經歷,也構成了獨一無二的人生軌跡,在接納中我們能尋得內心安寧。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宏大視角看,不同文明在發展進程中也充滿了曲折與未竟之事,古埃及文明的神秘消逝、瑪雅文明的突然衰落,這些文明的遺憾同樣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啓示着我們在面對自身生活的不如意時,應以更廣闊的胸懷接納,明白這是生命與文明發展的常態。
**第二重,拒絕盲從的獨立。**他在《十三邀》裏講“父子騎驢”的寓言:“是老人騎還是孩子騎?倆人騎還是倆人牽着驢?什麼都聽別人的意見,這種人不能安頓自己。”
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貫穿他的一生。從台大轉系時拒絕“熱門專業”的誘惑,到學術研究中堅持“常民視角”對抗主流史觀,再到晚年對人工智能的冷靜審視——他始終保持“往裏看”的清醒,不被潮流裹挾。
他認為,“你成為今天這個樣子,你自己是要負責任的”,只有堅守內心的判斷,才能在複雜的世界中站穩腳跟,實現真正的自我安頓。
在歷史研究中,他也強調史學家應在史料範圍內,誠實地揭去誤解與偏見,不偏不倚地重建史事發展輪廓,這種對獨立、客觀的追求,延伸到生活中便是對自我思想的堅守。
第三重,聯結他人的温暖。“往裏走”不是封閉自我,而是在認清自己後更好地擁抱世界。
他回憶抗戰時“不認識的人在必要時幫把手,扶着我過去”,那些陌生人的善意,成了他一生的精神養分。在《經緯華夏》的結尾,他期盼《禮記・大同》的理想,正是這種温暖的延伸:真正的安頓,是在安頓好自己之後,懂得“人跟人之間不再有面對面的接觸,人把自己封鎖在小盒子裏邊,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別人”是最大的危機。
他倡導“修己以安人,心有餘力要安他人,從你附近的人‘安’起,從親戚家人到鄰居、同胞到百姓、到全人類”,在與他人的聯結中,拓展生命的廣度與深度,讓內心的安頓更具力量。
他相信中國人從來不是一盤散沙,個體應在羣體中找到自身價值,以羣體的和諧發展為己任,這種對羣體關係的重視,正是其“往裏走”後向外拓展的生動實踐。


許倬雲晚年在《經緯華夏》的後記裏寫下“餘白”二字,説自己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拼圖”。
這種清醒的“未完成感”,恰是“往裏走”的真諦——安頓不是終點,而是終身的旅程。他用95年的生命證明:身體的殘缺可以用精神的豐盈彌補,時代的動盪可以用內心的堅定對抗,歷史的厚重可以轉化為當下的力量。
如今這位“雲的觀察者”已然遠行,但他播撒的“往裏走”的種子正在生長:年輕人帶着《往裏走,安頓自己》對抗精神內耗,學者們循着他的思路探索文明對話,普通人在他的文字裏學會與自己和解。
重要的不是抓住雲,而是永遠保持仰望的姿態!當我們再看天上的雲時,或許會想起那個總在歷史褶皺裏尋找温度的學者。
他沒能親手觸摸到“九州同”的雲,但他留下的“往裏走”的智慧,早已化作千萬人心中的錨,在這個動盪的時代,穩穩地繫住了無數漂泊的靈魂。
他告訴我們,“不要糟蹋自己,不要屈服於這個世界”,在不斷向內探索、向外聯結的過程中,我們終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安頓之所,讓生命在歲月長河中綻放獨特的光彩。
許倬雲在疫情中火起來,讓“讀書人”的形象在反智主義中被重新召喚。疫情年代,信息爆炸、真假難辨,一部分人滑向反智和陰謀論,另一部分人卻重新開始敬重“真正的學者”。很多年輕人在紛亂中找到了認同的温和出口——不必極端,也不必自卑,可以在文化上做個“有根的現代人”。
我們也該有自己的文明視野與人文情懷。歷史的意義在於理解文明如何誕生、如何興衰,讓我們知道人類應該如何自處。
他的“道”是人本主義的温度與深度;
他的“名”是告訴我們,歷史不再只是帝王將相的編年體,而是每個普通人生命價值的疊加和共振;
他的“用”是告訴我們,人的存在才是文明最根本的尺度,其他都是手段與路徑。
—— · END · ——
No.6479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齋主 水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