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南京照相館》解惑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31分钟前

《南京照相館》成了暑期檔的黑馬。
作為甯浩“徒弟”的青年導演申奧,此前的代表作有《受益人》《孤注一擲》《新生》,都是類型化的現代戲,而《南京照相館》是一部歷史災難題材,十分考驗主創的史實掌握和尺度把握。

看完電影出來,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油然而生:也許這一代導演、編劇等待的就是類似的機會,而當這樣的契機出現,他們會向觀眾證明自己不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比一些前輩更好。
過往取材於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真實罪證影像的電影,包括但不限於羅冠羣的《屠城血證》(1987)、吳子牛的《南京1937》(1995)、牟敦芾的《黑太陽南京大屠殺》(1995)、鄭方南的《棲霞寺1937》(2004)、陸川的《南京!南京!》(2009)、德國導演佛羅瑞·加侖伯格(Florian Gallenberger)的《拉貝日記》(2009)和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2011)。
和以上電影相比,《南京照相館》是敍事最紮實的一部,同類型中也最具國際傳播的潛力。用受邀來華觀影的國際友人埃文·凱爾(Evan Kail)的話説:“這部電影並不迴避黑暗,也不粉飾傷痛,而是以巨大的藝術勇氣直面民族的傷疤。”
對這部值得去影院觀看的佳作,本文不過多劇透,而是就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映後問題進行答疑,希望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這部電影。

一個問題,是部分角色的方言。
很多觀眾聽不出來一些角色的口音,比如高葉飾演的演員林毓秀和王真兒飾演的照相館老闆娘趙宜芳,尤其是後者,甚至有觀眾以為她講的是山東話或河南話。

實際上《南京照相館》的口音問題,謎底就在謎面上。
導演這次非常聰明,乾脆就讓演員講自己家鄉口音,畢竟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只會説方言,這樣設計也符合歷史真實。
比如王驍和周遊就是南京人,高葉是常州人,所以她講的是常州話。對北方觀眾來説,上海話和常州話區別不大,但包郵區能聽出細微差異。
王真兒的口音最難判斷,我一開始覺得她講的可能是安徽話,但肯定不是山東或河南方言,下來一看演員籍貫,確定她片中講的是徐州話,正式稱謂是中原官話-徐淮片。

**而國民政府在當年實際統治的區域,也就是長江中下游與東南沿海的這幾個省份,基本上政令不出包郵區。**從以上演員的方言配置來看,也都是非常契合的。
主角中唯一的例外,是説普通話的郵差蘇柳昌,演員劉昊然是河南人,開拍前和導演討論過,是否需要學習南京話,申奧回答不用,因為阿昌的設定就是一個生活在南京的外地人。

今天有很多人提到南京大屠殺,第一反應只是日軍在一座中國的大城市裏殺了35萬人,但實際上,南京在當時不是一座普通的大城市,而是中國的首都。侵略者在另一個國家的首都肆意屠殺35萬人,除了旨在摧毀中國軍民的抵抗意志,還帶有極強的侮辱性。

片中有一處細節,牆壁上蔣介石戰前的巨幅畫像,被機槍打了密密麻麻的彈孔,這種對於侮辱的呈現,和陸川《南京!南京!》裏日本兵把孫中山雕塑拉倒的舉動如出一轍。
話説回來,因為南京是首都,而且在1927-1937的“黃金十年”獲得了極大發展,所以存在很多在此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就像今天的北上廣深也會吸引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一樣。劉昊然的角色不講吳儂軟語,看似和周圍語系不同,實際是關照了藝術真實背後的歷史真實。
當然,作為民國首都的南京不止有外地人,也有很多在此工作和生活的外國人。
比如後來在大屠殺中挺身而出的約翰·拉貝(John H. D. Rabe)、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伯恩哈爾·阿爾普·辛德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等人,這些在日軍槍口下拯救中國難民的外國商人、記者、傳教士們,不是在戰爭中聞訊趕來南京,而是一開始就身處於這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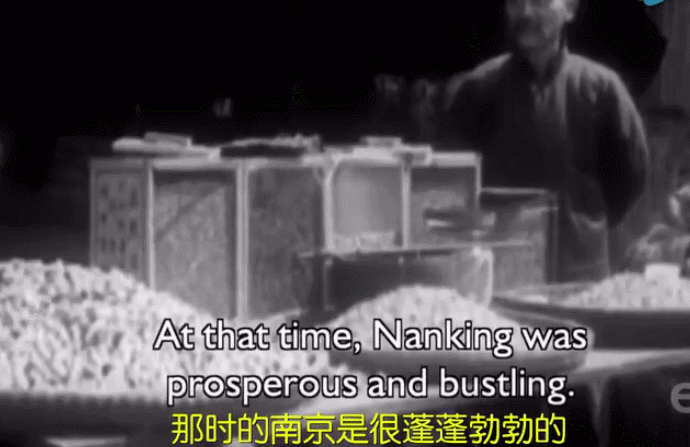


另一個問題,是潰兵在挹江門的衝突一幕。
關於南京會戰末期的潰敗,電影是通過城內的散兵遊勇與挹江門守軍的火併呈現的。但這不是《南京照相館》的首創,在陸川那部《南京!南京!》裏已經出現過,片中劉燁飾演的角色,出場就是在挹江門守軍陣列,負責攔截潰兵衝卡。
《南京!南京!》背景字幕更為詳細地註明了負責挹江門守衞的是宋希濂的36師,這支部隊和87、88師一樣,都是最早裝備德械的中央調整師。36師也是《八佰》裏王千源角色的原部隊,魏晨台詞提到的“宋長官”就是宋希濂。
“八·一三”淞滬抗戰前,36師駐紮在西安,接到調令後星夜馳援上海戰場,萬里赴國難。三個月打下來,36師損失慘重,撤到南京城下已是強弩之末。
電影開篇那場被網友譽為“《西線無戰事》質感”的戰壕戲,雖然時間不長,但真實傳遞了南京守軍那種疲於奔命過後強打精神的狀態,尤其是臨時補充到外圍陣線的新兵,面對日軍的優勢兵力,呈現出被碾壓的態勢。
憑淞滬戰場下來的各部,南京城已經無力固守,組織一場大會戰于軍事角度無益;但從政治角度考慮,南京又是首都,直接棄守會挫傷人心。最終,湘系出身的北伐名將唐生智主動請纓擔當南京城的最高防務。

具體到戰役末期的混亂,就與這位南京衞戍司令長官不無關係。
12月11日夜晚,鑑於戰場不利形勢,唐生智下達撤退方案,按照計劃,大部守軍兵分幾路從正面突圍,留一小部分牽制敵軍,最後渡江北撤。可在下達正式命令後,唐生智又下達了一道口諭:各部守軍如不能突圍,可以渡江後撤。
也正是這一個“富有彈性”的命令,導致本就分屬不同派系的將領開始離心,各自為戰,指揮系統隨即陷入混亂。
有的部隊不按照原定計劃撤離,擾亂了戰場秩序;有的部隊不顧友軍形勢,自顧自地放棄了陣地;有的高級軍官未等下屬各部整合聚攏,便擅自撤離;有的部隊由於通訊不暢,根本沒有收到撤退命令。例如挹江門守軍與兄弟部隊的衝突,就是由於一些部隊未按照計劃路線突圍。
而在《南京!南京!》和《南京照相館》的劇情中,更像是潰兵們接到了撤退命令,而城北的36師尚未接到,自然認為這些人是逃兵,所以這兩方就產生了根本性的誤會。在有限的時長內,劇情這樣設計也是合理的。
另外,《南京!南京!》裏被衝卡潰兵踩死的36師少校,原型是教導總隊第一旅第二團的上校團長謝承瑞。
在抗戰初期國民革命軍的中高層指揮官中,謝承瑞不屬於保定、黃埔系,而屬於少見的旅歐派,曾入法國兵工學校和楓丹白露炮兵學校學習軍事。謝將軍在保衞首都的戰役中悍不畏死,最後卻在光華門的踩踏事故中意外身亡,也是南京淪陷前混亂局面的縮影。


最後一個問題,其實是在電影之外,即一些觀眾不清楚,拍這個電影的意義是什麼——有人覺得這類題材會給自己添堵;有人覺得這類題材以往已經太多;還有人覺得這類題材國內誰不知道,應該拿給日本人看。
但在我看來,我們以往拍的不夠嚴肅的抗戰題材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手撕鬼子),而真正客觀呈現歷史的作品,卻寥寥無幾。然而前面那些“不夠好”或是“完全不好”的內容,長期以來已經佔據了主流觀眾的視野和心智,並影響了人們的歷史認知和價值判斷。
其造成的結果,一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真的知道那段歷史,而是以為自己知道;另一個問題在於,先入為主的印象會令觀眾對同類題材產生逆反心理,這反而會導致對《八佰》《南京照相館》這樣真正嚴肅的創作的誤判。
我們總譴責日本人不承認侵略史,但實際上,過往那些拍抗日神劇的導演、編劇和演員,也沒有認真呈現我們的抵抗史。
想讓《南京照相館》這樣的電影也被日本觀眾記住,我們首先自己應該走進電影院,力挺這樣的創作,而不是讓它落入忽視、遮蔽與遺忘的邊緣。

在這一點上,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其實是幾年前一個大學教師在課堂上關於“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數字”的爭議言論,當事人就認為:30萬的概念沒有證據支持,只是一種史學寫作的籠統概述,今天的人不應當糾結於歷史仇恨。
但實際上,這一言論充分暴露了發言者對於歷史的一知半解,以及對於系統性反思的學藝不精——今天的歐洲能在二戰納粹問題上達成共識,是建立在紐倫堡審判對納粹體制和法西斯分子的徹底糾錯的基礎之上,但在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缺少這樣的歷史機遇與問責基礎。
首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史料可以證明,“30多萬這個數字來源於戰後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歷史性判決,具有法律效力” ,且考慮到日軍毀屍滅跡的行徑,這只是遇難者數字的下限。
其次,在整場事件的點評中,我最同意的是詩人方閒海當時寫在微博的一段話:
“‘我覺得不應當永遠去恨,而應當反思戰爭是怎麼來的。’——這句話值得細品,也是上海這個教學事件的關鍵句。這觀點的邏輯顯得極其庸俗化的‘知識思維’。其實人類在經歷極端的生存處境之後,恰恰是需要用‘恨’來制衡理性的,而不是用中性化的‘反思”,這種反思恰恰會讓人遺忘或淡忘歷史,背離真正的理性。我以為,恨和反思,缺一不可。不恨哪有大愛?”
—— · END · ——
No.6480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