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為一位數學家?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科普中国子品牌,倡导“溯源守拙,问学求新”。1小时前
 波蘭裔美國數學家 Mark Kac 是 20 世紀傑出數學家,現代概率論發展的先驅,特別是推動了概率論在統計物理學中的應用。他最廣為人知的故事是提出問題“可以聽出鼓的形狀嗎?”由此引發了相關譜理論的研究。Mark Kac 最大的特點是能將複雜概念以簡單直觀的方式呈現,寫作風格清晰簡潔,因此備受同行讚譽。本文摘自他的自傳《機運之謎》(Enigmas of Chance: An Autobiography),記錄了一個少年如何與數學結緣的故事。
波蘭裔美國數學家 Mark Kac 是 20 世紀傑出數學家,現代概率論發展的先驅,特別是推動了概率論在統計物理學中的應用。他最廣為人知的故事是提出問題“可以聽出鼓的形狀嗎?”由此引發了相關譜理論的研究。Mark Kac 最大的特點是能將複雜概念以簡單直觀的方式呈現,寫作風格清晰簡潔,因此備受同行讚譽。本文摘自他的自傳《機運之謎》(Enigmas of Chance: An Autobiography),記錄了一個少年如何與數學結緣的故事。
撰文 | Mark Kac
翻譯 | 蔡聰明
 Mark Kac(1914.8.3—1984.10.26)
Mark Kac(1914.8.3—1984.10.26)
這是 1930 年夏天,在波蘭所發生的事情。那年我 16 歲。高中的最後一年在 9 月就要開學,我必須思考未來的前途作生涯規劃。因為數學與物理都是我拿手的,所以選擇讀工程似乎是實際與合理的事情。“一個家庭一個哲學家就已足夠”,這是我母親表述問題與建議解答的方式。“一個家庭一個哲學家”是指我的父親,他在德國的萊比錫大學讀哲學並且得到博士學位,其後又在莫斯科大學得到歷史與語言學結合的博士學位。儘管有這些優秀的學歷,但是由於社會普遍反猶,讓他無法找到任何教職,除了在一個學校當了兩年短暫的校長之外。我父親參與我外祖父經營的紡織事業,多年後也宣告失敗而結束,他只好靠着微薄的家教收入維生。他可能是歷史上懂得希伯來文、拉丁文、希臘文、甚至是斯拉夫舊教文的唯一商人。因為他的一些學生是當地希臘正教學院的學生,所以他很方便就學得後者。
這樣的生活並不是我母親對她的兒子所期望的,因此讀工程似乎是正確的方向。然而,在 1930 年的夏天,選擇大學的科系在我心目中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一個經常折磨數學家與科學家間歇性發作的“疾病”,突然發生在我的身上,那就是:對一個問題着迷。發病的症狀都類似,而且很容易辨認,特別是患者的妻子更是心有慼慼焉,因為患者表現出的反社會行為持續增強。最常見的是:茶飯不思,也不睡覺。我的症狀特別顯著,因此家人開始為我擔心。
事實上,我的問題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甚至也不會產生重大的後續發展,這就是三次方程式的求解問題。答案早在 1545 年就由意大利的數學家卡丹 (Cardano,1501-1576) 所發表。我所不知道的只是,他是如何想到與推導出來的。
 波蘭教育專家們為中學所設計的數學課程,在解完二次方程式之後就停止了。對於三次或更高次方程式好奇的學生,他們會回答説:“這對你們太高深了”,或者説:“不要急,當你以後讀到高等數學時,就會學到。”因此這個問題就如同一個禁地。但是我不理會它,決心要自己弄明白三次方程式的求解問題。
波蘭教育專家們為中學所設計的數學課程,在解完二次方程式之後就停止了。對於三次或更高次方程式好奇的學生,他們會回答説:“這對你們太高深了”,或者説:“不要急,當你以後讀到高等數學時,就會學到。”因此這個問題就如同一個禁地。但是我不理會它,決心要自己弄明白三次方程式的求解問題。
我拿起一本暑期數學讀物,打開三次方程式這一節,讀到第一行我就被打敗了。開頭這樣寫着: “令 x=u+v. ”因為我知道答案是兩個立方根之和,所以令 x=u+v,顯然是預期這樣的解答形式,但是整體説來,我覺得這對學習者是不公平的。
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很接近於數學教學的一個奇妙的分水嶺:一邊是如何想出證明或推理的策略,這大部分是超越邏輯的範疇;另一邊是證明或推理的技巧,這是純演繹的工作,因此具有邏輯與形式的特性。換言之,這是在求知過程中,動機與實踐的區別。不幸地,絕大部分的數學書都只呈現後者,而忽略前者。
在不瞭解背後動機之下,我無法接受只是形式的推演。直接令 x=u+v,而不説明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對我是一種冒犯。我問父親,但是他太專注於他那瀕臨衰敗的事業,以至於對我沒有什麼幫助。因此我立定決心,要自己找尋一個滿意且不同的推導方法。我父親則抱持懷疑的態度,這從他願意出高價就看得出來。只要我做成功,他就給我 5 元波蘭幣的獎金(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我這一生中,有好多次因沉迷於問題而發狂的紀錄,有些問題在數學與科學上還產生過一些影響,但是在 1930 年後,我從未像這次那麼努力與狂熱的工作。我很早就起牀,幾乎沒有時間吃早餐,我整天都在做計算,在一大堆白紙上寫滿公式,直到深夜累壞倒在牀上。跟我講話是沒有用的,因為我只會回應無意義的單音節,“嗯”、“啊?”。我停止與朋友會面,甚至放棄跟女朋友約會。由於缺少策略,我的工作漫無方向,經常重複走着沒有結果的老路,蹣跚於死衚衕中。
直到有一天早晨,答案突然出現在眼前,卡丹公式就在眼前的紙頁上放光!我花一整天或更多的時間,從堆積如山的紙堆中拾取論證的線索。最後終於把整個推導過程精煉成三到四頁。我父親把我辛勞的成果瀏覽一遍後,就付給我獎金。
不久學校開學了,我把整理好的文章交給數學老師。他是一個親切的人,喜愛伏特加酒,他在聖彼得堡大學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當我認識他時,他已很少記得他所學的,並且也不在乎。不過,他還是很小心地研讀我的文章,並且代我投稿到華沙的《少年數學家》這本雜誌。到此似乎就結束了,因為雜誌社一直沒有通知我文章已收到,又經過了幾個月也沒有從遙遠的華沙傳來任何訊息。
然後,在 1931 年 5 月初,距離期末考只有幾個禮拜的時間,好消息突然降臨。在上午的時段,宗教靈脩的課程正要開始。因為只有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同學要接受教導,對於我們少數幾個非天主教徒的學生,這段是自由時間。現在上課鐘聲響了,朦朧微暗的走廊幾乎沒有學生。我遲了一些離開教室,在匆忙之中差一點就撞上正要進入教室的牧師。就在這時,我看見校長朝我走來。我猜這必是衝着我而來,因為宗教課從未有外行的專家會來造訪,而且我的周遭沒有人,走廊也只是通到教室的死巷。
根據我的經驗,會見校長大概不會是什麼好事,於是我開始回想,到底我有沒有做錯什麼事情,才讓校長走出辦公室來找我(有別於通常的召人進入校長室),我擔心可能要被處罰。事實上,從他神秘的表情看來,他將要獎賞我!甚至在他開口之前,還特別調整一下自己以示莊重,這是一個學生在快要畢業的前夕所無法想象的事。他的第一句話就讓事情明朗。他説:“教育部的參事 Rusiecki 閣下,正在本校訪問,下午兩點半在他的辦公室要接見你。”這時果戈裏《巡按將軍》的景象立刻在我腦海浮現,不過 Rusiecki 是“真實的”人物,這讓我有幾秒鐘的時間一直回味着“參事閣下”這句話。原來 Rusiecki 是《少年數學家》雜誌的主編。
在兩點半整,我以週末最佳的整裝打理好自己去會見 Rusiecki 先生。他個子高大,有點瘦,蓄小鬍子,戴着金邊眼鏡。他對我講話時,宛如我們的地位是平等的。
“我們已經收到你的論文,會拖這麼久是有理由的。在編輯會議的討論中, 起先我們相信你的方法是已經知道的,因為在文獻上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推導出卡丹公式,也許你只是重新發現其中之一而已。然而,經過我們搜尋文獻的結果,最後確信你的方法是新的,因此我們準備要刊登你的論文。”
他們實現了承諾。在我畢業幾個月後,論文註銷來了,我用 Katz 的名字發表,因為我覺得德文的拼字 Katz,比斯拉夫文的 Kac 還要優雅。
在我會見 Rusiecki 先生要結束前,他問我將來有什麼計劃。我告訴他説,家人要我讀工程。他説:“不,你應該讀數學,顯然你對數學有天分。”我聽從他的勸告,走上數學之路,這救了我的性命。我的數學足夠好,也足夠幸運,我在 1938 年申請到博士後出國深造的研究獎學金。這是由波蘭富有的猶太家庭 Parnas 所捐贈,規定要有一個名額給猶太籍申請者,為期兩年期的獎學金。我在 1938 年 12 月抵達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二次世界大戰讓我滯留在美國,有家歸不得。如果我當初去讀工程,無疑地,我必然留在波蘭,跟我的家人和六百萬猶太同胞一樣,走上被希特勒屠殺的相同命運。
最後附言:在幾年前我有一位朋友,也是美國年輕的數學之星 Gian-Carlo Rota 在洛克斐勒大學演講,題目是 “Umbral Calculus”, 探討用新方法來處理不變式理論。在演講中, Rota 順便討論 Sylvester 定理,這是關於二元齊次式的一個美妙結果。他説:“我現在展示給你們看,如何用 Sylvester 定理來求解三次方程式。”我只聽他講幾句話,立刻就感覺到電流傳佈全身。因為我認識到,那就是在 1930 年夏天我所發現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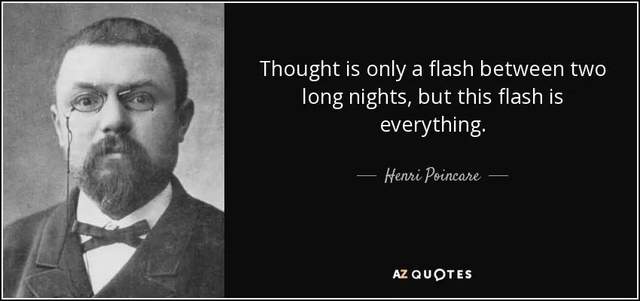 編者注
編者注
1:Kac的文章發表於1931年,原文是波蘭文,後來有人翻譯成英文,見https://old.maa.org/press/periodicals/convergence/mark-kac-s-first-publication-a-translation-of-o-nowym-sposobie-rozwi-zywania-r-wna-stopnia-trzeciego-6
2:Rota的證明,可見下文69頁5.4節:
J.P.S. Kung and G.-C. Rota, The theory of binary forms, Bull. Amer. Math. Soc. (N.S.), 10 (1984), 27-85.
 Kac的自傳,1985年出版
Kac的自傳,1985年出版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數學縱貫線”。原文摘自Mark Kac的自傳《機運之謎》(蔡聰明譯)第一章。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