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拜波伏娃是不是拜錯了神?_風聞
后沙月光-后沙月光官方账号-21分钟前
8月1日期間,有多所高校官微同日推送法國作家波伏娃的作品《清算已畢》中的摘錄內容。

還有一些人跑到波伏娃老家哭墳,她的墓碑上有一大半都是中文塗鴉。
對於波伏娃突然“走紅”,引起了很多網友的聯想和警覺,也引發了很大爭議。
一些人將波伏娃當成神來拜,極力拔高她的作品和思想,將她宣揚為“女權主義”的旗幟。
在激烈的爭論下,波伏娃被扒得體無完膚,她與終身伴侶薩特之間的“開放式關係”的混亂程度比色情小説還誇張,還涉及未成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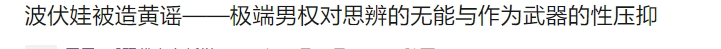
為了她辯護的人則聲稱,波伏娃被“造黃謠”,是想用私生活貶低她,是“色情凝視”,是在逃避“嚴肅的哲學討論”。
其實,早在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出版後,法國人就用“皮條客”、“色情狂”、“流產一百次”……還有更難聽的詞彙罵過她。
更有趣是,造黃謠的恰恰是波伏娃自己。

法國最知名的芭蕾舞演員克萊奧·德·梅羅德(Cléode Mérode,1875-1966),曾被法國《畫報》(L’Illustration)票選為“法蘭西第一美人”,她甩開第二名一千多票。
她的形象出現在歐美的香煙盒、撲克牌、招貼畫、年曆和明信片上。
追求她的王公貴族、富賈鉅商遍佈整歐洲,但她一輩子只有兩個男人,一位是法國貴族(相處10年,男方死於傷寒病),一位是西班牙侯爵(相處13年,因男方出軌分手)
然而,或許是出於妒忌,1949年,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公然造她黃謠,稱她是“高級妓女”,説她忙着勾引貴族們……
克萊奧以毀損名譽的罪名起訴了波伏娃,法院判定克萊奧勝訴,要求波伏娃向她賠償1法郎,並道歉。
但由於波伏娃本人和《第二性》的影響力,克萊奧至死也無法走出被造黃謠的陰影。
那些用“被造黃謠”來為波伏娃開脱的人,不覺得臉疼嗎?
對於波伏娃那些亂七八糟的爛事,網上現在有很多。
不過,私生活屬於私德,與她對社會領域的“貢獻”並沒有直接關係,所以就不細説了。
而她在二戰期間的表現,則是個大問題,這不屬於私德,值得一説。

西蒙.波伏娃,1908年1月9日出生於巴黎。
父親喬治是一名律師,母親弗朗索瓦是銀行家的女兒。
她説她的童年“非常非常的幸福”,她有文學天賦,並擁有極為良好的教育資源,7歲就開始寫小説,8歲學英語。
1922年,她的外公破產,財產被清算一空。她的生活質量也一落千丈,實際上,她家的富裕生活是靠母親(外公資助)支撐的。
她的父親只是一個收入微薄的律師,妻子沒錢後,他就開始用耳光來回應向他要錢的妻子。
家庭變故,對波伏娃後來的婚姻觀可能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1925年,17歲的波伏娃以優異成績通過法國中學畢業會考,進入了索邦大學,這對當時的法國女孩來説還是個新鮮事。
她讀書比男生更刻苦,因為家庭陷入經濟危機,她也知道讀書是她唯一的出路。
1927年6月,她獲得了哲學學位證書,但她的人生道路仍然是文學。
1929年,在法國教師資格考試中,她與來自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考生保羅.薩特相識。從此,兩人開始了一段驚世駭俗的戀情。
她與薩特在靈魂上結合在一起,但肉體各自對外開放,互不隱瞞。
怎麼理解?法國佬的事,愛怎麼理解怎麼理解吧,反正我是跟不上。

由於薩特的成就和名氣,波伏娃被稱為了薩特身後的女人。
當一切順風順水的時候,他們的命運卻發生了改變,德國人打過來了。
薩特在1940年2月應徵入伍。波伏娃在火車站送別時,跟身邊那些妻子、母親和女友們一樣,也在哭泣,也在祈禱。
6月21日,在薩特35歲生日那天,他和戰友們成了德軍的戰俘。
薩特去前線沒幾天,波伏娃就和薩特的朋友博斯特度過了“一段熱烈的生活”,而薩特還來信勸她趕緊離開巴黎。
博斯特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波伏娃女學生奧爾加·科薩基維奇的男友。
而奧爾加是波伏娃的同性情人,她也是薩特的情人,波伏娃介紹的。
這種關係是不是很燒腦?而這種燒腦的關係,還有好幾段。
波伏娃並不想離開巴黎,因為她在這裏很舒適,法國人也不相信德軍能在6月份攻佔巴黎。
4月,德軍佔領丹麥和挪威,然後進入比利時,繞開了法軍的馬奇諾防線,通過阿登地區(Ardennen)入侵法國。
薩特再次來信,催促波伏娃逃離巴黎,“為了我,我的愛人,我的小花。”
巴黎淪陷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實,出於恐懼,波伏娃加入了“逃離潮”,前往昂熱。這一路,她跟難民沒有兩樣,吃了很多苦。
薩特事先為她安排的居住地是朋友莫雷爾夫人的家,莫雷爾夫人讓兒子開車將波伏娃接到家中。這裏住滿了逃難的法國名人,大家準備繼續逃,走海路離開法國。
波伏娃卻連一天也呆不住,這裏的生活太艱難了,她不停地聽着收音機。
當她知道德軍沒有在法國大開殺戒時,她又想回到巴黎。
四天之後,她告別莫雷爾夫人,坐着一位荷蘭人的汽車,逆着難民潮向巴黎走去。
侵略者的合作者
雖然網上有些人為波伏娃在巴黎淪陷期間的行為辯白,但大多都回避了一點:她是在有機會逃離法國的情況下,主動回到巴黎的。
荷蘭人由於加不到汽油,停下了汽車。波伏娃坐上了德國卡車,最後坐着一輛紅十字會汽車,來到了巴黎,住進酒店。

巴黎屬於德軍佔領區,波伏瓦面臨着一個新環境。
據説,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她在迪呂伊高中(Lycèe Duruy)找到了一份工作。
同時,波伏娃還為維希廣播電台工作,利用她的名氣為德軍進行美化。
Les événements historiques qui ont marqué cette autrice so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t la guerre froide.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lle travaille pour Radio Vichy(法國方面對她人生這段經歷的記錄)
維希政權就是法國的“汪偽政權”,它的廣播電台就是德軍宣傳工具。想要得到這份工作,沒有德軍同意是不可能的。
波伏娃因為與侵略者合作,又過了上舒服的生活,又可以終日泡在左岸的“花神咖啡館”和“雙叟咖啡館”。
她又搞上了另一個女學生娜塔莉,但兩人經常打架,因為娜塔莉不喜歡學習,只喜歡肉體刺激。
不過,放蕩不羈的娜塔莉可以幫助波伏娃在食品配額制之外,弄到巴黎城郊農民那裏的美食,兩人就在打架與和好之間循環着。
7月,博斯特被從戰俘營釋放(他跟波伏娃好了幾天之後,也去當兵了),又與波伏娃在各個酒店偷偷開房。

波伏娃對德軍的讚美之詞相當肉麻,她説,自己對德軍有一種“不自覺的友善”;德國人對“身體的膜拜”,令她感到神魂顛倒。
波伏娃還説,“只有在那些晚上,我才發覺派對的真正意義。”
所謂派對,就是法國“合作者”為德軍組織的“酒色狂歡”,這曾是法國解放後的禁忌話題。
波伏娃在納粹佔領巴黎時期,就沉迷於那些通宵達旦、縱情酒色的派對。

“合作者”在巴黎到處組織舉辦這種派對,一是為了討好德國人,二是為了麻醉法國人。
有人説,波伏娃是一些派對的組織者。不過,這並沒有真憑實據。但她喜歡參加這種派對,是她自己承認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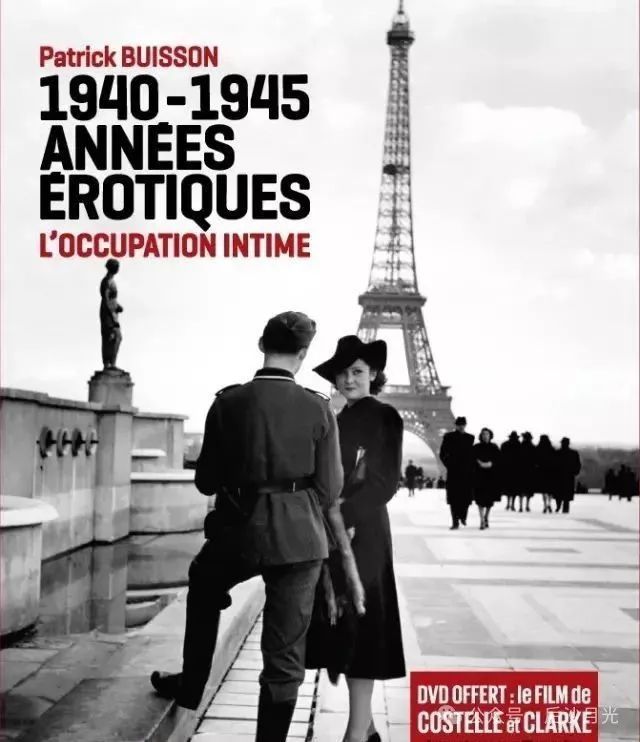
在法國作家比松(Patrick Buisson)所寫的《1940-1945 色情年代》這本書中,曾描述了一些法國女人忘了死去的丈夫、忘了關在集中營裏的兄弟,每天在晚上10點至清晨5點的宵禁時間跑去跟“野蠻人”尋歡作樂。
1942年,巴黎的嬰兒出生率暴漲,成為歷史上三大高峯期之一。
另一個暴漲的紀錄是:1941年,干邑白蘭地僅僅在四個月內的銷量就超過了巴黎前兩年的銷量,1941年全年法國喝掉了驚人的3000萬瓶干邑。

巴黎的女人如此迎奉德軍,當然離不開波伏娃這類名人的“開導”,讓她們放下心理負擔,去討好德國男人。

法國解放後,雖然戴高樂政府清算了一些法奸,但很多“合作者”都逃過了清算。
波伏娃和薩特後來還有很多故事,這裏講不完。
但不管怎麼説,國內“女權”把波伏娃當成神來拜,絕對是拜錯了。
其實,無論是“女權”、還是“環保”、“動保”、“LGBT”,早就只剩下了一塊高大上的招牌,內容已經完全被扭曲,並走向極端。
除了製造對立,還是製造對立。
波伏娃,不會想到,她居然會在網絡時代成了中國那些所謂“女權”的神。
波伏娃只是一個符號,炒作波伏娃的真正目的是想為國內“女權”樹立一面旗幟,讓女人理直氣壯地走向墮落。
一個為男友“拉皮條”、一個侵略者的“合作者”、一個“遇陽則陰,遇陰則陽”的女人,怎麼就代表女權了?
再者説,她喜歡男人,而“女權”憎恨男人,這真是一種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