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原子人會夢見大洪水嗎?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51分钟前
文 | 飛劍客
最近因為武大楊某事件,讓我們看到豆瓣生活組裏那股“性別法西斯”的暗流,其實這種氛圍在很多年以前已然濃厚。説到“性別法西斯”,請容我借用這個激烈但不無道理的詞,雖然這裏面沒有什麼“法團主義”“階級調和”元素,但它指向一種極端的、試圖將個體完全收編入一個不容異議的**“性別種族”陣營**的機制。

豆瓣生活組常常是以八卦和“日常生活”主題切入,比如“絕望的直女”在感慨男女日常生活上“本質”不同,逐漸把“男”“女”想象成兩個互不相容的族羣。先是驅逐被視為“異族”的男性存在,繼而將矛頭轉向那些不夠“純粹”、“愛男”的女性成員。
這種二元對立下的清洗邏輯,將性別本身塑造成了不可調和的敵我陣營,彷彿“男性”與“女性”已不再是複雜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是被抽離出個體具體性、在想象中被凝固為兩個擁有截然不同“優劣等級”的“種族”。
我們常將豆瓣“生活組”現象歸因於某些理論或外部因素的輸入,這當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察角度。但據筆者持續觀察,這種現象的驅動力,更多的時候是基於直覺、感受和情感,而非思維與邏輯。
也就是説,清洗的動力,往往並不是來源於哪本女權的經典,而是最直觀、最無需解釋的“性別”標籤——一眼就能分辨,一秒就能站隊。
説到底,是因為“性別”“地域”等變成了民族國家內部最容易抓住的身份,人們從這種最易感知的身份標籤,汲取最強烈的情感和經驗的共鳴。它像一道閃電,劈開了原本複雜難辨的世界,讓人誤以為只要把“他”或“她”劃出去,就能換來乾淨、安全、同質的生活。
無法否認的是,促使性別被如此鮮明地推到前台,並被賦予超越其他社會關係解釋權的原因,這種非理性情緒除了思維的引導,確實還有着根植於我們共有的、包裹着我們的感官現實與生活肌理。
身體、空間和人際關係
互聯網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再把網絡空間和現實空間分隔開,儘管現實空間中還有着“沉默的大多數",但我們也沒法再輕視網絡空間的極化趨勢對現實生活的影響。
空間理論家列斐伏爾指出,我們棲居的空間絕非中立容器。它先被既有的社會關係塑造,繼而又生產出新的關係。他還強調,一切社會空間皆始於我們自己的身體。
社會秩序、規範、權力結構並非從天而降的抽象規則,而是人類身體最初感知和構建的空間感、方向感、距離感以及對他人身體存在的感知(姿態、表情、力量、互動)。 我們通過身體經驗理解“接近”與“遙遠”、“內部”與“外部”、“上與下”、“我與你”。然而,自笛卡兒以降的西方哲學傳統,沉溺於身心二元對立,割裂了空間體驗的鮮活源頭。
為具體闡釋空間形態如何塑造社會關係(如性別角色、人際關係等),此處試舉三種典型形態為例:
一種是老國企法團社會(如過去的國企大院),其空間形態的特徵是將生產空間(工廠車間)與生活空間(職工住宅、食堂、醫院、學校、商店、工人俱樂部)高度整合在同一個物理圍牆之內。
男性工人多在鋼鐵、重型機械、採礦廠,女性工人則多在與之配套的的紡織、食品、日化廠,工作與生活空間高度疊合,物理區隔模糊。空間安排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促進了男女在日常空間中的協作共存,形成了一種相對緊密的社區紐帶。

在這種空間裏,性別角色雖存在,但被共同的單位身份、集體生活節奏和麪對面的頻繁互動所調和,嵌入到更廣泛的“單位人”協作網絡中。
一種是美式郊區模式。這並非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美國法律與資本(房地產、汽車工業)合謀的產物。它通過區劃等手段,以白人中產為核心,系統地排斥低收入者與有色人種,製造了階級與種族隔離空間。這種低密度、依賴汽車的空間結構將生活成本高度外部化(如通勤、育兒、房屋維護),以及社會化公共服務幾乎沒有,也影響了人際關係模式。
之前小紅書有觀察指出,美國很多地方都太村了,這種空間對單身生活十分不友善——房屋維護(剪草、修葺)、通勤採購、育兒(遠離祖輩支持)等任務,倘若單靠個人完成成本極高。在這種空間裏,組建家庭成為提升效率、降低生存成本的現實選擇。

高密度城市則是土地稀缺、追求規模經濟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資本高度集中和高強度利用土地的體現。與前兩種空間形態不同,這種城市形態發展起來,便利店、快餐、外賣、洗衣店、發達的公共交通和家政服務網絡,使得獨居在經濟和物理上完全可行且舒適。
儘管房租/房價壓力巨大,但成熟的租賃市場和迷你户型降低了門檻,緊湊住房設計的普及為個體化生存提供了物理支持,降低了對組建家庭或依賴親緣關係的必要性。同時,便捷的租賃市場使個體能快速進入或退出社會關係,形成了更為鬆散的人際紐帶。
這種都市形態,也動搖了基礎的時間體驗。空間對於時間感知同樣具有塑造力。以日本都市為例,其夜生活文化將活躍時段大幅延後,直至凌晨,導致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接近日出前的時段,人們常常難以清晰界定“昨天”與“今天”的界限。
為了解決這種源於現代都市生活節奏的時間混亂,日本社會發展出一種非正式規則:將一天的界限與商業活動的運營時間調整相關聯,例如,凌晨1點被標記為“25時”,凌晨3點為“27時”,依據“首班電車時間”來錨定“新的一天”,體現了空間如何深度介入身體對時間的感知。

在這樣的時空下,深夜飢餓、家務繁重、物品短缺、緊急配送,在以往可能需要向鄰居借鹽、請親朋幫忙、依賴社區小店的場景,如今很容易被外賣或一次到店消費高效解決。
享受便利的用户,通常只能觸摸到這條複雜服務鏈條的最末端:遞送餐盒的手、結賬的店員。驅動這一切運行的後台支撐力量:倉儲物流、基礎設施維護、清潔工、分揀員、物流司機乃至維繫這個城市機器轉動的能源和通信網絡背後的龐大勞動階級——則高度抽象化、透明化、隱形化。
都市社會高效隔離的同時,人際交往的重要維度,特別是異性互動容易滑向兩端:要麼高度依賴線上的、被濾鏡和算法精心篩選的符號化呈現;要麼僅限於高度功能化、短暫的服務場景(點單、簽收快遞)。前者容易形成基於幻想和理想化的連接,後者則強化了他人為工具的認知。
原子人會夢見大洪水嗎?
任何宏觀變遷必沉澱於微觀日常感受。“情感結構”是一個由馬克思主義學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概念,它比明確的哲學思維或意識形態更早出現、更基礎,也更貼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感受。
無可否認,“現代城市”大幅抬高了獨自生活的可行性與便利性。當所有需求,都能被標準化服務即時響應,所有互動都圍繞明確的功能目標時,人們在享受自由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滑入一種普遍的感知模式——他人的存在似乎越來越變成作為特定需求的響應者時才有意義。
而便利,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對真實人際關聯的“去熟悉化”為代價的。這並非現代城市形態的必然宿命,但卻是其高密度、高效率生活邏輯下潛藏且日益顯現的危機。
由此生成的“原子化”主體,呈現出區別於傳統共同體成員的政治——情感結構。首先,表現為立場的缺乏“再生產性”:由於不再嵌入能夠持續生成、維繫與傳遞共同信念、規範與身份認同的社羣再生產機制,政治態度缺乏自我複製與代際傳遞的能力。
其次,流動是以市民社會中高度個體化的利益導向為座標系,立場被即時可兑現的得失算計所牽引;容易“時尚單品化”,政治觀點被快速採納、展示與拋棄;常常搖擺幅度大,可能因特定事件刺激,從激進的“左”轉向保守甚至另類的“右”;最後在頻繁的搖擺和幻滅後,容易滑向一種犬儒主義,聲稱看穿一切,拒絕代替性方案,認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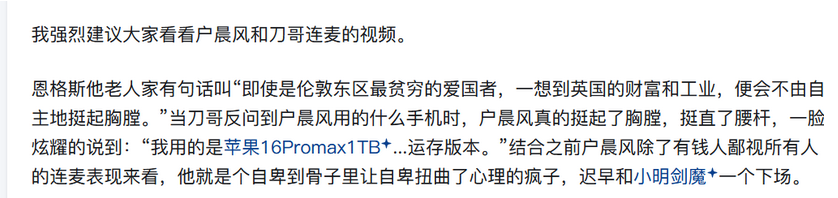
理解這種原子化與政治傾向的根源,我們需回到社會聯結的本質。**共同體的核心特徵,在於其內部互動排斥純粹的商品計價邏輯。**成員間以“人情”、“信任”、“信息”等作為非正式通貨,通過互惠性義務(如照料、互助)構建信任網絡與支持,形成一個商品邏輯無法完全滲透的領域,最小如家庭。其經濟規模龐大,卻因不可計價而逃逸於利潤的捕捉。
資本主義為了將這片“非市場”領域納入其積累和獲取利潤的軌道,就必須拆解許多的共同體,將個體變成彼此孤立、可清晰計價的經濟單元。於是,在近幾十年,我們看到家庭、鄰里、社區、老國企單位的紐帶被不斷削弱,同時,性別對立、代際衝突等話語被不斷生產和放大,其作用往往是瓦解支撐互惠與信任的情感基礎設施。
當下網絡上流行的許多言論(如“斷親”、“託舉”、“生物爹”),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社會關係被削弱後的迴響。當個體失去了共同體、情感寄託和社會支持網絡,就變得異常脆弱:更加焦慮地存錢,更恐懼失業,被迫更深地依賴和受制於勞動力市場。
就像有人説的,資本主義把人原本有的東西拿走,轉頭又重新賣給你,導致人都自覺自己缺了什麼。這種説不清道不明的缺失,正是城市化幾代人情感結構上的一個印記。
但人終究是渴望歸屬與認同的,沒有人真正甘願成為孤島。個體必然尋求各種形式的聯合以填補真空,於是,各種“臨時共同體”湧現,如相同次元相同愛好,最廣泛的是相同身份政治,就像圍繞網絡性別議題瞬間集結的觀點陣營。
這些基於情境或單一議題的聯結雖提供短暫的情感宣泄與身份標籤,因其高度的情境性,無法提供真實共同體所賦予的情感支持、互惠與穩定的社會安全網。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對“體制”的競逐便不難理解。既然傳統共同體和法團(人情網絡、老國企單位)已被拆解或弱化,而資本主導的公司主義基本沒有互助的土壤,個體轉向體制尋求庇護,這未必是出於對公共權力的認同。體制內單位提供了一種以工具性庇護為主導的結構,主要為成員提供基礎性的安全網(即“兜底”),本質上是法理型依附,缺乏情感深度,它至少提供了一種較稀缺的穩定性和基本保障。

但其規模有限,受制於編制等剛性約束,只是少數人的避風港。更多的人既無法回到前現代的血緣—地緣共同體,也難以在資本邏輯的抽象化(市場)和國家權力的抽象化(科層制)中找到情感的安頓,除了走向家庭(這又是激進的性別話語所要消解的對象),他們只能在“臨時共同體”的尋找慰藉,有時候也會變得十分狂熱,呈現出組織化的特徵。
**為了在短時間內獲得高強度的情感黏合,“臨時的共同體”必須製造“緊急狀態”動員。**這裏要結合前文提到的現代生活,對於身體(空間)的區隔,性別法西斯把現代城市提供的標準化服務,想象為可脱離他者(異性勞動者)而永續運行的“自動母體”。在此邏輯裏,對他者的排斥、清潔就是對便利、秩序與自我保存的維護。這為原子化個體的犬儒提供了最後的激情出口。
最終,當所有這些尋求穩定與意義的嘗試,都因其內在侷限(情境性、工具性、破壞性)而無法提供持久的支持與真實的歸屬時,個體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懸浮狀態,而社會整體也將陷入去工業化和組織化的失序洪流中。
重建共同體,並不只是要回到過去
“共同體”(Community),與“共產主義”(Communism)詞出同源,皆源於拉丁語Communis,意為“共同的”、“共享的”。這詞源上的血脈相連,本身就暗示着某種關聯——對共享生活、共同價值、互助互惠的嚮往,深植於人性與社會性的渴望。當原子化的孤獨與懸浮感日益沉重,“重建社羣”、“建設社區”的呼聲便自然湧現,似乎成為解困的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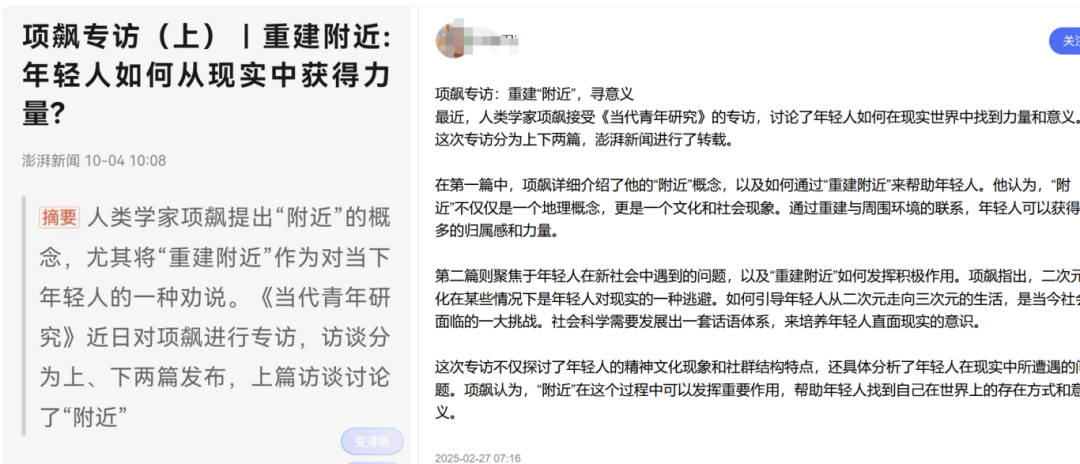
然而,這些談何容易。
在生產關係的總體性約束下,任何局部化的社區營造都面臨着矛盾,社區一旦試圖在經濟場域中自我維持,便不可避免地受商品化邏輯的侵蝕;若完全脱離市場,又要面臨資源枯竭。
同時,當下的中國社會,一方面國家通過科層制提供低限度的再分配,但科層理性日益技術化、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市場以靈活積累的方式吸納勞動力,卻不承擔任何再生產責任。結果是社會領域被壓縮為“剩餘範疇”,無法生成自主的公共性。而社區自治空間被“物業—業委會—開發商”的市場準治理結構所佔據,公共性議題基本被轉譯為“業主權益”或“消費維權”,缺乏階級視角。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隨着全球化階級和世界公民的興起,本土和全球化大城市的分離,如性別對立,身份政治這種全球化階級共享的政治議程帶來的撕裂並不是社區和“附近”這種東西的紐帶所能制約。
當然,重建共同體無論如何艱難,也必須往前探索。畢竟原子人真的抵禦不了整個工業社會熱寂後的大洪水。起碼,這個事情對中國人來説也不會比近代以來的艱苦奮鬥在物理意義上更難。
目前起碼我們可以總結一些已有的經驗和認知。首先所謂“再共同體化”,絕非迴歸被浪漫化的前現代的血緣—地緣,這在高度流動性的現代社會既不現實,也沒法成為根本訴求。
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的內在擴張性,其目標不僅在於瓦解社會聯結,甚至瞄準了社會聯結的最小單元:家庭,力圖將包括親密關係在內的都納入可計價的商品化範疇。當下激烈的性別對立現象,可視為這一商品化進程深入至最私密領域所引發的劇烈陣痛,或許預示着舊有親密關係模式在重塑。
其次,在整個社會的宏觀尺度上,我們必須正視單位制解體後遺留的巨大**“社會再生產真空”**。老國企單位體系曾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生產與再生產功能,儘管其本身也存在諸多侷限。任何尋求替代方案的嘗試,都必須思考如何在新的空間生產邏輯和社會經濟條件下,重建某種形式的“嵌入性”結構。
這種結構需要能夠有效承擔起部分社會再生產的職能(如照料、互助、情感支持、共享),為原子化的個體提供具有實質內容的社會性支持與歸屬感,使其生活與發展得以穩固“嵌入”於可靠的社會網絡之中。
最終,我們所討論的所焦慮的這些身份問題,紐帶問題,共同體問題,絕非僅僅是社會治理的技術性議題,**其本質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命題,觸及社會主義未竟的議程。**它要求將“共同體”的願景從懷舊中解放出來,重新置於對生產關係進行總體性變革的框架中來審視。
只有當社會不再是資本邏輯下空間產物,而是轉化為社會成員共同佔有、共同管理生產資料與生活空間,人與人之間的敵對狀態,方有可能得到實質性的緩解。這就意味着我們必然要追求一種新的現代生活圖景。
原子人會夢見大洪水嗎?也許會,只是在那場夢裏,沒有方舟,也沒有“我們”與“他們”的救生艇,只有無數座自以為安全的孤島在同一瞬間被同一道浪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