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紀 | 中國美學的“中國”與“傳統”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2分钟前
劉成紀|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6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自近代西方美學傳入中國,如何建構中國美學的話語體系就成為重大問題。像美在意境、美在境界、美在意象等提法,均是試圖通過一個概念對美進行本質主義式的定性判斷,而遺忘了美的存在語境、基本構成和展開狀態。事實上,面對無限多元的中國美學,試圖用一個概念或語詞統攝它的所有面向和全部意義缺乏任何可能性,這隻會導致美學史書寫的片面和狹隘化。像王國維所談的意境和境界,它們被使用的上限基本沒有逾出唐五代;宗白華用意境談中國藝術,其主題也是限於宋元以後的中國詩畫。但明顯的問題是,中國美學並不僅僅只有意境或境界,也不僅僅只涉及傳統詩詞書畫,更不僅僅只對解釋中國的局部歷史有效,一種美的普遍而連續的歷史,絕對不可能憑藉一個概念就可以得到充分掌握。當然,事實上,王國維、宗白華兩位先賢也並沒有試圖用簡單的概念為中國美學定性。像王國維,他談詩詞時用意境或境界,談金石學時用古雅,作《宋元戲曲考》則全然放棄了相關概念。與此一致,20世紀60年代後,宗白華開始研究先秦兩漢美學,這時他就棄用了意境,轉而談中國早期美學的“錯彩鏤金”等問題。
這種現象説明,**在當代視野下,將無限多元的中國美學史向一個概念集約,既無法有效闡明美和藝術的歷史,也存在着對前人美學史觀的誤判。**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美學史家開始從思想史、命題史、文化史和觀念史諸方面對中國美學進行更寬泛把握的原因所在。在這一背景下,即便仍用概念史的方式研究中國美學,它也不是僅關乎單一概念,而是要面對一個概念的家族或星叢。由此形成的美學是構成性的、框架性的,而非由某一概念或定性判斷一貫到底。但是,概念以星叢形式出現仍然無法形成對中國美學史的有效描述,這是因為傳統中國沒有美學學科,它涉及的問題並沒有被古人概念化。而今人圍繞中國美學設置出的種種理論和相關建構,則大多具有對歷史的強制性質。

劉成紀著:《中國美學的身、物、圖、畫》,文化藝術出版社
就此而言,可能一種更徹底的方式是存在的,那就是放棄一切建構中國美學史的理論企圖,直接看中國歷史到底能夠給予美學什麼。它既不是本質主義的,也不是構成主義的,而是還原主義的;是通過回到歷史現場,看到底是什麼構成了談論中國美學的基礎。也就是説,講中國美學,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對“何謂中國”的認識,其次是看它藉以棲身的傳統,最後是看它如何以美的方式展開自身。當然,在這個連續性的問題序列裏,如果古人對“中國”和“中國傳統”的認識本身就是審美化的,那麼,美學就不僅僅是其中的知識構成,而是瀰漫成了整個中國歷史。或者説,中國歷史既生成了它的美學,同時也接受了美學的建構。這樣,談論中國美學藉以棲身的基礎和傳統,也就是在談論中國美學本身。**以此為背景,中國美學將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視野,甚至一切歷史都是美學史,中國美學則相應反轉為“美學中國”。**近年來,我國學者常常會談到中國美學的天下觀或天下體系,原因概出於此。
何謂“中國”
那麼,何謂中國?這個問題的提出是近代以來由“西方”概念反向限定的結果。在傳統中國人的心目中,所謂中國就是天下。這個天下無所不包,由此就缺乏一個他者視角形成對其自身的反觀和鑑別。在這一背景下,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涉及歷史、哲學、文化諸層面,但奠基性的仍然是它的地理環境。如1902年梁啓超作《中國地理大勢論》,開篇就講:“中國者,天然大一統之國也。人種一統,言語一統,文學一統,教義一統,風俗一統,而其根原莫不由於地勢。”1947年,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簡史》中談中國哲學的背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它的地理環境,並以“大陸國家”與西方的“海洋國家”相區別。20世紀80年代,相關地理層面的國家認知漸趨成熟,如費孝通講:“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具體的生存空間。中華民族的家園坐落在亞洲東部,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西岸諸島,北有廣漠,東南是海,西南是山的這一片廣闊的大陸上。這片大陸的四面有自然屏障,內部有結構完整的體系,形成一個地理單元。”在歷史領域,1933年傅斯年在其《夷夏東西説》中開篇即講:“歷史憑藉地理而生。”這是以地理認知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前提。此後,中國在東亞作為獨立地理單元的特性被我國史學界反覆強調,如嚴文明講:“中國本身乃是一個巨大的地理單元,它同外部世界處於一種相對隔離或半隔離的狀態。這就決定了中國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嚴文明這裏所講的“土著性”,是借地理的一統為中國文化的自成一體提供依據,以反駁近代以降西方學者提出的種種“中國文化西來説”。美和藝術作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對它的本土屬性的認識,當然同樣離不開這種地理環境。
在現代,地理學幾乎是一切自然和人文科學的基礎。在這一層面談美學,大致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地理的景觀性或景觀地理學,如自然山川之美;二是區域性自然或人文地理環境對美和藝術的孕育。但是,這兩種關於美學與地理學關係的認識,均意味着美學仍外在於地理學。這是因為,無論地理作為審美對象,還是美和藝術的產生條件,都預示着它是附着性和衍生性的,其主體並不在美學的涵攝範圍之內。
那麼,到底什麼才構成了地理的審美本性?從哲學上講,人存在於自然地理空間之中,沒有人能否定他親歷的周邊自然山川的真實性,但是,人的感知只涉及對象事物的表象,而非本質。同時,人對自然地理空間的認識永遠是人在認識,它先設的主體性和觀念性永遠無法祛除。這樣,貌似客觀的自然地理,就依然是人認知能力的外化形式,人認識的過程也必然是對其重組和建構的過程。由此形成的自然空間秩序,則必然因為人賦予了它合理性並順應了人的需要而天然具有審美的性質。這就是一般所講的“認識論的審美化”。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就不再僅僅是自然地理的附着和衍生因素,而是構成了它的真正本質。換言之,人總是按照美的規律給予世界人化的造型,這種“人化”並不僅僅包括人的勞動實踐,而且也包括在認知層面被人的感官和觀念給予了適己性建構。這種適己性,就是審美性。
**以此為背景看傳統中國對其地理疆域及天下的認識,中國就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或文化的中國,而是在一般地理和文化背後潛藏着一個更加根深蒂固的“美學的中國”。**比如按照現代科學的地理認知,中國陸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千米,海洋麪積約473萬平千米,在這一廣袤的地理空間之內,分佈着美麗的山川河嶽和萬千自然景觀,這構成了一種地理或景觀地理學的事實。但在觀念層面,古代中國人賦予它的美卻不僅僅是景觀性的,而更在於其地理空間認知本身的自恰性。或者説,古人的空間地理認知愈是自洽,愈是完型化,便愈是會與實然地理狀況產生衝突,但這產生衝突和齟齬的地方,正是審美生長的地方。比如中國古代的天圓地方觀念。這裏的“圓”顯然並不是天本身圓,而是人面對無限蒼穹,只能以目光所及為自己規劃出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空間弧線;所謂地的“方”也不是地本身方,而是為了區隔天地而進行的差異化表述。再如四山模式和四海觀念。這種模式以黃河中游為中心,在四方設定出拱衞中原的四座山嶽,由此支撐的天下則成為一個四平八穩的涼亭式結構。但事實上,早期中國的地勢也是西高東低的,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淮南子·天文訓》);四山中的南嶽和北嶽長期存在非確定性。同樣,在四山之外,人們相信其生活世界的周邊被四個大海環衞,但北海和西海究竟在哪裏,至今仍存在爭議。又如它的中心-邊緣觀念。自《尚書·禹貢》始,天下中心被確立,即作為“有夏之居”的河洛或“中邦”,但這個中心顯然也不是地理學的事實,而是因為處於這個中心的人最早掌握了地理空間論述的主流話語。由此排出的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的審美階梯,則是這種審美地理學的外向展開形式。

最後是對這一地理框架的審美填充。自先秦至兩漢,中國人逐步將各種審美元素組入這一由天圓地方、四山拱衞、四海環繞、中心邊緣構成的審美化空間框架。其中,天地分有玄、黃兩種色彩;東方對應四季裏的春、五行裏的木、五色裏的青、五音裏的角、五味裏的酸,南方對應四季裏的夏、五行裏的火、五色裏的赤、五音裏的徵、五味裏的苦,西方對應四季裏的秋、五行裏的金、五色裏的白、五音裏的商、五味裏的辛,北方對應於四季裏的冬、五行裏的水、五色裏的黑、五音裏的羽,五味裏的鹹。這是一個既秩序井然又琳琅滿目、色香味俱全的審美世界。至於中央之地,則集中了這一審美世界中最重要、最美好的東西,如一年四季的夏秋之間、五行裏農業民族最珍視的土、五色裏最高貴的黃、五音裏最中正的宮、五味裏最香甜的甘,等等。這樣,本已審美化的空間地理框架,就藉助這些具體審美元素的有序置入,變得更加飽滿豐盈起來。這是一種盛宴式的地理學!
從地理學因人的前置性介入而天然具有審美屬性,到天圓地方的空間秩序、中心邊緣的審美階梯制,再到各種審美元素對這一架構的填充,可以看出一種圍繞美而形成的不斷累積和疊加的效應。至此,**中國美學的研究對象已經不再是中國人局部性的知識經驗,而是以滿天滿地的方式堆砌成了中國的全部。**或者説,它已從中國美學的局部問題轉換成美學中國的整體問題。但問題到此仍沒有結束。比如傳統中國講天下,天然意味着還存在着一個沒有觸及的超驗區域,這就是天上;講方形大地的周邊是四海,那也必然還有四海之外。對此,西方漢學家一般認為,中國人並沒有獨立於現實之上的天上或神的世界,“四海之外”也同樣是被虛置的。但事實也不盡然,起碼自殷商起,中國人就有其至上神(帝)。這個至上神雖然沒有獨立自存的世界,但它往往在與人類的交往中顯現威力。到漢代,這種威力被以神蹟的方式具象化,這就是上天向人間垂示的諸多祥瑞和災異。與此一致,四海之外也不是被全然虛置,而是被視為仙人的居地。這樣,如果説中國人對於審美空間的塑造更多是此岸性的,那麼,它起碼在天的至高和海的至遠之外,設置出了一種審美化的邊飾。前者是祥瑞呈現的靈暈之美,後者是仙人呈現的飄逸之美。至此,關於中國傳統國家地理空間的審美化建構,大致實現了完型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事實上存在着兩種中國的理解:一個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中國,對它的美的認識大抵只存在於景觀地理學層面;另一個是傳統觀念中的中國,它的美固然也表現於景觀,但那畢竟是表象性的,其更深層的美在於中國人賦予了他的世界一種空間結構的自洽性。這個結構看似不是自然本有的,但卻未必不是真實的,因為數千年來,中國人就生活在這個他們自我營建的世界結構之中,並相信它就是世界的實有樣態。這意味着人對世界的認識同樣存在着兩種真實:一是科學上的真實,二是觀念上的真實。當然,當人對真實的認識以人的認識或觀念為先導,這本身就是對真實的真實性的否定,但是現代哲學業已闡明,人對世界的認識永遠是人在認識,人的先導性永遠無法祛除,這就決定了任何真實均與事物的自存或實有狀態存在距離,均具有“信以為真”的性質。就此而言,真實更多是一個觀念問題,而非科學問題,所謂觀念史研究正是在此獲得了它的廣泛意義。同時,如果認識過程中人的先導性無法祛除,而為了達至真實又必須祛除這種先導,這就必然會將真實或真理問題逼向一個絕對的死角。它只具有邏輯的可能性,而不具有任何現實性。在這一層面,真實或真理就至多是一個可以無限趨近的問題,而不是可以真正實現的問題。當然,也正是絕對真實或真理的不可實現,美向世界敞開了它的無限領域。也就是説,在“人在認識”這一前提可以被祛除之前,人生存的世界永遠是一個“人化”的世界,一個需要被不斷祛魅的世界,一個前科學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前科學性,就是它的審美性。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傳統中國人賦予其世界框架的自洽性天然具有審美性質,而且直到現代乃至將來,審美依然會是人認識和把握世界的常態。
何謂“中國傳統”
在世界範圍內,可能沒有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一樣更加重視自己的傳統。從古至今,幾乎它的一切新變均要從歷史中尋找依據,均來自對已逝歷史的回溯和重温。那麼,什麼是中國傳統?現代以來,通過中西比較形成對中國傳統的差異化認識,幾乎成了一切中國人文科學研究的基礎。比如講中國文化重天人合一、重禮樂教化,中國藝術重抒情言志、重表現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西方處在它的反面。但是,這種非此即彼的差異化比較,對完整地理解中國傳統是有害無益的,因為它忽視了人類文化整體趨同的側面。這樣,在中西差異的背景上看中國傳統,至多隻能説它在人類共性的基礎上於某些方面顯現出了更加突出的特徵,而不能説它就是為中國所專屬的獨一性特徵。同時,受現代學科分類的影響,研究者往往囿於自己專擅的領域,只及一點不及其餘,這極易導致相關結論的碎片化和狹隘化。在這一背景下,為所有的比較找到共有的基礎就顯得十分重要。

那麼,這個共有基礎會是什麼,它對美學又意味着什麼?可以認為,人類作為一種需要通過勞動來維繫生存的物種,其包括美與藝術在內的思想和文化,均最根本地奠基於其生產方式。與此一致,自上古始,中國雖然有漁獵、遊牧、農耕等諸種生產方式,但農耕在其中佔據了主體和主流位置,這就是中國的重農傳統。當然,農耕並不僅僅意味着生產糧食、飼養家畜,它同樣也孕育美和藝術。像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時期,我國黃河流域進入早期農業的繁榮時代,這也是當時整個黃河流域陶器/陶藝大發展的時代。兩者同時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原因在於陶器製作以人對泥土屬性的洞悉為前提,而這種洞悉則奠基於農耕生產所建構的人地關係。也就是説,陶器是從泥土中生長出的器物,它像穀物一樣深植於泥土,是農業生產的天然伴侶。與此一致,中國人對美和藝術的認識也是農耕性的。其中,美關乎農業養殖活動,按《説文》:“美,甘也,從羊大。”這是將美的味覺和視覺感受建基於家畜飼養。與此相應,“藝”與“種”具有互文性。按《説文》:“藝(埶),種也。從丮坴,丮持種之。”“種(穜),藝(埶)也。”兩者都是指農業種植。又按《説文》段注:“周時六藝,字蓋亦作埶。儒者之於禮、樂、射、御、書、數,猶農者之樹藝也。”這意味着,在傳統中國人的觀念中,不僅日常審美經驗和藝術製作從農業生產中衍生而出,而且代表更高階文明的“六藝”也被視為農業的“產品”。
以此為背景,中國整個屬人的世界和相關人事活動幾乎均被與農業生產關聯了起來,從而使農業性成為中國性的直接指稱。比如:
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滕文公上》)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禮記·王制》)
君子擇人以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説苑·雜言》)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其惡。(《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韓詩外傳》卷十)
朝庭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庭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論衡·程材》)
在傳統中國等級森嚴的社會,士夫與農夫、食祿與食田、樹人與樹田、尚仁與司農、君子之道與農夫之耕、朝廷與田畝、刀筆與耒耜、文書與農業之間,存在着難以跨越的社會等級和價值差異,但如上類比性論述卻説明,兩者不僅存在着本質性的關聯,而且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一切社會階層和精神價值的上升,均離不開農業這個基礎。所謂“三尺講台一畝田,種桃種李種春風”,農耕以其深植於泥土的本性,既種出了穀物,也種出了文明和文化,同時也種出了中國美學和藝術。
農業產生活動,它的主體是農夫,它勞作的對象是土地,這種勞動方式形成的最基本關係是人地關係,所謂中國社會的農業基礎則最根本地體現為以土地為基礎。西方學者認為,在世界範圍內,“中華文明尤以其與土地的關係緊密而聞名於世”,正是在強調土地之於中國文明的奠基性。那麼,中國傳統農業,除了在人地交互中生產出了穀物,衍生出了美和藝術,以及文化與文明,土地本身之於中國美學到底又意味着什麼?
**首先是對土地生命屬性的體認。**在18世紀,受中國傳統農業經濟模式的影響,法國重農學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觀點,即在人類的一切生產活動中,唯有農人的勞動才能真正增加人類的財富。這是因為,手工業對自然材料的加工,只是改變了事物的外觀形式,並沒有帶來事物內在性質的變化,因此不會對人類財富真正起到增進作用。商業流通更是如此,只是將作為商品的現成品在人與人之間進行了傳遞活動。與此相比,農業生產既不是加工已有物料,也不是流通現有財富,而是人從土地得到了額外的饋贈。它來自土地的自生產,產出的是一種全新的產品。基於這一點,在人類的一切生產活動中,唯有“土地永遠是一切財富首要的、唯一的來源”。顯然,土地之所以能夠以外在於人的方式為人類增加財富,原因在於它自身有生殖力,這就觸及中國美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即土地及周遭自然世界並不是僵死的,而是一個活躍的生命體。按《説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從這種釋義可以看到,“土”的本性就是它的生命性。它之所以能“吐生物”,在於它包含生命的元質。與此一致,“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這説明“土”與“生”具有互文性,是生命最基本的載體和表徵。以此為背景,《説文》釋“地”雲:“地,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這是説“地”是“土”的呈現形式,它一方面對內包藴生命的元質,另一方面對外陳列、展開生命的物化形式。據此不難看出,談中國美學如果必須談它的生命精神,必須談“天地之大德曰生”,必須談一個生意氤氲、大化流行、生生不息、鳶飛魚躍的生命世界,那麼,它就必然以中國傳統農業對土地生命屬性的體認為基底。董仲舒雲:“生之性,農之本也。”(《春秋繁露·五行逆順》)這既涉及經濟學層面人如何生存的問題,也涉及中國美學生命精神的本源問題。概言之,所謂農本,不僅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之本,同時也是中國美學乃至哲學的精神之本。

**土地,除了它的生命屬性,另一個對中國美學形成至深影響的屬性是它的非移動性。**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對土地這一特性的討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關乎哲學的,如“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道德經·第三十九章》),這是講土地因它的寧靜不動而顯現道性;如“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莊子·大宗師》),這是講大地以它的恆在為人提供安居;“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管子·版法解》),這是強調土地以它的包容和堅固為萬物提供生存基礎;如“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雲”(《禮記·樂記》),這是以天地動與靜的協調來表徵禮樂。二是關乎人之現實生存的,主要涉及土地的不可移動對人的財富觀念和民性的影響,如“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無二慮”(《呂氏春秋·上農》),這是説農民以土地和穀物為財富,這類財富的難以移動是其安土重遷、固守家園的根本原因;相反,商人的財富(如金錢)多是便攜式的,這直接導致他們輕視遷徙,結果“國家有患皆有遠志”(《呂氏春秋·上農》)。三是關乎民族性的,主要涉及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比較,如西漢晁錯《守邊勸農疏》雲:“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漢書·晁錯傳》)。現代以來,研究民族關係史和社會學的學者也注意到這一點,如札奇斯欽講:“農業民族是定居在可以耕作的土地之上,視土地為他們最主要的財產,或生命線……但在遊牧社會里,人是要隨着家畜,逐水草而移動的。因此他們的財產都是動的,沒有不動產的觀念,更沒有土地的私有。”費孝通也講:“農業和遊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於土地的。遊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裏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裏……大體上説,這是鄉土社會的特性之一。”
從上引文獻可以看到,土地的不可移動直接導致了農業民族對其腳下土地的固着,進而影響到其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財富觀念。在文學藝術方面,中國文學所表現出的懷鄉情結、故園意識、遊子思婦主題及至愛國主義傳統,大抵也是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在人的情感世界的映像形式。與此相反,商人往往因為“重利輕別離”而成為其中的反面角色,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天性輕薄,而更多是因為其財產便於攜帶,適於遠遊。以此為背景,在哲學和美學方面,土地的寧靜和素樸為中國哲學和美學提供了最基本的精神底色,它的虛懷、質樸、仁厚、包容、堅固往往成為美好人格的象徵。由此昭示的理想化生存則是一種安居於土地的生存方式,如老子所言:“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第八十章)後世,中國士人的歸隱意識和中國美學的山水田園傳統,也大抵源自土地因其不可移動而給人帶來的精神依靠和安全感。
所謂農本,可以化約為以土地為本,但對於具體的農業生產而言,它所面對的並不僅是土地本身,而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一個龐大的自然生態系統。那麼,中國人如何面對土地之上的自然萬物?對此,中國哲學首先將人植入這個由植物、動物、溪流、湖泊、山川構成的龐大自然系統中,認為土地是它們共同的生命本源和歸宿。如《孔子家語·困誓》雲:“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汩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在這個由泉水、百穀、草木、禽獸排出的自然序列中,人並不是其中特異的品類,而是其中的組成部分。換言之,它們在共同秉持泥土生命本性的意義上是同質的,在相互關係上是共生的,在價值上是平等的。莊子所説“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正是強調了人與萬物的共生性及由此導出的眾生之間的無差別性。《莊子》又講:“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莊子·馬蹄》)則是將人與萬物的共生、共處作為人生理想。
**就此看中國人的自然審美,它就不僅僅是人在自然景觀中獲得感性愉悦的問題,而是有其深層的觀念基礎,**即它首先是審美者對土地生命本性的體認,其次是以人與萬物的共生、共處、共遊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出共情關係,即“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基於這種間性或雙向互賞關係,人就應該遏制自己的主體性,儘量站在自然的立場上看待自然,即“以物觀物”或“以自然之眼觀物”;其情感表達也是追求最大限度遏制代自然立言的衝動,而讓自然説它自己,即“以自然之舌言情”。
可以認為,在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建構上,中國美學所表現的謙卑是無與倫比的。這和農業民族對其生命來處的體認有關,也和土地因其不可移動而為人提供的安居有關。當然,這種對腳下土地的謙敬和對每一種自然生命的尊重也會限制人的審美視野。如美國漢學家艾蘭曾注意到,中國早期文獻中寫到水,很少有西方式的大海和狂風巨浪,而是更多囿於人的農業經驗。如其所言:“使中國哲人興味盎然的水是現於大江、小溪和農田周圍的灌溉溝渠中的水。這是雨和由降雨形成的水潭,尋常普通而非無邊無涯,它滋養了生命併為眾人所體驗。”這裏的小溝小渠、水潭溪流,正是中國傳統田園詩畫和園林的原生形式,它意藴深遠但缺乏西方大海的崇高氣象。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基於農耕經驗的自然興趣也並沒有妨礙他們對遠方世界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更加審美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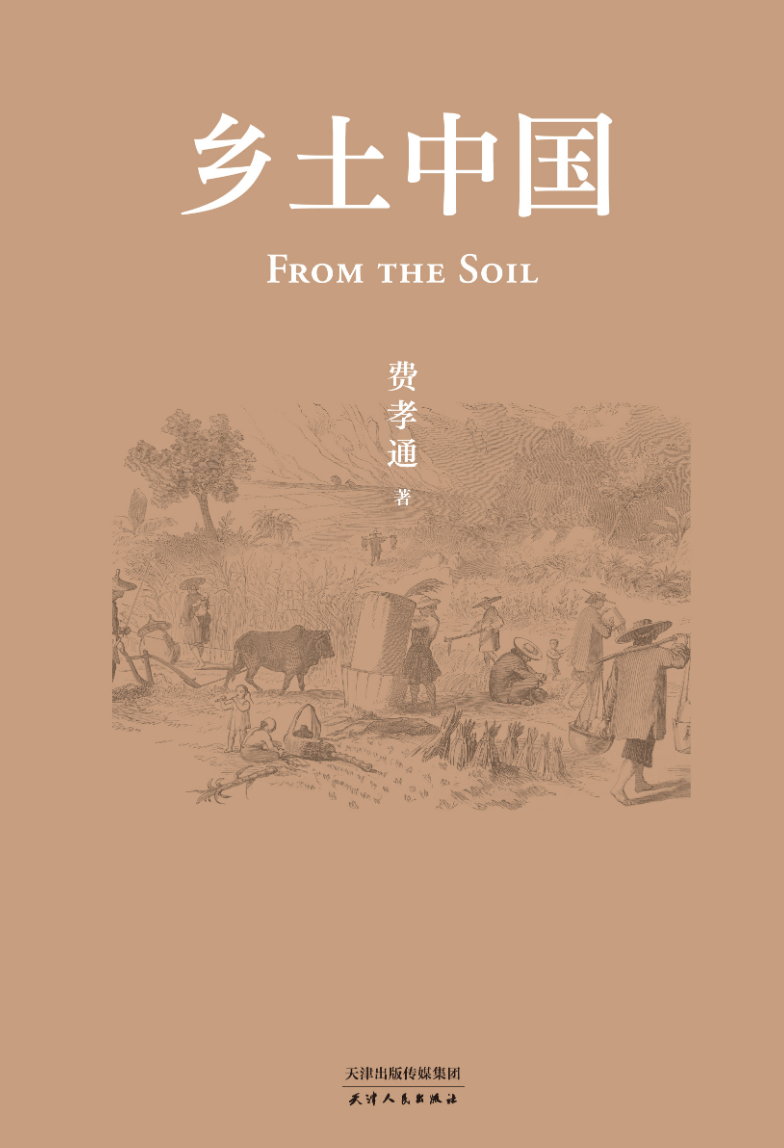
中國傳統農業制度是將人束縛於土地的制度,如費孝通所言:“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這種對土地的黏着或固着必然使人將自我視為天下的中心,並從自我出發看待外部世界。至於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之所以是審美化的,原因無非是兩點:一是在認知層面,它天然雜合了人對外部空間世界的想象。由此形成的世界肯定不是世界本有的樣子,而只可能是按照人的主觀意願或美的規律被造型的樣子。二是在價值層面,人為了證明自己當下生存的合理性,總是樂於將自己當下的狀態視為最美好的狀態。農夫或農夫式的民族由於從未走出過腳下的土地,缺乏他者的比較,更是如此。像中國歷史上的洛陽,它之所以被視為“地中”,並被認為最集中體現了天地、四時、風雨、陰陽對人類的加持,無非是因為這裏是中國早期的農業中心。以此為中心,它由近及遠排出審美化的文明階梯,即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同時,將五行、四季、五色、五音、五味等諸多哲學和審美元素鋪排在它的中心和四方。這種自然秩序無疑也不在客觀的自然世界本身,而是被用審美的方式賦予了合理而自洽的形式。這就是由人對土地的固着所生髮出的世界觀,也是傳統農耕文明為中國美學作出的持久而獨特的貢獻。
中國美學的展開
**中國美學是傳統農耕文明的產物。農耕生產對土地生命本質的發現,為中國美學植入了內在深度。土地的不可移動一方面為中國人提供了精神安居,另一方面則外發為一種審美化的自然觀和宇宙觀。**這極易給人一種印象,即傳統中國是鄉土中國,它的審美主體是農民,它的審美場域是農民居住的村落及周邊鄉野。但弔詭的是,在中國美學史上,農民卻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這種審美的權力,他更多是和他居住的村落一起,成為外在於鄉村的文人士夫的審美對象。那麼,這個外在於鄉村的視角是什麼?顯然它並不在鄉村本身,而在與鄉村對立的城市。也就是説,任何審美活動都需要一個他者視角,當農業、鄉村成為審美對象,已天然預示着審美者將自身抽離出鄉村,以城市視角形成對鄉村的回望和反觀。據此看中國美學的展開,除了需要認識農業、鄉村之於中國美學的奠基性,更需要注意的是城市視角對這一基礎的超越。與此一致,在中國這個以農為本的國度,雖然農業的價值被高度重視,但鄉村卻從來沒有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相反,這個中心在城市。這是一種相當奇異的現象。它提示人們,雖然中國美學奠基於農耕文明,但這一定位卻來自城市視角的反向建構。就此而言,談中國美學只談鄉村而不談城市,就終究與它的本相隔了一層。下面我將首先補足這一環節,然後看城市如何在與鄉村的互動中共同展開了中國美學。
**現代形態的中國城市美學研究,是被新時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激活的。**此前,中國美學家對意境、境界、意象的討論,對中國美學人間性、生命性和山水花鳥詩畫的研究,均具有鄉村、農耕或自然的底色,乃至揮之不去的泥土的影子。但是人作為一種羣居動物,作為社會關係的總和,聚集是他的本性。這種聚集可以是家庭形式、村落形式,更可以是城市形式。也就是説,在現代人的城鄉觀念中,雖然人們總是強調兩者的對立,但事實上從鄉村到城市或者從自然到社會是順向生成的。如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所言:“古往今來多少城市都是大地的產兒。它們都折射出農民征服大地時所表現的勤勞智慧。農民深翻土地以求收穫作物,農民把畜羣趕進圍欄以求安全,農民調來水源以求滋潤田禾,農民建造谷囤糧倉以求貯存收穫物……所以從技術角度看,城市不過是把農民營造大地的這種種技能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城市的產生建基於人的羣性或社會性,而這種本性是人與生俱來的,這就意味着城市史與人類史具有等長的性質,甚至人類史就是城市的生成史。仍如劉易斯·芒福德所言:“遠在城市產生之前就已經有了小村落、聖祠和村鎮;而在村莊之前則早已有了宿營地、貯物場、洞穴及石冢;而在所有這些形式產生之前則早已有了某些社會生活傾向——這顯然是人類同許多其他動物物種所共有的傾向。”在此,劉易斯·芒福德甚至將城市出現的動因推到了自然界“其他動物物種”,這看似有點誇張,但起碼説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城市雖然以巨型的人工造物形式出現,但它奠基於人甚至動物的聚集本能,本質上是精神性的;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文明古國都不缺乏它的城市史,需要調整的只是研究者看待自身歷史的角度。
就像西方學者從城鄉關係看城市的產生,對於中國城市美學的認知同樣要從鄉村和農耕傳統講起。而且,鑑於農耕傳統之於中國美學的奠基性,這一傳統與中國城市建構的關係可能遠較西方要更為緊密。比如在中國古代,帝王貴胄、王公大夫居住於城市,但重農思想卻是由他們提出來的。作為這種思想的儀式表現,每年立春時節,他們都要在王城的東郊舉行農業祭祀和親耕活動,以宣示人間萬事以農為先,並藉此為天下作出示範。至今,中央政府每年年初均要發佈關於“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仍是在延續這一傳統。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早期社會的城鄉關係中,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美學上的主導地位可能比其他國度都要強化,這是因為,圍繞城市形成的財富聚集,並非來自城鄉之間的自由貿易,而是來自周邊農民的地租和貢賦。按《尚書·禹貢》,自夏代以來,中央王城與天下九州的關係就是貢賦關係。此後,農民無償向處於城市的各級官府納糧、交税、服役則成為常態。比較而言,基於貿易的城鄉關係是相對鬆弛的,而地租、貢賦卻是強制性的,更能凸顯城鄉之間的主從關係。當然,這種關係得以形成的前提仍是土地所具有的財富溢出效應,即土地除滿足耕種者及家庭的基本衣食需要外,仍可以憑藉其生殖力帶來財富的盈餘。如《呂氏春秋·上農》雲:“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這“益”的部分形成對城市的財富輸送和供養,城市則靠對鄉村的搜刮、盤剝將自身武裝成物態化的審美奇觀,同時成為美和藝術的製造、流通和傳播中心。

從美學角度理解這種中國式的城鄉關係,可以認為,一方面鄉村或農耕經驗構成了中國美學的基礎,另一方面,城鄉之間的權力主從關係,則又必然意味着城市在其中佔據了主導位置。也就是説,**鄉村生成城市,城市反向主導鄉村,基礎性和主導性可以作為對兩者關係的基本定位。**以此為背景看中國城市美學,它首先涉及城市自身的審美構成,然後涉及它對周邊鄉村的統攝。就第一點而論,按照《周禮·考工記》提供的王城佈局,中國早期城市不能説沒有商業交易,但它在其中只佔極小的分量。比如周代王城主體建築為“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格局,其中的“市”不但在排序上居於末端,而且處於最不顯眼的位置。後世,中國傳統都城的商業性逐漸提高,如漢唐時期的東市西市,宋代汴梁城的街市和夜市等,但權力和象徵意義仍是壓倒性的。這意味着對中國城市美學史的研究,擺在第一位的並不是它在商業屬性上與現代如何會通,而是要把握禮制這個核心。同時,它和周邊世界的主從關係雖是政治性的,但根本上還是基於它從自我出發的天下觀念。如《尚書·禹貢》按照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排出的五服體系,就是以文明或審美階梯制的方式為其統攝天下提供了正當理由。據此,理解中國傳統城市美學,不僅要關注它自身的禮制特性,而且也應注意到它和周邊世界構成的關係也是禮制性的。
至於看待世界的方式,則在城鄉之間有一個重要的置換,即居於鄉村的農夫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以對腳下土地的固着為前提的,而一個王朝的天下觀念則是以王城為中心看世界。在此,農夫的個體或村落中心就置換為基於王權主體的王城中心,後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公共性。但顯然,兩者又是一體同構的,所謂王朝視野不過是對農夫視野的放大,就像王城不過是村落的放大一樣。
**城市與鄉村,兩者既具有一體性,又具有主從性,這意味着在一個統一的社會有機體內部,鄉村的價值在於它可以提供什麼,城市的價值則在於它佔有了什麼。**比較而言,城市會因為它對權力、財富和美的佔有而穩居於社會價值鏈的頂端,鄉村則恰恰相反。如司馬遷雲:“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史記·貨殖列傳》)這顯然把農業及相應的鄉村放置在了價值鏈的末端。以此為背景,城鄉之間的對立就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永恆張力,而逃離鄉村、嚮往城市則必然主導人的價值選擇。如司馬遷所言:“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記·貨殖列傳》)這裏所講的“富厚”之地是城市性的,社會各階層蜂擁而起的“歸富厚”“奔富厚”浪潮同樣指向城市,城市則因此成為慾望性審美的強化象徵形式。從中國歷史看,歷代王朝的更迭無不遵循了起於鄉野,最終雄居於王城的道路,歷代士人的功名利祿之路也無不沿襲了同樣的路線圖。這涉及人的政治雄心、天下情懷或自我實現等問題,但慾望性的審美取向是其根本動因。
當然,在這種主導性的“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浪潮中,也並非不存在相反的力量。自先秦始,中國社會就有穩定的隱士史,逃離城市、返歸鄉野是其基本精神取向。後世,山水田園詩畫更賦予鄉村作為士人精神家園的性質。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傳統的隱士和山水田園書寫,均有隱在的城市視角。也就是説,書寫隱士者本身大多並非隱士,而是居於王城的史官和士夫;歌頌山水田園之美者也大多並不真正生活於鄉村,而是站在鄉村之外形成對鄉村的回望和旁觀。比如在中國文學中,可能真正算得上鄉村書寫的只有農事詩一類,至於田園詩則不過是詩人用景觀性的鄉村寄寓其人生理想。於此,鄉村並沒有構成詩人生活的現實,至少在精神上他仍然處於實然的鄉村之外,這就是所謂的城市視角。在中國歷史上,可能只有陶淵明試圖在實然的鄉村和生活理想之間尋求統一,但他最終失敗了,併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充分進入城市,可以達至慾望滿足,但精神不得自由;充分迴歸鄉村,可以實現精神自由,但又必然因此陷入貧困。這種矛盾,使中國傳統士人的生活態度長期在兩者之間往復擺盪,即一方面“形在江海之上”,另一方面“心存魏闕之下”;一方面行走於“滾滾紅塵長安道”,另一方面感嘆“田園將蕪胡不歸”。在這種慾望滿足與精神自由的博弈中,他們最終找到了一種兩者兼得的方式,即生活的城市化和精神的鄉村化,在佔有王權給予的功名利祿和獲得個人的精神自由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這就是所謂的“中隱”。如白居易所言:“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中隱》)但是,在由此昭示的城鄉關係中,城市仍然佔據主位,仍如白居易《中隱》詩所言:“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如果將這裏的“秋山”和“春園”視為鄉村元素,那麼,它至多是處於城市的近郊,只能算作城市生活的外在配置物,而不是真正的鄉村。以此為背景,自西晉王康琚作《反招隱詩》始,“大隱”開始進入中國士人視野,到唐宋則成為中國隱逸思想的主流。這種隱居既不是陶淵明式的直接置身於鄉野,也不是白居易標榜的在城鄉之間晃盪,而是直接做城中的隱者,即“大隱隱朝市”(《反招隱詩》),或者“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蘇軾《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與此相應的則是城市文人園林的發展。就這種園林體現的城鄉關係看,它是在城市內部置入鄉村元素,引人在塵囂之中體驗田圃雲水之思。於此,**農業、鄉村不再是城市的對立物,而是被全面納入城市,成為城市生活的組成部分。這是中國傳統城市最終徹底主導鄉村的寫照。**當然,作為“城中村”形式出現的園林,更不是真正的鄉村,而是士人意象化的鄉村追憶和想象。它被納入城市的過程也是徹底將“鄉村”審美化的過程。
在唐宋時期,與城市文人園林進一步呼應的是農業生產的園藝化發展。一個重要的證據是當時的農書弱化了對鄉村農業生產經驗的記錄,開始大量涉及士人閒暇時在園林中的種植活動,甚至有喧賓奪主之勢。如石聲漢所言,在唐宋時代,文人雅士們“把農書的許多‘譜’、‘錄’,從原來(與農業生產)確有一定關係的花卉、果樹,演變到筍譜、石譜、香譜;由相牛、相馬,演變到相鷹、相鶴、相貝,乃至於古錢譜;由養魚演變到蟹譜等,都摻進了‘農家’類裏。這個不良風氣,明末發展到頂點:一些閒得無聊的文士,在悠閒生活中,寫了不少欣賞瓶花、花市,甚至於飲食店趣味的書,也都收在‘農家之言’裏面,像高濂的《遵生八箋》之類。”

石聲漢是中國現代著名農業史家,他將這種農業生產的園藝化稱為“不良風氣”,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趨勢卻使農業真正成為美學。據此不難看出,中國傳統農業本身具有美學屬性,如它對土地生命本性的體認和從自我出發的天下觀念,這對中國美學而言是奠基性的。在此基礎上,城市作為鄉村力量的集結和湧現形式,它一方面自身成為美和藝術的主角,另一方面則反向重建了人對鄉村的認識,從而使中國美學實現了從鄉村視角向城市視角的轉換。進而言之,這種轉換並不僅僅是對鄉村的回望或反觀式審美,也包括在城市內部重建一種意象化的鄉村,即園林和相關園藝活動。
**如果對中國美學做出一種概觀式把握,它大體就存在於這種從鄉到城、再從城到鄉的迴旋式運動中。**這一過程看似是對農業審美價值的不斷提升,但唯有不斷回溯它的本源才能真正發現並激活它的生命。這是必須反覆強調農耕文明之於中國美學奠基性的原因所在,也是講中國美學必須首先澄清其農業背景的基本理由。但是如上文所示,單單講清其農業背景仍然無法真正認識中國美學,因為它的歷史中存在着城市這一更趨強勢的對立物。這樣,作為一種為中國美學重置歷史基礎的學術努力,可能首先要完成中國傳統農業美學和城市美學的雙重書寫,然後才能通過對兩者互動關係的辨析,構建出中國美學的完整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