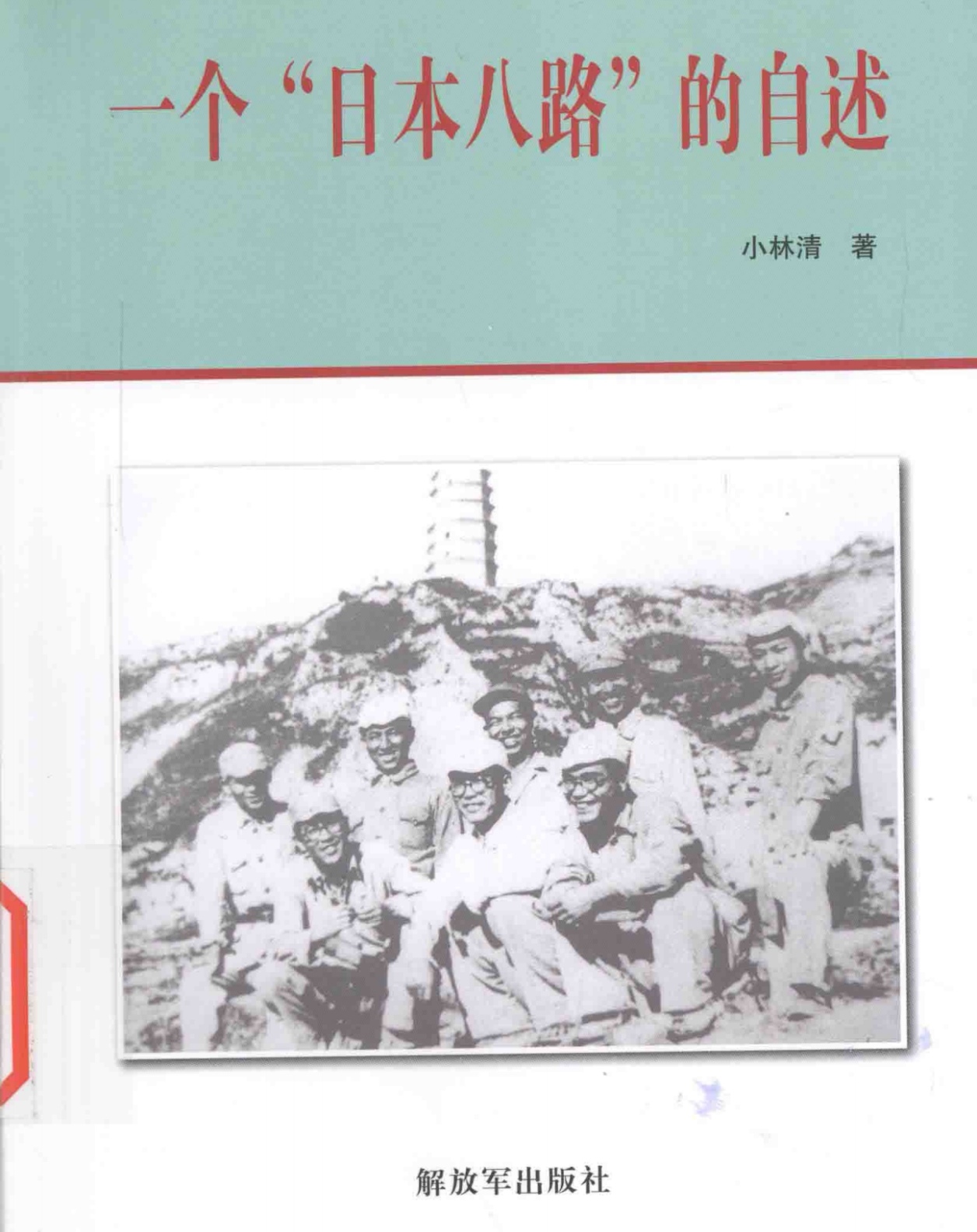從獸到人之路——讀《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1小时前
抗戰勝利80週年前夕,説説自己昨天讀小林清著《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一書的若干感想。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與任何剝削階級的軍隊一樣,不但是對國內外人民進行鎮壓與屠戮的暴力機器,內部也實行森嚴的等級制對士兵進行殘酷的剝削與野蠻的欺凌。
據1939年在駐山東威海日軍服役的二等兵小林清回憶:
“在作戰或‘掃蕩’中,長官們命令士兵把中國老百姓的糧食、有用的東西都拿走,把鍋打爛,把活的東西全殺死,把房子燒燬。而且還藉口為了試驗膽量,強迫不願殺戮的士兵去殺害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凡任務沒有執行好的,都要受懲罰。” 而日軍內部,士兵不但動輒挨打受罵,而且糧餉也經常被以各種藉口剋扣。士兵每頓口糧約一斤,不但質量逐年下降,還常被長官剋扣,私賣給日本僑民以牟利。剋扣口糧的藉口是:“要訓練萬一吃不飽肚子時也能作戰的能力,實行減食。”
士兵的薪金不但每月扣去“貯金”(如一、二等兵月薪8.8元,要以“貯金”形式強迫儲蓄3元,只到手5.8元),還要購買“公債”,不買就影響升職。
在這樣殘酷的剝削下,加之日本國內因為戰爭而加重的經濟危機,士兵們的家庭日益貧困化。小林清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來自北海道一户貧農家庭的二等兵長谷川戰死了。在給長谷川燒屍開追悼會的時候,中隊長山本中尉拿出一封信,是長谷川的父親寫給山本中隊長的。信中説:
“我們全家陷入貧困飢餓之中,飢寒交迫,已無生路。雖然這樣做對不起我那孝心的兒子,但是,還是請中隊長想法讓我的兒子長谷川快點戰死吧,除了指望他那筆戰死撫卹津貼外,再也沒有別的生活出路了。”
小林清説:“這封信,連山本中隊長都沒有勇氣拿出來給長谷川看。直到長谷川戰死了,才拿出給大家看。中隊長把這封信給我們看的時候,那長滿橫肉的雙頰上也流下了兩行眼淚。”
那麼,這個流下眼淚的山本中隊長是個同情士兵的“好長官”嗎?
不。小林清説:
“我們中隊有一名叫平田的新兵,他家裏匯來了三十元錢,家中給他的信上寫得明明白白,然而,收到信後很長時間連匯款單的影子也見不着。平田不敢向長官追問,自己又偷偷地寫了一封信,問家裏是否真的寄來錢了。家裏回信説的的確確寄來了,知道他在軍隊裏吃不飽飯,家裏沒有勞動力,就賣掉了僅有的一塊田,把賣田的錢給寄了三十元。平田收到信,非常傷心,拿着信到野戰郵政局查問,結果知道匯款單和錢已被中隊長山本中尉偷偷地領走了。他氣憤極了,回到中隊找中隊長講理,中隊長説平田玷辱了皇軍的‘榮譽’,把平田吊在馬棚裏毒打了一頓。大夥看了不忍心,前去求情,中隊長才放了平田。平田當時忍氣吞聲沒説什麼,但在氣憤之餘;於當天夜裏,就用刺刀切腹自殺了。”(同上,第38頁。)
因此,山本為長谷川流的那幾滴眼淚,或許不無一點兔死狐悲之感,但在我們看來更多的不過是惺惺作態而已。而且很可能也正因為看到了這些部屬家裏的苦況,才更讓這些下級軍官們明白留在底層是何等悽慘,所以更要加緊蒐括士兵,加緊屠戮掠奪中國百姓,好立功、升職、加薪、往上爬,獲得更多的特權、利益,以免自己和家人也陷入長谷川、平田那樣的境地。所以小林清指出,日軍的大隊、中隊指揮官甚至掌握軍營小賣部的士官長,向日僑倒賣軍需(因為軍隊可以得到不及市價1/3
且質量有保證的煙酒、日用品等),截留士兵家裏寄來的匯款單……以中飽私囊大發橫財,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而在階級覺悟被喚醒之前,日軍內部的這種剝削壓迫雖然也令士兵們不滿,日軍對中國百姓的燒殺淫掠,雖然也令一部分士兵感到不適,但並不會讓他們真的起來反抗。相反,不少人倒是會像中隊長山本那樣產生更強烈的“要向食物鏈頂端爬”的想法。小林清説自己雖然在軍中捱打受欺,恨透了長官,但心裏仍然認為自己是“武士”,要“為天皇盡忠”。看到中國老百姓被日軍屠殺,他那時似乎並沒有多少共情,更多的是擔心這會激起中國人更強烈的反抗,使戰爭長期化,“拖延我們日本士兵回國的時間”(同上,第30頁)。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就是這樣將人訓練成野獸,而且是以法西斯的內卷邏輯,讓他們一天天變得更為貪婪與兇殘。
那麼,小林清為什麼能幡然醒悟,成為一名“日本八路”呢?
答案再簡單不過了:他被八路軍俘虜了。
你也許會覺得:“這不是廢話嗎?還用你説?”
可是,最簡單的答案往往有着最深刻的內涵:人之所以能夠被改造,社會之所以能夠被改造,不僅是因為人們對現狀的不滿,更重要的是因為對將來有了堅強的希望與信念。英國前首相“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為資本主義辯護,並不説資本主義多好,而是説沒有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小林清也是如此。他在日軍裏受盡欺壓,看到日軍對平民的暴行,對戰爭的前景也日益悲觀,但又能怎麼樣呢?他在那個處境中,不知道也不能想像還有什麼別的出路。然而被八路軍俘虜之後,小林親身體會了八路軍是怎樣對待俘虜的,親眼看到八路軍與老百姓、八路軍的幹部與戰士是怎樣的關係,他才真正明白世界上確實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軍隊、另一種戰鬥、另一種活法。
剛被俘時,小林清是極為抗拒的,甚至有過“被俘可恥,只求速死”或找機會逃回日軍的想法。他確實逃跑過,被民兵抓了回來。而且,一名後來被俘的軍曹告訴小林,中隊長已經將小林作為戰死者處理,火化了他的“屍體”並將他的“骨灰”與陣亡通知書都寄到家裏了。這就徹底斷絕了小林清逃回日軍的念頭。小林清自己説是因為憤慨於中隊長竟對士兵生死如此草率,但我想可能還有一個原因:一個被軍官判定“陣亡”的士兵竟然歸隊,犯下錯誤的軍官該如何免責呢?恐怕只好讓你真的“陣亡”了。
但這些只是加重了小林清對日軍的失望與對戰爭的悲觀。而真正令他轉變的,是他看到老百姓像對待親人一樣對待八路軍,而八路軍也爭着幫老百姓幹活兒。有一次,小林清拿了老鄉家一雙筷子去用,八路軍管理員向老鄉賠禮道歉,不顧老鄉一再推辭,拿出錢來一定要賠償。敵工科科長張昆沒有罵小林清,而是教育他説:“這是八路軍的紀律:不拿羣眾一針一線。”小林清從此明白了:八路軍不但有比日軍遠為嚴明的紀律,而且這個紀律決不是像日軍那樣靠打罵來維持。
小林清還寫道:
“八路軍五支隊的王彬司令員、王文政委、仲曦東主任、五旅的吳克華司令員、高錦純政委、歐陽文主任等都來看望我,啓發教育我,幫助我覺醒。而且每次來,他們詳細瞭解我們的生活情況,問我們是否習慣,有什麼要求等。這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温暖。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誠懇的態度,就像一家人一樣。這是我在日本軍隊中從來沒有見過的事情。
他們是司令員、政委、主任,要是在日本軍隊中,應該是校級以上的軍銜了。但是他們卻穿着極其樸素的軍裝,簡直和士兵沒有兩樣。他們的一舉一動總是表現着一種旺盛的戰鬥意志和必勝的信心。他們過的是世界上各國軍隊中最低標準的生活,使用着最落後的武器,進行着最艱苦卓絕的戰爭。他們只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保衞自己的祖國,拯救自己的同胞,反對法西斯侵略。
總之,八路軍是一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崇高信仰,有嚴格紀律,有堅強的戰鬥力的軍隊。
這樣的軍隊,日本沒有,世界上任何地方也不會有,只有中國才有!
他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他們意志堅強,胸懷開闊,態度和藹,感情真摯。他們的言行深深地打動、温暖了我的心。我開始認識到他們的行動是正義的,我應該同情和支持他們的鬥爭。
我終於把自己的真實軍銜和獨立步兵第十九大隊的情況都向仲主任和張昆詳細地交代了。
張昆高興地對我説:
‘這就是你覺醒的開始!’”(69—70頁)
1941年,小林清在延安的“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後,與其他34名日本學員一起參加了八路軍。
在膠東戰場,小林清培訓八路軍學習使用日式機槍與擲彈筒,向日軍作戰場喊話等宣傳工作。在1942年反“冬季大掃蕩”戰鬥中,為了掩護幾百名老鄉突圍,小林清與另一名日本同志原田架起機槍,向日本侵略軍開火……(159—164頁)
而令小林清印象最為深刻的卻是這樣一件事:
1944年,小林清對日軍碉堡作完戰地喊話返回途中,住在一户“堡壘户”家裏,半夜遇到偽軍進村搜查。這家的姑娘叫趙玉芳,20來歲,是個婦救會長。她制止了想要拿槍拼命的小林,把他按在炕上,在偽軍上門時,又繫着衣服絆紐,裝作剛起牀的樣子,指着矇頭躺在炕上的小林説:“這是我男人,病了。”趙大叔又拿了一隻大母雞和一疊鈔票塞給偽軍,才將他們打發走。小林很感謝趙玉芳一家。趙玉芳卻爽朗地説:“應該的。等勝利了,我們還要感謝你們這些‘日本八路’呢!”
小林清寫道: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又一次救了我,又一次用國際主義無私無畏的崇高精神教育了我。這樣的黨和人民當然無敵於天下。這種精神鞭策我在為國際主義正義而戰的道路上,邁開大步前進!”(232頁)
多年前我讀過一篇報道:一位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日本老人指着“珍愛和平,反對戰爭”的標語對講解員説:“我對這兩句話有意見。”
“什麼意見?”講解員不冷不熱地問,心想是不是碰上找事兒的了。
“珍愛和平沒問題。反對戰爭,這要分析。和平是被侵略破壞的;戰爭卻是從反抗開始的。靠和平能把侵略者趕跑嗎?不是用戰爭才打敗日本鬼子的嗎?”
講解員楞住了:這是日本人嗎?怎麼比我受的教育還“紅”啊?
我依稀記得這位日本老人是與小林清有類似經歷的“日本八路”——小林寬澄。
以這兩位小林同志為代表的“日本八路”,已經不是簡單地、消極地“反戰”,而是積極投身於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投身於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事業。
促成他們的巨大轉變的,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而從小林清書中的敍述看,促成這一轉變的主要因素及邏輯是:
1.一開始是法西斯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這是他們最切身的感受。
2.然後是戰場的失利與其家庭日本國內生活的困苦——長期來看,這是一個不斷增長的因素,但短期來看,會受戰局波動的影響:如日軍打了些勝仗,這個因素的作用就會減弱,“皇軍不可戰勝論”就會有市場。
3.被俘後受到共產黨八路軍全面系統的教育和引導,包括他們自己對兩支軍隊不同本質的切身體會——如前所述,這是最有決定性的因素。小林寬澄到韶山參觀時,操着山東口音的漢語説:“我本來是個日本鬼子。是毛主席、共產黨讓我成為了一名反法西斯線士、一個‘日本八路’。”
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讓人們不但在理論上更在事實上看到光明在哪裏。
這就是此書令我再次確認的一條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