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有凌雲志,重上花果山——致黑猴問世一週年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41分钟前
文 | 天書
三天銷量突破一千萬的神話彷彿還在昨天,黑猴問世就已來到一週年了。一年的時間裏玩家沒等來真正的DLC,最終等來的是剛剛在科隆展上官宣的《黑神話鍾馗》。雖然但是,不留戀於已經收穫的風景,打點行裝重新出發,也挺好。

毫無疑問,時至今日還有大量的玩家仍然沒走出黑猴出世帶來的衝擊。打出真結局,跟着動畫重走完西遊路,聽着《未竟》中唱着“名注齊天夢一般”,我想會有不少人跟我一樣,既滿足又悵然。
出手即是頂尖3A水平的遊戲本體,堪稱國漫新標杆的《六樣情》動畫,由馮驥親自填詞的多首意境高絕的配樂,以及最後的未竟之路……我悵然的是,為什麼等到我這個80後已變成中登,這樣的東西才出來?又還要等多久,更多的黑猴才能出現?
很多單機玩家從很早以前就堅信並期待着中國3A時代終有到來的一天,但與其説是因為相信中國的市場規模和發展速度,就認為這一天必然會到來,到不如説是因為大家都有一着種不甘——不是因為相信會出現,而是認為一定要出現。
沒有什麼事是每個人都坐等其成就能發生的。從《大眾軟件》創刊到《血獅》暴雷,從《仙劍》系列作為“中國遊戲之光”長期霸榜到著名檄文《誰謀殺了我們的遊戲》面世,中國玩家因追求“自己的”好遊戲而一次又一次碰得頭破血流,但就是心有不甘。如果不是因為不甘,怎麼會總是自討苦吃,歐美日韓的遊戲伺候中國玩家,這福氣不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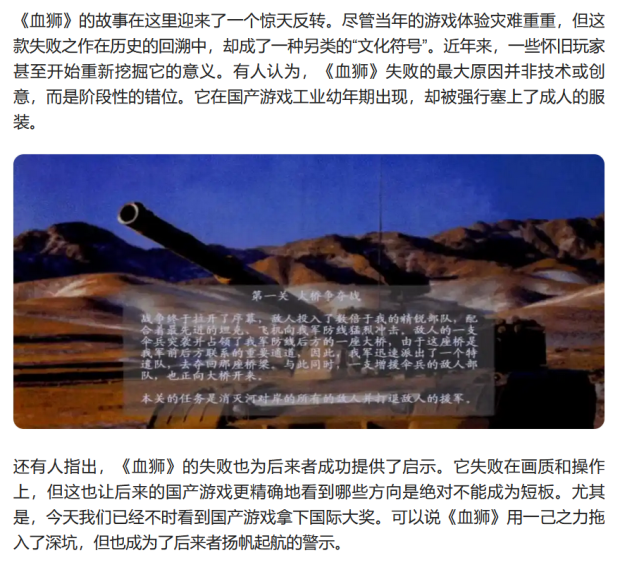
寫出《誰謀殺了我們的遊戲》的正是馮驥,時年25歲。對07年中國遊戲業的反思只是他的起點,甚至還遠沒走入低俗。又過七年之後面對《鬥戰神》的失敗,看者可以認為是徹底證明國內大環境不行,也可以認為馮驥的出走未嘗不是一個新契機。但對身處局中之人來説,只有走出去,做下去,未來才有一線生機。
直到今天,我們的社會中還是有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有一批人總是執着於去做“自己的東西”,為什麼社會要以此為榮譽自豪。他們習慣把中國的手機,中國的汽車,中國的電影,中國的遊戲……等等都冠以“愛國營銷”和“民族情緒”,彷彿唯有如此貶低和否定,才能掩藏他們被映襯出的庸碌。
**即使只談市場經濟,有人選擇去做一些有抱負的東西,也是市場能運轉下去的必要條件。**正如《誰謀殺了我們的遊戲》質問的首先不是為什麼沒有好遊戲,而是為什麼彼時的中國遊戲行業一片血色。如果每個從業者都選擇甘於當馮驥文中自嘲的“狗東西”,那就算是氪金遊戲行業,一直不變革也會走向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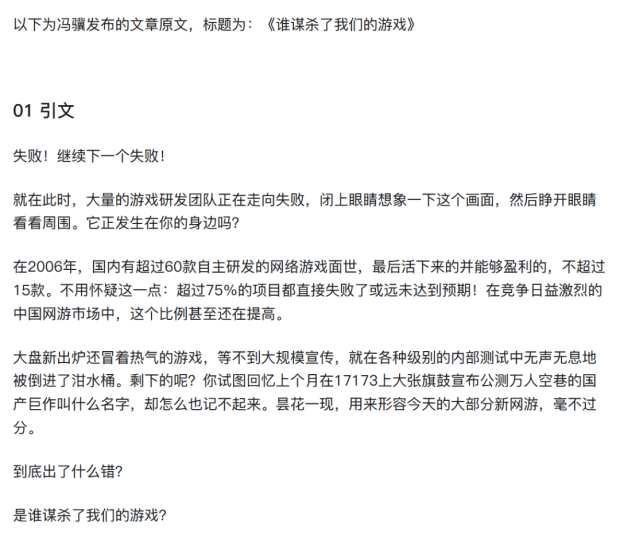
何況,總會有些人去追求高於基本生計之上的回報。就像《黑神話》的另一位主創楊奇,其過往言論所體現的三觀和馮驥差異很大,但這不妨礙兩個人對做出一款單機大作都有着高於其他的信念。這也是我們的社會得以維持運轉和發展的基礎。
現代社會的人們信念常常參差百態各有不同,就算我國頭三十年,社會觀念也遠説不上各方面統一,更不用説市場經濟的當下。即便三觀再不同,只要還有着一分做好一件事情的擔當和抱負,只要起碼還相信在腳下這片土地做好一件事情能獲得回報,就會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組成分子。個體的思想往往光怪陸離,但多數人的社會實踐總能指向同一個方向。
回到《誰謀殺了我們的遊戲》出現的2007年。彼時的中國人均GDP不過2461美元,如果按今天一些人喜歡唸叨的“月薪三千沒資格談宏大敍事”理論,那麼別説夢想做自己的遊戲,當時的中國人玩遊戲都得算大逆不道了。然而事實是,今日中國得以在各領域取得的發展突破,多數早在那時,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經因在這片土地上不斷實踐和奮鬥的人打下了基礎。
我們的社會中總有些人用“有奶才是娘”的思維方式衡量一切,所以他們不理解很多事情,他們認為哪裏好就去哪裏是天經地義,他們認為只有發達國家的人才配談愛國。但他們沒法解釋如果人人都“有奶才是娘”,那社會是如何實現進步的。所以他們總是想把中國的發展歸於“模仿”、“剽竊”、“搭便車”,“發達國家的施捨”等等。
他們忘了,除了“有奶就是娘”,還有另一句話叫“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我們不評判這兩句話哪句更能代表人類社會的多數狀態,但起碼,一個社會的發展終究多數時候還是靠“不嫌母醜不嫌家貧”的人們在推動着。
從07年再往前看,像馮驥這批生於80年代初期的人,他們的成長期面臨的精神危機某種程度上完全不亞於前幾代人。世界上先是蘇東解體和冷戰結束的劇變,然後是美國步步壓迫的陰雲,內部是八九十年代的社會亂象以及思想觀念的空前混亂。而且因為信息傳播的便利和對外交流的擴大,讓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發展差距被放大到無以復加。
如果按“有奶就是娘”的世界觀,中國在那會早該亡國了。不開玩笑,“戰爭爆發怎麼辦”、“中國再次被侵略怎麼辦”是那時很多少年期80後們的精神危機。無需諱言,那些年也的確是移民高潮。結果,目睹了社會的腐敗落後混亂失序,經歷了嚴重精神危機後,很多人不但沒被種種陰暗將精神徹底擊垮,反而在彼時就堅定了對未來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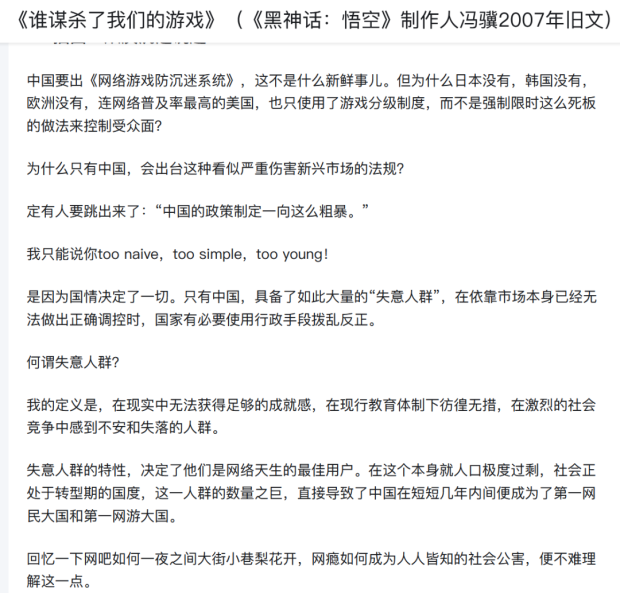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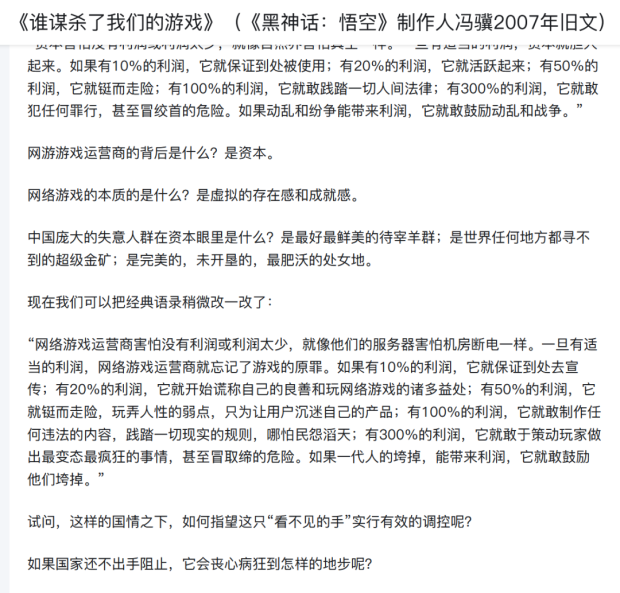
**這種信念的基礎,首先就是前面説的,中國玩家那種不甘。**我們可以一直玩別人做的遊戲,但我們也有想玩自己做的遊戲的權利;別人的文化產品再好,終究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精神需求和心靈歸屬;今天人有我無的東西,無非因為別人比我們發展早,只要肯趕超,就沒有需要頂禮膜拜的神話。這種不甘正是最基本的人之常理。
進一步説,只是這種樸素的、狗不嫌家貧式的不甘,還不足以讓馮驥們進化成後來的鐵血戰狼。就如我們可以相信沒有馮驥,楊奇一樣可能做出頂級國產遊戲,但那大概率不會是以《未竟》收尾的黑神話。
前段時間《開放時代雜誌》的一篇文章將郭帆馮驥和韓寒郭敬明這兩類80後代表加以區分,認為前者這類ACG愛好者和發燒友羣體**是“技術浪漫主義”的一代,是中國的“百科全書派”,**他們持續地學習和“成長”,從未“成熟”,拒絕長大。(ACG是動畫,漫畫,遊戲,再加上泛幻想類的文學和各種文化產品就是ACG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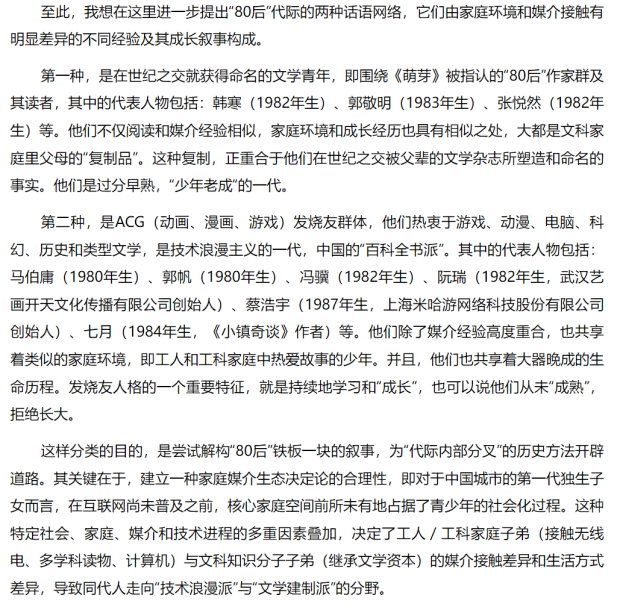
這的確是從80後開始,河殤思維顯著退潮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只從教育經歷看,80一代接受的歷史和革命政治沒比之前的代際有重大不同,強度甚至還有所不如。但隨着ACG文化和互聯網興起,得以讓80一代從三觀塑形期開始就比上幾代人更深入的“開眼看世界”。
在以“百科全書”般的姿態汲取泛ACG文化的過程中,瞭解了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光明面也就同時瞭解到了陰暗面,也常常會獲得很多可以和學校教授的歷史和唯物主義教育互相參照印證的內容。
這當然不是説ACG愛好者的世界觀都一致,就像馮驥和楊奇這對搭檔世界觀迥然不同,ACG圈子不管當年還是現在,世界觀都可以説是光怪陸離,極度複雜分化。但ACG羣體會產生大量和馮驥三觀類似的人,卻幾乎可以説是一個必然事件。
這裏我們不得不拿出一個已經被公知弄髒了的詞——“知識分子”。以這個詞本該有的意義來説,擁有“百科全書”視野的ACG愛好者們,**毫無疑問是一種掌握先進信息媒介工具和傳播方式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雖然在單一領域可能不如傳統定義中的知識分子那樣專精,但在知識結構,綜合視野,思維開放程度等方面往往有着時代給予的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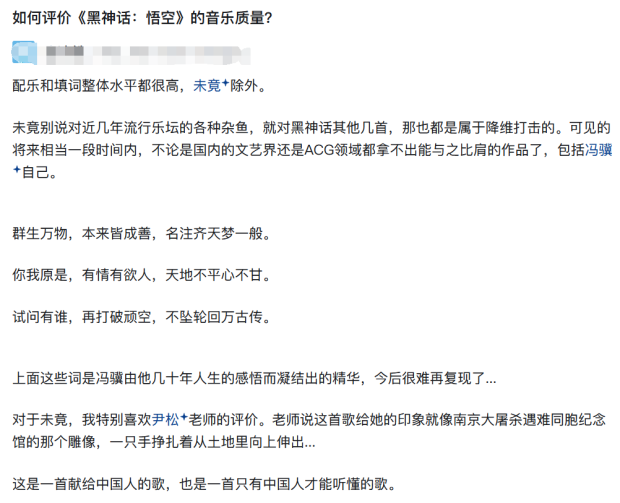
不得不説,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一些明顯沒比其他人擁有顯著知識優勢的人長期把持了知識分子一詞的代表權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比如從前的公知和現在的董宇輝之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陣營中開知識分子研究先河的葛蘭西那裏,知識分子這個身份不為任何羣體所壟斷,所有人都可以是知識分子,因為最簡單的勞作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術要求和相應的知識。
只不過社會分工以及對知識掌握的程度不同,並非所有人都能執行知識分子的職能。葛蘭西進一步化分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所謂傳統知識分子是指超越階級,或者不關心階級,不關心國家政治生活的知識分子,如教士僧侶,文人世家,閉門不出的書齋先生等;而資本主時代到來後,有機知識分子開始大量出現,他們伴隨着新階級的產生而產生。
他們不像傳統知識分子那樣只關心知識本身,而是用知識深度參與、塑造社會觀念和大眾認知。他們傳播的並非是價值中立的知識,實際是將階級意識形態轉化為大眾知識,並且是一個階級奪取文化領導權的主力。
用葛蘭西的話説,有機知識分子就是統治階層的觀念代理人。所以一個知識分子只要符合“有機知識分子”的特徵,**他就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一定是為了某個階級而發聲的。**這就剝掉了很多“知識分子”身上那種超然的光環。
在當時的意大利,葛蘭西看到了太多曾經的同路人最終倒向了法西斯主義,變成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陣營的有機知識分子。作為意大利共產黨的創立者,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理論和有機知識分子理論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屬於無產階級,能傳播灌輸無產階級意識,為無產階級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有機知識分子出現。
從有機知識分子的定義看,ACG愛好者們天然處於賽博公共空間中,只要不是完全不關心現實的重度死宅,**可以説每一個ACG愛好者都是有機知識分子。**他們從ACG愛好出發,熱衷於交流,討論,發散,構建和輸出屬於自己的知識和話語體系,從賽博世界影響介入三次元空間。毫無疑問,今天我們的社會文化早已被ACG知識和話語體系深度影響改變了。
現在,來到了問題的最後。有機知識分子要為階級發聲,那麼ACG愛好者們為哪個階級發聲?
就像前面説的,ACG圈子的世界觀是光怪陸離的。在今天來説,不管是在階層取代階級且高度分化的韋伯語境中,還是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語境中,簡單的階級劃分都已沒法在文化屬性上準確的定義一個人。從小鎮青年到江浙滬獨生女,在技術媒介普惠下,大家都很容易共享同一套ACG文化經驗。
但從黑神話,黑哪吒這些產品的爆發式擴散來看,**整個ACG圈子越來越追求文化主體性的趨勢是明顯的。**從電影到遊戲,這些ACG文化的領軍人物們在做的事情也都是在塑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主體性,以及基於共同體的最大文化公約數。這無疑是技術媒介進一步普惠的結果。
ACG愛好者們作為一種有機知識分子,隨着在社會中越來越普及,結構越來越深入基層,其“有機”的成分也在不斷深入,成為一種新時代的“紮根羣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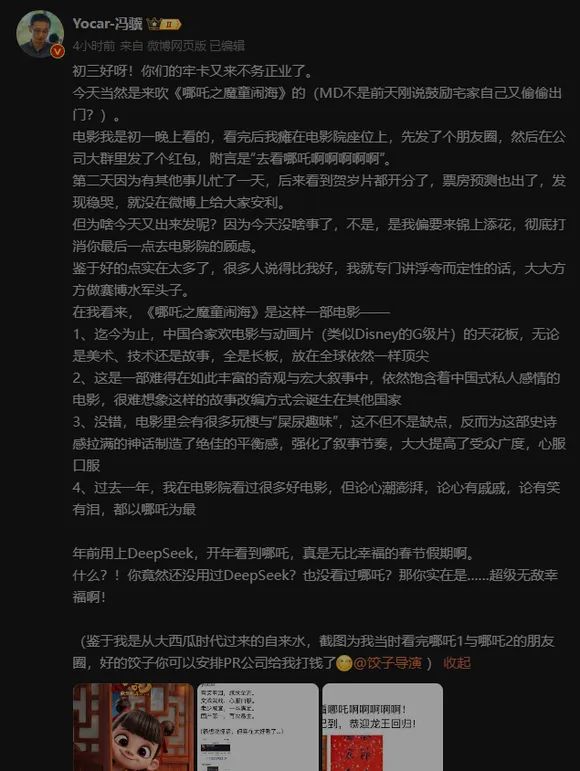
不過,如果討論只是停留到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ACG愛好者們為文化建構主體性,為共同體文化而發聲這一層,那這反而是危險的。西方社會在上升期,毫無例外都有這種文化主體性和公約數的建構,甚至説如果只是追求內部階級調和,那指向的將是何種道路歷史早已演示過了。我們與他們,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主體性建構當然要有根本性的不同之處。這種不同之處是什麼?
答案就是“未竟”,是“試比天高”,是“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每一個新中國人,骨子裏都有抹不去的最大政治公約數。是這個公約數,讓各個階級,羣體,民族凝聚在一起,組成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中國。這個公約數的底層邏輯,始終指向着最廣大人民羣眾。
改開後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和世界形勢變化,這個底層邏輯間或被人擱置淡忘,但每到中國社會的緊要關頭迷茫關頭,它總會展露出來,指引着我們未竟之路在何方。這個公約數的底層邏輯不光是主體性的,也是革命性的,它是紅色的。

所以,ACG愛好者作為新時代的有機知識分子,越是規模擴張,越會更多承擔起為這個最大政治公約數而進行文化建構的歷史責任。馮驥煉化楊奇,正是這一過程的生動寫照。

當然,這種建構不會是整齊劃一的,不會是樣板式的。ACG一代的文化經驗多樣而不羈,並不受傳統知識範式的規訓,在建構文化主體性的同時,也可能會摻雜着強烈的個人ACG情懷烙印。就好像馮驥和楊奇始終繞不開當年的《鬥戰神》和白骨夫人,以至於在黑猴發售之初引發了不算小的爭議。

所以,ACG一代在未來繼續參與文化主體性建構的過程中,大概仍然離不開這樣那樣的爭議。這種爭議會被放大,會被攻擊,會陷入吉列的豆蒸。但一個有機知識分子到底是服務於哪一個階級,哪一個共同體,歷史實踐總會給出一個公道的答案。眼下最重要的,首先是要準備好出發,去行該行之事。正如那句話,“踏上取經路,比抵達靈山更重要”。
一切都只是開始。黑猴還只有一個,破球和哪吒也不知道何時才有競品。悲觀無用,樂觀太早,重構主體性的道路註定不會平靜。就像這幾個作品,取得了多大成功的同時,也承受着多大的非議。
丟失主體性太久之後,很多人就會執真為假,以為找回主體性如黑猴的假結局一樣,是給自己戴上禁箍。尤其這禁箍的底色還是紅色,他們更加恐懼戴上了之後,就失去了自我。

**實際上,這紅色恰恰不是禁箍,而是在輪迴中指引我們找回“我是誰”的意根。**還記得打通真結局之後如何拿到意根嗎?一週目通關之後是拿不到意根的,要開啓二週目再入輪迴之後才能拿到。
紅色固然深刻於我們的主體性之中,但它也是隱遁的。在這個全球紅色低潮久矣,舊有秩序將盡的節點,時代正呼喚着更多的人成為天命之人。只有經歷重重磨鍊,跨過萬般考驗,我們才能尋回它的真意,真正繼承那未竟的意志。

取經之路永遠未竟;未竟,就永遠有未盡的無限可能。永遠不要灰心和絕望,我們總可以像前輩們一樣,打破一切,重新出發。
正所謂——
久有凌雲志,
重上花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