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理論被質疑,該如何理解生命運轉的底層邏輯?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科普中国子品牌,倡导“溯源守拙,问学求新”。1小时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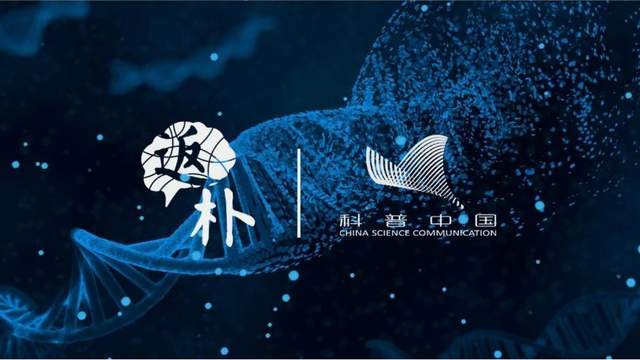 對生命本質的探索是人類永恆的追求,而不同的生命觀會引領我們走向不同的認知方向。“基因決定論”長久以來被視為解釋生命運作的核心理論,讓人們以為基因是生命的絕對主宰,掌控着生命的一切奧秘。然而,隨着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理論的侷限性逐漸凸顯。菲利普・鮑爾所著的《生命傳》(How Life Works),以獨特的筆觸梳理了生命科學的發展脈絡,打破了基因決定論的迷思,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生命認知維度。
對生命本質的探索是人類永恆的追求,而不同的生命觀會引領我們走向不同的認知方向。“基因決定論”長久以來被視為解釋生命運作的核心理論,讓人們以為基因是生命的絕對主宰,掌控着生命的一切奧秘。然而,隨着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理論的侷限性逐漸凸顯。菲利普・鮑爾所著的《生命傳》(How Life Works),以獨特的筆觸梳理了生命科學的發展脈絡,打破了基因決定論的迷思,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生命認知維度。
近日,《生命傳》作者、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菲利普·鮑爾,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研究員吳家睿教授,以及財經作家吳晨圍繞《生命傳》展開深度對話,共同探討生命科學領域的認知革新與複雜生命的運作邏輯。
對話中,菲利普·鮑爾從基因的動態編輯、多層級系統的湧現性,到生命體的目的性與進化中基因調控機制的創新等方面深入闡釋了生命並非“機器”的核心觀點;吳家睿教授則從系統生物學視角出發,強調生命的“湧現性”與層級組織對複雜性的支撐;此外,他們還探討了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等技術的潛力與倫理邊界,以及AI在生命科學中的角色定位。對談以英文進行,以下是經過翻譯的三位嘉賓的對談實錄,內容有刪減。
1
認知革命
關於生命如何運轉的新解讀
吳晨:歡迎來到系列對話節目,我是吳晨,擔任本次對談活動主持人。我們今天對話的是《生命傳》的作者菲利普·鮑爾,他是科學作家,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也是歐盟委員會合成生物學專家團的成員、 BBC 科學的故事的欄目出版人。同時我們也請到了吳家睿教授,他是上海交通大學主動健康戰略與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科學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國家蛋白質科學研究(上海)設施的主任,也是中國科學院系統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主任。我之前跟菲利普、吳教授聊天時就説過《生命傳》這本書非常棒,但對於領域外的人來説,要真正理解其中的細節並不容易。鮑爾先生,你能向中國的觀眾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再簡要説説《生命傳》這本書嗎?
菲利普·鮑爾:關於這個問題,我的部分回答會包含在自我介紹裏。1988年,我加入《自然》(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在那裏待了大約20年,負責物理科學領域的編輯工作,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自然》工作期間,我處理物理科學領域的論文,其中一些會與生物學有交叉,可能涉及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我們能瞭解到所有正在發生的科研動態,每週都會得知那些被接受的生物學論文的情況。
《自然》打算發表的論文中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某項研究發現了一個基因,我們原本以為它只與人體或生命的某一方面有關,結果卻發現它竟然還與另一些截然不同、完全出乎我們意料的方面有關聯。過了一段時間,我鼓起勇氣問:這到底意味着什麼?我記得負責那篇論文的編輯當時説:“我們也不清楚。”似乎在基因的作用方式中有某些層面是我們一直沒能完全搞懂的,它們並非只承擔單一職責,不像我們以為的一個基因對應一種性狀,反而更像是以一種更微妙、更復雜的方式在發揮作用。這就讓我對基因到底在做什麼、又不做什麼產生了一連串疑問,這些疑問在我心裏盤桓了很久。
後來,我有幸在2019年夏天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系統生物學系待了三個月。但我之前的那些疑問並沒有真正得到解答,恰恰相反,我意識到未知的問題其實比我想象的更多,我們對生物學的認知正在發生的轉變也比我預想的更深刻。
細胞和分子層面的生物學知識幾乎每一處都和我過去的認知不一樣。比如蛋白質的性質和形態,我們總説蛋白質是控制人體一切活動的分子,但實際上,它們的作用機制、功能以及形態往往和我們學到的大相徑庭。
所以説,那些我們曾經在教科書裏讀到的,或者上學時學到的常規知識似乎每一個方面都在被改寫。在我看來,這些新發現共同勾勒出了一幅與傳統認知截然不同的圖景。傳統觀點認為,我們生命所需的所有信息都編碼在DNA分子裏,就像讀取計算機程序或一本書那樣,通過解讀DNA就能“構建”出生命。但如今我們對“生命如何運轉”的理解早已不是這樣了。而這本書正是試圖解釋這種轉變的原因,也想探尋一些關於“生命如何運轉”的新解讀。
吳晨:吳教授也同樣深耕這個領域,請你分享一下讀完這本書的看法。
吳家睿:能和菲利普交流這本關於生命的書,我感到非常榮幸,我很高興地發現,他的觀點和我的看法頗為相似。就在2020年,我寫過一本名為《生物學是什麼》的書,我在書中也有類似的看法:問題並不在於基因是生命的決定因素,而是要理解生命。生命背後有着更為複雜的故事。
首先,生命充滿了隨機的“噪聲”和不確定性,所以我們不能將生命等同於機器,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其次,生命是複雜的。這裏的複雜性指的是,當生命從分子層面到細胞層面,再到組織、器官層面,不同層面之間存在着各種聯繫,並且會湧現出新的特性。比如説,從分子層面到細胞層面,細胞會呈現出一些新的特性,而這些特性是無法直接從基因序列中解讀出來的。這正是複雜系統所具有的特性。我們常説,這種湧現出的新特性是複雜系統的體現,這也讓我們明白了早期還原論的侷限性。
我過去在大學接受的訓練也認為只要理解了分子、基因序列或是蛋白質結構,就能清晰地解釋、理解生命的運行機制。但當我真正投身研究工作,尤其是在系統生物學領域時,我才意識到,我們不能一味地依賴還原論,而應該從複雜系統的層面去思考生命。生命科學領域有很多研究都是如此:它並非找到一個結論就能宣告結束的領域,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會不斷有新的事物被創造出來,我們也能不斷給出新的解釋,但我們無法像在物理學中那樣,找到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定律。
 紀錄片《人體內旅行》劇照。
紀錄片《人體內旅行》劇照。
2
生命並非機器
一切遠比提取DNA信息複雜
吳晨:我以前在《經濟學人》工作過,記得幾年前我們有一期封面文章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編輯出“聰明基因” 並植入孩子體內嗎?這樣一來,競爭就會隨之產生。那些富豪、超級富豪或許能培育出新一代聰明孩子,因為他們掌握了基因工程技術。但我從菲利普這本書裏瞭解到,事情並非像人們想得那樣簡單。書中引用了《自私的基因》這本書,這是一本非常暢銷的書,你説它或許讓人們對基因的理解產生了一些誤解。能否再跟我們多講講,為什麼我們不能簡單地只盯着基因?
菲利普·鮑爾:首先,我想強調一點,生命並非機器,我們也不是機器。這一點絕對是核心所在。一旦我們理解了生命的運作方式就會發現,整個人類歷史上,我們從未造出過一台能像我們自身這樣運作的機器。把我們和機器這樣類比是極具誤導性的。
我們曾經認為,在我們的DNA中,只有部分片段是用來合成蛋白質分子的,其餘部分實際上沒什麼作用。那些參與合成蛋白質的片段,可能只佔我們整個DNA的1%到2%,而剩下的部分,有時被人們稱作“垃圾DNA”,但現在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的DNA進行着非常豐富的活動,基因所攜帶的信息在轉譯成蛋白質之前可能會被改變、被編輯。同一個基因實際上可以產生多種不同的蛋白質,而且在我們體內,同一種基因會在不同類型的細胞中(比如皮膚細胞、肝細胞、肺細胞)產生不同的蛋白質。這也呼應了吳家睿教授所説的,生命是一個開放系統,不同層級有着不同的規律。即便在蛋白質合成這個層面,生命也是一個開放系統:細胞或組織類型所攜帶的更高層級的信息,有時會反過來影響基因會合成哪種蛋白質。所以説,這遠比單純“讀取DNA中的信息”要複雜得多。
我們現在確實在考慮進行基因編輯,甚至可能對人類進行編輯,或許是出於醫療目的,考慮這麼做有充分的理由,但我認為,這也讓“每個人都更清楚基因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變得愈發重要,因為未來會出現一些影響我們所有人生活的決策。而且,現在已經有一些公司開始宣稱,如果你做體外受精(IVF),他們可以對胚胎的基因組進行測序,然後告訴你哪個胚胎最好、哪個會最聰明。甚至已經有公司開始做出這樣的承諾。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非常危險,因為事情根本沒那麼簡單。
我們擁有的任何複雜性狀,那些我們很在意的東西(比如智力、身高),甚至像眼睛顏色這樣的性狀,都不像我們想得那麼簡單。任何複雜性狀往往都受多個不同基因的影響,而每個基因的影響都非常小。由於存在太多不同的影響因素,我們所能得到的也只能是概率。
我們知道基因對智力有影響,人們對這種影響的程度存在爭議,但個體之間的差異可能約有50% 與基因差異有關。與此同時,那些看似與智力相關的基因,其實還在發揮其他作用。大多數基因都會影響不止一種性狀。這非常複雜,就像吳家睿教授所説,這是一個我們尚未完全理解且完全無法預測的複雜系統。因此,我們所掌握的只有這些概率,這絕非簡單的“信息讀取”。而且,對於像智力這樣的性狀,我們顯然不能説“這個基因是智力基因”。
吳晨:我記得你提到過(吳教授也提到過“湧現性”),在不同的尺度下,會出現新的現象、新的事物,而我們不應把這些簡單歸因於最基礎的層面。你能談談對生命這個複雜系統及其湧現性的理解嗎?
菲利普·鮑爾:在我看來,生命的運作存在一系列不同的層級:從分子、基因、蛋白質,到我們細胞內的分子集合。其中有一整套我們過去並不瞭解的層級,是由分子構成的複雜集合,它們不像機器,反倒更像一個個“聚會”或“委員會”,在我們體內共同做出“決策”。
再往上是細胞,細胞聚集形成不同的組織,這一過程本身就很複雜。組織構成器官,最終形成我們個體,而個體之上還有生態系統。每個層級都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則,這些規則並非完全由更低層級的情況所決定或限定。因此存在一種信息的“過濾”:有些細節對於更高層級而言並不重要。這正是“湧現性”的核心:當系統邁向更高層級時,低層級的部分信息會被捨棄或變得無關緊要。細想之下,這也是像我們這樣複雜的生命體能夠運轉的唯一方式。
如果我們的生命活動依賴於每個分子在精確的時間出現在精確的位置,完成它該做的工作,那這種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正如吳家睿教授所説,生命充滿了“噪聲”。生物學中存在大量的隨機性。分子並非總能出現在它們“應該”在的地方,也並非總能保持它們“應該”有的結構,但即便如此,生命依然能持續運轉。
因此,在生物學中,生命活動不依賴於所有事物都處於正確位置,這一點其實至關重要。任何物體、任何物理實體的行為,都不取決於所有單個電子、原子,甚至亞原子粒子的具體活動,如果真的依賴這些,世界根本無法正常運轉。
而且在這些更高的層級上,事物有了其特定的意義。我是説,我現在望向窗外,看到了一棵樹。要知道,對這棵樹來説,重要的是葉子的存在,葉子是綠色的,因為它們能吸收光線。在更高、更大的層級上,存在着一整套正在進行的過程。比如樹枝必須足夠堅固、堅硬以抵禦風力,而這也並不依賴於每一個單獨的原子。
事實上,萬物皆是如此運作,你的身體也存在這種湧現性和一系列層級,生物學領域也不例外。在生物學中,正因為其系統極其複雜,所以具備這種抵禦低層級細節干擾的穩健性就顯得尤為重要。要知道,在這漫長的歲月裏,這個極其複雜的系統時刻都在發生着各種變化,卻依然能持續運轉下去。
吳晨:吳教授,你之前似乎提到過,在生命進化過程中細胞間區室化的形成為實現分工創造了條件。你能再詳細解釋一下嗎?關於生命是如何運作的,以及複雜生命體是如何運轉的,你是否同意菲利普的觀點,或者有不同的見解?
吳家睿:我認為這仍是一個尚無定論的開放性問題,但我同意菲利普的觀點。複雜性是逐步演化融入生命的。這意味着當我們談論生命時,應關注兩個維度:一個是進化,另一個則與環境緊密相關。
我就用菲利普剛才提到的“垃圾 DNA”來舉例,説説我對複雜性的理解。在早期生命形式中,比如細菌這類我們稱為原核生物的生命體,它們是最簡單的。通常來説,這類細菌的基因組幾乎全是編碼蛋白質的核酸序列,也就是説,這些簡單生物的基因序列基本上用於指導蛋白質的合成。但在進化過程中,“垃圾DNA”逐漸出現了。
舉例來説,到了真核生物階段,我們可以以單細胞真核生物為例,這類生物從原核生物進化而來,其基因組規模顯著擴大。此時,“垃圾DNA”的數量超過了編碼DNA序列。這意味着,許多序列逐漸有了其他用途,不再直接用於編碼蛋白質或合成蛋白質。這就是原核生物與真核生物的差異所在。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因為進化。而為什麼會有進化?因為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作用。
隨着簡單生物的進化,它們逐漸發現需要更多這類DNA,現在我們不能再稱之為“垃圾 DNA”,而應稱為“非編碼DNA”,它們用於調控編碼DNA,從而增加了這些編碼DNA的複雜度,這正和菲利普所説的基因調控機制相契合。
説到我們人類,在人類基因組中,編碼DNA僅佔大約1.5%,大部分序列都是非編碼DNA,編碼DNA負責合成蛋白質。早年,我們把蛋白質看作生命機器中一種 “零件”之類的東西。但非編碼DNA為何會大幅增加?這些非編碼DNA並非無用的“垃圾”,它們有其存在意義,能夠讓一個編碼蛋白質的DNA在不同條件下對蛋白質的合成任務有不同的響應,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由此可見,生命的複雜性顯著提升,這並非僅僅依靠編碼DNA,非編碼DNA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非編碼DNA能與環境相適應。即便在今天,人類所具備的智力等特徵,都可能與非編碼DNA有關,而這並非直接由編碼DNA所產生的蛋白質決定。所以你看,在談論生命的複雜性時,我們應當考慮到目的性,比如我在菲利普的書中讀到過關於“目的性”的內容。書中提到,生命是有目的的,它們會試圖探尋生命的意義,或者説為生命賦予意義。
不過,我仍有疑問,想請菲利普詳細談談他對“意義”的理解。我在他的書中看到,他説進化本身是沒有目的的,但生命體卻會獲得或擁有目的性。所以我在想,從環境中是否存在某種潛在的“目的性”,到最終產生具有目的性的生命,這一過程是否成立?
菲利普·鮑爾:非常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沒錯,這其實正是我想要傳達的核心觀點。理解所有分子的活動以及它們如何協同作用,這固然很有意義,也十分重要。但歸根結底,這一切的本質是什麼?它們在“構建”的究竟是什麼?或許用“構建”這個詞並不太準確,更確切地説,它們在通過協作創造出具有目的性、擁有目標的實體。
在我看來,這恰恰是生命體與非生命體的區別所在:生命體有目標、有目的、有意圖。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它們都會像我們人類一樣思考,也不意味着它們都會有意識地權衡。不過我認為,擁有類似能力的動物其實比我們之前認為的要多得多。但我敢肯定,許多高等哺乳動物是具備這種能力的,鳥類或許也擁有某種意識。
這正是進化論中耐人尋味的一點。我想我在書中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進化是一個非常擅長創造具有目的性實體的系統。進化本身並非在朝着某個方向努力,也並非刻意要創造出某種特定的生物。它只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會誕生出這些具有目的性、擁有目標的實體。
那麼,這種目的性是如何從分子系統中產生的呢?我認為這正是生物學的核心問題:這樣的特性是如何誕生的?我在書中談到了“意義”,認為生物學(或者説進化)是一個創造“意義”的系統。我的意思是,任何生物體在其所處的環境中,都會從環境中獲取各種信息,比如温度高低、光照強度、營養物質的分佈、捕食者帶來的危險等,而生物體必須理解這些信息的意義。用一種擬人化的説法就是,生物體必須判斷哪些信息重要、哪些不重要,因為它不需要所有信息,也不需要所有細節,所以必須做出這樣的判斷。而這本質上就是關於“意義”的問題:生物體必須判斷,這條信息對我有意義嗎?順帶一提,這些信息也可能來自生物體內部。我們人類就是這樣,比如感覺今天不太餓,或者有點不舒服,又或者特別有活力,這些都是來自我們自身的信息。
所以,進化針對“對某種生物而言什麼是有價值的”做出了不同的判斷。但我認為,這其實可以被看作一個創造“意義”的過程:即為了實現自身目標,對該實體而言什麼是有意義的。
 紀錄片《人類基因組》劇照。
紀錄片《人類基因組》劇照。
3
幻想與現實
基因編輯技術從來不是100%精準的
吳晨:我記得你(菲利普·鮑爾)在書中還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説法:人們常説人類與類人猿的基因組有98.8%的相似度,但我們其實與它們差異巨大,科學家們試圖解釋這個情況,我想這想表達的是進化只需對基因組做一點點調整,就能產生全新的、不同的物種。但這也凸顯了一個事實:即便只是微小的變化,其影響也可能很大。當然,我們不能把所有這些變化都歸因於基因組。不過,基因組確實是儲存遺傳信息並將其傳遞給後代的地方。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自然和進化是如何真正塑造不同物種的?這或許不是你當前要探討的內容,可能你會在下一本書中嘗試研究,但人們對此確實會很感興趣。你用這個説法指出了人們對基因組相似度的理解存在誤解。那麼,這種誤解為什麼會存在呢?
菲利普·鮑爾:(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人類基因組計劃説起。該計劃旨在對人類的全部DNA進行測序,始於1990年左右,大致在2003年完成。
在該計劃啓動前,如果你問該領域的許多科學家:人類有多少個基因,這裏我指的是編碼蛋白質的基因,他們會告訴你,我們當時已經對一些簡單生物的基因數量做過研究,發現其中一些可能有1萬到2萬個基因。因此,很多人認為,既然人類比線蟲複雜得多,基因數量肯定也更多,典型的推測是可能有8萬到10萬個基因。但當我們真正完成基因組測序後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人類的基因數量與線蟲差不多,只有約2萬個,甚至可能僅約1.9萬個編碼蛋白質的基因。
那麼,既然我們的基因數量與簡單生物基本相同,而且很多基因實際上是共有的,我們是如何變得如此複雜,還擁有了智力等能力的呢?就像吳家睿教授所説的,關鍵在於調控,在於這些基因如何被使用,這一點至關重要。在進化過程中,當生物向越來越複雜的方向過渡時,情況就是如此。每次過渡中,新基因的出現並不多,但基因調控的方式卻有了許多新變化,基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控制、相互開關的新方式不斷湧現。
因此,這才是進化變化的關鍵,生物越複雜,其基因調控機制就越豐富。正如吳家睿教授所説,我們基因組的很大一部分,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核心都是調控。而且,有一點似乎很明確:從類人猿祖先到我們人類的過渡使我們擁有了能進行語言交流、創造文化等能力的大腦,這是其他類人猿所不具備的,至少達不到我們的程度,背後的原因我們目前還不完全清楚,但無論具體是什麼,都是調控方式的改變,而非新基因的出現。
吳晨:吳教授,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我想問問,生命是如何在進化過程中實現自組織的呢?
吳家睿:我想補充一點。我認為生命的複雜性,除了基因組從簡單的編碼DNA演變為非編碼DNA之外,還體現在從分子、細胞層面到更高層面的組織層級上。比如,原核生物如大腸桿菌或細菌,細胞內結構無序,我們稱之為“低區室化”。
所以在原核細胞內,從DNA到RNA再到蛋白質的合成過程,都在同一個“空間”裏進行。但當進化到真核細胞時,如酵母,細胞內出現了細胞核、線粒體等不同的細胞器,負責執行不同的生命活動;這種區室化讓細胞變得更復雜。
這就像人類社會的發展,原始社會中,每個人做着類似的事,比如狩獵、採集,沒有分工;而進入文明社會後,從農業時代開始,人們有了分工,有的負責宗教,有的負責管理,有的負責烹飪。到了工業社會,分工更復雜。可以想象,從簡單生物到真核生物,再到動植物乃至人類,它們從細胞層面就開始發展出多細胞組織。多細胞生物的細胞並非處於同一層級,而是形成了不同的層級結構。這對生命的複雜性而言至關重要。
所以,現在我們意識到所有生物的組織方式都是獨特的,不僅基因組如此。我在書中提到,進化最初推動細胞內部形成複雜的區室化,進而演化出真核細胞。但如果想讓細胞內部更復雜,有限的空間無法分隔出足夠多的功能區域。這時生命展現出了創造性,演化成了多細胞生物。
人類有超過30萬億個細胞。可以想象,這種區室化不僅存在於細胞內部,還延伸到了細胞之外。細胞形成不同類型的組織,不同組織形成器官。人類甚至有神經系統這樣的更高層級組織。所以,生命與非生命的區別之一,就是它能形成不同的組織層級。我認為這是生命複雜性的一個重要特徵。
吳晨:我想順着吳教授的話,再向菲利普提個問題,幫助我們理解。這也是你在書中從不同層面探討的內容:我們該如何理解生命?
細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現在很多人嘗試構建虛擬細胞,因為它可能成為眾多實驗的基礎。胚胎是另一個重要起點,你在書中多次強調發育生物學,而胚胎是起點,因為在胚胎階段,生物非常相似,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快照”。此外,器官層面也有一些有趣的特性。菲利普,你能講講你對細胞、胚胎和器官層面的生命的理解嗎?這些是構建生命運作的不同複雜尺度。
菲利普·鮑爾:首先,細胞是現存最小的生命體,我們能稱之為“活着”的最小單位。在細胞之下的層面,我們需要了解分子的功能、相互作用、形態等。這些信息很重要,但僅靠這些層面無法理解生命如何運作,因為分子本身並不“活着”。只有到了細胞層面,我們才真正接觸到“活着”的東西。
但我們是多細胞、多組織生物。這意味着,當我們體內的細胞分裂、增殖,發育成胚胎和生物體時,它們必須特化,每個細胞都擁有相同的DNA和基因組,但在不同組織中會以不同方式使用這些遺傳信息。這是促成我們這樣的複雜生物出現的關鍵創新。
那麼這一過程是如何實現的?一個細胞如何變成皮膚細胞或神經細胞?這是理解發育的核心問題。
這是一個迷人且尚未完全破解的問題,但有一點很明確:細胞的去向並非預設好的。每個細胞通過接收周圍環境的信息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例如,發育過程中,如果一個細胞周圍的細胞“決定” 變成肌肉細胞,那麼它很可能也會變成肌肉細胞。
胚胎從單個受精卵(處於類幹細胞狀態,可發育成任何組織)發育而來,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前一階段的狀態決定後一階段的發展。
這一切都受基因影響,但在這個層面,我們應該把正在生長的胚胎及其細胞看作是在“利用”基因作為資源。基因不會指令細胞做什麼,細胞之間相互決策,藉助基因來實現這些決策並改變自身特性。胚胎生長過程中發生的一切,其動因存在於更高層面:細胞和組織層面,而非基因層面。但這些層面始終在相互通信。
吳晨:正如你在書中強調的,生物學是一門複雜的學科,每隔大約十年,我們就需要重新審視對生物學的理解。之前我們談到了基因編輯,因為我們現在有了強大的工具來進行基因改造。對普通人來説,生物學、醫療健康的未來常常圍繞兩個問題:我們能通過基因編輯治療遺傳病嗎?我們能利用幹細胞等機制實現返老還童,活到100歲甚至更久嗎?畢竟,如果我們掌握了胚胎髮育等過程,為什麼不能更長壽呢?這些是基於科學突破的希望和想象。但我們目前處於什麼階段?對未來可能的突破,我們能有哪些現實的期待?
菲利普·鮑爾:沒錯。有些人可能會疑惑:如果基因並非處於主導地位,那基因編輯怎麼會起作用呢?
有時候基因確實是主導的,但並不像人們想得那麼頻繁。有些疾病明確與特定基因突變相關,在某些情況下,只要攜帶這種突變,就一定會患病。囊性纖維化就是一個例子,它有很多突變類型,有些影響輕微,但有些突變只要存在,就一定會導致囊性纖維化。鐮狀細胞貧血也是如此,與特定基因突變相關。在這些病例中,基因編輯可以實現治癒。
單基因疾病有很多,但大多數都很罕見,也很可怕。囊性纖維化和鐮狀細胞貧血之所以為人熟知,是因為它們相對不那麼罕見。但我們容易患上的大多數疾病,比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等。
這些疾病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受多個基因影響。因此,基因編輯是否能在這些疾病上發揮作用,就不那麼明確了。因為,首先,你得針對很多不同的基因進行編輯,但你卻不確定哪些才是關鍵基因。而且你無法確保這些改變不會影響基因的其他功能。此外,我們現有的基因編輯技術從來不是100%精準的,你可能會編輯到一些並非目標的基因,或者一些非目標的DNA片段。
所以關於基因編輯,首先要明確的是,它只對少數幾種疾病有效。即便對於這些疾病,關於我們是否應該進行基因編輯,也存在很多爭議。所以,在返老還童、組織生成或組織再生等方面,相關的討論仍在進行中。
這可以説是一種科學幻想,我們能夠培育出任何器官,這樣當我們自身的器官像往常一樣衰竭時,就能用從自身組織培育出的替代器官進行移植。而這些器官來自我們自身的組織,這意味着我們不必擔心移植後的排斥反應。所以説,這是一種幻想,我們還不確定這些事情能實現到什麼程度。但就目前而言,似乎並沒有明顯的理由表明我們無法在某種組織培養中培育出可用於移植的完整器官。
 紀錄片《破譯DNA密碼》劇照。
紀錄片《破譯DNA密碼》劇照。
4
希望與邊界
合成生物學技術與倫理規範
吳晨:我想這很自然地過渡到合成生物學的話題,因為在我看來,我們對生物體的瞭解更加深入了,也擁有了強大的工具來進行改造。當然,我們能製造出機器與生物體的混合體,比如水母機器人之類的東西,這有點嚇人,我們可以稍後再談這個。但仍然有一派觀點會説,我們不應該“扮演上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扮演上帝,那你其實是在做危險的事情,因為這裏面存在一些倫理問題需要我們考慮。那麼,關於合成生物學的倫理問題和應用,你認為我們需要注意什麼,以及在應用時應遵循什麼原則呢?這個問題也想問問吳教授,請菲利普先説説吧。
菲利普·鮑爾:“合成生物學”乍一聽可能會讓人覺得有點嚇人。確實如此,它聽起來像是在“扮演上帝”,像是在隨意擺弄生命。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擁有合成生物學相關的技術已有大約50年了。我記得是在20世紀70年代,我們首次開始掌握基因編輯的方法。而最初的基因編輯就是在細菌身上進行的。如今,通過對細菌進行基因編輯來生產的藥物已經有很多種了。具體來説,就是將基因導入細菌中,然後在培養罐裏培養這些細菌,為它們提供所需的各種營養物質等,細菌就會產生這種物質,而這種物質如果僅靠化學方法是很難生產出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那算是一種合成生物學。
但如今提到“合成生物學”這個詞時,我們通常指的是比單純向細菌中植入基因更復雜的事情。合成生物學的現代發展同樣始於對細菌的基因編輯。這大概是在21世紀初,目的是讓細菌表現出更像機器的特性,或者説更具工程化的功能。這也是一種合成生物學,而且其應用前景十分明確。有人希望讓細菌生產生物燃料或氫氣,以製造綠色能源。所以開展這些研究有充分的理由,但幾乎所有研究都集中在細菌上。
正如吳家睿教授之前所説,細菌的結構簡單得多,它們只擁有自身所需的DNA,不需要通過複雜的DNA排列方式來實現特定功能,因為它們無須分化成不同的細胞類型,只需要進行復制即可。因此,我們可以對細菌進行這類工程改造和合成生物學研究。但如果研究對象更復雜,哪怕是酵母這種單細胞真核生物,它的細胞結構與我們人類細胞更相似,難度也會大幅增加。而如果要對人類細胞進行合成生物學研究,比如設計複雜的基因迴路植入細胞,讓細胞執行特定功能,甚至讓它們分化成我們體內不存在的全新細胞類型,這些想法雖然很有吸引力,但實現起來難度極大。
所以,我覺得開展合成生物學研究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在很多方面它並沒有引發特別大的爭議。但即便是研究細菌,我們也要確保不會有意或無意地創造出一種能在野外繁殖並大量滋生的病原體。
吳晨:吳教授,關於合成生物學的倫理問題及相關指導原則,你有什麼補充的嗎?
吳家睿:合成生物學如今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生物技術,它不僅支持生物學研究,還支撐着食品、醫藥及所有行業的發展。然而,這項新技術也對人類價值觀和生物安全構成了挑戰。因此,政府強調,在應用包括合成生物學在內的任何生物技術時,必須首先考慮倫理規範。而且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例如,關於轉基因技術,社會上仍存在巨大爭議,一方認為它對人類、產業和人類發展非常有用;另一方則認為它對人類來説非常危險。
你看,即便是植物基因編輯,人們也會關注當培育出轉基因植物,也就是將一種外源基因轉移到一種植物中時是否存在危險。如今,對植物進行基因修飾時,“是否危險”“是否為轉基因植物” 等問題都很敏感。實際上,基因編輯確實改變了基因組,但這種改變是在同一種生物體內進行的。由此可見,這一問題的爭議性很大。比如,説到幹細胞和動物克隆,從技術角度看,我們可以克隆人。但社會有明確的倫理規則禁止通過這種技術克隆人。我們甚至可以克隆猴子,但不能克隆人。這是監管問題,而非技術問題。
所以你能發現,技術發展非常迅速,倫理學界也在不斷討論這些新技術如何應用於人類,以及這些應用是否會對人類構成危險。我認為,即便在今天,我們仍面臨這樣的挑戰。許多技術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無論是基因編輯還是幹細胞技術。對於這些技術,不能簡單地用“可行”或“不可行”來評判。
 電影《別讓我走》海報,海報中的三位主角為克隆人,故事中,人類會為了給自己提供備用器官而克隆自己。
電影《別讓我走》海報,海報中的三位主角為克隆人,故事中,人類會為了給自己提供備用器官而克隆自己。
5
尾聲
AI、癌症與生命教育
吳晨:考慮到時間,我想接着問最後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當然是展望未來,有種説法是,20世紀是比特的世紀,而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21世紀是基因的世紀。我認為未來有很多可能性。那麼,我們如何預測未來?AI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生命本身,或許還能為我們提供可用的工具?AI方面已有不少領先成果,比如 AlphaFold(由英國DeepMind公司開發的一個人工智能程序,專門用於預測蛋白質的三維結構),這是一項非常強大的新進展,它能幫助我們理解甚至創造新的蛋白質結構。我想知道,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些新進展?它們將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生命、深入理解生物學,甚至推動合成生物學的發展?菲利普,請説説你的看法。
菲利普·鮑爾:首先我認為,人工智能有巨大的應用潛力,因為無論是在生物學領域,還是在其他學科或世界其他領域,只要我們處理的是非常複雜的系統,AI都能發揮作用。AI能夠發現我們人類自己無法察覺的模式和規律。AlphaFold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AlphaFold程序的兩位開發者獲得了去年的諾貝爾化學獎。要知道,AlphaFold解決了蛋白質化學領域一個長期存在的難題:僅知道構成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如何預測蛋白質的結構和形狀?從這一點來看,它的用處非常大。
但研發出一種有效的藥物,還有很多其他環節。這些環節中的大多數,對藥物能否真正起效、能否成功推向市場而言都很重要。所以,很遺憾,AlphaFold不會給藥物研發帶來革命性變革,但它確實是一個出色的工具。
而且,正如你所説,它正被用於設計新的蛋白質,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它能設計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全新蛋白質結構,告訴我們如何製造這些蛋白質,而我們也確實能成功製造出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説明AI 能幫助我們解決非常複雜的問題。
但我擔心的是,有些人會認為,既然生命如此複雜,比如基因調控等機制我們難以理解,那借助AI就是理解生命的途徑,於是完全依賴AI。
無論如何,在我看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我們想要理解細胞內正在發生的各種過程。而這種理解,我認為是無法通過AI獲得的,AI只能告訴我們輸入這些分子後,細胞會有什麼反應,僅此而已。所以,我堅持認為,AI在研究中應始終被當作一種工具,而不是用來替代對細胞內活動的真正理解和理論構建。
吳晨:《經濟學人》最近有一期封面報道稱,人類最終將能夠攻克癌症。當然,這樣的標題每十年都會出現一次。但癌症作為人類關注的重大疾病,仍然非常複雜。
而你在書中強調,基於基因組測序等技術的個性化治療所引發的熱潮,可能並不像人們預期的那樣令人滿意、那樣神奇。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點?我們怎樣才能對近期的醫學研究和醫療健康發展做出切實的預測呢?
菲利普·鮑爾:癌症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疾病,而且其實它並不完全像傳統意義上的疾病。它不像有些疾病是由病原體引發的,雖然有時會由環境因素誘發,本質上,我覺得它更像是我們的細胞自身容易陷入的一種狀態,細胞會形成多種狀態以構成不同組織,而癌症就是其中一種狀態。
事實上,近年來在認知上有了新的進展:我們過去認為癌症是細胞發生特定基因突變後,不受控制地增殖,形成大量細胞並破壞身體。現在我們對癌症的理解更傾向於一種“錯亂的發育”,我在書中也用了這個詞。所以,腫瘤並非由完全相同的細胞隨機堆積而成,它們其實有一定結構,包含不同細胞類型,本質上更接近器官,一個非常粗糙、危險的器官。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個性化治療可能會發揮作用:如果我們從患者的腫瘤中取樣,瞭解腫瘤類型及其包含的癌細胞種類,就能選擇適合該類細胞的藥物,而不是用通用療法。這樣或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我見過的最令人興奮的癌症治療進展之一是嘗試用我之前提到的細胞重編程技術來重新編程癌細胞。如我所説,癌細胞陷入了癌變狀態,但我們知道細胞可以從一種類型轉化為另一種,所以有人在研究如何將癌細胞轉化回健康細胞,或者至少轉化為一種靜止、不增殖的細胞。如果能實現,這種方法的創傷和干擾會小得多。
所以,生物學領域的這些新想法,是可以像這樣創造性地應用於醫療領域。我認為,我們對生物學中這些層級結構的理解越深入,就越能明確需要在哪個層面進行干預。我非常樂觀地認為,這種對生物學更深入、更細緻地理解,將帶來各種臨牀突破。
吳晨:這真的很有意思。我覺得《生命傳》這本書讀起來也非常引人入勝。我想最後一個問題,還是回到菲利普你説的,你希望AI成為我們研究的強大工具,而非替代品。這意味着我們需要新一代的人依然對複雜的生命保持好奇,依然能被《生命傳》這類書籍吸引。那麼,我們該如何引導、推動或鼓勵人們對周遭世界更具好奇心呢?這個問題我也想問問吳教授。
菲利普·鮑爾:我認為,幾乎所有關於生命世界的書籍都應該從生命世界本身説起,從這個世界所擁有的奇妙寶藏説起,比如珊瑚、水母、老虎,還有那些令人驚歎的植物。這樣做是為了提醒我們,即便我們深入到基因、蛋白質等微觀層面去探索,我們所談論的歸根結底還是我們周遭這個非凡的生命世界。而且,我覺得真正的起點應該是對這一切的敬畏,敬畏進化所造就的奇蹟,敬畏進化所展現的創造力,以及生命體自身所彰顯的活力。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永遠都不該忘記,這才是我們探索的終極命題。
吳晨:吳教授,我們該如何鼓勵人們抱有更強的好奇心,去閲讀像《生命傳》這類書籍呢?
吳家睿:我認為,首先我們應該擁有開放的心態。如今,很多培訓越來越注重技術本身,卻沒有培養人們去適應這個瞬息萬變的環境。所以,開放的心態是其一。
其二,要深入思考。如今,海量信息湧入我們的大腦,以至於人們不像以前那樣願意花時間思考了,大家只是接收信息,卻不去思考。不思考,就不會想去讀書。而如果能思考,人們就會意識到自己的知識有限,有很多不懂的東西,於是就會想去讀書。他們會去讀像菲利普的這本書,或者我的書。我認為,這正是我們生命價值的體現——學會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我一直覺得“知不足者好學”,至少要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保持求知慾,這樣才會想去讀書。
吳晨:好的,最後一個簡短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幫助普通人理解複雜的生命科學?《生命傳》這本書內容比較深刻,不是能夠很輕鬆讀懂的,有些章節確實得全力以赴才能讀懂,但很多章節真的很吸引人。菲利普,對於讀者來説,閲讀你的書、理解複雜的生命科學,有什麼技巧呢?
菲利普·鮑爾:我想首先要説的是,我希望讀者從書中得到的是一個更豐富的認知,而不是認為我們不過是由基因造就的機器。有種説法認為生命就是如此,我覺得這種説法低估了生命的意義。而且,在我看來,現代生物學不僅沒有證明這種觀點,甚至沒有暗示過這種觀點,這在我看來是一種非常狹隘的生命觀。
所以我想説,生命遠比這更豐富,而“更豐富”其實也意味着它遠比這更復雜。或許我們應該用這樣的比喻去理解生命:它不是計算機程序,不是機器,而是一個社會。
吳晨:請吳教授做最後的點評。你對《生命傳》這本書有何評價?為什麼推薦它呢?
吳家睿:我認為這本書能為你提供多維度的視角去思考當下的生命。我們讀教科書時,獲取的知識往往比較陳舊,其中大部分來自我們所説的還原論科學家的研究,這種認知已經過時了。
就像你説的,人們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知識體系。因此,當你讀這類書時,就應該換一種思維方式。比如,傳統觀念認為生命是機器,但這本書告訴你,生命並非機器。以前有人説生命很簡單,而這本書告訴你生命並不簡單,還解釋了為什麼不簡單。所以我認為,對於理解生命而言,這本書對於開闊思路、啓發思考非常重要。
本文內容由中信出版社授權提供。
注:本文封面圖片來自版權圖庫,轉載使用可能引發版權糾紛。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