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真實,年代劇就沒有意義_風聞
大脚-08-28 11:15
《生萬物》熱播以後,輿論分成了兩個極端,核心觀點:
正:革命的徹底性會讓後人懷疑革命的必要性;
反:地主的家產和土地,是世世代代辛勤勞作積攢下來的,不是剝削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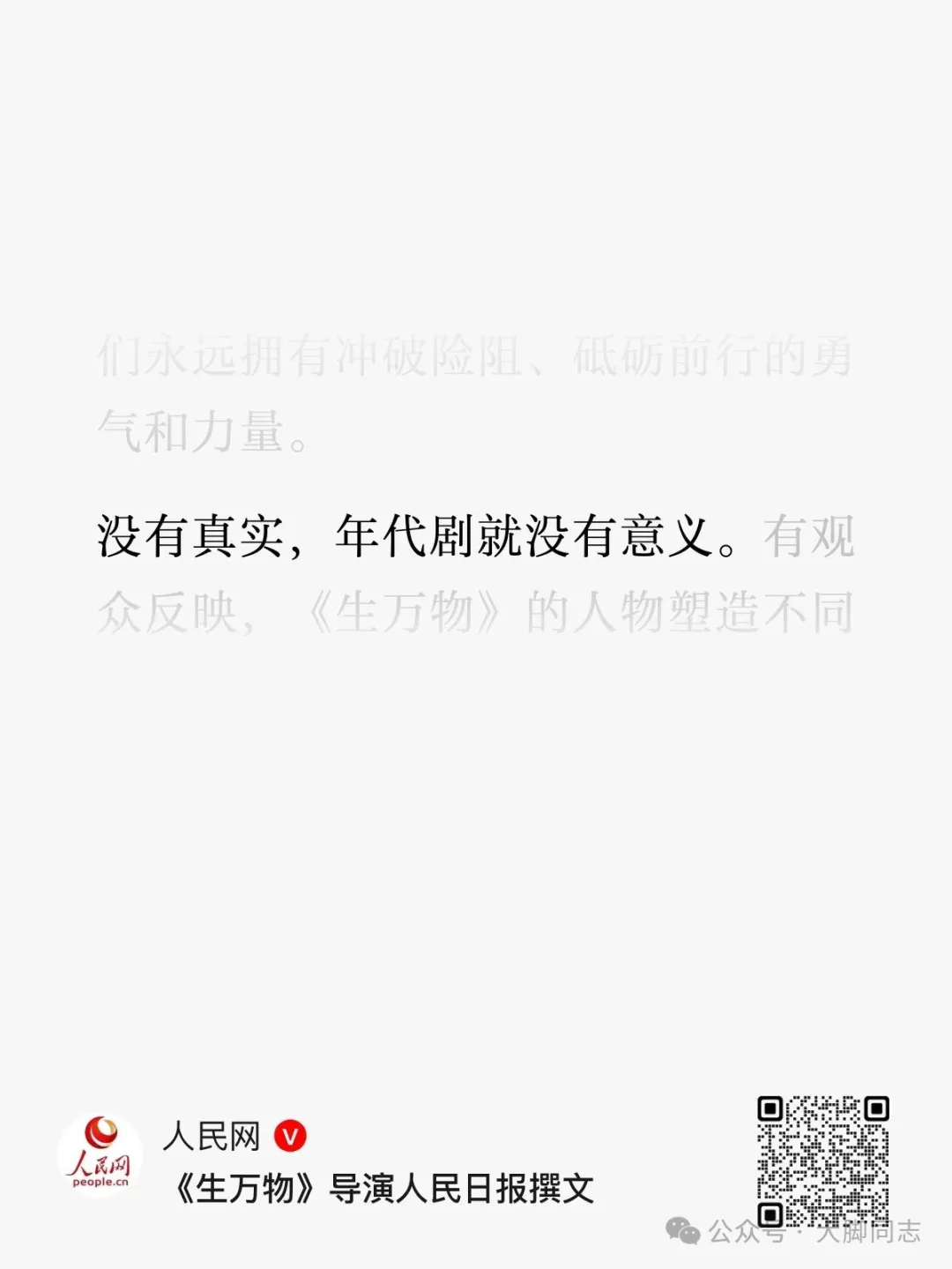
正如該劇導演講的,沒有真實,年代劇就沒有意義。
那麼,解放前,真實的農村是什麼情況呢?咱就用該劇所反映的山東農村來掰扯掰扯。
一、地主階層的權力結構與經濟壟斷
民國時期的山東農村,土地分配極度不均,形成了地主階層對農業生產資料的絕對壟斷。在魯南和蘇北地區,地主階級不僅佔有大量土地,還通過複雜的權力網絡控制着農村社會的一切生活領域。根據山東省檔案館1935年的《佃農契約》原件顯示,契約中明確規定"見東家行跪禮"、“天災自負損失"等條款,佃户在面對地主時完全處於無權地位。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構成了整個山東農村社會的基礎結構。
大地主與軍政權力的勾結是維持這一剝削體系的重要支柱。在魯西南地區,許多大地主兼任當地保安團團長職務,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據記載,這些地主家的護院裝備精良,“甚至有機槍等重型武器”。他們通過武力威懾維持對佃户的控制,任何反抗都可能遭到殘酷鎮壓。1934年,山東省榮成縣南下河惡霸地主張鳳楷擔任區長,平日欺壓人民,無惡不作。他養的一條惡狗經常攔路咬人,當地羣眾卻敢怒不敢言。當貧農陳竹青在割草時用鐮刀抵擋撲咬他的惡狗導致狗死亡後,張鳳楷竟暴跳如雷,揚言要抓陳竹青"抵命”,最終逼得陳竹青逃亡他鄉,其父陳緝乾被逼為狗"出殯"、“守靈”,甚至最終含冤吐血而死。

表:民國時期山東農村地主與佃户經濟狀況對比
地主對佃户的經濟控制達到了驚人的程度。1935年山東農村經濟調查報告顯示,農村物物交換佔比超70%,而地主掌握絕對定價權。在安丘地區,地主石次鑾擁有淩河鎮附近幾乎全部土地,出了葛家灘到淩河鎮走十幾華里,“腳都踩不到一點別姓的土地”。這種對土地的壟斷使地主能夠隨意制定剝削規則,如春天借出一斗糠谷,收穫時就要收回一斗麥子,若不能及時償還,秋後則變為三鬥穀子。
在魯南地區,地主的子弟"竟要任意把佃貧農的子弟當馬騎着去上學"。這種人格侮辱不僅體現了階級間的極端不平等,還從心理上強化了農民的服從意識。地主通過一系列禮儀規制維持這種等級秩序,如河北省檔案館《冀中農村調查》記載的"佃户見地主需行跪禮",在山東地區也有類似規定,佃户在路上遇到地主必須低頭讓路,不得直視正視。
二、初夜權:人格侮辱與性奴役
解放前,山東農村最為黑暗的一面,是地主對佃户新娘實行 “初夜權"制度。這一野蠻慣例在魯南和蘇北地區廣泛存在,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極為恥辱的一頁。據記載:“農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須先陪地主睡,讓地主老爺’破瓜’"。這種制度並非個別地主的偶然惡行,而是成為一種系統性的社會壓迫工具,在山東許多地方甚至被視為"不成文的法規”。
初夜權制度在山東的地域分佈主要集中在魯南和魯西南地區。抗戰時任豐縣、魚台等地婦女部部長的張令儀回憶道:1938年,在魯南,“我第一次聽説有這樣的事:佃貧農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權”。她進一步指出,中共單縣縣委書記張子敬親口對她講述,因佃種了單縣辛羊區張寨地主的田地,張新婚時,妻子被張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權。
初夜權的實施形式多樣,從相對"委婉"的嘗新到赤裸裸的暴力強迫。在江蘇蘇北地區,沐陽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僱工幾乎都受過他的蹂躪。“老的也好,醜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於滿臉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當被問及為何這樣做時,他竟稱這是"嘗新”。這種將人性徹底物化的態度,反映了地主階層對農民極端蔑視的心理。
地主通過多重身份強化對農民的控制,他們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種身份,處於極為強勢的地位。例如沭陽縣耀南區長安鄉地主袁席山,有地9頃,有位佃户搬來的第一夜,他就帶着門勇,打壞佃户家的門,姦淫其妻,“地主及門勇一夜去打幾次門,小笆門都被打壞了”。
初夜權制度對農村社會倫理的破壞是毀滅性的。1942年4月,蘇北新四軍領導人鄧子恢指出: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包括"可以自由姦淫以至霸佔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權利”。反之,佃農"如果討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爺的牀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這種價值的完全顛倒,反映了地主階層如何通過性特權來強化社會控制。
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總會會長霍士廉在1940年8月11日的山東職工聯合大會上報告:“魯南許多落後的地區,存在着超經濟的剝削和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如初夜權。”
三、經濟剝削與生存控制
民國時期山東農村的地主階層通過精密的經濟剝削體系對農民進行殘酷掠奪,這一體系由地租剝削、高利貸盤剝和超經濟強制共同構成,形成了幾乎天衣無縫的剝削網絡。根據1935年山東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農村物物交換佔比超70%,而地主掌握絕對定價權。這種經濟控制使農民陷入永無止境的貧困循環,難以擺脱被奴役的命運。
地租剝削是地主榨取農民剩餘勞動的主要方式。在山東地區,地租形式主要有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和勞役地租三種,其中實物地租最為普遍。地主通常採取分成租制,比例從對半分成到倒四六分成(地主得六成)不等。遇到災年,地主往往不肯減少地租,迫使農民借債交租,從而陷入高利貸的陷阱。
高利貸盤剝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另一種重要手段。在安丘地區,許多地主規定:窮人春天借走一斗糠谷,收了莊稼就要還一斗麥子。如果到時候還不起,秋收以後就必須還三鬥穀子。這種驚人的利率使農民一旦借債,就很難徹底還清。民國四年春,安丘一户鄭姓農民找地主石次鑾借了兩鬥穀子。當年遭遇旱災和蝗災,田裏顆粒無收,石次鑾卻逼其還六鬥穀子。鄭姓農民無力償還,只能拖家帶口逃荒到江蘇安徽一帶。後來無奈返回家鄉時,石次鑾硬是用三鬥糠谷把鄭姓農民的女兒換走,帶回去當了使喚丫頭。小姑娘在石家受到打罵虐待,最後跑回家中,全家人無路可走,一起跳灣自殺。
地主還通過超經濟強制手段對農民進行額外剝削。在魯南地區,地主經常強迫佃户提供無償勞役,包括修建房屋、抬轎趕車、洗衣做飯等種種雜役。這種勞役通常沒有任何報酬,甚至不給飯吃。佃户的家庭成員也常常被強制為地主家提供服務,特別是女性成員往往被迫成為地主的傭人甚至性奴隸。1930年代山東佃户日記中,“命不如牛"的記載比比皆是,地主對佃户的婚配權、懲戒權構成嚴密的人身控制網絡。

表:民國山東農村地主採用的地租形式及剝削率
地主對農民的經濟控制還體現在對生產資料的壟斷上。除了土地之外,地主還控制着水利設施、大型農具、牲畜等重要生產資料。農民在使用這些設施時必須支付高昂費用,進一步加重了負擔。在魯西南地區,有些地主甚至控制着打穀場、磨坊等基本生活設施,農民使用時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糧食作為報酬。這種全方位的控制使農民在生產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地主的"恩賜”,從而被迫接受各種不平等條件。
災年剝削是地主擴大土地積累的重要手段。每當發生旱災、水災或蝗災時,地主不僅不肯減租,反而趁機壓低價格購買農民的土地、房屋甚至子女。1926年山東大旱,許多農民不得不賣兒鬻女換取糧食。地主則利用這個機會大肆兼併土地,擴大自己的產業。在安丘縣,地主石次鑾就是通過災年放貸致富的典型代表。他囤積大量糧食,等到災荒最嚴重時以極高利息借出,迫使農民用土地或子女作為抵押。
四、文化壓迫與意識形態控制
地主階層不僅通過經濟手段剝削農民,還通過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控制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這種文化壓迫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禮儀規制到教育壟斷,從道德話語到宗教信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精神控制體系。在山東農村,地主往往以 “鄉紳” 、“道德楷模” 自居,通過控制解釋權來合理化自己的特權地位。
禮儀規制是地主強化階級差異的重要手段。在河北省檔案館《冀中農村調查》記載的"佃户見地主需行跪禮",在山東地區也有類似規定。佃户在路上遇到地主必須低頭讓路,不得直視正視。説話時要用敬語,自稱"小人"或"奴才"。這種日常禮儀的強制要求,從行為習慣上內化了階級差異,使農民在潛意識中接受自己的卑下地位。山東省檔案館1932年《佃農契約》原件中"見東家行跪禮"的條款,更是將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以契約形式固定下來,賦予了它一定的"合法性"。
地主通過對文化符號的壟斷來強化自己的權威。在魯南地區,許多大地主自稱是書香門第,標榜"耕讀傳家",實際上卻壟斷教育資源,禁止佃户子女讀書識字。他們通過控制文化解釋權,將社會等級制度描繪成天經地義的秩序,任何挑戰這一秩序的行為都被稱為"大逆不道"。
宗教與迷信是地主控制農民的另一工具。許多地主以宗教捐助人的身份出現,資助修建廟宇,擔任寺院的護法,從而控制宗教信仰體系。他們散佈"天命論"、“命運觀”,勸説農民接受現有的社會等級制度,許諾來世的回報以換取今世的順從。在魯西南地區,地主們常常宣傳"富貴在天,貧賤有命"的觀念,將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歸結為前世註定,從而消解農民的反抗意識。
地主的司法特權使他們能夠任意懲罰農民而不受制裁。在許多地區,地主私設公堂,對所謂"不守規矩"的佃户進行審判和處罰。據記載,在臨沂張莊,莊主族長張大富擁有全莊土地,還享有初夜權,“誰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對於敢於反抗的農民,地主往往施以殘酷的私刑,包括鞭打、灌屎尿、烙鐵燙等酷刑,甚至活埋或沉塘。
性別壓迫是地主意識形態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地主的道德話語中,女性被視為財產和性工具,特別是佃户家庭的女性更是面臨雙重壓迫。在魯南地區,地主對佃户妻女的初夜權要求被視為一種"慣例",甚至被某些地主美稱為"嘗新"。這種將性剝削制度化的行為,反映了地主階層對農民人格的徹底蔑視。真實案例中,反抗地主的女性多遭發賣或私刑處死。
地主還通過控制婚姻來維持階級純潔性。大地主之間通過聯姻強化彼此之間的聯繫,形成一個鞏固的利益集團。相反,他們嚴格禁止子女與佃户通婚,以防財產外流。這種階級內婚制不僅保證了經濟資源的集中,也再生產了社會等級差異。
教育壟斷是地主維持文化霸權的重要途徑。在民國山東農村,絕大多數佃户子女無法上學讀書,地主故意維持文盲狀態以便更容易控制農民。少數地主資助的村學主要面向自有子弟和富農子女,課程內容強調忠孝節義等傳統道德,強化等級觀念。這種教育不平等不僅限制了農民子女的向上流動,也再生產了文化資本的不平等分佈。
有人説,地主的家產和幾百畝土地,是世世代代辛勤勞作積攢下來的,不是剝削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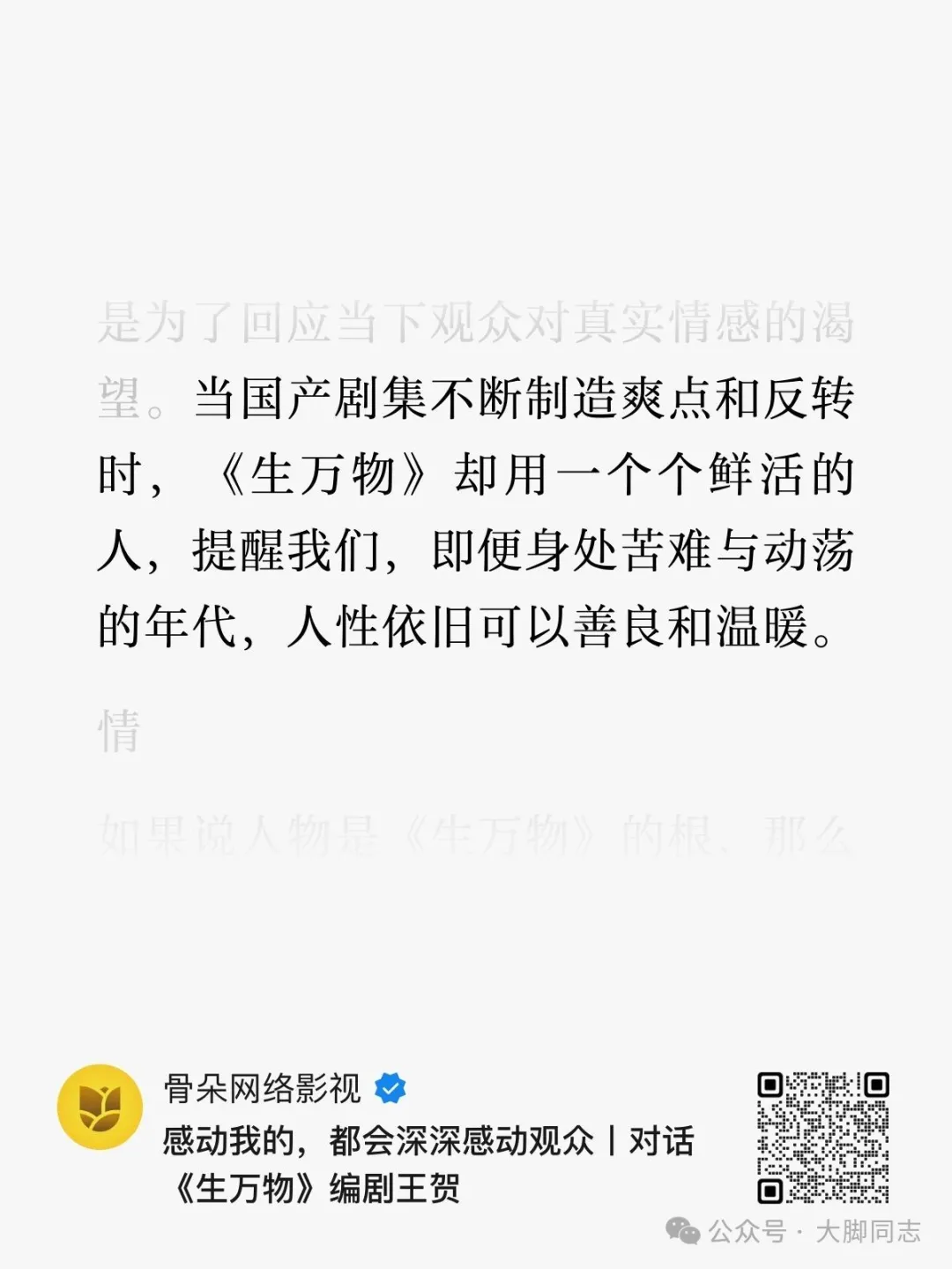
有娛樂媒體採訪《生萬物》的編劇,提到了“人性論”。
這種以抽象、超階級的“人性論”來美化或淡化地主階級剝削本質的敍事,是一種典型的“庸俗人性論”,它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在歷史觀上是反動的。
“庸俗人性論”的敍事策略,就是將地主和農民首先抽象為脱離具體社會歷史環境的、純粹的“人”,然後賦予他們一些永恆的、抽象的“人性”特質(如善良、温暖、自私、殘暴)。這種做法抽空了“階級”這一最核心、最本質的規定性,從而巧妙地掩蓋了地主作為封建剝削階級的根本屬性。
在地主階級中,在某些時刻表現出“善良”或“温暖”的行為(例如,荒年減一點租、過年給佃户送點肉)。但是:
這些行為是偶然的、局部的、非本質的。這些行為的規模和限度完全由地主掌控,其根本目的是維繫其剝削關係的穩定,是一種“懷柔”式的統治術,如同牧民餵養牲口以保證其持續產奶一樣,本質上是為了更長久的剝削。這些微小的“善舉”與其系統性的、制度化的剝削(高額地租、高利貸、勞役、初夜權) 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用一滴蜜糖的甜味,去掩蓋一整碗黃連的苦味,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欺騙。
它通過渲染“人性温暖”的細節,潛移默化地向觀眾傳遞一種信息:“那個時代雖然苦,但地主和農民之間也有温情,鬥爭並非你死我活。” 這直接質疑和消解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如果地主並非那麼可惡,農民並非那麼痛苦,那麼一場席捲全國的、暴風驟雨般的革命豈不是失去了合法性?
講了這麼多,有人説,地主有好人壞人。事實上,跟好人壞人沒關係,跟他們的比例也沒關係,這些也都是私德層面的東西。
正如羣裏朋友討論的時候所講,根本性的問題是這個階級是嚴重落後的,這種生產關係是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阻礙中國發展的,是中國近代以來落後的根本原因(甚至沒有之一)。要進入現代社會,要進行工業化,要發展生產力,首先就是改變落後的生產關係,消滅落後的階級。幾十年來,看阿拉伯國家和伊朗等國,地主階級掌權,國家體制還是封建領主酋長式的制度現在最落後,然後是革命不徹底的聯合政府模式(伊朗,黎巴嫩),最終還是無法完成現代化和獨立自主,只有由革命化政黨領導的全社會全國家改造,才能在當今激烈的國際鬥爭中生存發展。
這確實不是一個簡單地用“好人”或“壞人”的道德標尺就能衡量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社會結構、生產關係和歷史發展的根本性命題。地主作為一個階級,其根本問題在於其所代表的封建生產關係已經嚴重落後,成為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實現現代化的桎梏。 上面所詳述的種種殘暴剝削行為,正是這種落後生產關係最極端、最赤裸的表現。
地主通過收取高額地租攫取了絕大部分農業剩餘,這使得直接生產者(佃農和貧農)沒有剩餘來改善生產工具(如購買更好的農具、肥料),也沒有任何積極性去提高生產效率。這是一種內卷化的、無法進行擴大再生產的簡單循環模式。農民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承受着沉重的剝削,其購買力被壓縮到極限。這導致工業品失去了廣闊的農村市場,中國的民族工業因此無法發展壯大。農民對地主有人身依附關係,被禁錮在田地裏,無法自由地向工業和城市流動,使得工業化進程缺乏必需的勞動力後備軍。
因此,不打破這個僵化、反動的經濟結構,中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就無從談起。 消滅地主階級,進行土地革命,其目的不僅僅為了“均貧富”,更是為了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為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積累原始資本、創造國內市場。
回顧民國時期山東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地主個人行為的道德審判上。更應看到,地主的“惡”是制度之惡、結構之惡的集中體現。那個時代的悲劇,根源在於一套已經完全不適應現代世界、並且殘酷壓榨大多數人的社會經濟制度。
終結這一制度的,正是由一個有科學理論指導、有嚴密組織紀律、以徹底改造社會為目標的革命化政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最徹底的社會革命。 這場革命掃蕩了地主階級,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從而為中國此後的發展,無論走了多少彎路,清除了最大、最根本的一個障礙。
這是理解中國近代史、以及很多發展中國家為何陷入困境的一把關鍵鑰匙。生產關係的變革,是社會進步最根本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