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潛艇還是戰略陷阱?澳學者呼籲堅持戰略自主_風聞
北京对话-北京对话官方账号-北京枢纽型国际对话智库平台,致力于中外交流08-29 07:21
Club提要:洛伊研究所國際安全項目主任薩姆·羅格文(Sam Roggeveen)接受“Pacific Polarity”專訪時闡述其新書《針鼴戰略》觀點,認為AUKUS核潛艇項目在產能和技術上難以兑現,還將澳大利亞過於綁定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削弱防務自主。羅格文指出,澳不宜過度依賴美國在亞太的承諾,需依靠自身能力維護戰略自主,並在複雜國際環境中避免被動追隨或妥協。
“Pacific Polarity”是一個關注亞太地緣政治的智庫播客平台,由北京對話助理研究員李澤西等青年學者聯合創辦。
Club Briefing: Sam Roggeveen,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at the Lowy Institute, outlined the core arguments of his new book The Echidna Strategy:Australia’s Search for Power and Peace in an interview with Pacific Polarity. He argued that the AUKUS nuclear submarine program faces serious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that make timely delivery unlikely, while strategically tying Australia too closely to the U.S. goal of containing China—thereby undermining Australia’s defense autonomy. Roggeveen stressed that Australia should rely more on its own capabilities to preserve strategic independence. He also noted that America’s commit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cannot be fully relied upon, and that Australia must depend on its own strengths to maintain autonomy and avoid passive alignment or compromise in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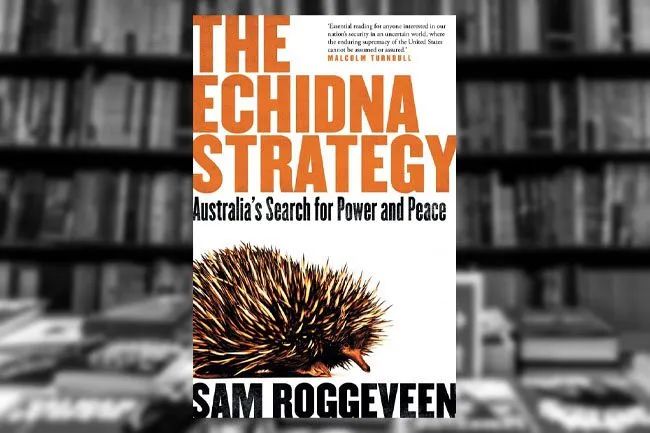
《針鼴戰略:澳大利亞尋求力量與和平之路》(圖源:獨立澳大利亞)
**李澤西:**歡迎收聽本期Pacific Polarity。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嘉賓是薩姆·羅格文(Sam Roggeveen)。他是洛伊研究所國際安全項目主任,也是該所《The Interpreter》專欄的創始編輯。他著有《針鼴戰略:澳大利亞尋求力量與和平之路》(The Echidna Strategy: Australia’s Search for Power and Peace)以及《我們自己的脱歐:澳大利亞空心化政治及其可能走向》(Our Very Own Brexit: Australia’s Hollow Politics and Where it Could Lead Us)。在加入洛伊研究所之前,他曾任澳大利亞最高情報機構——國家評估辦公室(ONA)的高級戰略分析師,主要研究北亞戰略事務,包括核戰略和亞洲軍事力量。他還曾在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從事軍控政策工作,並在國防情報組織擔任分析員。薩姆,非常高興你能參與。
**薩姆·****羅格文:**謝謝你,很高興能來。
**李澤西:**你的新書《針鼴戰略》似乎主要被一些反對AUKUS的人引用,用來支撐他們的論點。你怎麼看待這種用途?能不能也簡要談談書裏的核心觀點?
**薩姆·****羅格文:**我當然不能反對人們用這本書來反對AUKUS。畢竟我自己在書裏也提出了相當明確的反對理由,所以我當然不會反對,事實上我還很歡迎這種使用。我對這本書的反響也非常滿意。
值得先簡單説清楚,反對AUKUS的主要理由是什麼。而當我説“反對AUKUS”的時候,主要是針對其核心目的——核動力潛艇項目。AUKUS還有所謂的“第二支柱”,涉及與美英在一些新興軍事技術上的合作;對此我個人沒有異議。所以我們重點談潛艇。
我認為質疑核潛艇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純粹的現實操作問題:我們難以想象澳大利亞能夠按時按預算獲得所有這些潛艇,甚至哪怕只是一部分,因為阻礙實在太大。首先是美國的造船能力,這是澳大利亞國內爭論的核心。目前美國一年大約能造1.1到1.2艘核潛艇,而要滿足本國需求再加上澳大利亞的訂單,他們必須把產能提升到2.3艘。很難想象美國能實現這一點。
其次是澳大利亞方面。我們即將啓動一個澳大利亞歷史上最複雜的工程項目——核潛艇建造;這實際上是兩個項目:先是運營“弗吉尼亞級”,再是與英國共同建造“AUKUS級”。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對現役“柯林斯級”潛艇進行大規模升級。也就是説,澳大利亞要同時承擔三個重疊的潛艇項目,而我們過去從未同時成功執行過超過一個潛艇項目。這對澳大利亞來説是巨大的負擔。基於這些現實原因,對AUKUS的可行性保持懷疑完全合理。
再説戰略層面。假設所有難題都克服了,澳大利亞真的如期如數拿到了八艘核潛艇。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把澳大利亞的海軍力量中心,放在了這八艘擁有全球投射能力的潛艇上。而它們的最初設計目的,本質上是為了補充美國的海軍力量,幫助美國執行遏制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內活動、甚至對中國大陸發射導彈的戰略。這種能力將澳大利亞緊緊綁定在美國的戰略目標上。
如果從“澳大利亞防務自立”的角度出發,獲取核潛艇的邏輯就非常薄弱。它真正説得通的前提是:澳大利亞要與美國“並肩作戰”,也就是説把自己的戰略目標服從於美國的戰略目標。在我看來,這既沒有必要,也對中國具有一定挑釁性,而這並不是澳大利亞防務政策應該有的目標。所以,我反對AUKUS,不僅是出於現實操作的擔憂,更是因為戰略上它讓澳大利亞的安全困境變得更嚴峻。
AUKUS還有另一個內容,就是允許美國核潛艇使用澳大利亞西部的斯特靈海軍基地,預計會有四艘美軍潛艇常駐。另外一個相關舉措(雖然不完全屬於AUKUS),是升級達爾文以南廷德爾空軍基地,為美軍轟炸機提供使用。我認為這些安排同樣讓澳大利亞在潛在衝突中成為潛在打擊目標。這並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安全收益,反而讓我們更危險。

2025年3月16日,美國海軍“弗吉尼亞”級攻擊潛艇“明尼蘇達”號出現在澳大利亞西海岸(圖源:法新社)
總而言之,這就是我反對AUKUS的理由——既有實際操作問題,也有戰略上的根本問題。
至於我是否介意人們用我的論點反對AUKUS?我當然不介意,我非常樂意。唯一需要提醒的是,我感覺很多支持者來自澳大利亞政治左翼。我自己並不是左翼人士,我在書的引言中特意説明了這一點。有時候我覺得,左翼之所以接受我的觀點,部分原因是他們對美國天生就有一些偏見。但我個人並不持這種態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美國的安全保障對澳大利亞是巨大的好處。但現在世界變了。
我純粹從現實出發,認為美國今後對澳大利亞的安全保障會越來越不可靠,因此澳大利亞必須更多依靠自己。這就是我所説的“防務自立”。而AUKUS正好走向了反方向——讓我們對美國的依賴更深,而我認為我們應該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李澤西:你剛才提到,一些支持你觀點的人,支持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持更強的反美立場。因此有人批評説,反對AUKUS實際上等同於支持中國。顯然,這不是你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但在一個越來越被“中美對立”所框定的國際話語環境裏,人們常常覺得必須站隊。你怎麼看“反對AUKUS就是在幫中國”這種批評?你又怎麼看這種更廣泛的“中美二元對立”相關話語架構?
**薩姆·****羅格文:**我認為這顯然是一個非常膚淺的論點。這兩者完全可以兼容,並不難調和。真正的爭論只是關於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從我的角度看,一個錯誤的想法是相信美國會全心全意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美國會在某種程度上幫我們,但我認為未來美澳同盟的重要性會下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因此如果澳大利亞希望在中國崛起的時代保持主權和戰略自主,我們必須靠自己。
另外我要説的是,總體來看,澳大利亞國內的討論還是相對成熟的。你剛才説的那種論調——“反對AUKUS就一定是親中”——其實在澳大利亞的辯論中相當少見。偶爾會有,但大多不是主流聲音。所以總體上,我覺得澳大利亞在這個問題上的相關討論還是比較成熟的。
李澤西:有人可能會不同意你的前提假設,即美國會逐漸撤離亞洲。總體上,你聽過最有説服力的“美國會繼續維持必要的投入來抗衡中國”的相關論點是什麼?
**薩姆·**羅格文:我聽過的最有説服力的理由其實圍繞“美國的地位”問題。
我覺得“這場對抗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論點並不具有説服力。美國經濟龐大而充滿活力,擁有數千枚核武器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我覺得很難相信美國人多年來所主張的説法,即“除非美國是亞洲的主導力量,否則它就不安全”。我不覺得這種論證能成立。
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呢?如果不是核心利益,那就是“地位”。我聽到不少資深且受尊敬的分析家認為,美國最終會與中國對抗,進入一場新的冷戰,因為它擔心自己被降級為二流國家,而美國的自我認知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我覺得這是最有説服力的理由。歷史上,美國確實有時會採取一些看似短視、與其直接利益不符的行動,僅僅是為了維持自己的主導地位。
但另一方面,相關證據並不一致。美國也會相當冷酷地評估自身利益,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它的很多做法就並不像是一個把“地位”放在首位的國家。所以這大概是我聽到的最有説服力的理由,但我仍然不會給它太高的分量。
李澤西:你有沒有關注到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最近提出的“太平洋防務條約”設想?
**薩姆·**羅格文:是的,我瞭解到了。
李澤西:我簡單描述一下。他的設想是,把亞洲現有的“網格狀”安全關係變得更制度化,打造一個類似北約的集體防禦架構,讓美國不再只是依賴雙邊同盟。他設想這個框架初期會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和菲律賓,也就是所謂“四國小隊”。美國不應像以前那樣只提供“單向保護”,而應要求盟友在安全上做出對等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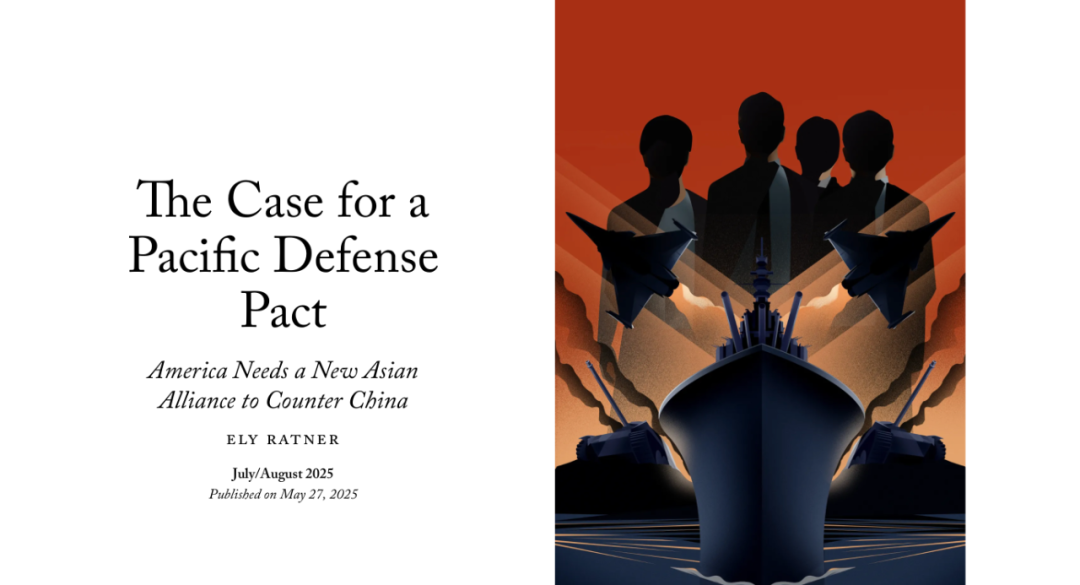
2025 年 5 月,伊利·拉特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建議美國推動建立一個類似於北約的**印太地區集體防衞機制,即“**太平洋防務條約”設想(圖源:《外交事務》)
**薩姆·**羅格文: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我不同意“中國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這一前提。 但先把這一點放一邊,假設拉特納是對的,如果應對辦法是發展一個在亞洲類似北約的聯盟,不論是隻包括“四國小隊”還是包括更多國家,我覺得這都是極不可能的方案。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些國家都和中國有着重要的經濟關係,它們都希望維護這種關係。因此,它們在外交和軍事上願意付出的代價會受到嚴重限制。
第二,地緣因素也使得這種設想難以成立。因為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不會是所有其他國家的核心利益。北約之所以能運作良好,是因為歐洲大陸在地緣上形成了一個連貫的戰略整體。對其中一個成員的攻擊,幾乎等同於對所有成員的攻擊。所以法國把西德當成自己的前線是合理的,蘇聯若攻擊西德,法國就更不安全。因此,法國、荷蘭、丹麥等國都有動力幫助德國防禦,反之亦然。
而在亞洲,這種邏輯並不成立。首先,海洋因素對於戰略地理影響巨大,這個區域範圍極其廣闊。比如説,如果中國和印度爆發軍事衝突,就像幾年前在中印邊境發生的那樣,那並不涉及澳大利亞的核心利益。印度的安全對澳大利亞來説確實重要,澳大利亞在那裏的確有利益,但還遠不到“值得作出重大軍事投入”的程度。反過來也一樣。澳大利亞的安全對印度不是核心利益。這同樣適用於日澳關係、日印關係,等等。
**李澤西:**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澳大利亞此前非常盲目地假設特朗普政府願意堅定支持AUKUS。即使是像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這樣堅決反對AUKUS的人,也預測美國會繼續維持AUKUS,他的理由是這對美國來説本來就極為有利。現在看來,美國卻在利用AUKUS要挾澳大利亞,在防務問題上做出更多、各式各樣的讓步。我覺得你似乎早已預見到了這種情況,但我想先問,你怎麼看待這種普遍的“意外感”?其次,特朗普政府通過向盟友和夥伴施壓、要求各方提供更多的戰略,真能服務於各方共同的戰略目標,還是隻會疏遠夥伴國?

馬爾科姆·特恩布爾對 AUKUS 協議的抨擊引發了澳大利亞政府與反對黨之間罕見的團結時刻(圖源:The Nightly)
**薩姆·****羅格文:**我們當然不應該再感到意外了。在特朗普政府剛上台的前幾個月,美國外交政策的咄咄逼人和強硬態度的確讓人震驚。比如對待加拿大的方式就令人極為震撼,本應震動澳大利亞政府,因為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許多方面都極為相似。我認為澳大利亞政府確實認識到了局勢的嚴峻性,你能從總理近幾個月一些講話的潛台詞中看到這種擔憂。這件事同樣也震動了澳大利亞社會。我認為最近一次大選就是一個信號,表明“讓美國再次偉大”及特朗普主義在澳大利亞極不受歡迎。甚至在大選勝利演講中,總理雖然只是在潛台詞中提及,但他説澳大利亞會始終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不會從其他地方尋找靈感。對我來説,這是對反對黨的明顯暗諷,因為反對黨在競選中對特朗普政府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理念發出過一些同情的聲音,但這在公眾中極不受歡迎。也值得看看總理在約翰·柯廷中心的主旨演講。
所以,是的,澳大利亞已經做出了一系列反應,準備應對未來可能比過去更加動盪的現實,甚至比第一次特朗普政府時期更艱難。上次澳大利亞算是“走運”的,畢竟相比其他盟友,我們的待遇要好得多。但這一次可能不會再一樣了。
歐洲的例子值得我們思考。據説特朗普政府認為,北約承諾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3.5%,甚至5%(包括相關基礎設施),這是一個巨大勝利。而且最近美歐之間簽署了一份貿易和經濟協議,從表面上看對美國極為有利。特朗普政府顯然認為這是非常重大的勝利。
但在國防開支問題上,我會想:歐洲國家為何要增加國防開支?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能讓美國繼續留在歐洲?還是因為他們擔心美國無論如何都會逐漸撤出?我傾向於認為是後者。他們看到美國長期從歐洲收縮的趨勢,因此花更多錢防務是完全合理的。
對澳大利亞來説,我認為邏輯是一樣的。我確實認為很有可能明年初,當下一個《國防戰略審查》公佈時,我們會再次提高國防預算。我覺得不會達到美國要求的GDP的3.5%,但我認為確實會有進一步增長。但問題在於,這是為了留住美國參與澳大利亞的防務,還是在買一份保險,預防美國不像過去那樣可靠?我們拭目以待。但我認為,這無疑已經成為一個公開的問題:美國盟友是否正在開始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未來會變得不那麼可靠。

2023年4月24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等官員在《國防戰略審查》發佈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向媒體講話(圖源:路透社)
**李澤西:**在《針鼴戰略》裏,你認為澳大利亞政府有一個“必做項”,就是要維持與太平洋國家的緊密夥伴關係。但有人認為真要實現其戰略目的可能太難了,因為只要中國在太平洋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就能突破第一島鏈,從而大大複雜化澳大利亞的防務規劃。澳大利亞真的能阻止哪怕一箇中國軍事基地的建立嗎?
**薩姆·****羅格文:**即便中國真的在太平洋島國建立一個軍事基地,雖然會是一個非常令人震撼的舉措,但這對澳大利亞來説並不是世界末日。這會讓我們的安全環境更復雜。
但實際上,我覺得這裏還有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我本人正考慮和同事一起做些研究:假設中國真的在太平洋島國地區建立一個軍事基地,駐紮一個小型艦隊或者半個中隊的海上巡邏機,那麼這對澳大利亞國防軍意味着什麼?我們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來持續監控、保持對這樣一個設施的情報掌握?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我還沒有深入研究過,但值得更多關注。我並不認為這是災難性的,但它確實會要求澳大利亞國防軍考慮更多可能情況。
比如,今年早些時候解放軍艦隊繞航澳大利亞,那已經是對澳大利亞國防軍的一次巨大考驗。有時我們甚至難以維持對它的持續監控,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海上資源去做這件事。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真正認真思考過澳大利亞大陸的防禦問題,以及對整個大陸的監視問題。但我認為,這將是我們未來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不過話説回來,我仍然認為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島國地區有着重要優勢,我們通過太平洋島國論壇以及我們的援助合作,與他們建立了更緊密的關係;澳大利亞是該地區最大的援助夥伴。我們還有文化和體育聯繫,經濟聯繫,比如季節性勞工項目,新西蘭也有類似安排,所以我們是有明顯優勢的。
實際上,我認為最重要的優勢是:太平洋對我們來説遠比對中國重要得多。所以這裏存在一種決心上的不對稱。我們永遠會把太平洋視為一級優先事項,而對中國來説,這可能是二級,甚至三級的優先事項。
李澤西:有一種觀點認為澳大利亞仍然需要依靠美國來制衡中國,因為即便加上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友,該地區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凝聚力與中國抗衡。而且無論如何,東南亞制衡中國的決心似乎沒有澳大利亞那麼強烈。你怎麼看?
**薩姆·****羅格文:**首先,美國是否會在東南亞制衡中國的力量,這不取決於我們,而取決於美國自己。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辦法能改變這一點。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戰略和經濟分量去左右美國的決定。美國會根據它自身的利益做決定。無論我們買多少潛艇,或給美國多少軍事基地,都不會改變這一點。因為歸根結底,美國會根據它的核心利益來決定,並會根據這些利益是否深度綁定到必須與中國打一場戰爭。
在我看來,很顯然東南亞沒有什麼對美國來説重要到它願意為此和中國開戰的利益。這一點在南海已經體現得很清楚。中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進行了大規模島礁建設,美國幾乎沒有採取什麼行動去阻止。原因就是,雖然美國當然更希望中國沒有這麼做,但它的利益並沒有深到要付出巨大代價去阻止中國。
這給我們一個非常嚴峻的結論:澳大利亞和本地區必須靠自己來應對。而且要指出,美國曆來把東南亞當作次要戰區,它的安全利益主要集中在東北亞。
即便越戰也沒有改變這一點。即便美國在越戰中投入了巨大的資源,也不能説明東南亞本身是美國的核心戰略優先。自二戰以來,東南亞都不是美國的戰略中心,現在更不是。

2024年3月6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墨爾本澳大利亞-東盟特別峯會上與時任東盟輪值主席國老撾總理宋賽·西潘敦聯合出席記者會(圖源:路透社)
**李澤西:**簡要談談您之前的著作《我們自己的脱歐》,您當時對澳大利亞的一個預測是,隨着主要政黨的初選票數下降,其中一個黨可能會因為絕望而迎合反移民情緒,從而破壞澳大利亞當前向亞洲開放的發展模式。事實上,在最近的大選中我們或許已經部分看到了這種跡象,兩大政黨實際上都支持限制國際學生人數,聲稱他們加劇了通脹、基礎設施緊張等問題,儘管中右翼聯盟黨更進一步採用了反對“大規模移民”的措辭。這也確實可能是一種有利可圖的政治策略。根據最新的洛伊研究所民調,53%的澳大利亞人認為移民數量過多,比去年上升了5個百分點。您認為您當時的預測得到驗證了嗎?未來可能會如何發展?
**薩姆·****羅格文:**一句話:沒有,我不認為得到驗證。當時我所指的情況,更接近於對澳大利亞國家發展模式的全面否定。我們不應誇大當前事態的規模。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的移民水平遠高於任何主要的經合組織國家。目前,大約30%的澳大利亞人出生在海外,而在另一個移民國家美國,這一比例大約是15%。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自本世紀初以來也大力推動移民,但其移民驅動的人口增長率現已大幅放緩,而澳大利亞尚未出現這種轉折。事實上,疫情之後,移民水平很快恢復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因此我們的人口仍在因移民而快速增長。
你説得沒錯,在邊際上,兩大黨確實抱怨過移民數量,但基本模式並未改變。澳大利亞依賴移民推動增長的模式依然如故。就我個人而言,我非常支持高水平的移民。但我在書中所提出的危險在於,兩大黨對高移民水平的支持,並非基於澳大利亞公眾的明確同意。這在我看來是危險的,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澳大利亞人是種族主義者,或對移民持敵意。我不會忽視你提到的洛伊研究所的民調等數據,但還有大量其他民調證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直觀觀察——你可以告訴我您的感受,但我的經驗是,澳大利亞人極其支持移民。這是世界上最不具種族主義色彩的社會之一,因此澳大利亞在這方面有一個極好的故事。
我的擔憂並不是澳大利亞人會因為種族主義或排外而拒絕移民,而是因為他們從未被真正徵詢過意見。結果可能是他們通過抗議性投票來反對政治階層,而這一政治階層未經同意便將這種發展模式強加給他們。這就是“脱歐”的類比。英國的政治精英同樣未經公眾同意,就將歐洲一體化模式強加給英國。因此,我將脱歐解讀為:它不是反對歐洲,也不是反對移民,而是反對政治精英強加於民的模式。
**李澤西:**在最近的大選中,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兩大政黨的政策普遍被認為缺乏雄心,而經濟與戰略前景卻日益嚴峻;很多議題似乎缺乏實質性辯論。與您書中的觀點相關之處在於,這場選舉似乎表明,為了避免出現“脱歐時刻”,而固守此前那種維持現狀的政治風格,可能並未產生好的結果。您怎麼看?此外,您是否認為,主要政黨政策缺乏雄心,是因為如您書中所提到的,有實際利益訴求的人正大批流失出兩大黨?
**薩姆·****羅格文:**首先,你説得沒錯,確實存在缺乏雄心的現象。許多政策分析人士指出,自本世紀初引入消費税以來,澳大利亞再未進行過重大經濟改革。也許有人會認為碳税是一個重大改革,但幾年後它就被取消了。所以,可以説澳大利亞確實缺乏雄心。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自那以來,澳大利亞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經如此。除去疫情期間那場非常短暫、非常輕微的衰退外,澳大利亞已經超過30年沒有出現過經濟衰退。所以很難説澳大利亞被嚴重管理不善。當然,我們很幸運,趕上了資源需求暴增,但這不可能只是運氣。若沒有相當合理的經濟管理,是不可能連續數十年避免衰退的。澳大利亞人很少願意將智慧歸功於政治家或公務員,但連疫情本身也證明,澳大利亞在政策層面有很強的領導力,並且具備巨大能力去應對困難和緊急情況。所以,這並不完全是一個關於停滯與缺乏雄心的故事。
儘管如此,我確實認為,有一個邏輯可以解釋為什麼澳大利亞不像1980到2000年那20年間那樣推進改革。我的書中得出的答案是:這是因為兩大黨如今都太小了,它們在澳大利亞公共生活中所佔的分量太淺。它們的黨員數量非常少,選民的支持率也很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執政,它們也沒有真正的掌控感,缺乏權威。因此,它們變得非常規避風險,不願引入重大改革,因為它們覺得自己沒有獲得公眾的授權去這麼做。
我認為這是解釋澳大利亞缺乏雄心的一個合理角度。當然,另一種解釋也可能成立,那就是改革本身極其困難。25年的間隔或許並不算反常,也許下一次重大改革就在不遠的將來。

2025年4月28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與工黨貝內隆選區議員傑羅姆·拉克薩勒在提前投票站與選民會面(圖源:Getty Images)
**李澤西:**最後,也許我們可以嘗試回到開頭的地方。在你的書《針鼴戰略》中,你其實是在主張澳大利亞採取某種意義上的“脱歐”,即做出與兩黨精英共識相悖的決定。首先,你會這樣理解自己的立場嗎?其次,這可能是一個更為哲學性的問題、不易泛泛而談:你對當下愈發尖鋭的“精英VS民眾”二元對立怎麼看?我們是否應該把這當作一個契機,去從根本上重新審視社會與政治結構,還是應該抵制民粹浪潮、重新認識精英的重要性?
**薩姆·****羅格文:**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公眾與精英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裂痕。我們掌握的所有民調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公眾對美澳同盟有着壓倒性的支持,對AUKUS也有相當穩固的支持。所以在這一議題上,並不存在公眾與精英的明顯分歧。我認為部分原因在於,當公眾面對自己不瞭解的問題時,往往會向精英尋求答案。因此,當我們看到公眾非常支持美澳同盟時,這很可能只是反映了精英本身也持有這樣的立場。特朗普政府讓這一點變得更復雜,因為特朗普在澳大利亞極不受歡迎,這引入了新的變數。
我確實認為,澳大利亞在精英與公眾之間的鴻溝上存在一些危險信號,而這其實是整個西方政治的普遍現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主要政黨都處在長期衰落之中。人們不再加入工會,也不像過去那樣去教堂,更不會像以前一樣參加各種公民組織。總的來説,我們正在見證公眾與公民生活的脱節。事實上,疫情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它加速了西方民主國家中原本就存在的社會原子化過程,因為我們發現,幾乎一切都可以在家裏完成:可以在家工作,可以在家購物,可以在家享受所有娛樂。因此,社會的原子化,也包括政治的原子化,早已存在,而疫情只是大幅加速了這一進程。
然而,與西方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這種原子化在澳大利亞並沒有催生民粹主義。我們沒有出現類似特朗普的人物,沒有出現“脱歐”,也沒有出現像德國或歐洲其他地方那樣的極右翼政黨的崛起。
我認為其中有很多原因。最常見的解釋是強制投票,這往往有利於中間路線而非極端勢力。我認為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們的精英沒有像其他西方國家那樣“讓公眾失望”。我剛才提到過疫情,我們的確經歷了嚴格的封鎖,但總體上我們度過得還不錯。特別是我們的經濟管理精英——不是衞生領域的精英,而是經濟管理精英——表現非常好,因此我們只經歷了非常短暫的衰退。這可能就是我們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差別。當然,這並不是説未來不會發生,但至少目前為止,民粹主義在澳大利亞還沒有真正站穩腳跟,不像西方世界的很多地方那樣。

2025年5月3日,選民在澳大利亞悉尼的一處投票站參加投票(圖源:新華社)
**李澤西:**稍微對你提出一點挑戰:畢竟疫情過後,生產率確實在下滑,社會凝聚力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再加上很多人都在談論澳大利亞整體戰略環境的急劇惡化。所以或許這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變化,人們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會對這種突然變壞的局勢做出反應。
**薩姆·****羅格文:**坦白説,我不是經濟領域的專家,所以不太願意在生產率問題上評論太多。關於更宏觀的問題,即澳大利亞是否可能面臨與西方其他國家相似的政治條件,我持開發態度。但至少從目前來看,似乎還沒有出現那樣的跡象。比如,選民脱離主要政黨,並沒有轉向極端勢力,而是轉向了其他中間派運動。“Teal運動”現象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所以我們並沒有看到主要政黨失寵導致極端主義更受歡迎。事實上,那種對大黨的失望與不滿,反而被引導到了其他總體上走中間路線的政治運動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