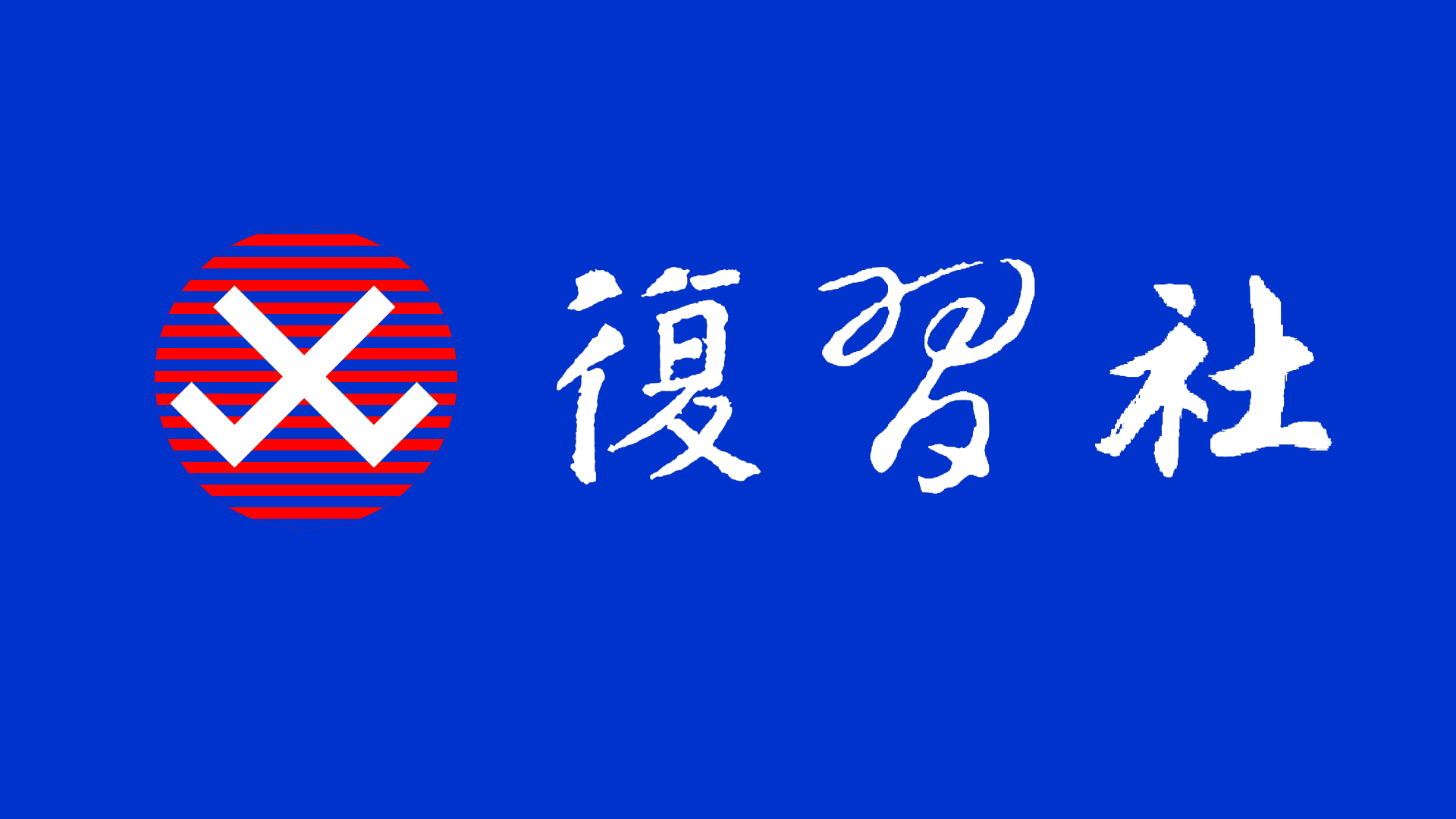發達國家的終結時代來了_風聞
江云天-08-29 12:05
——先發優勢帶來的超額利潤、無限增長的傳統模式與有限資源、公平分配之間的根本衝突,是當前全球經濟格局的核心矛盾。
一、先發優勢與超額利潤的 “不可持續性”:三重必然約束
發達國家依託工業革命、技術壟斷、全球規則制定權形成的 “超額利潤體系”,本質是 “歷史階段性紅利”,隨着時代發展必然面臨三重不可逆的約束,使其難以長期維持:
1. 技術擴散:超額利潤的 “護城河” 逐漸瓦解
先發優勢的核心是 “技術壟斷”(如早期蒸汽機、後來的半導體、現在的高端芯片),但技術的本質是 “可傳播、可模仿、可迭代” 的 —— 後發國家通過技術引進、人才培養、自主研發,必然逐步打破壟斷,壓縮超額利潤空間:
案例 1:製造業轉移。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依託汽車、電子產業的技術優勢,獲取全球製造業超額利潤;但隨着日本(汽車、半導體)、韓國(電子、造船)、中國(全產業鏈製造)的技術追趕,全球製造業利潤從 “美國壟斷” 轉向 “多極競爭”,美國汽車產業利潤率從 1960 年代的 15% 降至當前的 5% 左右。
案例 2:新能源技術。過去十年,歐美在光伏、風電技術上的先發優勢,隨着中國在光伏組件(全球產能佔比 80%)、風電整機(全球產能佔比 60%)的技術突破被打破,光伏度電成本從 2010 年的 3 美元 / 千瓦時降至 2023 年的 0.03 美元 / 千瓦時,歐美企業的超額利潤幾乎消失,行業利潤轉向 “規模效應 + 成本控制” 的競爭。
這種 “技術擴散→壟斷打破→利潤平均化” 的過程,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先發國家若不能持續創造顛覆性技術(如當前 AI、量子計算的競爭),超額利潤必然逐步萎縮。
2. 資源環境約束:無限增長與有限資源的根本衝突
發達國家的超額利潤,很大程度上建立在 “低成本佔用全球資源” 的基礎上(如殖民時代的原料掠奪、工業化時代的能源消耗),但地球資源(能源、礦產、生態容量)是有限的,這種 “資源依賴型增長” 必然面臨天花板:
數據層面:全球人均碳排放約 5 噸,而美國人均碳排放達 14 噸(是全球平均的 2.8 倍),這種 “高消耗、高排放” 的增長模式若被全球複製(如全球 78 億人都達到美國的碳排放水平),需要 5 個地球的生態容量,顯然不可持續。
現實矛盾:當前全球能源危機(俄烏衝突後的油氣價格波動)、礦產爭奪(鋰、鈷等新能源金屬的價格暴漲),本質是 “傳統增長模式下資源供需失衡” 的體現 —— 先發國家若繼續維持 “高資源消耗換超額利潤” 的路徑,必然引發與後發國家的資源爭奪,甚至對抗(如歐美對鋰資源的 “本土化戰略”、對非洲礦產的控制)。
3. 全球利益分配失衡:超額利潤的 “合法性危機”
先發國家的超額利潤,往往伴隨 “中心 - 外圍” 的全球分工體系(中心國家掌握技術、品牌、金融,獲取高利潤;外圍國家承擔製造、資源供給,獲取低利潤),這種分配模式隨着後發國家的崛起,必然引發 “合法性質疑”:
案例:蘋果手機的利潤分配。2023 年,一部售價 1000 美元的 iPhone,蘋果公司獲取約 50% 的利潤(500 美元),而中國組裝廠僅獲取約 3% 的利潤(30 美元),這種 “品牌技術壟斷→超額利潤” 的模式,隨着中國、印度等國本土品牌的崛起(如小米、傳音),正面臨 “利潤再分配” 的壓力 —— 消費者開始選擇性價比更高的非歐美品牌,蘋果的超額利潤空間已從 2015 年的 65% 降至 2023 年的 50%。
社會層面: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全球最富 10% 人口掌握 85% 的財富),本質是 “先發優勢帶來的超額利潤未被合理分配” 的結果,這種失衡必然引發後發國家的不滿(如發展中國家對 “數字税”“碳關税” 的反對),甚至導致全球治理體系的動盪(如 WTO 改革受阻、區域貿易協定碎片化)。
二、經濟增長魔咒的本質:“量的擴張” 替代 “質的提升”,陷入 “增長依賴症”
你提到的 “經濟增長魔咒”,核心是傳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 “無限量增長” 的路徑依賴 —— 將 “GDP 增長” 等同於 “社會進步”,忽視了增長的質量(公平分配、資源效率、民生福祉),最終導致 “增長無意義”(即 “GDP 增長但民生未改善”)或 “增長不可持續”(資源耗盡、生態崩潰):
1. 增長的 “邊際效益遞減”:投入越多,收益越少
傳統增長模式依賴 “資本、勞動力、資源” 的投入,但隨着投入增加,增長的邊際效益會逐步遞減:
工業時代:早期投入 1 單位資本,可帶來 2 單位 GDP 增長;但當產能過剩後(如鋼鐵、水泥),投入 1 單位資本可能僅帶來 0.5 單位 GDP 增長,甚至引發產能浪費(如中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從 2010 年的 85% 降至 2023 年的 78%)。
服務業時代:歐美髮達國家的 GDP 增長主要依賴服務業(如金融、醫療、教育),但這些行業的增長也面臨瓶頸 —— 金融行業過度擴張會引發金融危機(如 2008 年次貸危機),醫療教育的過度商業化會導致民生成本上升(美國人均醫療支出達 1.2 萬美元,是中國的 10 倍,但預期壽命低於中國)。
這種 “為了增長而增長” 的模式,最終會導致 “增長成本高於增長收益”,陷入 “增長魔咒”:不增長會引發失業、債務危機,增長又會帶來資源浪費、社會失衡。
2. 增長與民生的 “脱鈎”:增長不代表福祉提升
傳統增長模式將 “GDP 總量” 作為核心目標,忽視了 “增長成果如何分配”:
美國案例:2000-2023 年,美國 GDP 從 10 萬億美元增長至 25 萬億美元(增長 150%),但底層 50% 人口的實際收入僅增長 10%,而頂層 1% 人口的收入增長了 200%—— 這種 “增長偏向少數人” 的模式,導致社會撕裂(如民粹主義崛起、街頭抗議頻發),即使 GDP 持續增長,社會穩定性仍在下降。
中國警示:過去幾十年中國依託 “投資 + 出口” 實現高速增長,但也面臨 “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貧富差距” 等問題,因此提出 “高質量發展”(從 “速度優先” 轉向 “質量優先”),本質就是要破除 “增長魔咒”,讓增長與民生改善、生態保護掛鈎。
三、破局方向:構建 “有限富餘社會”—— 從 “量的爭奪” 轉向 “質的共享”
“有限富餘社會” 的核心不是 “否定增長”,而是 “重構增長的目標”—— 承認資源有限、增長有邊界,將經濟體系從 “無限量擴張” 轉向 “有限量優化”,核心是實現 “三個轉變”:
1. 增長目標:從 “GDP 總量” 轉向 “福祉總量”
不再將 GDP 作為唯一考核指標,而是建立 “多元評價體系”,包括:
公平分配指標:如基尼係數、中等收入羣體佔比(中國目標 2035 年中等收入羣體達 8 億人);
資源效率指標:如單位 GDP 能耗、水資源利用率(歐盟目標 2030 年單位 GDP 能耗較 1990 年下降 55%);
民生福祉指標:如預期壽命、教育醫療可及性(北歐國家將 “幸福指數” 納入政策制定依據)。
這種轉變的本質是:讓增長服務於 “人的全面發展”,而非 “資本的無限增殖”—— 例如,芬蘭的 GDP 增速雖僅 1-2%,但通過高福利、低貧富差距,連續多年蟬聯 “全球最幸福國家”,證明 “有限增長也能實現高福祉”。
2. 資源利用:從 “線性消耗” 轉向 “循環利用”
面對資源有限的約束,“有限富餘社會” 必須建立 “循環經濟體系”,減少對 “新增資源” 的依賴:
生產端:推行 “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如汽車行業的 “模塊化設計”,讓零部件可回收;電子行業的 “以舊換新”,減少電子垃圾);
消費端:倡導 “理性消費、共享消費”(如共享單車、二手平台的興起,減少 “一次性消費”;歐美 “極簡主義” 生活方式,降低人均資源消耗)。
案例:德國的 “循環經濟” 實踐 —— 德國垃圾回收率達 68%,再生資源產業產值佔 GDP 的 2%,通過 “垃圾收費、回收補貼” 等政策,實現了 “資源消耗下降但經濟仍增長”(2010-2023 年,德國單位 GDP 能耗下降 30%,GDP 增長 25%),證明 “有限資源也能支撐可持續增長”。
3. 全球治理:從 “零和博弈” 轉向 “多元協作”
破除 “中心 - 外圍” 的分工體系,建立 “公平的全球利益分配機制”,是構建有限富餘社會的關鍵:
技術共享: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開放低碳技術、醫療技術(如中國向非洲提供光伏技術援助,幫助非洲實現 “綠色工業化”),避免技術壟斷帶來的超額利潤,讓全球共享技術紅利;
規則公平:改革全球貿易、金融規則(如 WTO 的 “特殊與差別待遇” 條款,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政策空間;建立 “全球碳定價” 機制,避免 “碳關税” 成為貿易壁壘),讓後發國家有更多機會參與全球利益分配;
公共產品共建: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疫情、糧食安全等全球挑戰(如中國提出的 “全球發展倡議”,推動 100 多個國家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糧食合作),將 “資源爭奪” 轉化為 “合作共贏”。
四、破除增長魔咒,才能跳出零和博弈
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與超額利潤不可持續,本質是 “無限增長模式” 與 “有限資源、公平需求” 的根本衝突;而當前全球的對抗(貿易保護、技術脱鈎、資源爭奪),正是這種衝突的外在表現 —— 若繼續陷入 “零和博弈”,最終只會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生態崩潰、社會撕裂。
構建 “有限富餘社會”,不是要回到 “貧困時代”,而是要建立 “更合理的增長與分配體系”:承認增長有邊界,但通過 “質的提升”(公平分配、資源效率、民生福祉),讓有限的資源創造更多的共同福祉。這需要全球各國(無論是先發國家還是後發國家)放棄 “零和思維”,轉向 “共贏協作”—— 只有這樣,才能打破 “增長魔咒”,讓人類社會走向可持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