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體育行業二代的自白:我不接班了_風聞
懒熊体育-懒熊体育官方账号-从商业财经角度来解读体育事件,还原一个好故事08-30 1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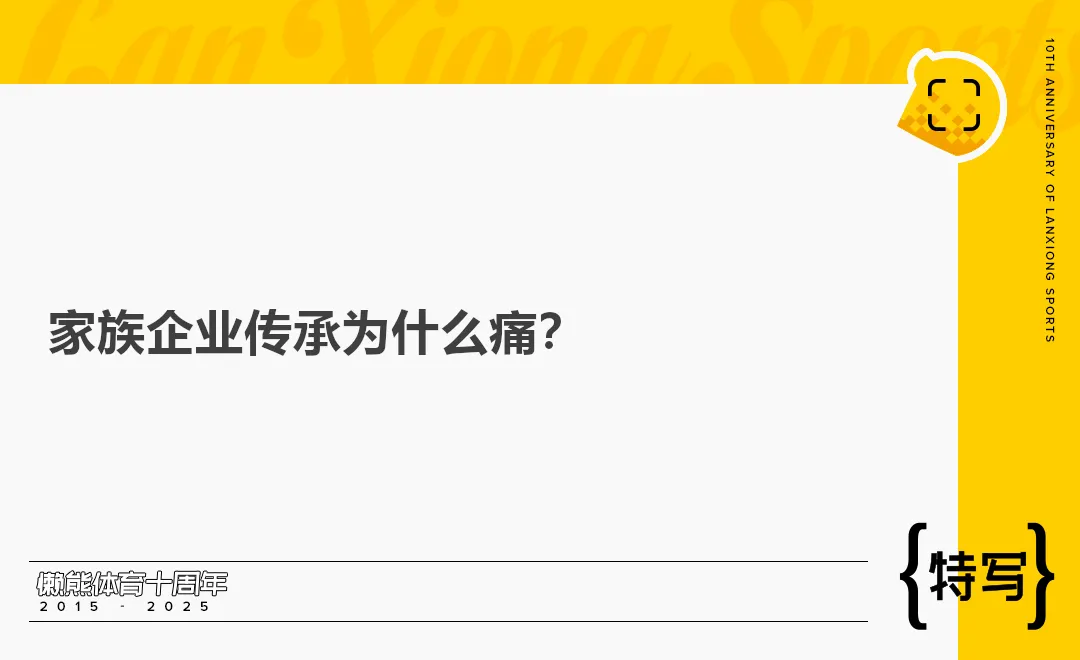
2025年,84歲的雙星名人創始人汪海控訴被孫子控制自由,兒媳和兒子則帶人闖入辦公室搶奪公章。更早的時候,萬洪建用頭撞擊玻璃牆櫃,滿頭血跡。而他的父親,雙彙集團創始人萬隆在一旁要求“拍照取證”……兩代人的分裂已經成了中國家族企業傳承的一種模式。
家族企業的問題在於,親情要被迫進入權力的地盤,在這裏沒有純粹的權力問題,也沒有純粹的倫理問題。在公司這個本應去人性的制度中,親情反而餵養了怨恨。更不要説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隔着兩種人格,兩個時代。
體育產業二代北辰的故事沒有上面的故事那麼戲劇化,但結局並沒有不同。這個故事從温暖開始。在一頭,是爸爸做的溜肉段,是樹林裏的錄音機,是揹着爸爸不讓死亡追上他。但在另一頭,是分家協議,是“刀刀見血”,是淚水漣漣。
北辰曾經認為自己是當仁不讓的接班人,但現在他已經放棄了繼承權。已經釋然的北辰為我們講了自己的故事。
以下是北辰的自述:
我是北辰,我的父親是某體育運動器材品牌A的創始人。
在2023年的某天之前,我已經在A公司工作了十三年,並自認為是A公司的接班人。但在那一天,我被父親從A公司總經理的職務上免職,讓出管理權,就此離開了這家親手帶上高點的公司。
同年,我創立了自己的品牌。此後行業裏一直有一種説法,這是我和我父親唱雙簧,壟斷市場。
我也以為父親在親自管理後,會體諒我,但是後來的事情出乎了我的意料。家庭內部的紛爭無法彌合,最終我放棄了繼承權。
思考之下,我決定把這個故事講出來,希望我的故事能為中國家族企業的傳承有所貢獻。

從作坊到行業老大
1992年,跟隨改革開放下海潮。我父親離開東北,拿着賣房子的錢,來到D市經商。
在D市,我父親注意到在這裏有一項運動相當流行。我父親感到這是個機會,於是開始為這項運動提供場地,很快就賺到了一筆錢。之後我父親又看中了這項運動相關的器材生意。於是90年代末,我父親創立了A公司。
在前十幾年,公司做得很辛苦。
我們在這個行業的競爭處在下風,被行業頭部公司B壓制。公司經營很難,有時候公司發工資還需要靠我的積蓄來週轉。
不僅如此,公司在輿論上也不佔上風。當時我父親想推動運動的發展,但很多人在網上説風涼話,説我父親這麼做是為了賣貨。我父親不服氣,就在網上跟人辯論,他不會打字,就用手寫板寫,一天也寫不了多少字。那個時候他本來就得了重病,又經常熬到下半夜,身體迅速就垮了。就這樣,家裏提出讓我趕緊回來幫忙。
那個時候我的工作非常順利。從某名牌大學畢業後我留在C市從政,家裏叫我回來的時候,我已經在C市做到了正處級,又是全市最年輕的市管後備幹部,仕途光明。所以關於要不要回去,當時我是糾結的。
但當我請假回家瞭解行業的時候,我看到當時做我們這行並不受人尊重,我父親當時快六十歲了,還有人讓他坐冷板凳,談下一單生意十分吃力,還要處處“哈着”甲方,這讓我很心酸,也是這種情緒讓我下決心辭掉了C市的工作,回來幫父親完成心願。
2010年我進入公司。
從C市到D市郊區,生活條件一落千丈,但最讓我苦惱的是,我家的公司沒有我頭腦中現代企業的樣子,還是作坊式的。
公司沒有計劃,也沒有分工,大家像沒頭蒼蠅一樣,眼前有什麼事情就處理什麼事情,每天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麼。
財務上,我母親負責公司財務,她當時的財務管理方式是,她手裏有很多張銀行卡,但公私不分,買衣服和買材料都用這些卡,到月底又開始回憶每筆錢的用途。我母親認為所有錢都進這張卡了,也沒亂花,錢能管丟?因為我父親不瞭解知識產權保護,公司甚至連創始時的名字都沒有保住,只能改名。
兩代人的思維差異很大,我和父母之間經常因為公司的事情產生矛盾。
有一次開會,計劃要討論一個業務問題,但父親講了快半個小時,一句重點都沒有。我提示他:“爸,咱能不能回到主題上?”我父親認為我不尊重他,散會後大發雷霆,然後我們爭吵起來,他告訴我:“你別幹了!”
這句話説出來對我衝擊非常大。這次衝突之後,我到C市散心,晚上我坐在水邊,想到自己公選上處長,在C市生活好好的,父母一句話把我叫回來了,在作坊一樣的公司給業務打補丁。現在就這麼隨隨便便告訴我別幹了,那讓我去哪裏呢?我感覺自己被欺騙了,整個人很迷茫,那一晚,我甚至有往水裏走的念頭。

後來我們意識到不能再吵下去了。內部,因為財務管理和其他原因,我父母發現一年下來很辛苦但賺不到什麼錢,很惱火。外部,公司的競爭形勢又異常嚴峻。內憂外患之下,我們達成共識——公司要改變。
那個時候我本來和父母提出直接把公司傳承給我,但被他們明確拒絕了。當時我沒有多想,因為當時我父親只有六十多歲,又對公司感情很深,我理解。於是我又提出由我承包公司,三年一個承包期,上交承包費。這次他們同意了。
2014年我接手A公司,一步步對公司進行大改造。
我把原來的公司關掉,成立了新公司。新公司是正規化的,公司從個體户變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在管理上,我引入董事會制度,父親和母親分別擔任董事長和副董事長,我擔任經理。我和父母提了一個要求,他們不要越過我指揮,團隊由我來帶領,“油瓶倒了我來扶”。然後我開始招聘高素質員工,一批大學生就是這個時候進入公司的。
在業務方面,公司做了重新定位。我們這項運動中有幾種不同的玩法,當時頭部企業,我們的競爭者B,與偏西式的玩法綁定,但我認為這種玩法正在走下坡路,所以把這塊市場主動讓給B品牌,而我們則和中式玩法綁定,後來吃到了中式玩法品類增長的紅利。
另一方面,我推動品牌高端化。因為市場未來一定會飽和,只有具備投資價值的產品才能勝出,所以我們要成為行業裏的愛馬仕。我認為體育產業的核心是賽事IP,要做出品牌就需要做賽事IP。於是我們開始做賽事,營銷上有了抓手。
疫情期間,在別人恐懼的時候,我們“貪婪”,逆勢投入,又讓公司上了一個大台階。最火熱的時候我們的產品需要提前一年預定。公司登上了創立以來的高峯。
當不再為業務吵架,我和父母的關係一度緩和了,我也很享受家人的其樂融融。但在公司成了行業老大之後,這種平靜戛然而止。

在家裏要憋瘋了
2022年,父母突然提出“在家裏要憋瘋了”,我母親還批評工廠不夠整潔,希望回來幫我管理廠務。我知道這樣的多頭管理對公司是不好的,但他們反覆和我提,我就同意了。
心軟,就會犯錯。
母親接管工廠後,把我安排在工廠的行政下屬架空了。控制了工廠之後,我父母開始干預行政條線(當時賽事、銷售、後勤和採購等等工作一般是大學生員工在做,我們把這些人統稱為行政條線)。
那個時候他們常對我抱怨,公司的年輕人不懂禮貌,見面不和他們打招呼。我把這種抱怨理解為是因為年紀大脾氣變了,雖然覺得很可笑,但還是囑咐公司裏的年輕人,見到我父母要停下打招呼,我以為這樣就可以了。但此後,他們又開始批評我業務做得這裏不對,那裏不對。小小的一件事,也要給我打電話——其實當時我們都在D市。這樣的電話基本兩個小時起步,有時我一天接會到兩、三個電話這樣的電話,連午飯都吃不上。
我受不了這樣的折磨,有一次我忍不住説了氣話:“你們要再這麼折磨我,我就不幹了,你們自己幹吧!”
他們回答:“好。”
我一下就愣了。
“我們不能接受你的挑戰,我們要證明我倆乾的比你好。”

他們是不是中邪了?
我父母當天就想接管公司。
這個時候一些老同事勸我不要和父母爭,出去避避風頭,等他們氣消了再回去,於是我就離開了D市。但當我在外面晃了快兩個月之後,我和同事們漸漸發現情況不對。他們不是慪氣,是玩真的。
中層先慌了,起草了聯名信給我父母。信的意思很簡單:公司大好局面剛出現,一家人不要折騰,希望儘快恢復董事會制度,讓公司回到正軌。
我因為這件事回了D市。回來我第一件事是先去爸媽家,我一進屋給他們磕了三個頭:“我錯了。”
然後我和父母聊了十幾個小時,他們之前批評我的事我一件一件做了解釋——當時我還認為這些批評是就事論事。出來之後我很得意,覺得這回思想工作做透了。
第二天我就直接去了公司正常工作,把業務接過來,沒有特意開會去説明什麼——我認為低調處理是保全父母的面子。
因為我“不請自回”,突然之間在釘釘上、在現實中都沒有人向他們彙報工作了,我父母覺得自己被欺負了,非常生氣。但因為公司上下人心思穩,他們只能忍下這口氣。公司看起來恢復了正常秩序。
因為出了這樣的事情,所以那一年的年會為了讓父母開心,我們刻意把他們“捧”得很高,他們以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的身份上台回顧了創立公司的過程,我父親還發布了公司未來的戰略。到了晚上的聯歡會,一個員工上台唱了一首歌《咱爸咱媽》——原本我們計劃要年後和這名員工解除合作關係,但他當時已經嗅到了領導層的裂縫,開始站隊。當時我就在台下,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這個親兒子就要出局了。
後來又發生了一系列事情:2022年,我接受了一家媒體的採訪,這家媒體把我的頭銜寫成了董事長,這顯然是一個無心之失,但我父親十分介意。
2023年,公司參加了一個行業展會。我在公司十幾年了,在行業有很多老朋友。在展會上,他們來到A公司的展位和我打招呼、合影。這樣正常的事情卻觸怒了我父親。回來之後,他説:“行業現在以北辰為尊。”
而我想不到除了傳承給我,還有其他可能,一直自認為是接班人,沒有警醒這些信號。
一次次類似的事件後,情況急轉直下,父母后來挑明瞭——我必須走。就這樣鬧了兩、三個月,親人已經不像親人了。雖然當時公司的人、財、物都在我手上,但再鬧下去公司和這個家都完了。我當時誤以為也許日後父母“親政”後會理解我的難處,一家人還有迴轉的餘地,所以退後了一步——那就分家吧。
但我搞不懂父母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本來是一個很唯物的人,但那段時間我甚至想從超自然的角度去解釋父母的行為,“他們是不是中邪了?”

三版協議
一開始談分家的時候,父母認為,既然我是承包的,那麼他們不想讓我承包了,我應該淨身出户。我提出我走可以,但作為股東,我有權利每年拿分紅。但公司這個時候每年的利潤已經很高,他們不願意給我分紅。
我們找來的中間人(也是我們家一個很有能力的親屬)提出,按照商業邏輯,應該把我承包期間創造的收益給我,但評估之後發現這筆錢是如此之多,如果一次性把這筆錢給出去,公司就沒法運轉了,哪怕是我父母當時已經給這筆錢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所以我們商定分期付款買斷我的股份。
談好之後,在親戚們的見證下,我們簽了分家協議。簽了協議之後出門,大晴天突然下起了雨,我的眼淚也流了下來。爸媽要求我不能繼續在這個行業工作,也不能繼續留在D市。我突然覺得很失落,天地之大,我該去哪裏?做什麼?
我以為這就算分家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媽突然提出要重新談。
談就談吧。為了讓第二稿協議有效力,我又找到一位和我們雙方關係都很好,德高望重的中間人,在D市專門租了一間會議室談。我們幾個從晚飯後一直談到第二天早上,終於達成一致,那個時候大家已經極度疲憊。
但就在回家的路上,我得知了他們又要反悔的消息。當我想請中間人和我們回去繼續談的時候,中間人説什麼也不回來了,其中的潛台詞很清楚:“你爸你媽不講信用”。
第二版協議後來還是簽了,但事情到這裏還沒有結束。
這一版協議裏包含迴歸條款。在剛起草協議的時候,我以為父母接手公司之後,會理解我的難處,所以我們在協議裏設置了“迴歸條款”。如果公司出了問題,或者觸發了約定的條件,我將自動迴歸。
不久之後,第二版協議被推翻就是因為這個迴歸條款。
他們再次反悔,我本來是非常抗拒的,我認為這種處理商業協議的方式太兒戲了。但最後我還是同意了,其中的曲折,不足與外人語。
2023年5月31日,我們終於在第三版、也是最後一版協議上落筆。同一天,A公司宣佈免去我的總經理職務。
我離開了自己奮鬥十三年,親手帶上高峯的企業。前後三版協議,一開始還温情脈脈,到最後已經圖窮匕見。至今這三版合同我都還保留着——這是記錄一個家庭分崩離析的文物。


原來是自作多情
就這樣2023年我創立了自己的品牌F。
我用了當年盤活A公司同樣的方法,定位理論。
任何行業都有一個對立定位的機會,經典的和年輕的,有可口可樂就有百事可樂。而我們發現在這個行業,年輕人這一塊是空白,一刀切下去市場就出來了,這樣一劃分,也把所有做老式器材的品牌逼到了牆角。
F比我父親的品牌起來的快多了。
主力產品用了51天銷售額就破了2億,當我們宣佈要漲價之後,漲價的前一天訂單雪片一樣的飛過來,那天我們單日下定簽單超過3000單。
一個晚上,我和同事們足足放了二十分鐘煙花來慶祝這個時刻,用年輕的方式,告訴這個行業,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
但家庭給我的折磨,並沒有隨那一萬響煙花停止。
我們家的事對我是曠日持久的心理折磨,在搶奪公司控制權的過程中,我父母的一些行為,讓我已經不認識他們了。
父親是在一次中層會議上宣佈我要離開的,即使那個時候我仍然對修復父子關係抱有幻想。但在這個會之前,我父親帶着當時的財務總監來到我的辦公室,我忍着眼淚勸他,“爸,我們是親父子,為一個公司鬧成這樣值得嗎?”但是我父親十分堅決:
“執行協議吧。”
然後就轉身走了。當時我的辦公桌上放着一張我爸我媽的照片,悲憤之下我把那張照片取出來扔掉了——這是一個毫無人情的家庭。
開會的時候,對着十幾個中層,我父親説:“現在北辰不再擔任總經理了。”之後是安靜。沒了。
沒有感謝,沒有送別,連場面話也沒有。
“這會我是不是不適合再開了?” 我問。
“你可以走了。”
我就一個人離開會議室,收拾好東西之後,我和司機兩個人像外國電影裏的上班族那樣抱着紙箱子孤零零地離開了。第二天,公司的門禁系統沒有我這個人了。
我經常想,如果我要送走一個和公司走過十幾年的人,會怎麼説,怎麼做?他是不是值得一句:“我們永遠歡迎你回來坐一坐”?
新品牌的火爆讓我父親非常惱火,他認為有些人是因為A公司買了新品牌的產品,怒氣衝衝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們撇清和A公司的關係。我們很快就在官方渠道聲明,F品牌和A公司沒有關係,如果因為誤會了兩者關係而訂購了F品牌的產品,可以退款。聲明發出以後幾乎沒有人退款,反而成了一次巨大的營銷勝利。但我不理解這樣的惱火,父親難道不應該為兒子的成就驕傲嗎?
但和這種陌生感並行的是,心理層面上他們還是我的父母。
我還是會想起小時候,我們家在林業局的小鎮生活。在小鎮家家户户都種菜的時候,我們家是種花的。當時家裏雖然物質條件並不好,但爸媽還是買了一台錄音機,到休息的時候,爸媽會在家裏炒好瓜子,帶上錄音機,領着我和弟弟去楊樹林裏聽歌。
直到成年,我還認為父母是我的心理支柱,我們一度可以託付生命。
我父親曾經和老朋友感慨,如果當年沒有我回來幫他,他不可能有時間去治療,病情會一步步惡化,“是我兒子救了我。”
2016年,有一天我父親來到我家,一進門我看見他滿頭大汗,還沒等説話他就倒在地上。
我們家到醫院不遠,我揹他去醫院可能會比做救護車更快。然後我背起父親就往醫院跑,我愛人當時和我一起,她沒有追上我。最後我花了15分鐘把父親背到急診室。等所有事情處理完,我一下就動不了了——我第一次知道脱力是什麼感覺。
但第二天,病因還沒有查出來,人在ICU也沒醒,我提出轉院。醫院答覆,轉院後果自負。在誰也不敢做決定的時候,我説:“我來負這個責。”我提前聯繫好了北京301醫院,等車到的時候,那邊的ICU已經準備好了。到了301之後,病因很快就查出來了,人也搶救過來了。我還記得父親醒過來之後,從牀上坐起來,和我説:“兒子你又救了我一次。”
這樣的割裂讓我有一段時間特別消沉,我愛人説我已經沒有人樣了。
有時頓悟就在一瞬間。2024年冬天,我去了一趟加拿大陪讀高中的兒子。在那段時間我還是一直想着家裏的事情。一天晚上,温哥華下起了小雨,那天很冷,我坐在房間裏看着窗外發呆。我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我問自己,孩子讓我失望到什麼程度,我才會剝奪孩子的繼承權?答案是不會。這個時候,窗外的黑夜“啪”的一下亮起來“自作多情”四個字。

我想起了佛教裏説的“自作多情”。佛印救下一個投河的女子,她告訴佛印三年前她本來嫁了一個好丈夫,又生了孩子,生活幸福。但後來因為她的疏忽,兒子淹死了,丈夫也拋棄了她,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佛印問她:“三年前你又有什麼呢?”所以佛家認為這一切都是“自作多情”,一切都是心湖的投影。
處理我們家的矛盾,我始終帶着親情的視角,我想的是,跟自己父母玩什麼權謀呢?如果不是出於親情,我離開A公司的時候可以把我承包期間創造的收入全部帶走,我也可以讓公司長時間陷入癱瘓。
我頓悟了,我痛苦因為我用情了,以至於讓情感的投影遮蔽了一場權力鬥爭。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在還在承包期的時候,我也曾經邀請股權專家為我們家設計過傳承方案,方案出來之後,我父親提出緩緩再籤,從此再無下文。後來有段時間我父親經常對我提起巴菲特、李嘉誠,還説想幹到九十歲,當時我認為這是個玩笑。
在我和A公司分道揚鑣之後,我明白在父母眼裏,我與他們之間不是傳承的關係,而是權力的競爭關係——在我沒有覺察的時候,他們早已經做出了決定。
在公司崛起之前,我父親的人生是很困頓的。他本來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我爺爺曾經解放前入黨的進城幹部,但後來我爺爺被下放,我父親的童年也一落千丈。畢業之後我父親被分配到林業局的機務段修火車。後來,他在D市創業的過程也很坎坷,一開始在火車站開了一家羊肉泡饃店,但一個多月就倒閉了。飯店倒閉後,我父母靠換廣告牌,刷油漆、安暖氣片養活全家,每天工作到很晚。公司剛開始也磕磕絆絆,直到我承包公司之前,我們家的情況都是比較動盪的。但另一方面我父親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想出人頭地,渴望成為焦點。
可以説我父親的願望和現實一直存在着錯位。
但我父親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公司會成為這麼大的企業,成為呼風喚雨的行業領袖。當錢到達一定數量級的時候,已經不再具有實際意義,但人心會因此生出其他的慾望。我父親觸碰到了以前觸碰不到又渴望的東西,他覺得機不可失,失不再來,他決定掄圓了活。而我在公司,是霸佔了他最珍視的東西。
我那次的低調回歸,在權力的視角下被定義為“奪權”。年輕人不和他打招呼是在向我效忠,而中層的聯名上書就是“逼宮”。
而在不惜代價要刪掉迴歸條款的時候,意圖已經展露得清清楚楚,他們要的是完全掌握公司。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所以我必須離開。而且要讓別人知道我永遠不會回來。
我離開後父親的一系列舉動都是在告訴別人這一點。比如公開表示“不會留1分錢給子女”,比如清洗團隊。
在我離開後,父親很快清洗了一批中層,哪怕他們都精明強幹,因為站隊更重要。當然,其中很多是當初上萬言書讓我回來的那些人。
當時發生的一件事對我刺激很大。有人舉報A公司一名員工向賽事贊助商索要賄賂。這個員工所屬的子公司高管請示父親怎麼處理,我父親交待要堅決處理。所以這名高管就以子公司的名義,在內部發文公佈了處理意見。但發文之後,我父親卻否認要處理索賄的員工,並以越俎代庖的由頭,以一種“林沖誤入白虎堂”的方式,開除了這個為公司勤懇工作十幾年的子公司高管。
本來離開之後我本來想修養一段時間,暫時離開行業。但這件事讓我預感到以後還將有更多的人被清洗,而這批人大部分都是公司的老員工和功臣,我要給他們一個交代,我這才很快創立了F品牌。
做了自己的品牌之後,我對A公司仍然有感情,在商業上對它留有餘地。但我父親告訴我們雙方都比較親近的朋友,現在我們兩個品牌之間,是“刀刀見血”的關係。
對我而言,已經沒有傳承這件事了。繼承權,我不要了。
從此我可以放開做自己的品牌了,畢竟在商場上,第二名沒有謙讓第一名的權力。我年富力強,我有信心能像當年那樣,把自己的品牌做成全國甚至全世界領先的品牌。
我釋然了,我也自由了。

命運已經註定
而我父親的公司命運已經註定。
中國企業傳承屢屢出現問題根源,在上一代的人格中。
從小開始我就被一件事情困擾:上學的時候我學習很好,經常是年級第一,後來工作了也算優秀。但不管怎麼出色,我父親幾乎沒有當面肯定過我,而是經常感慨:“如果你爸當年有這個條件……”。
這一度讓我很困惑,但當我開始研究心理學,我發現這是一種控制,他們擔心肯定會讓他們失去對子女的控制。而我母親也是一個控制慾很強的人,喜歡做服從性測試。當然這一切是在潛意識中發生的,他們自己都意識不到。
控制向前一步會變成“帝王思想”。疫情期間,我父親痴迷於各種歷史題材電視劇,尤其喜歡《雍正王朝》等二月河小説改編的劇——裏面總有一個被美化的千古一帝。在很多傳承出現問題的企業,老一輩都有“帝王情結”。他們抗拒提前做好傳承安排,為的是要把公司控制權抓在手裏直到最後一刻。
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跟不上、看不懂這個時代了。
在談最後一版分家協議的時候,我提出把一款產品專利分給我。
這款產品成型在大概十年前。當時我判斷既然行業有經典的品牌,就會有年輕的品牌,這是普遍的商業規律。讓別人做不如自己做,因此我推動研發了這款針對年輕人羣的產品,並拿到了專利。但我父親擔心這款產品會衝擊A的原有業務,我和他怎麼都説不通,項目就擱置了下來。
這款產品就是F品牌的產品原型。
我帶走的還有我父親覺得只會“花錢”,但實際上是流量入口的網紅和球員資源。一個賣耗材的線上商城,還有一個做場地管理系統,只有幾個人的小公司。但就是這個小公司管理了全國大量的場地,公眾號日活非常高,是一個極為精準的推廣渠道,通過它新品牌一下就鋪下去了。
我父親做這樣的判斷,因為他現在仍然是一個產品決定論者,只要做事情初心是好的,有好產品就能成功。
A公司誕生之後很多年,一直被B品牌壓着打。我父親不理解自己的產品這麼好,為什麼大家還是買B品牌?事實上,那個時候B品牌天天在電視上做營銷,贊助賽事。後來公司崛起,在我父親視角里,是因為艱苦奮鬥。沒有好產品,推銷好沒有用,沒有我,公司照樣能做起來。
事實上在過剩的時代,只有好產品已經不足以從叢林中殺出來,現在的商業世界是高度專業化和分工化的。A公司崛起的背後是一整套鋒利,又環環相扣的邏輯。
我在A公司的時候,採用了直銷的銷售方式,這是由高端定位決定的。要做高端就要做賽事等公關活動,代理商很難把總部的意志貫徹下去,只有自己做才能維護統一的品牌形象。所以多年來A公司在銷售上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
同時,產量保證了有節制的增長。因為市場需求經常是不理性的,超過實際需求的,留下產能缺口能規避過剩風險,讓產品在二手市場的價值放大,一手市場的需求保持旺盛,形成良性循環,從行業看,能讓同行兄弟都有錢賺,一起做大行業蛋糕。
而這套邏輯我父親是看不懂或者説不相信的,所以我離開之後,A公司採取了相反的邏輯。
一方面搞起了區域代理制度和辦事處,這些“藩鎮”導致很多品牌工作無法直達一個區域,尾大不掉。另一方面建廠快速增加產能,而我在A公司時認為行業未來走向還不明朗,貿然建廠有產能過剩的風險。

事實就是如此,工廠建成後很快產能過剩,A公司二手產品的價格應聲而落。
看到價格下跌,又找各地的代理商和黃牛壓貨,為此大幅降低訂貨的訂金比例——而當年我為了給黃牛炒作產品設置門檻,堅持要全款訂貨。
可以説A公司實質上是配合販子壓貨,這導致一線真實消費者很難直接拿到貨,貨到手的週期也變得很長,他們只好向販子採購,增加了採購成本。其中一旦有人真假混賣,消費者將受到二次傷害。另一方面,這樣的行為也增加了公司自己的風險。如果有一天產能上升到一個臨界點,品牌和代理商、黃牛之間將會上演一場拋貨的奪路狂奔。
這些錯誤決策也是組織潰敗的後果。有能力的人走了,上位的新人能力不足,但會在我父親面前説漂亮話,“巧言令色鮮矣仁”,他們的利用了我父親對業務的不熟悉,私下抱團劃分地盤,一起蛀空公司。現在A公司內部山頭林立,我父親很難聽到真話,有被架空的可能。
事實上,企業的結局從我父親決定不交班、我決定不接班那一刻就註定了。這種衰老是客觀的、必然的。當然,也是可悲的。

得到了,也失去了
我講這樣一個故事,是希望為中國企業的家族傳承提供一點看法。
對老一輩來説,如果真愛這個企業,對企業負責,就要做好傳承,否則企業就會隨着老一代生命的枯萎而消散。企業傳承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培養接班人需要時間,也需要用心,如果寄希望於二代在商業上天賦異稟,傳承失敗的可能性很高。所以老一輩應該全力以赴去把傳承作為企業的大事,早做打算,不要抗拒這件事,等到最後發現來不及了,再哀嘆孩子不成器。
對二代來説要有志氣,不要像我曾經那樣試圖通過傷害自己喚醒父母的愛。從心理學上講,這種行為説明還沒有長大。二代要面對現實,有的人也許就是愛自己勝過愛兒女,但又有誰規定企業就必須傳給孩子呢?所以如果和父母衝突,要保留好自己的合法權益,開始新的人生。與其窩裏鬥,不如出去做增量。
對我個人而言,這場風波讓我有所成長。常人不可能有的經歷讓我理解了人性的幽微,也對自己也有所反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原生家庭的投影,影響了身邊的人?現在我更平和了,這次創業,身邊的夥伴相比之前跟我工作的時候更快樂了。

我也丟失了一些東西。
離開後,我曾經給父親打了個電話:“您和媽媽經常教育我受人滴水之恩,要湧泉相報,那為什麼我救了您兩次,您卻一點也不顧念?”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響起一個冷靜的聲音:“那就算你把我的養育之情還了吧。”
電話這頭,我淚水漣漣。
以前,我經常會夢見爸媽。在有的夢裏,我還是孩子。爸正在做飯,做的是我愛吃的溜肉段。但這半年來我已經很少夢見他們了。
作為兒子,我希望父親長命百歲,但那片楊樹林,我們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