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後,一羣學者就如何科學救國展開激辯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科普中国子品牌,倡导“溯源守拙,问学求新”。09-03 10:11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學術界同全國各界一樣,也掀起“救亡圖存”的思潮。然而,在胡適、顧毓琇、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當時的知名學者之間,科學救國之路究竟是以純粹科學立本,還是發展應用科學為先,展開了一場大討論。而即便在抗戰勝利後的幾十年內,這一問題在一些重要的歷史節點仍不時成為爭論的焦點。
本文經授權摘自《奮起:抗戰中的科學與科學家》一書,本書採用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研究方法,融合軍事、教育、工業三重視角,不僅敍寫了一部科技史,更記錄了中華民族在危亡之時如何以科學微光照亮民族救亡的“至暗時刻”,是一部中國全民族抗戰時期科技救國的全景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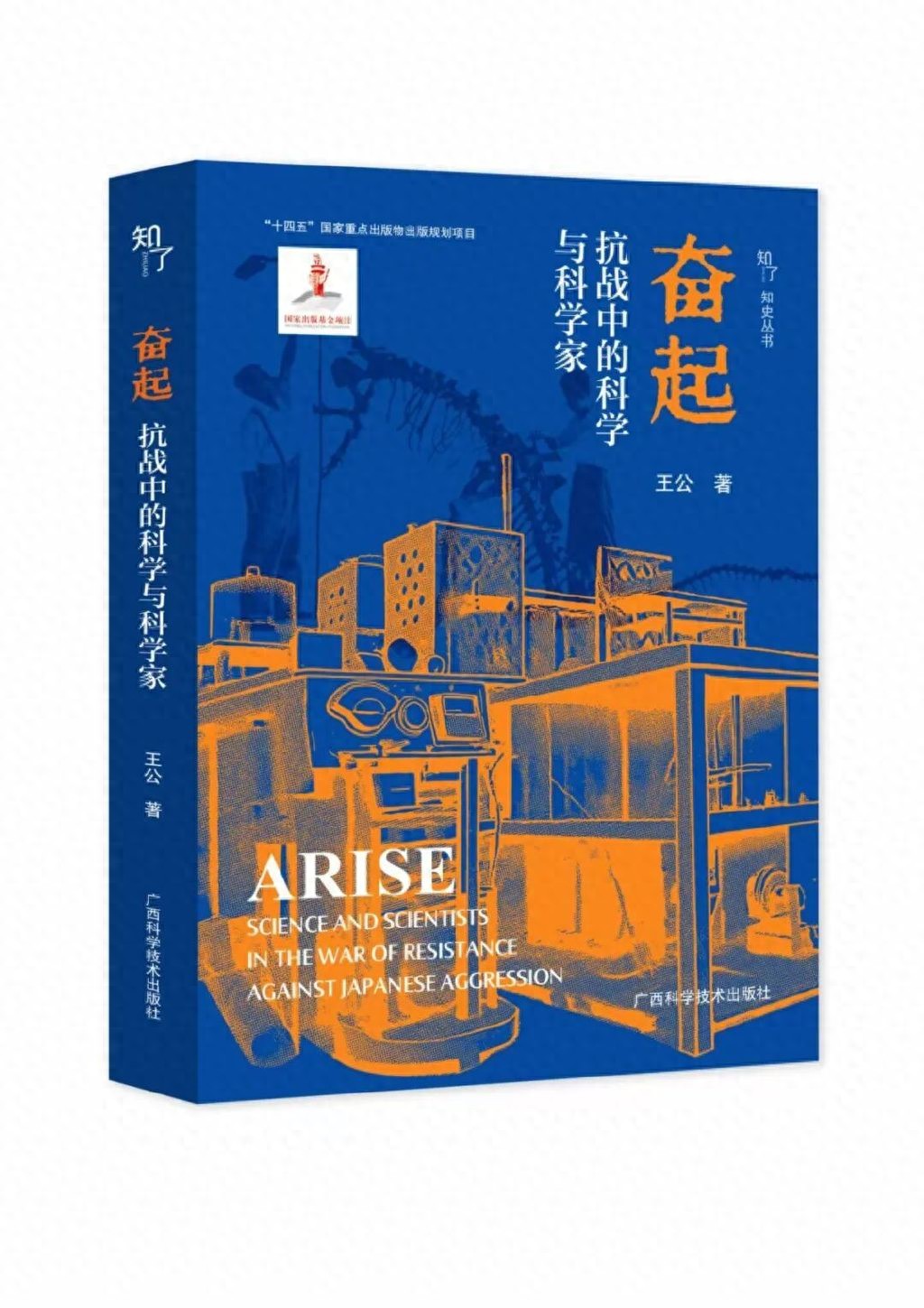 王公著,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8月)
王公著,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8月)
撰文 | 王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 世紀 30 年代,隨着中國的國立科研機構和主要高校相繼走上科學研究之路,中國的科技發展本應向前繼續邁進,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然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打破了無數中國科學家苦心經營的事業,面對日寇的鐵蹄、淪喪的國土、流離失所的同胞,中國的學者不得不振作起來,重新思考科學和民族的未來。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地區淪陷於日寇鐵蹄之下,廣袤的森林煤礦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落入日寇手中。此後,日本侵略者不斷蠶食華北地區,在那個“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書桌”的年代,全國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著名學者胡適、顧毓琇、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掀起了一場“科學與救國”的討論,彰顯出國難中知識分子自覺捍衞國家獨立的精神。
一
胡適:“求學而後可以救國”
1932 年 12 月初,胡適在長沙中山堂發表了題為《我們所應走的路》的重要演講。在演講中,胡適開宗明義地拋出“國難當前,我們究竟應該走哪條路”的問題,並明確回答“求學而後可以救國”。在胡適看來,中國外侮深重的原因,乃是科學不如人。他引用了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案例證明科學可以救國:1870 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令巴斯德十分氣憤,屈辱中他意識到挽救國運的唯一方式是科學研究。於是他集中全力探索細菌學,並取得了“物必先有微生物,然後腐化”的發現。這一發現被應用於法國的制酒、養蠶與畜牧業,不僅解決了長期困擾這三大行業的難題,還使 50 億法郎的賠款,由巴斯德一個人替國家償還,法國由此走向振興。基於此,胡適提出了他的主張:唯科學可以救國。胡適認為“救國不是搖旗吶喊能夠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於學術事業,苦心孤詣,實事求是地去努力才”“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在世界混亂的時候,有少數的人,不為時勢轉移,從根本上去做學問,不算什麼羞恥的事”“我們的責任是研究學術以貢獻國家和社會”“沒有科學,打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直觀來看,胡適所謂的救國“科學”代指具體的科學知識,更進一步來看,它還藴含科學文化的意味。以科學謀求國家的生存與獨立,這是五四運動以來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所極力倡導的,他們希望中國人能像巴斯德那樣,在遭受艱難境遇時向科學要答案。但是,作為思想家的胡適,對科學的宣揚與倡導仍停留於寬泛的綱領層面,因此科學界開啓了一場更為深入的“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論。
二
顧毓琇:“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
1933 年 1 月 1 日,在胡適發表演講一個月後,時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的顧毓琇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文章在讚賞胡適“唯科學可以救國”這一觀點的同時,進一步追問“我們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科學”。
在顧毓琇看來,科學事業包羅萬象,而面對眼前的危機必須認清需要怎樣的科學。他認為當今世界的科學,已經為中國提供了足夠的知識;中國在生死存亡之際,不必追求新的發明,而以國家目前的實力,也無力支持純粹的科學研究。“研究科學本來是人類智慧的探險,只有努力,沒有作用,超出空間,亦不顧時間。而‘救國’的問題便是既有目標,又要效果,並且要顧到空間、時間的迫切的要求。”由此,顧毓琇提出“要希望中國富強,要解決中國的生產問題,要中國的物質進步”,“我們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學的新發明,而是已有的科學發明的應用”。顧毓琇認為當前最能救國家於水火的是應用的科學,因此,他不希望每個人都去做發明家巴斯德,相反,他希望多數青年能夠學習應用科學家巴斯德,學他造酒、養蠶、為牛羊治病。
關於如何應用科學,顧毓琇也給出了他的見解。他説:“我們不必斤斤於中國人自己重新去發明一切已知的科學真理和事實。巴斯德的微菌,不是法國人專利的,就像牛頓的力學,不是為英國人發明的一樣。甚至於瓦特的蒸汽機,愛迪生的電燈泡,雖然多少是專利品,但是我們亦儘可以仿造。”舉步維艱之時,對顧毓琇來説,或許通過“模仿”的方式來應用科學是最為直接和高效的救國途徑。顧毓琇務實的眼光,不僅體現出他挽救國難的迫切願望,更顯示出艱難時局中他對發展科學的獨到見解。
三
中國知識界關於“科學救國”的討論
胡適的演講和顧毓琇的文章引起了科學界的反響。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化科主任吳憲認為,西方人是因為衣食住行都發展到了理想的狀態,所以才轉向研究科學。但這種科學與國計民生相去甚遠,因此,他提出當前中國不忙於做此種科學研究,但應用科學的研究則刻不容緩。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周先庚、講師張民覺也先後發表多篇文章,強調心理學,特別是心理技術在國防、工業、軍事等方面的應用價值。與科學家們的討論相呼應,帶有官方立場的國立中央研究院也發出了“科學研究事業應注重於應用方面”的聲音。一時間,主張發展應用科學的聲音可謂此起彼伏。
清華理學院教授薩本棟對如何發展應用科學,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清華大學實用科學研究會的演講中,薩本棟通過定義區分了純粹科學、應用科學與實用科學,他認為所謂實用科學即有用技術。儘管他肯定了實用科學在機械教育與產品製造方面的價值,但他對純粹科學的提倡則顯得更為突出。針對時人因國家危難而放棄純粹科學的做法,薩本棟堅決表示不認同,“因為現代的國防利器是許多純粹科學家、應用科學家及實用科學的人辛苦研究,經過長久的時間與屢次的改良才成功的。這些東西的基礎都是建在以前人們所認為未能應用的純粹科學之上”。帶着這樣的見解,薩本棟勸誡“現在立志於學應用或實用科學的人,應當特別注意自己在純粹科學方面的基礎是否穩固”。
薩本棟的觀點得到了清華理學院同人的回應。曾擔任過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的吳有訓,通過對學術獨立的追求,展現出他對純粹科學的肯定。他認為爭取獨立,對於某一學科而言,應當是“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專門學生,且能對該科領域之一部或數部,成就有意義的研究,結果為國際同行所公認……所以有意義的研究工作,是決定一個學科獨立的關鍵”。吳有訓所説的“有意義的研究”即指純粹科學、理論科學方面的研究。概而論之,為了實現國家獨立、學術獨立的目標,他認為必須加強對純粹科學的研究力度。在《清華大學理學院概況》一文中,吳有訓亦表達了相同的見解。
與清華理學院教授們的觀點遙相呼應,時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的竺可楨在《國風》期刊中發表了《航空救國和科學研究》一文,針對國人疾呼購買飛機以挽救時局的主張,竺可楨表達了自己的見地。他分析了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製造飛機失敗的原因,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人們對空氣浮力的有限瞭解,彼時的科學尚處於萌芽階段。而到了 20 世紀初,當科學發展到一定程度,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適逢其時,其製造飛機的成功可謂水到渠成。在歷史的對比中,竺可楨強調的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此外,竺可楨還在文章中談到歐美國家發展航空事業的空氣浮力定律與風管試驗。基於此,他總結到:“要講飛機救國,就得迎頭趕上,要迎頭趕上,就非去研究大氣力學和風管不可……要謀飛機的行動安全,非有敏捷精確的天氣報告不可,這又要靠地質學家、化學家、冶金學家和氣象學家的研究。”概言之,飛機救國的根基在科學,誠如其在文末所言:“飛機救國,必須從研究科學入手。”
日軍在鯨吞東三省後,開始進一步蠶食華北領土,國難日漸深重。面對危局,越來越多的聲音希望全國上下組織起來,一致抗日。科學界也逐漸走向組織化。
1935 年 6 月,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推動下,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選舉會召開,選舉產生蔡元培、丁燮林、李四光、竺可楨、汪敬熙等 11 位當然評議員,以及葉企孫、吳憲、侯德榜、林可勝、胡先驌、翁文灝等 30 位聘任評議員,丁文江兼任評議會秘書。丁文江在 1935 年《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中指出:“ 研究院的工作當然應當相當地偏重‘應用’。”作為中央研究院的領導核心,丁文江的科學觀無疑影響了研究院乃至全國科學界對科學發展路線的選擇。
1935 年 9 月,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第一次年會按計劃召開。1936年 4 月,第二次年會召開。這一年年初,丁文江因煤氣中毒不幸去世,翁文灝被推選為新的評議會秘書。
第二次年會共收到 13 件提案。其中,由翁文灝提議,陶孟和、丁燮林附議的提案《中國科學研究應對於國家及社會實際急需之問題特為注重案》(第一案),與由胡先驌提議,秉志、張其昀、謝家聲、王家楫附議的提案《請由中央研究院與國內各研究機關商洽積極從事與國防及生產有關之科學研究案》(第二案)經評議會審議通過後,合併為《我國科學研究應特別注重於國家及社會實際急需問題案》。在第一案中,以翁文灝為代表的科學家深入闡述了在當時特殊時期,注重發展國家及社會急需問題的理由。在國家艱難的特殊時期,他們認為應當採取特別策略予以應對。翁文灝回顧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他説當時參戰的歐洲各國,無不積極動員全國科學力量,致力於開發戰時急需的原料及替代品,同時還全力探索提高生產效率的途徑。以歐洲各國的組織化經驗為鑑,他認為身處同樣境遇的中國也理應如此。此外,翁文灝還提出了三項重要的辦法原則:一是由中央研究院通告所屬各研究機關,優先研究國家和社會需要最迫切的問題;二是對於急需的問題,應由評議會報送中央研究院,再由中央研究院分配至相關學術機關;三是各機關對於研究情況及所得結果,隨時向評議會報告。從翁文灝等人的表態中,可以看出他們深知科學研究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也深知自己身上的責任與使命,他們願意在特殊時期為國家所用,積極組織起來,共同應對國難。第二案由胡先驌等人提出,他們同樣強調在國事危急之秋,科學家應各展所長,為國家生死存亡而努力。該案也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事例佐證其主張:“歐西各國每當戰事一開,科學家皆全體動員,從事應付當前之需要。”與第一案相同,該案亦關注機關之間的協調問題:“宜由中央研究院與政府各部院參謀部兵工署資源委員會切實商討,條舉目前國防及生產有關最切要之問題,再與國內各研究機關接洽,使之分頭從事研究。”不難看出,胡先驌等人與翁文灝等科學家的立場相同,也倡導組織化的科學,進而更好地服務戰時國家所需。
評議會的提案得到顧毓琇的首肯。顧毓琇慷慨陳詞,認為當前的種種艱難環境,都迫切要求全國的學者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挑戰。他還詳細探討了如何完成這一光榮使命:明確需要,不以中央研究院已有的研究範圍為限制,中央研究院與政府對接國家需求等。顧毓琇殷切期望中央研究院和全國學術機關能夠齊心協力,共同投身科學救國的偉大事業之中。總而言之,正如他在同年發表的文章《民族自衞與軍備自給》中所言,在危急關頭,包括專門人才在內應實行“全國人力物力的總動員”。
無論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上翁文灝、胡先驌等人提出的議案,還是會後顧毓琇進行的討論,都表明國家危難已經深刻影響到中國科學的發展走向。身處國難危局,科學家羣體暫時放下了個人的自由探索與研究旨趣,協力共進以紓國家之困!
注:本文在與清華大學楊艦教授、張立和同學的多次討論中完成。
作者簡介
王公,副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家精神宣講團成員。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士、清華大學博士,美國匹茲堡大學、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科技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史,重點關注抗戰科技史、中國電子信息科學技術與工程史、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等。出版《奮起——抗戰中的科學與科學家》《抗戰時期營養保障體系的創建與中國營養學的建制化研究》《中國共產黨科技政策思想研究》等專著、合著八部,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課題。
 特 別 提 示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説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眾號內聯繫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