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美的當下“性”_風聞
娱乐硬糖-娱乐硬糖官方账号-09-04 16:37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有網友曬Papi醬推薦的生活好物時,盛讚“不愧是初代網紅”。另一羣網友指責她用詞不當:如果2015年走紅的Papi醬是初代,那麼千禧年的網紅應該叫什麼,怕不是老祖了吧?
**時代列車轟然碾過,碾碎的不僅是網紅,還有與之相伴而生的社會共識。**隨便歲月史書的糟糕結果顯而易見,《小時代》成了真高定代言,《新還珠》是00後名著,李少紅版《紅樓》最合原典,張紀中金庸劇實景拍攝美學大成……

問題的關鍵在於,不能光是“想當年”,也要管管“當年”的實情究竟如何。君不見《小時代》當初被罵拜物教,《新還珠》被羣嘲,觀眾嚷嚷着給李少紅“判刑”,大鬍子只顧實景拉遠鏡頭經常連主角五官都看不清。
作品是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人卻總是未完待續。最近,“老祖網紅”木子美因為曝光和《新週刊》創始人孫冕的性愛往事重回輿論焦點。年紀小的網友可能既不知道木子美,也不知道孫冕。勉強知道個柴靜,卻仍無法理解“疊羅漢”一詞的精妙。
比起一個網紅可以紅幾年,或許更有趣的問題是一個網紅可以紅幾次。一個人趕上一次浪潮、成為某種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已是不易,要每隔十來年就火一把,那真是穿越週期。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木子美的主食材固然是永恆的“性”,調味的卻是不同的“當下性”——從以身入局的先鋒寫作,到“燕郊絕戀”的市井歡愉,再到名人性史的揭露諷喻。這是不同的類型創作,也是時代的精神迴響。
老登的露怯
木子美現在的微博名叫“做個烏鴉也好”,9月1日她發微博説:“03年我寫日記火時,全網討論了3個月,各種陳詞濫調和現在的差不多。社會確實沒有進步。”
硬糖君覺得她説得不對,現在比2003年保守多了。當年的青少年圍觀木子美的性愛博客,現在的孩子看小説都要雙潔審判。最好笑的是以前“開眼看世界”的中年人,為了迎合年輕人的保守風也帶頭揮起大棒。就該有更多的木子美,把中登們的性愛賬本翻出來,讓他們在年輕人面前社會性死亡。
8月26日,木子美在微博回憶了她和孫冕激情燃燒的歲月。最光怪陸離的一段,木子美自認有紅樓風格,硬糖君感覺更接近《源氏物語》那種亂搞。“一次在老薛家裏,老薛一邊彈古箏,他(孫冕)和我一邊在沙發上做,那意境真是紅樓三人組,老薛彈完一曲過來疊羅漢,我們就成了三明治。那時沒心沒肺的我,多讓老藝術家們喜歡啊!”
疊羅漢梗火了以後,木子美又發佈了“疊羅漢名場面”,是柴靜《看見》的發佈會照片。柴靜坐正中,後面是十一位文化界為她站台的名人。遠在大洋彼岸的柴靜,恐怕也搞不明白自己怎麼就被捲入木子美宇宙了。羣眾七嘴八舌之際,木子美澄清:疊羅漢有葷疊和素疊,並在評論區回覆網友“一個合影疊而已,想太多”。

好嘛,被木子美老師將了一軍。把疊羅漢想成那檔子事,原是我心思髒。
通過一系列的回憶和輿論發酵,木子美表面是祝賀往昔炮友們事業欣欣向榮,實則通過爆料讓當事人瑟瑟發抖。嚇人可不帶這麼嚇的,木子美應該出一本新書叫《嚇木友人帳》。當事人不澄清或者追究木子美造謠,要麼清者自清要麼確有其事,而羣眾大概率相信後者。

硬糖君有一句記憶很深的話:木子美會時不時從一麻袋的300條JJ裏,拿出幾條來戲弄它們。這才是文藝圈最嚇人的“恐怖片”。那些光環之下有一圈陰影,陰影裏站在木子美。她手裏拿着賬本,隨便翻一頁都是一場性事、一種揭露。
**木子美由此完成了一個“文化弒父者”的角色。**她沒有直接言説,而是通過這些爆炸性的“瓜”,讓公眾自發去討論文藝圈的亂象。用最私密的身體敍事,撕開了文藝老登們用才華、地位和名譽編織的光環,繼而迎合了年輕一代對偽善的、掌握話語權的既得利益者的普遍反感情緒。
市井歡愉時代
2015年的路邊,卡姆觀察挺着大肚子的司機時,木子美也正和其中一個司機展開着《燕郊絕戀》。不同的是,卡姆眼裏的司機是“沙河沙河,走了走了!”木子美眼裏的司機則是“即便知道你的過去,我還是願意和你在一起。”

在那個市井歡愉的時代,雖沒了千禧年的理想幻夢,卻仍稱得上活力四射。人們大膽追求俗世的幸福,連木子美都想和司機“過日子”了。
表面上看,木子美願意在一段穩定的親密關係裏停駐,是司機在“救風塵”。但從木子美的視角,她反而才是司機的“拯救者”。她非常動情地寫道:“遇到他時,他是個受着命運折磨,負債十幾萬,一天拉十幾個小時活,還出了小事故的司機。活得疲憊又麻木。他不經意閃爍的才華,讓我產生小崇拜,以及把他從泥潭裏打撈出來的衝動。”
哦莫,這不就是羣眾最近鼓吹的“野草般的共生”?當然,若採用小紅書和抖音網友的鋭評,又是永遠不要去扶貧男人,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是。

回看這段“你是風兒我是沙”的愛情,司機所表現出來的勇敢,無非是他在家庭和情愛之間既要又要的貪心。司機回家攤牌,母親和媳婦一起教訓他,結果跑出來到木子美那兒,她居然把這種行為稱作“逃學”。家庭的沉重和無法擺脱,就像青少年不喜歡還強上的學。情愛的自由和寬縱,是他唯一可以棲息的精神港灣。
“眼圈紅紅的,我抱着他。那時,他每天受的苦,都是對我的愛。”難以想象萬花叢中過的木子美,也有這麼上頭的時候。這樣悽美決絕的愛情,最後在對簿公堂時,對方卻説“不得已原告與被告發展成為情人關係。”笑死,難道木子美拿刀逼司機跟自己上牀?可即便司機如此絕情,木子美也沒有説對方壞話,只當相忘於江湖。
必須相信,木子美肯定期待司機每天流過汗的充滿男性魅力的身體,但她更期待的恐怕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家庭。木子美3歲的時候,母親就將父親捉姦在牀了。她從那會兒學會了“疊羅漢”,也在心裏積攢了對完整的、有愛的、堅固的家的深度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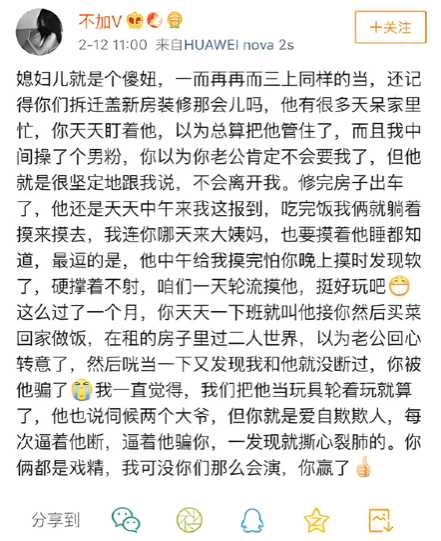
我們不用弗洛伊德那一套,説一切對性的渴望都源於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缺失,也不用峯哥的理論説木子美的“性解放”源於“性壓抑”。木子美和司機的故事,巧妙地戲仿並顛覆了傳統的“從良敍事”:
傳統語境中,放蕩女性通過依附一個男人並回歸家庭獲得救贖。木子美看似從良,但對象卻是一個經濟和社會地位低於她的已婚男性,這本身就包含了強烈的反叛與諷刺。她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構建一種新型關係,但遺憾失敗了。
先鋒賦魅
世紀初的“身體寫作”是石破天驚的。木子美説搖滾歌手王磊“很快就爽完了”,蓋章認證對方身體不好。衞慧在《上海寶貝》裏寫馬克進入倪可時,感覺像坐在熱乎乎而危險的消防栓上。棉棉的金句則頗有哲理,“男人一硬就傻,硬男人心軟,軟男人心硬”。
很難想象,為什麼千禧年初的女作家都偏愛情色寫作。甚者像木子美,為了找靈感直接用身體積累素材。對於同行,她還非常鄙視其缺乏直接經驗,認為衞慧等人寫書不過是隻看過幾部AV的小學生作品。
追根溯源,這種身體寫作屬於新東方主義,是後殖民主義的一個分流。典型特點是東方的男性孱弱無力,具體表現就是陽痿。西方男性充滿雄性魅力,特長就是征服女主人公。但我們今天不談文藝批評,只分析這種寫作潮流與時代形成的微妙呼應。
**木子美當年在《城市畫報》開了性專欄,以每兩週換一個情人的體驗式寫作聞名。**她在網絡上的紀實寫作《遺情書》,一度成為當時點擊最高的私人網頁。最初的爆點,源於人們發現木子美提到的搖滾歌手王磊,就是那個“北崔健南王磊”的王磊。

有記者問木子美的炮友有多少個?她曾回答65個。這個帶有挑釁意味的問題,根本挑釁不了木子美。單從《遺情書》的內容來看,木子美確實最為徹底地充當了埃萊娜·西蘇的理論實踐者。這種純粹肉體經驗的得意炫示,引發了一場無關痛癢卻又正中下懷的網絡風暴。道德君子勸人從良,苦心勸諭。貞潔烈女面紅耳赤,痛加批判。
最忙的時候,木子美甚至告訴要求採訪的記者和她上牀,牀上有多少時間就能採訪多長時間。我們不知道是否有記者進行了“身體採訪”,可以明確的是,木子美是最佳的“時代記者”。
她忠實地記錄下每個牀伴的身體反應,也用一場場輿論留存了時代激盪的側影。“我的態度是:荒淫無度的性行為儘量控制在物質技術能夠發揮作用的層面,這是保證身體完好無缺,讓你有機會後悔或繼續享樂的前提;然後是心理上單純地將性行為看成它本身,這是防止心靈支離破碎的途徑。”
**世紀初是一個賦魅的時代,從世界的未來到個人的身體都讓人充滿探索欲。**甭管木子美是為了熱水澡跟人做愛,還是幫文藝青年開苞,她的筆觸始終帶着一股冷酷的、人類學式的觀察感。當17歲的知名導演對木子美説:“等我出名了再寫我”,更是洋溢着一種鮑勃·迪倫式的文藝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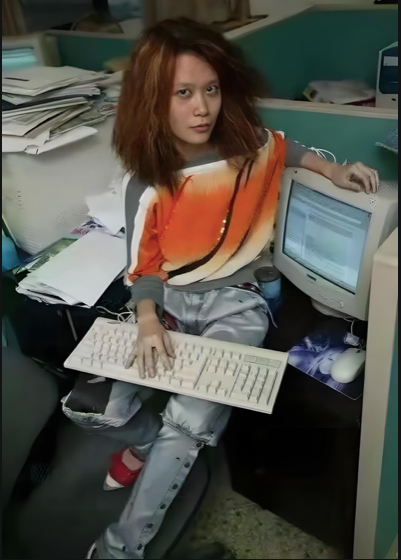
今天,純粹的“身體寫作”已不再先鋒,身體和性也不再是禁忌。在X(原推特)上我們能看見各種真真假假的身體寫作,比木子美更高難度的姿勢和駭人聽聞的情節都有,卻再也找不回那種先鋒體驗之感。
身體從來不是純粹的私域。它始終被權力所雕刻,也始終藴含着反抗權力的潛能。從這一點看,木子美走過的三個時代也是三面鏡子。世紀初的賦魅,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歡愉,當下的保守緊縮。其中,不僅僅能夠看到木子美本人,更是我們自己對權力、性別、道德和情感的複雜態度。
准此,歲月靜好的木子美,當下可能已經沒多少性了,但依然有其當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