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裏·薩克斯:歐洲被美國忽悠着反俄反中,造就自身安全困境_風聞
北京对话-北京对话官方账号-北京枢纽型国际对话智库平台,致力于中外交流09-05 07:33
Club提要:八月以來,特普會、特朗普會晤歐烏領導人等一系列外交斡旋接連上演,俄烏衝突的和談進程似乎按下了“加速鍵”。在這場新的大國角力和斡旋中,歐洲卻有可能被邊緣化,既無法主導議程,也缺乏獨立的安全與外交戰略。
在這一背景下,著名全球發展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近日撰文,直言西方對俄羅斯威脅的誇大與炒作,使歐洲陷入對美國的從屬地位和自身戰略的混亂之中。他指出,歐洲在對華態度上的盲目軍事化不僅損害自身利益,還會產生嚴重的外溢效應,進一步削弱其經濟與外交空間。
薩克斯同時提出,歐洲若要擺脱困境,就必須重建外交主動權,重審與俄中關係,在真正的安全利益與可持續發展上尋找突破。他的呼籲既是對歐洲現實的警醒,也折射出對歐洲仍有轉圜機會的期待。
Club Briefing: Since August, a series of diplomatic maneuvers—from the Putin-Trump meeting to Trump’s talks with European and Ukrainian leaders—have unfolded one after another, seemingly pressing the “accelerator” on peace negotiations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Yet in this new round of great-power bargaining, Europe risks being sidelined, unable to set the agenda and lacking an independent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gainst this backdrop, Jeffrey Sachs, renowned global development expert and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recently argued that the West’s exaggeration and hype of the “Russian threat” has trapped Europe in subservi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leaving its own strategy in disarray. He stressed that Europe’s blind militarization of its China policy not only undermines its own interests but also generates damaging spillover effects, further shrinking it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space.
Sachs contends that for Europe to break free of this predicament, it must reclaim diplomatic initiative, reassess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China, and seek breakthroughs grounded in genuine security interes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is call serves both as a sobering warning of Europe’s current reality and a reminder that opportunities for course correction still exist.

歐洲領導人帶着澤連斯基前往白宮(圖源:BBC)
當下,歐洲陷入了一個由自身造成的經濟與安全困境:對俄羅斯的危險敵意、與中國的互不信任,以及對美國的極端依賴。歐洲的對外政策幾乎完全由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恐懼所驅動——結果是對美國的安全依賴。
歐洲對美國的從屬幾乎完全源自對俄羅斯的深度恐懼,這種恐懼被東歐的“恐俄”國家以及關於烏克蘭戰爭的錯誤敍事不斷放大。在“俄羅斯是最大安全威脅”的信念驅動下,歐盟將經濟、貿易、環境、科技、外交等所有其他外交事務都從屬於美國。諷刺的是,歐洲緊緊依附於華盛頓,即便美國自身已在對歐外交中表現得更為虛弱、不穩定、反覆無常,甚至危險,乃至公開威脅到歐洲在格陵蘭的主權。
要開闢新的外交道路,歐洲必須克服其所謂“面臨俄羅斯威脅”的虛假前提。布魯塞爾—北約—英國的敍事認為,俄羅斯本質上是擴張主義的,只要有機會就會席捲歐洲。1945–1991年的蘇聯佔領東歐,被當作今天這一威脅的“鐵證”。但這種敍事嚴重誤讀了俄羅斯過去與現在的行為。
本文第一部分旨在糾正“俄羅斯對歐洲構成嚴重威脅”這一錯誤前提。第二部分將展望:一旦歐洲超越這種非理性的恐俄情緒,其對外政策將如何重塑。
虛假的“俄羅斯西向帝國主義”前提
歐洲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俄羅斯對歐洲安全構成威脅”的假設之上。然而,這一假設是錯誤的。事實上,俄羅斯在過去兩個世紀裏多次遭到西方大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的入侵,因此長期尋求通過在自身與西方之間建立“緩衝區”來保證安全。這一爭奪激烈的緩衝區包括當今的波蘭、烏克蘭、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這片區域正是西歐與俄羅斯之間最主要的安全困境所在。
自1800年以來,西方對俄主要戰爭包括:
1812年法國入侵俄國(拿破崙戰爭)
1853–1856年英法入侵俄國(克里米亞戰爭)
1914年8月1日德國向俄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8–1922年協約國干涉俄國內戰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期間蘇聯的宣傳報
這些戰爭無一例外都對俄羅斯的生存構成了生死攸關的威脅。對俄羅斯而言,二戰後未能徹底解除德國武裝、北約的建立、1955年西德加入北約、1991年後的北約東擴,以及美國在東歐不斷擴張的軍事基地和導彈系統,構成了二戰以來對其國家安全的最嚴重威脅。
與此同時,俄羅斯也確實有過幾次西向入侵:
1914年入侵東普魯士
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分割波蘭及1940年吞併波羅的海三國
1939年11月入侵芬蘭(冬季戰爭)
1945–1989年佔領東歐並繼續吞併波羅的海三國
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
歐洲普遍將這些事件視為俄羅斯擴張主義的鐵證。然而,這種看法是天真、失真的,並被宣傳所操控。在這五個案例中,俄羅斯的行動都源於其自身認定的國家安全需要,而非單純為擴張而擴張。這一基本事實正是解決當下歐洲—俄羅斯衝突的關鍵。俄羅斯尋求的不是向西擴張,而是核心安全保障。但西方長期未能認識到,更遑論尊重俄羅斯的核心安全利益。
接下來,我們逐一審視這五個被視為“擴張主義”的案例。
第一例:1914年入侵東普魯士——可以立即排除在外。德意志帝國於1914年8月1日先向俄國宣戰,俄國入侵東普魯士完全是對德國宣戰的直接回應。
第二例: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分割波蘭併吞並波羅的海三國,在西方被視為俄羅斯背信棄義的鐵證。但這種解讀過於簡單且錯誤。正如歷史學家E. H. Carr、Stephen Kotkin、Michael Jabara Carley所揭示,斯大林當時積極尋求與英法結盟,共同抵禦希特勒東擴威脅(生存空間、奴役斯拉夫人、擊敗布爾什維克)。但英法拒絕與蘇聯建立防禦同盟。波蘭更是拒絕在德蘇開戰時允許蘇軍進入波蘭領土。西方精英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仇恨,至少與他們對希特勒的恐懼一樣深。英國內部右翼精英在1930年代末甚至流行一句話:“寧要希特勒,不要共產主義”。
在無法達成防禦同盟的情況下,斯大林轉而通過劃分波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來延緩即將到來的納粹入侵,以為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之戰”爭取時間。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波蘭的分割和波羅的海的吞併可能確實延遲了德軍的進攻,從而幫助蘇聯避免迅速敗亡。
第三例:1939年冬季戰爭,在西方(尤其是芬蘭)被視為俄羅斯擴張的明證。然而,其根本動機同樣是防禦。蘇聯擔心納粹進攻可能部分從芬蘭方向發動,快速攻佔列寧格勒。於是提出與芬蘭交換領土:蘇聯希望獲得卡累利阿地峽及芬蘭灣部分島嶼,以換取其他俄方領土,從而更好防禦列寧格勒。芬蘭拒絕提議,蘇聯遂於1939年11月發動進攻。隨後在1941–1944年“繼續戰爭”中,芬蘭果真加入了希特勒的戰線對抗蘇聯。
第四例:冷戰時期蘇聯佔領東歐併吞並波羅的海三國,在歐洲被視為俄羅斯根本威脅的又一鐵證。毫無疑問,蘇聯佔領手段殘酷,但其動機依舊是防禦性的,這一點在西方敍事中完全被忽視。蘇聯為擊敗希特勒付出巨大代價,損失多達2700萬公民。戰後蘇聯唯一的核心要求,就是通過條約保障其安全,防止德國和西方再次構成威脅。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拒絕滿足這一基本安全訴求。冷戰的根源正是在於西方拒絕尊重俄羅斯的核心安全關切。當然,西方敍事卻反過來聲稱:冷戰完全是蘇聯企圖征服世界的結果。
這才是真實的歷史,歷史學家們熟知,但在美國和歐洲公眾中幾乎完全不為人知。二戰結束時,蘇聯尋求通過一份和平條約來確立一個統一、中立、非軍事化的德國。在1945年7月舉行的波茨坦會議上,蘇聯、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一致同意“徹底解除德國武裝並非軍事化,消除或管控所有可能用於軍事生產的德國工業。”當時設想的是,一個統一、和平、非軍事化的德國。這一切原本應通過一份正式的戰爭結束條約加以落實。但事實上,美國和英國卻竭力破壞這一核心原則。

英美蘇領導人在1945年7月舉行的波茨坦會議
早在1945年5月,温斯頓·丘吉爾就指示其總參謀長制定一份代號為“不可能行動”(Operation Unthinkable)的作戰計劃,準備在當年中期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儘管英國軍方認為這場戰爭在當時不可行,但“美英應當為與蘇聯的戰爭做準備”的觀念很快流行開來。軍事規劃者認為,最可能爆發戰爭的時間是20世紀50年代初。丘吉爾的目的似乎在於阻止波蘭及東歐其他國家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在美國,同樣是在1945年5月德國投降後的數週內,美國最高軍事策劃者便已把蘇聯視為下一個主要敵人。美英迅速網羅納粹科學家和高級情報人員(如納粹頭目萊因哈德·蓋倫,他後來在美國支持下建立了德國戰後的情報機構),開始籌劃與蘇聯的未來戰爭。
冷戰的爆發,主要源於美英拒絕履行波茨坦關於德國統一與非軍事化的共識。相反,西方拋棄了德國統一的設想,把美英法三佔區合併,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並在美國主導下對其進行再工業化與再軍事化。到1955年,西德已被接納進入北約。
歷史學者們激烈爭論波茨坦協定究竟是誰違約在先(例如,西方指責蘇聯未允許波蘭建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府),但毫無疑問,西方對西德的再軍事化是冷戰的關鍵誘因。
1952年,斯大林提議以中立與非軍事化為基礎實現德國統一,但遭到美國拒絕。1955年,蘇聯與奧地利達成協議,蘇聯撤出駐軍,以換取奧地利永久中立的承諾。5月15日,《奧地利國家條約》由蘇、美、英、法與奧地利共同簽署,結束了奧地利的佔領局面。蘇聯的目標不僅在於解決奧地利問題,更希望藉此向美國展示蘇聯在歐洲撤軍與中立並存的成功模式。然而,美國再次拒絕以德國的中立與非軍事化為基礎結束冷戰。甚至到了1957年,美國蘇聯事務權威喬治·凱南仍在BBC的“里斯講座”中公開熱切呼籲,美蘇應達成相互撤軍協議。他強調,蘇聯既無意圖也無能力入侵西歐。但美國冷戰派,由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領導,完全拒絕。德國的正式和平條約直到1990年統一時才最終簽署。
值得強調的是,1955年之後,蘇聯確實尊重了奧地利以及其他歐洲中立國(包括瑞典、芬蘭、瑞士、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中立地位。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最近聲稱,烏克蘭應當拒絕中立,因為芬蘭的中立“經歷不佳”(2024年芬蘭加入北約後結束中立)。這是十分荒謬的想法。芬蘭在中立時期保持了和平,實現了顯著的經濟繁榮,並在《世界幸福報告》中長期位居世界前列。
約翰·F·肯尼迪總統展現了以相互尊重各方安全利益為基礎結束冷戰的潛在路徑。他阻止了德國總理阿登納從法國獲取核武器,從而緩解了蘇聯對核武裝德國的擔憂。在此基礎上,肯尼迪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成功談判並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數月後,肯尼迪極可能因其和平倡議而遭CIA相關人員暗殺。2025年解密的文件證實,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當時正直接由CIA高官詹姆斯·安格爾頓操控。美國下一次對蘇聯的和平嘗試是由尼克松發起,但他也因“水門事件”被迫下台,而該事件同樣存在未解的CIA疑點。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最終通過單方面解散華沙條約組織並推動東歐民主化,結束了冷戰。我曾親歷其中一些事件,也見證了戈爾巴喬夫的和平努力。例如,1989年夏天,戈爾巴喬夫明確要求波蘭共產黨領導層與由“團結工會”領導的反對派組成聯合政府。華約的解體與東歐的民主化,在戈爾巴喬夫的推動下迅速展開,並促使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呼籲德國統一。這最終促成了1990年的兩德統一條約,以及德、美、英、法、蘇五國共同簽署的“2+4條約”。在1990年2月的談判中,美國與德國明確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在兩德統一的背景下“不向東擴張一寸”,這一點如今在西方屢遭否認,但卻有大量可驗證的證據。這一關鍵承諾多次作出,卻未寫入2+4條約文本中,因為該條約僅涉及德國統一,而非北約的東擴。
第五個案例是2022年2月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西方普遍將此視為俄羅斯“不可救藥的西向擴張主義”的證明。西方媒體、學者與宣傳機器最愛用的詞是“無端的”,以此證明普京不但想恢復俄羅斯帝國,還圖謀進一步擴張,因此歐洲必須為與俄羅斯的戰爭做準備。這完全是一個荒謬而巨大的謊言,但由於主流媒體不斷重複,已經在歐洲廣泛被接受。
事實是,2022年2月的俄國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挑釁的結果,甚至讓人懷疑這是否是美國有意設計,用來把俄羅斯引入戰爭、以便削弱或擊敗它。這一説法並非空穴來風,美國官員長期以來的一系列表態都證明了這一點。入侵發生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明確宣稱,華盛頓的目標是“讓俄羅斯虛弱到無法再做類似入侵烏克蘭這樣的事情。只要烏克蘭得到合適的裝備與支持,它就能獲勝。”

2023年,奧斯汀與澤連斯基在基輔會面(圖源:烏克蘭總統辦公室)
美國挑釁俄羅斯的首要方式,是在違背1990年承諾,推進北約東擴,其關鍵目的在於圍繞黑海佈設北約國家,從而剝奪俄羅斯通過克里米亞海軍基地投射力量至東地中海與中東的能力。本質上,這與帕麥斯頓和拿破崙三世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目標相同:將俄國艦隊逐出黑海。計劃中的北約環繞圈包括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和格魯吉亞,形成扼殺俄羅斯黑海海軍力量的絞索。布熱津斯基在其1997年的《大棋局》一書中明確描述過這一戰略,堅稱俄羅斯必然會屈服於西方的意志,並斷言俄國絕不會與中國結盟對抗歐洲。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整個時期都充滿了西方的傲慢(正如歷史學家喬納森·哈斯拉姆的經典論述所説),美國和歐洲自信可以毫無顧忌地推動北約和美軍武器系統(如宙斯盾導彈)不斷向東,而完全無視俄羅斯的國家安全關切。西方挑釁的清單太長,以下僅作概要:
第一,違背1990年的承諾,美國自克林頓1994年宣佈起正式推動北約東擴。當時,美國防部長佩裏曾考慮因這一魯莽舉動辭職。1999年第一輪擴張納入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同年北約對俄羅斯盟友塞爾維亞轟炸78天,將其肢解,並在科索沃設立大型軍事基地。2004年第二輪擴張納入七國,包括波羅的海三國及黑海沿岸的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2008年,歐盟多數成員承認科索沃獨立,背棄此前“歐洲邊界不可更改”的承諾。
第二,美國單方面廢棄核武控制框架: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2019年退出《中導條約》。儘管俄羅斯強烈反對,美國仍在波蘭和羅馬尼亞部署反導系統,並在2022年1月保留在烏克蘭部署的權利。
第三,美國深度介入烏克蘭國內政治,投入數十億美元操縱輿論、扶持媒體、影響政局。2004–2005年烏克蘭大選被廣泛視為美國主導的“顏色革命”。2013–2014年,美國直接出資支持邁丹抗議,並推動暴力政變,推翻中立立場的總統亞努科維奇,為親北約政權鋪路。我本人在2014年2月政變後不久曾受邀前往基輔,當地一家深度參與邁丹的美國非政府組織向我解釋了美國資金在抗議中的作用。

2013–2014年,烏克蘭邁丹抗議(圖源:美聯社)
第四,自2008年起,美國不顧多位歐洲領導人反對,堅持推動北約承諾未來吸收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當時的美國駐俄大使伯恩斯發回著名電報《“不”就是“不”:俄羅斯的北約擴張紅線》,明確警告俄國整個政治階層堅決反對北約東擴至烏克蘭,並擔心此舉會引發烏克蘭內戰。
第五,政變後,烏克蘭東部俄裔地區(頓巴斯)脱離新政權。俄德推動簽署《明斯克協議》,承諾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仍屬烏克蘭但享有類似意大利南蒂羅爾的高度自治。《明斯克二號協議》經聯合國安理會背書,本可終結衝突,但基輔政權在華盛頓支持下拒絕執行自治,導致俄西外交徹底惡化。
第六,到2020年,美國幫助烏克蘭擴軍至約百萬(現役加預備役),並支持其右翼武裝(如亞速營、右翼部門)多次攻擊頓巴斯,導致當地平民數千人死於烏方炮擊。
第七,2021年底,俄羅斯提出《俄美安全協議》草案,核心是要求停止北約擴張。美國拒絕,重申“開放政策”,堅持第三國無權干涉。美國和歐洲多次公開重申烏克蘭未來必入北約,並在2022年1月據稱告訴俄方,美國保留在烏克蘭部署中程導彈的權利。
第八,在2022年2月24日俄軍入侵後,烏克蘭很快同意在中立基礎上展開和談,談判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3月底,俄烏聯合發表聲明稱談判有實質進展。4月15日,一份接近全面和解的協議草案已經成形。但此時,美國介入並告知烏克蘭不會支持和平協議,而是支持烏克蘭繼續作戰。
失敗外交政策的高昂代價
俄羅斯從未對西歐國家提出任何領土要求,也未威脅過西歐,除了保留在遭受西方協助的導彈襲擊時進行報復的權利。在2014年“廣場政變”之前,俄羅斯對烏克蘭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政變之後直到2022年底,俄羅斯唯一的領土要求是克里米亞,目的是防止其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基地落入西方之手。直到伊斯坦布爾和平進程在美國的干預下失敗之後,俄羅斯才宣佈吞併烏克蘭的四個州(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和扎波羅熱)。如今俄羅斯的戰爭目標仍然有限,包括烏克蘭的中立、部分裁軍、永久不加入北約,以及克里米亞和四州劃歸俄羅斯,總計約佔烏克蘭1991年領土的19%。
這並不能證明俄羅斯存在向西擴張的帝國主義,也不是毫無緣由的要求。俄羅斯的戰爭目標是30多年來其不斷反對北約東擴、烏克蘭軍備化、美國放棄核軍控框架,以及西方深度干預烏克蘭內政(包括2014年美國支持的暴力政變)的結果。
歐洲選擇將過去30年的事件解讀為俄羅斯不可遏制的向西擴張主義——就像冷戰時期西方堅持認為蘇聯單方面應對冷戰負責一樣,儘管蘇聯多次提出通過德國的中立、統一與裁軍來實現和平。正如冷戰期間一樣,西方選擇挑釁俄羅斯,而不是承認其完全合理的安全關切。俄羅斯的每一個行動都被最大化地解讀為背信棄義,從不承認俄羅斯的立場。這是安全困境的典型寫照:對手之間完全各説各話,在錯誤假設下揣測最壞意圖並採取進攻性行動。
歐洲選擇以這種高度偏頗的視角來解讀冷戰和後冷戰,其代價巨大,而且代價仍在不斷增加。最重要的是,歐洲逐漸形成了在安全上完全依賴美國的認知。如果俄羅斯真的是不可救藥的擴張主義者,那麼美國確實是歐洲不可或缺的救世主;但如果俄羅斯的行為其實源於安全關切,那麼冷戰很可能早在數十年前就能在“奧地利中立模式”下結束,後冷戰時期也可能成為俄歐之間和平與互信不斷增長的時代。
事實上,歐洲與俄羅斯的經濟結構是互補的:俄羅斯在初級產品(農業、礦產、能源)和工程領域實力雄厚,而歐洲則擁有能源密集型產業和關鍵高新技術。美國長期以來反對歐俄之間因這種互補性而不斷增長的貿易聯繫,將俄羅斯能源產業視為美國能源行業的競爭對手,更廣泛地則將德俄之間的密切經貿投資關係視為對美國在西歐政治與經濟主導地位的威脅。正因如此,美國早在烏克蘭衝突爆發前就反對“北溪一號”和“北溪二號”管道。拜登甚至明確承諾,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終結“北溪二號”——然後這就變成事實了。美國反對北溪以及德俄經濟聯結,並非因烏克蘭問題,而是出於根本原則:歐盟與俄羅斯必須保持距離,否則美國將在歐洲失去影響力。

北溪管道2022年被炸(圖源:丹麥軍方)
烏克蘭戰爭與俄歐決裂對歐洲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歐洲對俄出口從2021年的約900億歐元驟降至2024年的300億歐元。能源成本飆升,歐洲不得不從廉價的俄羅斯管道天然氣轉向價格數倍於前的美國液化天然氣。德國工業自2020年以來萎縮約10%,化工和汽車行業都在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歐盟2025年的經濟增長率僅為1%,此後幾年也只能維持在1.5%左右。
德國總理梅爾茨呼籲永久禁止恢復“北溪”天然氣供應,但這幾乎是德國的經濟自殺契約。他的立場建立在“俄羅斯意圖與德國開戰”的認知上,但事實上,正是德國通過戰爭言論和大規模擴軍在挑釁俄羅斯。梅爾茨聲稱,“我們需要對俄羅斯的帝國主義野心有一個現實的認識。”他還説:“我們社會的一部分人有根深蒂固的戰爭恐懼。我不認同,但我理解。”更令人警惕的是,梅爾茨宣稱“外交手段已經耗盡”,然而自他上台以來,似乎根本沒有嘗試與普京總統對話。此外,他也選擇性忽視了2022年伊斯坦布爾進程中外交幾乎成功的事實——在美國叫停之前。
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與對俄羅斯如出一轍。西方經常指責中國有“險惡企圖”,實際上只是反映了自己的敵意。在1980至2010年間,中國迅速崛起為經濟強國,這讓美國領導人和戰略家認為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不符合美國利益。2015年,美國戰略家布萊克威爾與特利斯明確指出,美國的大戰略是維護霸權,而中國由於體量和成功對霸權構成威脅。他們主張美國及其盟友採取措施削弱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例如將中國排除在亞太新貿易集團之外、限制高科技出口、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税與其他限制、以及一系列反華措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措施並非因中國有具體“做錯”什麼,而僅僅是因為中國的持續增長被認為不利於美國的主導地位。
在對華與對俄政策中,媒體戰同樣是重要組成部分。以中國為例,西方聲稱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這一荒謬誇大的指控缺乏任何嚴肅證據,而西方卻普遍對以色列在加沙對數萬巴勒斯坦人的實際種族滅絕行為視而不見。此外,西方還散佈大量關於中國經濟的荒謬説法。例如,中國價值極高的“一帶一路”倡議(為發展中國家融資建設現代基礎設施)被污衊為“債務陷阱”;中國在綠色科技領域的巨大產能(如全球急需的太陽能組件)則被西方貶低為“產能過剩”,呼籲削減甚至關停。
在軍事方面,對華的安全困境與對俄如出一轍,被以最危險的方式解讀。美國長期宣稱自己有能力切斷中國的關鍵海上航道,但當中國為應對而增強海軍力量時,卻被指責為“軍事化”;美國海軍甚至宣稱要為2027年前與中國的戰爭做好準備,而不是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安全困境。北約則越來越多地呼籲在東亞積極介入,對抗中國。美國的歐洲盟友通常也跟隨美國在對華貿易和軍事上的強硬路線。
歐洲新外交政策
歐洲把自己逼進了死角:對美國亦步亦趨,拒絕與俄羅斯直接外交;因制裁和戰爭失去經濟優勢;承諾大規模且不可承受的軍費開支;同時切斷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長期經貿聯繫。其結果是債務攀升、經濟停滯,以及大戰風險的不斷加劇——這些或許對梅爾茨來説並不可怕,但對我們其他人而言應當感到極度擔憂。最可能的戰爭甚至未必是與俄羅斯,而可能是與美國——特朗普曾威脅,如果丹麥不“出售”格陵蘭,美國就要“直接奪取”。歐洲很可能最終發現自己沒有真正的朋友:既沒有俄羅斯或中國,也沒有美國,更沒有對歐洲包庇以色列種族滅絕心懷不滿的阿拉伯國家,以及仍為殖民與後殖民記憶所困的非洲,更不用説其他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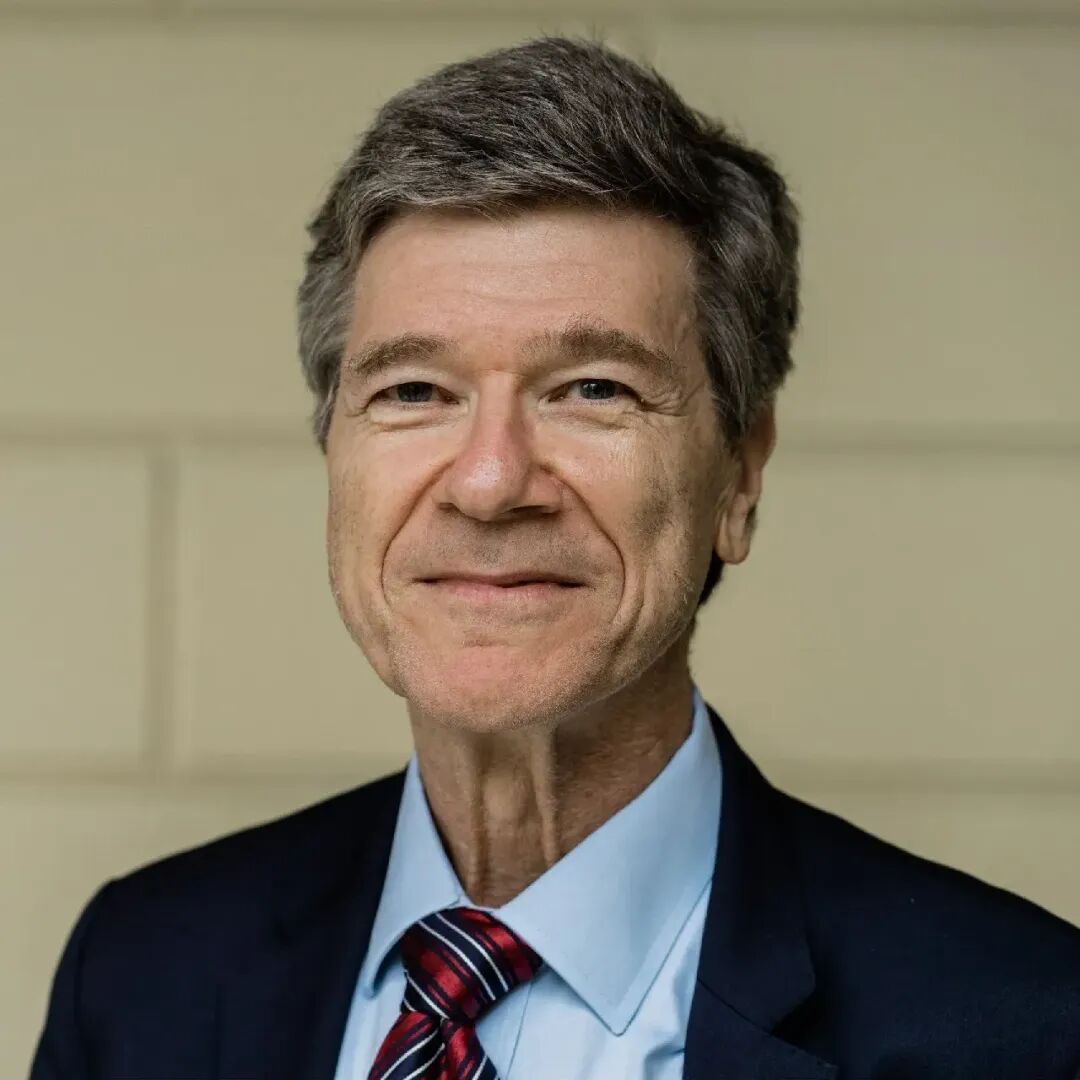
薩克斯資料圖
當然,還有另一條道路——而且是一條前景極為光明的道路,只要歐洲政治家能夠重新審視歐洲真正的安全利益與風險,並把外交重新確立為歐洲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提出十個切實可行的步驟,以實現符合歐洲真實需求的外交政策:
第一,與俄羅斯直接建立外交溝通。歐洲缺乏與俄羅斯的直接外交接觸,後果極其嚴重。歐洲甚至似乎信了自己的外交宣傳,以至於不去同俄羅斯直接討論核心問題。
第二,準備與俄羅斯就烏克蘭和未來的歐洲集體安全通過談判達成和平。最重要的是,歐洲應與俄羅斯達成一致:戰爭的結束必須基於一個堅固且不可逆的承諾,即北約不再東擴至烏克蘭、格魯吉亞或其他地區。同時,歐洲應接受一些對俄羅斯有利的烏克蘭領土調整。
第三,拒絕對華關係的軍事化,例如拒絕北約在東亞扮演任何角色。中國對歐洲安全不構成任何威脅,歐洲應停止盲目追隨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妄想。相反,歐洲應加強與中國的貿易、投資和氣候合作。
第四,制定一套合理的外交制度架構。現行模式完全不可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基本上個“反俄喉舌”;而有限的高層外交則混亂地由歐洲個別國家領導人、歐盟高級代表、歐盟委員會主席、歐洲理事會主席或其不固定的組合來主導。簡言之,歐洲根本沒有清晰的外交發聲人,因為根本沒有統一的外交政策。
第五,歐盟應認識到自身外交政策需要與北約脱鈎。事實上,歐洲並不需要北約,因為俄羅斯並沒有要入侵歐盟的打算。歐洲確實應當建設獨立於美國的防禦能力,但成本遠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5%——這個數字完全是對俄羅斯威脅的荒謬誇大。此外,歐洲防務不應等同於外交政策,但近年來兩者已被嚴重混淆。
第六,歐盟、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應合作推動歐亞大陸的綠色、數字和交通現代化。歐亞的可持續發展對四方都是共贏,且唯有通過和平合作才能實現。
第七,歐盟的“全球門户”計劃應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目前全球門户被定位為一帶一路的競爭對手,實際上兩者應攜手,共同為歐亞大陸的綠色能源、數字與交通基礎設施融資。
第八,歐盟應加大對“歐洲綠色協議”的投入,加速歐洲向低碳未來轉型,而不是將 GDP 的 5% 浪費在對歐洲毫無益處的軍費開支上。這一投入將帶來兩大好處:其一是區域與全球的氣候安全,其二是增強歐洲在未來綠色與數字技術中的競爭力,從而為歐洲創造新的增長模式。
第九,歐盟應與非洲聯盟合作,在非盟成員國大規模擴展教育與技能建設。非洲人口從 14 億將在本世紀中葉增至約 25 億,而歐盟人口僅約 4.5 億,非洲經濟的未來將深刻影響歐洲。非洲實現繁榮的最佳希望就在於迅速提升教育與技能水平。
第十,歐盟與金磚國家應明確告訴美國,未來的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霸權之上,而是建立在《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法治基礎上。這才是歐洲乃至全球真正的安全之路。依賴美國和北約是殘酷的幻想,尤其考慮到美國自身的動盪。相比之下,重申《聯合國憲章》能夠終止戰爭(例如結束以色列的有罪不罰,落實國際法院對“兩國方案”的裁決),並預防未來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