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裔美學者:GDP增速摻水、資本用腳投票,印經濟繁榮究竟什麼成色?_風聞
南亚研究通讯-南亚研究通讯官方账号-09-06 08:03
編者按
印度能否成為下一個全球製造中心?印度FDI淨額的急劇下跌可作為回應這一問題的關鍵信號——印度經濟基本面遠未如其宣傳中那般穩健且“未來可期”。作者論證,圍繞印度的兩大熱門敍事(“中國+1機遇”與“GDP高速增長”)均難以成立:其一,印度並未有效承接“中國+1”產業轉移機遇,製造業佔GDP的比重長期停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球份額自2016年起持續下滑,俄烏衝突後對資本密集型油氣行業的投資也未能有效拉動就業。即便是蘋果代工商的進駐,也因蘋果自身競爭力衰減、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而成效有限,未能實現產業集聚效應。其二,印度的“GDP高增長神話”是一個十足的“偽命題”。數值上,印官方的GDP計算方式有悖於國際通用模式,且以新冠疫情後的短期經濟反彈為基礎,政治性操作設計明顯;結構上,印經濟增長仍依賴公共管理、建築業、金融業三駕“馬車”,這些行業的就業帶動作用有限,遑論印金融市場衍生品交易失控、空殼公司欺詐等亂象頻發,暗藏系統性風險。作者認為,印度經濟困局並不源自“投資者反覆無常”等外因,政策微調無法化解問題。要想實現真正發展,印決策者需摒棄“大國”迷思,正視並着手解決過去長期迴避的結構性問題,即基礎教育質量低下、女性勞動力參與不足,人力資本匱乏拖低生產率,抵消低工資優勢,導致資本回報率無法匹配預期。然而,作者的建言未免過於理想化。結構性改革必需的政治決斷、社會共識與制度執行力,遠非道德層面的呼籲所能實現;倘若印度真正具備這些條件,其深層問題亦不致長期積累、沉痾難解。南亞研究通訊特此編譯本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整體客車廠的全女工班組。儘管泰米爾納德邦在女性工廠就業方面領先全國,其製造業從業人口亦僅佔全邦勞動力的16%。圖源:外媒
有時候,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數字卻足以折射重大信息。2024—25財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資(FDI)淨額僅3.53億美元,就是這樣一個數字。FDI淨額的計算方式是境外資金流入總額,減去外籍投資者匯出資金,再減去印度公民的海外投資額。照此標準,印度的這一指標已跌至過去25年最低紀錄的七分之一(上一個低點為2023—24財年的24億美元)。換個角度看,印度2024—2025年的FDI淨額,甚至還不到2020—21財年峯值440億美元的百分之一。
問題其實不在資金流入本身。資金總流入額雖有小幅波動,但其來源問題更耐人尋味:人口僅130萬的島國毛里求斯是印度最大的外資來源地,更驚人的是,它貢獻了印度全部外國投資流入額的25%。相比之下,真正的癥結在於資金外流——這一問題的答案卻並不神秘。無論是駐印外企還是印度本土投資者,都正在把資金轉出境外,導致FDI淨額持續收縮。2024—25財年,外商投資匯出520億美元,印度居民對外投資290億美元,兩項合計的資金流出規模約為兩年前的兩倍。
資金如此大規模流出印度,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我們不斷聽到“印度即將取代中國,成為全球下一個製造中心”的論調;專家學者也鄭重其事地描繪着2047年“發達印度”(Viksit Bharat)的藍圖。然而,既然外界對印度經濟前景如此看好,為何資本卻反其道行之,紛紛撤離印度?印度央行(RBI)對此給出的解釋要麼罔顧現實,要麼缺乏常識。該行聲稱,資金大規模流出恰恰“體現了印度市場的成熟度”,表明“外國投資者可在印度順暢進出”,進而斷言這“對印度經濟而言是積極信號”。這種説法顯然完全站不住腳。
印央行似乎完全忽略了經濟學界早已有之的“盧卡斯悖論”(the Lucas paradox,)。這一理論以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之名命名。他的核心觀點簡明扼要:作為貧困國家,印度擁有龐大的剩餘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的薪資水平低到令人同情。由此,在印度進行投資的潛在回報率,或許遠高於那些成熟的富裕經濟體。盧卡斯在其研究中寫道,這種資本回報率的差距可能大到“富裕國家不應再獲得任何投資流入”的程度。更直白地説,全球所有投資都理應流向印度這類貧困國家。
當然,現實並不按這套邏輯走:全球絕大部分投資依然流向富國。理論與實際之間的這道鴻溝,就是著名的“盧卡斯悖論”。它提醒我們,必須審視那些阻礙貧困國家將低工資優勢轉化為實際收益的各類短板。
印度所面臨的“盧卡斯悖論”問題更為尖鋭——畢竟外界普遍認為,印度已經具備了崛起潛力。無論是印度本土精英,還是國際有識之士,包括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這樣的知名人物都在積極展望“印度十年”乃至“印度世紀”。若情況果真如此樂觀,資本理應大量湧入印度才對,而非如逃離沉船般紛紛撤離。
眼下對印度的樂觀情緒,主要來自兩大熱門敍事。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所謂“中國+1”策略(China-plus-one),即企業不再把製造環節全部押注中國,而是分散到印度等其他低工資經濟體。這一敍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迅速升温——2018年下半年起,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税,當時外界普遍預期外資將大舉轉向印度,將其打造為新的全球製造業中心。為了迎接想象中的澎湃浪潮,印度政府2020年3月推出“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力圖把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從14%抬升到25%。

孟加拉國依靠女性勞動力崛起和基層教育曾迎來成衣業騰飛,卻因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經濟增長未能全面鋪開。圖源:外媒
“中國+1”敍事之所以聲勢不減,還因為印度被反覆宣稱為“增速最快的全球主要經濟體”。但問題是:一邊是“經濟超級大國”冉冉升起的劇情,一邊是資本大舉離場的現實,兩者如何自洽?要解開這個矛盾,就必須直面那些平時諱莫如深的問題:印度是否先天缺乏發展出口型製造業的能力,因而註定錯失全球機遇?所謂“高速GDP增長”是否只是誤讀數據的幻覺,掩蓋了對深層結構性僵疾的迴避?只有把這些問題攤開講透,才能重新評估印度的經濟前景、國際地位,以及真正可行的對策。
一、 “中國+1”幻象
七十多年來,印度始終沒能在國際製成品出口中站穩腳跟。導致這一困境的癥結始終未變:人力資本的長期匱乏拖低了生產率,而這低下的生產率,又把低工資本可能帶來的那點優勢抵消得一乾二淨。對“中國+1”的樂觀期待背後,其實藏着一個不太體面的現實:印度或許沒辦法把自身生產率提升到足夠高的水平。如此一來,對中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税就成了推動印度發展的唯一途徑。唯有如此,印度才能吸引外資、做大出口、創造自身亟需的低技能崗位。
然而,這種狹隘的思維恰恰迴避了歷史教訓:唯有立足長遠的生產率提升戰略,才能讓一個國家真正把握機遇、實現持久成功。不妨直截了當地追問:為何印度在20世紀50年代勞動密集型製成品出口競爭中不敵日本,60至70年代輸給了韓國與中國台灣,80至90年代又落後於中國大陸,進入新千年後,還被越南甩在了身後?不出所料,如今越南已成為“中國+1”機遇窗口的最大受益者。與所有曾超越印度的東亞經濟體一樣,越南的發展底氣源於兩大基石——普及大眾教育與高比例女性勞動力參與,而這兩點正是印度始終未能築牢的關鍵短板。

越南之所以能在印度跌倒的地方一躍而起,憑的正是普及教育和高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順勢切走中國的出口份額。圖源:外媒
布朗大學經濟學家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指出,當普及教育達到國際最低識字標準,且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處於較高水平時,便能催生出人力資本發展的良性循環。女性進入職場後會更加重視子女的健康與教育;這些孩子成年後生產率更高,而生產率提升的經濟環境,又會為女性勞動者創造更多機會,進而進一步強化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意願。
東亞奇蹟並非偶然,其實則是某一發展進程的現代演繹——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無論在產出結構與出口導向層面存在怎樣的差異,都曾經歷過這一進程。自250年前工業革命開啓以來,普及教育、女性參與勞動與生產率提升三者之間的自我強化式正反饋,始終是驅動經濟持續進步的“心臟起搏器”。倘若缺了這套良性循環,任何國家都無法保持長期穩健的生產率增長。
歷史經驗如此明確,以至於連信奉自由市場的盧卡斯也承認,人力資本匱乏是阻礙資本從富裕國家流向貧窮國家的關鍵瓶頸。他曾闡釋,降低不確定性、優化營商環境雖能助力吸引投資,但“聚焦於人力資本積累的政策,其潛力無疑要大得多”。如果人力資本跟不上,勞動者生產率將長期處於低位,即便勞動力成本低廉,也難以創造高資本回報,資本自然會望而卻步。孟加拉國就是現成的例子。該國之所以能在服裝出口領域取得成就,核心得益於一場基層運動——這場運動同步推動了教育普及與女性自主參與經濟活動。然而,正因缺乏對人力資本的持續投入,孟加拉國始終未能突破服裝業的單一產業侷限,無法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難以構建起更廣泛的經濟競爭力。

在維沙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一位母親攜子女走向校園;畫面映現,正是職業女性助推教育普及與經濟前行的生動註腳。圖源:外媒
2018年9月,特朗普對華加徵關税似乎給印度送來了“天賜良機”。相關輿論炒作迅速升温:2019年2月,一份聯合國報告預言印度將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印度商工部也忙着敦促出口商積極行動“抓緊窗口”。此後,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美國對華關税層層加碼,“印度接棒”“印度崛起”幾乎成了新的“共識”。可惜,這種看法從未得到任何數據支撐。
事實上,“中國+1”機遇早在特朗普關税政策之前就已顯現,且在當時就已逐漸從印度手中流失。哈佛大學學者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顯示,2010年代初,中國就開始逐步讓出部分勞動密集型出口份額。不過,這一轉變進程較為緩慢,原因有二:其一,中國生產商將部分產能從成本較高的沿海地區,轉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內陸地區;其二,中國擁有深度完善的零部件與原材料供應商網絡,這一優勢在其他國家幾乎難以復刻。
在搶佔中國讓出的市場份額方面,越南取得的進展最為顯著;在歐洲市場,波蘭有所斬獲;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國家則在中國新增投資的助力下,成為了另外一批受益方。反觀印度,其在全球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的佔比,自2012年起便趨於平穩,2016年後更是掉頭下滑。
印度藉助化工與石化產品,實現了向非勞動密集型出口的轉型。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歐美國家縮減俄羅斯原油進口規模,印度則趁機大幅購入低價俄羅斯原油,經煉化加工後對外出口精煉石油產品。因制裁限制,俄羅斯無法直接開展這類產品的出口貿易。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當美國關税為“中國+1”機遇窗口拓展更大空間之時,印度卻從勞動密集型出口領域轉向資本密集度更高的出口領域,而這類行業對其國內過剩勞動力資源的依賴程度極低。“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在拉動出口、創造就業兩大核心目標上均收效甚微,2025年初,印度政府已終止該計劃。
不過,也有一個例外——印度確實吸引到了蘋果iPhone手機的代工商。
二、咬一口蘋果
2017年5月起,蘋果的主要代工廠陸續在南印各邦設廠。它們招聘女工,並在廠區旁建起宿舍,這種模式與東亞地區相似。儘管仍然面臨生產率不足、工人罷工、人員流失率偏高等難題,這些iPhone代工廠的用工規模卻在穩步擴大。2025年初,在特朗普宣佈新一輪對華關税後,蘋果公司隨即表示將加快在印擴產步伐。而印度財經媒體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再次重彈六年前的老調:“中美貿易戰將利好印度出口商”。
誠然,這種樂觀預測並非毫無依據。經濟學家戴維·惠勒(David Wheeler)與我合著的一篇論文發現:過去的外商投資是預測未來投資的最佳指標。道理很簡單:外商大規模投資某國,等於向市場發出“此地宜商”的強烈信號,將吸引國內外配套企業跟進入駐,以滿足該地日益增長的原材料、投入品需求。我們把這類外溢性投資稱為“集聚效應”(agglomeration effects)。中國東部沿海,就是當代最經典的產業集聚範本。然而,置於印度的語境下,真正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並非蘋果公司是否會將更多手機訂單投向印度(這一點目前尚無定論),而是圍繞iPhone形成的生產活動能否撬動電子行業乃至其他行業的新投資流入。

在蘭契(Ranchi)的鄉間,一位農婦揹着孩子下地幹活——這幅畫面正是 GDP 統計永遠無法計入的部分。圖源:外媒
歷史給出的答案同樣不留情面:印度始終未能真正形成產業集聚效應。倘若印度當前真存在集聚紅利,外資和印本土資本眼下就不會大舉撤離。早先播下的產業種子,也未能生根發芽:在泰米爾納德邦,製造業僅吸納16%的勞動力,這一數字並無亮眼之處,僅略高於印度全國11.5%的平均水平。早年在泰邦設廠的諾基亞,即便在工廠關停前也未能帶動多少配套就業;泰邦的汽車產業以印度國內標準衡量雖可圈可點,但其存續長期依賴高關税保護,若以全球市場競爭標準審視,也只是“小魚小蝦”,並未催生機械或電氣行業實現顯著躍升。至於蘋果代工廠,富士康此前擬議的半導體投資項目最終也不了了之。
正如記者兼作家帕特里克·麥吉(Patrick McGee)在其近期著作《蘋果在中國:一家偉大公司的“俘獲”》(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一書中指出,蘋果對中國投入的規模之大、時間持續性之久,與它在印度的佈局完全不在一個量級。當年,蘋果投入鉅額資本,由總部加州的工程師手把手實地培訓,在中國成功培育出一個非凡的本土供應體系。這些投資為蘋果帶來了豐厚回報,背後關鍵原因在於充分借力中國深厚的人力資本儲備——而這一點,印度遠未達到同等水平。
一位業內專家曾對麥吉半開玩笑地説,“iPhone先是在中國組裝,拆解後再運到印度重新組裝。”當然,這種説法有點言過其實,況且,從基礎組裝業務起步本身並無不妥。但真正的問題是:印度能否以組裝業務為跳板,實現進一步發展?目前來看,現實並不樂觀——對中國機械設備、專業人才的高度依賴正成為印度發展的阻礙。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智能手機制造領域,即便在製鞋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同樣如此。
麥吉還警示稱,蘋果本身或許已是“明日黃花”。當年由蘋果一手扶持起來的中國供應鏈如今已成長為世界級手機廠商,其全球市場份額甚至超過了蘋果。一旦中國操作系統成為國際行業標準,這些中國企業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市場登頂。儘管蘋果大概率不會重蹈諾基亞的覆轍,淪為全球技術浪潮下的淘汰者,但它確實正逐漸走向二線陣營。從這一趨勢來看,印度此時試圖想“咬一口蘋果”、從蘋果產業鏈中分一杯羹,或許早已為時過晚。
而在人們津津樂道“特朗普關税再給印度送紅利”之際,最新消息卻給印度潑了冷水:在爭奪“中國+1”蛋糕的國家行列裏,印度可能面臨更高的關税。當然,特朗普這場永不停歇的關税輪盤最終停在哪兒、何時停,無人能知。與此同時,特朗普已經放話要對包括印度在內的金磚國家追加關税,並就印度進口俄羅斯原油一事威脅實施制裁。
此外,特朗普還警告美企“不得把崗位外包給印度”,並暗示收緊對技術工人(包括印度人在內)的簽證政策,這一系列變幻無常的政策令印度經濟前景再添變數。若從更宏觀的視角審視當前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便會發現,根本沒人能夠預知全球生產佈局未來將如何重新調整。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一連串朝令夕改、眼花繚亂的政策操作已重創全球貿易。儘管印度在世界貿易中所佔份額較小,但其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的關聯度極高。因此,若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印度經濟也將隨之受挫。
直白地説,特朗普所催生的“印度機遇”狂熱從始至終都帶有短視色彩,如今看來更可能演變為危險誤判。若印度無法通過優質大眾教育培育人力資本,也未能推動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那麼它在全球貿易中仍將步履蹣跚。
三、GDP 高增長神話
不幸的是,印度國內仍有一股持續噪音:GDP高速增長神話。輿論津津樂道的“高速增長”實則被大量相反證據“打臉”,其中尤為關鍵的是,印度經濟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僵化問題。儘管印國內各方極力高喊推動製造業發展,但該國製造業的GDP佔比始終未能提升。印度經濟增長依舊靠三駕馬車:公共管理、建築業、金融業,這些行業的主導地位從未變更。此外,落後的就業結構更令人擔憂——製造業就業規模毫無起色,而農業就業佔比在疫情期間上升後,至今仍高於疫情前水平;而印度在全球製造業貿易中的份額依舊微乎其微,這一現狀也印證了該國已錯失“中國+1”發展機遇。
於是,那些宣揚印度GDP高增長論調的人卻感到困惑:明明GDP 蹭蹭往上走,外資淨額為什麼反而縮減?其實,沒什麼可疑惑的——印度經濟的高速增長神話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事實很簡單:新冠疫情三年,印度的GDP跌幅遠超其他主要經濟體。稍有實務經驗的經濟學者都知道,經濟體在經歷大衰退之後,會出現高於平均水平的短暫增長,印度也不例外。將這段高於平均水平的“回彈”當作衡量經濟表現與增長潛力的標準,完全是自欺欺人。合理的衡量方式,是把衰退與復甦年份的經濟增長率拉通平均,由此計算的結果是4.5%。這一數字才是印度未來幾年更加可信的增長水平,而非近期輿論宣稱的6%以上。
再度審視印度GDP的統計方法,亦可得出類似結論。約兩年前,我就已指出,新冠疫情後印度所呈現的高增長數據中,有相當一大部分源於難以解釋的統計差異。通常,統計機構以兩條路徑估算GDP:一是衡量一國國民獲得的收入(收入法),二是衡量用於購買該國生產商品與服務的支出(支出法)。理論上,用這兩種方法計算出的結果應該完全一致,因為,國民收入總量必然等於對產出品的支出總量。然而,在2023年9月德里G20峯會前夕,印度兩種核算方式計算出的結果首次出現顯著差異:這讓印度的GDP數據可信度存疑——印度統計部門用於核算GDP的收入法數據,遠高於支出法下的商品與服務支出數據。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儘管統計差異普遍存在,但通常偏差數值較小,全球各國統計機構一般會對兩種核算結果取平均值,以便得出更均衡、客觀的GDP增長估值,但印度並未遵循這一常規做法。
若通過平滑處理,我們會再次得出結論:印度GDP的實際年增長率約為4.5%,這與疫情前一年印度經濟的增長水平基本相當。換言之,剔除異常波動後,無論從何種角度觀察,印度經濟的年均增速位於4%—5%區間,而非外界廣為宣揚的更高水平。
此外,印度GDP的增長結構常常被忽視,卻至關重要。要理解為何印度國內商品與服務消費需求及私人投資如此疲軟,增長構成是關鍵切入點。數十年來,拉動印度增長的核心動力始終集中於公共管理、建築業與金融服務業;即便在所謂的經濟自由化時期,再到近年推出旨在刺激製造業增長的PLI計劃,印度製造業在收入創造(即增加值)中的佔比,始終頑固地維持在14%左右。
事實是,印度經濟整體競爭力不足。其增長動力主要源於兩大渠道:一是政府對自身運營的投入或對基建項目的支出;二是監管鬆弛、風險積聚的金融部門。
自印度20世紀90年代初啓動所謂“經濟自由化”以來,該國金融體系始終深陷欺詐文化的泥潭。近年來,印度金融業的增長更是主要依賴向家庭發放貸款,這導致家庭債務、個人債務急劇攀升,眾多借款人任由貪婪的收債人擺佈,加劇了可能引爆金融危機的系統性風險(關於本文作者有關印度金融業弊病的詳細論述,參見重磅 | 當西方大肆吹噓印度時,一場金融危機卻正在醖釀…)。
這種狂熱正以層出不窮的新形式持續發酵。衍生品交易迅猛發展,使得印度在這類缺乏嚴格監管、易遭操縱的可疑業務中“榮登”全球榜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登頂”之路恰好發生在印度錯失“中國+1”製造業貿易機遇的同一時段。目前,全球逾75%的股票衍生品成交量集中於印度市場——你沒看錯這個數字。隨着全球主要參與者湧入印度衍生品“淘金熱”,印本土投資者也拿出微薄資金冒險追逐“一夜暴富”的幻夢。
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數據顯示,這些小型“散户”投資者中的93%都遭遇了虧損。即便在監管環境最佳的情況下,這樣慘淡的結果也不足為奇。而在印度這片金融“蠻荒之地”(financial Wild West),散户更處於極端劣勢。SEBI最近才對總部位於美國的簡街公司(Jane Street)展開調查——該公司憑藉雄厚資本操縱市場,攫取了超常利潤。
目前已發生的、由低財富羣體向高財富羣體的鉅額財富轉移,規模之巨已然令人咋舌,但這不過是印度更廣泛社會弊病的一個縮影。據報道,SEBI對簡街集團的調查尚未收尾,其同時也在對其他全球對沖基金開展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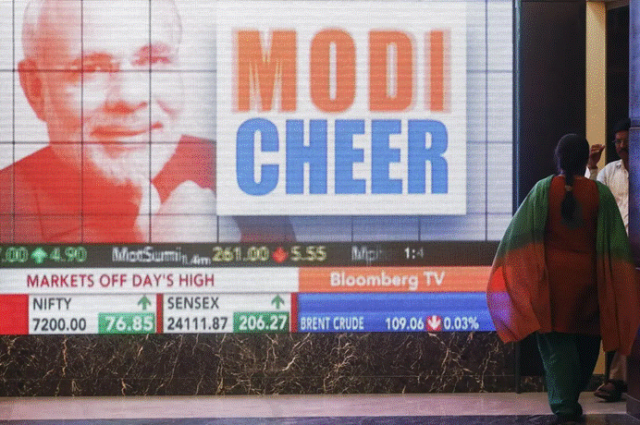
在孟買證券交易所(BSE),國際機構如魚得水,而本國散户卻在監管鬆弛、風險高企的市場中蒙受虧損。圖源:外媒
與此同時,一場“空殼公司騙局”正在上演。空殼公司通常無資產、無銷售、無僱員,往往只有一個難以追查的註冊地址,用於洗錢等非法活動。蹊蹺的是,市值高達1—2萬億盧比(摺合120—240億美元)的空殼公司竟堂而皇之地在印度證券交易所上市。無論以盧比還是美元計算,這一數額都令人震驚,而SEBI對此現象的關注卻姍姍來遲。SEBI的行事風格向來如此——總是亡羊補牢,事後補救,誰也不知道還有多少貓膩正在暗中進行。股市投資組合的連鎖性虧損,恐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又一觸發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傳統的銀行詐騙仍在持續。印度執法局(ED)已對阿尼爾·安巴尼集團(Anil Ambani Group)旗下公司提起指控,稱其犯下包括“挪用公共資金”在內的多項違法行為,罪狀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印度經濟活動模式呈現此種格局,就業增長自然疲弱。公共管理、金融服務業提供的崗位數量極其有限;建築業雖能創造就業,卻多為低質量、低薪且高危的崗位。於是,農業至今仍承載印度46%的勞動力,這一比例甚至高於疫情前。隨着印度人口與求職人數持續上升,農業從業人口不降反升,迄今已比2018年增加了7500萬人,這實在令人震驚。與此同時,製造業就業佔比仍停滯在11.5%。在非農業領域,新增勞動力主要流向低端服務業和建築業。
即便是疫情期間曾短暫擴張的信息技術崗位——其崗位提供數量峯值一度突破500萬個——如今也已迅速降温。自2024年起,印度多家大型IT服務企業紛紛裁員,今年更是幾乎未開展新增招聘。事實上,印度規模最大的IT服務企業塔塔諮詢(TCS)已宣佈將在2025年內裁減逾1.2萬名員工,約佔其員工總數的2%。
人工智能(AI)的興起進一步對印度IT領域的就業構成威脅:有專家預測,未來24至36個月內,AI將重創初級白領崗位。若特朗普政府後續強制要求美國企業限制僱傭外籍僱員,相關形勢還將更為嚴峻。所有這些不利因素,再疊加印度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質量普遍欠佳的問題,使得“以高技能崗位帶動就業”這一願景的可行性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人們早就不應該再執迷於GDP 增速這一單一指標。GDP對經濟福利的衡量本就十分有限。1968年5月,時任美國聯邦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曾有一段精闢論述:“國民生產總值(GNP)把空氣污染、香煙廣告,以及清理公路事故殘骸的救護車費用都算進增長……然而,GNP既不納入孩子們的健康狀況、所接受教育的質量,也不包含他們嬉戲時的歡笑。它無法衡量我們的才智與勇氣,也無法衡量我們的智慧與學識……一言以蔽之,它衡量一切,卻唯獨不衡量那些讓生命擁有價值的事物。”
肯尼迪的警示至今振聾發聵。百姓的真實處境,取決於就業狀況、健康水平、教育質量、環境污染程度,以及能否獲得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務——這些要素共同賦予人們尊嚴與生活品質。不斷攀升的GDP甚至無法準確反映購買力,它僅僅是數百萬艱難謀生者在可支配支出受到嚴重限制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一個算術結果。這樣的算式,對投資者而言根本不構成具有吸引力的市場,這也是境內外資本對印度持觀望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度面前有兩條道路:要麼,繼續沉湎於“GDP 高速增長”與“中國+1天賜良機”的敍事,並對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及其對世界貿易規則的破壞性影響“拍手叫好”;要麼,直面現實,儘管外界口頭上附和“印度崛起”的讚歌,但投資者在行動上卻對印度的潛力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印度長期未解的障礙阻礙着國家進步,而特朗普掀起的全球貿易失序,也將給印度帶來深遠衝擊。
辨喜(Swami Vivekananda,印度哲學家、宗教改革家)常引用《羯陀奧義書》(Katha Upanishad)的箴言:“起來,覺醒,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印度的決策者與媒體應以此為誡。若繼續沉迷於“超級大國”的臆測,只會讓國家誤入歧途、分散精力。現有證據為印度經濟前景描繪了一副冷靜嚴峻的圖景。印度從中得到的啓示,並非“投資者反覆無常”,亦非“微調政策即可化解問題”;真正的癥結在於,印度長期迴避那些根本性缺陷。人力資本薄弱、就業創造匱乏等結構性沉痾,始終阻礙印度實現包容性共享且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欲實現真正進步,印度必須將普及優質教育置於優先地位,全面釋放女性勞動力潛能,併為投資者與勞動者營造具備競爭力且公平的市場環境。只有當決策者幡然醒悟,正視並着手積極解決這些被長期忽視的根本問題,才能不負印度歷史上那些先賢經典所傳遞的智慧。否則,一切豪言壯語皆為空談,全球資本亦將湧向更具活力的經濟體。
**作者簡介:**阿紹卡·莫迪(Ashoka Mody),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印裔美國經濟學家,曾任職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代表作包括《歐元悲劇:九幕戲劇》(2018)與《印度之殤:被背叛的人民,從獨立到今天》(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