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景春 | 民間文學研究向田野要什麼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09-06 22:10
黃景春|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7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民間口頭文學是人類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在當今都市化時代它有沒有過時?如果説只要口頭交流還存在,口頭文學就不會過時,那麼,它的存在方式與過去有哪些不同?我們常説民間文學的第一生命形式是口頭講述和表演活動,而不是寫定的文本,那麼,民間文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就不應是梳理文獻、分析文本,而應是開展深入系統的田野調查。但是,今天的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還必須到遙遠的鄉村去嗎?都市裏湧現的民間文學、網絡上的民間文學改編和傳播如何調查?田野調查在當今社會如何自我更新才能保持自己的研究力度和效度?這是本文要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
民間文學是什麼
**民間文學屬於口頭傳統,基本存在形式是社會生活中的口頭講述、歌唱、表演活動。**從口頭傳統的角度來看,民間文學不是書寫在紙面上的文本,而是生動的口頭文本,是日常的口頭交流,以及作為社區交流事件的儀式性表演。按照理查德•鮑曼的説法:“口頭藝術是一種表演。理解這一觀念的基礎,是將表演作為一種言説的方式。”表演在本質上是一種交流的方式,“表演建立或展現了一個闡釋性框架,被交流的信息在此框架之中得到理解”。換句話説,表演是特定情境中的意義表達,其文化意義是社區成員共同創造和分享的。格爾茨説,“人是懸浮於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一種動物”,“意義是公眾所有的”。口頭表演的意義可能呈現在多個方面,譬如對歷史的追尋,對信仰的張揚,對情感的抒發,對現實焦慮的演繹和闡釋。表演者在與觀眾的言語、動作、情感交流中完成表演過程。受口頭表演理論影響,國內對民間文學的定義也在悄然變化。如萬建中把民間文學定義為一種活動,一種表演過程。他説:“民間文學是一個區域內廣大民眾羣體創作和傳播口頭文學的活動,它以口頭表演的方式存在,是一個表演的過程。”
表演是即時發生、即時觀賞的,無法跨時空呈現,其中的情節、歌詞等被記錄下來,才能轉化為後人欣賞和研究的對象。但是,記錄下來的文本無論多麼活靈活現,都不是民間文學的真人真事,而是真人的素描圖、真事的連環畫。素描圖、連環畫可以保留口頭表演的一些要點,特別是故事情節的主要脈絡,但也會漏掉很多信息。依靠這樣的書寫文本展開研究,就像根據素描圖研究一個人,根據連環畫研究一件事,很多環節都要靠猜想或合理化想象來彌補。所以,查閲文獻、梳理資料等案頭工作是民間文學研究的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環節,但並不是其全部的研究過程。詳備的文獻資料能夠呈現民間文學作品的歷史脈絡,對於理解它的發展演變和文化內涵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缺乏現場觀察和過程體驗,僅依靠不完整的記錄文本所進行的民間文學研究難免需要進行設想和推測,容易造成某些方面的過度闡釋或誤讀。芬蘭學者勞裏·航柯曾把口頭形態稱作民間文學的“第一生命”,把記錄成文本的流傳形態稱作民間文學的“第二生命”。研究者應更加重視對民間文學第一生命的把握,不能用第二生命的東西掩蓋其基本特性。
當然,民間文學還有更多的生命。文人對民間文學的深度改編,為它帶來第三生命。當今旅遊景區的舞台化呈現,互聯網上的改編和傳播,電子遊戲的開發和利用,甚至為民間文學帶來了第四、第五、第六生命。小時候聽老農説“貓狗九條命”,説的是小貓小狗的生命力特別頑強,那麼,民間文學到底有多少條命呢?現在還無法斷定。但是我們可以説,民間文學有多條生命,表明它具有適應社會發展的強大活力。對民間文學的任何一種生命形態,我們都要深入調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學術研究奠定在堅實的地基上。
怎樣研究民間文學
對民間文學書面文本進行故事情節、心理活動、語言風格的解讀,試圖對民間故事或史詩中的人物做形象分析,是常見的借用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來研究民間文學的套路。但這與其説是借用,不如説是誤用,因為這種借用其實並不成功,也很難取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譬如,針對現代小説戲劇人物,我們通常會分析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通過對某個人物的語言、動作、心理活動等細節剖析其性格特點,揭示其對特定時代的典型意義;但是,民間故事、史詩存在於一次次的口頭表演中,表演者在不同的時期和場所、面對不同觀眾,對一個角色的言語、動作的描述都不太一樣,呈現出來的口頭文本也不盡相同,上述對作家作品的細節分析方法用於研究民間文學也就無效了。如果僅拿某個民間文學的書面文本來分析,它跟其他異文有很大不同,那麼,相關分析就經不起推敲。我們經常説,民間文學中的人物不是典型化的,而是類型化的,理解類型化人物不能靠一個故事文本,而要靠同一個故事的眾多異文。那麼,異文如何獲得,如何對待?這其實就是我們應該怎樣研究民間文學的問題。

被譽為“中國荷馬”的居素甫·瑪瑪依演唱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
**民間文學研究應該建立在充分的文獻梳理和田野調查基礎之上。**對具有鮮活的表演形態的民間文學展開研究,需要做田野調查,細緻觀察表演過程,理清表演中的故事情節和情感表達,把握表演者與觀眾的交流,以及表演實踐與社區文化的互動,尋找影響口頭表演穩定與變異的內在要素。鮑曼認為表演是在闡釋性框架中進行的,“框架是一個有限定的、闡釋性的語境”。這個“框架”(frame)包括了與表演效果直接相關的多種特殊符碼、比喻性語言、文化傳統等,還有口頭表演的語境(context)所包括的觀眾構成、現場氛圍、時代精神等內容。一個有經驗的表演者對所有語境要素都能精準把握,並做出妥當的變通,從而順利完成每一場表演。語境是不斷改變的,理想故事在通向既定結局的過程中也會有一定的“轉折”,“轉折意味着主人公現有的狀態、處境或行動目的發生了大的變化”。表演者的處境或狀態也會有所改變,於是每一次表演形成的口頭文本都會有所不同,它們之間互為異文。民間文學研究要建立在對口頭表演儘可能多的觀察、體驗及描述之上,不僅對這個故事、這部史詩的表演要儘量多地聆聽、觀摩,對其他神話、傳説、歌謠也要做盡量多的調查和體驗;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體驗儘量多的口頭文本,通過錄音、錄像記錄表演現場的交流互動情況,進而考察口頭文本生成的過程,表演者個人經歷在口頭文本中的體現,以及文本寫定過程中融入的時代精神、倫理規範等。**通過大量田野調查可以發現口頭表演的特點,把握表演過程中的意義生成,理解口頭文本的可變性和多樣性。**所以,田野調查是研究民間文學的十分重要的方法。
**民間文學的田野調查不僅是為了蒐集第一手資料,也是理解社會生活的一種方法。**它獲取民間口頭文本、記錄表演現場的情形,更像民族學、人類學的民族誌生產過程。實際上,有學者早已指出:“現代民間文學研究日益向民俗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靠攏。”民間文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調查,民俗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也是如此。人類學家指出:“實地調查,即民族調查,是民族學的根本方法。”還有人認為:“田野工作是現代人類學的基石。我們這麼説是因為大多數人類學資料都是通過田野工作而取得的。”田野調查不僅是為了蒐集資料,更重要的目的是還原語境,賦予僵死的記錄文本以社會現實和生活感受。在語境中的研究可以減少脱離語境的歷史文獻所帶來的歧義,限制過度聯想和過度闡釋,讓研究更契合口頭文本的原意。所以,僅把田野調查視為獲得資料的手段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研究方法。日本民俗學家菅豐甚至認為它是具有優越性的方法:“假若將田野定位為純粹為了收集資料而採取的手段,那麼田野作業所具有的超凡的本質價值及其作為方法的優越性就將無從體現……更重要的是,田野作業是一種能夠獲得‘他者的現實’的方法,這種對生活現實的探知是文獻以及其他媒體資料無法得到的。”
當今的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都離不開田野調查,甚至歷史學、宗教學也有依託調查採訪的口述史、口述宗教研究。民間文學有歷史悠久的口頭表演傳統,研究民間文學需要做田野調查,需要引入口頭傳統的研究方法。
田野調查有倫理,有規則
田野調查,又叫田野作業、田野工作、實地調查等。中國古代有天子派官員到民間採集歌謠的“采詩制”,後來發展成採風傳統。文人採風,不僅是到民間蒐集民歌,還要了解民歌賴以生成的民風民俗。就其注重民歌產生的社會環境這點而言,古代採風與當代田野調查有相通之處,所以直到當代有些學者還把田野調查稱作“採風”。但是,田野調查作為多學科運用的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已經形成一套嚴格的操作規範,與古代的採風又不是一回事。
習慣於梳理歷史文獻的研究者,對田野調查所得資料的可靠性、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提出質疑,認為調查所得具有偶然性、不確定性,研究結論不具可驗證性。實際上,認為田野調查“不可靠”是十分奇怪的想法。人類學家一向認為:“田野調查的最大優勢在於它的直觀性和可靠性。在田野調查中,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觀對象,它所獲得的是直接的、具體的、生動的感性認識,特別是參與觀察更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當然,田野調查是有着嚴格倫理規範和操作守則的研究方法,我們必須照章行事。
田野倫理是開展田野調查之前必須弄明白的與調查對象打交道的道德規範。調查者對於當地人來説是一位(或一羣)突然闖入的陌生人,受到排斥、冷遇是常見的事情。調查者必須放下社會精英的架子,本着學習的態度與當地人溝通,平等待人,虛心請教,尊重調查對象,爭取儘快取得當地人的信任和幫助。能夠與調查對象交朋友、建立友誼,對於展開調查工作大有裨益。同時,調查者作為地方文化的“他者”,在調查過程中要保持專業精神和科學態度,對所見所聞保持價值中立,不褒貶當地的人和事,不透露自己的研究計劃和問題預設,以免引起糾紛和誤會。田野作業之後的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也當儘量使用化名指稱調查對象,避免給他們的工作生活造成不良影響。
學者們都希望經歷有温度的田野作業,跟當地人建立真誠情誼,成為好朋友。然而,調查者也不應向調查對象承諾太多,乃至於讓他們擁有調查材料使用的審查權。阿蘭·鄧迪斯曾討論過這個問題:“我知道成功的田野作業中所達到的和諧,往往會產生牢固的、温暖的,雖然可能不是終身的友情。但是將論文和專論的草稿給予資料提供者,讓他們具有否決權,或者,至少是審查的權力,我認為是不能接受的。”調查對象也是我們的研究對象,他們提供了材料,但對材料的判斷和運用是學者的權利,他們不能再提出人情或利益上的主張干擾研究工作。“從田野調查到學術研究,是一個轉換範疇的過程。田野中活生生的自然人,在學術研究中必須轉化為學術符號,它來自於田野,但已經不是那個自然人本身了,正像醫學上做人體解剖的屍體只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而不再是社會人一樣。”我們尊重每一位調查對象,但也要在學術的聚光燈下全面審視他,深入解剖他,讓他以及他提供的材料成為我們的分析對象。
田野調查是有操作守則的。我國民間文學對田野調查方法的介紹已有一百多年曆史。1921年胡愈之《論民間文學》一文就指出,民間文學“是口述的不成文的”,研究分兩個階段,一是採集,二是分類彙編。他所説的採集,其實就是田野調查。民國時期王顯恩編寫的《中國民間文藝》第七章專門討論“民間文藝的蒐集和研究”,討論了蒐集的範圍和途徑、從記錄到發表、研究的準備和類別等;他認為蒐集方法有直接與間接兩種,在記錄上強調“忠實的記述”。1950年,趙景深在《民間文藝概論》第八章“民間文藝的蒐集與整理”,對田野調查的“注意事項”有比較全面的要求:忠實的記錄;注意當地風俗習慣;遇見方言土語可用拼音註釋;歌曲應記譜;對地方戲可以照相、錄音、拍電影等;註明流行於何省何縣;有大同小異的故事或歌謠要一併記錄。這些操作規則對田野調查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應該説,1949年以後,比較正規的民間文學教材都會介紹田野調查的基本規程和要求,如張紫晨的《民間文學基本知識》下編主要討論民間文學的蒐集整理問題;鍾敬文的《民間文學概論》第七章提出了“全面蒐集,忠實紀錄,慎重整理”田野調查三項原則。我國民間文學的本科教材,對田野調查的必備技能都做了介紹。萬建中更在其專著中對民間文學的田野作業方法進行了專章講述,他認為民間文學的田野作業與其他學科的田野作業具有共同性,“但從民間文學的特性出發,它的田野作業步驟也應該有特殊性”。他把民間文學的田野作業的步驟分為:準備工作,包括調查設備、地方文獻資料、調查對象的選擇等;調查工作,參與觀察與訪談是調查的主要手段,對大型民俗活動要團隊作業、分工合作,從民間文學的演述現場獲得本真材料;分析整理,建立以民間文學類型為模式的分析整理機制,忠實民間文學的原貌;記錄撰寫,撰寫出民間文學文本和民間文學志文本。他還對神話、傳説、民間故事、歌謠和諺語的田野作業特點和操作步驟分別加以介紹,對田野作業的指導更具針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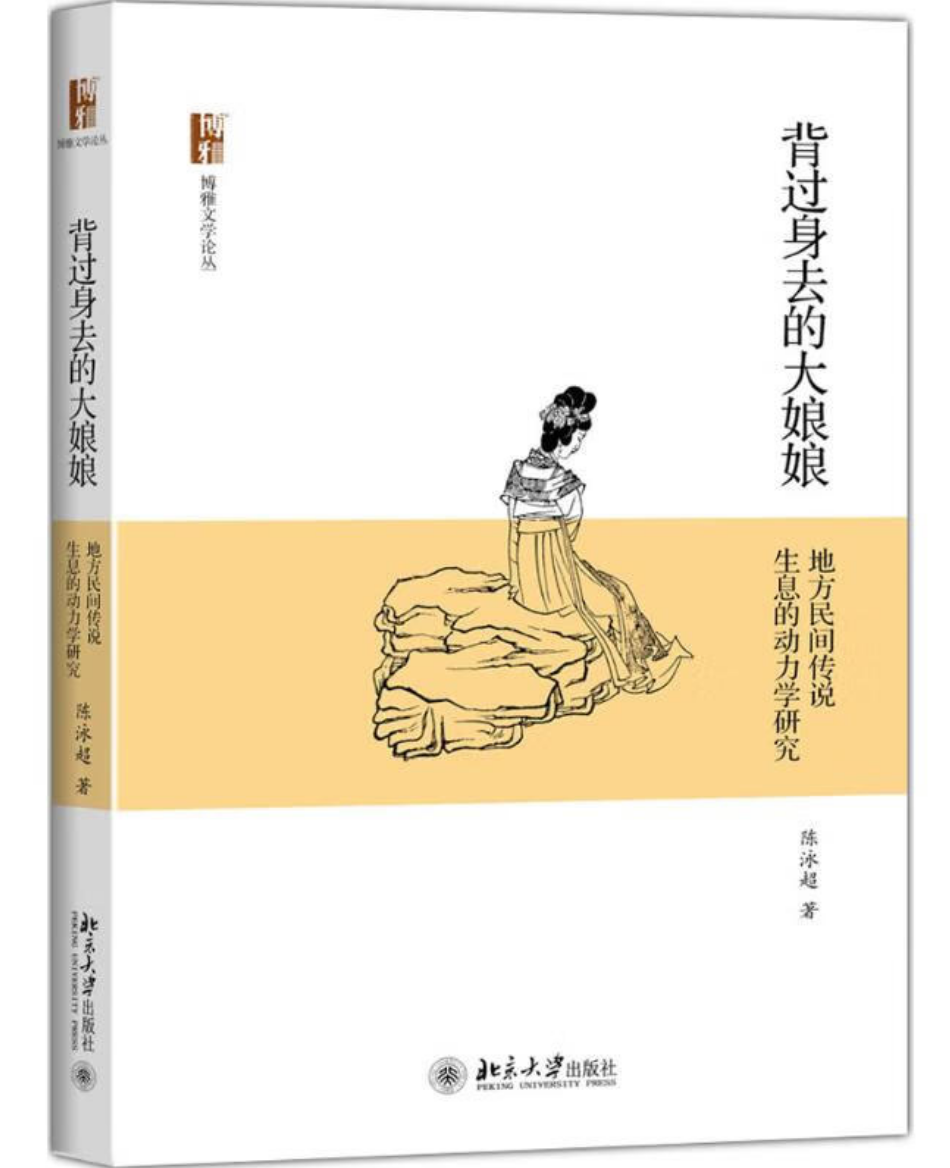
田野調查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工作,而是要反覆進行,所以補充調查、追蹤調查是常見的事情。陳泳超教授在2007—2014年間,連續十幾次帶學術團隊到山西洪洞縣做“接娘娘迎姑姑”調查,對當地廟會活動、“走親”習俗、祠廟祭祀、口頭講述等進行系統觀察和訪談,最終完成學術專著《背過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間傳説生息的動力學研究》(2015)。過去這項習俗在地方誌中的記載,少則十餘字,多則百來字,對其背後的傳説、信仰記載更少,無法分析傳説演變過程中當地人如何發揮作用。陳泳超經過調查積累了大量音像文字資料,最終完成了這部四十多萬字的學術著作。這是通過田野調查取得研究成果的成功案例。
**嚴格按照操作規則獲取的田野材料,跟圖書館查閲的文獻資料一樣可靠,而且更加生動翔實。**陳泳超對洪洞當地的文獻資料(包括近年當地人的私人撰述)掌握齊全,但研究過程中“還是以實際的田野調查和訪談為主要依據”,“大量使用我們團隊自己的錄音文檔”。因為調查材料確鑿可信且具有系統性,不僅能夠支撐學術研究,還拓寬了研究路徑,並在研究中解決了所預設的學術問題。正因如此,田野調查成為推進民間文學學科發展的重要動力。
田野調查是民間文學問題意識的源泉
**田野調查是多個學科得以持續發展的源頭活水,也是民間文學學科進步的發動機。**它不僅解決已有的問題,還能促使研究者發現新問題。新問題的解決固然需要新理論的指導,也需要新材料的支持。新材料的來源不外乎挖掘傳世文獻、出土地下文獻以及開展田野調查三種途徑。如果説前兩種文獻指向過去,可以增強研究者對特定對象的歷史演進的理解,那麼,田野調查則指向當下,為新問題的解決提供新思路,開闢新路徑。
中國文學研究過於倚重傳世文獻,進入20世紀也開始重視出土文獻,但對於田野調查一直比較忽視。我國曆代積累下來的文獻資料極其豐富,依靠傳世文獻、考古資料開展文學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我們都應具備這樣的能力;但我們還必須意識到,任何文獻記載都是對歷史事件的主觀化記錄和描述,遠非事件全貌。況且,對於民間口頭文本,文人在記錄時經常依據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和自己的理解、想象加以潤色,從而扭曲了它的原貌。魯迅曾指出,民歌“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採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按照主觀化的記錄和扭曲的描述來研究民間文學,難免會誤入歧途。如果能把傳世文獻、出土材料與田野調查所得結合起來,對提升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水平必將大有裨益。中國民間文學和民間信仰關係密切,兩者相互滲透,對它們的研究都離不開田野調查。但是,實際研究狀況是,國內學者都過於倚重文獻資料而忽視田野調查。學者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認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研究方法要有所突破,可以嘗試一種綜合性方法:“通過歷史研究、文本解讀來認識傳統背景,再由田野考察來探究結構、功能和習俗等;前兩者有助於後者,後者則有助於更清晰地理解傳統脈絡。”所謂“探究結構、功能和習俗”,也就是探究當代民間信仰的基本結構、文化功能和深層背景。這一探究過程經常激發研究者的新靈感,進而使其感知到新問題。歐大年對民間信仰研究方法的建議對於民間文學研究也有啓迪意義。民間文學的田野調查也應着力於探究結構和功能,不斷髮現新問題,通過對新問題的深究帶動學科向前發展。
對於通過田野調查探究新問題,進而推動學科向前發展這一點,做過田野調查的人——不管來自人類學、民族學,還是歷史學、民俗學——都深有同感。“置身於鄉村基層獨特的歷史文化氛圍之中,踏勘史蹟,採訪耆老,儘量擺脱文化優越感和異文化感,努力從鄉民的情感和立場出發去理解所見所聞的種種事件和現象,常常會有一種只可意會的文化體驗,而這種體驗又往往能帶來新的學術思想的靈感。這種意境是未曾做過類似工作的人所難以理解的。”田野調查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實際上,學者哪怕委託地方人士代做一些民間文學的蒐集整理,都會帶來意外驚喜。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做孟姜女故事研究時,先是依據歷史文獻梳理故事的演進脈絡。當他意識到各地還有很多孟姜女故事在講述時,他就通過《歌謠》週刊發佈啓事,擬出24個題目,徵集各地的孟姜女故事。接下來的收穫之豐讓他眼界大開,“材料的發現,逼着作者修正觀點”。他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原本只作歷史梳理,後來撰寫《孟姜女故事研究》,就在“歷史的系統”後面增加了“地域的系統”,介紹九個地區孟姜女故事的流傳情況。顧頡剛還親自在家鄉江陰地區蒐集吳語歌謠100首,後來出版《吳歌甲集》,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讚譽。胡適在序言中稱讚:“這部書的出世真可説是給中國文學史開一新紀元了。”孟姜女故事研究和吳歌蒐集整理創建了中國現代民俗學、民間文學的研究範式,也開創了民間文學田野調查方法運用之先例。
民間文學原本是地方風雅,無關民生大業,可是在當代經濟開發大潮中,很多神話、傳説、史詩、敍事詩都被用於地方經濟振興。這一進程唯有田野調查能夠洞悉其詳。**當代政治、經濟、文化語境對民間文學的影響如何,也只有通過深入系統的田野調查才能分析清楚。**民間文學幾乎所有問題的發現和解決都需要藉助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面臨的新問題
中國傳統學術的主流是對儒家經典的註疏和闡釋,由此還催生出小學、訓詁學、考據學等,它們都倚重於歷史文獻,田野採風很難進入碩彥名儒的法眼。中國現代民俗學、人類學引入田野調查,顧頡剛研究孟姜女、吳歌,凌純聲研究東北赫哲族文化,芮逸夫研究湘西苗族神話,都廣泛運用田野調查方法。20世紀50年代的民間文學蒐集整理活動,80年代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活動,還有非遺保護運動以來的各項民間文化調查活動,無不採用田野調查方法,每次都獲得了大量的田野資料,有力推動了民間文學的學科進步。
但是,那些面向古典文獻或作家作品的學科,仍然不瞭解田野調查,視其為不正當的資料來源。然而,就在我們不願對本國、本民族的口頭傳統做調查時,我們卻發現國外學者不遠千里萬里來到中國開展田野作業,並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日本學界蒐集到的中國口述神話、傳説、歌謠,以及在調查中獲得的民間藏書,經常讓中國學者汗顏。法國有些學者對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調查,甚至比國內同行還要系統。這些都應該讓我們警醒了!
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必須開展深入系統的田野調查,這不應有任何異議。當然,當代民間文學研究的田野調查也面臨新情況和新問題,必須嚴肅應對,妥善解決。
**第一,民間文學有多種生命形態,其中第一種最為重要,第二種也很常見,田野調查要放眼整體,兼容並收。**口頭講唱是轉瞬即逝的現場表演,需要藉助文字記錄其基本內容。文人在書寫時會注入自己的想法,而書面文本的傳播又會讓他們的想法滲透到後來的口頭講唱中。口頭表演與書面文本頻繁互動,相互生成。不過,隨着民眾識字率提高,寫故事的人越來越多,田野調查中經常會遇到“故事寫手”而不是“故事歌手”。當代調查發現,很多民間故事、歌謠的文本不是在講唱的基礎上寫定的,而是包括基層文化幹部在內的文人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知識積累編創出來的。另外,文人創作的“新故事”,直接以書面發表的形式面世,根本不是在講述或表演中產生的。所以,我們既要重視對口頭表演的調查,也要注意對書面文本的蒐集。
**第二,田野調查的方法要與時俱進,研究者除了到遙遠的鄉村,還要在城市社區做田野調查。**截至2020年底,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已經超過60%,城市裏積聚了最活躍、最具創造力的人羣,他們是中國文化生產和消費的主力軍。像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樣的超大城市,孕育出了豐富的都市文化。當代民間文學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是都市傳説的大量湧現和廣泛傳播,而調查都市傳説只能在都市圈內進行。同樣,當代旅遊業的繁榮帶動了對民間文學的產業化開發,如在舞台上展演民間故事或民間歌謠等,也需要在旅遊景區內進行調查。至於作家對民間文學的再創作,網絡遊戲公司對民間文學的開發利用,也主要是在城市裏進行的,相關調查研究也只能在城市裏完成。

皮影戲《白蛇傳》
**第三,我們還必須探索網絡田野調查的有效方法。**網絡空間成為民間文學創作、改編、傳播的重要平台,為民間文學發展提供了新機遇的同時,也引申出一系列新問題。網頁瀏覽者在轉引這些作品時又會做一些自己的更新和完善,從而形成網絡空間的集體創作、集體傳播。特別是明星緋聞、笑話之類,通過個人博客、自媒體平台、微信(包括朋友圈、公眾號)等途徑,傳播極為迅速,流佈面也很廣。口頭性一向被認為是民間文學的第一特徵,在網絡時代這一特徵淡化了,但集體性依然存在。這對傳統的田野調查方法提出重大挑戰。研究者改以網上關鍵詞檢索、微信瀏覽等方式蒐集信息。網絡田野調查應運而生。考察網絡民間文學的現實語境和交流互動,需要瀏覽大量的跟帖,甚至需要統計出各種跟帖的比例,以便做量化分析。民間文學的存在形態變了,田野調查方法也必須與時俱進,以保證研究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大,地方性、民族性口頭傳統豐富多彩,是民間文學研究的富礦。我們必須轉變學術觀念,充分認識到田野調查不僅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途徑,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是本學科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這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我們必須拋棄對田野調查的偏見,突破舊的學術觀念,把田野調查放到與文獻梳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對待。同時,我們還要大膽借鑑口頭表演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充分認識田野調查的重大學術價值,努力掌握都市化、網絡化時代的田野調查新方法,共同拓展民間文學的研究路徑,推動學科建設不斷登上新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