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評論丨加沙與“歷史終結”_風聞
听桥-有四块腹肌。32分钟前

2025年1月28日,北加沙。圖源: Ramez Habboub/Sipa via AP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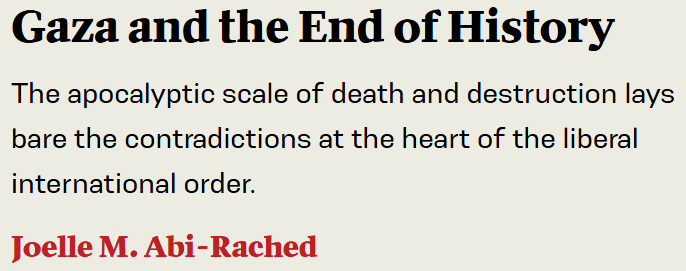
原文截圖
加沙與“歷史終結”
在近期於曼谷近期舉辦的一場關於加沙與人權的專題討論會上,有人問我,加沙被摧毀是否象徵着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分水嶺時刻。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以色列的攻擊已持續近兩年,我們已多次聽到類似説法:一個世界是在這一毀滅之前,一個世界是在這一毀滅之後。但我們真的理解這意味着什麼嗎?
作為雙重象徵的加沙
加沙遭到徹底摧毀的畫面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終歸謬本質。
以色列不只對加沙,還對黎巴嫩、伊朗、也門,如今更對敍利亞,實施了不受制約的轟炸;它以前所未有的全面方式摧毀了醫療系統和維繫人類生存的最基礎設施;它封鎖人道主義援助,襲擊糧食分發點,並將飢餓用作集體懲罰的工具;它對約旦河西岸定居者犯下的謀殺與掠奪土地行為置若罔聞:此番無休無止的殘暴侵略,僅有部分被這份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清單記錄,並被每一種合理化辯解與否認的機制強化,整體而言暴露了國際人道法的全面敗壞,主導人權話語的雙重標準,以及處在西方為維繫地緣政治霸權而拼力推行的諸多舉措之核心地位的種族主義。
今年早些時候,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研究者進行且由《國土報》報道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2% 的以色列猶太人支持將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56%的支持驅逐以色列本國的阿拉伯公民,47% 的贊同以色列國防軍 “效仿約書亞在耶利哥的做法——殺死所有居民”;而在那些將巴勒斯坦人視為 “亞瑪力人” 的受訪者中,93%的認為《聖經》中 “滅絕亞瑪力人” 的訓令至今仍適用。
至我 7 月下旬撰寫本文時,加沙糧食危機的嚴重程度,在西方媒體上引發了自本輪圍困開始以來對以色列軍事行動最強烈的批評;同時,以色列兩家著名人道組織——“醫師人權協會”(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與 “以色列被佔領地區人權信息中心”(B’Tselem),已加入全球眾多學者及團體的行列,宣佈以色列正在實施種族滅絕。面對這一切,民主、人權與道德責任將何去何從?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其新著《加沙之後的世界》(The World After Gaza)中給出了答案。本書基於西方帝國主義、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殖民遺產的更宏大連續背景,審視了以色列的種族滅絕行動。以色列種族滅絕行動的後果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對加沙人民的所作所為以及美國對那些作為的持續縱容正在迫使全球進行反思,與此同時,西方作為普世價值守護者的自我形象,在其同謀罪的重壓下決定性地瓦解了。儘管經過了長時間醖釀,但這一瓦解的嚴重程度眼下已超過冷戰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刻。
證據已有廣泛呈現,且在不斷增多。7 月,在向 “海牙小組” 的一次緊急會議發表演講時,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Gustavo Petro)坦率地向出席這次波哥大會議的三十二個國家提供了一種反烏托邦式的解讀。“海牙小組” 是今年 1 月由“進步國際”(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召集的一個全球聯盟,旨在依據國際法追究以色列的責任。佩特羅表示:“加沙不過是超級富豪們的一場實驗,他們想向全世界人民展示如何應對人類的反抗。” 他接着補充説“他們計劃轟炸我們所有人”,隨後又澄清,“至少是我們這些南半球國家的人”。他援引西班牙內戰期間對格爾尼卡(Guernica)的轟炸,強調這一 “野蠻行徑” 的另一受害者是多邊主義本身——“各國團結協作的機會”、“全球民主理念” 及其國際機構。
當然,正如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在《轟炸史》( A History of Bombing ,2000 年)中所述,從意大利在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到英國在印度及中東各地的攻擊,殖民國家曾習慣性地轟炸手無寸鐵的平民人口。正是格爾尼卡的歐洲背景,令其毀滅對西方而言施加了道德上的緊迫感,並賦予西方的罪行以歷史性意義,而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始終被拒絕這樣的意義。如今,很多西方人將對加沙聲援的日漸壯大視為對西方利益與價值觀的威脅,恰恰是因為這種聲援意圖將道德關切延伸到了那些“不合適”的受害者那裏。在國際法院,與南非一道指控以色列實施了種族滅絕二十個國家中,有十七個來自所謂 “全球南方”,這絕非偶然。
因此,加沙已成為雙重象徵:既是西方偽善的象徵,又是其受害者將人權與國際法作為謀求集體解放——如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稱呼被殖民對象的著名用語所説,“地球上的不幸者”的解放,無論他們是誰,也不論他們身處何方——的最終訴求平台的象徵。對全球秩序和人類未來而言,這其中的法律與道德反響不能被誇大。(弗朗茨·法農,生於1925年,卒於1961年,是法國作家、心理分析學家、革命家。 ——譯按)
永恆的歷史輪迴
一直在延續的毀滅的諸多悲劇當中,一個一再凸顯的古老模式是,加沙似乎無法擺脱一種歷史的永恆輪迴。
加沙是地球上有人類持續生活的最古老城市之一,幾個世紀以來反覆被摧毀和重建。拉丁文通俗譯本聖經《舊約·耶利米書》第 47 章第 5 節開篇即為Venit calvintium super Gazam,即“加沙已經光禿”。在《猶太古事記》( )中,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講述了加沙如何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遭到猶大·馬加比(Jonathan Maccabeus)的攻擊。在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和安提阿古六世(Antiochus VI)內鬥期間,馬加比抵達加沙,卻被拒之門外;為報復,他包圍了加沙,洗劫了加沙郊區,然後接受了和平請求,並將人質帶到了耶路撒冷。
數十年後,歷經一場大約在公元前 96 年結束的曠日持久的圍攻,猶太國王亞歷山大·雅諾(Alexander Jannaeus)佔領並徹底摧毀了加沙,這是其沿海擴張行動的一部分。這座城市一直處於荒蕪狀態,直到羅馬將軍和政治家龐培恢復其獨立,並在公元前 57 年由總督奧盧斯·比尼烏斯(Aulus Gabinius)在一處新址或在其附近加以重建。羅馬統治初期,這座城市再度繁榮起來,後來,伴隨公元 66 年第一次猶太羅馬起義爆發,猶太極端分子再次摧毀了它。“塞巴斯提斯(Sebaste)和亞實基倫(Ashkelon)都無法抵擋他們的怒火”,約瑟夫斯寫道。“他們將這些城市付之一炬,然後將安西頓(Anthedon)和加沙夷為平地。在這些城市附近,許多村莊遭到洗劫,無數居民遭到俘虜和屠殺。”
猶太人並非唯一憎恨“加沙人”(約瑟夫斯如此稱呼該地區居民)的民族。公元 395 年,波菲利(Porphyrius)被任命為加沙主教,他開始改變這座城市異教徒主導的人口,通常的做法是採取強制措施,包括拆除他們的神廟和將神聖空間重新用於敬拜基督教。今天,這位主教被認為是東正教和天主教傳統的早期聖人之一。1150 年,一座帶有他名字的教堂在一座五世紀教堂的地基上建成,用以向他致敬。2023 年 10 月 20 日以色列軍隊炮擊的正是這座教堂,當時有數百名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那裏避難,炮擊致死十八人。在主教的執事馬克撰寫的《聖波菲利傳》(Life of Saint Porphyrius )中,一個關鍵時刻是摧毀馬爾納斯聖殿(Temple of Marnas),這被描繪成對偶像崇拜的戰勝。馬克記錄了加沙人民如何被迫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最重要的宗教聖地被帝國軍隊摧毀,這是由主教和一羣懷恨在心的基督徒煽動的。
法國曆史學家讓-皮埃爾·菲利烏(Jean-Pierre Filiu)在《加沙:一部歷史》(Gaza: A History,2014)中記錄了這一漫長曆程。他追溯了從 “浩劫”(Nakba)、1967 年後的以色列佔領,到 2005 年以色列定居者撤離後全面封鎖確立,直至當代,這片狹長土地遭遇圍困的歷程,同時呈現了該地區歷史維度、政治能動性與全球意義的真正規模。儘管數十年來巴以問題在西方各國對外政策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如此恢弘的歷史仍鮮為人知,這一事實本身就反映出巴勒斯坦人在西方公眾意識中長期蒙受的非人化程度之深。他們充其量被化約為沒有文化、沒有歷史的“他者”(Others)或純粹受害者,對他們的日常刻畫也遠為負面。“我們的相當多歷史被遮蔽了” ,愛德華·薩義德在 1999 年指出。“我們是隱形的民族。” 二十五年多後的今天,情況依然如此。
對以色列近年來在加沙發起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如2008 至 2009 年的 “鑄鉛行動”、2012 年的 “防務之柱行動”、2014 年的 “護刃行動”,以及 2021 年的空襲,西方大國的反應總是遵循重複的模式:先是肯定以色列的 “自衞權” 與 “生存權”,隨後,最多在過度使用武力成為既成事實後提出温和或遲到的批評,且往往絕少有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或外交後果。在此期間,以色列對加沙施加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全球對其將兩百萬居民禁錮於 “露天監獄” 的做法愈發憤慨。
這樣説來,早在當前的種族滅絕發生之前,無數學者和人權組織就在譴責一種明顯的雙重標準:西方政府一方面宣稱致力於人權和國際法,另一方面卻未能追究以色列的責任,且直接援手其罪行,這助長了他們的破壞活動。這種免責模式——嚴格實施的對“受害者的受害者” 的漠不關心——本身就值得進行精神分析層面的探究。該模式涉及關乎猶太人大屠殺的懸而未決的罪責,再加上無法將阿拉伯語民族和穆斯林視為完全意義上的人類,反映了一種陰險的現代反猶主義,這種反猶主義一方面將支持以色列作為猶太身份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則將對一個民族的偏見等同於對特定國家行為的質疑。
西方正道之公信力的破產及嚴重後果
但此次的毀滅盡管與長期的壓迫一脈相承,卻又有所不同。
除了 “浩劫” 以來加沙經歷的十四場戰爭中前所未有的末日般的死亡與毀滅規模,首先還有米什拉所追蹤的清算:喪鐘已為自美國入侵伊拉克、布什政府動用酷刑(且從未為此承擔責任)並在 9·11事件後宣佈 “全球反恐戰爭” 以來,西方竭力維持和宣揚的不論任何道德權威敲響。過去二十二個月以來(且仍在持續),西方政府從經濟、物資和意識形態上極為赤裸裸地為以色列的種族滅絕式攻擊背書,這加速了西方自身在二戰廢墟上建起的基於規則的法律秩序的最終失信。這一秩序圍繞四項相互關聯的準則建構:侵略戰爭的非法性,普世人權與平民保護,問責暴行犯罪,多邊合作。
去年5月愛爾蘭、西班牙和挪威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案例,是證明了這一規則的例外。11月,國際刑事法院發佈對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的逮捕令後,德國、意大利和波蘭領導人誓言,若內塔尼亞胡到訪本國,它們將不會逮捕他或將其引渡至海牙。美國則對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以及聯合國巴勒斯坦領土人權特別報告員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Francesca Albanese)實施了制裁,同時,內塔尼亞胡自 2 月以來已三次入境美國。馬克龍近期宣佈法國將於今年 9 月在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國,而此前,在 10 月 7 日事件後的數月裏,法國曾堅決支持以色列,並聲稱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無效,因為以色列並非該法院成員國。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1949 年的《日內瓦公約》,1950 年的《紐倫堡原則》, 1998 年的《羅馬規約》:在相當決絕地踐踏自己幫助確立的這些準則及相關道德和法律框架過程中,西方大國正以一種他們似乎並未意識到或理解的方式,主導着自身信譽的最終崩塌。然而,那些病態體系正在更廣泛的世界顯現。最近,我在開羅、貝魯特和曼谷參加了多場會議,那些會議的主題多樣,涉及資本主義的未來、歷史創傷的長期後果以及人權話語的命運。來自全球南方的青年學生和資淺學者主張,徹底擺脱與西方相關的知識、政治和道德框架。
這些衝動的念想可以理解,那些批評也不應被輕慢。但因人權的普世性與西方的偽善存在密切關聯或被西方權力腐蝕而存在固有缺陷,於是完全斥之為騙局,則會帶來深重代價,這樣做可能加劇東西/南北分歧,激化令人想起亨廷頓 “文明衝突論”的那種 “我們與他們兩立” 的態勢,還為未來不受哪怕不完美的共同準則和價值觀約束的暴力、侵略和戰爭樹立了危險的先例。在這方面,包括樂施會、海外發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在內的主要人道主義組織和智庫已有警告稱,以色列對加沙救援工作的阻撓,可能破壞全球約一百三十個其他武裝衝突地區或長期存在衝突地區的人道主義響應。正如5月間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埃格(Mirjana Spoljaric Egger)進一步提醒聯合國安理會保護武裝衝突中平民公開辯論會的那樣,無視這些規則是 “道德逐底競賽:一條通往混亂和不可逆轉的絕望的快車道”。
對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民主和自由熱望蒙受無情打擊,人權籲求仍是反對威權統治主要防衞手段的地方的人們來講,戰後秩序基本規則的公信力受到侵蝕,嚴重損害到正在進行的反對不公正的政治鬥爭。
在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重要著作《匡正罪錯》(Righting Wrongs)中,人權觀察組織長期主任肯尼斯·羅斯(Kenneth Roth)令人信服地指出,揭露暴行和倡導正義不只是道德律令,更是在全球舞台上問責權力的關鍵也往往是唯一的手段。國際法和更廣泛的人權框架不只為追求和平與正義的內部秩序提供了框架,更構成了通往更公平、更公正未來的生命線。將一種純粹交易性而缺乏任何問責機制的治理交付給獨裁者、暴君和寡頭——在這種情形下,人權不再是內在的,且在法律上享有崇高地位,反而變得專斷——將是我們最嚴重的錯誤。
因此,佩特羅在波哥大談到,既有必要譴責當前盛行的“野蠻行徑”,又有必要賦予當前被背叛的原則以真正的意義,以維持“另一種人類,一種能夠集體性地愛和思考的人類的可能性”的生命力。正如他與海牙集團的工作所明確表明的那樣,在西方的正道日漸遭到蠶食之後,現在輪到全球南方舉起火炬,領導為真正的平等和正義而戰的鬥爭了。我們的最佳路線是,繼續推動批判性參與,揭露和挑戰西方的盲點、雙重標準、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暴行,同時推進普遍人權框架。
與過去相比,正在進行的攻擊的第二個層面是對健康和醫護權利(即生命權)的前所未有的武器化和系統性摧毀。那些可怕的數字眼下已廣為人知:數千兒童遇害,數千人被截肢,倖存者經歷着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損害。儘管健康和醫護在先前的衝突也中有遭到攻擊,且在烏克蘭、蘇丹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衝突中仍繼續遭到攻擊,但此前從未有過作為一項軍事戰略的全面摧毀整個醫療系統的情形,我們也從未見證如此多的醫護專業人員遭到系統性針對、綁架、虐待和折磨的情形。據世界衞生組織的一個數據庫,自 10 月 7 日以來,全球攻擊醫護系統的罪行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是在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犯下。
在今年 5 月發表的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論中,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醫學期刊之一《柳葉刀》終於譴責了加沙問題上的“沉默以對和逍遙法外”。這篇社論認為,世界各地的公共衞生專家不斷警告但完全徒勞的加沙醫療災難,已不再只是一場軍事暴力危機,更是一場全球共謀的危機:醫療機構的沉默和聯合國安理會的癱瘓,正在助長這些持續公然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社論堅信,結束這種沉默是全球醫療界的職業和道德責任,也是保護平民生命的先決條件。
去年冬天,在超過三十二天的時間裏,菲利烏親自記錄了加沙的情況,同時深入到一個駐紮在加沙中部和南部的所謂“人道主義區”的無國界醫生組織(MSF)小隊展開調查。據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位在現場目睹這場災難的西方專業歷史學家。他的見證融合了發自肺腑的報道——夜間車隊穿越無盡瓦礫的景象,關於家庭一再流離失所、醫院遭到蓄意攻擊的故事——和一位歷史學家有關加沙自 1967 年以來困境的長期見解。今年早些時候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他的日記節選呼應了過去兩年巴勒斯坦人、醫生和人道主義團體的報告,描繪了成為他所刻畫的有條不紊的驅逐和破壞項目(換言之,這正是種族清洗的定義)目標的一片地區。
菲利烏解釋説,他的目的是提供更多關於正在犯下的暴行的直接證據,不然這些暴行在以色列封鎖國際媒體渠道的情況下將無法被看到,並與“西方政府、知識分子精英和主流媒體”的“歷史修正主義”作鬥爭,儘管從一開始就有源源不斷的視頻、圖像、請求和報告從加沙地帶湧出。這是對在西方與以色列聯盟核心發生的人性滅絕和種族主義的另一種再明確不過的考量了,因為這些巴勒斯坦人的直接證詞在西方媒體上絕少被聽到或關注到,通常被視為反猶主義謊言或哈馬斯的宣傳而遭無視,而以色列軍隊和政府的聲明卻被報道,並且未經最基本的審查就被條件反射般地相信。
而現在,加沙正經歷饑荒,這促使西方精英們發表姍姍來遲的警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今年已有超過九千名兒童在加沙接受營養不良治療。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5 月份的一份報告,“這是世界上最嚴重的飢餓危機之一,正在即時展開”,“整個加沙的兩百一十萬人口……面臨長期食物短缺,近五十萬人陷入飢餓、急性營養不良、飢餓、疾病和死亡的災難性境地”。這一消息傳出後,七個歐洲國家在聯合聲明中表示,它們“不會對加沙地帶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人為人道主義災難保持沉默”, 歐盟也開始審查其與以色列的貿易協定。自那以來,局面已經惡化,達到了災難性的頂峯,以至於憤怒開始跨越黨派分歧,登上《紐約時報》的版面。
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在經歷二十二個月的自滿和共謀之後,一些歐洲和美國精英突然改變了腔調?認為基本事實或環境已經改變,認為直到現在真正的警告才恰當,這樣的自負挑戰了所有嚴肅分析。更確切地説,是因為飢餓長期以來一直是帝國主義冒險主義的致命弱點,是一座對開明國家來説太過遙遠的道德橋樑嗎?這樣認為是在討好西方,但這種轉變似乎是由功利主義考慮驅動的:面對民眾支持率急劇下降,試圖挽救一些信譽,或許也是姍姍來遲地意識到,內塔尼亞胡吞併西岸和加沙地帶的擴張主義野心若完全不受制約,對西方自身利益而言就意味着災難。
從加沙到“最後之人”
這樣,加沙就遠不止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
它是一個轉折點,赤裸裸地揭示了當代世界矛盾的全部範圍與殘酷深度:整個羣體根深蒂固的道德偏見與成見,名義上民主的政體內部的裂痕,以及抵抗力量顯而易見的脆弱性,甚至偶爾的徒勞無功。它展現了多數羣體可以如何迅速投降,不論是為了生存還是出於私利,並揭露了當今世界的根本弊病:始終無法承認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且應當享有尊嚴和生命,無論他們的信仰、膚色或宗教歸屬如何。普世人權框架已被徹底掏空,亟需緊急修復。聯合國自身不可或缺卻愈發無能,亟需徹底重組。當各政權滑向威權主義,偏執情緒肆虐,仇外心理延續,自由民主對許多人而言仍只是一種憧憬時,我們承受不起回到人權時代之前的代價。
菲利烏的紀實證言令人想起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的研究: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及活動人士曾於1932年前往德國觀察希特勒的發跡。當她的許多同時代人對德國迅速滑向納粹主義,以及希特勒1933年1月就任總理後對猶太人的早期迫害視而不見,遠遠地作壁上觀之時,韋伊成了最早、最清晰剖析魏瑪共和國崩潰的人士之一。她深具先見之明的觀察教導我們:國家一定要具備出於同情同理心的“根基”,唯有對每一個體承擔無條件的義務,才能阻止現代世界陷入永無休止的戰爭泥潭中。
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的所謂“發達自由民主國家”相當強烈地認同這些原則,以至於蘇聯解體後,弗朗西斯·福山得以在眾聲附和中論定,自由民主作為歷史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已經取得勝利。加沙持續進行的種族滅絕揭示出,圍繞政治合法性、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角逐遠未塵埃落定——歷史中圍繞權力、身份認同與正義的衝突將持續存在,直至人類訴求抵達“最後一人”。
(作者是貝魯特美利堅大學醫學史副教授。本文原題“Gaza and the End of History”,見於《波士頓評論》2025年夏季號。小標題為譯者添加,有多分段。譯者聽橋,對機器提供的初步譯文有校閲,不保證準確理解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