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誰在踐踏烏克蘭的“尊嚴”?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在支持烏克蘭的口號聲中,斯塔默和馬克龍私下還是急着把小澤送回到特朗普跟前。
據説在上週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談判破裂後,澤連斯基直飛英國,接受了英國首相斯塔默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接連5天的悉心“輔導”。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二人説服澤連斯基用順應特朗普的方式和他打交道,先獲取其好感。
也因此,澤連斯基隨後公開表示對白宮會晤“沒有按照預期的方式進行”感到非常遺憾,現在烏克蘭隨時準備以任何方便的形式簽署礦產和安全協議,並準備就結束衝突進行談判。
公開受辱後再“求饒”,歐洲的“斡旋”看來頗有成效。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烏克蘭和歐洲的確還無法獨立於美國,要求他們一夜之間硬起來不現實,這也是特朗普能這麼強硬的根本原因。

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背叛 —— 先是澤連斯基,不久是我們?美國背棄盟友
特朗普的確是太過強勢,但他起碼不裝:屬於我的我要,不屬於我的,只要我想要,也明確無誤地直接説出來。
他是商人,標榜是談判高手(Dealmaker),但他的談判技巧無非是以下幾個套路:
·面對只是籌碼的弱者(如澤連斯基),他直接“三板斧”下去,把對手打暈打懵,逼其就範。
·面對可作籌碼的強者(如普京總統),他會“無原則”讓步,以犧牲其他籌碼為代價,給對方一種“掌控大局”、佔盡便宜的感覺,而他自己盤算的是更大的利益。
·面對真正強大的對手(如當下中國),他會“恩威並施”,一方面高舉大棒(增加關税等),一方面“待價而沽”,先不出牌,在心理上讓對手捉摸不透;公開場合高調示強,作出“勢在必得”的樣子,私底下卻可能態度務實,盡力多拿,得不到也會放棄。
根據特朗普的個性,與其打交道最忌諱的是以下兩點:第一,用前政府和歐洲來當籌碼,他最恨的就是讓其“嚐盡羞辱”的拜登和在其眼裏與拜登“沆瀣一氣”的歐洲大部分政府。第二,談判對手不知輕重,沒牌硬打,覺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
無奈澤連斯基這次把這兩點全都給佔了,因此,他白宮受辱也就不奇怪了。
梅利尼克:烏克蘭駐德國的“噴子”大使
人們在同情澤連斯基的同時,也有聲音指出他在外交場合的口吻和處事方式值得商榷。拋開美方對其“不知感恩”“缺乏敬意”的抱怨,歐洲對基輔的表現也“有苦難言”。
澤連斯基一眾堅信本國抵禦俄羅斯侵略的同時,也是在捍衞西方的民主和價值,換而言之,“我們不僅在為自己而戰,也是在為你們流血犧牲”。正是因為西方許多國家也有此共識,所以澤連斯基及其團隊在向歐美伸手要錢時會“理直氣壯”“毫不含糊”。
以前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梅利尼克(Andrij Melnyk)為例:
2014年3月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吞併後,時任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在同年底正式任命在外交部負責“烏克蘭入歐事宜”的梅利尼克出任駐德國大使。他於2015年初正式就職,在任7年多,時間不算短。
梅利尼克上世紀70年代生於靠近波蘭邊境的利沃夫。他的家鄉在歷史上曾是波蘭領土(波蘭-立陶宛聯邦),二戰後蘇聯版圖大幅西移,利沃夫因而被納入烏克蘭蘇維埃加盟共和國,成為蘇聯領土。
其實,烏克蘭危機從一開始就是俄羅斯影響較重的東部和傳統上親西方的西部之間的衝突。西部歷史上屬於天主教的地盤,而東部則是東正教的範圍。加上斯大林時期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Holodomor)被烏克蘭人視作莫斯科的“種族清洗”,類同於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因此,蘇聯崩塌後,烏克蘭這個曾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並稱為“俄羅斯民族核心”的國家離心力很強。

梅利尼克在利沃夫大學專攻國際關係學以及德語翻譯,後來還去哈佛大學進修過,因此能説流利的德語和英語。他的意識形態無疑是親西方的,同時也是位比較激進的民族主義者。
梅利尼克在德國當大使期間,以口無遮攔、出言不遜的“非外交方式的言行”而出名。
2022年4月,烏東沿海城市馬裏烏波爾圍城戰正酣,正在波蘭訪問的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響應東道主杜達總統的建議,準備和波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的國家元首一起前往基輔以示支持。
出人預料的是,澤連斯基並不歡迎施泰因邁爾,認為他當年作為施羅德總理的“大內總管”(總理府部長)和默克爾政府的外交部長,應當為德國“錯誤的對俄政策”負責。
烏方要求把施泰因邁爾換成總理朔爾茨,德國政界因此譁然。朔爾茨則拒絕在本國元首被拒之門外的情況下,接受前往基輔的邀請,梅利尼克大使隨之便諷刺朔爾茨的行為像“受辱的肝腸”。
在中國有“肝火旺”的説法,在德國,肝臟也被認為與人的性情(特別是憤怒情緒)密切相關。在德語中,這個人體器官常被用來表達一個人情緒化時的表現。“受辱的肝腸”翻成中文就是“小肚雞腸”“小題大做”或“玻璃心”。
梅利尼克的話連德國反對黨都聽不下去了,認為這種表述“難以接受”。聯合政府的自民黨副主席庫比基説得更直截了當:“朔爾茨不是肝腸,而是聯邦德國的總理!”
梅利尼克對傳統上相對比較“親俄”的社民黨(SPD)成見頗深,他在接受德國《每日鏡報》採訪時曾表示,施泰因邁爾幾十年來編織了一張(對俄)的“關係蜘蛛網”。
據《明鏡》週刊報道,梅利尼克還曾大罵德國外交委員會主席羅特是“混蛋”(“Arschloch”)。這個罵人話在德語中相當粗俗,類似中文中的“國罵”。關鍵是,社民黨籍的羅特根本不屬於“知俄派”,而是堅定的“挺烏派”,德國最後決定向烏克蘭輸送重武器就有他的一份功勞。
“挺烏派”尚遭此運,不支持向烏克蘭運送武器的左翼黨自然就更成為梅利尼克攻擊的對象了。他曾向左翼黨議員(現加入了BSW)德馬西開炮説:“最好閉上您這張左(派)嘴!”(“Halten Sie lieber ihre linke Klappe”);或乾脆稱瓦根克內希特為“令人作嘔的巫婆”(“widerliche Hexe”)。
朔爾茨因擔心德國被拖入戰爭而一直拒絕向烏克蘭提供“金牛座”巡航導彈,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穆策尼希在議會辯論中支持朔爾茨的決定,並提出應該“凍結戰爭”。
這下可在梅利尼克那裏捅了馬蜂窩,他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這傢伙曾經是、現在仍是德國最令人作嘔的政治家。永遠都是。”這似乎還不夠,他繼續寫道:“穆策尼希先生可能看起來‘體面’。但我堅持我的觀點:他曾經是、現在仍是德國最冷酷無情、最陰險的政治家。比德國選擇黨和BSW更糟糕。如果他成為大聯合政府的外交部長,我就一槍把自己打死。”
他不僅對德國政治家出言不遜,而且還時有干涉德國內政的言論。譬如:在德國總理朔爾茨訪問莫斯科之前,他在德國廣播電台上指責朔爾茨“過於謹慎”,並呼籲朔爾茨在前往莫斯科時不僅要帶上“合適的毛衣”“還要在行李箱裏放入制裁的大棒”。他在接受《世界報》採訪時表示,朔爾茨當時拒絕停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這是“對烏克蘭的背刺”。
梅利尼克在任內並不認為自己的過激言論有何不妥,聲稱這是自己在當下情勢下的一種施壓方式,他在戰爭爆發前不久接受德國《明星》週刊(Stern)採訪時説:“我的任務就是將手放在傷口上。”(往傷口上撒鹽的意思)
除此之外,這位大使的“右翼”言論也引起媒體的關注和反彈:
他在採訪中否認烏克蘭極端右翼民族主義者、曾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班德拉是屠殺猶太人和波蘭人的兇手,稱其是被蘇聯刻意妖魔化的犧牲品。以色列大使館隨後指責梅利尼克“歪曲歷史事實,淡化Holocaust(大屠殺),並侮辱了被班德拉及其追隨者殺害的人”。烏克蘭外交部也與梅利尼克的言論保持距離。
在馬裏烏波爾保衞戰中戰功顯赫的“亞速營”因與極右勢力關係密切,也因成員中亦有不少新納粹分子而受到西方媒體的質疑和批評,聯合國人權組織指控其犯有人權罪行,而梅利尼克卻認為這是俄羅斯的“假敍事”。
德國民間對這位“噴子”大使頗有微詞,政界卻表現得相當剋制,即便不滿也非常隱忍。譬如,社民黨籍的“住房、城市發展和建築部”國務秘書(相當於副部長)巴托爾在推文中發表了“我覺得這位‘大使’已經令人無法忍受了”後不久,便刪除了這條推文並道歉。
2022年夏,梅利尼克因經常出言不遜而被召回。消息傳來,德國聯邦議院副議長埃卡特還對他表示敬意。這位綠黨政治家表示:“梅利尼克為他的國家全力以赴。他是一個不容忽視、不知疲倦的自由烏克蘭的聲音。”
其實,梅利尼克的“出格”言論反映出來的是烏克蘭人的“受害者情結”和“為歐洲民主而戰”的使命感。因此,雖然澤連斯基及其團隊很清楚,沒有美歐的支持,烏克蘭堅持不了多久,但他們在求助和要錢時,絲毫沒做卑微狀,而是理所當然。誰不給錢,或拖延給軍火,就會招來基輔的指責,甚至“梅利尼克式”的攻擊。
在這方面,澤連斯基“以身作則”:他與朔爾茨總理通話時幾乎要掛電話,因為他認為這種對話就像“在與一堵牆對話”。朔爾茨的優柔寡斷在他眼裏無異於“在烏克蘭背後捅刀”。
德國人好脾氣,也很理性,你可以隨便捏箍,但遇到特朗普這樣的“混世魔王”,你若還這樣,那就得“後果自負”了。
澤連斯基在白宮被當眾霸凌後,當年曾被烏方拒之門外的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還出來為其打抱不平,異常直率地批評了特朗普。他在飛往烏拉圭的途中對德新社表示:“當眾羞辱談判夥伴的那一刻,外交也就失敗了。我從未想過,我們有朝一日不得不在美國面前保護烏克蘭。”
“關於我們,卻沒有我們” (“über uns, aber ohne uns”)
如果我們把時間節點定格在冷戰之後,那麼烏克蘭的確可以被稱為純粹的“受害者”,而且是“雙重意義”上的“受害者”: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分得蘇聯核武庫的三分之一,擁有當時世界第三大核武庫,以及重要的設計、生產方式以及相關設備。
1994年12月5日,烏克蘭、俄羅斯、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簽署了《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為烏克蘭放棄核武並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提供安全保障。
俄英美三國承諾,1)尊重烏克蘭的獨立和主權以及現有邊界(沒做到),2)有義務不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威脅或使用武力(沒做到),3)不進行旨在使烏克蘭……屈從於經濟脅迫,從而獲得任何形式上的好處(沒做到)。4)在烏克蘭成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為的受害者或侵略威脅的對象時,立即尋求聯合國安理會採取行動,向烏克蘭提供援助(部分做到)。另外還有兩條在此省略。
烏克蘭正是在大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才同意銷燬核武器的。事實證明,這份《備忘錄》形同虛設,沒有提供任何“擔保”。
沒了核武,烏克蘭便失去了戰略威懾力。
如果基輔能如基辛格建議的那樣,在之後採取“左右逢源”的策略,它的日子或許會相當不錯。可惜,隨着北約和歐盟的不斷“東擴”,烏克蘭在西方的“誘惑”、“挑唆”和“慫恿”下選擇了戰略幼稚的“一邊倒”道路,也因此引發俄羅斯的強力反彈和武力干預。
歐美的支持從開始的“悲觀猶豫”,到中間讓基輔“不死不活”,再到最後特朗普的“改弦易轍”和“強搶明奪”,烏克蘭官民可謂嚐遍了作為“代理人”和“被閹者”的辛酸苦辣。
這次在英法兩國的斡旋(或壓力)之下,澤連斯基在“受辱”後表示願意重回華盛頓簽約,但有一個“條件”:閉門談判。
顯然,他絕對不想再重蹈覆轍,但同時也説明,他還試圖維護某種與美國“比肩齊眉”的地位。換而言之,關起門來你怎麼着都可以,但在外還是要保全我作為堂堂一國元首的尊嚴。
可是,正如中國人常説的那樣: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從古至今,弱國哪有外交可言,乞討何談尊嚴之有?
有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並用被譽為“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顧維鈞的話來加以佐證弱國也有外交。其實,顧對“弱國無外交”是有切膚感受的,只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國弱才更需要外交,才更要懂得如何外交。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無疑是一個“弱國”的外交使節據理力爭和巧妙斡旋的典範:他在《山東問題説貼》中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城耶路撒冷;他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與日本代表牧野伸顯(Makino Nobuaki)唇槍舌劍數十回合,讓對方難以招架,並因此贏得美英法三國首腦的盛讚。
但這位外交奇才最終並未能改變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結果,因為歐美代表擔心日本若退出可能導致巴黎和會流產,於是對東京作出了犧牲“戰勝國”中華民國主權利益的讓步。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此不妨從中外現代史中各選一例:
《慕尼黑協定》
當特朗普和普京為解決俄烏戰爭單獨談判時,不少人將這種不讓“受害者”烏克蘭參與的做法,比作1938年英法德意拋開當事國捷克斯洛伐克,簽訂割讓蘇台德地區的《慕尼黑協定》。
捷克總統帕維爾表示,美國不應在烏克蘭未參與的情況下私自達成協議,“否則將是慕尼黑綏靖歷史的某種重演,而捷克斯洛伐克對此深有體會”。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也提出:“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又回到了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關於1938年那段歷史,輿論的普遍認知是:第一,綏靖政策無法阻止侵略和擴張野心;第二,大國和強國以出賣小國和弱國利益來滿足自己的“內需和外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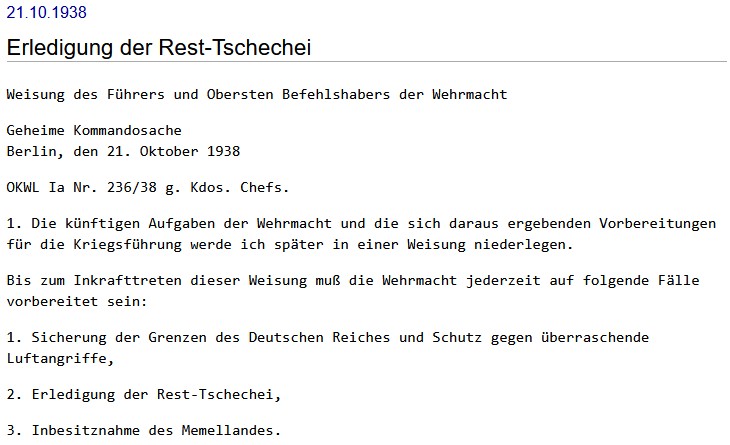
當年希特勒解決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文獻來源:NS-Archiv(納粹檔案)
人們可以把重點放在對希特勒掠奪“生存空間”的譴責上,但更可悲和可惡的是,英法這兩個並非“弱國”的國家,當年居然主動將布拉格這個“盟友”送上了納粹的祭壇;波蘭和匈牙利更是趁火打劫,參與了對鄰國的瓜分。難怪丘吉爾在戰後回憶錄中,將波匈兩國形容為“捷克斯洛伐克屍體上的禿鷲。”
英國首相張伯倫從慕尼黑返回英國後,在機場揮舞着協定文本宣稱“這是歷史上第二次英國首相從德國帶回保持尊嚴的和平,我相信這就是我們一個時代的和平。”
他在這裏略去的“第一次”是指1878年時任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率團前往柏林參加由德國首相俾斯麥主持的國際會議,重新談判俄羅斯和奧斯曼簽訂的《聖斯特凡諾條約》。在這次會議上,迪斯雷利通過強硬的外交手段,成功削弱了俄羅斯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確保了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的利益。
張伯倫返英後自吹自擂所謂的“和平成果”(Peace for our time),迪斯雷利歸國後亦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他聲稱帶回了“光榮的和平”(Peace with Honour),但一如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1878的《柏林條約》也是以縮小保加利亞領土範圍、承認奧匈帝國對波黑地區的佔領為代價的。

張伯倫在機場手持《慕尼黑協定》
這些“和平”論調,我們從特朗普這裏也能反覆聽到:他一再強調,自己的斡旋是為了避免每天新的死亡,是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為了和平。實際上,他單獨與俄羅斯媾和,是為了在烏克蘭和歐盟介入前,先為美國搶到最實惠的利益(礦藏),並以此(加上他其他的“帝國主義訴求”)作為自己的政績來為將來突破憲法的約束,延長執政時間鋪路。
同理,張伯倫之所以對希特勒採取綏靖政策,一方面是他對納粹政府的擴張決心和歐洲局勢的誤判,同時也是出於內政的需要: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後,英國的經濟已不堪新戰端的重負,民眾的厭戰情緒相當普遍;另外,英國在軍事上尚未做好與德國硬槓的準備,還需要時間備戰。
從這個意義上説,2014年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後與烏克蘭簽訂的兩份《明斯克協議》,也是歐盟“雙套車”德法兩國主持下的“綏靖”結果。默克爾和奧朗德事後都承認當時是為重新武裝烏克蘭爭取時間。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1945年的中華民國雖然不是一流強國,但畢竟還是遠東戰場的主力,並不算字面意義上的“弱國”。
然而,面對遭受侵略併為抵抗日寇付出極大生命財產代價的“盟國”,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商時卻出賣了中華民國的利益。
會前未邀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參加,據説是因為羅斯福極度鄙視蔣介石的指揮能力,而蔣又拒絕交出作戰指揮權,所以,羅斯福為防止中國戰線潰敗,最後以犧牲中國權利來換取斯大林的對日宣戰。

雅爾塔會議中的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
根據三方簽訂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協定》,蘇美英三大國領袖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但條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的權益應須予恢復,即:甲、庫頁島及臨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乙、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丙、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中蘇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三方商定,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三、千島羣島須交予蘇聯。
經諒解,有關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鐵路的協定,尚須徵得蔣介石的同意。蘇聯本身表示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中蘇友好同盟協定”,並以其武力協助中國達成自日本枷鎖下解放中國之目的。
當時三國約定,《雅爾塔協議》在一定時間內對蔣介石秘而不宣,但蔣介石已經隱隱約約知道了這個協定的一鱗半爪。鑑於蘇聯即將參加對日作戰,蔣介石指令組成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解決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相關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外蒙古“維持現狀”的問題。
對中國來説,“外蒙古的現狀”毫無疑問就是歸屬中國,但蘇聯理解的“現狀”是外蒙古脱離中國,這是它出兵對付日本的條件。
隨同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等一同前往莫斯科的蔣經國兼有雙重身份:佩掛上校軍銜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曾在蘇聯生活過12年,也多次與斯大林會晤過。蔣介石清楚此次任務十分艱鉅,在正式渠道談不攏時,希望蔣經國能夠與斯大林單獨接觸,爭取有利於中國的會談成果。
根據蔣經國後來的回憶,斯大林在正式談判時,“傲慢地、粗暴地”把《雅爾塔協議》文本摔向宋子文,揮着手中的煙斗説:“您可以討論問題,但在談判時必須以這個文件為基本依據。”
蔣經國據理力爭,用俄語説:“蘇聯肯出兵對付日本,這對中國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於蘇聯的出兵而使中國放棄對外蒙古行使主權,坦白地説是丟了外蒙古,這個要求中國實在難以遷就。因為這是個主權的問題,如果我們答應貴方要求,那麼中國四萬萬民眾都會罵我們是賣國賊。”“您應該知道,中國為了收復被日本侵略的失地,迄今已進行了七年抗戰。現在日本人還沒有被趕走,東北和台灣還沒有收回,再丟失外蒙這麼多領土,抗戰意義又何在呢?人民將不能饒恕我們。”
斯大林態度強硬地回應道:“您應該明白,今天不是我請求您提供幫助,而是您在請求我的幫助。日本佔領了中國,既然要讓蘇聯來幫忙,那就應該接受我們的要求。假如您的國家有實力,你們能夠自己粉碎日本人,能夠自己保全領土,那麼我當然無權提出要求。你們沒有這樣的力量,因此您現在説的都是廢話。”
此情此景,與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白宮紅着脖子爭吵的內容幾乎如出一轍。
到最後,已沒耐心的斯大林直截了當地説:“交還蒙古是不可能的。”他還對蔣經國説:“條約是個不可靠的東西。”言外之意,即便籤約,他也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國家,最終還是要靠本國的實力來鎖定利益。
在這場博弈中,蔣介石堅持的是“對付中共為優先”的思路,他認定抗戰之後必有一場內戰,兩害取其輕,因此力爭蘇聯在即將發生的國共戰爭中保持中立。為此,他放棄了對外蒙的主權立場。
“關於我們,但沒有我們”——澤連斯基如今的遭際,蔣經國當年經歷過,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也體會過。
歐洲不久前一直流行一種説法叫“基於價值觀的外交”,如今,特朗普的一通操作,在世人面前將這個“政治神話”徹底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結語
2014年爆發在烏克蘭的抗議活動和武力衝突被稱為“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
之所以被取名“尊嚴”,是因為抗議者要求基本人權、自由和尊嚴,也因為衝突中的死傷者成為尊嚴和正義鬥爭的象徵。這個冠名其實是在強調抗議活動已超越一般政治訴求,被上升到了“道德和倫理”的層面。
十多年後的今天,烏克蘭似乎還在為這份“尊嚴”而掙扎。只是,這次面對的不是國內的當政者,而是國際上的強權。
當然,大國未必強,小國未必弱。
歷史上,區區歐洲外海的英倫三島,曾建立起萬邦來朝的“日不落”帝國;滄海之東的“彈丸小國”日本一度曾野心膨脹到恨不得要與整個世界爭雄。反之,當年中華民國可謂幅員遼闊;今天的烏克蘭也算是俄羅斯之外最大的歐洲國家,但在強權面前,都先後尊嚴掃地。
悲觀主義者亞瑟·叔本華説,人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
強權的套路從古至今幾乎沒變,強國出賣弱國的理由也大同小異。不同的是,今天的強權比以往擁有了更多的手段。
人們渴望的“和平與正義”,是否只能成為強國利益碾壓下的犧牲品?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