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華勝:“美中對峙、俄歐博弈”的新格局會到來嗎?
guancha
導讀: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北京對話特約專家趙華勝近日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官網撰文,深入分析俄美關係的潛在轉向及其國際影響。
趙華勝指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俄美關係發生歷史性轉折,其速度和力度超出預期,也打破了俄烏衝突以來的戰略僵局。美國不再無條件支持烏克蘭,開始主動向俄羅斯釋放和解信號:俄羅斯最關切的安全問題被降級為“歐洲事務”,而“價值觀外交”所施加的意識形態框架,也被特朗普的現實主義風格弱化。
與此同時,核軍控談判重啓、歐洲駐軍調整被提上議程,俄美關係從“準戰爭狀態”逐步迴歸對話與合作。這一趨勢不僅動搖了傳統美歐聯盟,也挑戰了冷戰後確立的國際秩序邏輯。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指導,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在試圖“甩掉”俄烏衝突包袱的過程中,客觀上為俄美關係緩和創造了空間。
然而,俄美“破冰”仍面臨諸多挑戰:烏歐強烈抵制,美國內部親烏勢力與共和黨鷹派持續掣肘,特朗普外交風格多變等。三十年對抗的歷史遺產仍在發揮作用:俄羅斯對美深層疑慮難以消除,美國的霸權思維與俄羅斯的“主權至上”理念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依舊突出。儘管在能源、北極開發等領域存在合作空間,但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仍需以結束“代理人戰爭”和解除制裁為前提。“聯俄製華”設想缺乏現實土壤,中俄之間高度互信的戰略協作難以動搖。
這場轉折也暴露出西方內部的深刻裂痕:北約凝聚力減弱,美歐互信滑坡,歐洲或被迫進一步推進“戰略自主”。國際格局悄然生變:如果俄美繼續靠近,全球可能從“美歐對中俄”的對抗格局,演變為“美中對峙、俄歐博弈”的新動態。大國關係重組正加速推動多極化進程,但特朗普“交易式外交”背後的霸權本質,仍為全球局勢帶來高度不確定性。
趙華勝指出,中國需警惕俄美互動對全球戰略平衡的衝擊,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合作,為不確定時代中的國際秩序注入更多穩定性與確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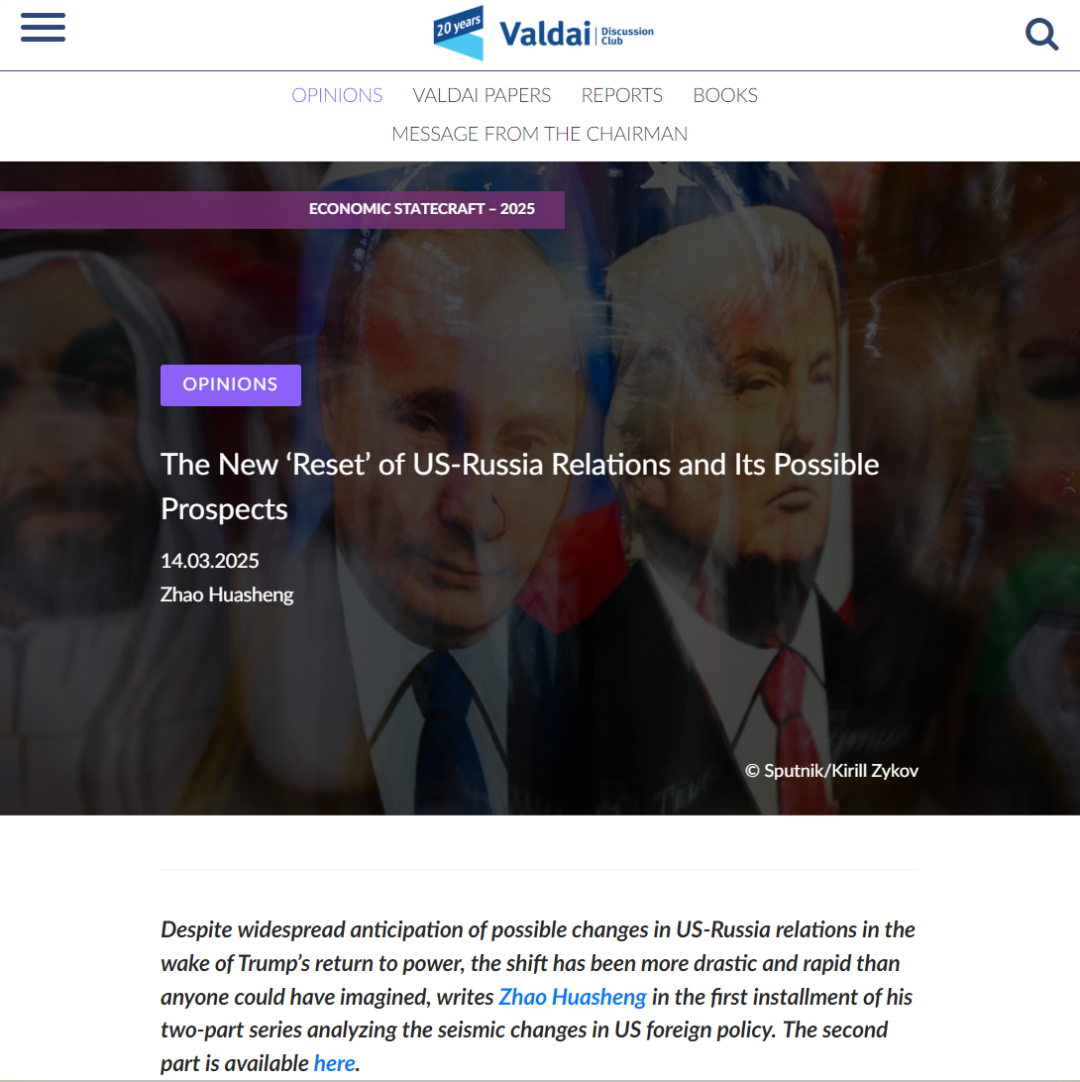
趙華勝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發表題為"The new ‘Reset’ of US-Russia Relations and Its Possible Prospects"的文章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網站
【文/趙華勝】
儘管對特朗普重新執政後俄美關係可能發生變化有普遍的預料,但轉變之劇烈和迅速還是超出了所有的想象。
自烏克蘭危機以來,特別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俄美關係一直處於不斷加深的危機通道中,這種狀況被認為將保持長期“穩定”,甚至在俄烏衝突結束之後也不會改變。但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沒有任何預熱,美國突然改變政策,開始與俄羅斯對話,迅速恢復與俄羅斯的關係,與此同時,美歐關係破裂,烏克蘭被美國事實上拋棄。在大國的歷史上,在基本條件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顛覆性地突然改換國家外交軌道的事例極其罕見,雖非絕無僅有,它超越了國際政治的一般規律。美國政策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國際形勢,也大幅度轉變了俄美關係的走向。
俄美關係在過去30多年裏曾有過多次起伏。俄羅斯獨立之初,在葉利欽和克林頓總統的熱心推動下,俄美關係開始了“蜜月時期”,1993年兩國宣佈為戰略伙伴,美俄關係達到高峯。但此後不久,由於北約東擴、科索沃戰爭、伊朗、伊拉克、軍控、車臣等問題,美俄關係進入了“冷和平”。
2000年小布什和普京分別就任總統,兩國對改善關係重燃希望。2001年“9.11事件”後,美俄關係迅速升温,達到了近乎於“同一戰壕的戰友”的水平。2002年5月,小布什訪俄,兩國宣佈將建立新戰略伙伴關係。但這次熱潮持續的時間也不長,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美俄關係再次轉冷。

2001年6月16日,普京和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在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市郊的布爾多城堡舉行會晤
2008年美俄總統換屆,奧巴馬和梅德韋傑夫分別出任總統。美俄關係又出現樂觀期望。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重啓”戰略。美俄關係稍有起色,但動力不足,踟躕徘徊,在梅德韋傑夫總統任期結束之前即已難以為繼,到2012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宮後,“重啓”徹底結束。隨後發生了烏克蘭危機,一系列衝突和制裁接踵而至,美俄關係跌入低谷。
2017年被認為對俄抱有好感的特朗普成為美國新總統,輿論曾普遍預測他將會給美俄關係帶來新局面。但與預測相反,由於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限制,美俄關係不僅沒有起色,反而愈加惡化。美國開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並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在2025年2月28日與澤林斯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爭吵中,特朗普驕傲地宣稱他的前任給烏克蘭的是破布(sheets),而他給的是導彈。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8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特朗普與澤連斯基在白宮會晤
那麼,這一次俄美關係改善會走多遠?它將重複以往失敗的宿命、還是會打破走不出去的歷史怪圈?它將長久持續還是曇花一現?
與以往相比,這次俄美關係變化有着一系列重要特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弱化了後冷戰時期困擾着俄美關係的一些癥結性矛盾。
在過去的30多年裏,北約東擴是俄美關係最大的問題。從冷戰時期起,北約就是蘇聯的最大安全威脅和頭號敵人。華約解散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政治上與西方和解,而國內陷入嚴重的社會動盪和經濟危機,國家衰弱不堪,對西方已構不成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北約不僅沒有降低對俄羅斯的安全威懾,反而不顧俄羅斯的強烈反對、利用俄羅斯無力阻攔的形勢,開始向東不斷擴大。俄羅斯也曾試圖以加入北約的形式改變與北約的對立結構,事實上,蘇聯在1955年就提出過加入北約的提議,是由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在蘇美維也納會議上提出的,在葉利欽和普京時期,俄羅斯也向北約表達過這一想法,不能排除其中有策略的成分,但北約也都沒有做出回應。
北約東擴導致俄羅斯對西方深深的怨憤和不信任,不斷刺激和激化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也成了阻礙俄美關係發展難以逾越的障礙。美國是北約東擴的主要推動力量,而且它表現得比歐洲還激進。在2008年北約布加勒斯特峯會上,是小布什總統提出邀請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只是由於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反對而未能實現,但由此開始了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進程。
現在特朗普政府明確表示烏克蘭不可能加入北約,排除了在可見將來接納烏克蘭的可能性,雖然這還不是問題的根本解決,俄羅斯認為它還需要國際法層面的保證,需要寫入到最終的和平條約中。2025年2月,北約在紀念成立75週年的華盛頓峯會上,已宣佈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過程不可逆轉。在俄羅斯看來,對這些政治立場也需要有正式的糾正。但無論如何,美國的新政策大大緩和了俄美關係的緊張,使消除兩國關係中的這個最大刺激因素出現了希望。未來如果烏克蘭加入以歐洲國家為主體的其它形式的軍事聯盟,它引起的衝突將主要是在俄羅斯和歐洲之間,而不是在俄羅斯和美國之間。如果北約滑向內部破碎鬆散、甚至解體,則北約擴大問題在俄美關係的議程上將自然消失。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8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特朗普與澤連斯基在白宮會晤 金橋智庫
安全問題始終是俄美關係中的焦點。美國把俄羅斯定位於安全威脅和對手,這一點被寫入了美國的官方戰略文件,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和《美國國防戰略報告》(2018),也寫在了拜登任職期間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2021)和2022年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
在重新執政後,特朗普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他對俄羅斯的擔心明顯降低,現在他認為俄羅斯主要是對歐洲的威脅,但不是對美國的主要威脅,而且,與美國的北約歐洲夥伴相反,他宣稱北約沒有遭受俄羅斯入侵的可能。美國新任國防部長皮特.海格賽斯(Pete Hegseth)在2025年2月烏克蘭國防聯繫小組會議上表示,美國對安全的注意力將從歐洲轉向亞太,歐洲的安全將主要由歐洲負責。
這表明,雖然特朗普政府還沒有就俄羅斯對美國安全威脅做出新的正式定義,但它的趨向已經很明顯,就是認為俄羅斯對美國的直接安全威脅降低,美國不再把俄羅斯作為主要的防範對象。如果俄烏衝突和平協議能夠達成,特朗普政府的這一想法將進一步發展,因為雖然中俄都是美國官方定義的安全威脅,但性質和特點有很大差異,中國被定義為全面持久的威脅,是世界上唯一能對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提出挑戰乃至取而代之的國家,而俄羅斯只是一個緊迫的威脅(acute threat),它的國力太弱,完全沒有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實力,更不用説替代它。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強化了俄羅斯威脅的緊迫性,如果戰爭結束,它的尖鋭性和迫切性會大大減輕,它對美國安全威脅的程度自然會隨之降低。
特朗普拋棄了美國的價值觀外交,這是一種“離經叛道”,在冷戰結束以來的歷任美國總統中絕無僅有。價值觀外交是美國自由主義外交的一個傳統支柱,它也是後冷戰時期俄美關係緊張和衝突的重要來源。從價值觀外交出發,美國和西方以意識形態劃線,把國家分成所謂民主和極權兩大陣營,把自己列入民主國家,自然帶有了政治上正確和道義上高尚的性質;把對手定義為極權國家,被打上反民主和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烙印。俄羅斯自然在極權國家之列,甚至被稱為是獨裁政權。
價值觀外交超越了傳統的以主權為基礎的國際法,它為干涉他國內政,發動“顏色革命”、推翻他國合法政權提供了“合法性”。價值觀外交與俄羅斯的外交理念完全對立,而且俄羅斯自身也價值觀外交的受害者。美國在俄羅斯和俄羅斯周邊推動“顏色革命”,支持俄羅斯的反對派和各周邊國家的反俄力量,蠶食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威脅俄羅斯的政權安全。俄烏衝突的發生也與美國推行價值觀外交有着脱不了的干係。
2013年,烏克蘭發生了“邁丹革命”(Maidan revolution),推翻了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權,親西方政權上台。“邁丹革命”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和推動,甚至有美國高官直接參與、現身於示威人羣中。俄羅斯把“邁丹革命”稱之為國家政變。以這一事件為拐點,形勢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烏克蘭完全倒向西方,確定了加入北約的國家戰略,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出現了一個不斷升温的火藥桶,最終以俄烏軍事衝突的形式激烈爆發,烏克蘭成了犧牲品。應該看到,美國的價值觀外交不是純粹的,它也受地緣政治利益的指導,服務於地緣政治利益,“顏色革命”所推翻的往往都是西方不喜歡的政權,而美國支持上台的基本是親西方的政權。

2015年8月,反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自治的抗議中,一名斯沃博達黨向警戒線內投擲手榴彈 法新社
特朗普的商人習性盡人所知,他看重實際利益,特別是經濟好處,對意識形態不甚在意,或者説完全沒有這種意識,自由民主等口號很少出現在他的詞彙中。只要有實際利益可圖,特朗普可以與任何國家發展關係,不管它屬於什麼陣營,同樣,如果他覺得佔了美國的“便宜”,或者説他想佔別國的便宜,那不管對方是誰,不管它是所謂民主國家還是集權國家,不管它是盟友還讓敵人,它也都“一視同仁”,不留情面。這一點在他對加拿大、墨西哥、丹麥、歐洲的態度上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不過,這不是通常理解的國家關係非意識形態化,它更多是出於一種極端和沒有規則底線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而且是霸權的行為。這也不是新的孤立主義,它並不拒絕插手國際事務,以利益為導向的佈局,既不是退回美國,也不是退回美洲。但無論如何,特朗普的這一做法至少降低了意識形態因素對兩國關係的負面影響。
在特朗普重新執政後,俄美有了重啓削減戰略武器談判的可能。核軍控是俄美安全關係的重要基石之一,START-3將與2026年2月到期,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俄美關於新條約的談判無法進行,如果在條約到期後沒有新條約接替,俄美的核武器發展將失去任何法律的限制,核競爭和核戰爭的風險都將上升。如果俄美能夠恢復談判,並進一步達成新條約,對於俄美關係的緩和也會有重要的積極影響。
同時,美國減少在歐洲軍事存在的可能對俄美關係來説也是向好的預期。美國是北約的主要作戰力量,是對俄羅斯北約軍事對峙的核心。美軍在歐洲一直保持着強大的軍事存在,目前美軍在歐洲有8萬多人的駐軍,有200多個常駐和臨時軍事基地,配備有海陸空重型武器,美軍已經部署到波蘭和羅馬尼亞等接近俄羅斯的前沿國家,美國的戰略轟戰機也會隨時進入歐洲。美國在2019年退出了中導條約,可以在歐洲重新部署針對俄羅斯的中短程導彈,這尤為惡化了俄羅斯的安全環境。
特朗普政府目前還沒有做出減少在歐洲駐軍的決定,但表示在考慮對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進行調整,不過,在安全重心向亞太轉移的背景下,在要求歐洲承擔起更大的安全責任的想法下,降低在歐洲的軍事存在應是合乎邏輯的結果。如果形勢真能向這一方向發展,俄美在歐洲軍事安全上的對峙可有所緩解,並且進一步為俄美討論形成新的歐洲安全格局和機制創造條件。

1987年12月8日,美、蘇兩國首腦在華盛頓簽訂了《中導條約》維基百科
概括地説,特朗普外交強烈衝擊了美國外交一系列重要觀念和政策。在烏克蘭問題上,他改變了由烏克蘭決定戰爭進程,美國無條件支持的政策,對澤林斯基政府施加壓力,迫使烏克蘭割讓領土和接受和平協議;在對俄關係上,他大幅度轉彎,實施對俄和解與合作政策,在“大棒”中增加了“胡蘿蔔”;在戰略思想上,它背離了大西洋主義,疏遠了聯盟政策,減低了對北約的支持,與歐洲發生衝突,造成美歐關係的嚴重分裂;在思想體系上,它拋棄了自由主義,放棄了價值觀外交,不以民主還是集權確定對外政策;在安全戰略上,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中俄的雙重抑制,更突出了中國威脅,淡化了俄羅斯對美國的安全威脅;在外交政策排序上,它以經濟利益為優先,把外交變成生意,以貿易戰代替槍炮戰,急於在烏克蘭實現和平,不管是以什麼條件。此外,還有一個可能的重大轉變,那就是美國對多極化問題上的態度,這個問題還不確定,暫且不論。
不過,這還不意味着俄美關係由此將順利地和持續地向前發展,它仍有許多嚴重的問題需要解決,許多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
從當前形勢的角度看,俄烏衝突是繞不過去的第一道門檻,如果俄美不能邁過這道坎,俄美關係後續的發展就無法順理成章地接上。就現在的情況來説,特朗普的目標明確,就是儘快拿到和平協議,結束戰爭。對特朗普的動機有不同看法,有觀點認為特朗普商人天性,不喜歡戰爭,他在其第一任期裏沒有發動過戰爭是很好的證明。這種觀點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盡然,在特朗普一邊急切結束俄烏衝突的同時,美國放縱巴以衝突的繼續,對也門胡賽武裝實施最嚴厲的空中打擊,對伊朗進行戰爭威脅,這表明特朗普也不是和平主義的信徒。也有人認為特朗普是覬覦諾貝爾和平獎,以滿足他的虛榮心。特朗普自己則説,他的動機一是因為太多人在戰爭中死去,二是因為使美國花了太多錢。

美國白宮新聞秘書長卡羅琳·萊維特2025年3月20日對外宣稱,總統特朗普“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帶重啓的軍事行動
不過,從實際的結果分析,特朗普更可能是把俄烏衝突看作是拜登留下的爛攤子,他顯然不想繼承拜登的這份“遺產”,要與它做出切割,表明拜登製造戰爭,而他結束戰爭。這還能使美國儘快從俄烏衝突中擺脱出來,以便全力投入“使美國再次偉大”的任務,否則他短短四年的任期將被消耗在這種戰爭中。實際上,拜登上台後就急忙從阿富汗撤軍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想法,但考慮的草率和混亂的組織使美軍阿富汗大撤退變成了一場大潰敗,成了特朗普用來嘲笑拜登愚蠢的素材。
特朗普的政策顯然有利於俄羅斯,它可以接受俄羅斯保有控制的土地,並壓烏克蘭做出妥協。特朗普“不站在任何一邊”的政策只能是表明不再站在烏克蘭一邊,因為美國本來是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的,這實際上等於是向俄羅斯的靠近。不過,這還不意味着最終的和平協議會就會達成。烏克蘭當局不會同意割讓領土,那等於對國家民族的背叛和政治上的死亡;它也不會同意去軍事化,那意味着它將在俄羅斯面前被解除武裝;即使現在不能加入北約,它可能也不會接受中立地位,那等於放棄與西方的安全合作和安全保障。雖然烏克蘭在戰場上處於劣勢,手裏缺少有力的談判籌碼,但它仍有能力堅持自己的立場,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力量,在它的背後有歐洲作它的戰略後盾和大後方。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和平條件尖鋭對立,雙方相互都不能接受,特別是在領土問題上,沒有兩全其美的餘地。在這種情況下,最終和平協議的達成將困難重重。特朗普的目標是迅速結束戰爭,達成和平協議,不管是什麼條件下的和平協議。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不得不同時或輪流對俄烏都施加壓力。誰成為和平協議的主要矛盾,誰就是他打擊的主要對象。
俄羅斯明確表示,和平協議必須考慮它的要求,它不會接受一個不符合它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和平方案。如果俄羅斯堅持自己的立場毫不妥協,如果特朗普認為俄羅斯變成停火的主要阻力,使他提出的和平協議無法落實,他會將矛頭轉到俄羅斯身上,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對俄羅斯實施更嚴厲的制裁,對此特朗普已説過多次。如此,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必然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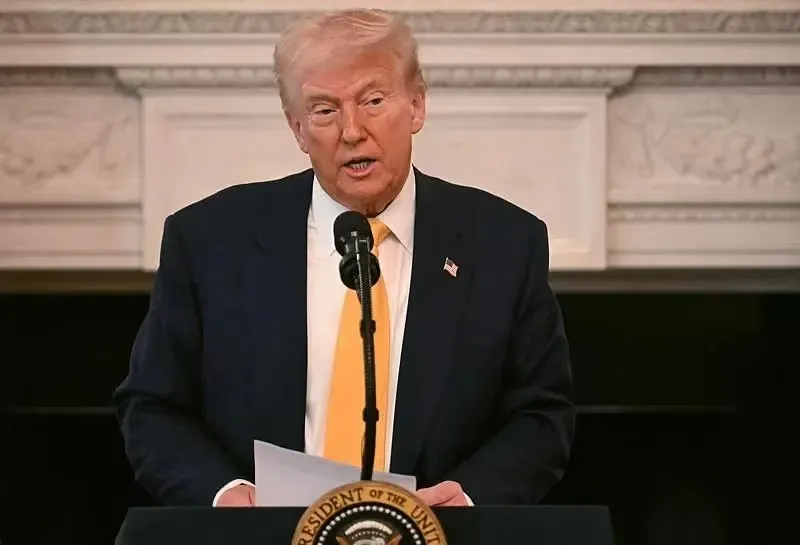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認為有機會達成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和平協議央視新聞
不過,如果出現和平協議無法很快達成的情況,特朗普將不得不做出選擇:是繼續把簽署和平協議作為與俄羅斯發展關係的前提條件,還是知難而退,改變思路,在戰爭仍然進行的狀態下繼續與俄羅斯發展關係。出於特朗普的戰略設想和個人喜好,他選擇後者的可能性應該更大一些。
俄美還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就是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和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美國是烏克蘭最重要的援助國,它向烏克蘭輸送飛機、大炮、坦克、導彈等重型武器,為烏克蘭提供在現代戰爭中至關重要的衞星偵查情報,為烏克蘭無人機打擊俄羅斯提供方位和導航,美國實際上也成為烏克蘭軍事行動的組成部分,這些無疑都是戰爭行為。同時,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前所未有的嚴厲經濟制裁,力圖扼殺俄羅斯財政和經濟來源。
美國新任國務卿魯比奧承認這是美國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但按照傳統的理解,俄美現在事實上是處於“準戰爭”狀態,或説是非正式戰爭狀態。在結束這場“代理人戰爭”之前,俄美關係不可能正常化,更不必説發展友好關係。而結束它的唯一途徑是美國不再向烏克蘭提供大規模軍事支持,開始改變對俄羅斯的經濟封鎖政策,並逐步解除大部分制裁。現在看來,這也不會是一個簡單和迅速的過程。

2019年6月28日,日本大坂,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G20領導人峯會時,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晤並嘗試與對方握手 路透社
特朗普與俄羅斯的關係仍是一個迷。關於特朗普與俄羅斯交好的動機和原因有許多猜測和分析。解讀五花八門,各色各樣。有説是因為他與俄羅斯源遠流長的關係,對俄羅斯有着一種莫名的好感,兩任斯拉夫裔夫人也影響了他;有説法是俄羅斯掌握着他不能見光的材料,他被俄羅斯要挾;有評論認為是因為他崇拜強人,尊重普京,與普京有特別的友好關係;有判斷是他要與拜登反其道而行之,實現他競選期間誇下的海口,最聳人聽聞的是説他是俄羅斯的內應,是長期隱藏的俄羅斯的間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特朗普對俄羅斯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他最終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俄美關係,這些很難為外人所知。他想與俄羅斯做“大交易”,他準備出什麼價?他要從俄羅斯得到什麼?不能確定他是準備重構俄美關係、使其成為一種戰略性合作關係、還是隻是因為他對俄羅斯和普京總統充滿好感,因此願意與俄羅斯發展關係,但無任何戰略意圖和目標。不同的思路也會影響俄美關係的發展方向。
特朗普決策快速、突然、急劇,但改變起來同樣是快速、突然、急劇。換句話説,特朗普外交不循常規,不按常理出牌,受即時性事件和情緒影響大,極易朝令夕改,突然轉彎,難以預知。簡單説,特朗普的個性就是變化莫測,他的政策穩定性和連續性沒有保證,發生政策反轉的可能性會一直與他同在。

2019年6月28日,日本大坂,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G20領導人峯會時,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晤並嘗試與對方握手
美國國內反俄親烏的力量依然強大,共和黨人、國會的反對派、精英階層、一些大利益集團仍堅持它們的立場,在特朗普就任後並沒有任何改變。在最初的震驚和沮喪過去後,它們會重新組織和重新集結,伺機發動反攻。反對派力量對特朗普是有力的制約,而且不僅僅是對他的對俄政策,也是對他的整個外交政策,乃至對特朗普政權本身。特朗普的對俄政策不僅不可能得到它們的支持,反而更加刺激了它們的反對態度。
因為立場相反,特朗普與對俄政策進展得越順利,俄美關係越發展,它招致的抨擊可能就越激烈,而一旦對俄關係遭遇挫折,更會遭到強力反攻,要求改變對俄政策的壓力就會更大;換句話説,不管俄美關係發展得順不順利,特朗普的對俄政策都會招致反對派的攻擊。在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特朗普可能轉而對俄羅斯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顯示他不僅不親俄,而且對俄更強硬,以彌補在國內政治上的失分,扭轉對自己不利的政治局面,事實上,特朗普為了自證也經常説他是對俄羅斯最嚴厲的人。
從更宏觀一些的視角看,俄美要發展戰略性合作關係,它的一個重大障礙是相互的負面認知。這是過去30多年俄美關係給兩國留下的沉重負資產,兩國相互的形象都是負面的,沒有基本的信任。這種認知是長期積澱而成,難以很快改變,特別是在俄烏衝突之後又大大加深。負面認知對形成高層次國家關係是無形的藩籬,導致對發展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缺乏信心,並且對政策的形成產生影響。
這次特朗普對俄的有利舉動雖在美歐引起譁然,但俄羅斯從領導層到精英界都反應比較冷靜,並沒有過分的欣喜之色,從俄主流學術界的認識看,多數觀點對兩國關係改善的前景持謹慎態度,有所保留,有的觀點還比較悲觀。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也提醒不要用玫瑰色來看待俄美關係的變化。這與過去俄美關係出現升温時輿論的熱情洋溢形成明顯的反差。這不表明俄羅斯不希望與美國發展關係,精英界主張與美歐和解的大有人在,這只是由於過去多次的痛苦教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使俄羅斯不敢再輕易地對美國加以信任,對俄美關係的長期穩定信心不足。
假使説,烏克蘭加入北約以及和平協議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俄美關係還將面臨一個重大挑戰,那就是它們在國際秩序建設上的原則性矛盾。特朗普奉行的美國優先政策實質也是一種霸權,是一種更加唯我獨尊的霸權體系,美國欲對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半島、烏克蘭礦產、加拿大土地的強取豪奪,都説明特朗普之下的美國仍是霸權。霸權與俄羅斯所追求的多極化世界觀不能相容。美國新政府也開始意識到現在已經是多元化的世界,國務卿魯比奧已談及這一點,俄羅斯外交和學術界也有判斷認為特朗普已經接受世界多極化的事實。不過,這還是一種尚在發展沒有定論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承認多極化的事實不意味着美國與俄羅斯在對多極化的理解和政策上一致。
《慕尼黑2025年安全報告》以“多極化”為標題,承認多極化已是世界的現實,但它以消極和負面的眼光看待這一變化,認為這一國際權力轉移過程有可能帶來更大混亂。美國對多極化的理解更可能與歐洲相似。俄羅斯在當今國際政治中的立足之地還是多極化、全球南方、金磚集團、上合組織等,它們是反映俄羅斯利益和追求的基本平台,只要有可能,俄羅斯與美國發展深層合作,但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外交框架去追隨美國,它仍將以繼續推進多極化、金磚集團、上合組織、與全球南方的合作為其外交的基本方向。

2024年2月18日,慕安會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閉幕致辭
俄美關係還有一個原則性問題,即它將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兩國是平等的關係還是從屬的關係。美國即是霸權,也就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它能否降尊紆貴,對俄羅斯以平等夥伴待之還需驗證。儘管特朗普政府對俄羅斯的態度比拜登時期有很大改變,使俄羅斯有了平等對話之感,但制裁的大棒仍高高懸在俄羅斯頭頂,這還不是真正的平等。而不論是美國的霸權體系、還是從屬性的國際地位又是俄羅斯所不能接受的。俄羅斯外交的核心概念是主權,這是它外交政策的基石,特別是俄烏衝突爆發之後,俄羅斯把主權放到至高無上的位置,受到特別強調。從主權出發,俄羅斯堅持獨立自主的地位,不屈從於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因此它不可能在特朗普的霸權體系裏尋找自己的位置。
俄美在地區問題上的關係比較複雜,它是兩個利益體系,有相容的利益,但比較少,合作機會也少,相異的利益多,因此發生衝突的可能也多,特別是在中東、西亞、東北亞地區。這仍將是俄美關係中的經常性矛盾,只是有時會和緩,有時會尖鋭。

美俄高官2025年2月18日在沙特首都會談,商討推動結束俄烏戰事,魯比奧、拉夫羅夫各率領美、俄代表團會談
從更長遠一些的視角看,假如説,特朗普的對俄友善政策能夠跨越各種障礙,頂住壓力,保持到他的任期結束,那俄美關係是否會突破大起大落的宿命還得看特朗普之後的政府及其政策,畢竟特朗普的對俄政策有較強的個人色彩,未來白宮的新主人能否會繼承下去現在不得而知。
特朗普外交使得西方內部大亂,造成了西方集團自形成以來最大的內部危機,它的前景不明。美歐的分裂或是越來越深,無可挽回,但也可能跌落到一定程度後再在新的基礎上進行彌合,這種可能性也許更大,當然舊日也不會再來。歐洲或是由此加速衰落,一體化走向鬆散,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逐漸邊緣化;但危機也可能給歐洲帶來強有力的刺激和動力,迫使它獨立自主,更加凝聚團結,謀劃新的發展格局。
北約受到的衝擊更加嚴重,在北約的核心力量美國準備減少對北約的責任、甚至威脅退出的情況下,北約的前景被蒙上了陰影。它成立之初有三大目標,即“留住美國、壓住德國、擋住俄國”,德國早已不是北約壓制的對象,現在美國又要遠離,三大目標只剩其一,即“擋住俄國”。
這將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在俄烏和平協議達成之後,隨着北約與俄羅斯關係的正常化,雙方有可能將探討形成新的歐洲安全框架,俄羅斯對歐洲安全威脅的嚴重性會逐漸減低,這將使北約的發展失去動力;另一方面,北約為了存在下去,也為了保持凝聚力,它需要不斷強化俄羅斯的安全威脅,持續地把俄羅斯作為歐洲的敵人,使雙邊關係始終保持一定的緊張度。從這一點説,北約本身又成為危險的刺激源。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1日,美國已就烏克蘭問題提出一項聯合國決議草案 央視新聞
俄美關係面臨着嶄新的形勢,踏上了一條沒走過的新路徑,這個過程能走多遠還不能確定,並且現在也不能斷定它一定是不可逆的。出於不同的原因,這個過程仍有回頭的可能,或是由於俄美髮生衝突,或是因為特朗普政策調整,或是特朗普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動搖或改變。但畢竟這個過程已經發生,而且正在快速發展,現在應面對的是這一現實,以此為出發點,而不是着眼於未來可能發生的逆轉。
總體而言,現在的形勢對俄美關係有利。特朗普是造成這一形勢的關鍵因素,所有的變化都與他有關。在冷戰之後的俄美關係中,從未出現過北約東擴、安全威脅、意識形態這三大矛盾同時緩解的情況,與此同時,在對多極化等重大問題上的認知上也出現鬆動。俄美開始恢復在一些傳統領域的合作,如削減戰略核武器、防擴散、反恐等,在原來被認為是競爭和衝突的一些領域,如北極、能源開發、天然氣管道等,兩國也開始探討合作的可能,並且合作的領域會繼續擴大。
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主要矛盾在俄美關係中都分量不重,不會成為尖鋭矛盾。特朗普特別關注貿易赤字,他認為美國的貿易伙伴都佔了美國的便宜,因此對它們大幅加税,引發與多國的關税戰,導致雙邊關係受損。這個問題在俄美關係中也會發生,但後果不至於太嚴重,因為俄美貿易額太小,2024年僅剩微不足道的35億美元,這對當年美國4.9萬億美元的貿易額來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而對俄羅斯加税對美國經濟意義不大,特朗普可能更多是把加税作為向俄羅斯施壓和懲罰的手段,比如他威脅對俄羅斯石油出口二次加税,但針對的卻是從俄羅斯購買石油的國家,因為俄美直接交易實在太少。
美國特朗普要為美國人創造就業機會,認為他國的製造業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俄羅斯的製造業不強,不是特朗普泄憤的對象。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俄羅斯不是美國的主要競爭者,不對美國技術霸權構成嚴重挑戰。在對美國社會危害嚴重和特朗普十分敏感的芬太尼問題上,俄羅斯也基本沾不上邊。
在俄烏衝突之後,未來俄美矛盾可能將主要表現在軍控、戰略安全、國際秩序、地區問題等領域,這些問題多為宏觀性質,它們對雙邊關係也有重大影響,但主要是對國家關係的整體性影響,相對來説直接刺激性小,不太容易導致兩國之間發生劇烈的直接衝突。
另外,未來歐洲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美國,成為對抗俄羅斯的主要力量,這意味着俄羅斯也會把歐洲看成更大的挑戰。拉夫羅夫説,過去500年來所有的悲劇都與歐洲有關,不管是十字軍、殖民化、還是兩次世界大戰,而美國並沒有煽風點火,這已經有點從歷史觀念上貶歐友美了。這也為國際格局可能的大變化埋下伏筆,從美歐對中俄的格局轉變為美對中、俄對歐的格局,這又將為美俄和中歐關係提供某種變化的空間。

當地時間2025年3月12日報道,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接受了三位美國博主納波利塔諾、約翰遜和瑙法爾一個半小時的採訪 法新社
綜上所述,在新的形勢下,俄美之間的重大碰撞點有實質性減少,發生嚴重衝突的機會降低,出現了多方面的雙邊合作議題;主觀上兩國都有改善關係的意願,尤其重要的是美國更加主動,特朗普的對俄政策雖然不是單一的,但總體上是以與俄羅斯和解合作為主。因此,從理論上説,向前發展將是未來俄美關係的主路徑,或説是它的基本方向。當然,當今的俄美關係如同整個國際政治一樣,其中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太多的偶然性事件發生的可能,太多難以預知的“黑天鵝”,就像這些年國際社會所一再經歷過的。特朗普因素的加入使已經撲朔迷離的國際政治更加變幻難測,因此,預測俄美關係的前景只能是根據已知事實的一種判斷,而不是一種確定。
對於未來俄美關係的發展,可以粗略地分為由低到高的四個層次:恢復接觸、選擇性合作、正常化、戰略伙伴關係。
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俄美恢復接觸不是一個普通的外交行為。在長達3年的時間裏,美歐與俄羅斯的外交聯繫幾乎完全中斷,不僅沒有外交往來,甚至學術、文化、體育往來也幾近於無,這被西方作為與俄羅斯勢不兩立的政治姿態和外交懲罰,偶爾有歐洲政治家訪俄或與俄領導人通話都會引起歐洲內部的激烈抨擊。而美國突然與俄羅斯進行接觸,而且開始就是在最高外交層次,這不能不引起極大震動。這是美國重大的外交轉向,並且帶有深刻的政治含義。在歐洲看來,這是向俄羅斯“投降”和對西方世界的“背叛”。俄美恢復接觸雖然簡單,但對俄美關係來説,它打開了恢復雙邊關係的第一道門,沒有接觸也就談不上其他。可以認為,俄美關係現在正處於恢復接觸的階段。
恢復接觸可以迅速實現,但這不意味着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自然到來。俄美關係積累了太多的沉痾痼疾,特別是俄烏衝突造成的嚴重障礙,使得國家關係正常化無法一蹴而就,它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來化解問題。這個過程或許較短,但也可能很長,在這個期間,也就是在雙邊關係正常化之前,兩國仍可能在某些領域和某些項目上開展合作,這可被稱為“選擇性合作”階段,因為它基本是某些單項的合作,而且是在非正常的國家關係之下。選擇性合作是俄美關係下一階段的可能形式,並且有可能持續較長一段時間。

2015年9月29日,普京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第70屆聯大會議期間會晤 法新社
正常的外交關係對一般國家來説是自然的,但對現階段的俄美關係來説仍是並不容易達到的高目標。正常化的國家關係不僅是指在外交形式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兩國關係的性質上。正常的國家關係可以是熱烈友好的,也可以是平平淡淡的,但不能是歧視和敵對性的。俄美關係之所以不正常,根本癥結在於兩國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就是要消除敵對狀態,它最主要的標誌是兩國結束“代理人戰爭”,美國逐步減少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解除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政策(不一定是全部制裁措施)。在俄美還處於“代理人戰爭”的情況下,在美國對俄保持全面制裁的情況下,兩國關係不能被認為是正常的。在2025年3月18日普京與特朗普的通話中,雙方都表示了恢復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意願,考慮到對俄美關係有利的形勢變化,如果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得以順利推行下去,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有較大可能。
戰略伙伴關係是俄美關係的最高階段,現階段這個目標可以想象,但可望不可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具備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現實環境。俄美曾經的兩次戰略伙伴關係都有特別的政治背景或現實需求,第一次是在冷戰剛剛結束的浪漫思潮影響之下,第二次是在“9.11事件”後恐怖主義崛起為美國最危險敵人的恐懼中,現在俄美既不再有浪漫的幻想,也沒有需要共同對付的巨大危險。
俄美也缺乏共同的重大戰略目標。中俄美關係是現在的一個熱點,出現了所謂尼克松2.0概念,也就是美國重拾尼克松大三角模式,但逆向操作,改為拉俄羅斯站到美國一邊,共同針對中國。在現今的條件下,這個模式已經無法奏效,難以再現。中美蘇大三角模式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因為蘇聯對中美都是最嚴重的安全危險,而且中蘇關係對中國沒有現實利益的牽扯,因而在冷戰的大環境下,中美能夠實現戰略聯合,共同抗衡蘇聯。現今中美俄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中國既不是俄羅斯和美國的共同敵人,而且中國在安全、外交、能源、經濟諸領域對俄羅斯有重大利益,是俄羅斯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戰略伙伴,中俄關系還比俄美關係更好、更密切、更牢固。

當地時間2025年4月7日,美國紐約,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交易大廳內,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照片擺放在桌上 視覺中國
特朗普政府確實準備改變對中俄“雙重遏制”的戰略,轉而尋求聯俄抑中,對此包括特朗普本人都不掩飾。但這一策略成功的機會很小,因為看不到俄羅斯有接受這一模式的充分理由,而不接受的原因有許多。任何理性的思維都會認識到這一點。這不是説俄羅斯不會與美國合作,相反,發展對美關係不能不為俄羅斯所熱望,特別是在當前俄烏衝突僵持不決的形勢下,它可一舉大大改變俄羅斯的處境。但俄羅斯不會願意充當美國遏制中國的工具,並且是以犧牲自身的重大利益為代價,當然,俄羅斯也要承受住特朗普的利益誘惑和極限施壓。
在對中國的戰略問題上,俄美可能有一些契合點的主要是在核軍控問題上,美國主張把中國拉入俄美核裁軍談判,俄羅斯尊重中國的立場,但也不反對美國的想法。事實上,美國也認識到大三角2.0模式難以重現,因此目前它只追求有限的目標,即儘可能使中俄拉開距離,重點是阻擾中俄在軍事和能源領域的合作,最主要的防止俄中結盟,同時拉近俄美的距離,特朗普對此已經説得非常直白,但對與俄羅斯結成針對中國的統一陣線並不抱太大期望。
隨着俄烏衝突開始接近談判階段,雅爾塔模式的概念在學術界也重新浮現,可將其稱之為雅爾塔2.0。雅爾塔模式的核心是二戰之後三大戰勝國分配戰利品,劃分勢力範圍,確定戰後的國際秩序。雅爾塔2.0只是取雅爾塔模式之意,而不是複製其形式,它的實質就是大國政治。但它具體是什麼樣子,現在還無清晰的圖景。
一種想象是把俄美假定為戰略合作的一方,兩國合謀決定烏克蘭和歐洲的未來。顯然,現在已經是不同的時代,俄美兩個大國無法安排歐洲和世界命運,它們也無法瓜分不屬於它們的利益。退一步説,即使置道義於不顧,回到蠻力時代的規則,美俄也沒有這樣的實力。而且,美國並沒表示要與俄羅斯共享特權,或給俄羅斯某種“勢力範圍”。
另一種想象是歐洲和烏克蘭也參與其中,形成俄美歐烏四方機制,它們既沒有戰勝國,也沒有戰敗國,而是針鋒相對的兩方,歐烏與俄陣線分明,但美國的角色並無一定,它也許會與俄形成默契,但更可能是選擇坐在“主席”的位置,操控各方。還有一種想象是中國入場,形成以中俄美為主的國際政治框架。

2025年4月7日,特朗普在與到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共見記者時再次表態説,歐盟對我們很糟糕,指責歐洲國家沒有購買足夠的美國商品 美聯社
俄美的國內政治條件也達不到戰略伙伴關係的程度。客觀地看,特朗普與俄對話與和平努力在國內政界和精英界也有支持者,包括在民主黨內,但這不等於它們會支持俄美戰略伙伴關係,那意味着與俄羅斯結成戰略統一陣線,與歐洲和烏克蘭形成對立,這是它們難以接受的。
而對俄羅斯來説,在與美國有過兩次失敗的教訓後,對再次與美國結為戰略伙伴會比較謹慎,特朗普的政策對俄羅斯是意外之喜,超出了俄羅斯的最好預期,受到俄羅斯的讚揚和鼓勵,但合作伙伴關係是現階段俄羅斯可追求的最現實目標,戰略伙伴關係是以後的事。俄美也許能夠在戰略合作上取得某種程度的推進,但它的可持續性要在特朗普之後才能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