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夢:老師因“威脅”學生遭行拘,揭示了一個日益尖鋭的教育困境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袁夢】
近日,浙江瑞安有一家長向媒體反映,一小學教師毆打自家10歲孩子,並把他抱到三樓窗口威脅要將其扔下。相關事件被報道後,迅速引來輿論關注。

監控視頻截圖
5月18日凌晨,瑞安市教育局發佈情況通報,稱視頻反映的問題屬實,因此“對林某某作出記過處分,給予該校校長誡勉談話。另外,公安部門經立案調查,對林某某作出行政拘留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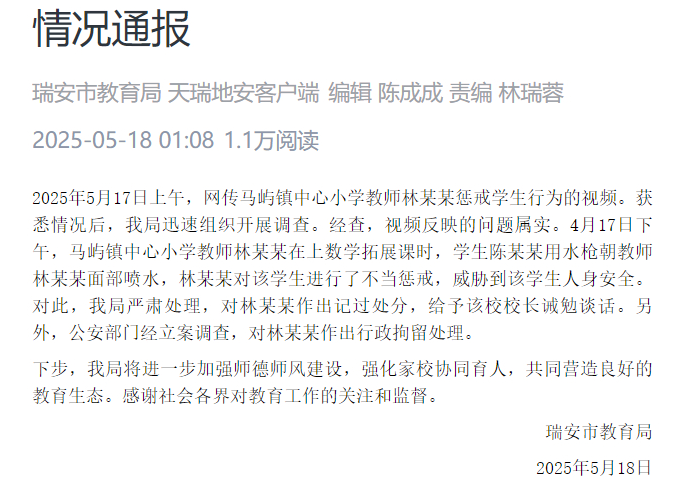
這一情況通報,尤其是最後提及的行拘處理,又引來一波爭議。比如,有網友認為老師行為過激,這處置理所應當;與此同時,有聲音指出當事學生“問題也很大”,對老師處罰過重。

微博上,部分網友在情況通報新聞下的留言
對於違規違紀的學生,如何懲戒才算適當?實際上,隨着家校矛盾日益尖鋭,這一問題已然成為眾多老師乃至學校的日常困擾之一。
一、問題的提出:懲戒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困境
我們在一些縣鄉學校調研時發現,現在教師對於懲戒學生這個問題十分為難:一方面,懲戒教育具有必要性,因為現在學生越來越難管,他們擁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也有更多逃避管理的方式;另一方面,教師們又擔心懲戒責任問題而不敢使用懲戒權,這就導致教師懲戒存在較高的失效風險。最終,教師們似乎也不知道如何教育學生,尤其是那些較多出現越軌行為的學生。
當我們詢問某校的政教主任,問題是否是因為教師懲戒權有限,他回答説:“並不是教師想要懲戒權,而是現在不知道怎麼能有效懲戒來應對學生問題。”
二、社會壓力下的教師懲戒權:懲戒教育何以成為問題
教師懲戒權弱化問題主要產生於部分教師的過度懲戒和家長學生對懲戒教育的負面反應,進而使得越來越多的教師在採取懲戒教育時感到十分擔憂。
第一,部分教師的過度懲戒對學生造成傷害引發社會熱議。
教師懲戒權成為一個問題,直接原因是近些年在網絡中傳播了一些由於教師過度懲戒而對學生造成身體或心理傷害的事件。家長和學生通過網絡傳播想要維護自身權益,爭取損失賠償。
雖然從全國教師實踐看,教師過度懲戒的比例並不多,但在傳統打罵教育理念之下,確實存在一些教師會採用相對粗暴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教育。對此,社會對這種教育方式產生了強烈的批評態度。因而,教師對學生能否懲戒、如何懲戒便成為當前教育的重要問題。
第二,傳統粗暴的懲戒教育不再符合家長和學生的教育需求。
在新世紀以前,傳統粗暴的懲戒教育曾經是社會相對主流的教育理念,大多數家長都會告訴教師“對小孩該打就打,該罵就罵”。打罵越狠,會被認為是教師對學生嚴格教育的表現。
但是隨着社會教育理念的民主化和多元化,一些家長和學生開始認為打罵教育並不能積極引導學生,不利於學生成長,而且有些教師可能將個人情緒發泄到學生身上,並且在出現過度懲戒事件後希望教師和學校給予回應。因此,家長對懲戒教育的態度越來越成為影響教師實施懲戒行為的重要因素。
第三,學校和政府在安全維穩要求下減少對教師懲戒的保護性支持。
在新世紀以前,教師是地方社會少量的知識精英以及對教育事業抱有情懷,具有較高權威和社會地位,全社會都十分尊重教師。為了促進教育發展,學校和政府也一般會積極保護教師。例如,筆者曾在湖北一所中學調研時瞭解到,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名學生曾在課堂上突發疾病去世,家長在瞭解事情原委後並沒有責怪教師和學校,教師也未因此受到處分責罰,不過出於人道主義關懷,學校仍支付了一筆慰問金。
而現在,一旦出現相關問題,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學校和政府難以對教師進行保護性支持。教師的教育壓力從教書育人向自我避責轉變。
三、教師不敢管和學生不好管:懲戒教育的困境
2020年,教育部頒佈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該規則於2021年正式實行。規則的公佈雖然論證了教師懲戒的合法性,且規定了教師懲戒的實施條件和範圍,但是未能徹底解決教師不敢管的懲戒問題。並且在當前社會教育環境日益複雜的背景下,學生越來越難以管教,從而使得懲戒教育的有效性問題存在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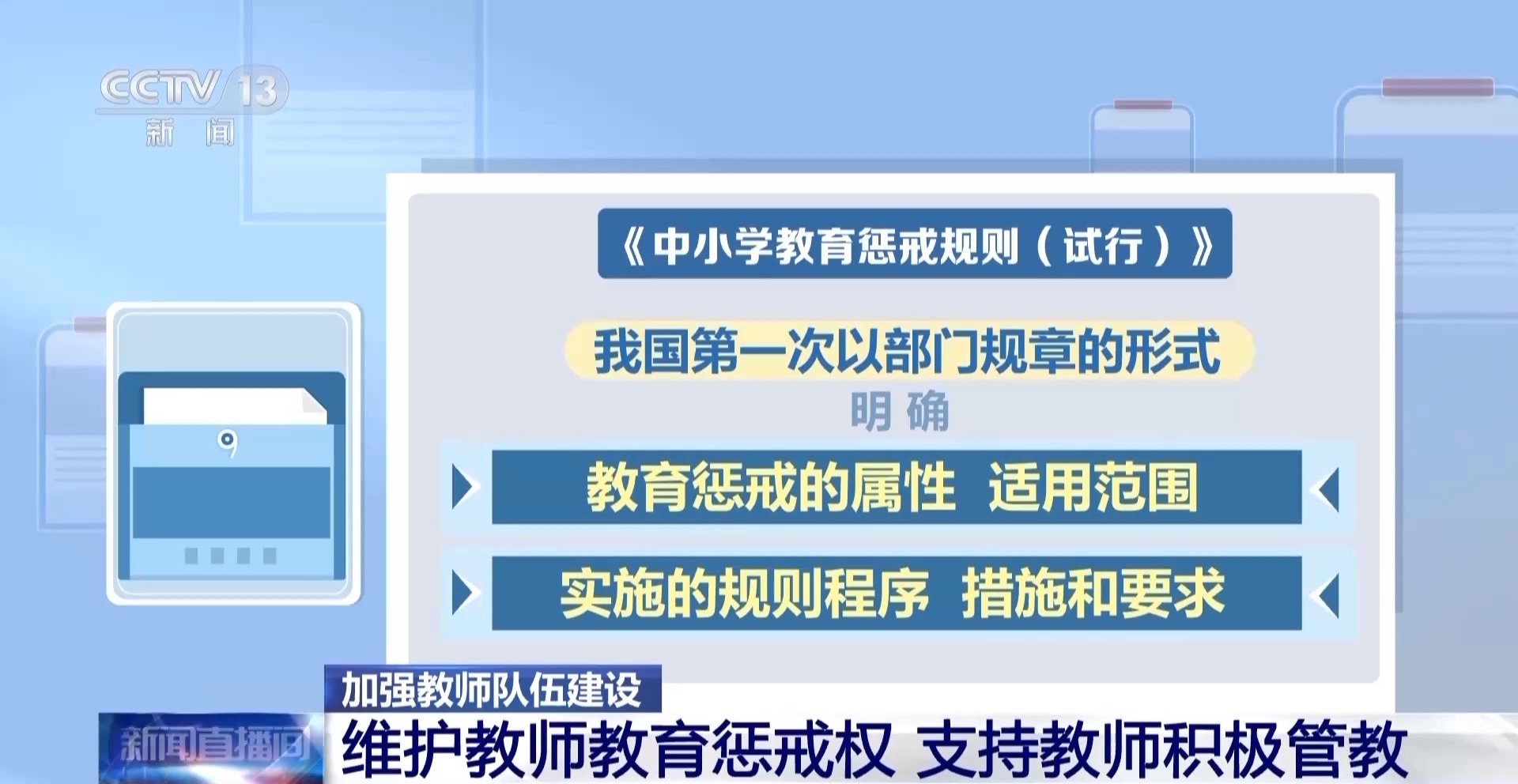
(一)教師不敢管
對於教師來説,考慮到社會輿論壓力和國家制度規定,他們會採用以下策略來避免承擔過度懲戒的責任:
第一,在教育學生時將自己的行為限定在規則範圍之內,比如採取批評教育、道德教育、勞動教育等方式,罰站不超過一節課時間,將尤為調皮的學生座位單獨隔開等方式。
第二,採取措施前得到學生或者家長的授權同意。
例如某縣初中的黃老師説:“我對學生會用戒尺,但用的時候,會問學生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捱打,自己想要挨幾下打、打哪裏,打完之後還會繼續問學生為什麼今天打他。打孩子之前,我也會先跟他家長溝通,問家長是我打,還是他打。如果家長説他自己管,那我就不打了;如果家長説讓我打,那我就打。”
第三,在班級內部制定班規班約,如果學生違反規範,就採取相應懲戒措施。
例如有的班級制定班規班約,如果有學生出現違規違紀行為,可能就會被處罰罰款上交給班級作為班費使用。還有班級實行積分制,每次犯錯都會積分,做了正向貢獻則可以抵消扣分。
第四,在教師在採取既有措施感覺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教師就會將學生交給學校政教處,政教處教師也主要使用批評、道德和勞動教育等方式,但是由於他們經驗豐富,在處理學生問題時有更多“講”的技巧,能讓學生心服口服。
第五,在學校也難以處理學生問題時,教師和學校就會“請家長”。但是“請家長”這個方式並不是對所有學生都有效,因為不少家庭缺乏現代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所以在面對學生問題時他們要麼只會打罵,要麼也管不了小孩。同時,許多縣域學校的學生的父母都在外務工,能被請來的家長一般都是爺爺奶奶,他們更是缺乏精力和能力管教小孩。
正如某中學的政教主任所言,“這些爺爺奶奶到學校之後,你説什麼都是説‘好’,但其實根本管不了小孩,他們唯一的訴求就是讓學校把小孩留在學校,不要讓他回家”。
第六,學校最底線的懲戒措施就是讓小孩回家反思,不過這種措施一般較少採用,而且按照規定不能超過一週。
第七,教師還有一些非正式的懲戒措施,尤其在家長不配合教師和學校處理學生問題的時候,教師一般會採用忽視、漠視的方式。因為對於教師而言,這種情況他們也具有深深無力感和委屈感,只能以此來減少教育成本和負面影響。
可以説,教師和學校以上的這些措施雖然能夠產生一些效用,但是並不能完全根本解決學生問題,他們只能儘可能勸説問題學生和減少問題學生的影響範圍。其原因在於學生和家長對懲罰教育的消極態度。
(二)學生不好管
而對於出現問題的學生來説,他們在知曉相應規則的情況下,也會鑽研出一些方法來應對懲戒,從而使既有的懲戒教育低效或無效。
第一,他們在認知和態度上會破解“打罵是為了自己好”“老師很辛苦,應該要感恩和聽老師的話”等道德教育話語。
比如一些學生會説“老師不辛苦,他們選擇了這份工作就要承受這份辛苦”“老師和家長要我們好好學習是對的,但是我們做不到”。
第二,他們會將違規違紀行為隱匿化。比如在學校裏儘量不違規違紀,但在校園之外打架、抽煙、喝酒,以及可能在網絡等虛擬空間做“開盲盒”“開户”等灰色行為。
第三,他們面對老師的懲罰採取隱性或顯性的抵抗方式。隱性抵抗方面,比如不認真聽教師的課堂,對教師的教育話語“左耳進、右耳出”;顯性抵抗方面,比如公開故意跟教師對着幹,甚至反過來打罵教師。
例如,在某縣初中八年級(8)班上,生物老師佈置了作業,有一個學生沒寫,老師就問為什麼沒寫作業,這個學生在全班直接大聲回答“因為不想寫所以不寫”,全班就鬨堂大笑,老師也沒説什麼,但這不僅讓老師很尷尬,還可能產生示範效應。還有其他老師檢查作業時,把作業扔在學生桌子上,結果這個學生把作業扔得比老師還遠。這個學生平時在家裏跟父母也是對打對罵。
第四,對既有懲罰措施祛魅。對於經常出現違規違紀行為的學生,他們受到較多形式的懲罰教育,而這種懲罰教育的效力會隨着次數和程度的增加而減弱。
例如有學生即使被老師調座調到前排或講桌旁邊,也不會認真學習。還有學生因在校外打架鬧事進入派出所後感覺“在戴上手銬的時候感到害怕,其他時候不害怕,因為進派出所了也就二十分鐘就被放出來了”。

(三)家長難配合
家長的態度也會對懲戒教育的效果產生影響。而在縣域學校,家長一般有三種態度。
第一種是積極支持的態度。這些家長會主動跟教師溝通,交流頻次較高,並且對教師的工作比較信任和支持,這就使得教師更願意對其小孩實施具有矯正和指導意義的懲戒教育。不過,這類家長一般只有幾個。
例如某老師表示,“對教師信任的家長,他放心把小孩交給你,那我對他的小孩確實也會更上心。”
第二種是相對隱身的態度。這些家長較少跟教師交流,通常也缺乏教育小孩的能力,對教師的懲戒教育具有不太穩定的態度,這使得教師會按照規則程序進行懲戒教育,避免因懲戒產生衝突和負面事件。
例如某政教主任指出,“這些家長沒出事的時候都好説話,但出了事什麼話都不好説”。
第三種是消極負面的態度。這些家長缺乏參與小孩教育的積極性,或者反對教師過於嚴格的教育方式,這使得教師在實行懲戒時非常矛盾且無力,因為來自這些家庭的學生往往違規違紀行為較多,教師為維持班級和學校秩序不得不實行懲戒,懲戒無效時又需要聯合家長,但家長往往配合度不高,所以懲戒又陷入無效的惡性循環。
例如某初中班主任舉出一些例子:“有個鄰居評價八年級某班的班主任是個新手,認為她在發現學生將手機帶入學校的情況下沒有幫忙掩蓋錯誤是有問題的”;“有些家長溺愛小孩,班上有個學生父母離異,媽媽暑假從外地回來,為討小孩歡心,就給小孩頭髮染成五顏六色,還會説老師管這麼多幹什麼”;“有些家長覺得老師管學生要叫家長就很煩,在背後還會詆譭老師。他們沒事也刷抖音,看到一些負面消息就會説老師不好,聊八卦的時候,一個人説不好,所有人也就都説不好了”。
四、如何協同:懲戒教育困境的實質與破解方向
綜上所述,當前懲戒教育困境的根本並非單純是教師懲戒權的問題,而是在教師、學校、政府和家長的協同參與下圍繞懲戒什麼、如何懲戒等問題展開的爭議。
教師懲戒權問題的出現是伴隨社會對教師懲戒權責的質疑而出現的,要求教師在實行懲戒時更加規範,避免對學生造成過度懲戒的傷害。但是這種質疑本身又同時引發了教師在懲戒實踐中的擔憂,因為懲戒實踐本身存在邊界模糊性。對此,國家制定了相關制度規則,這一方面保障了教師懲戒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卻又意外帶來了懲戒的有效性問題。
懲戒有效性問題是因為隨着社會發展,個體面臨許多新的、複雜的成長問題,既有的教師懲戒教育難以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並且在社會和家庭的教育意識日益強化的背景下,家長嘗試擁有更多教育話語權。但問題在於,對於縣域社會中多數農民家庭而言,雖然他們開始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但卻沒有實施良好教育的條件和能力,是一種“權利上參與但責任上未參與”的狀態。
這意味着在現代教育體系中,教育越來越需要教師、學校、政府和家長等多方主體的共同參與,而如何讓這種共同參與變得更加有效有序,就成為未來進一步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當前教育責任開始溢出班級和學校,但是政府和家庭還未能有效匹配,比如缺乏有效應對未成年人違法行為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措施、家長無法與學校形成積極合作關係、普遍出現“5+2<0”現象等等。因此,當前社會存在較多的教育空白地帶,這需要通過實踐逐漸在這些地帶達成各參與主體的關係平衡。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