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美國“加速主義”風頭無兩,但真正的危險還沒來到
guancha
在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今天,關於如何有效管控人工智能出現了兩大派別之爭:“技術管控派”和“資本加速派”。這一分歧也折射出了更深層的意識形態對立:前者傾向民主制度下的分權管理,後者則與右翼保守主義結合,支持集權以提升效率。
在本文作者看來,AI發展的核心問題並非技術本身,而是如何平衡平等與自由、權力與資本的關係,否則人類可能面臨比AI失控更嚴峻的內部分裂危機。本文根據作者在“人工智能賦能製造業:國際治理經驗與產業安全”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靖】
2023年11月,美國人工智能Open AI的首席科學家伊爾亞·蘇茨克維把他的合夥人、CEO薩姆·奧特曼開除了。然後奧特曼就領着整個團隊加入微軟,微軟馬上提供了資金,把他們都挖了過去。
第二天,Open AI的員工集體寫信説,這是個重大災難,又把薩姆·奧爾特曼從微軟請回來,重新加入Open AI。不久後,伊爾亞·蘇茨克維就辭職了。這場事故當時在硅谷和華爾街引起了巨大震動,它揭示了對待人工智能管理的根本性態度分歧。
“技術派”伊爾亞·蘇茨克維,認為人工智能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他們越研究越害怕,因為人工智能可以滲透到人類的所有生活,比如軍事、生活、信息、管理、醫療等等。
所以他們認為人工智能要管理好,要防止出錯,那就要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法規和條例,否則一旦失控,結果不可控。蘇茨克維的老師是傑弗裏·辛頓,他是最早發佈神經網絡研究的,也有很多支持者。
薩姆·奧特曼不是一個技術型的老闆,他負責融資,所以他代表的就是一種以盈利為目的資本驅動,他們認為資本驅動是最有效的驅動。既然想要資本驅動,就不太喜歡法治、規則這些東西。所以實際上,這兩個派別鬥爭的本質就是人工智能發展應該是資本驅動還是協調發展?

薩姆·奧特曼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爭鬥是薩姆·奧特曼贏了,但實際上引發了很多人的擔憂,比如跟基辛格一起寫作《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價值》的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就認為應該協調發展,所以拜登政府開始出台一些管理方法,包括安全、可信、可控和可預測。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大選開始了,特朗普贏了大選,立刻把拜登的管理方法全部廢掉。
當時支持薩姆·奧特曼的有一大堆新興資本,代表人物就是萬斯的老闆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也是其中之一。他們認為,管理人工智能更危險。
因為對人工智能的理解有兩個方面,一是對自然、對事實的認知,是唯物的,要靠不斷地做實驗、搞芯片、推算力,這是客觀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對客觀事實的分析、推算,這是唯心的。
他們認為,這兩種理解都有巨大的缺陷。比如,唯物的理解,就像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看大象,大家都認為自己看到了大象,但實際上大家都沒有看到完整的大象。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但對真理有不同的解釋。我們對客觀的認識永遠是有限的,是受到制約的,因為我們沒有上帝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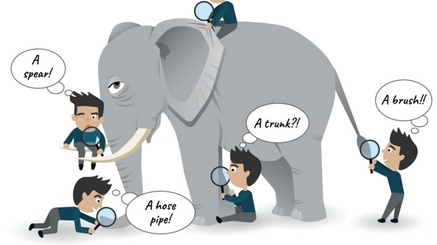
盲人摸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唯心的理解去思考人工智能,這種差距就更大了。人與人之間,集團之間,不同的組織之間,認識的分歧就更大了。在分歧如此巨大且瞭解不全面的情況下,去管理一個已經有發展勢頭,甚至可以自己獨立發展的人工智能,是更危險的。
搞不好,最後管不住,還造成了很大的危險,而這個危險恰好來自人類認識事物的不全面性和巨大的主觀認識,所以他們認為不但不應該管,還應該讓人工智能加速發展。人工智能發展越快,我們對人工智能的認識提高得越快。這樣我們才更有能力、更有水平去追上人工智能。
如果要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像伊爾亞·蘇茨克維這樣的人,就比較傾向於自由民主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因為他要講法律、講規則、講條例、講誠信。而從彼得·蒂爾這些所謂的“加速主義”來看,自然是反對民主主義。
民主制度的一個特點是分權,這造就了大量的官僚體系。本來現在的效率和效果都十分低下了,再搞出一大堆規則管理人工智能,簡直是災難。所以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反對自由的民主主義,贊成右翼保守主義。
這時候又來了一個新的思想家,跟他們一拍即合。這個人就是柯蒂斯·雅文。我仔細看了他的博客,他沒什麼一貫的思想,但有一個堅持了足足30年的認知——民主制度是個糟糕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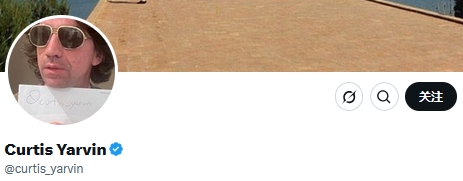
柯蒂斯·雅文
其原因在於,分權不僅會產生巨大的官僚體系,還會使得人類之間的不同意見、不同觀點、不同政策永遠得不到解決,永遠是一種妥協。學政治的都知道,民主制度就是妥協的制度化,但到最後,社會的進步就越來越慢。
因為妥協的代價就是沒有效率、沒有效果,幹不成事情。美國國會搞來搞去,但決策不了,搞到最後永遠達不到想要達到的目的,永遠是進兩步、退一步。
所以,美國要想解決當下政府面對的挑戰,不管是環保、人工智能還是能源等問題,必須提高整個社會運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果(effectively)和效率(efficiency)。
達到這一點就必須集權,當然他們不懂集權,只是從和民主完全相反的角度説,集權是好的。所以把它稱之為君主集權主義,或者反動的保守主義。
因為民主制度的產生就是把軍權打倒,把國王打倒、把皇帝打倒。現在出來一個人,又反過來説,那是好的,要集權。但他説的集權,不是以前那種君主專制,而是認為制度應該把權力集中起來。
所以皮特·蒂爾和埃隆·馬斯克這些人反對對人工智能進行管理,要讓人工智能自由自在地發展。他們認為,我們只要緊緊地跟上就可以了,於是加速主義一拍即合。
當然特朗普也很喜歡這個,所以現在有人説特朗普的理論指導思想就是這“兩個半人”,第一個是柯蒂斯·雅文,第二個是彼得·蒂爾,還有半個是馬斯克。
為什麼馬斯克是半個?因為他沒什麼理論,也沒什麼思想,他就一點,他説我作為一個天才,我作為一個最成功的企業家,我需要自由,蒂爾也想要自由,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雅文他不要自由了,他要權利,他是個極端的權利痴迷者。
所以大家都説,馬斯克這麼成功就是因為他要“加速主義”,他反對官僚、反對制度。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就給了人工智能巨大的鬆動,取消了之前的管制,允許人工智能自己發展。

當地時間1月20日,特朗普撤銷了前總統拜登所簽署的近80項總統行政令,其中包括《關於安全、可靠和可信地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
實際上,這反映了當今美國社會資本的分裂。我們知道華爾街的資本叫傳統資本或金融資本,這些資本是比較贊成民主制的。
人類有兩個中心,一箇中心是權力,一箇中心是財產。人要生活得好,要麼追求權力,要麼追求財產。和任何一個地方離得近,你的日子就會比較好過。但權力和財產放到一起,就會滋生腐敗。
所以正常情況下,權力跟財產應該是相互獨立的,一方面用權力來制約你怎麼發財、怎麼賺錢、怎麼花錢;另一方面,用財產來支撐你的權力。
但問題在於,是權力管資本,還是資本管權力?傳統的模式是,權力管資本,但資本主義革命之後就顛覆了這種模式。資本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資本管權力的勝利。今天所謂的民主制度,就是資本管權力。
資本管權力體現了所謂民主制度的特徵。第一要分權,不分權,就管不住;第二,權力要非人格化,權力跟着椅子走,不跟着屁股走,比如説你在總統辦公室的時候,你有權力;你離開總統辦公室,你就沒權力了。
第三,強調合同的重要性。因為資本之間沒有道德,也不講道德,只講競爭和財產。像特朗普那樣的人在中國選村長也選不上,因為他沒有道德。所以資本強調合同,最高合同就是憲法,最高權力也是非人格化的。
第四,最後一點,定期的換屆制度,過段時間就重新選擇領導人,防止專權。
民主制度就是資本管權力的制度,所以華爾街的老資本喜歡民主制度了,因為這樣可以把權力管住,可以定期地把掌權人換掉,特朗普行,就特朗普;特朗普不行,就換其他人,對不對?畢竟他們還可以道貌岸然地利用法治。
而硅谷的新資本不想這樣做,倒不是説不喜歡民主,而是他們認為民主分權的管理方式,使得他們的自由度受到了限制。為了打破這個限制,他們要求權力,要求自己掌權。這種對權力的嚮往,實際上,是利用權力來維護他們迅速獲得的財富,並捍衞他們在獲得財富過程中獲得的特權。
特朗普上台以後,人工智能確確實實面臨一個大的十字路口。一種是傳統的,包括中國、歐洲都是認為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事情是管控。否則像所有的新技術一樣,如果失控會走向反面。
所以要做到穩定、可靠、可預測。要做到這一點,大家就要合作和溝通。

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之友小組正式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中美之間的人工智能合作是被動合作。中美合作的目的不是幫彼此發展人工智能,而是我要知道你在做什麼;就是中國的人工智能在做什麼,要知會美國,美國的人工智能要做什麼,要知會中國。
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保證中美之間的壟斷,再一個目的是保障中美之間不要“你造你的矛,我造我的盾”,最後你的矛刺不穿我的盾,形成兩敗俱傷的局面。
所以人工智能合作小組也是管理方式,作為一個學者,我認為這是對的。對於特朗普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加速主義”,最正確的態度就是不要管,“加速主義”要幹到哪一步算一步。
其實“加速主義”的動力不是人工智能,而是賺錢、利潤。我認為“加速主義”是必然破產的,因為“加速主義”這些人走到一起,不是因為他們想要什麼,而是因為他們不要什麼;他們都不想要官僚、民主、制度、法律和制裁,都想自由自在地幹自己想幹的事情。
但是如果這個阻礙破除了,你就會發現,在想要什麼這個問題上,他們是有分歧的。柯蒂斯·雅文想要的是權力,而皮特·蒂爾想要發展人工智能,恰恰不想要權力制約自己,所以他們是有內在矛盾的。
馬斯克想要的是完全的自由主義。那什麼能最有效的制約自由主義呢?就是在平等基礎上的權力制約,比如説我在美國上課的時候,經常問我的學生,所謂的民主理念裏有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是平等,一個是自由,平等和自由哪個更重要?在我看來,平等更重要,沒有平等制約的自由,一定是不成立的。如果一個人比我力氣大,比我個子高,他不喜歡我了,如果沒有平等來制約,他一拳就能把我打倒,因為這是他的自由。
所以我們判定一個制度的好與壞,從根本上來説,不是判定權力管資本,還是資本管權力,而是要看這個制度能不能保障這個制度中的每一個成員平等,這是最重要的。
現在看來好像是“加速主義”佔上風,彼得·蒂爾風光無限,萬斯風光無限,馬斯克風光無限,但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危險不是首先來自人工智能的失控,而是來自支持“加速主義”的人本身,他們之間一定會鬧亂子、出矛盾。
現在把他們連到一起的是他們不想要的,等他們真正走到一起了,因為想要的不同也會鬧矛盾。那個時候,如果人工智能和權力、利潤和資本的鬥爭攪在一起,反而是更危險的。
(本文根據作者在《人工智能賦能製造業:國際治理經驗與產業安全》發言整理而成。)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