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豐澤:我在坦桑尼亞建大壩,真正遭罪的是跟兩撥人開會……
guancha
編者按:本碩博均讀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的曹豐澤,一畢業就去非洲參與基建工程的建設。從2021年至2024年,其在東南非以工程師和企業管理人員的身份工作了3年,足跡遍佈坦桑尼亞、贊比亞、南非等10個國家。3年下來,其對於非洲的社會有了豐富的觀察和思考。
其正式工作之後擔任實際職務的第一個項目是在坦桑尼亞的一座水電站。本文節選自其2025年4月出版的《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一個現代化的故事》一書,介紹了他在這個項目上的具體工作,以及與當地工人、管理者打交道的一些經歷和心得。觀察者網轉載上版,供各位讀者參考。
【文/曹豐澤】
一
我在項目上的具體工作,其實並不是什麼“高大上”的內容。恰恰相反,這些工作很可能比坐在北京的機關裏在A4紙上“雕花”還要瑣碎。為了讓讀者更身臨其境地瞭解海外項目上的生活,我不妨簡單講講自己在項目上每天都幹些什麼。
首先是排施工計劃。
簡單地説,一個項目可以分解成100項工作,假如一項接着一項幹,需要100年才能幹完。但是我們如果對工程有更深刻的瞭解,就會發現一些工作可以同時進行,每天同時幹5項工作,20年就能幹完。我們如果進一步優化計劃,對一些工作未雨綢繆,使之不必被銜接於另一項工作之後,而是可以適度提前,那麼我們可以做到每天同時幹10件工作,10年就能幹完了。
有的時候,按照正常的邏輯關係,要完成準備工作可能需要2000個人幹6個月;可是後面的工作卻只需要200個人幹2個月,然後再來1000個人幹2個月。這樣總共要幹10個月,總計14400個人月的工時,但人員總不可能不用時就全部辭退,過兩個月要用時再重新招。設備如果不用,也只能閒置在那裏吃灰。閒置的人力和設備也一樣要消耗成本。
通過優化調整工序,我可以做到始終僱用1440人,一共也用10個月把活兒幹完。雖然總工時沒變,總工期也沒變,但是人力和設備的成本卻大大降低了。
聽起來,這應該是一件早在施工開始之前就做好的事情。然而現實中並不是這樣。我們確實有總工程師早在施工初期就編好施工計劃,而且還有好幾個版本,但是隨着施工的進行,這些計劃早就失去了參考意義。
水電站屬於巨型工程,內部的工序極為複雜,與在城市裏簡單蓋棟樓不是一碼事。隨着施工的進行,工程結構的設計會不斷地發生變更和優化,施工順序也會調整。很多在建造初期沒有考慮到的施工邏輯關係,到了實際建造的階段也會不斷地浮現,給施工造成壓力。還有很多工序在設計的時候沒感覺很複雜,但是施工過程中才發現非常難做。隨着施工逐漸展開,原本粗糙的設計還會逐漸細化,這些細化結構的建造也要被排進計劃裏。
因此,所謂排施工計劃,絕不僅是排一張巨大的表,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嚴格按表施工。我要排剩餘工程計劃,從年度計劃、月計劃到周計劃;要排粗略的總體計劃,還要排詳細的分部分項工程計劃。這是一項看似使用計算機進行,本質上卻和中世紀無甚差異的工作,但是沒有辦法,這項工作極其重要,而且無法避免。

2021年9月大壩上游方向的景色
如今雖然號稱是AI(人工智能)的年代,但現實中的AI只能輕而易舉地代替一名博士去做設計和計算,卻很難代替一名工人去把鋼筋裝好,代替一名清潔工去把廁所刷乾淨。在未來可以預見的若干年內,這些人類社會中最基礎的工作仍很難被機器代替。
我們必須依靠這些計劃去管理現場的工長,給他們制定目標,發放獎金;也必須依靠這些計劃去推斷項目可能完成的時間,從而適當地增加或者減少資源的投入;還需要根據施工計劃中的邏輯關係去調整施工方案,儘可能避免因為一項關鍵工作卡住全局的情況。
要想保證施工計劃合理有效,就必須對現場相當熟悉,經常泡在工地。到了項目後期,我基本上已經可以做到在工地上遛達一圈,就能估算出現有這些工作面多久能夠完成——説實話,這算不得什麼本事,真正的核心技術是如何有效地通過獎罰激勵工人,讓他們比我預想的更快完成,而我並不掌握這門核心技術。
除了排施工計劃外,我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制訂各式各樣的技術方案。
一座大壩上,亂七八糟的“零件”實在太多,這裏一個孔,那裏一個閥門,每一個“零件”的規模都相當於一座建築。這個部分要怎麼建造,電從哪兒接,人從哪兒進,需要搭設哪些輔助設施,要安排多少人力、多少資源,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如何保障安全,都需要提前安排。
説白了,這項工作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但是想要考慮周全並不容易,需要有豐富的“混工地”的經驗。更何況,把技術方案編好本來也不是核心技術,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讓工人老老實實地按照我們的技術方案來施工,而我同樣也不掌握這門核心技術。
除此之外,還有些零七八碎的技術工作,比如做幾項科研課題,寫個工法,申請個專利。相比於讀博期間乾的那些活兒,此類文字工作對我來説實在是駕輕就熟、信手拈來,同時也令我煩得幾乎頭都要炸了。我有時候也要兼顧一些現場管理,每天都要在工地待上半天,檢查哪些工作沒有做好,哪裏的資源安排得不足,哪裏的資源卻在閒置;跟業主的工程師“扯扯皮”、驗驗倉。
坦桑尼亞的陽光極為毒辣,在工地上僅僅是走一圈就會讓人變得很狼狽,哪怕裹得嚴嚴實實也難免被曬得“爆皮”,但這一點恰恰是最沒什麼好抱怨的:既然幹了這行,風吹日曬就是默認必須被接受的,是這份工資的一部分,更何況跟每天待在工地12小時的工人們比,我這點苦真的不算什麼。事實上,每天在工地爬上爬下正是我內心感覺最輕鬆的時光,看着大壩一天天地長高,我覺得自己的人格也在變得完整。

作者曹豐澤
真正遭罪的,是跟業主和上級承包商開會。
簡單地説,我們的上級承包商是一家埃及公司,業主是坦桑尼亞的政府機關,按照時興的叫法,他們分別是我們的“爹”,和我們“爹的爹”。總體而言,業主的領導們人都還不錯,對我們這家中國企業也比較客氣,不跟我們玩兒太多的心眼兒,每次結算工程款時都很爽快,從不拖欠。唯一的問題在於,他們時常會覺得我們這些中國人在憋着壞算計他們。
坦桑尼亞的工程師們學歷並不低,很多都有歐美留學的背景,甚至還有博士,但他們沒有任何工程經驗。我們提出的很多技術方案,其實都是在中國的相似工程上驗證過的、非常成熟的技術,但是他們覺得這些技術和他們從書本上學到的不一樣,覺得可能是這些中國人在騙他們。
他們也説不好中國人具體是怎麼“騙”的,但堅信這裏面肯定有點貓膩,於是就會沒完沒了地卡着我們的方案不給通過,有些結構就一直無法施工。其實,我們的很多方案比他們的認知還要更保守一些,成本還要更高,這顯然不是在偷工減料。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仍然心存懷疑——這些中國人可能是在試圖掩蓋些什麼,要麼是彌補之前的缺陷,要麼是他們所不知的、更大的陰謀。
最離譜的一次是我剛來項目上沒多久的時候,業主的一位工程師指責我們的總工程師,稱大壩有嚴重的裂縫問題,總工程師一頭霧水:裂縫在哪,我怎麼不知道?那位工程師指着我説:“如果你們的大壩沒有裂縫問題,為什麼要請裂縫專家入場?”我和總工程師面面相覷很久,終於反應過來,原來是他看了我的簡歷,發現我讀博士時研究的是混凝土的抗裂,於是把我誤認成裂縫專家了。這實在是抬舉我了。
業主工程師中有一個老頭最為難纏。他並不是業主的一把手,只是個普通的班子成員。但業主的管理採用的是一種“民主制度”,只要有人不同意,方案就不能被通過。然而技術上的事情恐怕還真就不太適用“民主”,它更需要技術精湛的權威的拍板和負責。一個人沒完沒了地不通過,最後影響的是整個項目的進度。
水利工程的施工還得考慮季節因素,有些工作如果今年旱季沒幹,就不得不安排到明年旱季,工期要拖一年,其間耗費的成本不但中方企業承擔不起,恐怕坦桑尼亞這個國家也很難負擔。拖延一年還會增加質量甚至安全上的風險,這些風險又該如何應對?
中方和坦桑尼亞業主之間的分歧,總的來説還算比較好處理,畢竟我們之間隔着一層,也就是埃及的承包商,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另外,業主的團隊以工程師為主,技術人員總歸是比較樸素的,雖然他們挑的刺兒大都令人無語,或許也有謀私利的成分,但絕對不是主流,核心還是純粹對技術的質疑。
從雙方合作的角度講,我們也有義務向他們傳授水電站建設的知識和經驗。這些技術一不涉及國家安全,二不涉及商業機密,我本人作為一名樸素的技術人員,很樂於看到這些技術在全人類範圍內的擴散。我巴不得水電站在非洲遍地開花,讓全非洲的小孩兒都能用上電。
我們和埃及承包商的對抗,才真算是刀光劍影。
雙方之間有直接的合同關係,零和博弈的事情很多,我們多拿1元,他們就要少拿1元,矛盾衝突都很直接。
雙方的經營理念也完全不同,中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即使出海經營,精力也主要放在技術和生產上,認為商務合同只是一個輔助性的職能。結果就是,我們雖然能把活兒幹好,但最後未必能賺到錢。大環境如果比較好,合同壓力不大,還能賺到錢;隨着這幾年競爭激烈起來,競爭對手們在合同上的玩兒法越來越複雜,我們這種悶頭幹活兒的模式可就吃虧了。中東的企業則不然,在他們的觀念中,合同部才是公司運轉的核心,賺錢是公司運轉的唯一目的,而幹活兒則只是服務於賺錢的一個手段。假如不用幹活兒,直接通過玩合同條款就把錢賺了,那簡直再好不過了。
這兩種經營理念碰撞在一起,再加上中方本來就是合同中的乙方,先天弱勢,因此我們時常處於逆風之中。我們項目的合同部滿打滿算只有4個人,而中東企業僅合同部下轄的文檔部就有8個人,半棟樓的人都屬於合同部。即使我們的商務經理能力超羣,有時候也“雙拳難敵四手”,畢竟合同是對方的主業。
除了用一些高技術含量的合同方式外,他們還經常用一些低端的小伎倆,比如偷偷修改會議紀要的措辭和不易被發現的數字,在表格中偷偷隱藏一列對我們不利的內容,凡此種種。其實只要仔細檢查,這些小學生般的伎倆不難被識破,但他們的目的本來也不在於通過這些小伎倆直接矇騙我們。他們知道我們合同部的人少,於是故意用這些無休無止的小伎倆佔用合同部人員的精力,逼我們犯錯,這樣我們就很難在大的變更索賠上分出精力與他們對抗。更何況這些小伎倆實在太多,稍有疏忽,漏掉一兩個,就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不利,就算後期能夠彌補,至少也要佔用很多精力。
儘管經常處於逆風,但我們的合同部還是憑藉着精幹的人員素質打出過一些不錯的“交換比”,這背後也有不少是現場技術和生產人員的功勞。對我們而言,生產經理在工地上搶不到的工期,不能指望商務經理在談判桌上搶到。
相比於埃及公司,我們的技術能力確實更強,工作安排更加合理高效,現場的指揮調度也更順暢。埃及公司的廠房施工陷入停滯時,我們的大壩高度卻在迅速上升,毫無疑問,在業主那裏我們有着更強的話語權。假如到了預定工期,我們負責的部分按期完工了,而由於埃及公司的拖延,整個水電站沒法兒發電,這一大筆損失必然要由他們來承擔。到時候他們再怎麼玩兒合同,想把“鍋”扣到我們頭上,恐怕也是很難行得通的。可見,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技巧至關重要;但當實力相差懸殊時,伎倆就顯得有些蒼白了。
儘管如此,合同管理毫無疑問是包括我們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企業的短板,這個短板如果不趕快補齊,未來隨着國際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們吃的虧只會越來越多。商場如戰場,摳合同,錙銖必較,甚至玩低級伎倆,這些都並不可恥,只是市場競爭中的一種手段。
與埃及公司打交道的時間長了,我們逐漸發現,如果為了維護雙方的關係而故意去做一些讓步,他們反倒會覺得我們軟弱可欺,行為不專業,進而得寸進尺,對我們步步緊逼,最終反而維護不了雙方的關係;反之,我們如果據理力爭,給他們有力的回擊,甚至不惜訴諸仲裁“掀桌子”,他們反而會覺得我們是專業的建築承包商,職業素養高,對我們尊重起來,最終雙方的關係反而會變得更加友好。
可見,商業競爭中有着與人際交往時不完全相同的一套道德體系,做人的道德和禮儀在這裏未必適用。既然決定在國際市場上發展,就要遵守“弱肉強食”的規矩,這才是商界的道德,才是真正能夠贏得尊重的方式。
二
大壩的澆築是分塊進行的。我和技術人員們會按照施工的便利和設計情況綜合考慮,把大壩分成幾十個大大小小的澆築塊,每個分塊必須進行連續澆築。
碾壓混凝土壩的施工有一個很有趣,也很令人討厭的特徵,就是需要一段時間的連續施工,中間不能間斷。一旦間斷,碾壓混凝土的層面就會凝固,這叫作冷縫。如果不經處理直接繼續施工,那麼這一層面以上的混凝土和以下已經澆築過的部分,就會形成兩個結構。要想讓它們合二為一,變成一個結構,那就必須對這個層面進行嚴格的處理。
這一番處理流程極為煩瑣,而且需要上級承包商和業主監理單位的驗倉,合格後才能開始澆築,工期耽誤十天半個月是常事。因此,一旦澆築開始,直到達到本次澆築預計的高度之前,我們都會竭力避免澆築中斷。

雖然就算不澆築,我們也要每天上班,但是澆築帶給人的壓力是完全不同的。在海外項目上,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難以分開,要是沒那麼多活兒,回宿舍“划水”算不得什麼大過。現場的工長和工人們偶爾也會稱病在牀,偷一天懶,可能只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項目管理也不會深究。可是一旦開始澆築,情況就不同了,項目上的所有人都變得異常緊張。
首要問題就是物資供應。
我們規模最大的一次碾壓混凝土澆築,用了將近20萬立方米的混凝土,消耗水泥3萬多噸,火山灰2萬多噸。到澆築結束時,滿滿當當的幾座骨料山都被削平了。要知道,在碾壓混凝土連續澆築的同時,另外幾個區域的常態混凝土施工也不能停止。我們的巨型混凝土拌合站滿負荷開動,都快轉冒煙了。水泥和火山灰這些主要材料固然有一些庫存,但是如果沒有新的材料持續運進,要不了多久庫存就會見底。早在這次大規模混凝土澆築前一個月,項目經理就開始四處去催材料的供應,同時必須確保供應通道始終通暢。那段時間,我們都不敢惹他。
開始澆築的前一天,整個項目都如臨大敵,生怕業主搞出點什麼“幺蛾子”來不讓開始,那樣清理準備工作就白做了,再開始澆築不知道又要準備多久。和承包商、業主監理的工程師們溝通好,確保他們不會突然從中作梗,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有一次開倉澆築前,一切準備工序都已經就緒,就等業主監理的工程師同意,這時一名工程師突然作梗,找了各種各樣的理由不讓我們開始澆築。“縣官不如現管”,他只是業主方最低級別的工程師,但眼下他負責驗倉,就有這個權力,硬生生地拖了兩天時間,最後我們才弄清楚其中原因,他只是想跟我們要一雙鞋……
此外,混凝土的入倉通道也要詳細地安排清楚。
碾壓混凝土的澆築強度非常大,每小時的澆築量高達400立方米。如果澆築速度慢下來,澆築的速度跟不上混凝土凝固的速度,就又會出現上面所説的情況,形成冷縫,導致施工被迫停止。一般來説,單一的混凝土通道很難滿足這麼大的需求,通常需要兩三條通道同時開啓。有一部分混凝土從傳送帶輸送過來,另一部分則要由卡車裝載着拉進大壩倉號內。
這樣一來,有一個問題就變得十分致命:隨着澆築的進行,大壩會逐漸升高,前一天進入大壩的道路,到了第二天就會比大壩低1米。就算隨着澆築不斷把路墊高,一次大壩澆築可能有30多米高,而一條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連續墊高30多米,尤其是在本來就十分險峻的大峽谷中。這時候,我們就需要提前準備多條入倉道路,當大壩上升到一定高度時,舊的低位道路停用,新的高位道路啓用。留給我們銜接工序的時間非常短。
最大的一個澆築塊高達41米,整整施工了59天才澆築完。這59天裏,項目經理、生產經理、各工區負責人、技術員、試驗員,還有現場工長,大家的精神狀態都經歷一個微妙的過程。
剛開始是緊張,生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隨着時間的推移,施工步入正軌,人們也漸漸疲憊,日復一日的高強度工作熬得人們提不起太多精神,坐在車上也很少説話;隨後,這種疲憊逐漸轉化為麻木,打灰儼然成為大家生命的一部分,沒有什麼道理好講,也不再值得緊張或抱怨。到這一倉澆築結束的那天,食堂做了頓大餐,還給大家發了酒,但從每個人的臉上都看不出高興或難過,只覺得平平無奇。大家的情緒,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都已經被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完全榨乾,再也拿不出一分一毫來揮霍。

大壩碾壓混凝土施工
在我們開足馬力,進行大壩碾壓混凝土澆築的時候,施工現場會變得極為壯觀,宛如一次成體系的軍事行動。
混凝土拌合站開足馬力地生產,三四十輛自卸車排成隊列,依次在拌合站接下混凝土,沿着事先安排好的路線將混凝土運送進大壩澆築面。同時,另外一部分混凝土通過傳送帶輸送進大壩,位於傳送帶下方的鏟運機馬上做好準備,將送來的混凝土鏟運到指定的位置。然後,兩三台推土機將這些新到的混凝土攤鋪平整,每層固定在30釐米厚。隨後是七八台碾車,按照工程師提前安排好的路線對新鋪設的混凝土進行碾壓,直到碾壓成一種表面光滑、充滿彈性的狀態,走在上面像是腳踩海綿牀墊。在大壩施工區域的四周,還佈置着四五台水炮,一刻不停地向壩面噴淋着冷水,維持壩面的濕潤和温度適中,大壩兩側矗立的兩台塔吊也在忙碌地向壩內運輸着各種物資。
與此同時,還有幾百名工人在按照分工為大壩的上升提供輔助。他們有的在鋪設冷卻水管,這些冷卻水管會將大壩內部因為混凝土硬化而釋放的熱量帶走,防止大壩開裂;有的在給大壩切縫,這對大壩的受力結構至關重要;有的在提前架設混凝土模板、安裝止水;有的在大壩的上下游附近新鋪設的層面上拋灑水泥漿,提高大壩的抗滲性。
在大壩外面,試驗室在持續監測混凝土的各項性能是否達標;採石場在晝夜不停地爆破採石,並將砂石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拌合站;坦贊鐵路上,一列列貨車也在不斷地向項目上輸送着水泥和火山灰。坦桑尼亞的國家財富忙碌但有條不紊地向這處深山裏匯聚,這些分散的營養被拌合樓與推土機組成的龐大器官轉化成實體的血肉,一點一滴地凝固在峽谷的中央,變成坦桑尼亞這個有機體的一部分,讓這個瘦弱的孩童一天天長高長壯。
我就是這座龐大器官中容易替代卻真實有用的一個忙碌的細胞。
三
我一直認為,能讓這個由來自不同國家的5000多人組成的團隊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最後生產出一座大壩,是一項非常神奇的組織學秘術,而其中的“秘中之秘”就是中國工長與當地工人溝通的這一步。
可想而知,這些坦桑尼亞工人的學歷不可能很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會説英語。因為坦桑尼亞未曾有過很多建設項目,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沒有施工經驗,對工地上的事情一竅不通。而這些中國工長,儘管他們在國內都是擁有豐富經驗的建築工人,但顯然,他們的學歷也不可能很高,別説英語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連普通話都不會説,跟我交流都很成問題。那麼問題來了,每個中國工長要帶至少30個當地工人一起幹活,他們究竟是怎麼交流的?
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專門在工地上盯着一個不大不小的工作面研究多日,逐漸弄懂了他們的工作模式。弄懂了之後,我不禁感慨,生命果然永遠都能自己找到出路,不需要外人去“瞎操心”。
首先,為了解決“每個黑人在中國人眼中看起來都差不多”這個問題,這位中國工長會詢問每個坦桑尼亞工人的名字,然後寫在他們各自的安全帽上。當然,工長不會斯瓦希里語,也不會英語,他在安全帽上寫的是當地工人名字音譯成的漢字配合幾個英文字母,像什麼“K馬路”“硬搭理”。人均頂着一腦袋無意義漢字組成的自己的名字,乍看上去實在有點玄幻。但是人家在一起其樂融融,自己都覺得沒什麼,我自然也沒資格妄加評判。這樣一來,工長就能很容易地分清手下的每個工人,然後為每個工人佈置具體的工作。
其次,肢體語言永遠都是工程師最好的語言。當然,這裏的肢體語言並不是指打罵。工地上師傅打罵徒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工人都很有法治精神,如果捱了打,被打者一定會把打人者告上法庭。這裏説的肢體語言,指的是工長的親自演示。一個工作面的工作雖然複雜,但是如果將其拆解成許多道工序,那麼每一道工序其實都很簡單。
非洲的工人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他們對“本職工作”的理解極其狹窄,絕不會去完成“一項工作”,而只能幹“一道工序”,或者説某個固定的動作,一點兒也不多幹。只要閒下來,他們就聚在一起聊天“扯淡”。因此,同樣一個工作面,在中國只需要10個工人就能幹完,在非洲至少需要30個人。
但這種缺點又恰恰是他們的優勢所在。佈置給他的這道工序,只要他學會了,就一定會按照你的要求原原本本地把它幹好,不管是重複100次還是200次,他都不會趁你不注意而偷工減料。因此,只要你能夠把工作分解好,分解得足夠簡單,然後確保他們都學會了,還真就可以信任他們,你只需要偶爾檢查一下即可。

曹豐澤在非洲一個工地上的照片
最後,我不得不承認,人在一起相處久了,總能找到效率最高的語言交流方式,儘管這種方式可能十分古怪。很多中國工長一句英語都不會説,但是來坦桑尼亞幹了幾年之後,居然“學會了”斯瓦希里語。
這裏的“學會了”並不是指真的融會貫通,他們看不懂任何的斯瓦希里語文字,也不懂得任何斯瓦希里語語法。他們所謂的“斯瓦希里語”,其實就是拿一些斯瓦希里語單詞和簡單的英語單詞,用漢語的語法和連接詞串聯在一起,句尾還要添加漢語的語氣助詞諸如“呀”“哇”“啦”或者表達語氣的髒話。遇到專業性的詞語還會自動切換成漢語(準確地説是河南話)。他們的語言古怪,但極為流利,與他們相配合的當地工人也從來不會提出任何疑問,他們使用的彷彿是一種已經流傳了上千年的、極其成熟的語言。
有一次,一名中國電工讓當地工人看管好配電箱,但是那個工人技術不行,沒有看管好,漏電了。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是有一條狗路過旁邊的水坑被電死了。那名中國電工發現配電箱漏電,跑過來氣急敗壞地責備那個工人:“You see see you, dog 都×× finish了!”

在中國管理者眼中,這些老師傅是最基層的工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甚至沒有正式的“編制”,籤的是勞務派遣合同。但是在當地工人眼中,這些老師傅享有很高的權威。一方面,作為工長,他們是當地工人的直接管理者。機關的人事部門很難直接管理幾千名當地工人,他們的考勤、表現,很大程度上捏在這些中國老師傅手裏。另一方面,這些中國老師傅也是直接向他們傳授技術的人。他們在眼下的工程上學到的技術越多、越複雜,將來到了下一個項目上,他們能勝任的職位就會越高,賺得也就越多。
從理論上講,這樣的權力關係好像很容易導致尋租,但是現實中,據我觀察,施工項目的高流動性和跨文化交流的障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種尋租,大多數中國工長並沒有利用這種權力來謀取私利。除此之外,“高薪養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項目上,一個技術純熟的現場工長,每個月工資、獎金和各項福利加起來,到手收入有人民幣2萬多元,年收入將近30萬元。考慮到食宿、生活費用全包,這30萬元是他可以自由支配的錢。儘管如今國內的建築工人工資也不低,大城市的工人每個月的全勤收入普遍也有1萬多元,但國內的僱用遠沒有海外這麼穩定,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都在找活兒中度過,辛苦一年攢下的錢也並不多。如果從結餘的角度來看,同樣一名工人,在國內和國外的收入差距高達三四倍。因此,大部分中國工長非常珍惜海外的工作機會。
對當地工人而言,這份工作也十分值得珍惜。
在坦桑尼亞一般的建築工地上,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只有40萬先令,約合人民幣1100元,如果按坦桑尼亞最低工資標準則只有30萬先令。同時必須注意到,大多數坦桑尼亞人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正式僱用,相應的也就沒有穩定收入,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對大部分人而言實則是難以企及的上限而非下限。
而在水電站,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全勤的工資是60萬先令。隨着技術的精進,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的工資可以提高到90萬先令。特別優秀的工人,或者平地機、推土機這些高難度施工機械的駕駛員,工資最高可達120萬先令。如果説在項目上一個月可以賺到外面一年賺的錢,這是毫不誇張的。
大多數坦桑尼亞工人並不像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那樣不靠譜兒,比如拿到錢之後就立刻消失不見,揮霍一空之後再回來上班。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會攢錢的,至少不會隨意地透支消費,很多人甚至還有穩定的家庭,會拿着自己的收入去養家。誠然,相比於擁有勤儉文化傳統的中國人,他們沒有那麼勤勞,也沒有那麼熱愛儲蓄,也有更多的娛樂需求。但是,假如非要拿着中國人這套標準去比較,那全世界其他種族恐怕都要被説成“懶漢”,這樣的比較沒有任何意義。按照非洲的標準,坦桑尼亞的工人已經是相當勤懇可靠了。
有一次,一位中國師傅去找項目人事部門,申請給他的坦桑尼亞徒弟漲薪。他是灌漿工區的一名工長,這個工區的主要工作,簡單來説就是將水泥漿按照一定的規律注入大壩以下的地層中,提高大壩與地基之間的聯結程度,並且增強防滲性,防止上游水庫中的水滲到下游來。這份工作非常辛苦,因為他們通常是在幽暗狹小的大壩廊道內進行施工,裏面悶熱潮濕,噪聲巨大。而且因為工作的可調整性強,如果與其他工作面發生工序交叉,通常延緩施工的都是灌漿工。用我們項目經理的話説,“灌漿隊都是老實人,你們不準欺負他們”。這位灌漿工長的徒弟已經在項目上幹了兩年多,中間幾乎沒有回過家,完全按照項目上的高壓作息堅守崗位。兩年多下來,他的技術已經遠超一般的坦桑尼亞灌漿工,可以當半個中國工長用了,再拿和其他坦桑尼亞灌漿工一樣的工資已經不合理了。老師傅説得十分懇切,他對徒弟的關愛完全出自真心。
這些中國老師傅沒有太高的文化水平,也很難對半個地球以外的、與他從小生長環境截然不同的文明做到多麼的開放包容。但是人都有感情,與坦桑尼亞徒弟朝夕相處兩年多,每天在同樣幽暗艱苦的廊道里做着繁重的體力勞動,就算語言不通、文化不同,他們之間也必然會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這處與世隔絕的水電工地對中國人而言是異鄉,對坦桑尼亞人而言又何嘗不是“異鄉”?大家都是跨越千山萬水來吃這份辛苦,所求的同樣都是給自己的家人一個更好的生活。共同的目的必然創造共同的記憶,而共同的記憶也必然帶來共同的情感。極度艱苦中凝成的友誼是無法磨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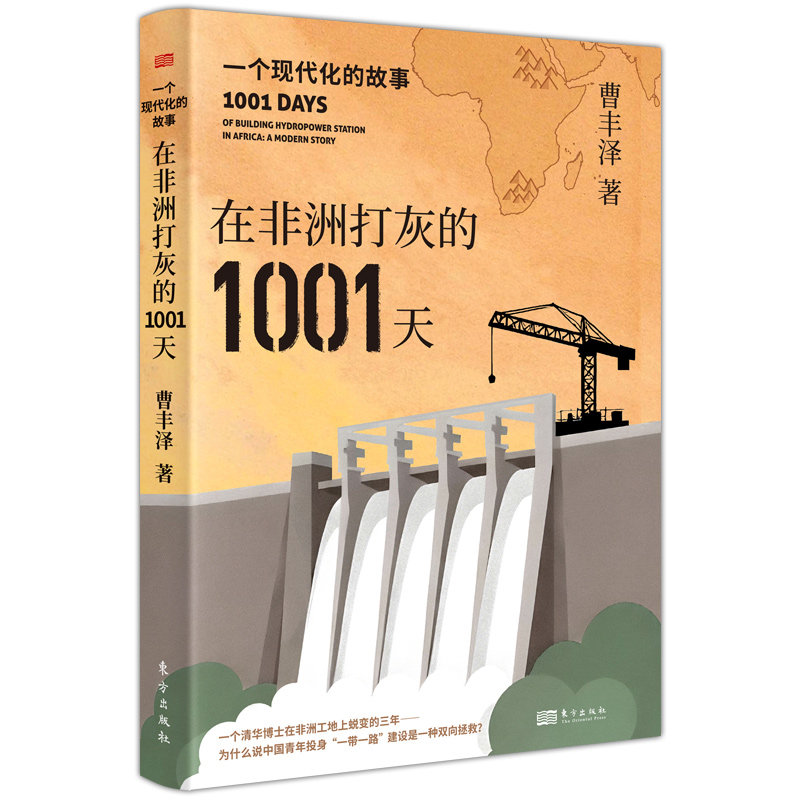
曹豐澤 著,東方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