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節觀影團| 冬曉:她不是詹周氏,她是周惠珍
guancha
【文/觀察者網 冬曉】
由陳可辛導演的電影《醬園弄·懸案》正在影院熱映。80年過去了,曾經那樁攪動舊上海灘的傳奇案件,真相到底如何?當事人又是如何在深淵之中重獲新生?

演員章子怡在電影《醬園弄》中飾演詹周氏
1945年3月21日清晨,家住上海市新昌路醬園弄3樓的張氏出門打水,在下樓梯時發現扶手上零星血跡,驚恐之餘大聲喚來了客堂間算命的王瞎子。
王瞎子本名王燮陽,是醬園弄的二房東,昨日深夜他曾聽到二樓租客詹雲影的房間裏傳出過奇怪的悶響。當時他大聲詢問,卻得到詹雲影的妻子詹周氏的回答,丈夫剛才做了噩夢,所以完全沒放在心上。這下聽到張氏的尖叫,他的心裏突然升起一股不詳的預感。
血水從二樓地板的縫隙裏滲出來,滴落在樓梯的扶手上。王瞎子和妻子見此情景頓感不妙,立刻衝到樓上。叩開房門,目光所及之處皆是未乾的血跡,詹周氏背對他們坐在地上,目光呆滯地説:“詹大塊頭已經給我殺了。”
案件發生67年後,彼時還未成年的醬園弄居民沈子可接受了電視媒體採訪,他回憶起那天經歷,詹周氏被當場擒獲,但裝着碎屍的箱子沒有被一併帶走,還遺留在房間,前來辦案的中國巡捕把案發現場的兩頭攔住,留出6、7米的距離。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鑽到人羣前面看熱鬧,卻被現場的慘狀嚇到,不禁感慨詹周氏怎麼這麼狠,能下得了手把人殺掉。
當時的上海仍處在侵略者的殘暴統治之下,隨着法西斯分子在各條戰線上的節節敗退,日偽政權對上海各界的高壓控制也愈發變本加厲。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和漢奸走狗們最後的瘋狂,因此上海的輿論場大多數時候都寂靜得如一潭死水。醬園弄殺夫案的出現,恰如同一粒投入水面石子,讓無數媒體蜂擁而至,如獲至寶。
畢竟,它無關政治,安全得緊,只是一樁血案,無外乎女人殺了男人,妻子殺了丈夫,宜作茶餘飯後的談資。案發僅一天,各大媒體就紛紛對此案大寫特寫,有叫“醬園弄血案”的,也有叫“箱屍案”的,1945年3月22日刊印的《中華日報》上則用大字寫着“毒婦謀殺親夫——撕屍滅跡分成八段”。
《申報》曾對此案的有過如下報道:案發當日詹雲影從遠東飯點賭光了錢才回家,詹周氏因為生活開支沒有着落,便生出了變賣一部分傢俱換錢擺個小攤經營的念頭。她對晚歸的詹雲影説,家裏的衣櫃台子能賣個5、6萬,這樣她就可以像其他人那樣在弄堂裏做油炸排骨年糕。然而詹雲影對此不以為意,説有這閒錢還不如去賭。被丈夫打擊到絕望的詹周氏在精神恍惚中,對入睡的丈夫對舉起了菜刀。
媒體竭盡全力地渲染着案件恐怖血腥的氛圍,但鑑於案情本身並不複雜,且兇手和兇器都一併抓獲,詹周氏殺夫一案很快就進入了審判的流程。開庭審理當日,法院內外被前來報道的媒體和圍觀的民眾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每個人都想親眼看看這個手持一把菜刀把丈夫剁成十六塊的女人到底是什麼樣貌,什麼來頭。
眾目睽睽之下,詹周氏平靜地對案發當日的一切娓娓道來,公眾也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女人的悲慘遭遇。

歷史上真實的詹周氏照片 紀錄片《檔案》
詹周氏原本姓杜,名春蘭,丹陽人,自幼父母雙亡,親戚將她撫養一段時間後,便在她9歲的時候將她賣給了上海一家當鋪做丫頭。17歲那年,由當鋪主人(姓周)做主許配給了當鋪的活夥計詹雲影。
前半生無依無靠的詹周氏本以為就此可以過上平穩安寧的生活,豈料所託非人,丈夫詹雲影是個吃喝嫖賭樣樣都沾的混蛋。剛結婚兩個月,詹周氏就發現他有外遇,對方是個同樣可憐的年輕姑娘,被詹雲影哄騙了身子還懷了孕。她走投無路之下找上門來,然而詹雲影卻兩手一攤,完全不管,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你奈我何的模樣。反而是詹周氏對那個年輕的女孩兒生出了許多憐憫,照顧她順利生產後,還幫她的孩子找了個領養的人家。
詹雲影在當鋪做朝奉(給典當物估價)的收入並不算豐厚,但足以維持夫妻二人在上海的日常開銷。只是他有嚴重賭癮,但凡口袋裏有點鈔票就要拉着狐朋狗友上牌桌,全然不管家裏還有沒有米可以下鍋。挨餓受凍的詹周氏把能典當的東西都典當了,也吃不上幾頓飽飯,最後只能腆着臉跟左鄰右舍借,可這借來借去又還不上,一來二去的,同住的街坊也就不願意再幫她。
為了能有個基本温飽,詹周氏求爺爺告奶奶託人幫忙在香煙廠(也有報道説是紡紗廠)裏找了個可以餬口的工作,這份工作十分辛勞,天不亮就得去上工,但她對此沒有任何怨言。誰知道丈夫詹雲影知道後對她大發雷霆,罵她是去外面勾引野男人,對她拳打腳踢,把她打得幾日都下不了牀,後來又幹脆將她囚在家裏。這樣一來,詹周氏好不容易謀到的差事也就徹底告吹了。
殺死詹雲影當天,詹周氏又變賣了衣櫃底的幾件衣物換了把菜刀,她原本打算用那把刀斬排骨在街口擺個小吃攤的,不料丈夫知道後又對她施以暴力。詹周氏萬念俱灰之下,到底是把刀砍向了睡夢中的他。
上海警察署出具的驗屍報告詳細記錄了詹雲影屍體被分割的情況,咽喉、兩膀、兩臂、手指、肚腹皆有刀口。由於詹周氏身形瘦小,目測估計體重不超過80斤,而他的丈夫則綽號“大塊頭”,體重近200斤。在身體力量要遠小於對方的情況下,詹周氏一人僅憑一刀就將其斃命,並獨立完成碎屍的全過程,怎麼想都不太可能,因此案發後,負責此案偵辦的人員疑心,詹周氏或許有同謀,且她對那人進行了包庇。
從現代刑偵的角度來看,這種推論並非全無道理,女性由於自然力天生弱於男性,在實施犯罪時,通常要藉助一定工具和外力,這使得女性犯罪有非常顯著的特點,比如藉助藥物進行毒殺,偽造成事故,或其他人聯合。
過往辦案經驗對推定“詹周氏殺夫必有幫兇”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真正在背後作祟的還是當時根深蒂固的“妻為夫綱”的封建思想。既嫁從夫,一個女人不可能擁有殺夫的主觀能動性,倘若她要謀殺自己的丈夫,必然是為了另一個同她苟且的姦夫。
為了逼問姦夫的下落,汪偽政府的辦案人員對詹周氏進行了嚴刑拷打,起初她一直堅稱是自己獨立作案,無他人協助。但肉體凡胎實在熬不過種種酷刑,不得已供出一人“賀大麻皮”,即賀賢惠,聲稱對方就是自己的姦夫。

賀賢惠(賀大麻皮/賀大麻子)照片 記錄片《檔案》
説來也是湊巧,案發後第二天賀賢惠人就不見了蹤影,這讓他身上的嫌疑陡增。據詹周氏交代,她跟賀賢惠是鄰居,以前吃不上飯的時候總找他借錢,他對自己很是同情,性格也算隨和,別人見自己總借錢不還後來也就不借給自己了,可賀賢惠不管手頭多拮据,都勻出一點給自己。時間一長,他倆就發生了關係。
今天的我們無從得知到底是賀賢惠以錢財為引誘脅迫詹周氏發生關係,還是詹周氏為求一條生路主動勾搭的賀賢惠,但賀賢惠前後給予詹周氏的3萬元錢,確實在她飢寒交迫之際讓她有機會活了下去。
除此之外,詹周氏還在審訊中供出另外一人,綽號“小寧波”的何寶華。此人是丈夫的朋友,彼此之間有所走動,慢慢地就好上了。她聲稱殺人一事跟賀賢惠沒關係,是她和何寶華一起謀劃事實的。案發當天,何寶華趁丈夫熟睡溜進她家,先動手在脖頸上砍了一刀,然後自己才又在丈夫的額頭上補了一刀。

何寶華(小寧波)照片 紀錄片《檔案》
以上供述經由媒體傳播,點燃了上海輿論界的熱情,人們恍然大悟感嘆道不出所料,這果然又一個“潘金蓮和西門慶”的故事。然而詹周氏在後續的庭審中當堂翻供,她説自己是受不了刑訊逼供才被屈打成招,賀賢惠沒有幫她殺夫,何寶華也沒有,她之所以構陷何寶華是因為他帶着丈夫到處去賭,自己恨透了他,想着藉此機會對他實施報復。
隨着案情的披露,社會的風向開始起了變化,有一部分人對詹周氏的悲慘遭遇很是同情,認為她罪不至死。得到外界聲援的詹周氏也退去了“一死了之”的消極念頭,積極地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起來。她説自己有精神病,殺夫時處於混亂的狀態中,彷彿腦子裏一直有人對她不停地喊,“你斬好了”,於是她便一段段地斬了丈夫放進箱子(即衣櫃)中。
然而法庭並不認可詹周氏關於自己精神失常的説法,他們指派法醫對詹周氏進行了仔細檢查,得出結論她沒有精神失常,並在5月3日的初審中宣判詹周氏死刑。
《新聞報》當時是這樣報道的:訊據被告供認,殺夫出於泄憤,分屍冀圖滅跡,各情歷歷自白,始終如一,核與偵訊所得,均相吻合,應以殺人重罪處斷。按房幃喋血,情無可原,分屍成塊,殘忍尤烈,應於論處死刑。
案件的審理到此告一段落,隨着諸多信息的披露,社會輿論對詹周氏的態度也分出涇渭分明的兩派。一派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更何況詹周氏這還是“謀殺親夫”,行為極其惡劣,對社會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對此等毒婦懲罰就該仿照古時的極刑,遊街示眾再絞死不説,還得浸豬籠,騎木驢。
而另外一派則認為,詹周氏殺夫情有可原,她原是個老實本分的女人,是被丈夫的惡劣行徑逼迫才舉起了殺人的菜刀。她的悲劇是封建社會造就的,她才是真正的犧牲品,考慮到以上因素,法庭應該對她網開一面,免除死刑。
兩派觀點的支持者圍繞“詹周氏是否該被免除一死”,在媒體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莫過於知名作家蘇青。她曾是和張愛玲齊名的人物,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結婚十年》一書,在裏面道盡瞭如何對婚姻失望以及選擇離婚投身工作的心路歷程。因此,蘇青對於詹周氏在婚姻中所遭受的痛苦,有着一份天然的感同身受。
在1945年6月出版的《雜誌》月刊上,蘇青發表了一篇題為《為殺夫者辯》的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詹周氏殺夫是遭丈夫長年累月虐待所致,又受封建思想荼毒,沒有申訴冤屈的門路。諸多負面情緒沉積難以壓制,求生不得求死無門的她出此下策才揮刀殺了人。而根據辦案人員的走訪調查,痛苦萬分的詹周氏的確曾嘗試過服藥自戕,幸或不幸地被人發現拉去醫院搶救,才撿回了一條命。
“生活悲慘,精神鬱傷,常受了委屈和難堪,經年累月的苦悶使心理變態,從來沒有過離婚的念頭,她也試過自殺,但是沒有死成,所以她只有殺人了。”——蘇青
除此之外,蘇青還辯駁説,詹周氏殺人時應的確處於精神失常的狀態,她質疑法院所請法醫恐怕並無精神疾病診斷的經驗,又舉例自己所知的某位法醫為占強奸案受害人便宜,竟肆意更改鑑定結果,以證明汪偽政府內部主導案件偵辦的官員盡是些胡作非為的蛀蟲。

與張愛玲齊名的知名女作家蘇青,因其與陳公博私交極深,備受爭議
以案件公開的資料和犯罪心理學分析,詹周氏殺夫時處於精神失常狀態的可能性很大。在刑事案件中,作案人碎屍的目的無非兩種,一是掩蓋罪證,藏匿痕跡,把屍體切割成小塊更容易轉移和掩埋,比如杭州許國利殺妻一案中,他就是將屍體分解衝入下水道,再偽造妻子失蹤的假象;二是彰顯力量,過度殺戮通常標誌着情緒宣泄,有些有嚴重心理疾病的作案人甚至會收藏受害者的部分屍塊和器官,當做某種戰利品。
而在詹周氏殺夫一案中,以上兩種情況都不符合,首先詹周氏在完成分屍後沒有任何躲藏掩飾的行為,這導致她在犯罪現場被抓獲;其次,詹周氏將屍體分解後裝入木箱,僅僅是因為前一日她恰好典當了箱內剩餘的衣服以置辦排骨年糕攤,而非像變態連環殺手一樣用於收藏,屬於臨時起意。
綜上所述,詹周氏的犯罪更像是重壓下精神崩潰後的激情犯罪,這在很多遭受長期家暴最後殺死丈夫的女性身上都有體現。王瞎子的證詞裏也提到他叩開房門時詹周氏處於完全的失神狀態,不躲不閃,只是一個勁兒的自語殺了人。在當時媒體刊登的報道中,也有醬園弄的居民提到被捕當天詹周氏還曾唸叨有個聲音叫她殺,結合她初上法庭一心求死不做任何掙扎對此事隻字不提,只是到後面才願意説出的情節以及平日裏為人和善的事實,詹周氏殺夫一案以死刑論處確實量刑過重。
蘇青的文章一經發表就引起了轟動,於是她趁熱打鐵,在7月刊的《雜誌》上開闢了“殺夫案筆談”的專欄,多位作家爭相撰稿請求法院再審時能額外開恩,給詹周氏留一線生機。
然而在上海灘橫行霸道的大漢奸羅君強正沉醉於弄權之中,他以“清官”自居,要求法院不需理會民間的議論,只管判處死刑。羅君強向來認為自己是周佛海的親信,希望靠着抱好這根大腿,做個人上人。可汪偽政府就屁大點兒的地盤,官位就那麼多,有權的官位就更是稀少,羅君強多年都乾的是有名無實的活,比如司法行政部的空頭部長,好不容易熬成汪偽上海市府的秘書長又兼“警税團”的副團長,總得找個機會顯擺一下到手的權力。
就這樣,詹周氏再審被判維持死刑。
正當詹周氏的命運進入倒計時之際,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一切又有了轉機。
時間迫近1945年的8月,汪偽政府的崩潰已是板上釘釘,各部門機關都亂成了一團,一位外國教會的嬤嬤此時出面作證詹周氏已懷有身孕,必須等孩子生下來才能執行死刑。此時汪偽政府的司法機關已徹底癱瘓,沒人再去認真驗證,細究這證詞是否可靠,只是草草將詹周氏收監,當做她確實是個孕婦處理。
這一拖就拖到了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宣佈投降,上海光復,蔣介石高興之餘大赦天下,詹周氏從死刑改判無期,繼而又從無期改判15年有期徒刑。
又是幾年過去,上海喜迎解放。1951年,已經在提籃橋監獄服刑7年的詹周氏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准許她取保候審。可她在上海舉目無親,無處可去,政府便為她安排到了鹽城的大豐農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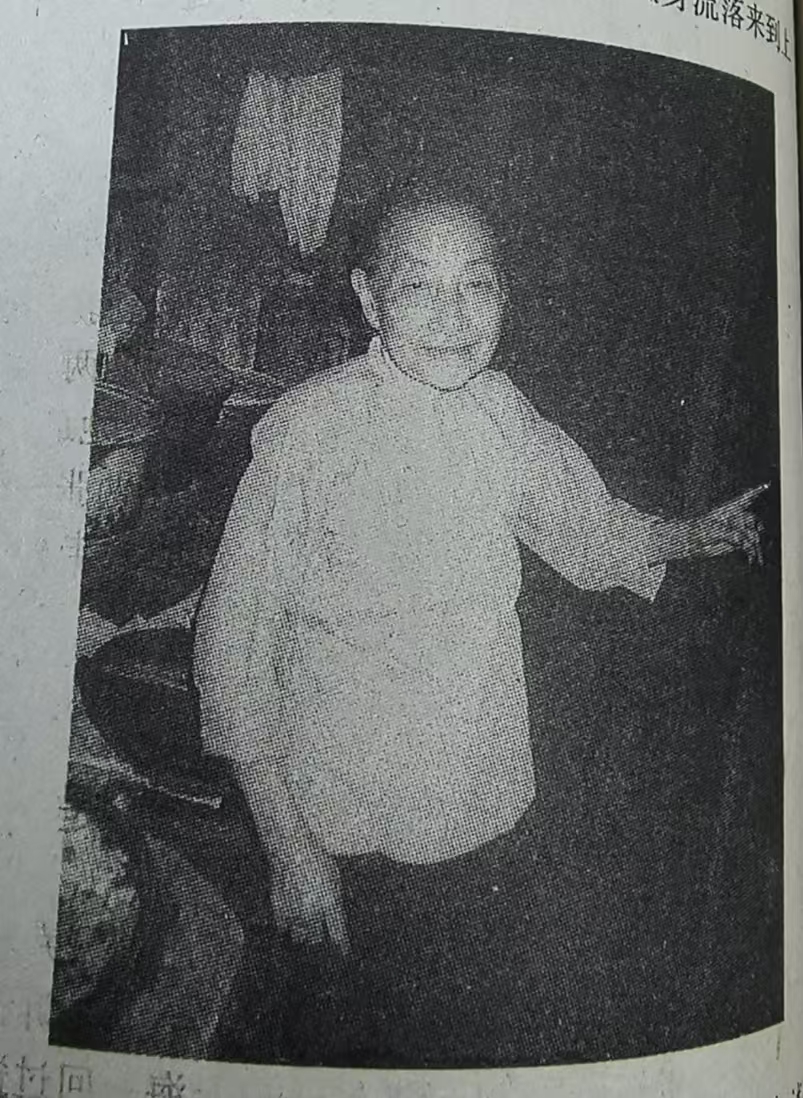
1990年7月刊《上海灘》雜誌上詹周氏的近照 作者供圖
自此,周惠珍過上了平靜安寧的生活。後經人介紹,1959年她在大豐農場結識了炊事員嚴少華,兩人結為夫妻,後半輩子相濡以沫。
嚴少華本是四川人,孤身流落上海,被有關部門收容送到大豐農場。結婚時,嚴少華44歲,周惠珍46歲,由於年齡已高,外加戰亂歲月中身體受損,已經不適合生育。他們都很喜歡小孩,因此認了很多鄰居家的孩子當乾兒子、乾女兒。嚴少華去世後,還經常會有乾兒子、乾女兒上門來看望乾媽周惠珍。
1990年,《上海灘》雜誌編輯徐平對已經改名為周惠珍的她進行了採訪,她説:“領導一直蠻照顧我的,我田裏做了沒幾天,就把我調到託兒所,一直做到1983年退休。”
周惠珍對自己後半生的生活非常滿意,她的房間裏擺滿了靠自己勞動換來各種物品:五斗櫃的煤油燈旁,放着一台12英寸的黑白電視,而在放置煤油爐的桌子上,還有一隻電飯煲。她驕傲地對來訪的編輯説:“除了這房子,屋裏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私人買的,蠻好,現在每個月有退休工資100元出頭。”
在《上海灘》那篇彌足珍貴的採訪裏,編輯徐平還記錄下了這樣一個樸素的細節:“周惠珍已經走過了75年,這些年,她最看重的,恐怕是牀頭櫃上,玻璃板下,她和嚴少華兩張一模一樣的結婚照,還有一張印有紅色大印的大豐縣選民證……”
是啊,歷史的陰影處,免去詹周氏一死的或許是文人的筆桿、教會的援手、亦或是市民的同情、歷史的偶然,但真正予她生路的是新生的人民政府。
不再作為詹雲影的妻子而存在,是勞動者周惠珍,也是選民周惠珍。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