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為什麼毛澤東率領的紅軍不可征服?斯諾的觀察説明了一切
guancha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驅動歷史轉變的車輪
二十三、斯諾對紅軍為什麼不可征服的認知
這一節,主要講斯諾對紅軍為什麼不可征服的觀察和認識。
1936年6月,毛主席東征山西返回陝北後,接待了一位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這次接待的作用非同尋常。如果説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還有中國工農紅軍,此前主要在國際共運圈子裏享有盛譽,此後卻一下子突破了國內外反動派的封鎖,在國內更大範圍、西方國家和海外華人華僑中也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這次結成的友情,甚至一直延續到那一代人的晚年。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
斯諾是第一個進入紅色區域採訪的西方記者。他到上海找宋慶齡,通過秘密渠道聯繫中共中央,在我地下黨人員的幫助下,衝破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從北京出發到西安,冒着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革命根據地。
他為什麼要冒這個險?因為心中有若干不得其解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只是他,蘇區以外包括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想知道。
1936年6月到10月,斯諾到紅都保安,與毛主席等進行了長時間對話,還到寧夏南部的豫旺,那是紅軍西方野戰軍和國民黨軍犬牙交錯的前線陣地,通過與彭德懷等談話和觀察,記錄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斯諾回到北平後,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然後彙編成《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10月在英國出版,到11月就發行了5版,風行各國,轟動世界。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以復社名義在上海翻譯出版了中譯本,改書名《西行漫記》為掩護,不到幾個月,就轟動國內和國外華僑所在地,出版了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此書不但在許多國家是暢銷書,也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通俗讀物,在全世界有億萬讀者。

斯諾拍攝的經典照片《抗戰之聲》,小號手為紅一方面軍營教導員謝立全。這張照片曾出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封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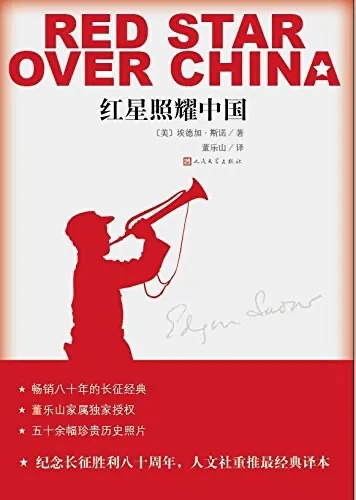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
斯諾在中譯本序文中説:“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語言,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裏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1]
他記下的那些鮮為人知的事,直到今天看了都感到新鮮。我們摘要介紹那些有助於深入理解毛主席軍事思想、紅軍隊伍建設和中國革命戰爭發起原因和目的的內容。如果對更多內容有興趣,可以把書找來看看。
斯諾進入蘇區後,遇到的第一個中央領導人是周恩來。[2]
東征回師後,彭德懷率領紅軍主力西征甘肅寧夏,蘇區東部面臨着國民黨重兵進攻的威脅。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留守東線,指揮東面各軍及地方部隊抗擊進攻敵人。斯諾是從這個方向進入蘇區的,所以在安塞縣白家坪先見到了周恩來。
斯諾説,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長着一臉黑色大鬍子,走上前來用温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囉,你想找什麼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那個鼎鼎大名的紅軍指揮員。斯諾評價説:“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斯諾拍攝的周恩來照片
第二天早晨,斯諾到周恩來所在的附近一個村莊的紅軍司令部。蔣介石懸賞8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在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哨兵。
周對斯諾説:“我接到報告,説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説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3]
這是斯諾所沒有想到的,他原以為即使允許到蘇區,對於拍照、蒐集材料或訪問談話等總會加以一定限制的。
周恩來盤腿坐在小炕桌前,開列了共需92天旅程的各個項目。他説,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但是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當時,斯諾嘴裏沒有作聲,但是心裏對那麼長時間是有保留的。但後來花的時間比建議長得多,離開蘇區時還不無遺憾地説:我捨不得離開,因為我看到的太少了。
斯諾記錄了他親眼見到的紅軍戰士的日常表現,還了解到他們的身世經歷,在革命隊伍中養成的思想觀念和作風,不用説一個外國人感到新鮮,就是今天中國的多數人也感到新鮮。瞭解這支革命隊伍的真實情況,才能更深刻地認識那場偉大革命戰爭。
斯諾吃飯時,兩個侍候他的小紅軍讓他感慨不已。[4]
他説,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口渴得要命。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他們穿着大了好幾號的制服,戴着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其中一個從身邊走過時,斯諾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他。幾分鐘後,他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李克農扯扯斯諾的袖子説:“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裏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裏來幫忙。他們不是傭僕。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斯諾道歉説:謝謝你——同志!那個少年先鋒隊員説:“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這讓斯諾非常感慨。他説: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

保安的小紅軍
紅軍是他從未見過的新型的民主的人民軍隊。在革命隊伍內部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是政治上平等的同志關係。這是毛主席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就明確制定的建軍原則,即便見到像他這樣尊貴的美國記者也不例外,這讓斯諾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斯諾同大約40名通訊部隊的紅軍一起前往中央駐地保安。[5]
只有他、一個外交部(應當是負責對外交往和接待)人員和一個叫李長林的紅軍指揮員有坐騎。那兩個分別騎着是一頭騾子、一頭驢子,只有斯諾跨在僅有的馬上。但這匹馬讓他擔心,為什麼?因為弓背像一彎新月,邁步像駱駝一樣緩慢,瘦腿軟弱發抖,隨時都有可能倒下,嚥下最後一口氣。
他問李長林,你們怎麼能夠騎着這種瘦狗去打仗呢?你們的紅軍騎兵就是這樣的嗎?李長林説:就是因為我們把這種牲口留在後方,我們的騎兵在前線才不可戰勝!要是有一匹馬又壯又能跑,就是毛澤東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線!我們在後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麼事情都是這樣:槍炮、糧食、農服、馬匹、騾子、駱駝、羊——最好的都送去給我們的紅軍戰士!
斯諾又認識了紅軍的一個重要特點:一切為了前線!最好的保障向前線部隊集中,而不是後方人員先滿足自己。
斯諾説,李長林看來是個好人,好布爾什維克,還是説故事的好手,他在李旁邊一起在山溝溝裏爬上爬下,一邊聽着他講一個接着一個的趣聞軼事。他在李長林身上發現,一種後來在這樣奇怪地鐵一般團結的中國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質,有某種東西,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集體的負擔或喜悦,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於他們與別人共自由同患難之中。
斯諾又記下了紅軍的一個內在特點:就是生死與共、榮辱與共的革命集體主義精神。現在不大講這個了,精緻利己主義者成了部分精英的特徵,但那在革命隊伍中行不通,那是革命隊伍的腐蝕劑。
斯諾問李長林結過婚沒有,李慢慢地説:結過婚了,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國民黨殺死了。斯諾説,我開始有一點點懂得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長期地、這樣毫不妥協地、這樣不像中國人地進行戰鬥。
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人民的屠殺政策,讓多少人失去了至親至愛哪!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帶來的是更多革命者戰鬥到底。就如毛主席所説: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斯諾不愧是罕見的世界級記者,在習以為常的紅軍戰士的現實中,發現了不一樣的能解答時代謎題的東西。
與斯諾一起走在路上的其他紅軍戰士,都是十幾歲的少年。有一個綽號叫“老狗”,年方17,實際看上去像14歲,他在福建蘇區參加長征,一路走過來的。同他一起的一個孩子外號叫老表,江西人,16歲。
斯諾問他們喜歡紅軍嗎?他們感到有些奇怪。老狗説:紅軍教我讀書寫字,現在我已經能夠操縱無線電,用步槍瞄準。紅軍幫助窮人。老表説:紅軍對待我們很好,我們從來沒捱過打,這裏大家都一樣。不像在白區裏,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裏大家打仗是為了幫助窮人,救中國。紅軍打地主和白匪,紅軍是抗日的。這樣的軍隊為什麼有人會不喜歡呢?
有一個是四川的,問他為什麼參加紅軍。他説,父母是貧農,只有4畝田,不夠養活他和兩個姊妹。紅軍到村子來時,全體農民都歡迎他們,給他們喝熱茶,做糖給他們吃。紅軍劇團演了戲,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參加窮人的軍隊時,他們很高興。
另一個少年大約19歲,在湖南當過鐵匠學徒,外號叫“鐵老虎”。紅軍到他縣裏時,他只穿了一雙草鞋、一條褲子就趕緊去參軍。為什麼?因為他要同那些不讓學徒吃飽的師傅打仗,同剝削他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窮人。紅軍對人民很好,不搶不打,不像白軍。
斯諾説,我同一個班長談話,他24歲,從1931年起就參加紅軍。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轟炸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燬了。他從田裏回到家裏,發現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別,參加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紅軍游擊隊,1935年在江西犧牲。
幾乎每人一部血淚史,一個社會搞成這個樣子,還有存在的合理性嗎?
斯諾説,雖然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人生悲劇,但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他感嘆,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着對於生存有着一種自信的感覺。

紅軍戰士在跳高
他説,這些戰士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麼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都跟着唱。
在這裏,斯諾又發現了一個公開的秘密,這也是紅軍隊伍的突出特點: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即使面對戰場和犧牲,他們也毫不悲觀。為什麼不呢?無產階級革命是解放全人類的事業,人類歷史一定走向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黑暗和不公平的共產主義,所有勞苦大眾都將得到翻身解放,為那樣的壯麗事業犧牲一切,是無上光榮的歸宿,是值得的,是死得其所,這就是革命樂觀主義的源頭活水。
斯諾還關注他們自覺的紀律。他講了一個例子:在走過山上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裏面的果子,在村子裏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士説説笑笑。
不能不承認,斯諾具有非常敏鋭的觀察判斷能力。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嚴明的羣眾紀律是這支軍隊的基因,是毛主席從在締造紅軍之初就嚴格要求遵守的。這與斯諾見到的反動軍隊完全不同。
斯諾到中共中央駐地保安後見到了更多,他應邀參觀了紅軍大學。[6]
他説,那是一個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這麼一家。
紅大校長林彪把200多名學員集合起來,聽斯諾講“英美對華政策”。斯諾講完後同意解答問題,但很快就發現這是個大錯誤。他説,紅軍大學請他吃的麪條,根本抵償不了遇到的難堪。

女子大學的露天教室
他列出學員提出的一些問題,證明自己回答不了情有可原。如:英國政府對成立親日的冀察委員會態度如何,對日軍進駐華北的態度如何?如果日本與中國開戰,德、意會幫助日本嗎?在英國和美國共產黨都是合法的,為什麼兩個國家都沒有工人政府?既然美國和英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什麼它們在中國駐有軍艦和軍隊?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對蘇聯的看法如何?
從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出,他真小瞧了紅大學員的胸懷和視野,不但斯諾意想不到,應對不及,即使我們今天回望時也超乎想象。
斯諾還被邀請去看紅軍劇社的演出。[7]
他説,那是一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學員、騾夫、婦女、被服工廠和鞋襪工廠的女工、合作社職工、蘇區郵局職工、士兵、木工、拖兒帶女的村民,都向河邊那塊大草地湧過去。演員們就在那裏演出,不遠處甚至還有幾頭羊在啃䓍。
斯諾説,很難想象有比這更加民主的場合了。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

露天劇社
節目有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節目一點也不精緻,道具都很簡單。但演出生機勃勃,幽默風趣,演員和觀眾打成一片,觀眾似乎真正在聽台上的説話。在演出之間,觀眾中不時有人叫喊,請別人即興唱歌,連斯諾也不肯放過,他極度尷尬地唱了一個《盪鞦韆的人》,才沒有讓他再來一個。
演出結束後,斯諾的好奇心未減,第二天採訪了劇社社長危拱之。
危拱之告訴他,一共有30個這樣的巡迴劇社,每個軍都有劇社,幾乎每個縣也都有。農民們老遠來看紅軍的演出,臨近白區邊界時,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他們到邊界的集市上去,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看他們的表演。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如果知道不答應,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他們的演出後,就不願再打紅軍了。
斯諾感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更巧妙的宣傳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是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佔領一個地方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瞭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
斯諾感嘆: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在覺醒的狀態下逐漸站起來,較之南京方面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他們贏得的支持似乎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們通過宣傳和具體行動,使億萬人民對於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概念。
羣眾性文藝演出,是極其生動有效的宣傳教育陣地。
在採訪過程中,因為國民黨軍要在南線發起進攻,斯諾想及早離開。陪同他的吳亮平勸説,蔣介石企圖消滅我們已經有幾十年了,這次他也不會成功,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那可不行!
他説的“真正的紅軍”,就是正在前線的紅軍主力部隊。
斯諾後來説,幸虧接受了他的勸告,否則就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不瞭解紅軍是中國唯一一支從政治上來説是鐵打的軍隊。
八九月份,他到了寧夏豫旺的方面軍駐地,在那裏見到了彭德懷等紅軍將領,也使他更進一步認識了紅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從檔案裏找出來的統計數據,讓斯諾感到極有興趣和意義。[8]

紅軍第一軍團在寧夏
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斯諾發現這完全錯了。紅軍的大部分是青年和工人,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鬥。普通士兵平均年齡19歲,他們大多數是在十五六歲參加紅軍。其中38%的士兵不是來自農業無產階級,而是來自工業無產階級,4%來自小資產階級(商人、知識分子、小地主子弟)。
紅軍包括指揮員在內50%以上的人,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60%到70%的士兵有文化,能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等,比白區普通軍隊的平均數高得多,比西北農民的平均數更高。因為紅軍士兵從入伍第一天起,就開始學習專門為他們編寫的紅色課本。
紅軍沒有正規薪餉。但每個士兵都有權取得一份土地,由他的家屬或當地蘇維埃耕種。如果不是蘇區本地人,則從沒收大地主而來的公田收益中取得一份報酬,公田收益也用於紅軍給養。公田勞動是義務的,但在土地分配中獲得好處的農民,願意合作來保衞改善了他們生活的制度。
紅軍軍官的平均年齡是24歲,這包括從班長到軍團長。儘管這些人很年輕,平均都有8年的作戰經驗。連以上軍官都有文化,雖然他們參加紅軍以前還不能認字寫字。紅軍指揮員1/3以前是國民黨軍人,有許多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生、張學良東北軍的前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馮玉祥國民軍的軍人,以及若干從法國、蘇聯、德國和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斯諾只見過一個美國留學生。
紅軍不叫兵,因為在中國這是很遭反感的字,紅軍稱自己為戰士。
紅軍士兵和軍官大多數未婚,但他們都以尊重態度對待農村婦女和姑娘,農民對紅軍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評價。斯諾説,我沒有聽到過強姦或侮辱農村婦女的事件。
紅軍指揮員傷亡率很高。他們同士兵並肩作戰,團長以下都是這樣。紅軍軍官習慣説:“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説:“弟兄們,向前衝!”在第一、二次反“圍剿”中,紅軍軍官傷亡率往往高達50%,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平均23%左右。
紅軍從最高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得穿得都一樣。但是,營長以上可以騎馬或騾子。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差別很小,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
斯諾説,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迷惑,就是共產黨人是怎樣給他的軍隊提供吃的、穿的和裝備呢?他原以為完全靠劫掠維持生活,但發現這種臆想是錯誤的,因為他看到紅軍每佔領一個地方,就着手建設他們的自給經濟,單單這個事實,就能夠守住一個根據地而不怕敵人的封鎖。
紅軍80%以上的槍械和70%以上的彈藥,是從敵軍那裏奪來的。這讓斯諾難以相信,但他看到紅軍正規軍基本是用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美國的機關槍、步槍、自動步槍、毛瑟槍和山炮裝備起來,這些武器都是大量賣給南京政府的。他看到紅軍使用的唯一俄國制步槍,是從馬鴻逵的軍隊那裏奪來的。
斯諾還説,共產黨沒有高薪的貪污的官員和將軍,而在其他的中國軍隊中,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軍費。在軍隊和蘇區中是厲行節約的。實際上,軍隊給人民造成的唯一負擔,是必須供給他們吃穿。
看到這樣細緻入微的描述,讓我們更加準確形象地認識這是一支什麼樣的革命軍隊,更加深入地理解紅軍獨一無二的內在特徵,理解紅軍的先進性、人民性和為什麼能戰無不勝。
斯諾還記下了大量觀察採訪的細節,特別是對毛主席等黨和紅軍領袖的採訪,留下了對領袖個人經歷特點、中國革命戰爭和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的獨到觀察和理解。下一節,我們繼續介紹其中的精彩片段。
[1]【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7頁。
[2]【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9-43頁。
[3]【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42頁。
[4]【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40-41頁。
[5]【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48-59頁。
[6]【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88-93頁。
[7]【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94-101頁。
[8]【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30-235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