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做好中國研究,需先完成“思想解殖”
guancha
【文/ 温鐵軍】
一、去殖民化知識生產的歷史經驗與新條件下的危與機
最近20多年,我一直在做的一種努力,就是繼承當年去殖民化鬥爭中所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思想家們的遺志。我將他們留下的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建設,變成今天我們在面對全球化挑戰時,需要錘鍊的話語體系。
不僅是我,很多在國內外開展鄉村建設試驗的學者,以及各個方面的社會組織等,大家都在向老一輩中像薩米爾·阿明這樣的思想家請益,不僅是阿明,我們也向同時期世界上能夠提出不同於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體系的學者請益。

薩米爾·阿明 資料圖
例如,我曾經和近幾年在國內有一定影響力的小約翰·柯布(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進行過長時間交流,並且和他的智庫團隊的主要成員進行了多次座談。我還與美國世界體系論的重要理論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美國耶魯大學)、方索瓦·胡塔(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以及寫出《華北小農經濟》的黃宗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寫出《亞當·斯密在北京》的喬瓦尼·阿瑞吉(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進行過面對面長談。我們試圖用老一代有批判性的西方學者具有理性高度的思想,來幫助我們分析在發展中國家調查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認識。
某種程度上,在發展中國家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體系與我們的認識是具有質的差異的,或者叫道的差異。道之不同當然就很難直接進行所謂的對話、交流等互動。所以,客觀上説,我們只要堅持長期以來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客觀存在的“反殖—解殖—去殖”道路,就一定要形成去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因為西方國家是數百年殖民化的始作俑者。
如果從道之不同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所謂的“道不同,不相為謀”應該是常態。由此看,我往往虛心地接受社會各界對我提出的批評,並且認為我們都有道理,只不過我可能更多考慮的是去殖民化,那就要對殖民化的話語體系及其背後的整個文化、制度等做出解構,並開展某種程度的批判,因此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容易被主流接受的提法。可將其歸納為“道不同”的體系之下話語建構的差異。
“三個世界”理論就是對冷戰時期殖民化話語體系的解構,是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在老冷戰如火如荼、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之後的1974年提出的。
因為“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對於冷戰具有比較重要的話語解構的作用,某種程度上,第三世界國家信奉的19世紀以來的老一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普遍認同的國際主義理論體系,逐漸被毛澤東思想的“三個世界”理論所替代。“三個世界”理論把當時冷戰階段被西方認同的、“一個世界兩個體系”框架下的蘇聯東歐聯盟陣營構建的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話語體系做了相當程度的解構,努力地團結了大多數仍然沒有完成解殖運動或正在處於去殖民化鬥爭之中的發展中國家。
因此,“三個世界”理論是對這個世界話語體系重構具有價值,也是對世界地緣政治重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話語建設。所以毛澤東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至今仍然應該是我們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起的“新冷戰”的重要的思想理論武器。於是,當代中國年輕人大量閲讀《毛澤東選集》,形成21世紀的“毛澤東熱”……
新中國成立時,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對中國做了“硬脱鈎”,制裁、封鎖中國。相對於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演變為列強分割、強取豪奪,1950年則是十六國聯軍針對中國發起朝鮮戰爭,最後以停戰告終。
雖然從結果看,朝鮮戰爭不分勝負,但是我們把戰線從鴨綠江邊推回了三八線,所以雙方都不認為最後簽訂的是終止戰爭的協議,只是一個停戰協定。歷史地看,這意味着冷戰階段爆發的美國以聯合國名義參與的熱戰,至今仍然沒有達到決出勝負才徹底停戰的條件。[1]所以,當今天“新冷戰”再度爆發的時候,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整個演變過程對我們來説仍然具有重大的歷史借鑑意義。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在開城板門店舉行。 圖自共產黨員網
1960年,中國與蘇聯也發生了“硬脱鈎”。此後,中國因須支付雙重成本而困難重重:一是償還朝鮮戰爭的軍事援助和戰後結盟時期無須即期支付的援助額,這是顯性成本;二是還得支付改變對蘇依附階段形成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經濟、政治等制度結構的隱性成本。
1950年的“硬脱鈎”和1960年的“硬脱鈎”是美、蘇兩個佔據世界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推出的,並不是中國主張“硬脱鈎”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正處於需要建設,特別是工業化建設的資本極度稀缺的階段,“硬脱鈎”對中國來説損失很大。不論哪一方發起的“硬脱鈎”,中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否則,西方霸權主義就不這麼搞了。
但是,兩個超級大國的“硬脱鈎”也使中國雖然被動卻徹底實現了“去依附”。中國在完成了主權獨立的政治條件下,接連進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的艱苦努力,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上,如何真正實現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文化延續的大國的自主發展道路更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畫句號。同理,我們在教育、醫療、文化、思想、理論、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仍然沒有形成在真正意義上可以支撐我們的獨立話語體系。
當談到我們如何繼承老一輩的遺志時,我們應該明確,即使在今天全球化解體的大潮之中,我們能夠使用的話語仍然是非常羸弱的,我們還沒有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拿出能夠保證我們應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挑戰的完整的話語。所以,今天我們所做的努力,不僅是應對現在的全球化挑戰,也並不只是在經濟上、政治上擺脱自帝國主義問世以來,長期形成的殖民化的話語體系。雖然我們都清楚,去殖、解殖運動在全球化大潮下處於相對弱勢,但並不意味着因此我們就要放棄去殖、解殖賦予我們大國的歷史使命,而是要堅持下去。
因此,我們在知識體系上、在思想理論建構上,尤其要自覺地做到去依附,才能有效地服務於發展中國家去殖、解殖的歷史的經驗過程,尤其是現在全球化解體所表達出來的資本主義已經走向內爆的演變過程。
薩米爾·阿明去世之前,我們深談過多次,他對中國寄予厚望。在分析資本主義進入金融資本階段必然走向內爆的規律的同時,他指出,中國的同志應該討論如何規避金融資本階段資本主義必然走向內爆所形成的全球化解體帶來的巨大代價,如何使我們這些試圖擺脱西方中心主義體系的國家、民族和地區,能夠在全球化向區域化重組的過程中繼續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解決這些問題仍然是我們今天的重要任務,尤其是思想理論建設、話語體系構建的重要任務。
在網絡時代,我們有幸看到各類人羣都有相對低成本介入網絡的條件。所以,相當多的年輕人不滿足於長期以來西方中心主義在教育文化領域一統天下的局面,早就開始了自己艱難的求知探索。
同樣,受益於網絡上的學習條件相對容易獲得且成本較低,我們通過調查研究所獲取的大量資料、針對這些資料所開展的交流討論分析,以及話語建構的多種努力,也都得到了廣泛傳播;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已經開始有了一定的反響。大家願意學習這些對發展中國家大量調查研究所形成的經驗性的討論,並最終演化成的知識積累和話語傳播,這説明年輕人的那種求新知的自覺性還存在着。
我們希望大家多交流,不要太急於把在經驗層次上形成的認知藉助某個現代學術方法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我們還是要儘可能堅持腳踏實地的作風。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我們要善於形成問題意識,只有清晰的問題意識,才能有效地指導我們對信息資料的蒐集、篩選、研究和交流。
二、樹立基於客觀歷史和在地經驗的世界觀
中華文明能夠傳承萬年在於這個文明的傳承不是人為的。世界範圍內的文明的延續都不是簡單人為的,既不是因為人種的先進,也不是因為其他的精神因素,而主要是因為外部的環境差異,亦即形成人類文明的稟賦條件的不同,從而導致人類文明的差異。
所以,文明確有差異但沒有對錯,更不應該區分先進與落後。人類文明多樣性存在自有其合理性,這些合理因素是內在的,比如,很多人認為非洲的部落制度是落後的,他們生存的方式好像很原始,但這種原始生存方式自有其在特定稟賦條件下維持生存的內在合理性。
文明的差異本來就應該是客觀的現象,先進和落後是資本主義時代,西方中心的殖民主義話語強加給人類文明差異的一種主觀判斷,所以得去掉這種價值觀來看。人類文明的發展主要是隨着氣候週期變化而派生的適應性演化,而氣候週期變化又是被氣候帶區分開的。不同文明在不同的氣候帶的覆蓋之下,就會因氣候週期性變化而形成不同的客觀生存條件。除此之外,氣候帶直接影響淺表地理資源,人類社會在早期從原始矇昧進入農業和狩獵文明的時候,是依賴淺表地理資源生存的。
所以,不同區域的氣候週期變化和不同氣候帶覆蓋之下的淺表地理資源的變化,導致了人類文明的差異性。
鄉建研究者的世界觀應該是更為貼近客觀的歷史演進的。從這個角度來説,人類進入被殖民化所決定的意識形態,其實體現的是西方中心主義世界觀,認定西方的演化過程是先進的、有普適性的。如果拋開西方中心主義,可以説無論東西方文明,無論南方北方國家,各種生存方式本身就是被不同文化構建的人類世界,當然具有文化多樣性的合理內因。
從這個角度説,我們通過鄉建推進人和自然之間的緊密結合,可以形成一個完全不再用殖民化以來的世界觀來看待這個世界的新的生態化世界觀和價值觀。
《從農業1.0到農業4.0》一書出版,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基於在地經驗的世界觀。這本書在定名的時候我很猶豫,其實想讓大家瞭解的是中國何以中國,想讓大家瞭解為什麼我們和西方不一樣。那麼要想建立一個清晰的問題意識來面對現在這個紛繁複雜的客觀世界,就需要有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南方世界觀”。誠然,由於大多數年輕人都處在現在這種制式教學體制下,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還是受到制式教育給定的知識板塊的桎梏。由此,這本書突破性明顯。
我們是想從青藏高原成為地球第三極對中國這個文明古國,以及對我們形成中華文明的客觀物質決定作用着手。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有和一般學到的知識不太一致的思想創新。
創新在於強調北緯30度線附近,唯獨中國是一個長期傳承不間斷的文明,客觀條件就是青藏高原隆起成為地球的第三極,把周邊的氣流帶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形成冷凝水,因此帶來降雪、降雨,使青藏高原有了世界最多的冰川和湖泊。由於太平洋板塊撞擊亞歐板塊造成中國地勢呈三級階梯狀逐級下降,水流也順勢而下,在整個中國大陸中東部地區形成了十幾條大江大河及多個大型湖泊。不僅東亞,包括整個東南亞、南亞在內的亞洲大部分地區都得益於青藏高原下泄的水流形成沖積平原。據此看青藏高原是這一帶文明長期延續的客觀條件。
從青藏高原成為地球第三極入手,是一個非常唯物的、從自然資源環境條件出發形成的亞洲原住民世界觀。以自然條件等因素看待世界文明形成的差異性,不至於陷入把某一種理論當成人類唯一的真理的困境,我們就會願意更多地借鑑各方面的思想理論創新。

三、鄉建理論的形成和方法論的發展
2003年7月19日,我們團隊在河北定州市翟城村開展了翟城鄉建試驗,我被推為負責人,同時擔任首任理事長。但這並非我本意,因為初創者並不是我,其實是當年搞鄉村建設工作的幾個中青年骨幹,包括已經去世的劉相波,還有今天仍然活躍在鄉建工作一線的邱建生等。當時,我覺得貿然進行翟城試驗既無經費也不具備任何工作條件,僅憑几個人的熱情恐怕不能持續下去。所以創辦翟城試驗的其實是從事鄉村建設志願者工作的中青年骨幹,我則是愚公移山故事裏那個“智叟”。
但我當時認為既然村幹部已經出資買回了那所廢棄的學校,羣眾也已經認準要做了,那就要儘可能做好。於是,我就儘量發動各方面的力量,動員大家廣泛參與,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勉為其難、竭盡所能將這個21世紀鄉村建設試驗維持下去。當然,這個社會試驗又跟老一輩建立的鄉村建設試驗區有相似之處,也就是在官方主辦的試驗區外主要由民間力量開展的另類試驗。
我們這些在中央政策研究機關任職的改革者從1987年起,以黨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創辦了各地農村改革試驗區。我當時是試驗區辦公室分管立項和監測的工作人員,在試驗方法的運用上很認真。因為各地試驗發現的問題及其應對方式對於政策思路的檢驗和政策調整的思考是比較重要的。
當年開辦的試驗區都在官方體系內,當時我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簡稱“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單位的“中共中央”“國務院”兩塊牌子比較利於協調與“三農”相關的各個方面工作,包括財政、税收、金融、流通、民政等。中央農研室也是當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單位,是對農村工作提出政策引導的主要部門。
當年推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有過爭議,搞農村政策研究的人並不認為應該意識形態化地描述,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作絕對正確的偉大創舉。在討論中有人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解決的問題遠不如它引發的問題更多,因此才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我也曾提出“如果農民分產經營就是市場經濟新體制,那麼小農經濟幾千年來豈不就是最現代化的制度”?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爭論中艱難推進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在地理、氣候、資源、物種、人文社會等各個方面都千差萬別的超大型大陸國家,要想深化改革,就得將改革內容分成幾個大的領域,結合不同地區因地制宜。因此,當社會上期盼中央一號文件變成全國統一部署的標準政策時,在我們自己內部先形成了在各地搞試驗區的討論,我們認為繼續用一箇中央文件指導全國一盤棋、齊步走的改革,不是千差萬別的農村地區真正需要的改革。真正的改革政策應該是分散風險的低成本制度變遷,所以需要分區試驗,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形成不同的政策導向,這才是一個客觀合理的政策過程,才能真正有效地用政策來指導各地不同的發展類型。
雖然客觀上也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但是,中央農研室在1987年暫停發佈中央一號文件,改為以不同地區的改革試驗來指導農村政策研究,形成對各地真正有實際意義的政策體系;即使是同一個類型的政策,也要在不同條件的地區做試驗。
比如,制定土地政策時我們就選了貴州湄潭——山區土地分割細碎,礙難再做調整;江蘇——鄉鎮企業高度發達地區,有足夠的工業產生剩餘來支持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山東——平原地區水利條件完善,適合規模經營;廣東南海——高度發達的大城市郊區,農民的工業收入高於農業收入。由此可以看出,當年一個制度調整的試驗,我們要選至少三個不同地區。
1987年,試驗區辦公室初創時,我負責項目審批的前期調研工作,有大量機會到不同類型的試驗地區做比較研究,每個地區各有經驗,也各有教訓,沒有對錯好壞的一定之規。沒有哪個地方的經驗就一定是全國普適的。
在開展試驗區工作之前,我被派出國學習試驗研究方法,從方法論角度看所謂的後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最為有效的、對社會科學理論建設最有意義的,也是試驗研究,即通過不同條件下的比較試驗,來觀察其效果,通過比對其客觀發生的成本收益,形成科學理論。
回國後,我參與各地試驗設計、開展不同項目的審批立項工作。當年,這套科研體系在中國差異巨大的土地上推進,恰恰使得我們有條件得到大量的資料和數據,我使用的分析方法又是以量化分析為基礎,於是我就在各個試驗區建立抽樣框來採集數據,然後做不同地方數據資料的對比分析研究,再加上還有一個試驗區國際化的情況,需要補充進來。
試驗區建設初期,因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負債情況很嚴重,我們以此為據得到世界銀行的一筆“部門調整貸款”。這是以中國政府名義申報下來的政策性軟貸款,是一筆極低利息和極長還款週期的資金,相當於給了我國一筆長期美元貸款用於短期還債。但,我們也得將世界銀行對中國轉制的要求融入改革試驗,所以就有一定的西方意識形態、西方制度體系對中國改制的介入,這套科研體系由此而成為一個多方面因素構成的有國際影響的試驗體系。
因為長期參與試驗區的技術類工作,所以開始我被任命為項目調研處負責人,等做了幾年試驗,已經有大量的數據、案例,可以做試驗報告的時候,我被改任為監測評估(Monetary and Evaluating Project)處處長,要向世界銀行提供監測報告。世界銀行作為債權人每年組織兩次評估檢查,他們請世界上各個領域的頂尖專家來評估中國的改革試驗,我們就得準備數據、資料應對專家組,這些情況要求我必須認真。
有領導當時對我的評價是“得之於認真,失之於認真”。誠然,我對被試驗數據體系證偽的彙報是認真的,無論最初的政策設計源於何處,我願意修改的表述只不過是把“證偽”改為“不能證明”。誠然,所謂科學試驗,要求的就是一個不斷證偽才能逐漸地接近客觀真實的調整過程。
20世紀80年代全球主流是“新自由主義”,在國內也已經比較意識形態化了,所以導致我在試驗區的認真證偽就跟有關人員意識形態化的政策傾向相悖,形成了一些不太一致的意見,我提出證偽是從數據分析得出來的,但那些試驗項目的主持者並不在意監測數據,要求體現的是被他們認為是“普世價值”的道理。此外,在官方體系內的試驗需要的是證明試驗成功的過程,而我做的是證偽,又是必須報憂的,所以最後是報憂得憂。
總之,參與政策研究試驗區工作這11年是一個非常鍛鍊人、考驗人,也是使人能夠在研究中不斷取得思想進步的過程。得到對客觀世界的接近於真知灼見的認知過程,是非常可貴的經歷,失去多少都不算什麼,因為有了大量的數據分析來證明或者證偽使我在研究上更貼近了客觀真實。從1987年到1998年參與政策試驗的這個研究過程,讓我形成了“‘三農’問題取代農業問題”的政策建議,是我現在的思想認識的基礎研究過程,值得看重。
2001—2003年“三農”工作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三農”工作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7月19日,我們開始了在河北定州市翟城試驗。2004年3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提出,“三農”工作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4月,我們開始了農民骨幹、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三結合的鄉建培訓。
當時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想繼續我們在1998年被中斷的試驗。我1998年離開試驗區的工作崗位,5年之後,當再有條件到村裏開展試驗的時候,就換了一個新的試驗主題:生態農業與環保農村。當時中央剛剛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誠然,那時的我們開展農村生態化試驗困難重重,並未預見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生態文明,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全國上下開始強調生態化。
所以,如果講科學實驗、講方法論,我確有相對比較長時期地堅持腳踏實地地一點一滴去做不同地區、不同條件下的數據採集、資料分類、案例調查,然後做出各種數據分析報告的,堅持這些科學研究方法讓我的認識能力有了一定的改變。

2005年,温鐵軍(中)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與農民學員一起勞動。
我們學術界的很多研究方法是工業化時代產生的,比如結構主義、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這些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跟工業化時代多種標準化部件裝配的結構化的工業生產方式高度相關。到了信息化時代,學者們提出系統論,同時期其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相繼提出的信息系統內的熵增熵減等緊密結合,又從一般意義的系統論發展到所謂的混沌理論。建議大家多瞭解這些作為科學研究方法論基礎的重要思想。
現在,隨着生態化的提出,借鑑了“道家思想”的整全科學的方法論體系,又成為一個新的、對以前的多個不同的方法論的思想體系的挑戰。最近我也在要求科研團隊要考慮更多地去借鑑整全科學。最近福建團隊幾十個人在做採用整全科學方法論指導之下的村莊調查,只是由於學習能力不足,他們難以對調查產生的資料及時做分析,尚未與工作中的問題結合,資料還沒有被很好地開發和利用。
希望大家理解,舊式農村調查應該更新,只有運用這些不斷更新的科研方法,我們才能更接近於客觀真實,要利用下鄉機會去了解不同的資源、地理、氣候環境條件下,經濟、社會、人文等領域的差異,我們才能夠逐漸地形成提煉出相對抽象的客觀真實的,或者叫作思想理論昇華的基本條件。
特別得提醒參與鄉建的年輕人,現在學校要求大家都做計量分析,但是往往很多老師所獲取的數據本身是沒有做檢驗的,尤其是那些被當作學術成果發表的,很多都是隻提及抽樣數據而沒有技術報告,這樣如何做抽樣,如何清理數據保證準確度,如果這些基礎性的操作都搞不清楚,這樣形成的數據分析到底是否可靠很難説。
計量分析毋庸置疑是個很重要的方法,但在做數據採集之前至少得有點前測驗或者預調查,只有對於所研究的客體本身有了一定的問題意識,才能開展研究。其實方法論上講得是很清楚的,如果沒有一定的前測驗或預調查,是不可能形成問題意識的。研究報告開宗明義,是“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oblem”,得有問題意識才能討論它的背景,弄清問題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然後才有概念、才能重新界定,據此形成假説及驗證假説的變量結構、指標體系的設計,以及涉及實際調研方法的討論。
所以,我到高校工作之後,有些遠離實際的老師跟我強調所謂的方法科學,我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與其爭執。無論項目審查還是論文審查,只要是堅持以這套所謂科學的方法為名的人,他們實質上大都是不願意下鄉做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的。對此類項目我只好任其通過,因為這不是哪個學生或教師的問題,而是學術研究體系出了意識形態化的指導思想偏差的問題。在這個體系下,任何試圖堅持真正科學方法的人難免被排斥,這種情況不能怪哪一個人,也不能怪哪一個部門,主要是一段時期以來有些傾向性的問題沒有被提出來討論。
我始終認為所謂學者,就是要“終身當學生的人”。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非常複雜的領域面前,我還是初學者。越是深入做調查研究,特別是越多做國際比較研究,就越發現我們的知識非常有限。
人類的自然科學到現在為止對自然界的認識有限,自然界變化多端的複雜性恐怕大大超過人類現在的認知能力。同理,醫學對於人體的認知能力也有限。若然,則大家應該有一種認知上的不斷進取,並且敢於自以為非。我們遠遠沒有達到更為全面地認識客觀世界的層次,也更談不上深度。
希望大家理解功成不必在我,只要一代一代地做下去,總會不斷地豐富我們自己的認識能力,逐步地改變一百多年來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後面去吃嚼剩下的殘羹冷炙的境遇的。我們還是要從調查研究出發,從國際比較研究出發,來形成客觀的經驗的歸納總結,這樣我們才能逐漸地提升認知。
我們要以實際行動續寫百年鄉建史,這個工作很重要。2005年我在開展現實調查研究和試驗項目的同時,就把曾經從事鄉村建設的幾個年輕的小知識分子召集起來,我們認為需要構建一套歷史觀,要在中國近代化被西方制度和思想全面衝擊下,做一點經驗歸納和思想梳理。
我特別強調,不要再做好人好事般的經驗梳理,而是要看到知識分子與廣大羣眾相結合的實踐中形成的思想演變的歷程。同理,我們對於過去前輩們從事鄉村建設的經驗過程和他們的思想演變過程,尤其要做出儘可能客觀的梳理,不要延續讓後來者讀起來催人淚下的那種故事會。這樣,可以使得幾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思想自覺的努力,以及這些知識分子深入鄉土社會與廣大羣眾結合所做出的一些社會改變,能夠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
四、知識生產的歷史觀與現實困境
我要做鄉建百年曆史研究的計劃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就開始關注如何理解中國在發展的問題上所形成的自主的發展經驗,其中不只涉及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當代史,我希望能夠把鄉建研究的觸角前伸到整個近代史,甚至再往前延伸到古代史,特別是秦漢、隋唐等大一統崩解後的大族遷徙,這樣我們才能夠對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在何處、我們向何處去這樣的基本問題有所解讀。
我當時形成的認識,也和當時的形勢相關。誠然,當時的年輕人沒有像今天的年輕人這樣,為了高考而耗盡全部精力深陷在制式教育的做題體系中,大家沒有條件系統地形成知識基礎。我形成知識的年代,還沒有一考定終身的“制度藩籬”,所以當時大家可以憑興趣讀很多書。我從小養成的習慣是“亂讀書不求甚解”,所以很多人問我最喜歡哪本書,對哪本書的印象最深,我回答不出來。
其實,我從小亂看書一般都記不住書名、作者,也不喜歡抄金句,翻到有意思的書就留心多看兩眼,沒意思的書就速讀瀏覽後扔到一邊。而且,我也沒有非得按照書裏的內容或作者給定的邏輯做思考的興趣,這就造成我從小到大的考試除英語之外成績都不太好,因為我吃不下那些所謂建構邏輯來解釋世界的教科書及其遵循的學科理論,後來的工作中我也總是不太願意照搬成套的學科理論給出解釋,因此,我更不願意照搬根據制式教育的教科書所形成的歷史分析。後來,當我帶着年輕人一起研究近現代史中的鄉建進程的時候,我希望至少應該把幾代人從事鄉村建設100多年的歷史中不同的做法做出歸納,把到底怎麼應對大勢演變搞清楚。
眾所周知,梁漱溟和晏陽初都是鄉村建設中的大家,大家普遍認為他們做事業的時候都是思想比較清晰的,他們的實踐也都是不斷成功的,然而,後人更應該看到這些社會改良事業往往是非常坎坷,且充滿各種艱難險阻的,參與者有時候甚至有生命危險。
晏陽初是“海歸”,他初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近100萬美元[2]的資助用以推進鄉村建設,接受資助也意味着得接受基金會的要求。從其所對應的思想看,晏陽初一開始對中國農民的認識是初步的,他認為中國農民“愚、貧、弱、私”:第一大特點是愚昧;第二大特點是貧困,因為愚昧所以貧困;第三大特點是弱勢,因為貧困所以弱勢;第四大特點是自私,因為弱勢所以更為自私。但,當他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明白要丟掉城裏人的眼鏡,更要丟掉西洋人、東洋人的眼鏡,必須換上一副農民的眼鏡,才能看得清楚農民、農村是怎麼回事,這是他在工作中有了實踐經驗之後才領悟到的。

晏陽初(右)
當他應政府要求去改變農村上層建築的時候,儘管擁有縣級的治權、警權,能夠把縣級的地方武裝力量和警察力量整編成一個體系,甚至能夠讓這個武裝體系下沉到鄉鎮,但他最終沒能改變地方的精英勢力盤根錯節所形成的地方治理結構。晏陽初主持的鄉村建設、鄉村改良,可以説是成功甚少,甚至可以説是在屢戰屢敗的過程中屢敗屢戰。
梁漱溟在山東和豫東一帶開闢的鄉村建設區域跨省、跨縣,面積很大,他能做到大面積擴展,是因為當時中國各個地方其實都處在割據狀態,山東省當局也向梁漱溟賦予了縣級的治權。但河北、山東、河南三省交界處這個“三不管”地帶,可不是個容易待的地方,梁漱溟的做法不同於晏陽初,他要搞至今都被認同的“小政府”,提出“裁局設科”,把上級部門下沉到縣的局改為縣級政府內設機構的“科”,同時推進合署辦公。[3]任何鄉民來縣府,進一間大屋子就能把所有的手續都辦完。
梁漱溟對鄉村治理結構的改動也是相當大的,為了維持這種改動,為了壓得住地方精英羣體和豪紳勢力,他在鄒平建立了民兵自衞系統,鄒平的十三鄉就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廠,共造了1300多支槍,能夠武裝這一方設在基層的治安力量。[4]他的鄉村治理之所以成功,一定程度上是他在“割據”大局中有自己的武裝。同理,被泰戈爾稱頌的、民國鄉建中被立為“村民自治”模範省的山西,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在閻錫山武裝力量維護“割據”條件下推進村治改良。

梁漱溟在山東鄉建院時期與工作人員合影
晏陽初、梁漱溟是鄉村建設兩大重要人物,他們在過去的經驗教訓並沒有被後來者認真總結過,我們今天應如何看待前輩的工作,如何一代接一代繼續我們的努力。如果在這些歷史問題上沒有梳理,只是簡單照搬了別人的研究,那麼我們想要客觀地看待整個鄉村建設的演化過程就會有障礙,得去除這些障礙才有真研究。
今天年輕人逐漸地學有所成,儘管他們在現有的教育體制內很難生存,但他們仍然堅持着,其實我自己在體制內也是個另類,只不過歷經各種各樣的困難總算是堅持住了一定要實踐出真知的初衷。我認為,鄉建人應該堅持的是陳雲同志強調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能做到這樣的人少,但我們還是應該將這種態度堅持下去。
五、告別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應對全球化解體大危機
我有意識地選了幾個不同方面跟大家交流,其實可選擇的領域還有很多。主要是從所謂第三世界解殖運動也是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體系的建構過程來警醒大家打碎殖民主義的革命尚未成功,應該認識到即使獲取獨立主權的南方國家也大多沒有完成思想和文化上的解殖任務。我們在今天所謂全球化解體的大危機面前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出讓民族國家利益的反應也恰恰説明,我們距離完成在思想領域中的解殖任務,尚且有相當大的空間。
當然,客觀上今天出現的輿論亂象,本身也是因為我們長期在這方面的工作欠缺,造成我們今天面對着所謂“新冷戰”幾乎沒有軟實力,更無以抵抗;面對全球化解體過程中必然發生的危機趨勢,對“新冷戰”中必然發生熱戰這種危險的局面,南方國家的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工作準備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因此我們團隊的研究及話語構建工作,需要更多地從客觀實踐、從國別比較研究來昇華我們的認識;當然也包括從歷史的研究中來深化我們的認識。
我們針對的就是全球化解體勢必連帶爆發的大危機,中國身處其中難逃大危機的成本轉嫁。在應對這個挑戰的過程中,只有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不斷理清自己的思想,才能採取相對比較積極的行動來直面這種挑戰。
參考文獻
[1]參見《毛澤東戰爭指導藝術》:“經過激烈的較量,朝鮮戰爭雖然是以交戰雙方用停戰(休戰)宣告結束,但是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卻是以偉大的勝利告終的。”
[2]參見張瑞勝等:《壯志未酬——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農村(1934—1944)》,《中國農史》2017年第3期。
[3]參見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梁漱溟與山東鄉村建設》,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參見察應坤:《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對農村危機的思考與拯救》,博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2020年,第14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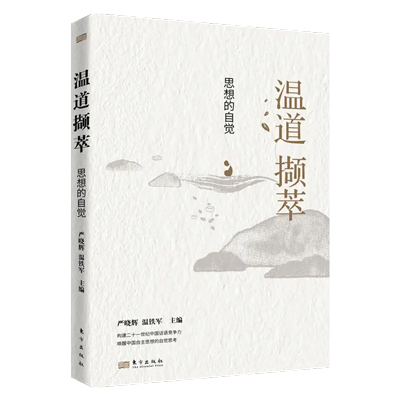
本文節選自《温道擷萃:思想的自覺》,嚴曉輝、温鐵軍主編,東方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