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如何排隊?
guancha
(文/蒂莫西·泰勒)
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是人人都面臨約束,這意味着人們必須權衡、取捨、做出選擇。經濟學的這一核心概念,即權衡、取捨並做出選擇,適用於許多決策行為。因此,這種用經濟學的思想和分析方法解釋和研究社會科學中其他領域的現象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經濟學將其觸角伸向了人類活動的許多方面。近年來,經濟學研究已經擴展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並提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洞見。
我從1986年以來,一直擔任《經濟展望雜誌》的執行主編,這是美國經濟學會出版的一本著名學術期刊。我日常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瑪卡萊斯特學院工作。每次在聚會上與某個人聊天,或是和出租車司機或飛機上的鄰座閒談的時候,當我告訴對方我為一本經濟學學術期刊工作時,他們的反應相當一致。他們會先悄悄翻個白眼,然後微微搖頭,用身體語言表明:“哇,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發現這種反應其實反映了下面幾種疑慮。人們可能會覺得,我肯定是個怪人或學痴,也有可能會隨時開始喋喋不休地談論統計學或某個經濟學定理,所以要對我多加小心。比這更糟的是,我很可能是某種怪異的狂熱分子,比如極端的資本主義者,或者極端的社會主義者。我還一眼就可以看出,無論是哪種情況,對方都認為我很可能馬上就要大放厥詞,而我感興趣的東西極度乏味枯燥,讓人難以忍受。在很多情況下,我幾乎可以看到對面的人在默默祈禱:“拜託,拜託,千萬別讓他談論經濟學。”在另一些情況下,人們則會問我諸如此類的問題:“那麼,你對經濟有什麼看法?”或是問:“你認為股市會怎麼樣?”
好吧,我可能略有一點誇大其辭,但絕不是過分地誇張。經濟學家好像確實和一般人不一樣。我想給你們講三個經濟學家用來自嘲的故事,它們也許能説明上述不同之處到底在哪裏。這些故事當然只是笑話,但它們的確從某種程度上揭示了經濟學家是如何看待世界的。經濟學家認為,世界是一個充滿選擇之所,有時候這些選擇出乎意料,並可能導致人們做出令人不安的反應和互動。
先講第一個故事。這是一個老故事,主角是明尼蘇達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奧斯瓦爾德·布朗利(Oswald Brownlee)和約翰·豪斯(John Hause)。有一天,他們兩人在回家的路上想買些牛排做晚餐,於是就在沿途的一個市場停了下來。當時正值晚餐時間,市場上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他們取了一個號碼,排到了隊尾,比如説,他們排在了第20號。不過,他們想早點回家,於是他們來到排在隊伍前列的一個人面前,提出給那個人一點錢,並和他交換位置。可他們發現,那個人完全無法理解他們這個花錢買靠前位置的提議。
作為經濟學家,他們清楚地知道,這種假裝不理解的態度只是一種討價還價的策略,目的是抬高自己的要價。所以,很自然地,他們心知肚明地提高了出價。這個時候,其他排隊的人開始注意到他們的策略,並紛紛對此表達了意見。雖然很難用一句話總結所有人的反應,但可以公平地説,大家的普遍反應是對他們的提議極為不滿,甚至可以説對他們充滿了敵意。
現在,請努力設想,這兩位站在隊伍中的經濟學家會怎麼做?他們開始向排隊的人解釋,他們只是在嘗試做出一種互惠互利的交換,即他們付出一些錢來換取一些時間。歸根結底,這筆交易不會影響其他人。假設某人之前排在第18號,那麼在交易之後他仍然排在第18號。如果他們成功達成交易,買到了排在第1號的人的位置,那個人會和他們交換位置,排到隊伍後面的第20號,因此這個交易不會對隊伍中的其他人造成任何影響。在任何一個經濟學家看來,這種交易都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在這個故事裏,不管怎麼説,人羣開始情緒激奮。一些人完全看不到這個經濟學提議的合理性。最後,這兩位經濟學家只能灰溜溜地回家,點一份外賣披薩當晚餐。
下面再講第二個故事。大多數人可能都很熟悉下面的場景:你到了機場後發現,航空公司賣出的機票比飛機上的座位多,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航空公司會發布公告稱:“我們的航班超售,如果有哪位乘客願意乘坐下一班飛機,從而獲得一張免費機票或者一張價值300美元的機票優惠券,請與登機口的工作人員聯繫。”他們最終總是能找到一位自願這樣做的乘客,順利解決問題。但這種情況並非從一開始便是如此的。
在大約1978年之前,航空公司如果超售機票,即賣出的機票數量多於航班上的座位數,而作為乘客的你不幸在起飛前才到達登機口,飛機已經坐滿、沒有空位,那麼你會被簡單粗暴地踢到下一班飛機,沒得選擇,也沒有補償。一位名叫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於1968年發表了一篇名為《解決航空公司超售問題的實用方案》的文章。他提出了一個堪稱實用的基本構想,即航空公司應該要求人們寫下自己在什麼條件下願意延遲到下一班航班,然後航空公司可以選擇出價最低的乘客。
文章發表之初,人們普遍認為這只是學院派經濟學家慣幹之事,即提出一個愚蠢而不切實際的提議,既不可能真正實施,更不會真正奏效,而且還聽上去怪里怪氣,並有一點令人不安,甚至就像試圖在雜貨店花錢購買隊伍靠前的位置一樣不可理喻。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當航空公司開始被要求為那些因超售而延誤到下一個航班的乘客提供免費機票時,航空公司和乘客都發現,這種方案實際上行之有效。它不僅有利於乘客,因為他們現在可以選擇是否被踢到下一班飛機,而且對航空公司更有利。
航空公司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放心地超售機票,而不必受到懲罰。他們知道,如果航班真的超員,他們總是能夠找到一個自願讓出座位的人,即使需要為那個人提供補償,但那個人的做法畢竟是出於自願,而不是違背自己意願的被迫行為。事實表明,讓人們可以自願選擇延誤到下一個航班,而不是無奈地被踢到下一個航班,這對包括乘客和航空公司在內的所有各方都更加有利。
下面再講第三個故事。這個故事有時候會被經濟學家歸入高爾夫球場笑話之列。它講的是有一天,三位朋友去打高爾夫。這三位朋友分別是一位牧師、一位社工和一位經濟學家。他們在球場上打球時,排在他們前面的那羣人打得非常非常地慢。一天結束之時,我們這三位打高爾夫球的朋友已經氣得火冒三丈,因為他們一直在沒完沒了地等待。
他們去找高爾夫球場的經理投訴,説:“你看,我們前面的那羣人打得實在太慢了,他們毀了所有其他打球的人的心情。”經理回答説:“哦,我實在很抱歉。我們會確保這種情況不再發生。但你們知道,你們前面打球的人是一羣盲人。他們使用的是那種會發出聲響的球,而他們基本上是靠聽聲音來打球的。很抱歉給你們帶來了不便,未來我們會盡量彌補你們。”
你們可以想象一下這三個朋友會怎麼説。牧師説:“哦,我總是告誡人們要寬容,而現在我發現,我自己對他人也不夠寬容。我對自己實在是太失望了。”社工説:“哦,你們知道,我一直致力於為殘疾人士提供便利,但現在我本人遇到了為他們提供便利的情況,我感覺這一次我似乎背叛了自己真正的職業使命。”
經濟學家靜靜地聽完了整場對話和其他人所説的一切,停頓了一分鐘,然後抬起頭説:“你們為什麼不讓盲人們在晚上打球呢?”當然,我在此必須強調,我並不是想説,盲人只應該被允許在黑夜裏打高爾夫球。我想説的是,高爾夫球場開放一些夜場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如果很多盲人希望在夜間時段打高爾夫球,並且我相信青睞夜場的人可能還要加上一些有怪癖的高爾夫球手,畢竟只要有人在冰山頂上鑿出18個洞,都會吸引一些人去打高爾夫。所以嘛,我覺得對這些人來説,多一個選擇顯然是好事一樁。對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説,這個高爾夫球場笑話生動地説明,跳出固有思維模式,認真觀察某種情況並願意提出一些存在特定邏輯的額外選擇,這是一種幫助我們應對問題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當然,在上面的故事裏,經濟學家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能不夠深思熟慮或稍顯缺乏同情心,所以它才會被當作一個笑話,但經濟學家願意沿着這種思路思考,直到達成目的。我在這裏想討論一個更宏大的主題。經濟學並不僅僅侷限於那些很多人乍一聽到“經濟學”這個詞就會想到的常規話題,比如下季度的GDP是否會增長,失業率是否會下降;也不僅僅是關於國際貿易的話題,比如貿易赤字問題,或是進口石油問題、工作崗位外包問題和如何應對預算赤字的問題;又或是工會、污染、創新、技術、貧困和不平等等問題。經濟學研究的領域遠遠超出了經濟本身。事實上,經濟學絕非僅與經濟相關。
經濟學最常被引用的定義之一來自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在193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他強調,經濟學研究的是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裏做出選擇的不可避免的需要。我們所有人都不可能完全擁有我們想要的一切。以下是羅賓斯在他那篇著名論文中的觀點。羅賓斯寫道:
我們可以支配的時間是有限的……達成目標的物質手段也是有限的。我們已經被逐出了天堂。
我們既沒有永恆的生命,也沒有滿足願望的無窮手段……滿足特定願望的手段稀缺,這是人類行為中幾乎普遍存在的一種狀態。
我喜歡上面引用的羅賓斯關於人類已經被逐出天堂的説法。他真正想要強調的是,在一個不得不進行權衡、取捨的世界裏,人們必須做出選擇。除了做出選擇,我們別無選擇。有時候,經濟學甚至被稱為“選擇的科學”。雖然這種説法有些誇張,讓我忍不住想撇嘴,但公平地説,經濟學的確高度關注選擇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的選擇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無疑,從擁抱選擇這一理念出發理解經濟學,可能會賦予經濟學一些令人驚訝的含義。
經濟學研究的領域相當廣泛。它不只研究你買了什麼、存了什麼、在哪裏工作或政府的經濟政策。它從人類擁有多少時間以及他們選擇如何利用這些時間的角度出發,思考和研究人類的行為。此外,它關注的是人們一生中擁有的時間,而不是僅僅侷限於一個星期或一個月。所以,經濟學所研究的不僅僅是關於工作、購買、儲蓄等人們通常認為經濟學關注的領域,還涵蓋了其他一系列選擇,比如結婚、生孩子、是否違法甚至是實施恐怖行為、是否向慈善機構捐獻,以及是否捐獻腎臟等等。
經濟學的另一重含義是,選擇意味着目的性。你有時會聽到下面的説法,即經濟學家假設每個人都永遠是理性的。這種説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你需要注意它到底意味着什麼。理性並不意味着每個人都知道一切,每個人都可以完美地計算一切,同時每個人都完全不帶任何偏見。理性當然也並不意味着所有人對他們想要選擇的東西都具有或應該具有相同的偏好。它真正的意思是,人們會盡最大努力弄清楚自己想要什麼,而如果條件發生改變,比如他們想要的東西的成本變高或者自己獲得的收益變低,那麼人們通常會調整自己的行為,做出不同的選擇。
如果成本和收益以價格來表示,那這個框架就是適用的。它同時也適用於其他類型的成本和收益之間的比較,比如時間、個人精力或聲譽。這種觀點認為,人們並不總是擁有完整的信息。他們並不總是能夠充分處理信息。他們會犯錯誤。有時候,這可能會帶來人們不希望看到的後果。
經濟學家説人是理性的,並不是説人類擁有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和決策能力,或許在非常簡化的模型中,人們可能會遵循這些思路做出一些假設,但從更普遍的經濟學角度來看,理性單純意味着人類的行為是為了實現某種目的。人類針對外部環境做出選擇,不會一次又一次地被愚弄,就像老牌搖滾樂隊誰人樂隊(The Who)的歌《我不會再次受到欺騙》所唱的那樣。至少,那些做選擇的人不會以同樣的方式一次一次地遭到愚弄,因為理性會阻止他們。
經濟學的第三重含義是,這些選擇可能會帶來複雜的相互作用。人們想要的許多東西是由我們稱之為“市場”的機制所提供的,還有一些東西則是由我們稱之為“計劃”的機制所提供的。其中,在後一種機制中,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按照政府指令進行配置。那麼,當這些機制被納入考量,個體的需求和慾望必須以某種方式加以協調。例如,市場中不可能長期存在下面的情況:某種商品的生產成本非常高,但卻以遠遠低於成本的價格被出售。同樣,市場中也不可能長期存在某種商品成本很低,但售價卻大大高於成本的情況。在第二種情況下,生產者之間的相互競爭最終會導致該商品的價格下跌。
就計劃機制而言,也不可能出現下面的情況,即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政府的支出很高,但税收很低。這種情形是不可持續的。人們不會永遠願意借錢給這樣的政府,就像希臘和愛爾蘭等國此前出現的情況,以及阿根廷、俄羅斯和墨西哥等許多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歷過的那樣。同樣,從長期來看,政府支出很低而税收很高的情況也不大可能出現,因為政客之間的競爭將使得這種狀態無法持續,政府要麼會減税,要麼會增加支出。你可以將這種總體視角推而廣之,擴展到其他機制中各方的互動,例如家庭機制、非營利組織和俱樂部機制等。這裏的重點是,經濟學家所關注的是這些機制中不同方面存在的激勵會如何影響人們的選擇,以及其可如何應用於自然世界中發生的各種情況,比如什麼樣的激勵和選擇可以降低人類在發生自然災害時付出的代價。
最後需要強調,所有這些有目的的選擇相互作用,其產生的力量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自從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了經典著作《國富論》開始,經濟學家一直強調被後人稱為“看不見的手”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人們追求私利的行為同樣可以使整個社會受益。在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認為這種理論並不難理解。例如,某家商業企業努力生產某種商品,這種商品的品質良好,可以為企業帶來良好的信譽和穩定的客源。企業這樣做是出於自利目的,即賺取利潤。另一方面,消費者四處尋找可以滿足其自身偏好並具有最高性價比的商品,這種行為同樣是出於自利目的。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消費者為企業提供了創新的激勵,而企業則為消費者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商品。
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就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往往會帶來各方均可受益的結果。這是一種非凡的社會洞察力,其力量和影響可能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它也可能以其他方式發揮作用。
大約一百年前,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託(Vilfre¬do Pareto)曾寫道:“人類的努力被用在兩個不同的方面:它們或是被用於經濟商品的生產或改造,或是被用於侵吞他人生產的商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位名叫傑克·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的現代經濟學家借用電影《星球大戰》的説法,將上述第二種動機命名為“原力的黑暗面”。畢竟,企業可能會試圖用廉價的產品、虛假的承諾和誤導性的語言來欺騙消費者。偷盜是一種自利的行為,貪污也一樣,還有向大氣和水源中排放污染物亦如此。戰爭往往是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正如法庭上你來我往的訴訟官司,或是利用政治權力控制資源,以推行某些選民並不那麼支持的政策。
從長遠來看,即使不是出於自利的考慮,投票支持那些承諾全面減税並增加政府支出的政客也註定不會有什麼結果。追求私利的行為固然可以表現為創建公司等組織形式,但是也可能表現為創建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仇恨、嫉妒、種族主義等都是人類固有的自利動機,自利動機並不僅僅是那些温和向善的方式。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足夠寬泛,不僅涵蓋了自利力量的光明一面,以及這種對自利的追求可以如何造福於社會,還涵蓋了自利力量的黑暗面及其如何以破壞性的方式發揮作用。
通過關注選擇、選擇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選擇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經濟學顯然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領導者。選修經濟學課程的學生遠比選修其他社會科學課程的學生要多,結合商科專業看更是如此,商科專業通常會學習大量的經濟學知識。經濟學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更多關注。畢竟,在美國,白宮設立了經濟顧問委員會,沒有設立社會學顧問委員會、政治學顧問委員會或是心理學顧問委員會。經濟學家也受到媒體的更多關注。例如,《紐約時報》多年來連續刊登了一系列由學術經濟學家撰寫的評論專欄,而沒有其他社會科學專業人士撰寫的評論專欄。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在社會科學中,才有“經濟學帝國主義”這一説法。
經濟學家將他們的概念工具,即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做出有目的選擇的概念,運用到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中,並且在近年來還越來越多地運用到了心理學中。事實上,經濟學家圈子裏流傳着一個老笑話,即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們面臨的選擇,而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則是人們實際上並沒有做任何選擇。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講,這個笑話包含了兩種關於人們行為動機的觀點,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其中一種觀點認為,人們受制於成長經歷、遺傳、社會壓力、同伴,以及他們在生活中面臨的其他限制,其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早已預先設定。
另一種相對應的觀點則認為,雖然上述所有因素都很重要,但人們確實可以在極大的範圍內做出選擇。而個人這些有目的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可能如何相互作用,正是經濟學發揮作用的領域。至少在我看來,鑑於經濟學所關注的是人們所做的選擇,這門學科或許擁有驚人的樂觀前景。
對本書主題的概述暗示了經濟學所涵蓋主題的廣度,許多人不會想到這些主題會涉及經濟學,但事實上,這些主題是學術經濟學家們着力研究的領域。例如,想一想人們在面臨是否捐獻器官或交通擁堵時做出的選擇,以及人們如何設置不同的選擇。顯然,這可以視作經典排隊問題的現代版本。此外,選擇在決定宗教信仰時發揮了什麼作用?在婚姻中的作用又是什麼?畢竟,在某種意義上,選擇一位伴侶與選擇一份工作別無二致。還有是否生兒育女的選擇—隨着社會財富日益增加,選擇成為父母的代價也在不斷變化。職業選擇又是如何做出的?一個人為何選擇犯罪或是成為恐怖分子?以及有目的之選擇與諸多不同動機(包括種族歧視,或公平和互惠、合作、慈善和捐獻,或有關冒險、從眾、成癮和超重等諸多選擇)的相互作用。
經濟學中的選擇與自然災害、投票等,以及經濟狀況和收入與人們是否認為自己幸福的調查之間有何相互作用?例如,我們如何解釋下面的發現:儘管幾十年來經濟持續增長,但人們的幸福感似乎並沒有呈現上升趨勢?對於那些學過經濟學的人來説,下面的想法通常並不新鮮,甚至並不特別具有爭議,那就是:經濟學可以而且應該適用於人們在任何方面做出的選擇。但對許多其他人來説,他們可能確實沒有想到經濟學框架可以應用於上述領域的個人選擇。
説到這裏,我希望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你們對經濟學的一些擔心,或者至少讓你感覺到,經濟學或許值得先學上一學,直到你們自己做出判斷。但我猜想,很多人的內心深處仍然存有一點點疑慮。我用“有目的之選擇”這種説法精心包裝了經濟學,但我能聽到你們中的一些人會問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歸根結底,這是否只是一個漂亮的修辭,旨在掩蓋“貪婪有可取之處”的論點?對於這個問題,簡短的回答是:不是。而更長的回答是,“貪婪”並不等同於一個人試圖按照自己意識到的私利行事,並據此做出選擇。但畢竟,貪婪是《神曲》以及一些宗教所列出的七宗罪之一。它的定義通常和貪慾、妄念、攫取和無度索求等詞語聯繫在一起。而我在本書中會給出一條清晰的界限,將上述意義上的貪婪與在資源稀缺的世界裏儘可能做出最好選擇區分開來。
著名古代猶太哲學家,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紀的希勒爾(Hillel)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如果我不為自己,誰會為我?但如果我只為自己,那麼我又成了什麼人?”希勒爾的話表達了一種平衡感:是的,你可以為自己考慮,但不能只為了自己。你不必單純為了造福他人而犧牲自我。總要有人站在“我”這邊維護“我”的利益,而我自己是最可能這樣做的人選。認為貪婪無罪的想法是一種愚蠢的情緒。它甚至可能只是為了譁眾取寵而故作愚蠢。但是,“貪婪為惡”也可能是一個愚蠢的説法,因為如果將其發揮到極致,在考慮人們如何真正做決策,以及人們在做選擇時應該考慮什麼才算合理時,它會強調一種含糊不清的感性認知。
我們的世界紛繁複雜—正確地理解自利行為具有強大而重要的作用。我們不能一言以蔽之,單純地將這一切都斥為貪婪。事實上,理解和接受人們對自利的追求,可能正是我們口中“現代”的真正意義。對於這種觀點最著名的論述來自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77年的著作《慾望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內容是關於資本主義興起和現代思維方式的歷史。
假設你回到了中世紀早期。在那個時候,許多經濟活動都極其固化。你生來就註定擁有某種身份,你可能是一個農民或一位貴族,也許是一個鐵匠或鞋匠。在那時,價格和工資遵從傳統。人們接受所謂公平的價格,即由國王和教會根據自己認定的所謂“正確的看法”而設定的價格。擁有特定身份的窮人被教導應該對自己的身份心存感激。他們應該對自己的貧窮心存感激,並且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富人則應該對自己的富有心存感激,因為那是他們的位置。
然後,到16世紀和17世紀,一種緩慢的演變逐漸發生。你開始在更大的市場上進行更多的遠距離交易。銀行業和金融業開始興起。制定獨立的商法成為必要。人們開始有可能選擇改變他們出生時的地位。當然,在那時候,平民雖然不可能真正成為皇室成員,但可以變得富有,而財富可以讓他們在社會上被重視。
人們開始擺脱前現代社會的狀態,即交換主要通過傳統的家庭紐帶進行的狀態。他們開始認為,自己可以依託法律和社會而有所選擇。隨着這種變化的發生,經濟學家也開始擁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18世紀左右。這一點並非巧合。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他的經濟學鉅著《國富論》,他在書中寫道,國家的財富不是建立在戰爭或掠奪之上,也不是建立在金銀的積累之上。相反,國家財富建立的基礎是人們根據生產任務進行分工,從事專門的工作,在工廠進行合作以及進行遠距離交易。
關於如何創造財富的理念也開始發生轉變。它不再是要贏得戰爭或參加十字軍東征,而是變成了向世界各地派出商船,並生產出商品。所謂“有目的之自利”這一經濟理念的基礎是人們可以自主地做出選擇。你不會被困在某個角色裏,試圖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並沒有錯。事實上,部分擺脱對集體的關注可能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要步驟,目前全球許多國家仍在這種轉變的進程之中。
我認為,我們可以公平地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觀點,即在看待生活時,現代觀點有別於傳統觀點之處恰是前者向更完全的自我意識轉變,即相信自我的命運並非天生註定,而是可以做出選擇,並接受靠這種選擇得來的自我是正當的。簡言之,經濟學遠遠不止是關乎金錢和商業,也絕不僅是某種簡單的假設,比如“貪婪有可取之處”,然後運用這個假設來為我們周圍世界任何不公平的現象進行辯護。相反,經濟學尋求更深層面上的理解。它試圖揭示和探索人們出於某種目的而做出選擇這一現實,無論這種目的是短視的還是富有遠見卓識的。同時,人們的選擇與市場和計劃等社會機制相互作用,並且這些選擇的結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
如果經濟學能以恰當的方式被人們加以應用,那麼它將帶來令人欣喜的豐富成果。我希望你們能夠明白,經濟學所涵蓋的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普遍認識,因為經濟學的選擇導向框架已經延伸到了廣泛的領域。它使得我們能夠從意想不到的角度研究各種有趣的主題。以這種方式,經濟學幫助我們獲得了對種種人類行為和社會行為的深刻洞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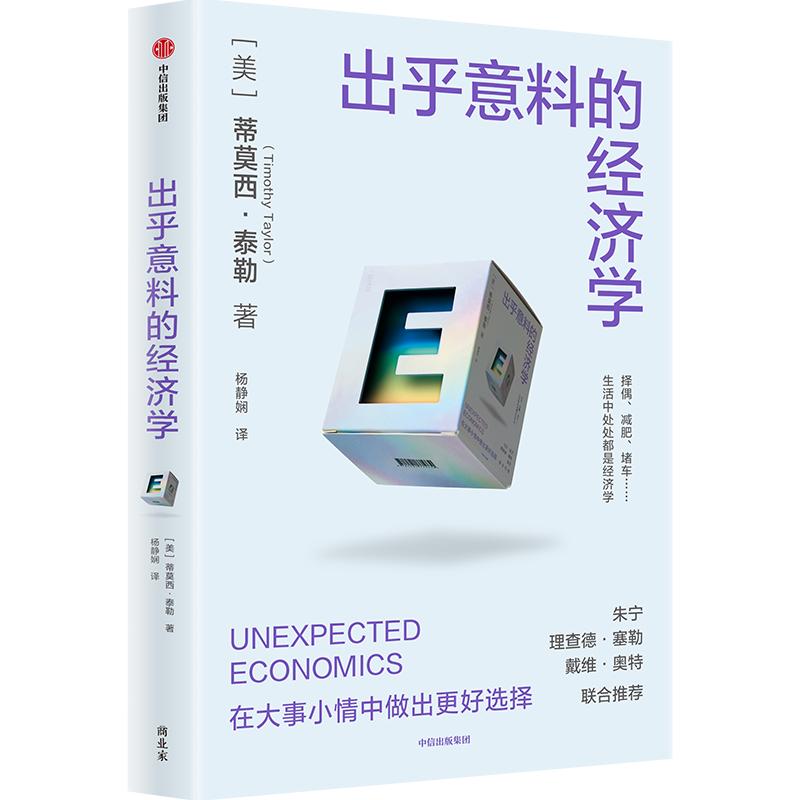
本文摘自《出乎意料的經濟學》
經濟學頂刊主編,《斯坦福極簡經濟學》作者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