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布盧姆:為迎合美政府,大批新興智庫塑造對華新論調?
guancha
編者按:自20世紀初以來,華盛頓智庫一直是美國政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思想工廠”不僅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更在政權更迭時充當人才庫,為新政府輸送專業人士。
然而,這套延續百年的智庫模式如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從伊拉克戰爭的集體誤判到金融危機後民粹主義的興起,公眾對專家權威的信任日漸衰落。隨着特朗普重返白宮,一場關乎華盛頓權力重新分配的深刻變革正在上演。
對此,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於2025年6月發佈了一篇研究報告,完整勾勒了這一變革的來龍去脈。作者朱利安·布盧姆(Julian Blum)曾任法國駐美大使館特派專員,在任期間得以近距離接觸並深入研究美國智庫生態。其報告詳細梳理了智庫界從特朗普首任期的激烈博弈,到拜登時期的表面復甦,再到如今新興力量徹底勝出的全過程。
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編譯此文,觀察者網轉載,供讀者閲讀參考。
【文/朱利安·布盧姆,編譯/山杉】
2010年,美國政治學家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對華盛頓主要智庫的聲望仍頗為滿意,彼時這些智庫正如日中天。他高度讚揚了這些權威機構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的核心作用,所提及的機構不乏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基金會、彼得森研究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哈德遜研究所以及蘭德公司等業界翹楚。
這些智庫大多雲集於馬薩諸塞大道(又稱“智庫街”),與白宮不過咫尺之遙,充分彰顯了其在華盛頓權力中樞的核心地位。他們擁有令其歐洲同行望塵莫及的上億甚至數十億美元的龐大預算,也為數千名研究人員提供支持。
智庫之所以擁有強大影響力,源於它們在華盛頓體系中發揮的兩大核心功能:
首先,智庫充當連接政治界與學術界的重要橋樑。智庫成功地將自己定位為國家的專業智力服務提供者,以“超黨派”的學術嚴謹態度和深度分析能力,處理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議題。它們通過發佈研究報告和舉行高層政策簡報會來為決策者提供智力支持,部分智庫還與聯邦機構簽訂多年期合作協議。
其次,智庫承擔着人才儲備庫和政治精英孵化器的重要使命,為歷屆政府輸送數百名專業管理人才。它們之所以能夠發揮人才供應者的作用,得益於美國政治制度中獨特的“政黨分贓制”(spoils system)傳統,每次政府換屆都會有至少4000名人員進出政府部門。
對於專注外交政策的智庫——如CSIS、布魯金斯學會、哈德遜研究所、蘭德公司或對外關係委員會(CFR)——與政府的密切關係使其成為外國政府眼中的重要溝通橋樑。各國政府普遍將這些智庫視為通達美國決策層的重要渠道。在此背景下,智庫經常在危機時期發揮非官方外交平台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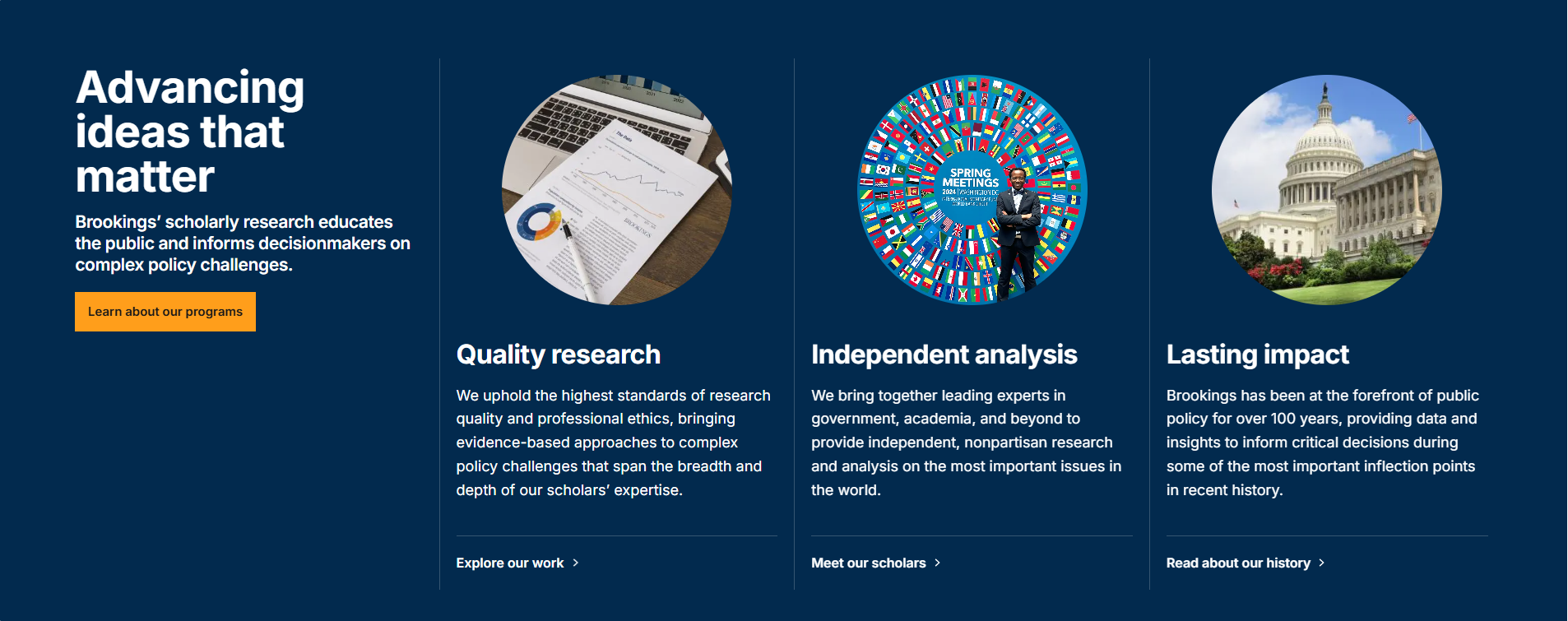
布魯金斯學會官網頁面介紹
然而,報告認為,智庫承擔的“提供信息”與“施加影響”這兩大使命之間存在根本性矛盾。在美國,智庫憑藉501c(3)(譯者注:美國税法中的一個條款,專門為某些非營利組織提供免税待遇)非營利組織的法律身份,享有資金來源保密的特權。這種制度安排堪稱諷刺:智庫標榜服務公共利益,但在運作透明度方面,竟然比受到嚴格法律約束的遊説集團更加神秘莫測。正是這種不透明性,助長了外界對智庫淪為私人財團或外國勢力代理人的質疑,嚴重損害了這些機構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過去二十年來,專注於特定議題或主要為特定政治立場(如環保、社會正義、削減政府開支等)搖旗吶喊的智庫大幅增加。目前美國擁有超過1800家智庫,如今全美智庫數量已逾1800家,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早已偏離了彼得·辛格所推崇的經典智庫模式。
外交與國防政策領域的智庫此前似乎獨善其身,雖未受碎片化和政治化浪潮衝擊,但隨着特朗普重返白宮,這一領域正遭遇史無前例的危機。作為華盛頓建制派的中流砥柱,外交政策智庫難逃MAGA運動的猛烈衝擊——在該運動眼中,智庫與“深層政府”(Deep State)無異。
數十年來在政策制定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主要超黨派戰略智庫,其存在價值正受到兩大變化的根本性挑戰:一是外交政策和國防議題的政治化使得提供“中立”的技術性專業建議變得幾乎不可能;二是智庫長期維護的國際主義政策共識正在瓦解。
因此,當前所面臨的可能不是智庫的消亡,而是華盛頓戰略環境的深刻重塑——新興力量的崛起威脅着傳統智庫的地位,曾經統一連貫的政策諮詢領域正在走向分化。
一、“利益集團”:兩黨制的守護者
(一)美國智庫的歷史成因
華盛頓諸多重要智庫的興起,是美國20世紀兩大政治變革潮流交匯的結果。智庫現象既彰顯了技術專家治國理念的深入人心,亦折射出國際主義思潮在美國統治精英中的蔓延。
20世紀初葉,“進步時代”的歷史浪潮催生了第一批智庫。它們誕生於改革派政治人物與工業巨擘(如安德魯·卡內基和約翰·D·洛克菲勒)的聯盟。這些早期機構秉承超黨派專業知識的實證主義理想,致力於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引入國家決策過程。
卡內基基金會(1910年)、布魯金斯研究所(1916年)和對外關係委員會(1921年)的相繼成立,標誌着一種獨具美國特色的智庫模式正式登上歷史舞台:政府體系之外,私人資本慷慨支持,技術官僚專業至上。這一時期,美國慈善事業走向制度化,鉅額捐贈基金紛紛湧現,為智庫在知識界的生根發芽提供了豐厚土壤。智庫興起這一現象,實則與美國現代行政國家的崛起以及新興資本主義官僚階層的形成密不可分。
報告分析,在外交政策領域,早期大型私人智庫絕非政治中立。這些機構推崇“專家治國”理念,與國際關係中國際主義思潮的興起息息相關。國際主義者認為,步入20世紀的美國理應發揮與其新興實力相稱的全球作用,肩負起推進自由民主的歷史使命。這些智庫機構毫不掩飾其精英主義色彩,公然挑戰美國自華盛頓時代以來在歐亞大陸奉行的不干預傳統。
《凡爾賽條約》簽署之際,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對外關係委員會(CFR)鼎力支持威爾遜總統的政治理念(威爾遜正是美國國際主義的倡導者)。歷史學家斯蒂芬·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深入研究揭示,二戰期間CFR舉足輕重,實際上成為羅斯福總統的“第二國務院”。該機構專家們身處美國外交理念大轉折的風口浪尖,推動國家從孤立主義走向全新的外交路線。這一路線主導美國對外政策長達半個多世紀,其核心要義可概括為:國際主義理念與軍事超強實力相結合。
1945年後,智庫在鞏固這一新共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積極投身於“國家安全體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構建。所謂“國家安全體制”,是指冷戰時期為維護美國霸權而精心打造的整套國家機器。
戰後數十年間,第二波專注於國際和戰略問題的重要智庫應運而生。與早期智庫不同,這些機構由聯邦政府部門或實力雄厚的軍工企業資助,包括蘭德公司(1948年)、哈德遜研究所(1961年)、CSIS(1962年)。1979年傳統基金會橫空出世,這一具有濃厚共和黨色彩的機構對國內政策領域的無黨派智庫傳統發起衝擊。然而,外交政策領域依然是技術官僚理想的最後堡壘。各大智庫繼續以二戰後外交理念的守護者自居,地位不可撼動。
直至2010年代,華盛頓各智庫都認同一個基本共識:美國理應運用實力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共識超越黨派藩籬,不受各機構政治取向影響。縱觀美國戰略決策圈的知識精英,雖偶有分歧,但在以下核心議題上立場如一:維護歐亞聯盟體系、強化北約機制、堅定支持以色列、推廣民主人權理念、深入開展反恐戰爭。
(二)奧巴馬—特朗普—拜登時期:“利益集團”奮起反抗
僅僅把二十世紀對技術專家的質疑歸咎於MAGA運動,未免有失偏頗。早在特朗普橫空出世之前,智庫的影響力及其對外交政策的掌控就已經備受爭議。儘管如此,歷屆政府並未將其束之高閣。2000年代初期,專家階層對伊拉克戰爭的一邊倒支持,為十年後人們指控這一圈子因循守舊、甚至貪腐變質埋下了伏筆。
奧巴馬執政末期,其顧問團隊旨在讓美國外交政策迴歸某些基本原則,並公開表達了對建制派的不滿。建制派對總統的政策倡議持敵視態度,在伊朗核問題上尤其如此。奧巴馬因反對伊拉克戰爭而當選總統,致力於為美國外交政策開闢新的道路,推行更加温和的外交路線。具體而言,就是轉向亞洲,並從中東泥潭中抽身而退。
奧巴馬的顧問兼撰稿人本·羅茲(Ben Rhodes)一針見血地將智庫世界比作“利益集團”(“blob”)。這個詞源自1980年代的一部恐怖片,片中一種外星生物會吞噬所經之處的一切生命。對華盛頓精英集團及其專家階層固步自封的不滿情緒,後來成為部分民主黨評論人士經常提及的話題。自此以後,“blob”和“blobaganda”(blob與propaganda的合成詞)進入了政治話語體系,專門用來諷刺首都戰略圈的思想僵化和抱團取暖。
特朗普首任期間,對維護既有秩序的華盛頓建制派的不信任情緒空前高漲。雖然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羅伯特·萊特希澤(obert Lighthizer)、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賈裏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等少數心腹力推“美國優先”理念,竭力踐行特朗普的顛覆性議程,但“利益集團”在捍衞美國外交政策根基方面卻表現出了頑強的韌性。任期伊始,確實有聲音認為智庫社區危在旦夕,面臨“生存危機”。然而,這些機構在政府技術部門的牢固根基,恰恰成為諸多重大議題得以存續的關鍵所在。
華盛頓建制派毫不掩飾其對特朗普政策的反對,而是公開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資深學者、政治學家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僅力圖洗刷這種污名,更呼籲要讓“利益集團”復興,並直言自己就是“利益集團”的一分子。布蘭茲振振有詞地寫道:“跳出條條框框思考問題固然有其價值……但條條框框之所以存在,往往自有其道理。”

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
拜登上台執政以及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似乎讓智庫重新煥發生機,其所代表的國際主義路線也得以復甦。拜登政府彷彿要徹底翻過特朗普這一頁,開始從華盛頓最具聲望的智庫中招攬核心外交和經濟政策制定者: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卡內基基金會主席)、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卡內基出身)、艾薇兒·海恩斯(Avril Haines,新美國安全中心)、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布魯金斯學會)。
許多觀察人士,如記者雅各布·海爾布倫(Jacob Heilbrunn),將此稱為“利益集團”的“復活”,甚至是“復仇”——憑藉其可靠專業知識的承諾,對抗特朗普的反建制衝擊。媒體報道顯示,俄羅斯發動侵略戰爭後,拜登政府每週都與布魯金斯學會、大西洋理事會、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等知名智庫保持通話。這一時期也見證了老牌大西洋主義倡導者重新獲得影響力,如約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和亞歷山大·韋爾什博夫(Alexander Vershbow),二人均來自大西洋理事會。
各大智庫意識到自身面臨的信任危機,並在此期間積極尋求構建新的思想框架,力圖讓美國民眾重新接受適應21世紀的國際主義政策。傑克·沙利文提出的綱領性概念“中產階級外交政策”就是在卡內基基金會孕育而生的,這完全是華盛頓知識精英為適應國內政治形勢而做出的產物。
在為反恐戰爭提供理論支撐之後,智庫將關注焦點轉向大國競爭的迴歸,尤其是對華競爭。正值拜登執政期間,部分智庫甚至利用“軸心”(axis)概念,將俄羅斯、伊朗等國納入其中,塑造對立陣營。這一理論框架着重強調全球戰場的有機聯繫,為美軍在歐亞大陸的長期駐紮和國防預算的大幅攀升提供了理論支撐。
新美國安全中心學者安德里亞·肯德爾-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提出的“動盪軸心”(axis of upheaval)概念更是深得兩黨青睞,在2023-2024年間廣為流傳。哈馬斯10月7日襲擊事件後,親以反伊勢力捲土重來,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民主防務基金會等機構重新活躍,新保守主義思潮再度抬頭。
然而,特朗普的再次勝選將一切重新洗牌。
二、“美國優先”:另類生態系統的崛起
(一)“美國優先”的崛起
報告分析認為,拜登時代各大智庫的表面復甦以及戰略重新接觸主義的迴歸,實際上掩蓋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一個致力於“美國優先”理念的另類生態系統正在崛起。
這個生態系統致力於為“美國優先”提供理論支撐,目標是將其打造成美國新的戰略學説。MAGA運動的戰略家們深信,特朗普首屆政府之所以舉步維艱,根源在於內部“深層政府”官僚的掣肘抵制。因此他們得出結論:必須徹底更換現有的政治精英,代之以忠誠可靠的新人。
從2021年國會山衝擊事件到2024年11月大選勝利,智庫儼然成為新美國右翼手中的制度化利器。這段政治過渡期見證了一個全新圈層的凝聚成型。
報告援引歷史學家瑪雅·坎德爾(Maya Kandel)的分析,認為所謂“國家保守主義”(national-conservative)運動正是以各類研究機構、政策論壇和理論刊物為紐帶而構建的。誠如坎德爾所言,外交政策領域的“美國優先”路線表面上頗為模糊,既有偏向里根式“以實力求和平”理念的温和派,也有主張全面戰略收縮的激進派。然而,無論立場如何迥異,他們在一個根本問題上卻高度契合,即堅決摒棄20世紀的自由國際秩序。
2021年,傳統基金會搖身一變,將自己定位為MAGA反建制專業主義的核心機構。這個在1980年代與里根主義密切相關的智庫,在路易斯安那州歷史學家凱文·羅伯茨(Kevin Roberts)的領導下,徹底實現了向特朗普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轉向。在外交政策領域,羅伯茨大刀闊斧地將機構推向修正主義軌道,更加強調內政外交的有機結合。
根據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馬伊達·魯格(Majda Ruge)對共和黨內部思想流派的分類,傳統基金會從“霸權至上”(primacy)的堡壘轉向“優先化”(prioritization)的立場,核心理念是將對華競爭置於首位,與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的理念日趨合拍。

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
科爾比是特朗普第一屆政府時期的國防部前副部長,正成為共和黨內這一路線的代表人物。科爾比憑藉犀利的民粹主義言辭,通過在X平台上的日常發聲以及其小型組織“馬拉松倡議”(the Marathon Initiative),已然躍升為華盛頓“利益集團”的頭號批判者。秉承對美國實力的冷峻現實主義判斷,科爾比力主將國家資源傾囊投入對華生存競爭,即便這意味着要犧牲共和黨外交政策的某些核心要素——無論是北約義務、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還是對伊朗協議的堅決抵制,統統都要為大國博弈讓路。
報告認為,儘管傳統基金會在海外備受關注,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更龐大的組織網絡中的重要節點之一。因此,備受媒體熱議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與其説是單一機構的產物,不如説是這個正在形成的思想網絡的集體表達。該項目的參與者涵蓋了眾多自2021年以來崛起或獲得關注的小型智庫組織,對特朗普忠心耿耿,並與其首任任期淵源頗深。
儘管同為非營利組織,這些新興機構與馬薩諸塞大道上的老牌智庫幾乎毫無相似之處。它們在資金來源方面缺乏透明度,研究質量乏善可陳,更談不上開放辯論的學術風氣,其政治影響力完全仰仗於與特朗普的密切關係。
典型代表包括:拉塞爾·沃特(Russell Vought)的“美國復興中心”(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專攻行政體制改革;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美國優先法律基金會”(America First Legal),聚焦移民政策;法學家奧倫·卡斯(Oren Cass)的“美國指南針”(American Compass),為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經濟路線搖旗吶喊;索拉布·夏爾馬(Saurabh Sharma)的“美國時刻”(American Moment),旨在培養新一代忠於特朗普主義的年輕骨幹。
作為保守派哲學家利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思想在西海岸的傳統據點,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精英主義色彩濃厚的機構。如今,它已成為引導這一新興保守派政治陣營走向民族主義、對抗“深層政府”的重要推手。該研究所通過設立獎學金項目培養保守主義新秀,積極參與自2019年起舉辦的全國保守主義大會(NatCon),並在華盛頓設立分部,始終在保守主義陣營中佔據重要地位。
選戰期間,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常被視為“2025計劃”聯盟的勁敵,堪稱為促進特朗普主義政治項目而臨時創建的新型機構中最耀眼的一個。該機構由特朗普首屆政府舊部創立——核心人物包括前顧問布魯克·羅林斯(Brooke Rollins)和摔跤業巨頭琳達·麥克馬洪(Linda McMahon)——與傳統“利益機構”機構截然不同,AFPI毫不掩飾地宣示對MAGA運動領袖的絕對忠誠。在外交政策領域,其綱領性文件《美國國家安全的美國優先路徑》(An America First Approach to U.S. National Security)火力全開,痛斥民主共和兩黨構成的“單一政黨霸權”,高調宣稱要專一捍衞美國人民利益,儘管具體主張不乏模糊之處。
隨着媒體、各國外交部門和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這個與MAGA陣營關聯的政策網絡的存在,他們在選舉前的一年半時間裏密切關注這些機構的政策產出,並積極尋求與其研究人員進行訪談。各方心知肚明:一旦特朗普重返白宮,這些人必將成為政策溝通的核心樞紐。
(二)勝券在握:另類政策生態圈問鼎權力核心
特朗普2025年1月重新入主白宮數月後,事實已經昭然若揭:這些新興智庫在去年11月的選舉中大獲全勝。《政治報》在就職典禮後不久發表文章,標題為“我們如今身處特朗普的華盛頓”,生動刻畫了這些新興機構對傳統智庫的全面碾壓。
報告對比分析指出,首任期內,特朗普不得不向建制派低頭,從華府老牌精英中選拔關鍵職位人選。而此番人事佈局,則徹底宣告了MAGA“反精英集團”的華麗登場。經過四年蟄伏,在各路新興機構的悉心孵化下,這股力量終於迎來了收穫時刻。
論人事佈局,AFPI可謂大獲全勝,一舉拿下十多個內閣部長或重要機構負責人職位。具體人選包括:約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出任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帕姆·邦迪(Pam Bondi)擔任司法部長、琳達·麥克馬(Linda McMahon)洪執掌教育部、布魯克·羅林斯(Brooke Rollins)主管農業部,以及基思·凱洛格(Keith Kellogg)出任烏克蘭和平特使。
雖然在外交政策領域的直接影響力相對有限,“2025項目”網絡同樣在關鍵崗位上站穩了腳跟:湯姆·霍曼(Tom Homan)負責邊境事務,拉塞爾·沃特(Russell Vought)執掌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卡拉·弗雷德(Kara Frederick)裏克進駐白宮,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領導聯邦通信委員會。
大選塵埃落定後,傳統基金會在其總部大樓醒目位置懸掛起那張經典照片——特朗普遇刺不倒、振臂高呼的瞬間。海報還配上了“恭喜總統先生”的字樣,政治表態可謂一目瞭然。其中深意不言而喻:特朗普的勝利,亦即傳統基金會及其掌門人凱文·羅伯茨押寶成功。羅伯茨堅定地選擇與這位億萬富翁站在一邊,憑藉每年超過4000萬美元的預算,傳統基金會現已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智庫。

2024年11月,華盛頓特區,傳統基金會大樓上張貼的慶祝特朗普勝選的海報。 作者拍攝
直到最後關頭,更多建制派評論人士仍抱有幻想,寄望特朗普會基於專業技能考量,網羅一批能夠獲得跨黨派認同的温和派人士。然而,美國企業研究所、哈德遜研究所、大西洋理事會等傳統新保守主義重鎮,儘管在競選期間極力示好特朗普陣營,最終仍在這屆共和黨政府中淪為邊緣角色。
邁克·沃爾茨出任國家安全顧問,曾為這些干預主義機構帶來一線生機。政府初期,國家安全顧問辦公室一度成為哈德遜研究所、大西洋理事會等機構推銷其親烏政策主張的為數不多的發聲平台。
然而好景不長。“信號門”(Signalgate)風波過後,沃爾茨及其副手亞歷克斯·王(Alex Wong)在總統孤立主義支持者的施壓下雙雙出局,這對華盛頓建制派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更令人玩味的是,那些長期被視為政府潛在人選的新保守主義學者,如馬修·克勒尼格(Matthew Kroenig,大西洋理事會)、麗貝卡·海因裏希斯(Rebecca Heinrichs,哈德遜研究所)和維多利亞·科茨(Victoria Coates,傳統基金會),至今仍未獲得重用。
然而報告分析指出,最近針對伊朗的系列軍事行動表明,新保守主義陣營在公共輿論場仍有一席之地。雖然在政府內部影響力有限,但他們仍可依託媒體生態系統中的盟友發聲,比如通過福克斯新聞和《國家評論》等平台,或者在國會中發揮作用,那裏仍有不少共和黨議員願意聽取哈德遜研究所或民主保衞基金會等機構的政策建議。
傳統共和黨智庫陣營中,曼哈頓研究所是個值得關注的例外。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研究機構專注於經濟和城市政策研究,具有保守派乃至自由意志主義色彩。如今該機構通過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和白宮經濟顧問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在新政府內部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
在外交政策和國防相關職位任命中,最終獲得重用的是那些主張收縮外交政策的“約束派”人士(the restrainers),以及將對華防務作為優先要務的“優先派”人士(the prioritizers),埃爾布里奇·科爾比就是其中代表。科爾比出任國防部政治事務副部長後,其政策理念在五角大樓內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在傳統基金會的亞歷克斯·維雷茲-格林(曾任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的顧問)的協助下,科爾比正在對軍政人員進行大規模調整,以鞏固其修正主義政策立場。
報告認為,克萊蒙特研究所的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被任命為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這一重要人事安排同樣體現了政策轉向:更傾向於支持美國戰略收縮和帶有MAGA意識形態色彩的外交政策。與J.D.萬斯和馬可·魯比奧關係密切的美國指南針智庫也在國務院佔有一席之地,其保護主義政策主張正通過特朗普的關税大棒得以兑現。
這家由經濟學家奧倫·卡斯(Oren Cass)領導的智庫最近在華盛頓舉辦盛大慶典,既慶祝成立五週年,更彰顯其政策理念在思想界的全面勝利。然而,2025年6月美國對伊朗軍事幹預引發的激烈爭議表明,內部分歧依然暗流湧動。儘管主張政權更迭的聲音在共和黨聯盟中已幾乎銷聲匿跡,但許多特朗普主義人士仍帶有強烈的親以色列傾向。MAGA聯盟內部這些根深蒂固的戰略分歧正在浮出水面。
曾經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MAGA媒體,如布萊巴特和NewsMax,如今已經翻身做主,獲得了政府的全面准入權。這些非主流智庫現在充分利用與全球最強大政府的密切關係獲利。在商界、遊説集團以及希望向美國政府傳遞信息的外國政府看來,這些機構已經成為與傳統大型智庫同樣重要,甚至更具價值的溝通渠道。
不滿足於當前的勝利,這些機構已經公開宣佈要長期確立MAGA理念的地位。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在更換領導層後宣佈,正在制定讓特朗普主義延續“未來一百年”的規劃。傳統基金會同樣致力於特朗普主義的制度化建設,近期收購了由總統女婿賈裏德·庫什納和前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大衞·弗裏德曼共同創立的亞伯拉罕協議研究所。
對於MAGA陣營中未能進入政府任職的專家學者,他們依託各自的智庫平台搶佔輿論陣地,為政府的爭議性政策搖旗吶喊。美國指南針的奧倫·卡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媒體面前堅定地為特朗普的關税政策辯護。美國復興中心的歷史學家蘇曼特拉·邁特拉(Sumantra Maitra)則在2024年提出“休眠北約”(dormant NATO)這一概念,為美國退出北約的計劃提供理論支撐,如今又在努力將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執念包裝成切實可行的政策方案。
(三)兩黨制約派運動的興起
報告認為,除了MAGA陣營之外,近年來華盛頓在戰略問題上的觀點呈現出更為廣泛的多元化趨勢,兩黨制約派和進步派組織在推動非干預主義政策方面聲勢漸起,影響力與日俱增。政治學家因德吉特·帕馬爾(Inderjeet Pamar)指出,科赫兄弟的資金支持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科赫家族是美國共和黨的大金主之一。圖為科赫兄弟
這對兄弟是著名的慈善家,秉持自由主義理念,堅決反對美國的對外干預政策。直到五年前,由科赫家族長期資助的卡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還是華盛頓唯一一個致力於削減美國在全球軍事部署的主要智庫機構。時至今日,賈斯汀·洛根(譯者注:Justin Logan,卡託研究所國防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已成為制約派陣營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認可。
此後,一系列新興機構相繼成立,其中包括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該所的誕生令人稱奇——科赫兄弟與進步派的索羅斯基金會,竟因重塑美國外交政策的共同關切而攜手合作。自2019年成立以來,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匯聚了來自左右兩翼的修正主義學者,為左翼的特里塔·帕爾西(Trita Parsi)和右翼的安德魯·巴切維奇(Andrew Bacevich)等人提供了重要的學術陣地。
昆西研究所還致力於挑戰傳統智庫的主導地位。該所設立了外交政策民主化中心,由本·弗里曼(Ben Freeman)主持,專門揭露國防工業與研究機構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同樣秉承反干預理念的還有國防優先組織(Defense Priorities),這家小型智庫目前通過研究員邁克爾·迪米諾(Michael DiMino)與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團隊保持着微妙聯繫。
報告認為,外部事件的衝擊,在反干預主義思潮的興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有時甚至起到了激進化的效果。衝突的不斷增多雖然讓新保守主義的“軸心”論調重新抬頭,但同時也推動了一些研究人員轉向剋制派立場。
2022年,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這個素來偏左的智庫,迎來了一批從大西洋理事會出走的學者。他們因反對華盛頓對基輔的無條件支持而憤然離去。這個“重新想象美國大戰略”團隊同樣獲得了科赫基金會的資助,成員包括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和克里斯托弗·普雷布爾(Christopher Preble),此後影響力不斷擴大。
在卡內基基金會,克里斯·奇維斯(Chris Chivvis)和斯蒂芬·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在的美國治國之道項目,也越來越頻繁地批評美國能力的過度擴張。2024年夏天華盛頓北約峯會期間,這些來自左右兩翼的智庫學者形成了統一戰線,共同簽署請願書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
在左翼陣營,加沙戰爭的衝擊尤為深遠,使批評美國支持以色列政策的聲音獲得了空前關注,而華盛頓建制派歷來與特拉維夫關係密切。
國際政策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在這場辯論中表現尤為活躍,該中心由埃及人權活動家南希·奧凱爾(Nancy Okail)領導,成員包括前伯尼·桑德斯顧問馬特·杜斯(Matt Duss),他們痛斥拜登政府的雙重標準——支持烏克蘭,卻對加沙的暴行視若無睹。
在昆西研究所,特里塔·帕爾西(Trita Parsi)這位推動美伊關係緩和的知名倡導者,正在牽頭批評美國的對以政策。2024年夏天,昆西研究所還招募了安內爾·謝林(Annelle Sheline),其因反對民主黨加沙政策而從拜登政府辭職。
儘管這些反干預主義機構的研究人員很少進入政府任職,但他們對特朗普的某些國際政策頗為認同。特別是馬特·杜斯(Matt Duss)和斯蒂芬·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等左翼專家,公開支持任命埃爾布里奇·科爾比等修正主義共和黨人。在2025年初夏美國是否應與以色列聯合干預伊朗的問題上,韋特海姆、帕爾西、杜斯、阿什福德等左翼學者,竟與塔克·卡爾森、史蒂夫·班農、柯特·米爾斯等右翼人士站在了同一戰壕,反映了當今華盛頓在某些議題上意識形態界限的模糊化。
三、無黨派智庫走向末路
(一)特朗普政府劍指傳統智庫
2024年11月5日大選落幕次日,素有“智庫街”之稱的華盛頓馬薩諸塞大道愁雲慘淡。特朗普重返白宮,不僅令華盛頓政策圈專家們在政治和心理層面備受衝擊,更讓眾多研究機構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要知道,這些機構中不少研究人員此前已獲承諾,將在哈里斯政府中身居要職。
很快,他們也切身感受到了政府效率部(DOGE)掀起的整頓風暴,以及新政府對華盛頓建制派發起的全面攻勢。按照MAGA意識形態的劃分,凡屬“深層政府”範疇的機構——無論是非政府組織、媒體還是高等院校——無一例外,各大智庫自然也在劫難逃,紛紛捲入這場激烈的意識形態較量。
聯邦政府斷然凍結對民間社會的資助,首當其衝的便是那些在外交政策領域秉承國際主義理念的老牌機構。美國和平研究所(USIP)和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包括其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的著名凱南中心——這兩個由國會資助的重要機構已經遭到DOGE的重創,被迫關門,其間不乏戲劇性場面。據媒體報道,DOGE人員突擊檢查USIP辦公場所,在私人安保公司的幫助下破門而入,將內部工作人員盡數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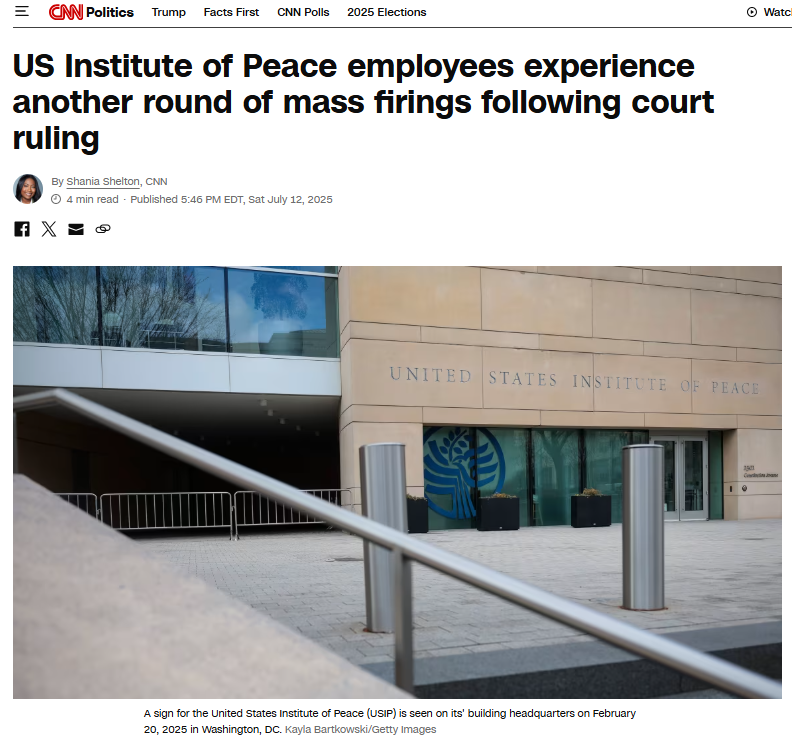
CNN相關報道截圖
雖暫未面臨關閉危機,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會、布魯金斯學會等重量級智庫亦紛紛遭受資金削減重創。具體而言,CSIS歐洲中心等專門項目與國務院、國防部的合作協議被一紙廢止,相關研究工作戛然而止。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削減措施明顯具有選擇性,集中打擊特定研究領域,其政治動機昭然若揭。顯而易見,這些舉措絕非單純為了提升政府“效率”。
凡與“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理念沾邊的項目,概遭封殺,無一倖免。反虛假信息這一高敏感領域更是成為政府斷供行動的重點目標,迫使大西洋理事會數字取證實驗室等核心機構不得不忍痛割愛,裁減部分頂尖研究人員。
氣候變化與發展研究同樣也未能倖免。這種嚴峻形勢讓不少機構陷入財政緊縮困境,不得不四處尋求新的資金來源。報告認為,此舉勢必帶來始料未及的負面效應:外國勢力的滲透活動恐將趁機抬頭,那些意圖左右華盛頓政策走向的境外資金必將蠢蠢欲動,伺機而入。
(二)無黨派智庫模式身陷困境
報告分析指出,長遠來看,傳統智庫正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這些主要依靠私人資助維持運營的機構,幾乎被完全排擠出政府決策圈。昔日為歷屆政府源源不斷輸送專業人才的智庫,如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影響力被徹底切斷。它們不得不與黨派色彩更為濃厚的智庫羣體以及Palantir、Anduril等科技公司展開激烈角逐,而這些新興勢力正大舉進軍政府部門,搶佔要職。
失去昔日的政府准入優勢後,這些老牌智庫憂心忡忡,擔心自己會在捐助者和合作夥伴眼中失去價值。眾多無黨派機構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戰略抉擇:要麼堅守非政治立場,即便新政府的政策與其核心理念背道而馳;要麼倒向民主黨陣營,但這勢必要背叛其恪守已久的中立傳統。
在政府加強管控主要高校的大背景下,華盛頓各大研究機構內部正在激烈辯論,陣營分化日趨明顯。索羅斯家族旗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正在力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充當政府的學術制衡力量,但該機構管理層斷然拒絕,既擔心遭到政府報復,又希望維護機構的學術傳統。
眼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等最知名的智庫都選擇明哲保身,採取審慎策略,專注於技術性議題研究。雖然私下裏有譴責聲音,但公開發表的文章主要聚焦於對華競爭、與海灣國家的夥伴關係等議題,並刻意迴避氣候變化等敏感話題。
然而,從長遠視角來看,當前危機似乎只是進一步暴露了無黨派智庫模式的內在脆弱性,使其更加依賴贊助人的意志。
面對錯綜複雜的政治雷區,研究獨立性與現實影響力之間的平衡術愈發舉步維艱。智庫正在加速蜕變,印證了社會學家托馬斯·梅德韋茨(Thomas Medvetz)早在2012年就發出的警告。他當時分析了“倡導型模式”(advocacy model)的興起——這類智庫更專注於為金主和政治贊助人搖旗吶喊,而非潛心學術,以優質研究推動公共議題的深入辯論。
E.J.法根(E. J. Fagan)與梅德韋茨觀點不謀而合,他近期進一步剖析了美國智庫如何既是政治極化的必然產物,又是這一進程的推手。除了資金來源日趨枯竭迫使智庫加大對私營部門的依賴外,信息傳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趨勢也在倒逼那些希望保持公眾影響力的研究機構調整傳播策略。作為“專家治國”理念的中堅力量,尤其在外交政策這一傳統優勢領域,老牌智庫還面臨着公眾對專業權威日益加深的質疑。新冠疫情和烏克蘭戰爭更是將這種不信任推向了新的高度。
那麼,這一戰略性行業在未來數年將何去何從?
彼得·辛格在2010年曾以“思想工廠”(idea factories)為喻,思考智庫在重大政治變局後可能出現的“去工業化”現象:“智庫行業是否會重蹈美國製造業的覆轍?”毫無疑問,知識精英羣體面臨的危機,特別是外交政策領域的智庫危機,目前已達到可能難以逆轉的臨界點。
(三)智庫日益淪為政治庇護的工具
外交政策類智庫並非走向消亡,而是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智庫與政治遊説集團的界限將日趨模糊,碎片化和極化現象愈發嚴重,外交政策領域也不例外。然而,這種變化是以犧牲研究品質和學術辯論為代價的。
可以預見,未來幾年各類新智庫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2021-2024年期間,MAGA陣營戰略性地利用智庫為重新奪權做準備,這充分證明了美國政治體系將繼續對這些本質上具有雙重性質的機構保持濃厚興趣。這些機構善於偽裝,表面上是中立的專業知識平台,實則暗中為黨派利益搖旗吶喊,手法更加隱蔽靈活。對於那些試圖左右公共辯論的政治企業家而言,智庫身份相比遊説集團具有天然優勢——缺乏透明度。
州級黨派智庫的激增,恰恰印證了這種做法日益普遍。這些小型智庫目標明確,結構靈活,與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形成利益共同體。背後的金主往往是同一批人,他們通過資金紐帶,力圖將特定議題推上政策前台。以地方共和黨智庫“州政策網絡”為例,該組織在未來幾年勢必繼續壯大,其民主黨對應機構“州優先夥伴關係”亦是如此。
也可以預見,智庫將成為民主黨未來幾年政治和思想重整的核心力量。拜登政府落幕後,多位核心人物紛紛轉戰智庫,意圖影響黨內路線。例如,前國內政策顧問尼拉·坦登(Neera Tanden)現已執掌美國進步中心這一民主黨重要智庫。中間派、市場導向的尼斯卡寧中心(Niskanen Center)目前代表着民主黨內更加自由化、技術官僚化的路線。該機構將自己定位為民主黨內新興派系的先鋒,主張通過國家干預推動新型生產主義,以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挑戰。
另一邊,羅斯福研究所(the Roosevelt Institute)則高舉左翼大旗,秉承沃倫-桑德斯路線,繼續推進反壟斷鬥爭。這一斗爭的標誌性人物當屬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莉娜·汗(Lina Khan),汗的幕僚長伊麗莎白·威爾金斯(Elizabeth Wilkins)現已接任該研究所負責人。這兩大智庫所代表的不同路線已經開始公開交鋒。
報告認為,在外交政策領域,民主黨左翼將採取何種路線,哪些機構或人物將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目前還難以明確判斷。國際政策中心、昆西研究所以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傳統智庫已經吸納了拜登政府的眾多外交政策核心人物:哈里斯的國安顧問菲爾·戈登(Phil Gordon)現身布魯金斯學會,中東事務主管佈雷特·麥格克(Brett McGurk)轉戰貝爾弗中心,前國安會戰略主任麗貝卡·利斯納(Rebecca Lissner)投奔外交關係委員會。至於前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他成為哈佛肯尼迪學院首任基辛格治國方略與世界秩序實踐講席教授。
然而,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前國防部負責印太事務的助理部長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加入了科爾比創立的馬拉松倡議智庫。這一人事流動或許預示着外交政策陣營的傳統界限正在悄然鬆動。未來幾年,這些不同派系和思潮的力量對比將逐漸明朗,特別是在中期選舉期間。屆時,民粹主義與中間路線、國際主義與戰略收縮之間的辯論仍將持續發酵。
四、時代終結的預警信號
特朗普就職典禮當日,傳統基金會總部舉辦盛大觀禮活動,敞開大門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數千名共和黨支持者共慶勝利。華盛頓政治精英圈外的普通民眾排隊數小時,只為進入這座已成為美國保守主義象徵的機構。此景此情,在布魯金斯學會或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等傳統智庫簡直難以想象。
這表明,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處於華盛頓政治體系核心地位的智庫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基金會所代表的新模式——黨派色彩鮮明、意識形態立場堅定,全面擁抱政治民粹主義轉向,資金來源直指共和黨選民——如今已然取代了卡內基基金會在一個多世紀前所開創的技術專家治理理念。
在外交政策領域,華盛頓智庫圈呈現的思想多元化格局或許值得肯定。新興研究機構和學者羣體提出了迥然不同的政策主張。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思想供給對民意需求的必要回應——民調數據早已表明,美國民眾對冷戰遺留的干預主義政策深感厭倦。
然而,這種觀點分化是以專業領域日益加劇的極化為代價的,智庫日益淪為政治贊助的工具。研究質量每況愈下,學術獨立性蕩然無存,思辨交鋒失去活力,這些都成為變革的犧牲品。事實上,智庫被政治活動家工具化已成為常態,當前態勢顯示這一趨勢短期內難以扭轉。
更為嚴重的是,特朗普政府同時對高等學府發起攻擊,這意味着在美國的學術界,能夠獨立從事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研究、不受政治干預的機構正變得越來越少。這種變化的衝擊波早已越出美國國界:這些頂尖學術機構素來享譽全球,其專家學者的觀點仍然備受關注,影響力有增無減。如今這些機構江河日下,研究水準每況愈下,勢必讓全球的研究人員和決策者痛失一座重要的智慧寶庫。

特朗普 資料圖:紐約時報
若從更宏觀的角度審視,智庫格局的變化更深層地反映了20世紀初以來美國國家體制的根本性轉變。這些老牌智庫的式微,或許預示一個歷史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技術官僚治國理念盛行,國家將專業知識的生產外包給具有重要政策影響力的獨立機構。
正如“2025項目”的主要策劃者之一保羅·丹斯(Paul Dans)在最近接受採訪時所言,國家體制的這種轉型正是本屆政府計劃的核心組成部分。丹斯宣稱:“我們必須徹底關閉進步主義時代的大門,方能重建真正的民主。”他進一步解釋道:“進步主義催生了一種思維模式,認為專家精英階層應當主宰普通民眾的生活,因為老百姓缺乏管理自身命運的常識。過去百年間,聯邦政府的整座大廈正是在這種反民主的理念指導下拔地而起。”由此看來,智庫的命運不過是華盛頓這場驚天動地的歷史鉅變中的預警信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