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歐樹軍 | 波蘭尼《大轉型》的世紀預言:當市場吞噬社會,我們如何自救?
guancha
上世紀80年代,王紹光教授曾兩次試圖將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引入中國,卻無人問津。彼時中國市場化尚未啓程,書中描繪的“市場社會”之痛顯得遙遠而陌生。三十多年後,經歷過市場化改革、技術異化、全球秩序動盪的我們,重讀這本1944年的經典,方覺其如手術刀般精準的洞見——它早已預言了我們正在經歷的撕裂與陣痛。
2025年上海書展前期,王紹光與歐樹軍兩位老師圍繞《大轉型》一書,進行了一場思想對談,深入剖析了波蘭尼的核心警示:市場並非“自然法則”,它是由國家力量塑造的制度產物。當市場肆意侵蝕,必然激起社會的自我保護。而脱離社會保護和市場規則落地所需的制度成本,“自由”只會淪為空洞的口號甚至災難。
《大轉型》像一部映照現實的鏡子,波蘭尼對“市場社會”的批判、對社會自我保護必然性的揭示、對“嵌入”倫理的經濟之呼喚,為我們理解自身困境、探索出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座標。它提醒我們: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
本次對話由活字文化和觀察者網聯合推出,感謝活字文化授權發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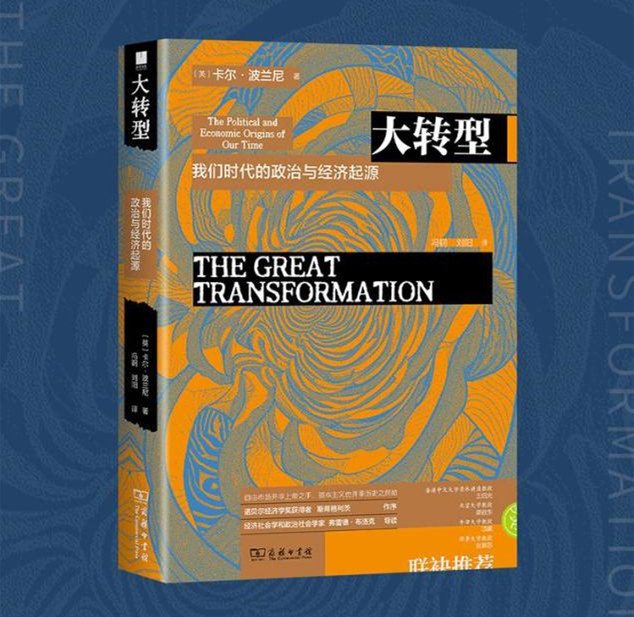
歐樹軍: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請王紹光老師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大轉型》這本書,這已經是這本書的第三個簡體中文版。這本書在中國內地的影響離不開譯者的貢獻,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跟這本書的其中一位譯者劉陽有關,他去年不幸離開了人世。我想首先請王老師介紹一下這本書引進翻譯的過程,以及您對簡體中文版的評價。
王紹光:卡爾·波蘭尼這本書我接觸得比較早,大概是1984年前後我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碩士研究生階段就接觸了。那時我已經在美國待了兩年,第一次有機會回國探親,當時就有這麼一種衝動,想把這本書帶回國內找人翻譯。那時候中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還沒有市場化,大家想象不到波蘭尼書裏描述的那些需要避免的局面,當時在中國還基本上沒有。這種書對當時的美國人來講是有迫切性的,因為里根當了總統,他在急劇推行市場化措施。而對中國來講,那時候市場化改革基本上還沒有起步,跟中國的相關性幾乎沒有,所以當時沒人對我這個提議有興趣。
又過了兩年,1986年我又回了一次國,那時候要回來做研究,待的時間比較長一點,我又一次向人推薦這本書,但同樣,這時候市場化的影響對人們來講是個遙遠的未來,根本沒有辦法想象,還是沒人有興趣。
當時跟我一起在國內做研究的,有兩位稍微左翼一點的美國學者。我們經常在聊天時會談到美國政治,他們會把這本書看得很重,我當時也想象不到未來有一天,這本書對中國的相關性會非常之高。
真正想到的時候,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我們經歷了大下崗,幾年內大概有六七千萬人下崗,這是人類歷史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下崗潮,那個時候市場化已經在急劇的推進。到了本世紀初,很多本來不是市場化的東西也開始市場化了,包括教育、醫療都開始市場化。這個時候人們再來讀波蘭尼這本書,就有了相關性。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在講課的時候就會更多地提到波蘭尼,2008年我還專門做過一次講座講《大轉型》這本書。對這本書,我早就希望有一箇中文版,但可惜最初只有一個台灣地區出的繁體字版,叫《鉅變》,當時大陸大多數人看不到。所以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劉陽和馮鋼翻譯的這本書,我覺得非常及時。這麼年輕的一位譯者,突然走掉了,我覺得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
波蘭尼和哈耶克的“對話”
歐樹軍:《大轉型》是一部非常好的比較經濟思想史的著作,它的寫法有點類似於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幾乎沒有提到法國,但又無時無刻不在拿美國和法國做比較。波蘭尼在這本書中也有類似的寫作方式,就是他幾乎沒有提到哈耶克,但實際上字裏行間又無時無刻不在和哈耶克進行思想的對話。這場對話發生在81年前,您怎麼評價這場對話在他們那個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價值?
王紹光:卡爾·波蘭尼這本書是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也是1944年出版的,我們今天很自然地會想象他們可能當時有一場辯論。更讓我們容易產生這種聯想的是,他們有一段時間都在維也納生活,所以如果有什麼維也納圈子的話,他們也許有機會碰到。但是他們兩個人的年齡其實相差不小,我懷疑他們不在一個圈層裏面。
當時是二戰的倒數第二年,二戰還沒有結束,人們會關心戰後世界到底會往哪個方向走。波蘭尼這本書更多的是解釋人們為什麼會走向這場戰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過了不久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這本書實際上是講戰爭的起源是什麼。他追溯到人類社會出現的一種新社會,跟人類歷史上的社會都不一樣,叫市場社會,他討論的是這個東西。

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
哈耶克那個時候也寫了這本書,更多地反映他在維也納學派裏面接觸到的一些老師的想法。我想説的是,這兩個人的書在1944年出版以後,實際上開始都沒有什麼太大反響,這是我的瞭解。一個書寫得好不好,會不會有重大反響,產生很深遠的意義,不取決於這些書本身的內容,而取決於這些書的接受者。我們用接受學的角度來講,書的接受者也在製造閲讀的內容,把自己的經歷、自己的感悟都帶到閲讀裏面去,就使得這個書的影響可能會變得更大一點。
這兩本書起到更大的作用是後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判斷他們寫這兩本書是不是為了辯論。我懷疑不是,可能僅僅是湊巧而已。這兩本書真正開始發生影響是後來的事情,我的印象裏,至少從波蘭尼這本書來講的話,里根上台後,新自由主義開始蔓延,是這本書開始產生很大影響的一個契機。就是他反對的東西現在開始出現了,他預測可能會造成惡果的東西現在開始出現,這時候他這個書的反應可能會更大一些。
哈耶克剛剛到美國的時候,其實也是不太受待見的,所以他到芝加哥的時候,各個學系都沒有收他,只是把他放到思想委員會里面去,當時經濟學系並沒有吸收他。他後來獲諾貝爾獎,很大程度上跟諾貝爾獎頒發時的那個時代有關,而不是這本書。
1944年這本書出版時,並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用谷歌的Ngram Viewer查詢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與卡爾·波蘭尼在文獻中出現的頻率,可以發現三點觀察:第一,1970年代中期以前,兩人出現的次數都不太多;他們真正受到廣泛重視,是1980年以後的事。第二,兩人出現頻次的曲線幾乎完全同步,這意味着,哈耶克受重視的時候,波蘭尼同樣也受到重視。第三,總體而言,幾乎在所有時段,波蘭尼出現的頻次都略高於哈耶克,這一點也許會出乎很多人所料。
人類社會不能變成一個市場社會
歐樹軍:今天似乎每個人都把市場作為一個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市場經濟、市場生活無處不在,但波蘭尼非常肯定地把自生自發的市場作為一個烏托邦,您認為他為什麼會這麼看?
王紹光:波蘭尼其實要反駁兩樣東西,第一個市場是自然的東西,波蘭尼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市場是創造出來的,是包括國家這些東西創造出來的。第二個波蘭尼最重要的不是要反對市場經濟,反對市場,他是要反對以市場原則來統治整個社會這樣一種情況,他叫作市場社會。

匈牙利哲學家卡爾·波蘭尼(1886年10月25日—1964年4月23日)
所以你看波蘭尼的書,他並不反對有市場,他只是説某些領域不能市場化。在日常的比如商品交換的領域,市場當然是好的,從古到今都有市場,中國也罷,外國也罷,都有市場。但波蘭尼的判斷是市場社會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到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開始出現市場社會這種可能性,這個東西是需要警惕的。
不能把市場的交易原則適用於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尤其點了幾個方面,比如自然環境不能把它市場化,貨幣不能把它市場化,土地不能把它市場化,有些東西你是不能把它市場化的。所以他更多的不是談市場本身,而是談市場本身不是自然而然的,市場社會的出現實際上是跟國家政策相關的,更重要的是他反對出現一個市場社會。
歐樹軍:這裏面有沒有對把逐利、獲利作為人類唯一動機的批評呢?或者説,市場經濟很容易導向這樣一種認識?
王紹光:“市場經濟是自然而然”這種理論,就隱含着市場是交換,交換的都是要互相獲利,你獲了利,我獲了利,在市場裏面的交易造成了所有人都從中間獲利,好像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波蘭尼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人類以前打交道,重要的不是獲利而是互惠。他講到了人類交往的一些其他原則,而且在人類發展的長期歷史中,這些原則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其實,我覺得只要觀察一下我們周邊的生活,就能夠體會到他這個觀點。剛才我講到1996年以後出現了六七千萬人的大下崗,這對很多家庭來説是毀滅性的,一家的經濟支柱突然一下失去了工作,不僅沒有了收入,而且也沒有了跟工作相關的一些保障,包括養老、醫療都沒有了。那時候怎麼辦呢?很多家庭實際上是靠家庭內部的相互接濟。相互接濟實際上就是波蘭尼在這本書裏面寫的互惠。就是人類從交易中間獲取最大的利益,這實際上是不自然的,是反人類的,它有存在的必要,有存在的可能性,但不能把這個原則變成整個社會的運作原則。社會的運作原則裏面還應該包括互惠,包括接濟。
我記得我以前講《大轉型》的時候也會引梁漱溟的話,講中國古代的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里面小家庭、大家庭連在一起,一家碰到困難以後要互相接濟。我很懷疑梁漱溟從來沒有讀過波蘭尼的書,但他的説法在很大程度上跟波蘭尼的説法是一一對應的。
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催生了政府幹預
歐樹軍:其實這是一種對於倫理型經濟的推崇,在這本書中,波蘭尼之所以被一些經濟人類學家所尊敬,也是因為他從文化人類學、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反思從倫理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所謂的“撒旦的磨坊”或者“脱繮的野馬”。
我們從這個意義上重新去理解這本書的結構,實際上分成三大塊,第一篇和第三篇開頭和結尾講的是國際體系、世界格局的演變,而且恰恰是距離我們今天一百年前的情況。中間第二部分是它的核心,就是市場經濟的擴張,“撒旦的磨坊”在不停地運轉,反過來就是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而政府的干預好像是這種雙向運動的產物,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波蘭尼在這本書中對於國家、對於政府的功能和作用的定位,他認為政府是被這些市場經濟所製造出來的問題,以及社會的自我保護訴求推着往前走的,是一個很被動的過程。
您怎麼評價對政府幹預這種比較被動、消極的看法?當然,現在政府似乎都越來越積極,越來越干預主義。
王紹光:波蘭尼的論點實際上也不是他自己創造的,在他之前也有人談到倫理和經濟的關係。實際上,古典政治經濟學裏也講物價。物價不僅僅是由交換貨物的稀缺或者充盈來決定的,很大程度上還有倫理的東西在裏面。如果對一個窮人要價太高,這個價格就不是一個符合倫理的價格,就不是一個正確的價格。所以古典經濟學裏已經有這些把倫理和經濟融在一起的成分。只是後來出現了自由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它説這個東西是可以分開的,人只要自私自利,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用這個原則做交往的話,就可以促進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但波蘭尼之類的理論家是反對這套東西的,他不認為是這個樣子。就是市場經濟或者説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永遠是嵌入在社會倫理這些原則上的,它不能完全脱離社會和倫理的基礎,這是他的觀點,這也是事實。即便我們完全不看波蘭尼的書,僅僅看歷史的發展,看歷史事實的話,好像也是如此。
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葉是第一次工業革命,這個時間是非常無情的,就是那些資本家們想方設法榨取所有工人最後一滴血的過程。我記得有一個統計數據,英國工人的預期壽命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不是上升的,而是下降的。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財富,照理説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人的預期壽命應該是上升的。但恰恰相反,因為有少部分人把好處都拿走了,很多人沒有拿到好處,而且受到了損害,他們占人口的大多數,使得整個人口的預期壽命是下降的。
這是很殘酷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19世紀中葉就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工人運動,出現了工人政黨、社會主義政黨、共產主義政黨。這些對社會的衝擊是很大的,你不做出反應,你這個體制可能就要垮台。包括像普魯士這樣的政權,實際上是很反動的,但像俾斯麥他也不得不搞出一點福利出來。俾斯麥搞福利的動機不是為了這些工人們好,他是説這是唯一能夠抵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種理念對人們的吸引的東西。
所以現在追溯福利國家的起源,往往會追溯到俾斯麥這裏,大家會覺得很奇怪,但他做出的反應或者開始出現反向運動,並不是他情願的,因為你不做反向運動,一股腦地往市場社會那個方向走,一定撞南牆,這個體制就會崩潰,所以就會出現反向運動。
當然,反向運動有可能是完全被動的,不得不這樣,像俾斯麥那樣子。但也可能是一個好一點的政府,比如説社會主義的政府,它可能會主動做出調整,及時出台政策,來回應以前市場化造成的極端化,進行糾正糾偏,然後出現反向運動,改善大多數人的福利,中國就是如此。所以主動還是被動,要取決於這個制度是什麼樣的制度。
民主的危機
歐樹軍:您剛才的這個提法,讓我想起波蘭尼在這本書中,把大規模的窮人羣體、赤貧羣體的出現作為所謂現代政治思想的共同起源,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都是因為處理這個問題而出現的。波蘭尼在比較了自由主義的處理方案和保守主義的處理方案之後,認為市場經濟成了市場資本主義的宗教,類似於基督教這種普世化的宗教,而歐文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工業社會的宗教,也因此贏得了巨大的號召力。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積極的、主動的、謀求自己正當性的政府,或者是回應社會自我保護訴求的政府,它有可能防止市場經濟過度侵蝕到其他領域,去恢復一種倫理經濟的正常狀態。或者説用我們更熟悉的説法,這種看上去被動的、看得見的政府幹預,如果不是一個跟哈耶克之間的對話,也可以視為是和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對話。
王紹光:這個可能還要回到1944年波蘭尼寫這本書之前,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是在做寫作思考準備。這個時候歐洲沒有福利國家,有些國家有一些福利政策,但是政府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微不足道,可能只有1%、2%而已,就是杯水車薪的感覺。所以波蘭尼寫這本書的時候,他是沒有一個福利國家作為參照系的,他的參照系是歐文這樣的人,但歐文並不是政府。歐文也是一個有錢人,一個資本家,他只不過有善心,憧憬一個大家都能受益的社會,他甚至在一些地方進行一些實驗,所有的人住在一起,有食堂、共同的俱樂部。
恩格斯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即來自於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東西。但馬克思主義會批評這些空想社會主義,因為歐文的實驗最後是失敗的。波蘭尼本人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他對馬克思的那些理論也不贊成,更傾向於歐文這樣的改良主義,反倒是波蘭尼的夫人是一位共產黨員,雖然她後來退出了共產黨。

空想社會主義(英文:utopian socialism)是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之一,準確的譯法為烏托邦社會主義,主要流行於19世紀初期的西歐,著名代表人物為:歐文、聖西門和傅立葉。
卡爾·波蘭尼後來到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他太太不能進美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有一條法律,共產黨員不能入美國。他太太是前共產黨員,也不能進美國,結果只有待在加拿大,波蘭尼就得在美國和加拿大之間來回跑。現在波蘭尼的女兒在加拿大,建立了一個研究所也是在加拿大。
再回頭説福利國家。福利國家的出現應該是二戰以後,我在很多文章裏面都引到一張統計表,就是各國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你一看這個數據就很清楚,二戰結束時,基本上歐美各國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都在5%以下,就是基本上沒有福利國家。真正出現福利國家是什麼時候?是二戰以後。因為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歐洲出現了蘇聯和東歐國家,在亞洲出現了中國、朝鮮、越南,在拉美60年代初又出現了古巴,有一個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這個陣營給在歐美地區生活的人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作為一個參照,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有生命力,經濟發展速度很好,人們有基本的福利,迫使歐美國家也不得不出台福利政策。所以回頭再去看統計數據也很清楚,到60年代,社會主義保障的支出佔GDP的比重可能達到10%,到了70年代可能達到了20%,到80年代可能達到了25%,這個時候就是歐美福利國家的黃金期。因為它在不斷地擴張,水平也相當高。
到了8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弱化,蘇聯的吸引力弱化了,東歐國家開始出現了顏色革命的初期階段,比如説波蘭團結工會。當時西方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支持力度已經很大了,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瓦解的跡象,這個時候新自由主義就開始出現了,並且越來越膨脹,福利國家的增長就幾乎停止了。所以80年代可能是福利國家最後的頂點,再往後這些國家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就沒有再往上增長了。
所以70年代中期,有三本書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本書叫作《財政國家的危機》,這本書第一頁就講現在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所有人都想要福利,但所有人都不願意多交税。福利是需要花錢的,尤其是醫療、養老都是非常昂貴的福利。要這些東西,就要有錢,就得靠税收。大家都想要福利,但都不想要税收,這就是財政危機。
第二本書是哈貝馬斯的《正當性危機》。西方的政治體制出現正當性危機,也跟福利國家有關。福利國家實際上是一種交換關係,我給你福利,你支持我的政治體制,這個政治體制就有了正當性。一旦這個關係開始有走下坡路的跡象,這個正當性的危機就出現了。
第三本書就是樹軍經常研究的亨廷頓和綿貫讓治、克羅齊在1975年出的一本書,就叫作《民主的危機》。這裏面講的也是同一件事情,老百姓都要福利,給我們的負擔太大了,結果造成了民主的危機。
亨廷頓提出瞭解決民主危機的兩條出路,第一條道路,有些事情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就是要把很多事情排除在民主決策以外,讓市場而不是政府決定——這就是後來英國的撒切爾、美國的里根走的路,就是自由主義道路。第二條道路,就是老百姓不要太關心政治了,也不要鼓動太多老百姓關心政治,老百姓最好不關心政治,這樣才能天下太平。這就是反向運動產生的原因,也是反向運動又走到另一個極端的原因,就是新自由主義。
今天歐美國家的民主又走向危機了,我覺得跟70年代的危機是連續的,是延續的,中間只是因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垮台,暫時性製造了一種幻覺,認為歷史終結了,就是福山1989年寫的《歷史的終結》。這種幻覺持續的時間大概有十幾二十年,到了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後,這種幻覺就開始破滅了,所以現在西方又出現了比70年代更嚴重的民主危機。所以這個反向運動不是説反一次就完了的,它會像鐘擺一樣來來回回走。政治體制會不會主動地應對這些挑戰,那要看政治體制的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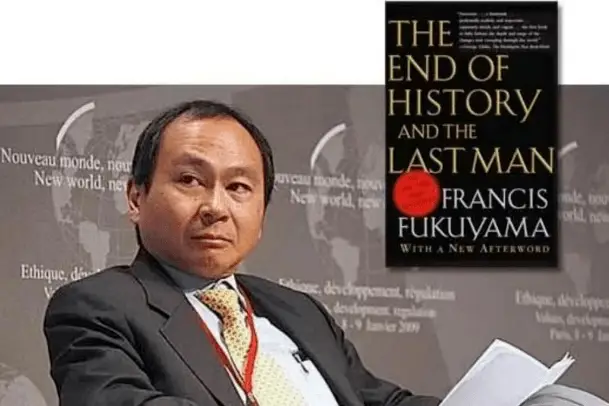
歷史終結論是日裔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於1988年在其所作的“歷史的終點”講座中提出: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美國,沒有例外
歐樹軍:您剛才也談到了美國的情況,在這本《大轉型》裏面,波蘭尼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提法,我覺得也是非常深刻和有創造性的,他認為美國憲法明確地把人民和經濟生活隔離開,因為憲法當中並沒有任何經濟條款,所以他由此判斷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把市場社會作為法律基礎的國家,市場社會成了美國的建國思想,因為它事實上是把人民和資本的權力以及資本家能夠發揮的經濟權力,隔離開了。您在美國生活了多年,您怎麼看待他的這樣一個判斷?
王紹光:美國也不是例外,市場嵌入在社會和倫理的網絡中間,也會出現反向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比於其他的歐洲國家,美國有幾個特點:一個是它的資源特別豐富,土地特別廣大,人口非常非常少。今天美國有3億人,但它在向西擴張的時候人口是很少的,那麼大的土地,那麼多的資源,這是得天獨厚的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哪怕窮人,給你一塊地,你也活得下去。所以在一定的時間裏,美國用憲法規定將經濟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並沒有問題。
但你走極端也是不行的,比如説美國以前出現過一個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19世紀末有人覺得美國的貧富懸殊太大了,應該像歐洲國家一樣引入個人所得税,進行財富的再分配。但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個人所得税是共產主義的税,不能收,這在歐洲國家是不會出現的,所以它是走到過極端的。但同樣的,當美國走到太極端的時候也會出現反向運動,比如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個進步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跟波蘭尼講的要保護社會、保護弱者的反向運動是連在一起的。
美國在20世紀初的時候,是一個極為糟糕的社會。田雷翻譯過一本書,叫《事故共和國》,裏面就提到美國在一段時間裏,資本家為了錢是完全不管工人的死活,傷殘率極高,工人在工廠打工是個很危險的事情。但是進步運動來了以後,迫使這個體制不得不做出一些反應。
還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就是美國以前沒有食品安全、藥品安全這個説法,那個時候吃東西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西方人愛吃香腸,後來有人發現香腸裏面經常有老鼠尾巴,因為生產香腸的那個車間亂七八糟的,老鼠跑來跑去,死老鼠也在裏面,全都打到裏面成了香腸。所以後來出了一本書,叫《The Jungle》,Jungle是森林的意思,在英文裏也形容一個地方無法無天,就好像進了森林一樣。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叫《屠場》,講的就是資本家為了掙錢,無所不用其極。這本書是1906年,由著名記者厄普頓•辛克萊寫成的,發表以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大家啥也不敢吃了,這樣就使得美國出台了《食品安全法》,也是一個反向運動。所以即使在美國這樣有得天獨厚條件的地方,反向運動可能會出現得晚一點,但還是不得不做出反向運動。
無政府主義和政府幹預主義的碰撞
歐樹軍:我們知道《大轉型》這本書的影響非常大,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也是您曾經的同事,他在1961年開始讀博士研究生的時候就非常喜歡這本書,甚至認為這本書影響了他一生的研究道路——就是在一個高度結構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如何去處理財富和權力,以及政治信念和階級相互的關係,包括如何培育平等的理念。
詹姆斯·斯科特本人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立場,不知道您如何判斷他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立場和波蘭尼認為政府幹預主義是必要的這種思想之間的關聯?
王紹光:提到詹姆斯·斯科特,我當年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時候,他是我的同事,比我年長許多,他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就是他出其不意地給你一個説法,你就覺得受到很大的啓發。比如説我開始研究認證,就是因為和他的一頓午餐。當時他突然問我人為什麼有名字?然後跟我講名字實際上是一種認證的標誌,認證為什麼很重要,我受到了極大的啓發。他是很聰明的一個人,確實受到了波蘭尼的影響。波蘭尼的影響後來被人歸納成叫作倫理經濟(Moral Economy)。斯科特本人有一本研究東南亞的書,標題就是《農民的倫理經濟》(Moral Economy of Peasant)。
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就跟波蘭尼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樣。無政府主義者可能相信政府是惡的,社會自身會做出反應,社會有自我保護的能力。但我不太確定我能同意斯科特的想法,就是你把希望完全放在社會自生自滅的自我修復上,我這裏講的社會是狹義的社會,就是社會力量,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社會羣體自我做出反應的這個社會。
我不太確定這種自我保護是不是比有國家干預來進行保護更好,我自己對歷史的解讀是由國家代表社會來進行保護,反應更快,力度更大。斯科特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樣的,他認為社會應該自我保護,國家干預往往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他大量的著作都是寫這樣的案例,這作為一種警示是有必要的。但認為這就是唯一的,是必須避免的,完全不能採取的,就走到另一個極端了。所以對斯科特我們可以表達無限的尊敬,他的很多觀點我們願意吸收,但也不能全盤地接受他的觀點。

美國知名政治學家、東南亞研究專家詹姆斯·C.斯科特(1936年12月2日-2024年7月19日)
歐樹軍:斯科特本人在一本小書裏面,英文叫《為無政府主義喝彩》,中文翻譯成《六論自發性》,把無政府主義作為農民、工匠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他認為這個東西有利於保存所謂下層階級自由、自主和互助的精神。我覺得這種對於國家高度標準化、清晰化的思維,或者他説的這種對極端現代化思維的反思,實際上是因為在美國式的高度資本主義化的世界裏,似乎只有這種途徑。
儘管這種途徑在政策的回應上很多時候也是無能為力的,但是這種把無政府主義視為保存下層階級的所謂自由、自主和互助精神的政治觀念,似乎又在其他的世界中也有很大的影響力,我覺得可能也是斯科特本人在很多學科有廣泛影響的一個原因。
王紹光:對,斯科特本人生活在美國,據我回憶,他的第一本書大概是關於腐敗的研究,這也是跟美國相關的。但他後來的研究基本上都跟東南亞國家相關,也包括中國西南部這些地方,就是有山的地方,他研究的很多都是有山的地方。所以他基於這些地區的研究,依然堅信或者加強了他的無政府主義信仰,很可能是他認為在這些地方的普通老百姓表現出來的自發創造性,對一些困難的應對是值得尊重的,這個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確實是如此。但如果把這些經驗放大到在任何社會里讓社會自己去自發地保護自己,這恐怕就走到另一個極端了。
所以如果我們讀斯科特的話,我覺得更多要吸收的是他給我們的警示作用,哪些事情不能走到極端,但同時我們也要看歷史,看我們自己的經驗,來得出結論。如果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它做出回應來保護社會,可以更高效,速度更快,效果更好,那也是一個好的政府。這就是我們需要一分為二來吸收斯科特的思想。
自由是有代價的
歐樹軍:可能也許在我看來,斯科特是吸收了波蘭尼這種對於所謂社會的自我保護訴求,他是説社會各個階層在自身權力和利益受到傷害之後,都會自發地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自我保護,所以他比較推崇這種下層的抗爭和互助。
談到這一點,我想起另外一位美國政治社會學家叫帕特南,他2020年出版了一本書叫《浮沉世紀》。他這裏面有一個主線,美國經歷了從鍍金時代到新鍍金時代,就是所謂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觀念的反覆更替。斯科特講的無政府主義的互助,波蘭尼講的社會各個階級的自我保護訴求,實際上都是一種集體主義精神的反映,就是階級內部的互助,和各個階級之間無形地形成了一種自我保護的訴求。
這是不是也反映在波蘭尼對人的自由究竟是什麼的反思上?他講應該對人類社會的自由有一個新的理解,就是除了對所謂社會和死亡的理解之外,還有一個對自由的理解。但是這個自由顯然和個人主義自由是不一樣的,我記得他對自由的定義是説只有當每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存在某種責任,為他人創造更多自由的時候,人類社會才會有真正的自由。我不知道您怎麼看待他的這種自由觀?
王紹光:我是很怕談自由的,因為幾乎每100個人至少有120種自由,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去談。因為你談的自由,跟這個人談的自由,那個人談的自由,是不一樣的,所以很難產生對話。剛才你提到帕特南,帕特南他關注的事情都跟civil society有關係,這個civil society我們中文把它翻譯成公民社會,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公民會社,而不是公民社會。
他關注的是在社會里面存在一些團體,就是會社。他早期研究意大利民主,發現意大利哪些地區這種會社比較多一些,民主效果就好一點。他後來研究美國,覺得美國現在衰亡了,很重要的是公民會社沒有了。以前美國人經常會結成很多這樣的公民會社,但現在這個東西慢慢瓦解了,使得美國整個社會構成的細胞開始破滅,開始瓦解,所以他關注的是這個東西。
如果説帕特南跟斯科特、波蘭尼有什麼相關之處的話,就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比較信任社會的修復能力,或者會社的自我修復能力。不同之處是,波蘭尼生活的時代還沒有國家干預提供大規模福利保護社會的先例,所以他還不能設想出這樣的東西。
斯科特和帕特南他們是經歷過的,他們依然這樣相信。所以還是我剛才説的這個觀點,就是他們説的東西都有道理,他們覺得應該警示的東西我們都應該警示,這個社會如果有自我的修復能力,那樣最好,讓它起作用,不要去阻礙它。但同時如果它不夠的話,政府就應該出手保護社會。所以這樣看,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更全面一點。
歐樹軍:也就是説人的這種自由,某種程度是離不開政府幹預的保護。這也是一種新的權利觀念。
王紹光:我20年前經常推薦一本書,叫《權利的成本》,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很強調自由的美國學者,突然去研究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俄羅斯轉向市場經濟,轉向所謂的民主以後,大家都有自由了。但當時的俄羅斯,監獄裏面亂七八糟的、無法無天,這種情況下自由是有代價的,你如果沒有錢去建立很好的監獄體系,沒有錢去建立各種各樣制度,這個自由就是亂七八糟的,所以自由是有代價的。我們抽象地談自由,談怎麼去實現自由,可以一直談下去,但當你真正要把自由落地,讓更多人擁有自由,那就要靠具體的措施和具體的制度。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前幾年給外國人上課,外國人對於有監控鏡頭這件事情非常敏感,他覺得這剝奪了自由,但中國人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嚴重,而且你會發現在中國生活了一段時間,比如三年、五年以上的外國人,他的感受也不一樣。我看到外國人説這個東西給我了自由,我晚上一個人在外頭散步的時候,我不用擔心會不會受到攻擊,我的東西會不會被搶,如果是那樣,我反倒是失去了自由。所以自由這個東西是要落地的,你抽象地談自由,監控也不要,警察也不要,那是最自由了,但在那種情況下誰有自由?只有暴徒、小偷才有自由。

《大轉型》的現實意義
歐樹軍:《大轉型》這本書有很多提法,其實放到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對於所謂人被變成一個勞動力然後又被商品化的一種反思,或者説是當代社會的反向自我保護運動?如果説是的話,《大轉型》這本書是不是也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理解當代很多社會問題的一個比較適用的理論工具?
王紹光:對,我想只要有人相信靠市場平等交易就能解決問題,波蘭尼這本書就還有實用價值。其他你剛才提到的那些東西也是一樣,就是在這些領域裏面,政府有些時候其實是需要謹慎的,斯科特講的也不錯,你是不是每聽到一句不滿都要出手?你要平衡各種利益,長期的、短期的,少數人的、多數人的,都要平衡。所以有些時候沒有出台應對的政策,不是説這些地方不應該出現,恐怕僅僅是時間還沒到而已。所以你剛才提到所有的那些問題,在我看來是需要解決的。什麼時候會解決,不知道。但我有一個很簡單的預判,就是即便這些問題解決了,新問題依然會層出不窮。
歐樹軍:最後一個問題,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處在一個非常嚴重的撕裂階段,這個撕裂在思想界尤其在政治學界被表述為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在政策層面有一個所謂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衝突,在政治哲學層面可能存在一個現代性和對反現代性的反思。
如果我們回到《大轉型》,波蘭尼也有對文明的理解,他用政治經濟的因素去定義文明,尤其是把19世紀的西方文明定義為一個自由競爭的自生自發的市場經濟文明,所謂的大轉型就是它造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了美國的小羅斯福新政、蘇聯的新經濟政策,還有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他把這三種政治上的方案都視為是所謂以自生自發的市場觀念為核心的19世紀西方文明大轉型的一個產物。
在這個意義上,今天是不是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波蘭尼所面對的那樣一個時代環境中?如果説有這樣一種時代的相似性或者時代精神轉型的需求,我們今天重新去讀波蘭尼的《大轉型》,您覺得有什麼樣的啓發?
王紹光:你剛才一直在用“大轉型”這個詞,據我所知這個書稿寫好以後,它的書名不叫《大轉型》。我現在記不太清原來的書名叫什麼,但不是《大轉型》。是書商為了賣書建議他改為《大轉型》。如果看這個書本身的文本,“大轉型”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非常之少,幾乎沒有出現,包括反向運動都很少,實際上是人們讀了之後歸納出來的。
“大轉型”到底是什麼含義?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一個解讀就是人類以前沒有市場社會,只有市場經濟,從市場經濟變成市場社會,這是一個大轉型。但這是一個不好的大轉型。我們今天讀《大轉型》,更多是期待一個好的大轉型,就是從一個被蹂躪毒打的社會變成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社會,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期待讀進了這本書裏。
今天的社會跟一百年前有一樣的地方,也有太多不一樣的地方。一百年前的1925年,蘇聯才剛剛出現,還沒有取得任何成功,蘇聯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後才真正展現出它的制度優越性。所以在那個時候,還很難想象有“另一個世界”。但今天,在經歷了福山講的“歷史的終結”、撒切爾講的“你別無選擇”後,我們可以做出回應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儘管蘇聯失敗了,但它有過成功的經驗,有過成功的時期,而且這個時期還比較長。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的社會主義國家,一百年前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比非洲大多數國家還要貧窮,情況還要糟糕。但我們現在提供了一個可以説比較成功的經驗,這個經驗也許對全世界其他國家也有參考的價值,所以我們可以展示另一種模型、模式是可能的,我們現在並不是十全十美,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但畢竟我們克服了更多的、更麻煩的困難,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所以比起波蘭尼,我對人類社會的走向會更樂觀一點,而且我們的走向會更具體一點、更特定一點。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可以更自信地講這條路是走得通的,這跟一百年前是很不一樣的。
歐樹軍:您剛才這個提法讓我想起阿瑞吉寫的《亞當·斯密在北京》,他那本書似乎可以説是續寫《大轉型》的思想方案,提出了中國代表了一個非歐洲民族和歐洲民族能夠真正平等競爭、真正和平相處的可能性。
王紹光:是的,亞當·斯密其實也是被嚴重誤讀的,亞當·斯密的書裏面也有很多地方會談到倫理的問題。反倒是後來從亞當·斯密裏發展出來所謂的自由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這些東西都剝離掉了,好像亞當·斯密僅僅是一個強調市場競爭的人。但其實亞當·斯密也談到國家建設和國家能力的重要性,這些都被後來的很多人剝離出去了,認為這不是亞當·斯密的重心,這是隻讀《國富論》其中某一些章節而不讀其他的章節,也不讀亞當·斯密其他書的人產生的誤解。所以《亞當·斯密在北京》,絕對不是那些人理解的亞當·斯密,而是一個更飽滿的亞當·斯密。
歐樹軍:我們今天就到這兒,謝謝王老師。
王紹光:好。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