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蒂斯塔:西方主導貨幣金融體系已被扭曲,金磚須認真考慮替代機制-保羅·巴蒂斯塔
guancha
在特朗普“解放日”對等關税威脅下,許多國家競相與美國達成協議,而巴西、印度、中國和南非等金磚國家則選擇“硬抗”,這會對全球多極化格局產生怎樣的衝擊?
本期《PacificPolarity》節目邀請到巴西經濟學家保羅·諾蓋拉·巴蒂斯塔。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巴西執行董事(2007-2015年)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總部上海)創始副行長(2015-2017年),巴蒂斯塔深度參與國際金融治理,並著有《金磚國家及其創建的融資機制》等專著。其雙重經歷為審視當前全球金融權力結構提供了獨特視角。
在巴蒂斯塔看來,特朗普的“對等關税”政策刻意針對金磚國家(如巴西、印度關税高達50%,中國、南非30%),其動機源於將金磚視為“對手”和“反美力量”,旨在打壓其挑戰美元霸權和創建替代貨幣的努力,此舉客觀上可能強化金磚內部凝聚力。
其次,IMF與NDB存在根本性差異:IMF由西方(尤其美國)控制,淪為地緣政治工具;而NDB由金磚五國主導,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他尖鋭地指出,IMF自2010年投票權改革後15年停滯不前,西方背棄改革承諾,根源在於將IMF視作政治武器,不願賦予中國等新興大國應有話語權,其治理結構已“高度畸形”。
巴蒂斯塔對IMF改革徹底失望的判斷,以及他對NDB等替代機制發展的強調,指向了全球南方對現有由西方主導、缺乏公平性的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增長的不滿與離心力。這種結構性矛盾,正推動着國際金融權力格局加速重構,新興力量尋求建立更加公正、不受單一霸權支配的新秩序成為必然趨勢。

資料圖:保羅·巴蒂斯塔(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
**李澤西:**歡迎收聽本期《PacificPolarity》。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保羅·諾蓋拉·巴蒂斯塔(Paulo Nogueira BatistaJr.)。他是一位巴西經濟學家,2007年至2015年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負責巴西及其他國家事務。他也是新開發銀行(又稱金磚銀行)的創始人之一,該行總部設在上海,他在2015年至2017年間擔任副行長。他著有七本書以及多篇經濟論文和出版物,包括《金磚國家及其創建的融資機制》和《IMF改革的出路》。保羅,很高興你能來參加節目。
**巴蒂斯塔:**謝謝你,很高興參與對話。
**李澤西:**也許我們可以先從最近的新聞談起:特朗普的“對等關税”正式生效。人們注意到的一點是,無論是否是有意為之,金磚國家似乎受到了特別沉重的打擊。埃文·費根鮑姆(Evan Feigenbaum)最近指出,許多國家爭相與美國達成協議,而巴西、印度、中國和南非則選擇“硬抗”。他認為,特朗普在這方面對金磚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你對此怎麼看?
**巴蒂斯塔:**我認為金磚國家確實受到了特別嚴重的打擊。巴西和印度的部分商品關税高達50%,有些甚至略高。南非遭遇了30%的關税,中國目前也是30%。至於俄羅斯,自烏克蘭衝突爆發以來就一直處於制裁之下,因此幾乎沒有貿易往來,或者至少沒有屬於特朗普所理解的關税範疇內的貿易。
所以是的,我認為金磚國家正被刻意針對,而特朗普本人也給出原因。他不止一次表示,他將金磚國家視為對手、敵對力量、反美力量。他一直強調,金磚國家必須放棄挑戰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以及放棄創建替代貨幣的嘗試。

近日,巴西總統盧拉在種植葡萄(受關税影響的商品之一)時拍攝了一段視頻,並向特朗普喊話,建議他來巴西聊聊 社交媒體
最近他的一些舉動也讓人意外。以巴西為例,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因為特朗普提出的理由與貿易沒多大關係;美國對超過一半巴西出口美國的商品徵收50%的關税,主要是基於非貿易因素,比如所謂針對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特朗普的密切盟友、甚至可以説是附庸——的“政治迫害”;他還提到巴西最高法院對大型科技公司的限制措施;以及對巴西即時支付系統“PIX”削弱美國信用卡品牌(特別是Visa和MasterCard)市場份額的擔憂。這是個很奇怪的局面。
至於印度,這在戰略上尤其重要。特朗普突然對印度下重手,對金磚國家很關鍵。眾所周知,印度自認為與美國有特殊關係,這影響了它在金磚內部的態度。但現在看來,這種所謂“特殊關係”或許只是印度在“意淫”,因為這並沒有阻止美國對印度徵收高達50%的關税,這將幾乎切斷貿易。因此,特朗普雖然對貿易和經濟造成了很大傷害,但他可能在無意間加強了金磚的凝聚力,我希望接下來局面將朝這個方向發展。
**李澤西:**聊聊你的背景吧,你曾在IMF和新開發銀行(NDB)工作過,這兩個機構的共同目標都是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貸款,但在架構和運作上有很大不同。你在這兩家機構都擔任過領導職務,你認為它們在實際運作中最重要的差別是什麼?
**巴蒂斯塔:**這兩個機構的性質不同;IMF主要致力於為面臨國際收支或其他經濟困難的國家提供國際收支支持和宏觀經濟支持。而總部設在上海的新開發銀行在性質上更類似世界銀行(World Bank),是一家發展銀行,其主要職能是為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項目提供支持。NDB是我們金磚國家在2012年至2014年間談判建立的,旨在替代世界銀行,而不是IMF。
但IMF與NDB最大的區別在於政治屬性。IMF由西方,尤其是美國及其盟友控制,是西方的政治工具;而NDB則是由發展中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建立的銀行,由五個創始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共同控制。所以從政治意義上講,它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機構,目標與總部設在華盛頓、由西方主導的機構(主要是IMF和世界銀行)有本質區別。
**李澤西:**在IMF時,您在2008至2010年間推動了改革,將投票權向發展中國家傾斜。然而,自那之後,儘管全球經濟力量繼續從“全球北方”轉移,卻再無進一步改革。您最近評論説,缺乏進一步改革的一個關鍵原因是,任何新的改革都可能增加中國的投票權份額,而西方國家會反對。那麼,西方是否有可能提出一種改革方案,專門增加小型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以發達國家為代價),同時讓作為新興超級大國且部分地區高度發達的中國,其投票權基本保持不變?發展中國家對此會有何反應?這又會如何影響金磚國家以及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互動,尤其是在您提到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對潛在世界新秩序感興趣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對華盛頓主導的開發機構缺乏改革感到不滿?
**巴蒂斯塔:**我有機會參與2008和2010年的改革,正如你所説,這些改革將投票權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即從發達國家轉向全球南方。但這些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治理結構。中國的份額增加了,巴西的份額也增加了,還有其他一些國家,但該機構依然由西方控制,基本上是由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主導。正如你所説,自2010年以來,15年間毫無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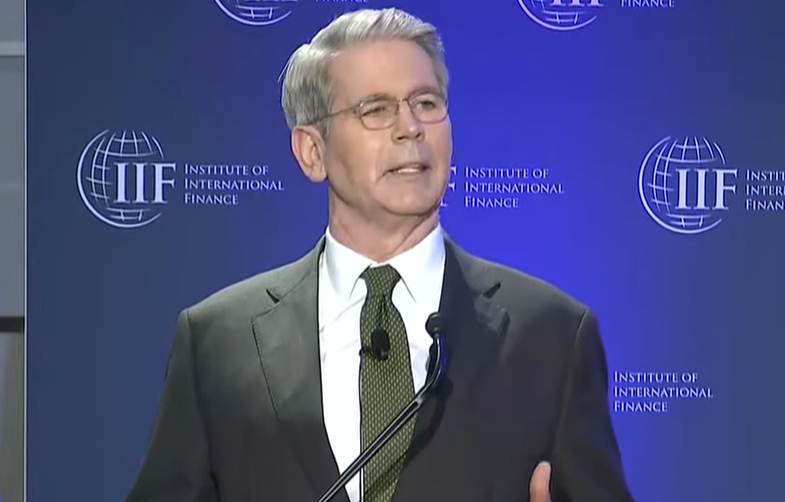
今年4月,美國財長貝森特“炮轟”IMF和世界銀行“同中國走得太近”
在這段時間裏,西方國家——歐洲人和美國人——背棄了他們推動IMF進一步改革的承諾。這些是領導人層面做出的書面承諾,卻被西方人卑劣地忽視。我記得在執行董事會的會議上,我質問過美國人和歐洲人,當時的行長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我對他們説:“你們現在的説法與領導人簽署的文件完全不符”。但他們的反應就像自己什麼都沒承諾過一樣。
金磚國家就此開始着手創建自己的機制——設在上海的新開發銀行以及應急儲備安排(CRA)——絕非巧合。這兩個機制正是在我們遭遇西方重大背叛後建立的。
改革已經停滯。讓我再補充一點:不僅IMF改革15年停滯不前,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IMF和世界銀行都不可能出現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原因是西方國家堅持控制世行和IMF,認為它們是政治武器、地緣政治工具。
你提到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至少可以在不觸碰西方反對底線的情況下,增加小國的投票權?理論上是可以的。在IMF的現有架構中有兩種方法:一是增加基本票數(basicvotes),這樣所有小國,無論發達還是發展中,都會受益;二是提高配額公式中的壓縮係數(compressionfactor)以傾向於小國。
但這些措施的意義有限。為什麼?因為它們必須設計成不觸動IMF架構中的一個基本原則:美國是唯一一個擁有否決權的國家(重大決策需85%多數,美國份額必須始終高於15%)。任何讓美國份額跌破15%的改革,都會被美國自動否決。
關於中國,你説得對。中國按任何指標來看,都是IMF和世行中最缺乏足夠代表的國家。因此,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必須大幅提升中國在IMF和世行中的份額。但美國和歐洲願意嗎?不,他們視中國為主要對手,不願在自己掌控的機構中給中國更多空間。所以,中國將繼續在IMF和世行中份額不足,這一點不會改變。
當然,我並不是説IMF無法改進運作,它是可以的。我去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一些我認為可行的部分調整,這些調整不會觸碰美國和歐洲的否決底線。其他人也有類似提議,但這些調整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治理結構。
這正是我們發展中國家、金磚國家需要思考替代機制的原因。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設在上海的新開發銀行,也需要推動應急儲備安排變得更有實效。在最近於里約召開的金磚峯會上,這方面有了一些進展,因為領導人在《里約宣言》中對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提出了有益的指導意見,如果落實,將有助於讓它們比現在更有意義。
**李澤西:**我之所以會這樣提問,是因為我覺得,既然西方目前似乎越來越專注於遏制中國,那麼他們或許願意考慮推動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的改革,以便拉攏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站到他們一邊。顯而易見,過去三四年裏,西方——尤其是美國——越來越多地談論“全球南方”;與此同時,中國也同樣重點關注全球南方。那麼,這是否會給西方帶來動力,特別是向較小的全球南方國家賦予更多權力呢?
**巴蒂斯塔:**我不這麼認為;他們基本上是希望在現狀下凍結治理結構凍結,然後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如果需要的話,會有選擇性地援助一些全球南方國家;但請注意,是有選擇性的。這意味着不會一視同仁。全球南方國家能否獲得援助,取決於它們是否親近西方、親近美國和歐洲。比如,一個國家如果很獨立、試圖走自己的路,那它可能在獲得世行和IMF支持方面遇到很大困難,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相反,如果某個國家對美國和西方很順從,比如現在的阿根廷,那它可能會更容易從IMF和世行獲得支持。
從地緣政治以及我們作為金磚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獨立性來看,這種狀況是不可接受的。這種問題在我任職時就存在,即缺乏公平對待。比如,烏克蘭因為被需要用來削弱俄羅斯,所以可以得到它想要的一切;無論它的宏觀經濟政策多麼放縱,依然可以從IMF和世行獲得資金。反觀塞爾維亞,雖然可能需要支持,但因為被認為與俄羅斯走得太近,它的任何請求甚至都不會進入執行董事會討論。這是一個高度畸形的局面。坦率地説,我感到遺憾,因為我在2007到2015年任職期間曾努力推動IMF轉型為21世紀的機構,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未能實現這一重大目標。我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這個目標也無法實現。
所以,我再強調一遍,金磚國家,尤其是中國——中國的組織性更強——必須認真考慮建立替代機制,不僅是替代世界銀行和IMF,還要替代整個由西方主導的貨幣與金融體系,因為這一整套體系已經被扭曲,變成了權力、打壓、歧視的工具,這種現象隨處可見。
**李澤西:**全球南方——甚至不僅僅是全球南方——常見的不滿之一是,IMF的貸款附帶許多條件。IMF可能會辯解説,這些條件是必要的,因為他們希望讓受援國走上更好、更可持續的增長軌道。但有批評認為,這麼做可能是為了推動華爾街利益,比如方便資本外逃、削弱受援國與西方企業競爭的能力。作為局內人,您認為IMF堅持附加條件的背後原因是什麼?您覺得這種做法會改變嗎,畢竟在全球南方很不得人心?
**巴蒂斯塔:**我同意你對IMF官方説法和批評者觀點的總結,這兩方面都各有幾分道理。作為一個機構,IMF在放貸時必須確保借款國有能力償還,這就意味着它必須看到這些國家在執行可持續的經濟政策,就像你説的那樣。
另一方面,批評者的觀點也對,因為IMF在施加條件時,往往無視各國的特殊性,忽視政治侷限性。尤其值得強調的是,IMF的做法高度不公正:如果你是西方的寵兒,即使執行了很多宏觀經濟上有問題的政策,也依然可以在IMF那邊過關;但如果你很獨立,被華盛頓、布魯塞爾、倫敦、巴黎看不順眼,那即便有一個紮實的調整方案,也很難獲得支持。
這種缺乏公平性的現象嚴重到足以削弱IMF整個理論基礎——理論上沒錯,資金不能無條件給,必須伴隨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但當你在內部工作多年,就會發現這套理論在實踐中是極度失衡、不公平的,導致機構的公信力受損。
而這種不平衡之所以可能存在,完全是因為IMF的治理結構畸形,使其實際上變成了一個“北大西洋貨幣基金組織”,而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如我的印度同事拉克什·莫漢(Rakesh Mohan)在執行董事會上説的那樣:這是一個北大西洋貨幣基金,不是國際貨幣基金。這就是現實。

新開發銀行行長羅塞夫表示,如果更多全球南方國家能夠積極學習中國的現代化經驗,加強國際合作,將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微信公眾號“新開發銀行”
我們必須停止對改革的幻想,這種變化不會發生。我們可以繼續重複那些關於讓IMF和世行更具代表性的標準説辭,但要清楚,這不會實現。我們必須在充分了解華盛頓體制內哪些事情可能發生、哪些絕不可能發生的前提下,制定我們自己的行動方案。
**李澤西:**新開發銀行(NDB),又稱金磚銀行,也面臨代表性問題:五個創始成員的集體表決權比例不得低於55%左右。您在一次採訪中指出,這無疑會妨礙吸納新成員。為什麼會這樣設定?這是為了制度性地鞏固創始成員國的權力嗎,類似於你之前説的西方對IMF的掌控,只是那是不明言的安排,而這是放在明面上的設計?
**巴蒂斯塔:**我同意,這目的是為了鞏固五個創始成員國的權力。但我認為這也是我們當初犯下的一個錯誤:55%的最低比例實在太高。這種架構下,銀行或許只能吸引一些不太在意表決權的小國,它們把NDB當作融資來源;但要吸引像印尼這樣的大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就很困難。印尼是世界人口前五、GDP前十的大國,為什麼要接受比南非低得多的份額?南非無論從國土、GDP還是人口規模都遠小於印尼。要吸引印尼、土耳其這樣的國家,在這個架構下很難實現。我不認為這就是擴員不力的唯一原因,但它確實是個重要因素,源於我們當初談判時的失誤。
**李澤西:**關於貸款附加條件,NDB一直強調自己做法與IMF相反,不對貸款附加任何條件。這是否會增加資金被管理不善的風險?理想的中間路線是什麼?
**巴蒂斯塔:**其實並非完全如此。我們的初衷(寫入了戰略文件和章程)是尊重借款國自身的政策框架,不像IMF或世行那樣去“改革”別國經濟結構。我們會設定項目條件、監督項目進展,但這是以項目為導向,而不是干涉宏觀經濟政策。我們不是去“拯救國家”,而是幫助國家、尊重它們的政策選擇。
但這種理念是否落實?我不清楚。因為NDB的一個軟肋是透明度很低,比之前的銀行還不透明,這並非我們的初衷。外界很難了解項目運作的細節,這值得研究者去深入調查。
**李澤西:**您作為銀行創始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為什麼您提到的很多設想沒有落實?是政治作梗嗎?還是當時沒想到這些問題?
**巴蒂斯塔:**建立一家全球多邊開發銀行是一項艱鉅工程,需要“中國式耐心”。2015年我搬到上海時,我們有很多目標,但10年過去,許多都未實現。例如,成員國目前只有10個(5個創始+5個新成員),最近哥倫比亞加入是個亮點,但離真正的全球銀行還差得遠。
另一個目標是用本幣開展業務,而不僅限於美元,這有一定進展,但NDB仍以美元為主。現任行長、巴西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正努力推動本幣結算和擴員,我希望她能成功。
但事實是,10年後銀行仍缺乏透明度,很多職位長期空缺,項目運作情況不明,成員數量過少。即使有55%的創始成員國比例限制,我們也完全可以吸納更多小國,但沒有做到。為什麼?需要調查。我相信未來10年可以比前10年做得更好。
**李澤西:**您剛剛提到可能會推動一些制度改革,但顯然這會很困難,因為這需要各國達成共識。您認為這仍然有可能嗎?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繞過這個障礙?
**巴蒂斯塔:**您會建議哪些制度改革?具體是指什麼?
**李澤西:**比如説55%的最低比例。
**巴蒂斯塔:**要改革《章程》需要經過一個程序,這個程序會涉及到所有成員國(目前是10個國家)的議會批准,所以這是一個緩慢而艱難的過程。如果我們要走這條路,我建議仔細審視《章程》中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後一次性提出,因為過程非常難推進,所以最好做成一個整體方案。我希望這個方案能夠設計得非常好,因為説實話,除了個別一兩點,我認為《章程》是成功的。我記得我在上海時,《章程》確實幫到了我,寫得很清晰。
當然,也可以挑出一些可批評的地方。你提到的55%最低比例,確實是一個痛點。但總體上《章程》沒問題,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修訂。我們真正的問題是“憲法以下層級”的,也就是銀行內部的一些制度性問題,這些問題即便改革《章程》也無法解決。

2025年7月7日,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總統盧拉在第17屆金磚國家峯會新聞發佈會上講話。 視覺中國
**李澤西:**您能詳細談談,您認為這些問題該怎麼解決,以及為什麼在頭十年裏沒有解決嗎?
**巴蒂斯塔:**一個是憲法層面的,也就是《章程》;另一個是銀行內部的規則和慣例,這些不完全依賴《章程》。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首先,我不太理解為什麼金磚國家沒有派出最優秀的人才到銀行。很多被任命到管理層或其他職位的人,並不理想。因為新開發銀行需要的是既有技術能力,又有地緣政治視野的人,要明白我們創建新開發銀行的目的,不是去複製一個世界銀行,或者其他西方建立的傳統多邊銀行,而是要做出不一樣的東西。但有這種認識的人,也必須技術能力上過硬。我不確定我們派去的人能同時滿足這兩點。
我不想點名,但我基本認為銀行領導層缺乏對這家銀行應有意義的認識。它不是一個例行事務,不是給來自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國的人提供高薪職位的機會,不是這樣的。這是一家昂貴的銀行,成員國投入了大量資金,所以必須有所產出。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任命既有技術能力,又有堅定地緣政治使命感的人,而這點我們沒有做到。
這還涉及一個比較微妙、難以解釋的問題:管理層對銀行負有職責,行長和副行長必須為機構本身服務,而不是充當各自國家的代表。這一點非常重要,但在實際中經常被混淆。我見過一些副行長在銀行中完全把自己當作所在國的代表。這實際上是違法的,但確實發生了。事實是,NDB經常不遵守自己的治理規則。
我現在直言不諱,我們沒必要把問題藏着掖着,自己假裝不存在;我們必須正視過去十年的不足,才能在未來十年取得進步。我對未來是有信心的。如果你去上海,可以參觀NDB漂亮的大樓,裏面有大約100名員工,聲望很高。中國國家領導人最近訪問了銀行,這是史無前例的;迪爾瑪·羅塞夫總統還獲得了中國政府授予的最高榮譽勳章,這顯示了中國政府對她本人以及她所領導的銀行的尊重。所以,這家銀行未來十年完全有潛力成為非常重要的機構。我希望我們不要辜負這個潛力。
**李澤西:**我從其他渠道聽説,行長和副行長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各自國家的代表。比如,迪爾瑪·羅塞夫的第一任期,其實是在完成上一位巴西籍候選人的任期。上一位候選人是由博索納羅任命的。後來盧拉總統當選,就用迪爾瑪·羅塞夫取代了前任候選人,成為他自己推舉的行長人選。這基本上就是直接發生的,替換為羅夫塞當時不需要任何人投票認可,她今年才真正經過選舉。如果明年巴西大選反對派獲勝,他們也可能會換上自己的人選。這樣一來,這些職位實際上就是各自國家的代表,而不是大家選的那個人。您覺得這是個問題嗎?您怎麼看?
**巴蒂斯塔:**這是一個問題。我來解釋一下。法律規定和現實政治之間存在差異。比如説,按照法律,IMF行長和副行長應當只是基金組織的官員,而不是其原籍國的代表。這是法律層面。那麼政治層面呢?政治層面在於,作為一種不成文的規則,IMF的行長總是由歐洲人擔任,而世界銀行的行長總是由美國人擔任。這並不是偶然,美國和歐洲人非常清楚IMF行長和世行行長的國籍是有意義的。所以他們堅持這一不成文的規則,完全不會改變想法。法律上,IMF和世行的管理層不是國家代表,但政治現實是:如果IMF行長是法國人,這對法國有意義;如果世行行長是美國人,這對美國有意義;如果IMF的副行長是中國人,這對中國也有意義。
在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的情況中也是如此。我們在起草《協定條款》時也遵循同樣的原則:行長和副行長只對銀行負責。但在實踐中,這一原則並沒有嚴格遵守。由於我們這些國家在處理這類問題上缺乏經驗,管理層中有些人表現得非常粗鄙。舉個例子,來自俄羅斯的副行長在任10年,直到現在才被替換,他在銀行內部的行為完全就是作為俄羅斯政府的代理人,完全不加掩飾。
這種現象部分是因為NDB實際上沒有常駐董事會,所以各國往往把副行長和行長視為本國代表,這違反了銀行的法律架構。正確的做法是,即使你是俄羅斯人、中國人、巴西人、印度人、南非人,你與本國政府保持密切聯繫無可厚非,但必須把所管理的機構利益放在首位,考慮整個機構,而不是隻考慮它對自己國家的作用。建立一支能理解這種微妙之處的高層官僚隊伍,是一項挑戰。
再説巴西的例子。根據輪值規則,從2020年起我們有權任命銀行的第二任行長。當時巴西執政的是博索納羅政府。説實話,博索納羅政府很糟糕——如果你覺得特朗普是個差勁的總統,那你也會覺得博索納羅很糟,因為他就是特朗普的粗俗版模仿者。不出意外,博索納羅任命了一位完全不具備資格的人擔任行長,馬科斯·特羅約(Marcos Troyjo)。他的表現非常糟糕,因為他基本不在銀行工作,大部分時間不住在上海,最初是因為疫情,後來就成了習慣。

8月5日,巴西極右翼議員抗議最高法院逮捕博索納羅,一度導致立法會議停擺
2022年盧拉贏得大選,2023年開始執政後,得知這一問題:博索納羅任命的巴西行長根本沒在履職。於是巴西政府向特羅約傳達了希望他辭職的意願,並準備了一位極有分量的候選人:巴西前總統。當巴西成功説服特羅約辭職,並任命前總統來完成巴西剩下的三年任期時,這立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升了NDB的國際形象。這顯示出巴西對新開發銀行的重視:願意派一位前總統來擔任行長。
你剛才問,如果2026年右翼陣營、博索納羅或其盟友再次贏得選舉,會怎樣?確實有這種可能,那將是一場艱難的選舉。按原定規則,迪爾瑪·羅塞夫本應在2025年7月卸任,輪到俄羅斯任命行長。但俄羅斯提出希望她繼續留任。據我所知,這不是她主動提出的,而是普京向盧拉轉達的請求,既是對她工作的肯定,也可能是因為在當前對俄製裁的背景下,俄羅斯籍行長可能會嚴重損害銀行利益。我對此感到意外,盧拉和迪爾瑪可能也一樣。無論如何,她接受了繼續任職,但我不確定她是否願意幹滿五年。如果2026年盧拉政府被右翼取代,而新政府對她抱有敵意,我推測她會辭職,因為這會讓她的工作變得非常困難。
因此,我希望,如果2026年右翼、特朗普式的勢力在巴西勝選,而迪爾瑪辭職,那麼俄羅斯能夠行使權利,任命新行長來完成她剩下的任期。畢竟她的任期還剩五年,下一位就該輪到俄羅斯了。
**李澤西:**你之前提到過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CRA),這是成員國央行同意將貨幣集中到一個共同的緊急流動性基金的機制。據説當時部分談判是在澳大利亞進行的。你能詳細説説這個故事嗎?
**巴蒂斯塔:**是的,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我們在談判即將收尾的時候,正好五個金磚國家的代表經常一起出席G20和IMF的會議。所以我們利用在華盛頓、墨爾本、悉尼等地開會的機會,在會議之外同步推進CRA的談判。最後敲定主要懸而未決事項的關鍵會議,就是在墨爾本我們下榻的一家酒店裏完成的。當時我們忙於CRA談判,幾乎沒空理會G20的事務。不過澳大利亞在談判中並沒有任何角色,只是我們碰巧都在墨爾本,於是就藉機把CRA談成了。

特朗普簽署“天才法案”(GeniusAct)
**李澤西:**最後展望一下,最近還有一條新聞,説美國打算利用穩定幣來維持美元的主導地位,這在特朗普的説法裏叫作“天才法案”(GeniusAct)。但加密貨幣的最初設想之一,是取代現有貨幣,削弱各國政府對本國貨幣的控制。你認為加密貨幣在“去美元化”的討論中會扮演怎樣的角色?
**巴蒂斯塔:**我不認為由私人機構發行的加密貨幣在這方面能發揮實質作用。真正可能推動去美元化的,是各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CBDC)。這與私人加密貨幣不同,它由央行數字化發行,可以作為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目前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都在研發央行數字貨幣。我們需要整合這些央行數字貨幣,把它們納入統一的支付體系和儲備體系,最終創造一種新的儲備貨幣;這是美國人最不願看到的。
特朗普對此態度強硬,但問題在於,美國最大的敵人不是金磚國家,而是它自己。美國濫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藉此實施各種制裁、凍結他國儲備、搞長臂管轄,導致外界對美元的信任嚴重受損。
我去年在俄羅斯參加會議,最後由普京總統總結髮言並回答提問。我問他:總統先生,您認為金磚國家在去美元化方面的角色是什麼?他非常平靜、毫無諷刺地回答:“等等,我們不是反對美元,是美元在反對我們。”這句話説得很到位。
如果美元能被中立地管理,我們根本不需要討論去美元化。當然,數字貨幣會發揮作用,但絕不是美國眾議院立法設想的那種由私人企業發行的加密貨幣。美國經濟學家、前IMF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寫過一篇很好的文章,指出美國目前籌備加密貨幣的方式,是導致金融危機、不穩定和洗錢的“配方”,與“去美元化”討論毫無關係。這更像是一場騙局,是美國又一次自找的麻煩。建立新體系的正確路徑,只能是各國央行協調行動。
**李澤西:**非常感謝你接受PacificPolarity的採訪,保羅。我們對金磚國家和IMF的不同運作方式,以及你在兩大機構的幕後經歷,都收穫了很多知識。
**巴蒂斯塔:**謝謝邀請,很高興和你交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