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奧弗裏:對於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西方正經歷一場認知革命
guancha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值此之際,觀察者網推出系列專題“14年抗戰史不容歪曲和篡改”。
本文作者理查德·奧弗裏是西方少有的認識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貢獻,並將第二次世界大戰開端提前到1931年的歷史學家。文章首發於2025年第2期《抗日戰爭研究》,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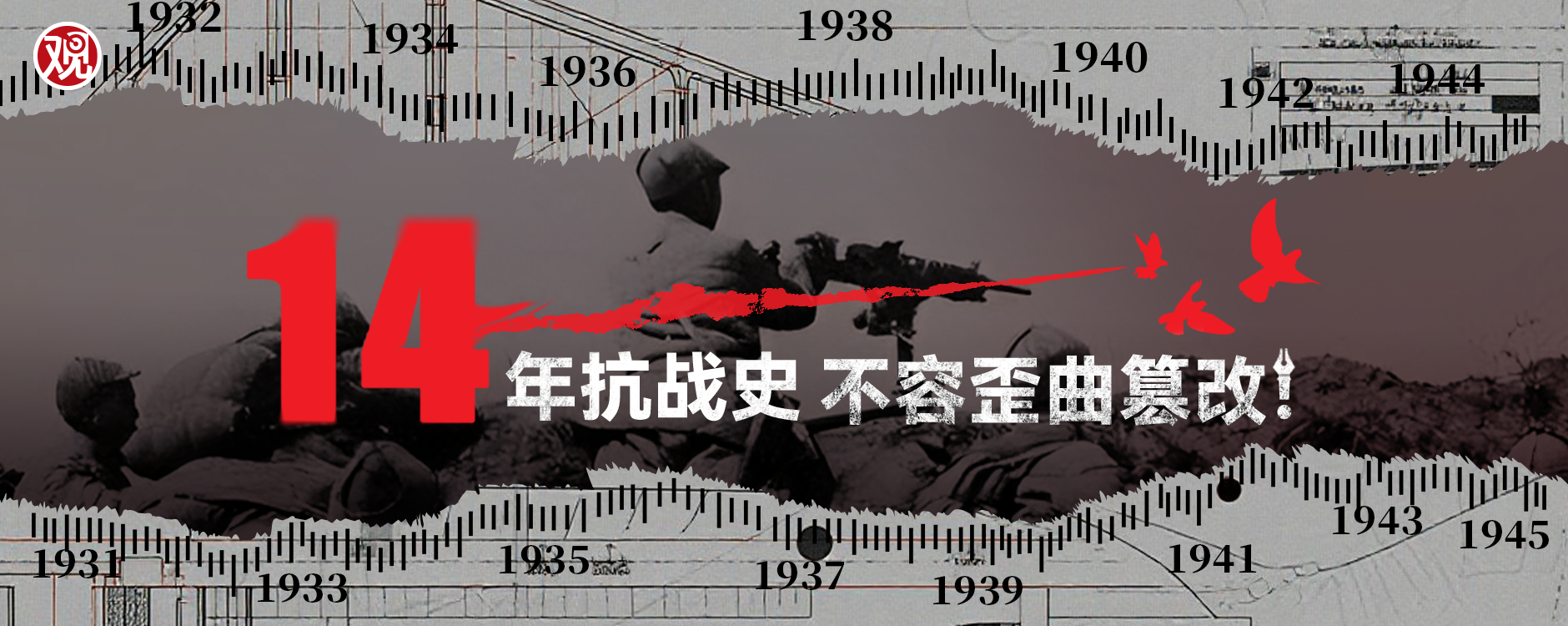
【文/理查德·奧弗裏】
在西方學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敍事中,中國很少獲得其作為主要盟國應有的篇幅,但在戰時宣傳和官方文獻中,中國國旗總是與蘇聯、美國和英國國旗並列飄揚。
中國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第四盟國,自1931年起與日本作戰,在1941年12月對德國宣戰。然而,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從未被邀請參加其他三個主要盟國的會議,中國的將軍們也不被允許加入討論和決定西方戰時戰略重大問題的英美聯合參謀長會議(Combined Chiefs of Staff)。1945年9月2日,美國按自己的意願組織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中國戰區的日軍投降儀式於9月9日舉行。
中國較低的地位在戰後的二戰史敍事中一再被重複,它反映的是戰時觀點,即中國軍隊裝備簡陋、指揮無能,對擊敗軸心國的貢獻微乎其微。有關中國戰局的確切消息甚少傳至外界,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儘管做出承諾,卻始終不願向中國提供蔣介石及其政府所請求的財政援助和租借物資。
在二戰期間及戰後的歲月裏,中國戰場被認為不如蘇聯、北非和歐洲戰場重要。傳統主流觀點認為,美國軍隊在橫跨中太平洋和東南亞島嶼的激烈戰鬥中扮演了擊敗日本的主要角色。1945年8月,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在短短數週內便被蘇聯紅軍橫掃。儘管中國軍隊曾與英聯邦部隊在緬甸並肩作戰,但戰後英國對該戰場的記憶幾乎完全聚焦於英國方面的貢獻。
一、 西方有關中國抗戰的敍事變遷
21世紀以來的25年,西方關於中國二戰貢獻的歷史敍事發生了變化。這部分歸因於更多中國檔案向西方學者開放,同時也與中國崛起為現代軍事與經濟超級大國密切相關。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變化,促使學界深入研究中國現代化的起源,探討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危機與戰爭。這一趨勢推動了對中國戰時軍事史和社會史的更多關注。
一批西方學者為加深對中國抗戰的理解作出了卓越貢獻。2013年,拉納·米德(Rana Mitter)《中日戰爭(1937—1945)》一書出版,這是首部用英文撰寫的中國抗戰通史。2017年,劍橋大學歷史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戰時中國》一書出版,努力將中國抗戰置於20世紀30年代更廣闊的背景下,並將敍事延續至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美國曆史學家莎拉·潘恩(Sarah C.M.Paine)在2012年出版的《亞洲戰爭(1911—1949)》中,將抗日戰爭置於更宏觀的視野,即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席捲中國的戰爭之中。同年,冷戰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出版《躁動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雖主要關注更長時段內中國地緣政治的變遷,但也詳細探討了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
關於中國抗戰的軍事史研究也日益豐富,這些研究有助於填補西方對中國軍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認知上的空白,瞭解其在持續遭受日本侵略直至1944年“一號作戰”期間仍有能力避免徹底失敗的原因。
由馬克·皮蒂(Mark Peattie)、愛德華·J.德里亞(Edward Drea)與方德萬編輯的論文集《為中國而戰:1937—1945年中日戰爭軍事歷史論文集》於2010年出版,全面概述日本侵華戰爭的軍事背景、軍事對抗的進程以及雙方軍隊的特點和素質。如今,人們已無法忽視或貶低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來中國軍隊的軍事貢獻,它比英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早2年多,比美國參戰早近5年。此外,西方學界也首次深入理解了中國戰時經濟的表現及其諸多侷限,這得益於約書亞·霍華德(Joshua Howard)的開創性英文著作《戰爭中的工人:中國軍工勞動力(1937—1953年)》。該書提供了關於國民政府軍工生產及勞動力狀況的原始統計數據,為西方史學界填補了長期缺失的實證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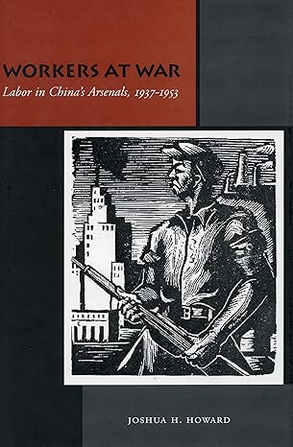
《戰爭中的工人:中國軍工勞動力(1937—1953年)》
最後,陶涵(Jay Taylor)撰寫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是一部全面的蔣介石英文傳記,呈現了一個更完整和富有人情味的形象,展現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動盪時期,蔣介石如何在國外壓力和國內對手之間尋求平衡,推動國家發展的歷史。該書對二戰期間西方政治家對蔣介石的評價,以及戰後史學界對這些評價的延續提供了新的觀點。
二、 日本侵華戰爭與全球危機
新史學的一個成果是將中國置於更漫長、更廣泛的全球危機之中,這一危機發軔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在20世紀30年代加劇。在一戰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動中,列強有關中國戰後地位的考慮是重要變量。
一戰後,中國仍然是一個動盪且分裂的國家,在西方看來,它是地區不穩定和潛在衝突的根源。對於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英國而言,雖然此時不得不對中國作出一定讓步,但維持在華貿易和戰略利益仍然是優先事項。
中國的動盪推動了日本國內關於強化帝國統治以提升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討論,以致日本出現一種信念,即控制更多領土能夠解決日本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這直接導致日本關東軍貿然發動軍事行動,先是在中國東北地區,隨後擴展至華北地區。
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列強和日本在全球範圍內大肆擴張,日本侵華戰爭現在可被理解為此類帝國擴張的激進延伸。帝國史學家比戰爭史學家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連續性。1914年之前,擴張領土被帝國視為傳播優越文化(Superior Culture)和文明的手段,同時也是在快速現代化的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利益的一種方式,還被看作大國地位的象徵。英國、法國、荷蘭、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都極力推行海外帝國擴張計劃。
到一戰爆發時,那些沒有被列強直接統治的非洲和亞洲地區幾乎完全被殖民化。一戰後,列強仍然熱衷於擴張。英國和法國通過對德國前殖民地和奧斯曼帝國前行省的委任統治,擴大了直接控制的領土。與之相對,日本在中國擴張勢力範圍的希望受挫,意大利在歐洲的野心未能實現,德國則被剝奪了所有殖民地。這三個國家開始對英國和法國的全球霸權感到不滿,三國的激進民族主義勢力主張“弱勢”列強(The “Have-not” Powers)應在帝國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日本在中國、意大利在東非、德國在中歐瘋狂地擴張,希望藉此挑戰英法的霸權。
正是基於這一原因,近年的二戰歷史書寫開始將敍事起點定在1931年,而非傳統的1939年9月。兩本書將1931年放入標題:理查德·奧弗裏的《二戰新史(1931—1945)》和安德魯·N.布坎南(Andrew N. Buchanan)的《全球視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1953)》。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動可被視為20世紀30年代新帝國主義擴張的第一步。一旦日本政府承認了關東軍的行動,便幾乎默認了進一步的擴張浪潮。這是1919年後建立的全球秩序首次受到軍事行動和領土佔領的挑戰,而這種模式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反覆上演。到英國和法國因德國入侵波蘭而宣戰時,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和戰爭已經持續了8年;意大利軍隊自1935—1936年在埃塞俄比亞、1936—1939年在西班牙、1939年春在阿爾巴尼亞的行動已有4年;納粹德國在開啓對波蘭的帝國主義侵略之前,已經佔領了奧地利和半個捷克斯洛伐克2年。帝國的每一步擴張,都加劇了戰後秩序的不穩定,全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大增。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藉口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炮轟北大營,日本騎兵的鐵蹄踏進瀋陽城。中國軍網
在這些衝突中,中國戰場的規模最大、代價最高,這也是將二戰這場全球性戰爭的起點定為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原因。在西方關於20世紀30年代的傳統敍事中,九一八事變被視為一個短暫的插曲,其重要性低於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活動。然而,近年來的新敍事將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也納入其中,並描繪了此後5年日本軍政官員不斷向華北各省推進,直到北京被日軍包圍的歷史。在中國發生的危機削弱了國際聯盟的信譽和效力,它未能阻止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入侵。
正是日本的持續侵犯,最終促使蔣介石於1937年7月迎戰日本,試圖阻止其進一步的侵略,同時聯合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團結整個國家抵抗共同的敵人——日本。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儘管西方大國未明確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但它們積極向中國政府及其軍隊提供軍事援助和建議。
這也是日本與西方關係急劇惡化的時期,雖然雙方沒有發生直接對抗,但西方日益擔憂日本威脅到他們在東亞的經濟和戰略利益,開始警惕日本在該地區的角色變化。在西方列強看來,一戰後既有秩序面臨着危險的挑戰,這些挑戰還包括意大利在非洲和地中海的行動以及德國在中歐的行動。

東北抗日聯軍戰士
20世紀30年代,各國紛紛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顧問和人員的舉措表明,由日本侵略引發的中國危機已高度國際化。近年來,西方的研究揭示了意大利、英國、德國、蘇聯以及美國的援華行動。這些國家系基於自身利益介入中國事務,中國自身的軍事現代化才是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堡壘。1931年,蔣介石邀請英國皇家海軍為中國的海軍改革提供建議,但英國欲藉此向中國兜售軍艦。
1933年,墨索里尼批准意大利向中國派遣空軍顧問團,向中國空軍出售意大利飛機;1935年,意大利將軍羅伯託·洛蒂(Roberto Lordi)短暫擔任了中國空軍的參謀長。1932年,一羣美國飛行員在杭州發起了一個私人航空項目,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該項目擴大,到1940年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航空技術和裝備來源,並最終促成飛虎隊的組建,它與中國軍隊並肩戰鬥到1945年。
1937—1941年,蘇聯直接向中國提供航空人員和飛機援助,發起“澤特行動”(Operation Zet),共向中國派遣了900架飛機及數百名飛行員和機械師,其中200人在對日作戰中犧牲。蘇聯的介入源於斯大林的戰略考量,即利用中國戰場牽制日本,防止其染指蘇聯遠東地區。如今,西方關於這些援助行動的研究越來越多,進一步表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命運是一個國際問題,而不僅僅侷限於亞洲範疇的考慮。
三、 被忽視的第四盟國
最近10年,在關於歐洲戰爭爆發的歷史敍事中,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描述也發生了變化。對當時的英法兩大帝國而言,20世紀30年代末的最大威脅是納粹德國。希特勒大規模重整軍備,顯然有意向中東歐地區擴張。次要威脅則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它成為英法在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的主要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發生在中國的戰爭不可避免地被輕視。然而,英國政府依然認識到日本侵略對其在華商業和政治利益的威脅,並試圖在避免戰爭的前提下,找到遏制日本野心的辦法。結果,正如弗蘭科·馬克裏(Franco Macri)所稱,這導致了一場與日本的“代理戰爭”:在不與日軍直接交戰的情況下,英國向中國提供資源和資金,幫助其抗戰。
美國政府同樣關注日本的擴張,以及它對美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和資源利益所構成的威脅。喬納森·馬歇爾(Jonathan Marshall)的研究表明,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開始認真看待發生在中國的戰爭,尤其是當日本可能通過華南地區進一步擴張至列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威脅錫、橡膠和錳的供應時。雖然這種擔憂尚未促使羅斯福向蔣介石提供軍事援助,但美國的政策已受到希望加強中國抵抗和遏制日本擴張的意圖的影響。
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英法對德宣戰的同時,蘇聯與日本在中國東北諾門罕附近發生了一場短暫的衝突,最終以日軍的局部失敗和東京與莫斯科達成協議而告終。而就在此前一個月,蘇聯與德國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1939年8月23日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百度百科
這些事件共同導致中國戰場的重要性被進一步削弱,使得中國幾乎無法再從任何主要大國獲得實質性援助。蘇聯撤回了對中國的支持,日本軍隊得以向南推進,並在接下來的一年中擴大了侵略範圍。1940年5-6月,英法在歐洲的失敗使中國的處境更加艱難:英國因陷入對德孤軍奮戰,已無力在亞洲採取更多行動;而法國的敗降與淪陷則為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提供了機會。這最終導致通過緬甸和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地區的對華補給線被切斷。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以及汪精衞傀儡政權之間的分裂,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瓦解。從1939年底到1941年底,中國戰場多呈僵持局面,因而在西方傳統史學敍事中篇幅甚微。儘管近年關於中國抗戰的軍事史研究有所進展,但亞洲戰場仍然未能得到足夠的關注。當代西方學界普遍認為中國軍隊指揮不力、裝備落後,而蔣介石政府腐敗無能,這得到了後續歷史的印證。
直到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間,日軍嚴重侵犯了英國和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亞洲戰場才進入主流討論之中。然而,即便如此,學界的關注點依然集中在太平洋戰爭和東南亞戰場。儘管中國戰場更為廣闊,交戰兵力動輒以百萬計,戰爭規模遠超太平洋戰爭,但1942年2月英國在新加坡的慘敗,以及美國在菲律賓的失敗,卻受到更多的關注。
1941年發生的兩件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徹底改變了中國在更廣闊戰局中的地位:德國入侵蘇聯,以及日本對西方控制的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發動突襲。這兩個事件對中國的重要影響已廣為人知。德國的入侵使得蘇聯被牽制在歐洲戰場,從而讓日本得以鞏固對中國的控制,並向東南亞的資源腹地擴張,使中國更加孤立。
然而,日本的南進政策也使美國正式參戰,從而促成中美之間比以往更為緊密的軍事與政治合作。為強化中國的立場,蔣介石於1941年12月正式對德國宣戰,使中國成為主要盟國之一。然而,蔣介石的宣戰在國際敍事中往往被忽視,甚至在盟國內部也幾乎未受到重視。當中國領導人要求英國、美國和蘇聯將其視為“大聯盟”中的主要盟國時,這一訴求被無視。
這暴露了羅斯福政府外交政策中的矛盾:羅斯福在言辭上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中國成為戰後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國政府與軍方高層在行動中卻普遍將中國視為一個被動的盟友,認為其在軍事上與經濟上都過於孱弱,僅能發揮次要作用。蔣介石還希望中國代表能加入1941年12月由美英主導的聯合參謀長會議,以參與共同戰略的制定,但同樣遭到拒絕。他進一步提議,應該設立一個由中國主導的戰略指揮機構,統籌從緬甸、南太平洋到中國腹地的亞洲戰區,因為中國在該地區承擔了最主要的作戰任務。
然而,這一提議也未能得到回應。英國在印度新德里設立了東南亞戰區司令部,而羅斯福則任命美國將領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為駐中緬印戰區美軍最高指揮官。令人驚訝的是,儘管中國作為主要國家對日作戰已超過4年,但其潛在貢獻卻幾乎未受到西方的關注,而這種態度也與西方公眾對中國抗戰缺乏興趣的狀況相一致。
蔣介石原本希望參戰後的美國能夠帶來比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及其飛虎隊提供的空中支援更大的軍事承諾。然而,對橙色作戰計劃(War Plan Orange)的最新研究表明,自美軍制定這一美日戰爭應急計劃以來,美國海軍和陸軍規劃者始終不願在中國大陸投入地面部隊以發起攻勢,原因在於後勤補給的困難以及地理上的挑戰。
相反,他們更傾向於採取一條橫跨太平洋島嶼的進攻路線,逐步佔領基地,為戰略轟炸提供跳板——這一戰略正是美國海軍與陸軍航空隊在1941—1945年間所執行的作戰方針。因此,蔣介石從中美同盟中所獲得的支持遠遠達不到他的期望。
而史迪威的任命,正如近年來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最終被證明是災難性的。史迪威是一個傲慢且自私的指揮官,幾乎沒去理解自己所接觸的文化,並且對蔣介石及中國高層指揮官嗤之以鼻,認為他們腐敗無能。

1943年11月,羅斯福、蔣介石、丘吉爾在開羅會議時的照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埃裏克·塞澤科恩(Eric Setzekorn)在其2024年出版的新作《不確定的盟友:約瑟夫·史迪威將軍與中緬印戰區》中,詳細揭示了史迪威與他在中緬印戰區應當協助的中國軍政要員之間的惡劣關係。塞澤科恩指出,史迪威未能理解羅斯福及美國政府希望與蔣介石建立合作關係,以維護戰後美國在該地區利益的戰略目標,反而單方面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從中國軍隊那裏攫取資源,以支持美國的作戰計劃。當代西方史學界更直言不諱地揭示了史迪威在戰略決策上的誤判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同時也指出,儘管羅斯福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在戰後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他更傾向於優先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史迪威在執行政策時完全遵循這一立場。
在西方盟國的戰略中,處於相持階段的中國戰場被賦予無足輕重的角色,這在美國於1941年春季發起並得到英國和加拿大支持的租借法案計劃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羅斯福雖然將中國納入租借計劃,並向蔣介石做出承諾,但實際提供給中國的物資與蘇聯和英國相比,不過是杯水車薪。
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路線的困難:運輸或者必須經過緬甸北部(直至1942年該路線被日軍切斷),或者只能通過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峯”航線,以致物資大多堆積在印度的倉庫裏。那些真正進入中國的物資,優先服務於美國的軍事利益,首先是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然後是自1944年夏天起駐紮成都、執行對日轟炸任務的美國陸軍航空隊第二十轟炸軍司令部。**中國方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資中,**98%被美軍使用。中國僅獲得供應全球的37000輛坦克中的100輛、11400門高射炮中的208門,以及43000架飛機中的1378架。這一數量極為有限,反映出中國戰場在整個同盟國後勤體系中的優先級不高,而近年來關於租借法案的研究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戰場在同盟國組織者眼中微不足道的地位。
在盟國大戰略討論中,蔣介石同樣被置於次要地位。直到1943年11月,他才首次受邀出席開羅會議。在會議上,他與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討論了中國戰區的局勢。丘吉爾對中國要求與其他主要盟國平起平坐的主張不屑一顧,而羅斯福熱衷於讓中國繼續作戰,並承諾設法通過緬甸開闢援助通道,保證在擊敗日本後尊重中國主權,讓中國在對日佔領中發揮重要作用。
英國和美國雖然同意廢除中國給予外國貿易和金融特權的不平等條約,但有證據表明,丘吉爾私下仍希望戰後能恢復這些特權。儘管蔣介石對自己被納入同盟體系感到滿意,但他對會議的實際成果持懷疑態度。
事實證明,他的擔憂並非多餘。當羅斯福和丘吉爾結束與斯大林在德黑蘭的會談返回開羅時,他們便背棄了重新開闢緬甸援華通道的承諾。此外,儘管羅斯福的“四警察”(Four Policemen)構想包括中國,但西方學界現已公認,中國並未被真正視為平等的大國,斯大林對此尤其不以為然。
蔣介石未被邀請參加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而在此次會議上,斯大林在蔣介石毫不知情、亦未給予認可的情況下,在中國北方的勢力範圍方面獲得重大利益。同樣,他也未能出席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即決定戰後秩序的關鍵會議,蔣介石對此深感不滿。最終,美國主導了對日佔領,而中國未能派遣一兵一卒參與其中。
結語:對“第四盟國”的重新評價
西方學界關於中國二戰地位的新研究路徑,有助於更全面地書寫亞洲戰場的歷史,也使人們更能理解中國人在其戰爭努力被拿來與蘇聯或美國對比時所感受到的憤懣情緒。中國並未被視為平等的盟友,而主要盟國對蔣介石及對西北地區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及其背後的原因,如今學界可以更客觀地加以重構。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長達14年的抗戰是否對盟軍勝利有實質性貢獻。儘管戰爭持續多年,中日雙方始終未能取得針對彼此的決定性勝利。日本試圖鞏固其對中國大片領土的控制,但中國的抵抗不僅證明了日本並非不可戰勝,還牽制了其大量陸空部隊。
這些兵力和裝備本可以投入太平洋戰場,協助日本海軍,或投入日本國內。考慮到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在動員和裝備人力方面面臨的重重困難,他們始終未屈服於日本,實屬不易。此外,中國不像蘇聯那樣,大規模接受並囤積租借援助物資以應用於戰後經濟。儘管美國負責租借援助物資的官員時有抱怨,但中國獲得的租借援助遠少於蘇聯或英國,給盟國帶來的經濟負擔相對較輕。儘管在當時未得到充分認可,但中國的抵抗仍為盟軍作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果中國戰敗並淪為日本的附庸,將在政治和軍事上對其他盟國形成重大挑戰。
還有一件事,如今西方歷史學家已非常清楚。學界加強了對中國戰時社會的研究,促使人們更加關注中國戰時社會的狀況及民眾遭受的苦難。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研究尤其讓英語世界認識到中國平民所遭受苦難的廣度與深度。她描述的犧牲多種多樣:經濟資源被嚴重破壞;難民潮席捲全國,多達1億人逃離日本佔領區;饑荒廣泛蔓延,甚至發生毀滅性饑饉;無數中國女性被迫淪為慰安婦;日軍在佔領區的殘暴行徑令人髮指,他們對游擊戰的回應是“殺光、搶光、燒光”。其他國家,即便是蘇聯也未曾遭受如此廣泛的苦難。這一認知使歷史學家將歐洲經歷置於更為合適的背景之中,並促進針對交戰國戰時社會的比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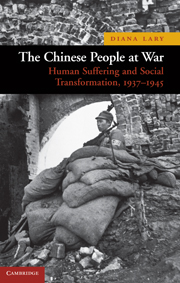
《戰爭下的中國人:社會苦難與轉型(1937—1945)》, [英]戴安娜•拉里
拉里還揭示了戰後中國從國民黨向共產黨政權的過渡。如今,人們不僅將這一變化歸因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勝利,更看到其深層原因——戰時及戰後初期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全面崩潰。現代中國的根源可追溯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危機。因此,西方歷史學家如今更關注國共雙方意識形態、社會背景及軍事表現的成因。
在過去25年間,對於中國在二戰這場全球性戰爭及其影響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在認知方面經歷了一場革命。如今,人們已無法再將中國視為孤立且無關緊要的戰場,也不能再將其看作是相較於蘇德戰場或太平洋戰場的次要戰場。
對於深陷其中的人們而言,日本侵華戰爭是一場規模龐大、破壞力驚人的戰爭,波及中國全部領土和全體民眾。必須將中國戰場同歐洲戰場及大洋上的傳統戰場同等看待,同時,也應將中國的經歷置於全球變革的宏大歷史背景之中進行考察。這場變革使世界秩序不再由帝國與列強主導,民族國家取而代之,成為世界秩序的主要參與者。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這一變革的劇烈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