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鋭傑:天命人顛覆了“天命”
guancha
“有未知,才有驚喜;有挑戰,才有樂趣。”
8月20日的凌晨,遊戲科學的創始人、CEO,同時也是《黑神話:悟空》的製作人馮驥發表文章,解釋推出新作《黑神話:鍾馗》的緣由。
早前,不少玩家猜測遊戲科學即將發佈《黑神話:悟空》的DLC,此次《黑神話:鍾馗》的亮相,確實讓人始料未及。
也許正如黃鋭傑老師在《“歌未竟,東方白”——<黑神話:悟空>的否定性創造機制》所分析的,《黑神話》最終構建起一個既能直面死亡又能持續創造的雙向空間,既延續了《西遊記》的反叛精神,又實現了對傳統文化“天道”觀的創造性轉化。我們也期待着《黑神話:鍾馗》能再續《黑神話:悟空》的傳奇,“提劍也,要把這清濁辨!”

【文/ 黃鋭傑】
2024年8月發售的國產遊戲《黑神話:悟空》(以下簡稱《黑神話》)無疑是近一年來大眾文化領域的現象級作品。經過近一年的發酵,其影響力早已輻射至遊戲圈之外,並引起了學界關注。
《黑神話》發售半年後,另一部大眾文化領域的現象級作品《哪吒之魔童鬧海》(以下簡稱《哪吒2》)上映。許多研究者都指出,這兩部作品在短期內相繼出現,揭示了二者在“生產”環節的一致之處——都是中國文化工業逐漸成熟後的產品。

中國首款3A遊戲《黑神話:悟空》
關於這一點,研究工業史的李寅在一次關於《黑神話》與《哪吒2》的對談中即已挑明:
在工業發展的研究中有一個概念叫“產業公地”(industrial commons)。它的意思就是説一個工業要發展,它背後有很多因素,包括基礎設施,包括產業的上下游,包括大量熟練的勞動力,包括整個產業的環境,包括人的隱性的知識,甚至包括整個市場的開拓,其實都是某種公共產品。
……
我們的遊戲、電影產業,多年來國家投資和市場參與培育出來的產業公地它足夠大了,而我們的市場又這麼龐大,所以早晚有一天會出來一個像《黑神話》《哪吒2》的產品。[1]
那麼,為什麼從中國成熟的“產業公地”中誕生的一定是《黑神話》與《哪吒2》,而不是其他產品?李寅承認,這才是一個真正“讓人着迷”的問題:“經濟學沒有辦法解釋……勇氣是從哪兒來的?推動這樣的一個範式轉變的精神氣質是從哪兒來的?”[2]
已有研究者指出,創作出《黑神話》的團隊淵源有自,他們都是20世紀90年代的技術浪漫主義一代,較早接受了西方的技術,並將其用於製作中國的遊戲作品。[3]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這種意義上的技術浪漫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由《黑神話》出發,或許可以這麼回答:中國的技術浪漫主義意味着由技術出發尋找突破以西方為代表的技術文明的可能性。
技術,意味着什麼?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接續海德格爾指出,技術是西方形而上學的結果。
現代技術是對自然施加的暴力,而不是順從作為自然的存在在其增長過程中的去蔽模式:技術進入現代化的標誌就是,形而上學得到自我表現和自我實現,就像是計算理性完成了旨在佔有和支配自然的計劃,而這種被佔有和支配的自然本身也就失去了自然本來的意義。[4]
西方形而上學由“本質”“本性”出發理解“自然”,因此,扭曲了作為“生長”“湧現”之“自然”。這種意義上的對“自然”的理解不可能帶來“去蔽”意義上的“真理”,而必然淪為施加於“自然”的暴力。
斯蒂格勒進一步指出,在此過程中,創造出技術的存在者(或者按西方現代哲學的一貫叫法,稱之為主體)亦將反過來被技術決定。
我們作為自身的存在者,卻遠沒有藉助技術的方法成為自然的主宰,相反,我們自己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也服從技術的要求。如此定義的現代技術就是座架(gestell),即通過計算來一併檢示自然和人。[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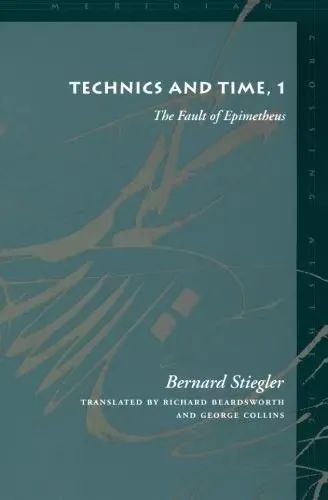
斯蒂格勒 《技術與時間》書影
如何才可能從海德格爾批判的“座架”中擺脱出來?與海德格爾不同,斯蒂格勒敏鋭地注意到了“座架”的兩面性。如果説現代技術仍不失為一種去蔽的形式,那麼它是最值得深思的:它是命運的舞台,是存在本身的歷史,座架“可以被當作一箇中轉站,它具有兩面性,由此我們可以把它比作雅努斯之頭”。[6]
古羅馬神祇雅努斯擁有兩副面孔,一副面向過去,一副面向未來。面向過去的技術扭曲了自然與我們自己,面向未來的技術將真正去除自然和我們身上的陰翳。
02
《黑神話》帶來了由西方締造的技術“座架”中“去蔽”的可能性。《黑神話》在遊戲類型上屬於角色扮演遊戲(role-playing game,RPG)。細查角色扮演遊戲的發展史,可以説這類遊戲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了三種重新構造主體或者説擺脱技術宰制生命的方式。
一切角色扮演遊戲不管講述的是什麼故事,目的都在於以“交互”為中介接引遊戲者進入新的現實。日本亞文化研究者東浩紀將這種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稱之為“遊戲性寫實主義”,認為這種現實主義將徹底抹去傳統文學的現實主義手法致力於通過連貫的敍事建構的主體性。
在他看來,遊戲出現後傳統的“宏大敍事”已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小敍事”。在遊戲世界裏,角色不過是數據模塊,玩家可以隨意組合,甚至基於這些角色形象進行同人作品式的再創作。這種“小敍事”本質上具有“去敍事性”,遊戲角色也因此失去了主體性。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角色即使死亡也能反覆重生,這正是“遊戲性寫實主義”的直接體現。[7]
東浩紀提到的角色扮演遊戲中的特殊死亡模式,其實就是玩家熟悉的存檔機制。在遊戲中,每當角色死亡並重新復活,實際上都是通過讀檔回到之前的存檔點的過程。根據車致新的研究,這一設計靈感源自早期歐洲流行的“洞窟探險”活動。探險者會在洞穴中不斷嘗試不同路徑,每當遇到死路時就重新選擇路線,經過多次嘗試最終完成探索。遊戲開發者受這一模式啓發,將其應用到角色扮演遊戲中。每當玩家在遊戲中保存進度,就像探險者記下自己的位置,而當角色死亡時,重新加載存檔則相當於探險者從失敗處重新出發,換一條路繼續前行。[8]
不過,這種存檔、回檔意義上的死亡模式果真如東浩紀所言,指向碎片化的“小敍事”嗎?與其説存檔讓玩家迴避了死亡帶來的終結,不如説它賦予了遊戲一種極致的現實主義色彩。每一次的存檔和回檔,看似在重複失敗,卻讓玩家有機會體驗角色生命的所有可能性。
這種設計讓主體變成一個開放且充滿變數的黑洞,玩家可以通過反覆探索修正自己的選擇。相比現實生活——主體只能在眾多岔路中選定一條並承受其後果,遊戲裏的主體卻能夠一次次推翻和重來。人生的道路因死亡而單一,而遊戲通過存檔功能,使無數未被選擇的道路重新浮現,讓玩家得以進入那些現實中永遠無法抵達的分岔小徑。
這是大多數角色扮演遊戲選擇的模式,但其“加強版現實主義”的缺陷也十分明顯。玩家在一次又一次存檔、回檔的過程中走上的不同道路,實質上不過是同一條道路。終點已經設定好,在岔路中摸索不過是為了找到得以通往終點的最合適的那條道路。這種意義上的死而復活反而成了一種規訓,路邊的路牌上無一例外寫着四個大字:請勿偏航。
意識到這一類角色扮演遊戲的難題,第二類角色扮演遊戲獨闢蹊徑,選擇了通過限制存檔,直面死亡的模式。這便是由日本遊戲製作者宮崎英高獨創的魂類遊戲。
這類遊戲採用了角色扮演遊戲常用的升級打怪成長模式,但有兩項特殊設定:一是遊戲內無法隨時存檔,進度只能在極少且難以抵達的安全點保存,途中常伴有致命風險;二是玩家每次死亡後在存檔點復活都會付出高昂的代價,關鍵資源往往因此失去。
對許多玩家而言,這種遊戲只會帶來難以忍受的挫敗感,魂類遊戲愛好者卻樂在其中。這種遊戲類型為遊戲現實主義提供了另一種詮釋。雖然它與前述可以反覆嘗試的角色扮演遊戲都在強調主體性,不過,魂類作品是在一次次受挫和堅持中,讓玩家切身體會到那種如同黑暗洞穴般的主體的存在的。
丹麥遊戲學者尤爾在《失敗的藝術——探索電子遊戲中的挫敗感》中早已指出,無論何種遊戲,其核心其實都是追求失敗。[9]設計優秀的遊戲往往不會讓玩家輕鬆成功,而是在通向終點的過程中,讓他們一次次跌倒、重來。正是這些失敗,塑造了玩家的主體性。
追求失敗戳穿了第一種遊戲現實主義塑造的主體的幻象——主體並非在順利前進中產生,而是在失敗的不確定性裏顯現。第一種遊戲現實主義試圖描繪出主體所有的可能面貌,而真正的主體,卻是在不斷阻滯和斷裂中,在與現實抗爭時,才會從沉睡中被喚起的主體。在這種遊戲現實主義中誕生的不是一個在完整敍事中被建構起來的肯定性主體,而是由無數破碎、斷裂、不連貫的瞬間拼湊而成的否定性主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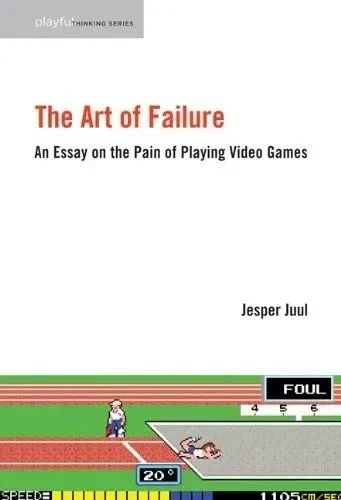
傑斯珀·尤爾 《失敗的藝術——探索電子遊戲中的挫敗感》
這種直面死亡、追求失敗的否定性的主體究竟意味着什麼?追根溯源,玩家在魂類遊戲中追求的並非失敗本身,而是多次失敗後最終成功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並非來自否定性本身,而是來自對否定性的克服以及在此過程中翻轉出來的“創造”。玩家認可的並非幻象之生命,而是在不斷挑戰死亡,一次次重來的過程中,伴隨着這一否定性創造“湧現”出來的生命本身。
然而,在魂類遊戲中,否定之創造不可持續。魂類遊戲的機制決定了玩家“成就感”的短暫:“成就感”來之不易,但也正因為來之不易所以不應持續。為了維持“成就感”,玩家只能一次又一次投身於新的追求失敗的過程中。這種意義上的“成就感”説到底是空洞的。
與這兩種遊戲現實主義不同,第三類角色扮演遊戲致力於呈現在魂類遊戲中已經初露端倪的湧現式生命本身,其代表是日本任天堂公司2017年發佈的現象級遊戲《塞爾達傳説:曠野之息》(以下簡稱《曠野之息》)。

《塞爾達傳説:曠野之息》知乎
《曠野之息》的遊戲機制更接近可以存檔的第一類角色扮演遊戲,但大幅度弱化了主線故事的存在感。玩家操控的主角林克一開始就被告知遊戲的終極目的即拯救公主,但玩家何時救公主完全由自己決定。
當玩家從主線故事中鬆綁,面對的是由曠野構成的開放世界。這個世界實現了基於物理規則的“湧現式交互”。在《曠野之息》中,玩家能夠按照物理規則,與世界中的各種元素自由互動。在這個過程中,玩家可以主動思考,靈活應對各種挑戰,甚至可以單純地投入無目的的樂趣創造中。
如果説第一種遊戲現實主義構造的主體不能脱離主線,那麼,《曠野之息》則讓玩家與角色合為一體:遊戲過程不再是按照設定軌跡反覆嘗試,而是玩家本人在世界中以自己的方式行動。這種體驗恰好呼應了休伯特·德雷福斯對人類本質的理解——在機器與人類的對比中,他指出機器的行為要麼嚴格遵循規則,要麼完全隨機,人的行為則總能在具體情境下自發地賦予意義。[10]《曠野之息》給予玩家的,正是這樣一種立足於完整規則框架之上的自由,在這樣的開放世界中玩家體驗到的生命自然湧現的自由。
如此一來,玩家便由海德格爾批判的西方形而上學“本質”“本性”意義上的“自然”回到了“生長”“湧現”之“自然”中。這正是海德格爾指引的道路。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將自然理解為“形式”,並通過“四因説”中的“動力因”和“目的因”來闡釋世界如何由“質料”逐步轉化為“形式”。
海德格爾對這種目的論式的“自然”提出了批判。他重新詮釋了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指出自然物的“自然”不在於既定的“形式”,而在於“通向自然的自然道路”。[11]換句話説,自然物是在生機流轉中才逐漸成為自己的,“自然”即是這種“生長”與“湧現”。由海德格爾出發的斯蒂格勒意識到了技術創造未來的可能性,但他恐怕並沒有意識到這條道路也可以迴歸海德格爾致力於追尋的更久遠的過去。
不過,《曠野之息》走上了海德格爾式的道路,同時也不得不面對海德格爾式的難題。晚年,海德格爾將“自然”歸結為作為本原(arche)的“大地”:萬物從大地中萌發,在生機流轉中開花結果,最終又凋零歸於大地。[12]
引入中國哲學的視角,上述思路的侷限在於,過於強調“生”,而忽略了“成”。僅僅把生機流轉歸結為“大地”,其實遮蔽了貫穿其間,賦予“生”以意義的“天道”。與西方形而上學的“形式”不同,“天道”構造了一種極為微弱的目的論。無目的,則必無生機,最終只剩下虛寂。在《曠野之息》玩家社區中,玩家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是:“玩塞爾達的時候感覺很孤獨,為什麼?”也可以視作這一難題的反映。[13]

海德格爾 《藝術作品的本源》書影
03
回到《黑神話》,按上述角色扮演遊戲的三種分類,《黑神話》最接近魂類遊戲。取經歸來的孫悟空遭天庭圍剿,死後化為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被分給五位妖王。玩家操控的天命人是花果山的一隻普通猴子,受白毛老猴指引,踏上了以集齊六根復活孫悟空為目標的艱難降妖之路。
相比一般的魂類遊戲,《黑神話》為吸引更多玩家,取消了死亡掉落資源設計,保留了有限存檔點機制,角色死亡後回到存檔點,需要重新上路面對各路刷新的妖魔。玩家操控的天命人死亡、存檔點復活、繼續挑戰的過程,便是典型的魂類遊戲“追求失敗”的過程。
然而,與一般魂類遊戲不同,《黑神話》的否定性創造機制引出了持續性的肯定。同時,對照以《曠野之息》為代表的第三類角色扮演遊戲,由持續性的肯定引導而來的湧現式生命並未歸於虛寂,一種類似於天道的弱目的論,更具體而言,一種反目的論的目的論,在持續指引着這一湧現式生命。要理解《黑神話》與這兩類角色扮演遊戲的聯繫與區別,必須回到《黑神話》獨特的否定性創造機制中。
《黑神話》中,玩家操控的天命人為集齊六根踏上降妖之路。這些妖魔按級別分為小怪、頭目、妖王、大王,是玩家在遊戲中的主要敵人。斬妖除魔構成了遊戲最基本的否定機制,但這僅僅是遊戲的淺層否定機制,在斬妖除魔的過程中,如果完成數個重要支線任務,玩家會意識到妖魔也不過是神佛為汲取靈藴而實現永生的工具,最終在“真結局”中選擇不戴金箍,與天庭和靈山對抗。一旦意識到這點,遊戲的深層否定機制才開始發揮作用。
這一深層否定機制的啓動,離不開遊戲收集六根的主線。六根的設定源自《西遊記》原著中孫悟空剛成為唐僧徒弟即將啓程西天取經時所擊斃的“六賊”,象徵六根清淨方能西行取經。
楊宸指出,以收集六根為主線,“《黑神話》實際上反寫了《西遊記》,因為孫悟空早已打死的‘六賊’正是玩家要尋找的、由孫悟空自身散落出去的‘六根’,等於説取得真經的孫悟空依然六根不淨,而玩家的所有行動無異於復活‘六賊’”。由此,他得出結論:“《黑神話》對‘傳統’的現代化改編具有鮮明的反叛內核”。[14]需要進一步考察的是,《黑神話》真的在復活“六賊”嗎?如果復活了“六賊”,這一“反叛”指向的是何種傳統?
在佛教中,“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源於原始佛教。“六根”接收“六境”(色、聲、香、味、觸、法,亦稱“六塵”)的刺激,進而形成“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識”即“六根”對“六境”進行“了別”的認知活動。[15]大乘佛教興起後,唯識宗在“六識”的基礎上,加上末那識與阿賴耶識,形成“八識”學説。
參之西方現代哲學的主體論,唯識論“八識”學説中的前六識基本相當於我們今天的“主體”概念。不過,這一“主體”只能説是顯性主體,顯性主體之下還有末那識這一隱性主體。眼、耳、鼻、舌、身五識收納於意識,但意識時有斷裂(如在夢中),末那識則恆常不斷,形成“我執”。如要破除末那識的“我執”,必須回到阿賴耶識。末那識恆執阿賴耶識為“我”,換言之,這一“我”不過是瀑布般的阿賴耶識轉變成現行諸法時所現。
《黑神話》裏的天命人確實在收集六根,這一過程可以視為重建六識意義上的顯性主體,但在與大聖殘軀對戰後,一旦他選擇不戴金箍,則意味着拒絕了繼承佛位後淪為天庭傀儡的這一主體。大聖殘軀在此意義上可視作形成“我執”的末那識,戰勝大聖殘軀,便意味着破除“我執”意義上的隱性主體,隱性主體既去,六識構成的顯性主體自然不復存在。換言之,如果選擇不戴金箍的“真結局”,則《黑神話》的這一反寫就自我顛倒為正寫,迴歸了《西遊記》的正統敍事。
然而,《黑神話》的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如果選擇不戴金箍,在玩家的“根器”界面中,六根圖中的意根將一直空缺,這意味着玩家對傀儡主體的拒絕。不過,一旦玩家選擇“再入輪迴”,六根圖中的意根便會自行出現。
這一意根意味着什麼,玩家社區中眾説紛紜。觸發“真結局”後,根據遊記圖鑑《影神圖》[16]中的“二郎顯聖真君”“翠笠武師”“彌勒”諸條目,許多玩家斷定是二郎神取走了意根,因此,在戰勝二郎神後,再對戰大聖殘軀,遊戲才會觸發“真結局”,但這一説法不能解釋在一週目[17]的“真結局”中意根為何缺位。
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一週目的正寫是在為二週目的再次反寫做準備。破除六根代表的主體後,真正填入二週目六根圖中的意根並非二郎神在第一週目中分得的孫悟空意根,而是二週目的天命人在繼承由二郎神處得來的記憶狀態的孫悟空意根後,朝向未來的全新意根。這一意根在重新收納眼、耳、鼻、舌、身五根的基礎上,通過重建六識,形成了新的主體。

《黑神話:悟空》,大聖殘軀。遊民圈子網站
從《鬥戰神》到《黑神話》,其最大的區別便在於選擇破舊還是選擇破舊立新。按馮驥的講法,兩者的區別在於:“我原來做《鬥戰神》,主要感覺是‘爽’,打妖怪爽,揭穿一些陰謀也很爽,他是一個孤膽英雄。到《黑神話:悟空》,我覺得眾生皆苦,人人都有自己的羈絆、煩惱、執念,而這些東西最後會交匯在一起,影響所有人的命運軌跡”。[18]
只破舊,便是一味否定,必然不可能轉為創造。破舊立新則意味着與否定對象建立切身聯繫,在徹底否定後朝向未來肯定一次。這種意義上的肯定才是有源之水,才可以持續。在《黑神話》中,每一次停下來打坐,都是玩家與遊戲中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短暫和解的時刻,但每一次和解都不是妥協,恰恰是為了在未來更好地守護這個舊世界。
引入傳統問題,這次反寫確實構成了對佛教傳統的反叛,但並不意味着對中國傳統的整體反叛。此時,指向“性空”的“六根”與“八識”反過來形成了一個大寫的主體。
回到中國傳統,這與宋儒做的工作非常類似。面對佛教衝擊,一方面,宋儒試圖通過改造佛教的唯識論,召喚出心性背後的天道,力排“性空”之説;另一方面,與漢儒不同,宋儒對“天”的理解不源自“天”本身,反而選擇學習佛教來建構儒家自身的心性論,進而以“性”釋“天”,由此開啓了一場影響深遠的修身運動。
不過,這場運動雖對天道有新解,但未動搖天道根基,修身的選擇意味着由改造主體出發,接引天道。近代以來,伴隨革命傳統的興起,主體修身已不再為接引天道,而為改換天地。在《影神圖》的“大聖殘軀”條目中,悟空告誡八戒:“這供品,本該給那種地收菜的人吃。我們吃了,他們就少吃一點”。對不公的反抗,是孫悟空和繼承其遺志的天命人要改換天地的根本原因。聯繫“二郎顯聖真君”條目中象徵孫悟空意根的梅花意象,以及遊戲最後一章結尾處的“未竟”二字,我們不難聯想到這一革命傳統。
由收集六根走向破除六根,再由破除六根走向重建六根,《黑神話》最終建立起了獨特的否定性創造機制。《黑神話》意識到了魂類遊戲否定性創造難以持續的難題,最終選擇將創造投向二週目代表的未來,改換天地的未來願景指引着玩家一次又一次投身失敗以及對失敗的克服中,並在此過程中感受着每一次朝向未來的生命湧動。同時,每一次朝向未來的生命湧動也會重新喚醒塵封的過去,將玩家與過去的革命記憶相連,與更古老的傳統相連。
這種朝向未來的雙向運動為遊戲的否定性機制賦予了最高強度,最終得以轉化為持續性的創造。另一方面,這種朝向未來的否定性創造也構成了一種反目的論的目的論,天命人顛覆了天庭與靈山合謀構造的“天命”這一目的論,同時,反目的論本身成了指引天命人邁入未來的力量。
參考文獻及註釋
[1]白廣大、李寅等:《從〈黑神話〉到〈哪吒〉,中國大眾文藝正在發生一場“工業革命”》,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https://mp.weixin.qq.com/s/CRcoH6AB4QduXRiqEEWubg,2025年4月5日訪問。
[2]同上。
[3]參見王洪喆:《〈黑神話:悟空〉為什麼會出現?——“長90年代”的技術浪漫主義與“80後”的多重時間》,載《開放時代》2025年第4期。
[4][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1卷(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裴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
[5]同上。
[6]同上。
[7][日]東浩紀:《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動物化的後現代2》,黃錦容譯,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頁。
[8]車致新:《遍歷與死亡:遊戲存檔的媒介考古》,載《讀書》2023年第4期。
[9][丹麥]傑斯珀·尤爾:《失敗的藝術——探索電子遊戲中的挫敗感》,楊子杵、楊建明譯,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5—48頁。
[10][美]休伯特·德雷福斯:《計算機不能做什麼——人工智能的極限》,寧春巖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64—280頁。
[11][德]海德格爾:《論φύσις的本質和概念。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第二卷第一章》,載海德格爾:《路標》,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77—355頁。
[12][德]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載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82頁。
[13]關於《曠野之息》的這一難題,參見嚴奕潔、黃鋭傑:《生命之“湧現”——〈塞爾達傳説:曠野之息〉與遊戲現實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載《上海文化》2024年第10期。
[14]楊宸:《抉心自食,遊戲“天命”——論〈黑神話:悟空〉的“矛盾”》,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2期。
[15]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頁。
[16]《黑神話》設計了名為《影神圖》的圖鑑系統,用於記錄玩家在遊戲過程中遇到的各類敵人和角色。
[17]在《黑神話》中,遊戲周目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它代表着玩家對遊戲世界的不同探索階段和遊戲體驗的層次。簡單來説,一週目指首次完整通關的主要劇情,二週目則是繼承一週目部分進度後的重複遊玩模式,包括新增劇情、隱藏結局及更高難度挑戰。該遊戲周目並未設置上限。
[18]張明萌:《對話〈黑神話:悟空〉製作人馮驥:你在自信之巔時,也在愚昧之淵》,載《南方人物週刊》2024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