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麗·馬特森:曾在留學中國的飛機上看《南京大屠殺》,悲不自勝
guanc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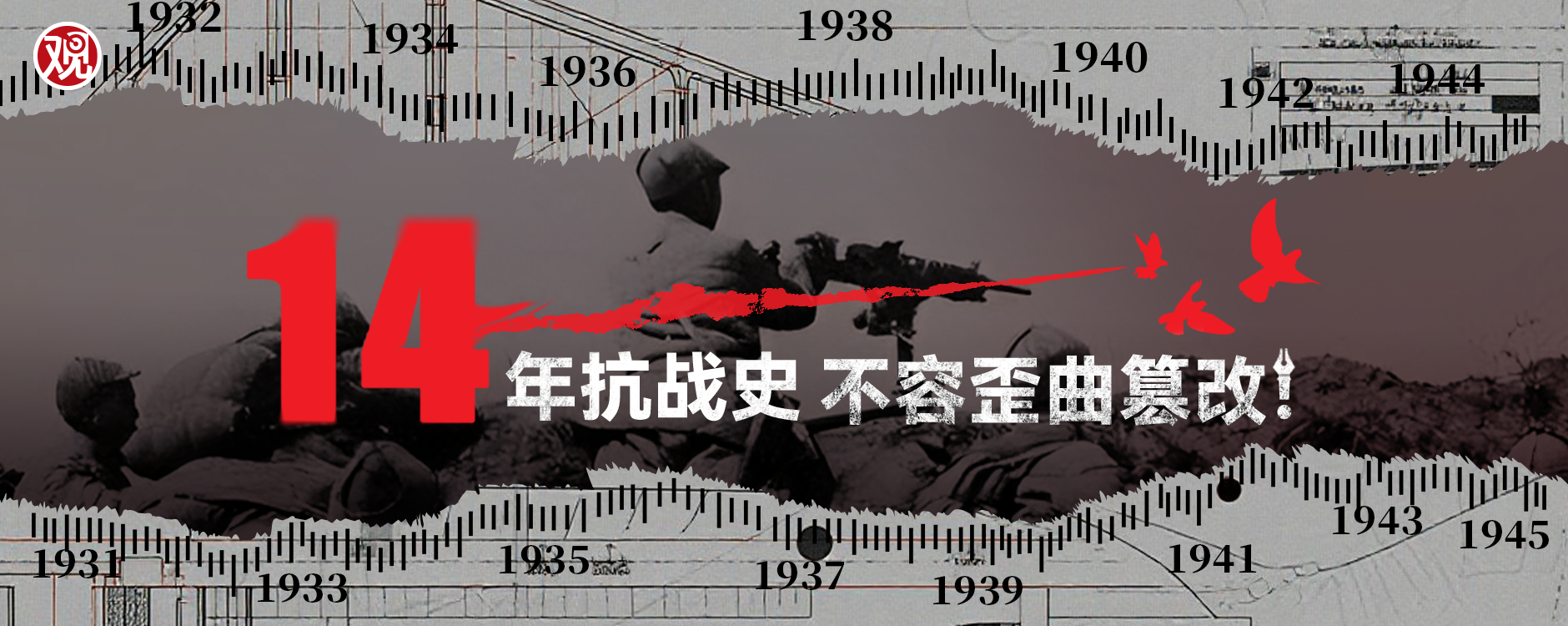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值此之際,觀察者網推出系列專題——“14年抗戰史不容歪曲和篡改”。
美國曆史學家、喬治城大學教授艾米麗·馬特森(Emily M. Matson),於今年年初在美國曆史學會年會上發表專題論文《共謀與冷戰政治:731部隊在中美關係中的漫長陰影》,詳細描述美國為了從日本手上獲取實驗數據從而掩蓋日軍731戰爭罪行的事實,並分析了這種美日共謀如何成為中美兩國關係的長期陰影。
這是一箇中國抗戰歷史真相被抹殺的典型案例,而揭露這一事實真相的,不止艾米麗·馬特森教授一人。
觀察者網近日遠程連線艾米麗·馬特森,請她講述作為美國曆史學家,在研究731部隊歷史真相時的感受,以及在當下中美關係緊張之際,如何正確看待中國14年抗戰史,在捍衞歷史真相的基礎上維護和平。

觀察者網連線美國東亞史專家艾米麗·馬特森 視頻截圖
【對話/觀察者網 高豔平】
“參觀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我深感震撼”
觀察者網:您關於731部隊歷史如何成為中美關係陰影的論文很有價值。我特別想了解,作為美國人,您最初是怎麼知曉731部隊這一在西方並不廣為人知的歷史史實的?當您發現日本軍隊對中國民眾犯下如此暴行時,您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艾米麗·馬特森 :**這要從我讀本科時説起。我本科主修東亞研究,學過好幾門東亞歷史課程,其中自然包括大量中國史內容,那時候我就知道了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的存在。
我最早接觸到的是南京大屠殺。2010年8月我從華盛頓特區飛往北京、開啓留學中國之旅的航班上,讀了張純如那本影響深遠的著作《南京大屠殺》。在飛機上我哭得非常傷心,周圍人可能都在納悶:這姑娘怎麼了?為什麼哭得這麼厲害?但對我來説,讀到那些內容實在太痛心了,簡直悲不自勝。
瞭解731部隊則是在稍後一段時間。我在高中階段,甚至更早的中小學時期,學過二戰歷史,但主要都是從西方視角——也就是美國和西歐的視角——來了解的。我們知道了納粹在集中營犯下的恐怖暴行,也略微聽説過比如太平洋戰場和美菲俘虜被日軍虐待的“巴丹死亡行軍”的情況。但我們從未學過日本軍隊對中國民眾及其他亞洲人民犯下的暴行。這讓我非常震驚,因為我從小到大居然對此一無所知,我覺得自己很有必要深入瞭解這段歷史。
觀察者網:那麼,是什麼促使您深入研究731部隊這個課題,並最終撰寫了這篇去年發表的論文?
**艾米麗·馬特森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東北地區與抗戰、偽滿洲國相關的博物館。
在做調研時,我去過位於哈爾濱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正是在那裏,我開始意識到,不僅是中國社會對731部隊暴行的集體記憶,還包括戰後盟軍最高司令部(即美國佔領軍)對暴行的掩蓋,以及部分731部隊成員被蘇聯紅軍俘虜後在伯力審判中被輕判,甚至根本未在東京審判中受到起訴——因為美國與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等人達成秘密交易,以獲取實驗數據為條件豁免了他們的戰爭罪責。
這些內容我之前略有耳聞,但在陳列館裏看到了相關展覽(據説至今仍在展出),深感震撼。

羣眾在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參觀
我意識到:在英美學術界,關於731部隊的研究其實非常少。雖然在1980年代有記者揭露了部分真相併公之於眾,1990年代也有所推進,但這仍不是美國社會廣泛討論的話題。
因此我認識到,深入研究這個課題非常重要——不僅是為了瞭解731部隊本身,更是為了釐清它與美國的關係,以及這段歷史如何可能影響至今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儘管事件發生在1940年代末。這確實是個被忽視的重要議題,我由衷希望能深入探索。
觀察者網:考慮到731部隊部分罪行證據可能較難獲取,您是如何一步步應對這些挑戰的?
艾米麗·馬特森:實際上美國在2010年代新解密了一批檔案資料,我居住地附近華盛頓特區和馬里蘭州大學的學者能夠獲取其中與731部隊相關的數據。
我知道冷戰結束後,國際上(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和日本)開放了更多檔案,1990年代初期以來,國際學術合作也大幅增加,這讓我得以利用這些資源。
雖然我未能親自訪問東北地區的當地檔案館,但我大量藉助了中國學術數據庫CNKI。由於我能説讀中文,得以查閲過去數十年間眾多關於731部隊及戰後美國掩蓋行徑的中國學術論文。我很幸運能在線獲取這些中文資料。
此外,我曾在2017年實地參觀過相關博物館。我的文章屬於歷史與史學史範疇,因此一手資料既包括731部隊歷史本身,也涉及對這些歷史如何被解讀和研究的過程。這就是我的資料來源。
不同羣體曾要求美國政府向受害者道歉
觀察者網:美國政府為了交換數據而掩蓋731罪行的歷史事實,在中國民眾中知曉度也不高。你曾在中國留學過,也認識了不少中國朋友,當發現自己國家的政府為獲取研究數據而掩蓋731部隊罪行時,您有何感受?作為學者,這一發現是否給您帶來內心衝突?
艾米麗·馬特森 :當然,我認為每個人都必須正視本國曆史中的陰暗面。每個國家的百姓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美國也不例外。這確實令我非常難過。我還了解到類似情況——戰後美國通過“回形針行動”赦免納粹科學家為美國所用。這讓我十分痛心。
鼓舞我的是,有些勇敢的美國人為此譴責美國政府,甚至要求道歉——不僅向受難的中國人,還包括美軍、英軍、蘇軍戰俘,以及我認為還有朝鮮平民和蒙古人等多羣體受害者。許多不同羣體都受到731部隊的傷害。美國前戰俘和英國戰俘也曾發起行動,要求美政府道歉並伸張正義。
1990年代,美國曆史學家謝爾登·哈里斯和史蒂文·恩迪科特等學者發表了大量關於731部隊及其後續生物戰指控的研究(我論文中引用的這個話題至今仍極具爭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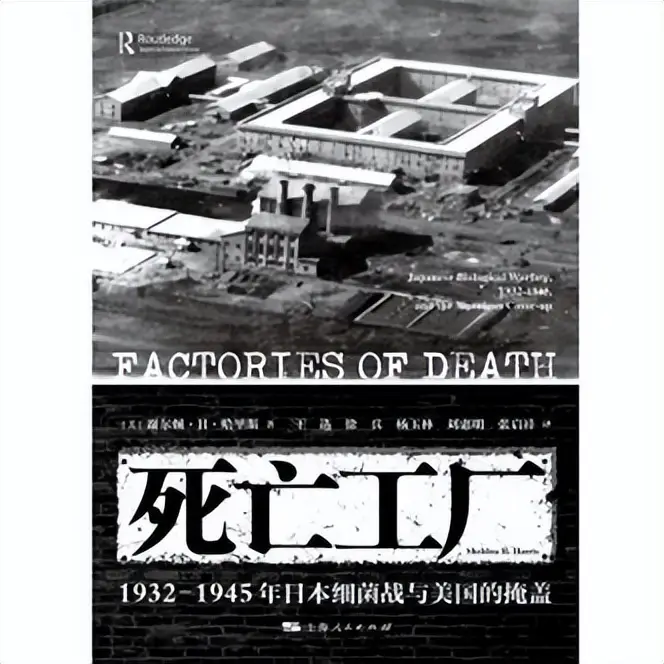
美國曆史學家謝爾登·哈里斯撰寫的《死亡工廠》,披露大量731部隊的歷史事實。
簡言之,這確實給我帶來些許內心衝突。作為歷史學者,這是我多年來必須面對的問題。我自認是個愛國者,但也敢於批評美國過去和現在可以改進之處。我承認這種張力確實存在,但真正的愛國意味着能持續指出國家的不足並推動改進——這個過程永無止境。這就是我的應對方式。
觀察者網:你在論文中説,中國政府利用731部隊歷史事實強化民眾的反美情緒,您用了“propaganda”這個詞。中國人可能會對此提出異議,你似乎暗示了中國操控歷史事實的一面,而非承認美國掩蓋歷史的行為。您想再解釋一下這個問題的立場嗎?
**艾米麗·馬特森:**這個問題確實讓我深思熟慮過。首先需要説明的是,英語中“propaganda”帶有貶義,但中文的“宣傳”更趨中性——我的論文裏出現這個詞時,採用的是中文語境的中性含義。我要澄清的是,中國揭露美國掩蓋731部隊罪行的做法完全正當,這是必要的歷史正義。與其用“操縱”這種帶有價值判斷的詞,我更傾向於中立的表述。
在地緣政治緊張時期,各國——不僅是中國,也包括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會援引歷史事件來強化立場。舉個例子:在2012年釣魚島爭端激化時,中國民眾面對日方行動,很自然就會聯想到20世紀日本對華的侵略歷史。同理,當中美關係緊張時,中國民眾追溯美國曆史上的侵略行為——不僅是731部隊問題,還包括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戰爭)、1999年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等事件——這實際上是國際政治中的常態反應。
在我看來,中國強調美國掩蓋731部隊罪行的歷史,在政治緊張時期更為突出,這本質上不是事實操縱,而是地緣政治互動中的自然現象。這些歷史記憶本身都是真實的,只是在特定時期會被更頻繁地喚起。
“被遺忘的盟友”:與冷戰時期地緣政治密切相關
觀察者網:您這樣解釋,我們的讀者會更容易接受。接下來一個問題,您可能對此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很多中國網友認為,西方媒體更強調歐洲納粹的暴行,而對亞洲尤其是日本侵華的暴行着墨較少,從而造成歷史問責上的不平衡?
艾米麗·馬特森 :我完全同意這種批評意見。我認為這種不平衡其實源於歷史記憶和冷戰背景。
您可能聽説過一位著名的英國中國史學者——拉納·米特(Rana Mitter)。他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我很喜歡這個説法。他在書中描述了中國是二戰期間西方“被遺忘的盟友”。
大約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冷戰開始後,中國和美國很快從盟友變成了對手。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更傾向於淡化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同時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德國納粹身上。這些前軸心國很快從美國的敵人變成了冷戰中的盟友。這就給歷史記憶帶來了一些非常複雜的因素。
我認為,西方之所以更強調納粹暴行,而不是日本的戰爭罪行,可能有幾個原因。
首先,這與美國自身的歷史記憶有關。我可以就此做很多批評。美國在二戰期間一直奉行“歐洲優先”戰略,亞洲戰場的衝突被視為相對次要。所以,美國雖然在太平洋地區和中國戰場也參與作戰,但總體來説,美國的重點始終放在歐洲。當然,對於英國和法國的歷史記憶而言,納粹暴行主要發生在西歐大陸,這也是地理和記憶上更貼近他們的原因。
此外,順便一提,美國和西歐其實也不太談論蘇聯對抗納粹德國的鬥爭。雖然這一點比日本侵華的討論稍微多一點,但仍然有限。我認為,這也與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現實有很大關係。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更深入地瞭解這些歷史背景。我認為,二戰在歐洲和亞洲的結束方式非常不同。比如我們剛剛在五月慶祝了“歐洲勝利日”, 納粹德國(德意志第三帝國1933-1945)在1945年5月就崩潰了,隨後分裂為兩個國家——西德和東德。於是,德國從一個戰時體制完全轉變為兩個全新的體制。戰後,這兩個新政府也完全不同。
然而,在日本,二戰後卻存在很多與戰時時代的尷尬連續性。例如,昭和天皇裕仁在東京審判中並未被起訴。相比之下,美、蘇、英、法四國組成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始清算德國法西斯的滔天罪行,這場審判在歷史上爭議要小得多。而許多日本人至今仍認為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正義”,這種看法影響了日本國內對戰爭歷史的記憶。裕仁天皇的“昭和”年號從1920年代一直持續到他1989年去世,也就是説,昭和時代從“九一八事變”之前一直延續到冷戰幾乎結束的時候。

受到審判的731部隊細菌戰戰犯。還有多位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頭子如石井四郎在美國的掩護下逃脱了罪行。
此外,在戰後美國主導的盟軍佔領日本時期(即SCAP佔領時期),還出現了一個叫“逆路線”(reverse course)的轉變。如果您看日本1946年的憲法,它其實是非常自由主義的。但隨着冷戰升温,美國並沒有繼續推動日本的民主化與去軍事化,反而希望重新武裝日本,將其作為冷戰中的盟友。
於是,許多前日本戰犯被釋放出獄,甚至重新擔任政府或企業中的重要職位,為冷戰做準備。這其中包括日本自民黨(LDP)的重要人物——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他因在偽滿洲國的活動而被列為甲級戰犯。
所以,這就是我對您問題的較長回答。我認為,從歷史角度看,這些因素導致了西方在對待日本戰爭罪行和納粹暴行時存在記憶和評價上的差異。
如果年輕一代對彼此國家知之甚少,又如何更好地處理雙邊關係
觀察者網:您之前提到過,美國或者西方很多人對“七三一部隊”並不瞭解,甚至可能只有少數人知道。那麼,您作為高校教授,如何在中美兩國,特別是面向年輕人,實事求是地講授這樣的歷史,以建設性的方式回應這種歷史評判中的不公?
**艾米麗·馬特森 :**我認為,無論是在中國、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在全球視野的框架下來教授歷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歷史往往被孤立地講述,好像只是“我們國家的歷史”,但實際上,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相互聯繫的世界裏,如果不從更全球化的視角去理解,就很難真正理解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學生應該學習世界歷史,包括其中的善與惡,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當今世界的複雜性。這種學習還應包括瞭解不同的視角。比如,中國的學生可以學習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民權運動;而美國的學生則可以學習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等等。我還可以舉出很多其他例子。
坦率地説,我認為中美雙方在彼此歷史的學習上都存在一些問題和偏見。但目前來看,據我觀察,在中國,普通中小學生對於美國曆史的瞭解,可能比美國中小學生對中國歷史的瞭解要多一些。因此,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我們該如何改變這一現狀?畢竟,很多人認為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如果我們的年輕一代對彼此國家知之甚少,我們又如何能最好地處理這一關係呢?
所以我認為這是我們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從我對學生了解的情況來看,Z世代(即出生於1995至2010年)人羣,可能比我們千禧一代(出生於1980至1994年)在學生時代學到的關於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等內容稍微多一些。而且,也有很多亞裔美國學生通過家族歷史瞭解這些歷史。但我認為,這方面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對未來中日關係持謹慎樂觀態度,更看好民間交流
觀察者網:我們回到“和解”的話題。您知道,德國在二戰中的罪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歐洲國家原諒,而日本在亞洲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對中國,至今仍存在很多未解的創傷。對中國來説,關鍵因素包括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比如否認戰爭罪行,同時強調自己是戰爭“受害者”;此外還有美國在戰後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掩飾。而且,過去一二十年,日本政客屢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在中國引發了持久的憤怒。
作為一位海外歷史學者,您如何評估這種二戰創傷在中日關係中的持續影響?如果我們參考歐洲的和解模式,您認為中日之間是否有可能走上一條類似的和解之路?如果要實現這樣的和解,又需要哪些必要條件?
艾米麗·馬特森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我會盡力回答。
首先,我認為歷史記憶並不是靜止不變的,它在每個國家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演變。以日本侵華的歷史記憶為例,自二戰結束以來,這種記憶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十年裏,這種記憶更多是地方性的。南京當地的學者、哈爾濱當地的學者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他們通過倖存者的口述、蒐集到的資料來還原這些暴行。但這段歷史真正成為國家敍事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如果您感興趣,我們可以再深入討論促成這一變化的不同因素。
關於靖國神社,我稍後也會提到。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問題,在中國受到更多關注,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後。其中一個因素是,1985年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這不僅引起了中國,也引起了韓國的強烈不滿。
靖國神社其實從明治維新時期就已存在,但在二戰後,特別是1970年代以後才變得極具爭議性。因為那時,不僅乙級和丙級戰犯,還有甲級戰犯——我相信包括東條英機在內共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被放入了靖國神社這一神道教的神社中。因此,這引發了日本國內很多抗議,實際上很多日本民眾對此也感到不滿,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認為這違背了政教分離原則;有的是因為戰爭死難者的家屬不滿戰犯與普通陣亡者被放在一起祭祀;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但國際上的抗議主要是在1980年代開始升温的。

日本,和中國、美國一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我必須説,日本社會中某些羣體,尤其是政界的一些人,確實存在歷史修正主義傾向。
靖國神社中的“遊就館”(Yūshūkan Museum)可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這裏祭祀着戰歿者和殉國者,作為靖國神社的設施,收藏並展示着戰歿者和軍事相關的資料。
我去年12月去日本時其實很想去參觀這個博物館。因為我聽説它非常有爭議,出於好奇我特別想去看看。但很遺憾,當時它因整修而關閉了。靖國神社本身是一個非常寧靜的地方,除非你瞭解它的歷史背景,否則你不會意識到它為什麼那麼有爭議。
這裏我可以分享一個我常在課堂上用來説明歷史記憶重要性的小故事:
加拿大流行歌手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在2014年曾參訪過靖國神社,但他參觀時並不知道這個地方存在這麼大的爭議。參觀完之後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張照片,並寫道:“哇,這真是一個寧靜的地方。”結果中國和韓國粉絲非常憤怒,他後來不得不刪帖並道歉,説“我愛我所有的韓國和中國粉絲”。一些韓國和中國政府官員也對此發表了批評。
這説明,即使是那些並不太參與政治的公眾人物,比如流行明星,也應該接受相關歷史教育,因為他們的影響力很大,可能會造成深遠影響。
回到靖國神社。它確實是一個非常複雜且具爭議性的話題,尤其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每當自民黨的政客參拜時,就會引發爭議。
不過我也想提到,其他一些日本政治家,尤其是在1990年代,對於正視歷史表現得更好。例如,在1990年代初,日本社會黨曾與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在1995年二戰結束50週年之際,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發表了著名的“村山談話”,明確為日本的戰爭罪行道歉。而在此之前,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也發表了“河野談話”,為所謂的“慰安婦”問題道歉,並明確承認日本軍隊確實做過很糟糕的事情。
此外,一些日本學者和記者也為揭露日軍暴行的真相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吉見義明(Yoshimi Yoshiaki)在挖掘“慰安婦”制度相關證據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記者本多勝一(Honda Katsuichi)早在1970年代就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日軍暴行的文章,題為《中國之旅》,他還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南京大屠殺:日本記者面對國家的恥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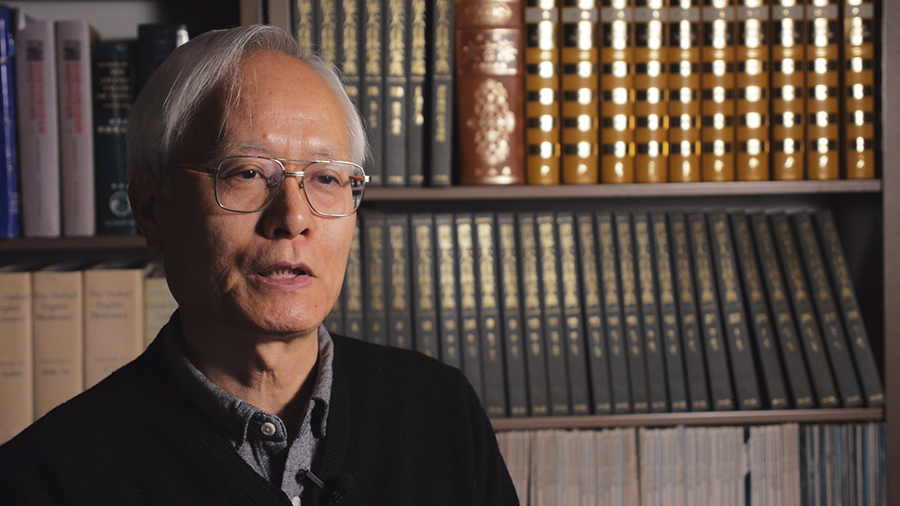
日本學者吉見義明
我本人也研究日本歷史,所以我知道,日本的情況其實非常複雜。媒體更多聚焦的是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但實際上,日本社會中也存在很多草根行動,甚至一些政治人物也在積極努力揭露這段可怕歷史的真相。
再回到您問題的第二部分,關於歐洲式和解模式的討論。
歐洲的和解模式,我認為,與冷戰背景有很大關係。戰後,比如北約(NATO)成立後,昔日的敵人——西德和法國——成為了盟友,並緊密合作。後來,這種合作也體現在歐盟中,法國和德國都是歐盟的重要成員國。因此,歐洲有很多多邊區域機制,讓昔日的敵對國家——軸心國和同盟國之間能夠合作。
相比之下,二戰後的亞洲採取的是國際關係學者所稱的“輪輻模式”(The Hub and Spokes Model)。也就是説,美國作為中心,與不同國家分別建立雙邊同盟關係,比如美國與韓國結盟,美國與日本結盟,但日本和韓國彼此之間在冷戰時期並不是盟友,儘管它們在1965年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冷戰期間也曾試圖建立一個類似亞洲版北約的組織,叫“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但這個組織於1977年解散,並不成功。
當然,現在亞洲有東盟(ASEAN),但在東北亞地區,並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北約或歐盟這樣的區域合作機制。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並不確定中日之間是否真的能走上一條類似歐洲的和解之路,因為缺乏這些已經存在數十年的區域合作框架。
不過,我認為兩國仍可以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甚至像東盟與中日韓(10+3)這樣的平台上繼續合作。
我對未來中日外交關係持謹慎樂觀態度,但我其實更看好的是民間交流。我認為,如果歷史學者、普通民眾,包括中國、日本和美國的老百姓,能夠更多地瞭解彼此,並促進積極的民間交流,這種基礎非常重要,那麼最終可能促成更高層次的外交和解。
正如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兩國的教育體系可以發揮很大作用,與此同時,鼓勵民間多元觀點的公開表達,這也非常重要。
當前中美局勢令人憂慮,但矛盾升級並非不可避免
觀察者網:正如您之前提到的,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中美之間存在很多誤解,美國從未經歷過被侵略或被佔領的慘痛經歷,您認為他們是否真正理解中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堅定決心?同時,中美之間有過“黑暗的篇章”——比如我們提到的美國幫助日本掩蓋“731”暴行真相相關歷史,也有“光明的篇章”(比如二戰時並肩作戰,以及1972年到2018年間兩國關係良好發展的時期)。您如何評估當前中美之間高度緊張的關係?今天我們紀念二戰勝利,是為了緬懷英烈,保衞二戰勝利果實,那麼中美雙方應該採取哪些步驟來來促進世界和平,避免掉入第三次世界大戰深淵?
**艾米麗·馬特森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首先,我想指出,美國雖然也經歷過被侵略的情況,但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上一次美國本土(即美國大陸)被入侵,是在1812年的戰爭期間。那是美國獨立戰爭後僅僅幾十年,當時英國再次入侵,並且還攻入了華盛頓特區,燒燬了白宮。我們的國歌《星條旗永不落》其實就是關於1812年戰爭以及抵抗英國入侵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説,這與中國國歌非常相似,因為中國國歌也是關於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如果比較兩首歌詞,你會發現它們都充滿戰鬥精神,都是關於保衞家園等內容,這點非常有意思。
但儘管如此,1812年的戰爭與中國的抗日戰爭完全不能相提並論。1812年戰爭的規模要小得多,而且發生在更久遠的過去,因此它在美國的歷史記憶中並沒有像中國的抗日戰爭那樣佔據重要地位。自那以後,美國大陸就再也沒有經歷過直接的入侵或攻擊,不過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在二戰期間確實曾遭受過襲擊。所以地方記憶可能會有很大不同。
我曾經有個來自阿拉斯加的學生,當我在課堂上説“美國自1812年以來就沒有被入侵過”時,她立刻糾正我説:“不好意思,我來自阿拉斯加,我們的一些島嶼在二戰期間曾被日本佔領。”我當時就説:“哦,原來是這樣。”
當然,這只是個例外情況,不是普遍現象。
您問到,美國人是否真的能理解中國人民抵抗殖民主義、反抗侵略的堅定決心?我認為,美國人是有潛力去理解的,因為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非常多元。大多數美國人要麼自己就是移民,要麼祖輩是從其他國家移民過來的,而這些國家很多都曾飽受戰亂之苦。他們來到美國,是為了尋找和平、自由和發展的機會。我認為,這其實也是美國最美好的象徵之一,比如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就代表着這一點。
所以我認為,有很多美國人確實珍視和平,也理解生活在戰亂國家是什麼感受,或者有家人親戚曾生活在戰亂之中。而且,正如我之前在採訪中提到的,美國的亞裔羣體越來越多,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就親歷過戰爭和侵略,比如華裔美國人、韓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還有來自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的移民。所以,如果我們把美國看作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組成的多元化國家,那麼我們就能夠通過彼此的經歷互相學習。因此,我認為很多美國人確實有潛力去理解這種反侵略、追求和平的堅定意志。
當然,教育體系仍需改進,尤其是在如何講述歷史的黑暗篇章與光明篇章方面,以及如何應對當前的雙邊緊張局勢。
回到您的問題:我如何評估當前的中美緊張關係?我確實對此感到擔憂。我注意到,來自中美兩國的媒體,尤其是來自北京和華盛頓的報道,都使用了非常強硬甚至好戰的措辭。我認為每個國家都需要關注的一點是: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交織影響。
舉個例子,在美國,很多政客可能對中國採取鷹派立場,因為這樣在國內眼裏顯得他們很強硬;同樣地,在中國,也可能有類似的情況,即為了展現對外的強硬姿態,外交上採取較為對抗的言辭。因此,這裏存在一種張力——既要處理好國際關係,又要顧及國內民眾的觀感,希望在他們眼中顯得強大或負責任。
所以,我對當前的雙邊緊張局勢感到憂慮。但中美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並不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地説,中美之間會繼續存在戰略競爭,但在許多領域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例如,在全球很多戰爭和衝突地區,如中東、非洲,甚至在俄烏戰爭問題上,中美都可以合作;在氣候變化這個全球性重大議題上,中美未來必須攜手應對;在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我們也需要共同探討如何進行監管;甚至在探索太空等新領域時,目前還沒有一個良好的國際規則體系來管理外太空交通等問題,中美也必須合作。
因此,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強調這些我們不僅應該合作、而且未來將不得不合作的領域,以此來促進和平。我們應該繼續尋找共同點,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那些領域。
此外,我之前提到了教育交流的重要性,除了政府間的外交聯繫,我們還應特別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無論是教育交流、文化交流還是民間往來。一位前美國大使——雖然他不是駐華大使,但曾代表美國國務院在中國工作,並在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時也在中國——他曾説,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中美關係的“肌腱”。正如人體有骨骼和肌肉,肌腱是將它們連接在一起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認為,我們絕不能低估這些民間交流的重要性。
除了政府間的直接對話以及軍隊之間保持溝通渠道暢通之外,我們還需要在地方層面加強交流,比如通過“姐妹城市”關係,或者美國某些州和城市與中國相應地區之間的次國家層級交流。舉個例子,我知道習近平主席年輕時曾在愛荷華州生活過,因此他與當地農民之間有一種特別的聯繫,這種地方層面的友好關係也很有趣。
以史為鑑,就是要正視歷史真相
觀察者網:今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日。有兩部電影——我想您可能聽説過——《七三一》和《南京照相館》,前者將在9月18日放映,後者已經放映,喚起了公眾的悲痛與憤怒。在抗戰勝利紀念的時候,作為歷史學家,您最想對中國的讀者或者觀眾説些什麼,關於這段歷史創傷?
艾米麗·馬特森 :是的,我聽説過這兩部電影。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新一部關於“七三一部隊”的電影將於九月上映,我們正計劃一起去看,我肯定到時候會控住不住情緒,甚至會流淚。
中國有個非常著名的成語,叫“以史為鑑”。我非常喜歡這個説法,我認為它非常重要。要“以史為鑑”,其中一個方式就是正視歷史真相,並通過不同視角互相學習——比如通過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以及各國曆史學家和其他學者之間的合作,我認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中國觀眾,我想表達我的哀悼與共情。中國人民在過去幾百年間經歷了太多苦難——戰爭、饑荒、流離失所。作為一名歷史學者,也作為一個普通美國人,我非常感激今年夏天能有機會重新回到中國,看到一個百姓生活祥和、經濟與社會取得巨大進步的國家。這不僅對中國來説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對世界來説也是如此。我相信很多美國人也會認同這一觀點,他們也為中國人民生活越來越好而感到高興。
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我在中國時,和我一位來自俄羅斯的朋友一起逛街(她很多年前曾和我一起在北京留學)。當時有位攤販問我們來自哪裏,回答完後他指着我們倆説:“兩個大國”。我趕快指着他和我們倆回答:“三個大國”。
當我們談到中美關係時,我想説,美國和中國是兩個偉大的國家。最後,我想真誠地祝願這兩個偉大的國家能擁有和平與繁榮,並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共同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