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呈:西方的“吸血鬼舞會”該結束了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禾呈】
一、從兩場歌唱大賽談起
《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茨表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其實,文化何嘗不是政治的延續。
就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2022年,美歐集體抵制俄羅斯選手參加“歐洲電視歌唱大賽”(Eurovision)。
那一年,不出意外,烏克蘭選手獲勝。來自烏克蘭的卡盧什樂團,身穿烏克蘭民族服飾,唱着富有民族特點的現代嘻哈,反覆唸誦關於母親的主題旋律。
那首名為《斯蒂芬妮婭》(Stefania)的歌,是樂隊主唱成員Oleh母親的故事,歌曲中有一句悽美的歌詞:“即使所有的道路都被摧毀,我也總會找到回家的路”。卡盧什樂團最終以總票數631分的戰績奪冠,歌曲確實催淚,但明眼人都知道,奪冠少不了政治加分。

被禁止參賽的俄羅斯哪能咽得下這口氣,歐洲不帶我玩,那我就自己玩。於是,3年後的2025年9月20日,俄羅斯隆重舉辦了“國際視界歌唱大賽”(Intervision)。
賽事籌備階段,普京就專門撥款7.5億盧布(約6500萬人民幣)支持資金,其中冠軍將摘獲3000萬盧布(約255萬人民幣)的獎金。臨近比賽,普京專門在上海合作組織峯會上主動引流,歡迎各國熱情參與。決賽當天,普京向大賽致以視頻祝賀,強調文化和音樂沒有國界,尊重傳統價值觀和文化多樣性是此次大賽的核心理念。

75歲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前來現場觀摩。這位平時在電視裏一臉嚴肅的老爺子,其實是個“音樂發燒友”,彈得一首好吉他,鍾情民謠和爵士,喜歡英國的披頭士,喜歡美國的辛納屈,更喜歡蘇聯的民謠歌手維索茨基。他還曾為自己的母校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校歌作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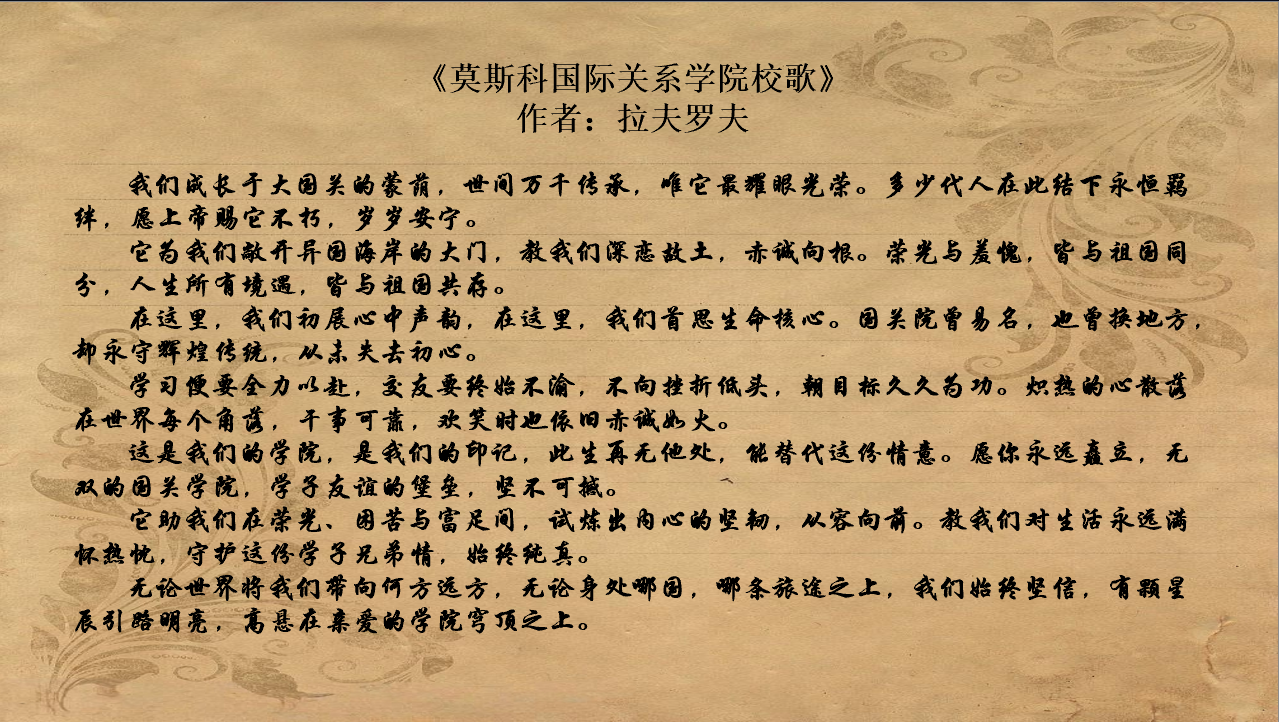
俄羅斯的這場賽事吸引了23國選手。中國是男低音歌手王晰參賽,女高音歌唱家吳碧霞則作為大賽評委。低音色的王昕被稱作“行走的大提琴”,他演唱了一曲《在路上》,“去遠方,去流浪,去他鄉”,娓娓傳達了中國人的羈旅思鄉。2013年,王晰曾隨中國海軍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13”軍演,在甲板上同俄太平洋艦隊歌舞團聯合演出,以醇厚低音和感染力贏得中俄官兵的喜愛,後來榮獲個人三等功。

此次歌唱比賽倡導的是“心繫祖國的音樂”,參賽選手需演唱帶有本民族特色的原唱歌曲。最終是越南選手德福奪冠,他歌唱了越南民族英雄“扶董天王”的故事。亞軍是吉爾吉斯斯坦選手阿曼,他以“遊牧三重奏”的形式演繹了一首《青春歲月》。卡塔爾選手以抒情的阿拉伯小調唱了一首《這就是你》,獲得季軍。三首歌曲驗證了一個樸素的道理: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真誠的,越能打動人。

很顯然,Eurovision所謂的“個性多元”與Intervision提倡的 “民族傳統”形成鮮明對比。兩場歌唱大賽的抗衡,並非單純的文化軟實力競爭,而是俄羅斯和歐洲文化漸行漸遠的標誌性事件。

二、歐洲的文化封殺
歐洲電視歌唱大賽原本是二戰後歐洲“文化團建”的產物,1956年在瑞士舉辦了第一屆,後來慢慢變成西方輸出價值觀的工具。1988年參賽的加拿大歌手席琳・狄翁就是通過歐歌賽展露頭角,後來那曲《我心永恆》火遍全球。
這些年,歐歌賽傳遞的個人主義、多元主義等新自由主義價值觀,與歐美主導的審美體系深度綁定。1998年以色列跨性別歌手Dana奪冠;2014年奧地利“變裝皇后”Conchita Wurst獲勝;2024年瑞士非二元歌手Nemo Mettler折桂。什麼是非二元歌手?就是性別認同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的音樂創作者,這完全符合美歐97種性別的新自由主義文化。
俄烏開戰後,歐美將文化領域作為 “非軍事對抗” 戰場,從體育到文學到藝術,對俄實施系統性文化封殺,本質是妖魔化俄羅斯形象,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與國際認同,看架勢是要開除俄羅斯的“球籍”。禁止俄參加歐歌賽只是其中的一環。
藝術無國界?不,西方的藝術有國界。英國倫敦交響樂團取消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曲》的演出;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暫停肖斯塔科維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上演;部分歐洲音樂學院移除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的教學曲目。而柴可夫斯基的旋律性、肖斯塔科維奇的思想性、拉赫瑪尼諾夫的抒情性,均對西方音樂發展有着深遠影響。
體育無國界?不,西方的體育有國界。國際奧委會、國際足聯、歐足聯禁止俄羅斯國家隊參賽,選手如若比賽需以“中立身份”(禁止使用國旗、國歌),即使“中立身份”也需滿足嚴苛條件,如未接受過俄政府資助。這一套,顯然是要把俄羅斯政府和俄羅斯人民區分開,又是一套分而治之的伎倆。
我們熟悉的阿布——阿布拉莫維奇——英國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的前老闆,被球迷稱為“切爾西最重要的男人”,苦心經營切爾西近20年,帶領球隊前後贏得21座冠軍,在2022年之後被英國人逼着賣掉切爾西,美西方紛紛對阿布制裁。阿布的經歷實際上反映了大多數歐洲對於俄羅斯的真實態度:
歐洲人內心從未真正接納俄羅斯人。有那麼一句著名的歐洲諺語:剝開一個俄羅斯人,會跳出一個韃靼人。

西方甚至連同俄羅斯有關的畫兒、貓兒、樹兒也要制裁。倫敦國家美術館2023年將法國印象派畫家德加的畫作《俄羅斯舞者》更名為《烏克蘭舞者》,這幅畫描繪三名系藍黃絲帶的舞者,美術館稱 “藍黃兩色象徵烏克蘭國旗”,故而更名。可問題是,該畫創作於1899年,當時烏克蘭屬俄羅斯帝國,“烏克蘭國旗”尚不存在。

西方的貓科動物聯合會還對俄羅斯的貓實施制裁,禁止俄羅斯貓海外參展,還把產於俄羅斯、能拉雪橇的“西伯利亞貓”更名為“歐亞森林貓”。歐洲禁止俄羅斯“屠格涅夫橡樹”參加“歐洲年度樹木”的評選,俄羅斯的這棵橡樹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所種,樹齡已200餘年。

有沒有人為貓、為樹發聲,它們招誰惹誰了?照這個架勢,我小時候玩的俄羅斯方塊是不是要叫烏克蘭方塊了?
歐盟前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曾有一句震驚四座的言論:“歐洲是花園,是人類能夠建立的政治自由、經濟繁榮和社會凝聚力的最佳組合,而世界其它地方大部分是叢林,叢林可能入侵花園。”

好好好,博雷利這老頭説的都對,歐洲花園的世界是“文明世界”,歐洲花園的價值是“普世價值”,彷彿歷史上的侵略者不是來自歐洲,而是來自亞非拉。
三、俄羅斯的文化突圍
面對美西方的“文化封殺”,普京自信地諷刺道,就讓西方過着沒有柴可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生活吧,但俄羅斯人沒有世界經典文化的滋養活不下去,不會“取消”貝多芬、巴赫或者歐亨利。
確實,殺了作品,封不住文明;捂住了耳朵,捂不住人心。幾百年後,沒人會記得“花園—叢林論”的作者博雷利,但仍有人會繼續閲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和美西方撕破臉後,普京在國際場合上頻頻提及“黃金十億”這個詞,強調説,所謂“黃金十億”國家(指的是人口約10億的西方國家)企圖維繫對世界的統治地位,對他國干涉主權、盤剝經濟利益並強加外來價值觀,這種政策破壞國際關係穩定,阻礙全人類發展。

“黃金十億”的説法由俄羅斯作家齊庫諾夫1990年在其專著《世界政府的陰謀:俄羅斯和黃金十億》中首次提出,後來成為俄羅斯特色政治術語。齊庫諾夫認為,約10億人的發達國家人口消耗了地球上所有資源的最大份額,並尋求擴大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控制,以確保本國的優勢地位。
這裏不得不提及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那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如果超過10億中國公民,都過上了跟澳大利亞人和美國人一樣的生活,那麼我們所有人都要走進一個非常悲慘的時期,我們的星球也不能承受。”
這句話其實暴露了西方潛意識的邏輯,只有美國人,歐洲人擁有享受美好生活的特權,中國人、俄羅斯人以及廣大亞非拉人民不配擁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中國的回答很簡單: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俄羅斯的回答也很簡單。普京強調,“黃金十億”國家的吸血鬼舞會該結束了!
俄羅斯民族的性格從來都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作為反制裁的一部分,俄羅斯除了在經濟上實施“進口替代”,文化上也搞 “進口替代”,打造了一批屬於俄羅斯、面向全世界的文化品牌,轟轟烈烈地掀起了一系列“文化反擊戰”。除了國際視界歌唱大賽,俄羅斯還打造了諸多文化品牌,具體如下:
首次舉辦未來運動會。普京親自出席運動會開幕式並致辭,強調“未來運動會不受政治形勢、任何形式的歧視和雙重標準影響,真正的體育運動將在賽場上大放異彩”。未來運動會通過“傳統體育+數字競技”融合模式,納入電子競技等新興項目,將冰球、籃球等傳統項目與虛擬競賽結合,吸引107個國家和地區參賽,形成了明顯的“非西方陣營”聚合效應。

首次舉辦反新殖民主義國際政黨論壇。俄羅斯精準把握全球南方國家反霸反殖的強烈訴求,成立“共同抵制新殖民主義”國際政黨論壇,促成來自50多國的400多名政黨代表與會。普京在賀信中指出,新殖民主義是幾個世紀以來“集體西方”對亞非拉人民進行掠奪和剝削的可恥遺產。俄羅斯願集聚力量,為建立民主的多極世界秩序而奮鬥。很顯然,俄羅斯要擔當國際社會反對單極化、追求多極化的第一旗手!

首次舉辦世界青年節。Z世代青年羣體作為全球輿論傳播的核心載體,成為各方爭奪的關鍵陣地。俄羅斯首次在索契舉行為期兩週的世界青年節,普京親自與會同青年面對面交流。這場活動覆蓋商業、科技、教育、環保等領域議題,通過脱口秀、辯論賽等年輕化形式,探討“Z世代如何應對全球挑戰”,吸引了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萬名青年代表,成功在西方的妖魔化俄羅斯的信息繭房中撕開一道口子。

俄羅斯還積極藉助金磚機制推動“去西方化”。作為2024年金磚主席國,俄羅斯直接搞了一波“替代工程”。金磚國家運動會對標歐洲盃、奧運會,讓新興市場國家的運動員有自己的舞台。金磚電影節叫板奧斯卡,專門展示非西方視角的電影。金磚文學獎跟諾貝爾文學獎打擂台,挖掘那些被西方忽視的優秀作家。
西方自己也沒有想到,經濟制裁加速了俄羅斯經濟的“去美元化“,文化封殺反倒助推了俄羅斯社會思潮的“去西方化”。俄羅斯衝在反霸第一線,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也逐漸掙脱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慢慢地打破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濾鏡。
四、第三條道路
國家是地理的囚徒。橫貫歐亞的俄羅斯宛如一個矛盾性人格,內心中東方與西方兩種人格總在相互角力。
歐亞兩股世界歷史潮流在俄羅斯發生碰撞,催生了俄羅斯民族深刻的矛盾性心理。俄羅斯既是西方又是東方,有時與西方對立,有時與東方對立,有時學習西方,有時學習東方。歷史上,斯拉夫派和歐洲派關於俄羅斯道路的爭論從未止息。
正因如此,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寫道,俄羅斯在文明認同上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
實際上,自彼得大帝時代以來,俄羅斯文明在歐洲文明面前都是弱勢一方、處於從屬地位。俄羅斯人往往“言必談希臘”“言必談歐洲”。
沙俄時代的貴族以講法語、德語為榮。貴族子女必須學習歐洲禮儀,否則不得繼承爵位。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就是來自德國的公主。

蘇聯時期,俄羅斯精英同樣對西方文化嚮往不已。赫魯曉夫1959年訪問美國時主動求見瑪麗蓮·夢露。波蘭代購的牛仔褲、東德流入的錄音機、來自美國的唱片都是蘇聯民眾之間的“硬通貨”。

葉利欽時代,俄羅斯更是全面倒向西方,從政治制度到經濟模式到社會生活幾乎全面照搬西方模式。為了嘗一口肯德基,莫斯科居民不惜排上2個小時的長隊。
但是,世道變了。世界慢慢迎來了覺醒時代,跳出了“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俄羅斯也迎來了覺醒時代,主動思考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慢慢同西方拉開了距離。
俄烏戰爭的外力更是將俄羅斯社會的自我認同達到頂峯。面對美歐的文化封殺,面對來自北約的高烈度對抗,俄羅斯人反倒更清楚自己是誰,更清楚自己從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逐漸確立了自身的身份、民族、國家和文明認同。
2024年,普京在新修訂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中,明確將俄羅斯確立為“文明型國家”,一個和歐洲迥然不同的文明,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東正教—東斯拉夫—歐亞文明。
普京曾向外界展示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個人祈禱室,在那裏他總結了俄羅斯民族的性格特點:俄羅斯人注重精神性,西方人注重物質性。
當西方人凍結並企圖挪用俄羅斯的海外資產,普京痛斥道,説什麼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契約精神,西方和400年前一樣還是海盜。
這讓人想起彼得大帝的一句名言,法國人看重香水(духи),我們看重心靈(духи)。在俄語中,“香水”和“心靈”兩個單詞的拼寫一樣,但是發音有區別。

普京的謀士蘇爾科夫曾寫下“混血兒的孤獨”一文,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將面臨地緣政治的“百年孤獨”。正如亞歷山大三世所言,俄羅斯的盟友只有陸軍和海軍,換句話説,俄羅斯的盟友只有自己。在這樣的百年孤獨中,俄羅斯終將找尋自己的道路,沿着“第三羅馬”塑造“第三文明”,這是既非東方既非西方的第三條道路。

普京能帶領俄羅斯走出“第三條道路”嗎?未來的俄羅斯還會在東西方之間搖擺麼?
這一點,恐怕只有時間能夠給出答案。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