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 | 女性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階級視角
guancha
10月13日至14日,全球婦女峯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
30年前,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以行動謀求平等、發展與和平”的主題激盪人心;30年後,中國再次召開全球婦女峯會,“我們將繼續繪製藍圖,並加強落實”,推動全球婦女事業發展的決心歷久彌堅。
站在中國近現代史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殖民和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同時以最終建設社會主義為目標;在這一斗爭中開展的“婦女解放運動”,包括“婦女”一詞,既是階級的也是性別的。
鍾雪萍老師在《女性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階級視角》一文中,站在民族革命和階級革命的語境下重審“性別話語”在中國的理論旅行,考察“女性”和“婦女”兩個概念背後不同的政治意涵,從而探討現代中國婦女主體的具體生成過程。
通過分析“婦女”一詞何以在當下“遇冷”的深層原因,她指出伴隨着改革開放時代“去政治”文化轉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興起,“女性”一詞的“迴歸”一方面提供了西方式性別平等的理論設想,另一方面也讓性別敍述被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深深吸納,從而引發新語境下的新問題。
最後,文章反向追問:當婦女解放在中國面臨“性別麻煩”,是不是在本質上也反映出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自身的一種“階級麻煩”?
在全球婦女峯會召開之際,觀察者網轉載此文,供讀者參考。文章系鍾雪萍老師2022年11月30日在杜克大學“女性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會議上的發言,原載於《現代中文學刊》2023年第3期。
【文/鍾雪萍,譯/王斐然】
一
在過去四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尤其自90年代初“性別”這一概念引入中國以來,中國學者(多數為女性,但也有男性學者)一直在直接或間接地討論,應該如何理解西方女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我在中國參加的不少與此有關的會議、工作坊和各種形式的活動中,總有這方面的討論,其中不乏激辯。
比如,2010年在北京舉行的題為“社會主義婦女解放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討論會、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與《婦女研究論叢》雜誌聯合舉辦的“革命與婦女解放”研討會、2018年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國婦女解放:文化想象與社會實踐”會議,以及2019年夏天,十多位學者(包括若干男性)就美國女性主義中國歷史學者白露(Tani Barlow)的著作《中國女性主義中的婦女問題》(2004),在上海師範大學進行討論交流,對“婦女”(woman/women)這一概念(我下文會討論這個術語)以及其他相關議題發表各自的看法。[2]疫情期間,繼續參與了一些網絡會議。在那些會議上,討論和爭論仍在繼續。

Tani E. 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4(左);湯尼•白露 著,沈齊齊 譯《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右)
就像其他眾多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一樣,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經由各種活躍的學術交流,中國譯介了不少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和主要論述。與此同時,這些理論和論述在中國也遭遇質疑,而且大都來自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頗為了解的學者。
當代中國的這些背景,與本次會議的核心議題有諸多聯繫,我將在下文中作一些簡短的討論。
二
我今天發言的標題看上去有點寬泛,但它的副標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階級視角”旨在把討論變得具體。確切而言,我將再次回到並分析兩個不同的中文用詞“婦女”(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反思它們背後的階級意涵和內部張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這些意涵和張力與(西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遭遇的“性別麻煩”有關,如何思考其中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歷史層面上的政治原因。

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明確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圖為山東濟南二賢街婦女投票選舉人民代表。
事實上,任何一個瞭解那些圍繞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女性主義爭論的人,都知道,在中文裏,這兩個詞語之間一直存在着張力。原因在於跟英語中的“女人”(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相比,中文的“婦女”和“女性”內含更多與歷史相關的政治含義。
論爭也主要與怎樣理解這些含義有關,尤其與怎樣理解中國革命及其政治語境和歷史意義有關。也就是説,雖然這兩個詞語都可被視為“現代”的“語言事件”,但與對應的英文詞語相比,內在於二者的歷史和張力更為豐富。這一特徵與頗為複雜的中國現代歷史和政治鬥爭直接有關。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自此,全國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婦女第一次與男子一樣分得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圖為河南洛陽專區洛陽縣平樂鄉婦女正在登記領取土地證。
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我討論這兩個詞之間的張力與階級問題的關係。[3]今天,我將繼續這一思路,但着重着眼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的階級性質,與內在於“婦女/女性”的階級含義之間的關係。
可以説,在很多方面,這兩個用詞一直或隱或現地反映着20至21世紀中國的革命、反革命和“去革命”之間的矛盾、辯證及其特有的“階級話語”。如果這兩個中文用詞都有(儘管是不同的)階級內涵,為什麼相較於“女性”,“婦女”這個詞會招致更多女性主義者的不滿?而對“女性”一詞,大多數女性主義者則少有同樣程度的關注和不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可以在“女性主義理論和帝國主義”這一主題下來再一次思考並討論這個問題。
三
我將通過以下三點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討論:(1)在階級意義上思考婦女解放和中國民族解放的關係;(2)簡單回顧“婦女”一詞的革命性起源;(3)改革開放時代,“去政治”文化轉向與“女性”一詞的崛起或迴歸。考慮到本次會議的核心議題,我最後會提出幾個問題,並以那些問題來結束這個發言。
1. 在階級意義上思考婦女解放和中國民族解放的關係
白露教授在她那本頗受關注的專著《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裏使用“誤用”(catachresis)這一概念,來探討現代中國的“婦女話語及其運作方式”如何幫助生產“現代”婦女主體。她的研究重點放在若干跟中國歷史相關的“運作方式”上,探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着“現代”中國婦女主體的構建及其未完成性。在這個意義上,“誤用”這一概念凸顯了現代中國婦女主體形成過程中的辯證以及發生軌跡,怎樣與歷史相勾連。
在題為“理論化‘婦女’”(“Theorizing ‘Women’”)的一章中,白露教授首先提及“婦”這個字的“歷史性誤用”,然後將其與現代中國“婦女”一詞的演變聯繫起來。她特別指出,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個詞被納入“國家話語”範疇。白露教授的這一論點,與很多女性主義學者傾向於把中共領導的婦女解放定義為“國家女權主義”(state feminism)相呼應。確實,“國家女權主義”這一提法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之際,並很快成為(尤其是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和評論者習慣採用的提法。[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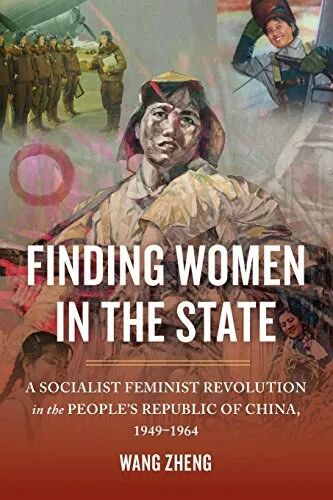
關於中國的“國家女權主義”,已有相當數量的英文出版物。以最新相關論著為例,可參閲Wang Zheng,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有趣的是,在這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意義上的“國家”和“婦女”之間相聯繫的關注中,經常被忽略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曾經的被壓迫民族(oppressed nation)和“婦女”之間的關聯。[5]如果我們把“婦女”與“民族(國家)”放在一起思考,並在“階級性”的大前提下強調兩者之間的聯繫,會有怎樣的發現?
在西方學界,有一個流行但值得商榷的論點,即馬克思的“階級”概念被髮錯地址,寄到“民族”,被“民族主義”取代並佔上風。這個論點也被不少研究中國現代史的西方學者接受。[6] 但是,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婦女問題和婦女解放引入這一討論,便可發現這類討論基本無視婦女問題及其重要的歷史和理論內涵,暴露出其自身的“男性中心”以及思考中的盲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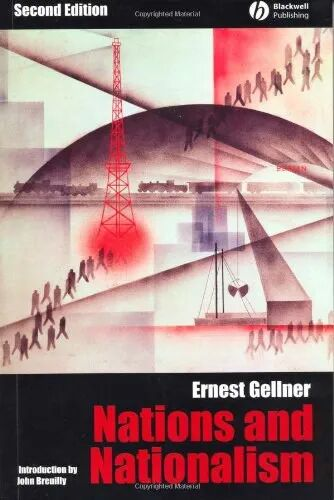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1983
我在此希望強調一個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殖民統治和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同時以最終建設社會主義為目標。在這一斗爭中開展的“婦女解放運動”,包括“婦女”一詞,從頭開始,就既是階級的同時也是性別的。正如林春對本發言稿回應中指出的,中國革命中的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貫穿始終,而婦女解放是其題中應有之義,不可能獨立於民族和階級的解放而完成。這不僅僅由於婦女參與在革命中,併成為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是因為具有雙重性的共產主義革命,歸根到底同時就是“女權主義”的。
讓我進一步展開一下。
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一書中,作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以第一章“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作為該書的開頭。[7]這一章雖然簡短,但基本上把中國革命置於中國和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階級歷史關係,以及中國內部的階級社會狀況的背景之下。邁斯納呼應馬克思的一個觀點,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為中國社會革命創造條件的“無意識歷史工具”。[8]
他指出:“在一個近代經濟部門被帝國主義所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幾乎不能指望羽翼未豐的中國資產階級除了充當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屬品之外還能幹點別的什麼事情,不管這個階級中的個別成員可能對外來統治滋生多麼強烈的民族主義憤恨。”[9] 邁斯納繼續説:“現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以現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為標誌:一個弱小的資產階級和一個更為弱小的無產階級。但是,並非只有這兩個現代階級是弱小的;現代中國歷史狀況的基本特徵是中國社會所有階級的軟弱性。”[10]
因此,邁斯納認為,上述條件使得“獨立的政治力量”——包括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中國現代政黨——的運作成為可能,與其説它們各自代表社會階級的不同利益,不如説是它們作為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佔有者,決定了社會各階級的命運。[11]

莫里斯·邁斯納 著,杜蒲 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作為西方少數持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中國歷史學家之一,邁斯納在認識到中國現代政治角力與社會階級之間關係的同時,把中國共產黨視為一個缺乏自身階級認同的“獨立政治力量”,實在顯得有點簡單化(reductive)。
簡單化的原因在於,在邁斯納的理論視野裏,“階級”沒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被清晰地理解為既是“結構的”(structure)也是“形成的”(formation)。而這一觀點,恰恰在中共對中國革命的解釋框架裏得到更確切的表述。所謂弱小的工人階級相對於民族資產階級而言是一個成長中的、強大的階級力量。而中國與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也滲透着超越國界的階級內容。

新中國建立後,大力開展掃盲運動。從農村到城市,成千上萬的勞動婦女走進識字班、民眾夜校、職工業餘學校,參加掃盲學習。圖為福建福州船民婦女在練習寫字。
在研究思考中國革命,社會主義時代和後社會主義時期以及各種相關的歷史和理論問題時,林春始終堅持首先從階級角度來理解現代中國和世界。[12] 她的新著《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討論到女權與階級鬥爭的關係。其中,“階級與民族: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不平衡發展”一節呼應了馬克思主義對20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和歷史狀況的思考和批評。她用“重疊式不平衡發展”(compressed uneven development)取代通常的“結合式發展”,因為前者更強調“共時性的動態過程,包括被壓縮的時間中空間發展的不均衡”。[13]
林春認為,在這個“被壓縮的時空運動”中,國內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的結構性階級性質相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霸權無情推進的過程,造成一個曾經擁有無與倫比財富的中華文明的陷落”;而“外國侵略和由此產生的半殖民地中國,是產生後者社會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同時,作為全球資本主義擴張“最薄弱環節”的一部分,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的推動進程”恰恰決定了中國的反抗鬥爭及其階級性質。她進一步指出:
逐漸衰落的清朝淪為資本主義叢林的犧牲品,民族反抗鬥爭亦隨之興起,中國在其所處的全球局勢中成為一個“階級的民族”(class nation)。……在敵對帝國主義勢力的圍攻下,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顯而易見的“階級地位”使其抵抗具有民族和階級解放一以貫之的特徵……正是這種歷史條件,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具有社會主義前瞻性的創新型工人階級先鋒組織。這個形成中的民族國家被剝削與壓迫的歷史地位,為形成一種革命民族主義的集體自我意識提供了支撐。[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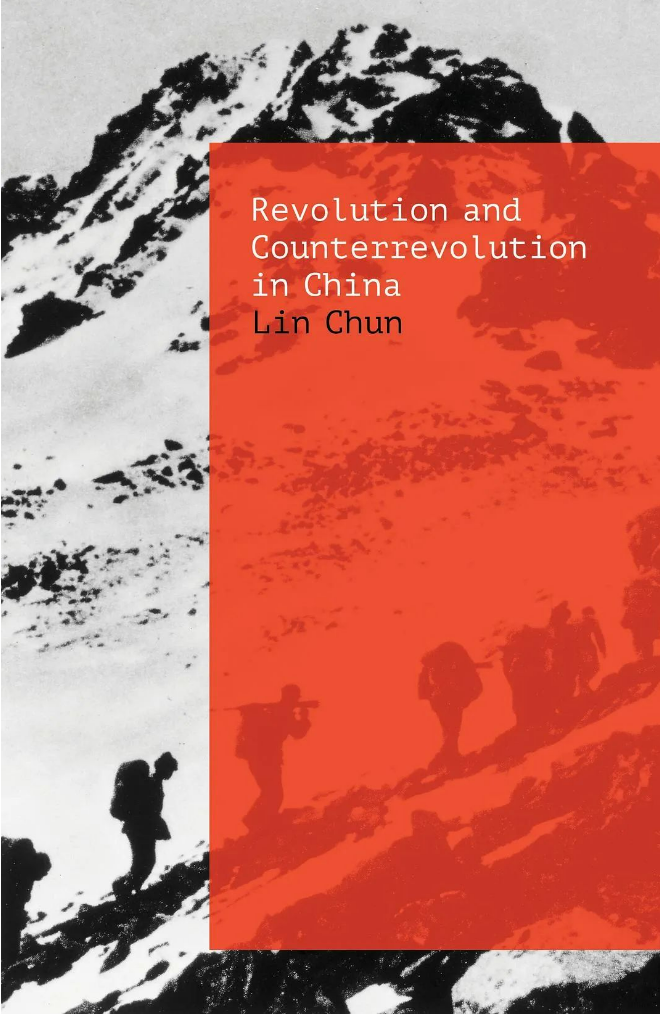
Lin Chun,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The Paradoxes of Chinese Struggle,Verso,2021
因此,本質上呈現一種對抗關係的“階級民族”(class nation),必須置於資本主義在其初始地區的發展及其全球化擴張的進程和產生的影響,以及與之相對的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各種鬥爭,努力尋找替代方案以求建立一個資本不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和在這些鬥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過渡形式等歷史背景下,加以理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林春指出必須反對“自由主義修正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都有”的“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輕視”,這種輕視“忽略了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大背景。而正是這些危機,讓中國爆發了全面革命”。[15]
我順便提一句,也正是由於這場革命的階級屬性及其果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新中國“榮獲”了西方帝國主義對她的仇視。
2. 簡單回顧“婦女”一詞的革命性起源
“中國爆發的全面革命”的階級性質,同時界定了中國婦女解放的階級屬性。也就是説“婦女/女性”之間的張力及其辯證,存在於上述提到的“被壓縮的時間”之中,與革命領導的婦女解放(以及對其的不滿)的階級屬性密切相關。
“婦女”是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佈的《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中選擇的用詞。決議特別指出,沒有婦女解放的目標,整個革命綱領就不完整。它還規定“中國共產黨認為婦女解放是要伴着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6]明確了“幫助婦女們獲得普通選舉權及一切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保護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舊社會一切禮教習俗的束縛”三項任務後,決議進一步規定,“這些運動,不過為達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須經過的站驛,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婦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由此,“婦女”一詞作為階級話語被明確政治化,日後成為中國革命話語中的一個關鍵詞。關於其含義的論爭仍在持續。

1907年愛國女校啞鈴操
當然,並不只有中共領導的革命最先開始呼籲婦女解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中國改良派或革命派的男女知識分子,都從各自的立場和角度表達了改變婦女境況的觀點。不論直白還是隱晦,他們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和辯論,以及他們對革命的呼籲,都與中國正作為為獨立和解放而鬥爭的階級民族,這樣一個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

何震夫婦與眾人合影。前排左起:何震、劉師培、柳亞子,後排左起:曼殊、朱少屏、鄧枚、林立山、韓筆海。
首先,被有些女性主義學者視為中國第一位女權主義者的何震(何殷震)。她在20世紀初寫下《女子解放問題》《論女子勞動問題》《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等多篇文章。除了關注傳統文化如何控制和約束婦女之外,何震還敏鋭地覺察到社會經濟結構與婦女(“女子”)之間的關係,並同時質疑現代歐洲婦女“自由”背後的經濟和階級問題。
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何震堅持認為,婦女必須在不依賴男人的情況下尋求自身解放。她指出婦女必須打破傳統性別關係的重要性,這個傳統性別關係是一個女性依賴男性的系統,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引入一個堅實的社會維度。她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對上層婦女與下層婦女之間同樣存在的階級壓迫的認識,以及對歐洲婦女的“虛假自由”的質疑,都標誌着“中國的女性主義”,從一開始就在社會—階級意識中孕育而生,並且以在理論上持有一種不妥協姿態為特徵。[17]
第二個例子是與20世紀初何震的論點相呼應的魯迅。他在談到“婦女問題”時更加不遺餘力地呼籲需要一場革命。確實,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的魯迅,始終支持婦女解放,並堅持認為只有在中國進行一場徹底的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婦女解放。

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女代表與領導合影。
很多中國人熟悉的例子之一,就是魯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的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關於為什麼這個問題比關注易卜生戲劇裏的中產階級妻子下決心離家出走更為重要,魯迅進行了切中肯綮的討論。
“走了以後怎樣?”魯迅問道,“伊孛生並無解答”,他用他標誌性的諷刺語氣指出,“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18]
“娜拉走後怎樣?”魯迅的問題超出了原著小資產階級的個人選擇範疇。對於娜拉來説,儘管她已經覺醒,但她“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説:“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19]
在此,魯迅間接響應了何震的觀點,繼續發問:“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20]
通過將婦女解放與反對現有經濟制度聯繫起來,魯迅認為我們需要一場真正的革命——用他的話來説就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儘管他承認自己也不知道這場革命“從那裏來,怎麼地來”。

Lydia H.Liu, Rebecca E.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這些一百多年前提出召喚革命的“婦女問題”討論,在中國革命及其婦女解放事業取得重大成就的幾十年以後的今天,仍然沒有過時,對討論婦女解放以及性別與階級之間關係的問題,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魯韌導演,張瑞芳主演,根據李準小説《李雙雙小傳》改編的電影《李雙雙》,1962年上映
可是,“婦女”這一用詞本身卻似乎未能同樣保持新鮮。這就引出下面第三點。
3. 改革開放時代,“去政治”轉向與“女性”一詞的崛起或迴歸
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伊始,中共領導的婦女解放,以及“婦女”一詞,就開始遭遇各種女性主義者的批評。這些批評和後來的“性別”轉向,同時又都伴隨着“國家”(state)從性別平等宣傳教育的公共領域中撤退,以及在同樣的領域裏出現的(用Danial Vukovich的話來説)“自由主義的報復”,(或隱或顯地)譴責整個中國革命,並把質疑延伸到革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婦女解放。[21]

孟悦/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於此同時“浮出歷史地表”的“新”批判視角,質疑“婦女”的所謂中性/雄性化,呼喚找/招回“女性”及其被遮蔽的“女性特質”。[22] 在這些“新”走向和“新”視點下,“婦女”這個字眼,隨同對“婦女解放”的被質疑,遭遇到“性別麻煩”:被視為“革命男權主義”的產物,在男性為座標的基礎上提倡男女平等,缺乏對“女性特質”的充分認可和認識……等等。西方女性主義認為真正的婦女解放應該是自下而上的。對此觀點的接受也很快成為評估和判斷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婦女”一詞的“自然”標準。
延續這一標準,除上述的沒有充分認可“女性特質”以外,還認為婦女主要受制於“國家利益”,缺乏從自身出發的“自我”意識等等。在文化層面上,“婦女”這個被認為不夠“女性化”的形象也成為公眾嘲笑的對象。內涵於“婦女”的階級和女權雙重意義及其政治性,則在這樣的“去革命”“去政治”的語境下被消解。可以説,在“後婦女解放時期”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反向的“婦女”性別歧視。取而代之的“女性”一詞,象徵着被壓抑的“女性氣質”的迴歸,把婦女問題從革命領域重新歸類到“女性”“個人”“身體”“喚起性慾的存在”以及與男性二元對立的思考層面裏。
可以説,在西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自身面臨的“歷史的狡計”(cunning of history,Nancy Fraser語)的全球影響力“協助”下,我們遇到了中國版的“歷史的狡計”。[23]一方面,就“男女平等”而言,面對國家從明確維護性別平等的話語和政策中撤退,“性別”概念的興起,有可能為增強性別平等政策和社會文化實踐提供必要的理念和批評,在某種程度上它也確實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同時維護和堅持婦女解放的遺產和實踐,“去革命”的“女性”和“性別”概念容易陷入個體的單薄,成為小資理念的收容品。改革開放以來,對女性和女性氣質的強調,在出現脱離歷史語境的“女性本質化”走向的同時,在市場化的大潮下,“女性特徵”迅速被消費主義的慾望及其邏輯所吸納所界定,向樂於站在資本一邊而非勞動一邊的小資產階級性別主體傾斜,其“性別意識覺醒”的思維方式往往以簡單的“男/女二元對立”為前提。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Routledge,2006
換句話説,在“後革命”的階級轉型中,“婦女”的衰落伴隨着“女性”的興起/迴歸,伴隨着城市小資產階級文化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以及後者愈發彰顯的其自身階級和性別訴求的某種結合。
不過,中國革命的深厚性以及內在其中的婦女解放和階級解放的直接關係,在轉型後仍然被繼續不斷書寫和認識,無論是在歷史層面,還是當下現實層面,譬如打工文學,尤其是來自皮村的女工文學,等等。
四
必須指出的是,與此同時,在中國這個“後婦女解放”的歷史語境裏,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也遭遇了自己的 “性別麻煩”。正如我在發言一開始提到的,面對上述的各種矛盾,許多中國女學者通過對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的歷史和遺產的重新強調和思考,質疑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侷限性和話語霸權。
我們也許可以問,這一在中國面臨的“性別麻煩”是不是在本質上也反映出(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自身的一種“階級麻煩”?
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我以為可以進一步提出和討論其它相關問題。由於時間關係,無法進一步展開,但我想以下面三個問題來結束我的發言:
1. 帝國主義發展的歷史中是否存在性別維度,後者又如何與階級(和種族)的維度產生聯繫?與馬克思主義的“離婚”(divorce)是否以及怎樣阻礙了(西方)女性主義在這方面的思考和理論化?
2. 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如何不再繼續躲在非西方世界的反帝鬥爭背後,走到前台直接面對和處理“帝國主義”這個問題,並與之鬥爭?
3.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有可能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做出貢獻嗎?如果有可能,應該怎麼做?如果沒有,那又是為什麼?
謝謝大家!
註釋
1 本文基於2022年11月30日在杜克大學“女性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會議上的發言。
2 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有一個翻譯備受批評的中譯本,湯尼·白露《中國女性主義思想中的婦女問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 Xueping Zhong, “The Clas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Women’s Liberation and Twentieth-First-Century Feminism”, Feminis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ing Zhu and Hui Faye Xiao, ed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76-102.
4 關於中國的“國家女權主義”,已有相當數量的英文出版物。以最新相關論著為例,可參閲Wang Zheng,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5 “nation/民族(國家)”跟 “nation-state/民族—國家”含義不同。
6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1983.Gellner對民族主義的討論引發討論和質疑。1997年,作者在《新左翼評論》上發表題為“對批評的回應”(“Reply to Critics”)。Gellner 的這一觀點也影響了一些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如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8、9、10、11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李玉玲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頁;第5頁;第6頁;第7頁;第11頁。
12 參見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Marxism,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3 Lin Chu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Verso, 2021, p.8.
14 Lin Chu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10-12.
15 Lin Chu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37
16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1冊)》,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年,第50頁。
17 He-Yin Zhen, “On the Ques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Lydia H.Liu, Rebecca E.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3-72.
18、19、20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66頁;第168頁;第170頁。
21 Danial Vukovich, China and Orientalism: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RC, Routledge, 2012.
22 對於這種與冷戰有關的 “性別轉向”的批判,詳見Lingzhen Wang, “Wang Ping and Women’s Cinema in Socialist China”, Signs 2015 vol.40, no.3, p.589-622.
23 Fraser, Nancy,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Cahiers du Genre, vol.50, no.1, 2011, p.165-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