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國學大會| 張維為:作為元敍事的文明型國家話語
guancha
中國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具有內源性文明動力、能汲取眾長而不失其魂的“文明型國家”。這一敍事不僅挑戰了西方中心論下的“歷史終結論”,也動搖了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話語霸權。
10月14日,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在上海開幕,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分論壇“從世界看中國:文明的賡續與創新”發表主旨演講,不僅回顧了他與世界中國學論壇的淵源,還從《中國震撼》引發的思想震盪,到與福山的世紀之辯,再到全球範圍內“文明型國家”話語的興起,勾勒出一條清晰的思想軌跡:中國不僅正在重新定義自身,也在重塑世界的認知圖景。文明型國家不僅是對西方“民族國家”範式的超越,更是對“歷史終結論”與“普世價值”敍事的根本性質疑。
本文為演講原文,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演講/張維為】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作為元敍事的文明型國家話語”(Civilizational State as a Meta-Narrative)。
參加今天的會議很有感觸,因為15年前的2010年11月,我參加了這個大會的前身(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論壇,我當時也是在第一分論壇宣讀了論文《“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中國模式》,系統梳理了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八大特徵(four supers and four uniques),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super large population)、超廣闊的疆域國土(super vast territory)、超悠久的歷史傳統(super long history)、超深厚的文化積澱(super rich cultures),以及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其中每一項都是古代與現代的結合(a blend of ancient and modern),在中國模式引導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這些特徵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
這些觀點在會場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當時爭論的主要是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中國算不算現代國家,而我的結論是中國模式和中國現代國家都是客觀事實,而且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已經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模式和西方現代性的超越。
1個月後,我又出版了《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出乎我的預料,此書很快就成了暢銷書(迄今已經銷售200多萬冊,10來種語言翻譯)。這本書當時引起了更大的爭論,有文章形容“中國模式派”和“普世價值派”的爭論白熱化。有人甚至針對“中國震撼”,寫了“中國遺憾”的長文。隨後不久,2011年6月,“歷史終結論”作者福山先生(Fukuyama)在上海與我就中國模式進行了一場影響頗大的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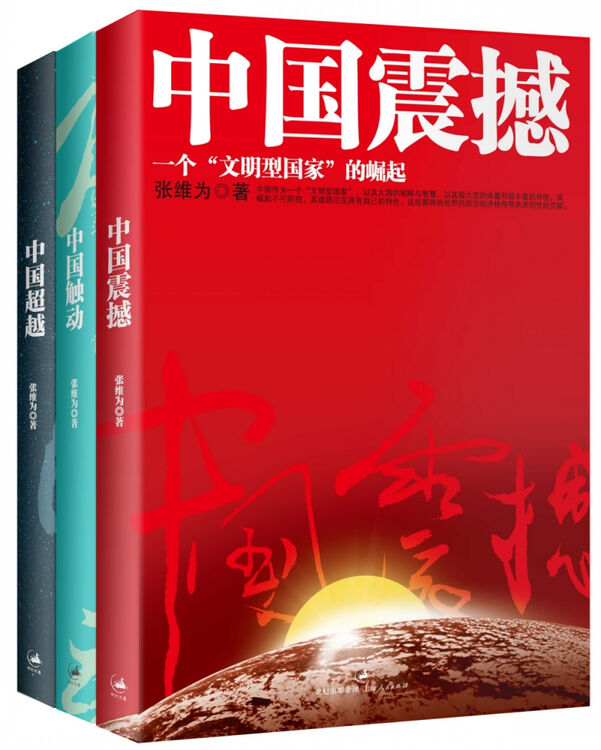
中國震撼三部曲:中國震撼·中國觸動·中國超越
我以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立論,指出“文明型國家”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和邏輯,中國還處在自己“全面上升的初級階段”,中國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
福山從“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的視角出發,認為當時正高歌猛進“阿拉伯之春”也可能在中國出現,而我則從文明型國家視角出發,認為這不可能,並預測“阿拉伯之春”不久將變成“阿拉伯之冬”,背後的道理是中國人講的“水土不服”,“水”指文化,阿拉伯國家的宗教文化以及經濟、社會、政治土壤都與西方如此之不同,“阿拉伯之冬”將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2011年6月27日,張維為(左)對話弗朗西斯·福山(右)
《中國震撼》出版後,被外國學者引用最多的一段話是:
“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隻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麼也可能是一個十多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今天看來這也是難以實現的願景。”
換言之,我認為文明型國家是高於西方“民族國家”的一種國家形態,我認為隨着世界經濟、科技的競爭加劇,跨國的區域整合從而實現更大的規模效應將是大勢所趨,走向某種“文明整合”、“文明型共同體”,甚至“文明型國家”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
我書中另一段被引用最多的話是:
“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座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endogenous civilization)。”
這意味着文明型國家否定了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敍事,各國人民都應該根據自己的民情國情和文化歷史傳承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開展不同文明的對話,這才是人間正道。
換言之,文明型國家敍事在解構西方“民族國家”敍事的同時,也在解構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敍事,及其支撐這兩種敍事的底層邏輯,即“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元敍事。
近年來,俄羅斯、印度、伊朗、土耳其等非西方大國紛紛稱自己為文明型國家,不少西方政治人物、專家學者也開始熱議這個概念,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20年1月刊文驚呼: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時代,21世紀將是“文明型國家”的世紀。這些國家都認為自己代表獨特的文明,拒絕西方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
其實,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文明型國家敍事對許多西方人士也很有吸引力。面對歐洲“再國家化”(re-nationalization)勢頭帶來的挑戰,法國總統馬克龍幾乎公開推崇文明型國家理想,他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作為這樣的例子,並宣佈法國的使命是引導歐洲進入文明覆興。對西方保守主義者來説,文明型國家敍事意味着捍衞傳統價值觀、抵制自由主義代表的文化墮落;對西方左翼來説,它更多地顯示了對本土文化和歷史的尊重,以及對西方帝國主義和自由主義霸權的拒絕。
文明型國家話語甚至使西方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反思西方“普世價值”敍事的困境。“普世價值”敍事者自稱這些價值是“普世的”,而非西方的或歐洲的,更非猶太教的。然而,正如歐洲政治學者布魯諾·馬塞斯(Bruno Maçães)所述:自由主義的西方“現在已經死亡,因為它造成了全球的無根化(rootlessness)”。他認為“西方社會為了實現其普世目標而犧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使西方社會深陷分裂,而重新塑造一個西方文明共同身份實屬不易。
總之,西方長期主導的民族國家、自由主義、“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所代表的軟實力,今天受到了文明型國家話語的挑戰,背後是全球南方軟硬實力的全面崛起,特別是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的文明型國家迅速走向世界政治、經濟、科技、軍事舞台的中央。在這個意義上,文明型國家敍事可能標誌着來自中國、來自全球南方的一種新的元敍事之開端,其意義估計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更加彰顯。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