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喜:不再跟着西方屁股定義“卡脖子”,這樣只會被動挨打
guancha

10月25日,新華社關於“十五五”規劃的報道中提到,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由此,我們可以清晰感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方式和路徑。
當今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人工智能無疑是重要驅動力量。自主研發的高性能芯片和操作系統、賦能千行百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大幅提高生產效率的機器人……在這條新賽道上,中國企業正以出色表現吸引着全球目光。
“十五五” 規劃發佈之際,觀察者網特邀首都經貿大學企業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孫喜分享觀點。他的研究方向聚焦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此次圍繞中國產業革命、前沿科技發展、創新路徑等方面進行交流。
觀察者網:本次十五五規劃中,對“卡脖子”問題有所闡述,您此前的觀點一直認為,企業才是科技創新的主體,您也對企業的縱向一體化戰略有所肯定,當前面對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等跨學科複雜度高的“卡脖子”領域,縱向一體化策略是否仍適用?應該如何去理解?政府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去幫助、引導企業發揮潛力?
**孫喜:**過去幾年,由於國際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我們國家的創新系統在這一過程中進行了一些因應性調整。其中最突出的調整有兩個,一是日益強調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二是強調建設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的一個重要樞紐,就是通過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等一系列形式,將企業創新發展、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的具體的卡脖子問題,轉化成國家科技任務和科技項目。
比如説對特定的科研機構進行了海量投入,進行光刻膠、光刻機的攻關。再比如説設立一些行業性機構,對行業共性技術進行攻關,幫助大多數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補齊技術升級中的短板。
過去幾年這種慣性態勢會讓人認為,政府幫助、引導企業發揮創新潛力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在企業和產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把這些難題變成具體的項目。
這個形式有它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是事後補救性質的。所謂事後補救的意思是説,通過這種體制機制人為地製造了一個時滯:從企業確實遇到卡脖子問題,到這些問題轉化成國家項目(項目申報),再到產生項目成果(項目驗收和交付),中間必然間隔或者延遲了若干年(因為我們的國家科技項目是以年為單位計劃、實施的)。
從長期來看,過於倚重這一形式勢必會導致一些問題,比如錯誤地估計現有產業基礎對解決卡脖子問題的支撐力度。很多時候我們不是沒有技術攻關的成果,而是由於特定的非技術因素——比如供需雙方之間溝通不暢等社會性原因——導致這些技術攻關的成果在特定的時期沒有得到更好的利用。最典型的一個歷史教訓,就是當年無錫油泵油嘴研究所去攻關柴油機的高壓共軌系統,產品已經做出來了,但是中國的柴油機廠都不用。
因為當時他們更信賴德國博世和日本電裝的技術。這種本土創新信任瓶頸的現象,被清華大學的高旭東老師稱為“後來者劣勢”。如果我們忽視了這方面的問題,就很有可能高估政府科技項目在創新轉型升級當中的作用,或者導致某種泛化的思路。
換句話説,當我們今天去討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充分結合、推動產業創新與轉型升級的時候,首先要盡一切努力地把全國統一大市場設計好、規範好,把市場機制用足用好,把現有產業基礎在各個領域的技術積累、各種社會力量充分調動起來。這其實是政府“有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從長期來看,這比單純推動科技攻關的項目制更加重要。
觀察者網:您認為企業應該是創新主體,因為只有企業能以更大的精力抵近市場、理解需求,但是真實市場需求跟真實社會需求之間,可能也有温差,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孫喜:**理解清楚剛才的問題,我們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政府幫助、引導企業發揮創新潛力的有效途徑。放眼長遠,當我們邁過眼下一些關鍵的“坎兒”之後,政府應該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與國內的一流企業、頂尖工程師和戰略科學家一起坐下來,共同商討和理解產業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
通過這個溝通過程,政府不僅能夠建立自己的工業理解能力,而且能夠“自我發現”對工業體系轉型升級,實現國家長期戰略目標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技術節點和技術系統發展路徑,進而定義出一批有重大意義的未來產品和未來工程(過去幾年的新疆光伏、雅魯藏布江水電等項目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典型),而不再是訴諸於過去那套跟在西方屁股後面定義卡脖子環節的思維方式——因為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這套思維方式最終只會導致被動挨打。
在這種“自我發現”的基礎上,政府進一步去扮演市場規則設計者(包括標準設計者)和關鍵買家的角色,用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不斷提高行業進入門檻、推動企業優勝劣汰;同時用這種廣而告之的方式為所有行業參與者創造一個共同的長期願景,打破行業之間的信息壁壘,引導和動員更多民族企業參與進來。(當年的大飛機項目就起到了這種廣而告之的效果:國家層面的戰略宣示吸引了機械、鋼鐵、紡織、電子、軟件等諸多行業的參與。)
以上提到的舉措,其實也可以有效彌合企業面對的真實市場需求與國家需要的真實社會需求之間的鴻溝,也即所謂“温差”的問題。(換言之,今天所謂的温差問題,其本質是國家治理和設計市場的能力不足。)
觀察者網:您認為在當前十五五規劃發佈,強調科技自立自強的背景下,企業縱向一體化的優勢是如何體現的?有沒有可以分享的技術突破案例?
**孫喜:**更重要的是,在剛剛提到的過程中進一步捋順產學研合作關係。讓那些想參與進來的企業都有資格成為科技創新的“出題人”,讓更多的創新主體成為更優秀的“出題人”,從而以一種更加分佈式的結構,讓企業創新過程中遇到的那些棘手問題可以在第一時間找到合適的高校、院所合作者得到及時解決,而不再是通過國家項目繞一個圈子。
這是實現科技投入多元化的根本出路,也是打破近年來國家科研項目異化的重要手段。換句話説,在這種路徑中,國家項目不再是一個雪中送炭的角色,而應該更多地發揮錦上添花的作用。
舉一個例子,過去幾年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中提到,我們在高端醫療影像設備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這些突破是怎麼發生的?源頭其實是在2008年邁瑞醫療找到了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希望一起開發中國本土的高端彩色超聲設備。當時飛利浦、通用電氣和西門子三家壟斷着全球高端彩超技術,高端彩超幾乎成了整個中國醫療設備行業的生死之戰。當時先進院年輕的研究員、現在南京大學的副校長鄭海榮就參與到這個產學研合作項目中,並且後來成長為這一領域最重要的領軍人物之一,邁瑞醫療也因此在市場上打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翻身仗。

邁瑞醫療相關合作技術突破
後來做國產磁共振設備的聯影醫療當時也在深圳,並在這一時期建立了與深圳先進院的合作關係(只不過後來聯影在上海與深圳之間最終選擇了上海)。而在這個過程中,鄭海榮和深圳先進院承擔的有關高端醫療影像設備的科研類和儀器類的國家項目,幾乎都不同程度地晚於同類的產學研合作項目。這就是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的體現,這就是國家科技項目錦上添花的作用。
觀察者網:那麼,目前的高科技領域“卡脖子”情況是否都能通過縱向一體化的戰略進行緩解?
**孫喜:**具體到高端芯片和工業軟件這些所謂跨學科複雜度比較高的“卡脖子”領域,其實還稍微有些行業間差異。相對而言,其實工業領域使用的芯片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採用用户牽頭的方式進行創新。海信進入電視芯片、格力進入空調芯片都是在反映這個邏輯,他們恰恰是因為沒有合適的本土供應商,所以不得不通過一體化的方式解決這些內在需求。
相比而言,通用計算芯片領域是一個市場容量更大、但產業分工程度更高的行業。純設計企業(海思等fabless)和純代工廠(如中芯國際)之間的關係,也已經脱離了過去的純粹交易關係,而受到越來越多外部因素(包括制度和政策)的調節。所以這個領域已經超出了縱向一體化的議題範疇。
相比之下,工業軟件行業更像工業芯片,碎片化程度更高,需求量相對更小,而且這些軟件都承載着產業領軍企業的關鍵技術經驗。所以我們會看到過去這些年中國工業軟件行業的發展呈現出兩個非常明顯的路徑:一是以當年的中國石油東方物探為代表,通過縱向一體化方式解決關鍵技術軟件化。二是近年來由國防科工委指導、軍工協會負責推動的工業軟件行業供需兩側的對接與交易撮合。
説白了,這兩條路徑都脱離了純粹的市場交易關係,而是通過更加組織化或社會化的方式來解決技術壁壘和信任瓶頸問題。
觀察者網:當前的技術革命中,競爭最激烈、影響可能也是最深遠的,就是人工智能技術革命,結合本次發佈的十五五規劃中相關的表述,從當前看,您認為中國以及中國企業應該怎樣參與到AI這一格局演變之中?
**孫喜:**前幾天和浙江的同志聊起來,他們説現在浙江正在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在工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比較下來之後發現,在這個領域做的最好的是浙大中控。為什麼呢?因為從褚健老師創業以來的三十年間,中控在工業自動化領域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行業經驗,到今天幾乎是中國流程性工業自動化控制的絕對領軍者。
這讓中控有能力最大程度地利用“窮舉法”(用工業場景中既有的、相對條理的經驗知識一條一條地訓練人工智能,確保其建立“如果A,那麼B”的基本判斷,而不是任由大模型自動推理)來完善它的人工智能方案、完善它的工業操作系統。
更重要的是,按照今天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水平,窮舉法仍然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管理工業場景最重要的途徑,沒有之一。相比之下,某些做互聯網和IT出身的企業去做人工智能工業應用,就沒有中控這麼得心應手。因為他沒有這樣的工業經驗基礎去實施“窮舉法”。
這個案例其實提示了我們理解中國企業參與AI變局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
第一個原則問題就是,我們要明確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在不同行業領域的應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些2G、2C的行業中,對安全和一致性的要求相對較低,場景中的變量相對較少,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利用大模型技術(經過適當遷移後)去解決一些行業應用問題。這也是互聯網和IT出身的企業能夠深度參與,並且取得一定成功的領域。轎車、家電、個人電腦這些產品能夠最先引入大模型,就是這個原因。
相比之下,在2B行業中,對一致性的要求、對安全性的要求、場景中變量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都要遠遠高於消費品領域和公用事業場景,這個時候就極度依賴工業企業的既有經驗積累對場景進行降維和分解(比如形成一組高度專用的機理模型),分解到人工智能能夠理解和操作的水平。所以中國企業過去30年參與全球分工積累下來的工業經驗絕對不是累贅,而是我們參與人工智能技術革命的“金鑰匙”。沒有這把“金鑰匙”,我們就打不開人工智能驅工業發展(設計/開發/生產/營銷)這扇大門。
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原則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傳統工業企業與人工智能企業之間的關係。作業場景、經驗數據來自傳統工業企業的積累,人工智能企業(或者某些善於人工智能研發的院校科研人員)的作用則是幫助傳統工業企業將這些經驗數據轉化成機理模型和AI。這個主客關係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導致很多問題,比如前面提到的供需兩側的溝通不暢,嚴重的時候會導致“此路不通”。
這個時候可能就需要國家做一些事情:比如通過設立一些工業人工智能領域的示範項目,為供需兩側的協同創新創造合適的機會和場所,解決信任瓶頸的問題。歸根結底,利用人工智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要着力處理好“新”與“老”的關係。
觀察者網:您曾對從0到1的“藍天研究”有過分析,認為只有以任務導向、響應需求為動力,以技術科學研究為“樞紐”,工程技術開發和自然科學研究才能實現徹底的時空統一,協同發展才能真正落地。您如何看待“十五五”規劃中關於基礎研究的相關表述?
**孫喜:**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隨着實踐的發展,中央對於基礎研究的認識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務實。我們去看2023年出版的《論科技自立自強》,其中收錄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2018年、2021年三次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以及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於基礎研究(及其目標導向、需求導向)、以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關係的有關論述,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從近兩年的情況看,無論是2023年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關於基礎研究問題的講話,還是今年6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包括這次的十五五規劃,同樣反映了這種務實的品格。
過去兩年,在有關“提高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這個議題的討論中,中央在論述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日益強調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今年的兩院院士大會也把使用了幾十年的“科技成果轉化”的説法改成了“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所有這些改變,其實都是在我們傳統的政策語言體系中,努力尋找與“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這一新的政策範式的契合點。這對我們理解新時期如何解決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相脱節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比如,十五五規劃提出了“加強基礎研究戰略性、前瞻性、體系性佈局”的要求,這其實就是對2023年“221講話”精神的一個延續。“221講話”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強調基礎研究要堅持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而今天“戰略性、前瞻性、體系性”的要求就是對目標導向的進一步深化。
觀察者網:那麼,該怎樣去避免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脱節,讓高校、研發機構真正服務於有需求的技術瓶頸突破?
**孫喜:**更進一步來看,只有當官產學研各界能夠像我們前面説到的那樣,坐在一起共同理解各個產業、乃至整個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方向的時候,這種戰略性、前瞻性、體系性佈局的效果才能夠實現最大化:此時,能夠引領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國家扮演了基礎研究“出題人”的角色,而且只有當國家對“發展方向”有清晰理解和把握的時候,國家的這種“出題”才是可操作的,也在最大程度上是有用的。但從現階段對大學“有組織科研”的考核方式來看,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顯然還有待深化。
當然,創新過程是高度不確定的,所以我們很難提前一二十年“押中”所有的重大基礎研究選題,國家也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出題人”。此時就需要我們更好地理解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比如前面我曾經提到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例子。先進院是我國在21世紀初創立的那批新型研發機構中的典型代表:工研院的發展定位、國家隊的科研實力,更重要的是紮根於深圳、珠三角的產業土壤。
我對先進院的觀察始於2018年,對其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實踐有一個概括,我稱之為“大樹模型”:科技創新、院所裏的基礎研究是樹根,產業發展是樹冠,企業做出的新產品是果實,而深度融合靠樹幹。樹幹的功能不只是把根系吸收到的水分和礦物質輸送到樹冠,更重要的是把樹冠吸收到的有機物輸送到根系,從而讓根系獲得發展的能量。
而在先進院,他的科研人員之所以願意接受樹冠(產業端)傳導下來的能量(需求知識和資金),因為他對科研人員的考核機制裏面就包括產業化的部分。你不僅要會發論文,還要懂得產業語言,還能做橫向課題,能夠把產業需求轉化成科學問題,去鑽研“有用的科學”。
當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可以同時表現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通路的時候,我們就要審慎地評價過去幾年科技體制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新動向。比如,科研工作要“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對“重大”的把握和評價應該放在什麼尺度上進行?在追逐英文期刊發表的風氣尚未完全消退之際,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確需要聚焦主責主業,攥起拳頭打人。
但是,如果中國科學院把“主責主業”的定義權完全交給下面的分院甚至專業所,對主責主業的狹隘把握就有可能同各專業所在歷史上形成的學科格局形成衝突,甚至出現“茄子地裏(特定專業所的主責主業限定在A領域)不能種豆角(特定課題組在B方向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問題。
再比如説,科研機構與行業領軍企業協同創新,在前沿領域佈局種子項目,其金額能否準確反映項目長期價值的重大性和戰略性?如果科研機構一味地追求一時一地的大項目、大買賣,甚至抱着“衝業績”的想法去看待產學研合作,而不願意做有長線意義的小買賣,就很有可能錯過技術與產業演進過程中真正的“從0到1”。這些在實踐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都亟待政策設計者投入更多精力去解決。
相比之下,受到學科評估機制的影響,過去20年的大學系統在不斷地(或者至少一度)遠離產業需求,不斷地貶低橫向課題,狹隘地、甚至日益圈子化地理解科研與基礎研究。所以,解決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脱節這一問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塑造科研體系、尤其是大學對需求導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去除枷鎖,打開眼界。
大學和科研院所只有平等地對待來自縱向課題和橫向課題的每一分錢,才能夠重建服務產業創新需求的積極性。從長期來看,我們要重新思考和建立關於基礎研究的輿論體系。比如過多地強調基礎研究“無用之用”的特徵,甚至以此否定“有用的科學”的可能性,或者一強調基礎研究的有用性和需求導向就誣之為“功利色彩”。(科技體系的功利色彩,不是長期以來的科技評價導向和過度倚重科研獎勵的薪酬體制導致的嗎?!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的科技評價導向,是需求導向、目標導向嗎?)其實2023年的“221講話”中“兩條腿走路”的表述,已經很深刻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重建關於基礎研究的輿論體系,也有利於從社會層面重新塑造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社會上很多同志對科技創新還抱有玫瑰色的幻想。
我曾經在一個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的會議上聽到河北省的同志自我批評,説科技成果轉化不力的原因是當地產業基礎太薄弱,導致北京的科技創新成果難以在本地找到落地場景。我當時給這位河北的同志做思想工作,我説“你太謙卑了!其實北京的科技創新成果,在北京本地也應用不上……”但從制度的層面,我們要深刻地意識到,這種“謙卑”絕對不是推動深度融合應有的態度和思維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對基礎研究祛魅。
觀察者網:目前,前沿技術迭代對產業生態的重塑也受到關注,您在以前的論文文章中傳遞出一個觀點,就是科學創新並非完全是“科學→技術→產業” 的線性發展路徑,也存在科學-技術、技術-經濟、技術-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的非線性過程,能否展開講講?
**孫喜:**這是一個很抽象的問題。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我特別喜歡講的一個故事,中國母乳研究的故事。母乳研究中有很大一塊內容是關於母乳的組分、以及這些組分功能的研究。中國的母乳研究起步很早,但在很長時間裏是很零散而且不繫統的。中國真正出現系統的、長期的母乳研究,是因為以三元、飛鶴、伊利為代表的一批乳製品企業開始進行自主創新。
比如三元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了千萬數據量級的母乳數據庫,並且在很長的時間裏跟蹤研究母乳組分、母乳微生物(益生菌)、各種組分的功能及其製備工藝。這才有了三元自主研發的中國特色的配方奶粉和各種創新性的發酵酸奶。正因如此,三元的首席科學家陳歷俊被社會上稱為“中國寶寶的姥爺”(因為老陳自己確實有一個女兒,而且他確實是個姥爺),更重要的是,到目前為止,陳歷俊是中國母乳研究領域最高產的學者。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產業發展帶動技術開發,技術開發帶動科學研究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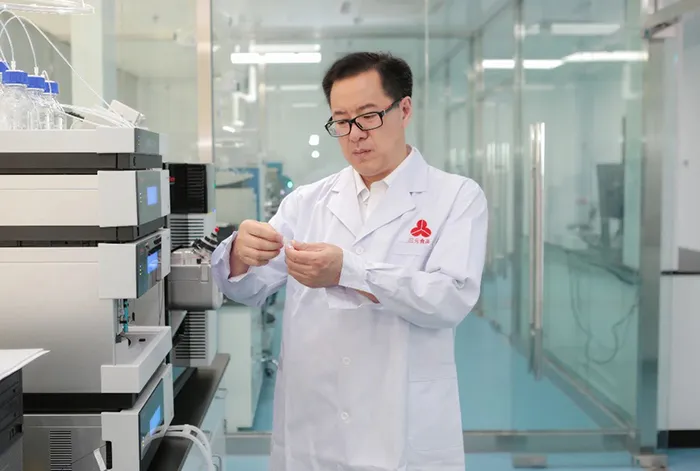
陳歷俊 國家動物健康與食品安全創新聯盟
第二個故事來自安徽,發生在農業領域。涉事企業叫格義。因為非技術原因,格義的處境比較困難,但他們卻做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產品。格義在秸稈深加工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溶液,並且很意外地發現這種溶液有提高糧食產量、恢復土地地力(修復鹽鹼地)的作用。在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中,他們發現這個溶液之所以能夠產生這樣的作用,是因為其中的有效成分不僅可以大量螯合土壤中的重金屬離子,從而有效減輕鹽鹼化土地對植物種子和根系的鹽脅迫;而且能夠為有益菌的繁殖提供充足的養料,進而強化農作物的抗逆性(使農業物更好地應對不利的生長條件)。
用格義自己的話講,“(這個道理)種地的老農民都懂,但材料只有我們有。”換句話説,科學原理早就在那裏,但就是沒人知道怎麼幹、用什麼實現。為什麼呢?因為格義處理秸稈的深加工工藝是他們自己開發的,所以這種意外發現的溶液也是原創的。更有趣的是,在格義推廣這種革命性產品的過程中,遇到一個很尷尬的限制:我們國家的法律要求化肥產品必須含有氮磷鉀,但他們的產品是有機物溶液,不含這些傳統化肥元素。所以他們還必須按照國家法律的要求,在其中加入一定的氮磷鉀成分,才能拿到化肥市場的“准入證”。
從這兩個例子來理解科學、技術與產業之間的非線性關係,我們不難發現創新的核心特徵就是實踐性。簡單而言,創新是幹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也不是算計出來的。實踐發展到哪裏,創新就可以發展到哪裏,“有用的科學”就可以發展到哪裏。所以“有用的科學”是有國界的,是被一個國家的工業體系嚴格定義並塑造出來的。
而具體到中國,由於我們擁有一個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極其豐富龐雜的工業體系,產業創新的實踐素材極大豐富,這勢必極大地降低重大創新的門檻(做出來的門檻和市場化的門檻)。這意味着,尊重人民羣眾的首創精神,讓各個行業都積極地開展創新實踐,直到把整個國民工業體系盤活起來,這個過程本身就可以孕育更多更好的重大創新。十五五規劃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置於“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之前、作為整個十五五期間十二項重點工作領域之首,也充分體現了這一邏輯。
但這就需要我們謹慎地對待所謂“戰略科學家”的議題:如果回到前述官產學研協同的政策範式,我們就不難發現,定義產業未來發展方向的戰略決策顯然不是靠“科學家”做出來的,對國家戰略的把握、對競爭態勢的洞悉、對產業基礎的理解,更多地依靠政治家、企業家和工程師的戰略眼光。
當很多人都以錢學森先生為例來説明“戰略科學家”的極端重要性時,他們大約忘了,錢老對十二年規劃最重要的建議、“先導彈後飛機”,是基於對中國工業基礎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出的。他們大約也忘了,作為錢老學術思想的重要體現,《工程控制論》的目的、內容和影響都深深地植根於工程領域。
準確把握創新的實踐性特徵,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今天西方、尤其是美國去討論原始創新的時候,如此偏愛重大原理突破導致的重大原始創新。因為去工業化導致他們產業創新的實踐基礎被削弱了,所以他們只能更多地寄希望於那些對實踐素材要求較低的新的理論模型。但我們要反問一句:一個好廚子,如果他手上有足夠的菜和油鹽醬醋,能夠做得出滿漢全席,他會去做分子料理嗎?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