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凱&薩金特:“去風險”是最荒謬的幻想,開放本身就是安全的最高形式-高志凱、托馬斯·薩金特
guancha
11月5日下午,由商務部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合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全球領導力學院承辦的第八屆虹橋論壇“開放貿易與安全發展”分論壇在國家發展中心(上海)舉行。論壇直面全球經貿核心議題,邀請中外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如何構建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全球經貿體系。
在CGTN《對話》欄目主持人許欽鐸主持下,蘇州大學講席教授、全球化智庫副主任高志凱與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教授,就“安全”概念的定義與美國的濫用、保護主義的風險、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關税政策與不確定性等話題開展對話。兩位嘉賓一致認為,歷史經驗表明,封閉與恐懼不會帶來安全,唯有以開放、理性與合作為基礎的全球秩序,才是通向持久安全與繁榮的道路。
以下為觀察者網整理的對話文字稿,未經嘉賓本人校閲,僅供讀者參考。
**許欽鐸:**近年來,我們看到“國家安全”的概念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範圍,如今涵蓋了經濟、科技、網絡等多個領域。安全的名義正越來越被用於為貿易限制和保護主義辯護。那麼,在開放貿易的背景下,我們該如何界定安全的邊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全球層面構建一個更加開放、安全與合作的經濟體系?
先請薩金特教授談談。您能幫我們理解“安全”這個概念嗎?我記得在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內,“經濟安全”還是個頗具爭議的説法,當時很多人並不確定它究竟意味着什麼。但如今到了其第二任期,幾乎沒有人再質疑這一提法,大家都默認“經濟安全”是理所當然的。那麼,請問,經濟安全有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定義?
**薩金特:**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常常用同一個詞,卻表達着完全不同的意思,有時甚至用它來掩飾真正的目的。
作為美國人,我必須説,當美國有人説“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做某事時,很多時候他並非真是為了國家安全,而是為了保護某種私人利益、以公共利益為代價。我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現在也依然在發生。所以我才説,沒有所謂的“統一定義”。比如,馬丁·雅克剛剛説到的“國家安全”,跟美國副總統萬斯説的“國家安全”,其實並不是一回事。

美媒透露,美國國防部近日已完成《國防戰略報告》的審查工作,將把關注重點從“威懾中國”轉向西半球及美國本土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我非常欣賞馬丁剛才提到的關於“學習與遺忘”的歷史教訓——像我這個年紀的人會覺得特別驚訝:八十年前,美國其實是深刻理解貿易與開放的益處的。那是因為我們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歷過錯誤,吃過虧之後才學到了正確的教訓。可如今,這些教訓基本上都被遺忘了。美國兩黨的領導人都對歷史知之甚少,他們甚至不瞭解美國自己的歷史,更別提中國歷史了。
聽了今天上午和下午的討論,我沒有太多要補充的。大家已經非常清楚地闡述了貿易開放的益處,包括背後的詳細邏輯:事實是,沒有所謂的“取捨”。支持開放的國家在各個方面都變得更加繁榮,而選擇封閉的國家則日漸萎縮。
**許欽鐸:**謝謝薩金特教授。高教授,您怎麼看?關於安全的概念如今被不斷延伸,有時甚至包括意識形態安全、價值觀安全。誰掌握了所謂的“話語權”,能設定議程、定義風險與安全,誰就相當於在全球貿易中佔據了道德和監管層面的制高點。比如現在有人提出所謂“民主供應鏈”。您怎麼看?
**高志凱:**非常感謝。我很榮幸能與我十分敬重的薩金特教授同台。謝謝你的提問。我想談幾點。 首先,如果忽視安全或輕視安全,一個國家必然會為此付出代價。 第二,如果把安全推向極端,你同樣會讓自己陷入不利。中國有句古話叫“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描述的是一場古代的惡戰。當你陷入極端的安全焦慮時,眼中的每一顆草、每一片葉子都彷彿成了敵軍。如果你在心裏惦記着“魔鬼”,你會在牆上甚至在空氣中都能看到“魔鬼”。
所以,在談論安全的概念時,我們必須保持平衡。
我兼任中國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長,我們的研究對象涵蓋廣義的能源問題,也以儘可能廣的視角理解安全。在中國,安全有二十多個門類: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軍事安全等等。安全確實存在,也絕不能忽略。但任何國家都不應沉溺於“安全至上”的絕對幻想。正如薩金特教授剛才提到的,如果把安全概念濫用以服務其他目的,比如被意識形態目標所綁架,那就已經偏離了安全的本意。那不是安全,而是以安全之名行他途之實。
我想給中美雙方的建議都是:不要因安全考量而“凍結”行動。要認真研究安全問題,但不要把它無限放大。面對安全,我們需要平衡的思維。
**許欽鐸:**謝謝高教授。薩金特教授,您剛才提到,美國的兩黨領導人都忘記了歷史,提到過上世紀三十年代、七十年代。您認為他們沒學到的教訓是什麼?是保護主義、關税的問題嗎?
**薩金特:**二十世紀的前半段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同時卻讓美國受益匪淺。那段歷史中有許多值得反思的教訓。讓我舉一個例子吧。
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幾乎所有科學領域的領軍人物都在歐洲——從俄羅斯、德國、法國到英國。美國當時只是個“邊陲學術地帶”,我們不是科學上的領軍者,美國的優秀學生要去德國、英國或法國求學。
可到了三十年代,由於諸多原因,奧地利、匈牙利、德國等國主動或被迫地把一批科學家趕出了歐洲,他們流亡到了美國。順帶一提,即便在當時入境美國也不容易,但他們最終留下來了。短短五年內,他們就幫助美國成為各個科學領域的世界領先者,包括經濟學——如果你願意把它看作科學的話。
正是這些名字:馮·諾依曼、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喬治·加莫夫(他是我岳父的論文導師)、愛德華·泰勒——這些人來到美國,他們的科技研究成功不僅幫助美國贏得了二戰,也推動了全世界的科技與學術的飛躍。

1933年10月,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離開歐洲入境美國時的美國報紙報道
我們一直在延續這條道路,剛剛談到了人力資源,而美國的很多初始人力資源其實來自中國。我本人是一名大學教授,我的許多優秀學生都來自中國,他們在中國學習數學、理科等基礎教育的內容,中國為他們支付了教育成本,然後他們到美國攻讀研究生,成為我最好的學生之一。所以我本人也是“開放”的受益者——我與許多在中國完成中學、本科教育,然後在美國讀研究生的學者共事,這讓我受益匪淺。
然而,看看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過去幾個月以來,美國政府卻表示打算限制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人數。這是在幹什麼,這不是在重蹈德國當年的覆轍嗎?難道我們沒從那段歷史中學到教訓嗎?這就是我所説的“被遺忘的教訓”。相較之下,我認為中國並沒有忘記這一點。
**許欽鐸:**您剛才的意思是,開放本身就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安全?
**薩金特:**絕對如此。我剛才就想這麼説——開放本身就是安全的最高形式。歷史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許欽鐸:**高教授,您剛才提到如果把安全推到極端,反而會帶來負面效果。那麼您認為,像保護主義或單邊主義這樣的做法,最終真的能實現推行者所宣稱的目標嗎?
**高志凱:**謝謝你的提問。在回答之前,請允許我先談談從歷史中學習的問題。
首先,我認為,當今世界格局是在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無條件投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本質上就是一個多極的世界,而非單極的。看看聯合國安理會的構成:五個常任理事國,包括中國,每個都有否決權。這説明在1945年國際秩序的奠基之初,創立者就希望這個秩序在最高層面——也就是聯合國安理會層面——實現權力的制衡。那後來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大國,自認為是世界的唯一一極,並要求所有人接受單極世界的説法?其實,從一開始,這個世界格局就是多極的。這是我想説的第一點。
第二點,今年9月3日,中國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的大型閲兵。當時我在央視的演播室做現場直播。走出直播間後,我看到歐盟外長——我不想點名——公開表示震驚。她問:“為什麼中國要慶祝法西斯戰敗?中國跟擊敗法西斯有什麼關係?”她甚至聲稱,中國在北京舉行閲兵是在“挑戰國際秩序”。
對此我公開回應:這位女士該回去重新上學了。中國在那場戰爭中犧牲了3500萬人,連續14年抗擊日本侵略者,並與美國等國並肩作戰,最終徹底終結了法西斯主義。如果卡婭·卡拉斯作為歐盟的最高外交官,連1945年發生了什麼都不知道,那她根本不配擔任這個職位。她應該回去學一學最基本的歷史常識——甚至不是回去念大學或高中,而是回幼兒園重修歷史啓蒙課。
第三點,我震驚於如今保護主義又在危險地抬頭。我呼籲世界各國共同捍衞自由貿易。因為保護主義從來不能真正保護任何人的利益。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以保護主義的名義行事,並沒有在維護美國人民的正當利益。
我堅信,美國絕大多數民眾其實是支持自由貿易的,因為自由貿易能讓他們受益最大。如今有些美國人説,不要“自由貿易”,要“公平貿易”。我想特別強調:從美國的利益角度來説,沒有自由貿易,就不會有真正的公平貿易。自由貿易是任何公平貿易的前提。否則,如果不談自由貿易,你認為的“公平”只是對你而言,對我就不公平。
所以我真心希望特朗普總統及其團隊能真正研究歷史,瞭解濫用關税和保護主義的危險。
最後,請容我在薩金特教授這樣一位傑出的諾貝爾獎得主面前指出一點:美國政府徵收的關税不是由中國來承擔的,而是由美國人民在支付。那是一種對美國民眾徵收的賦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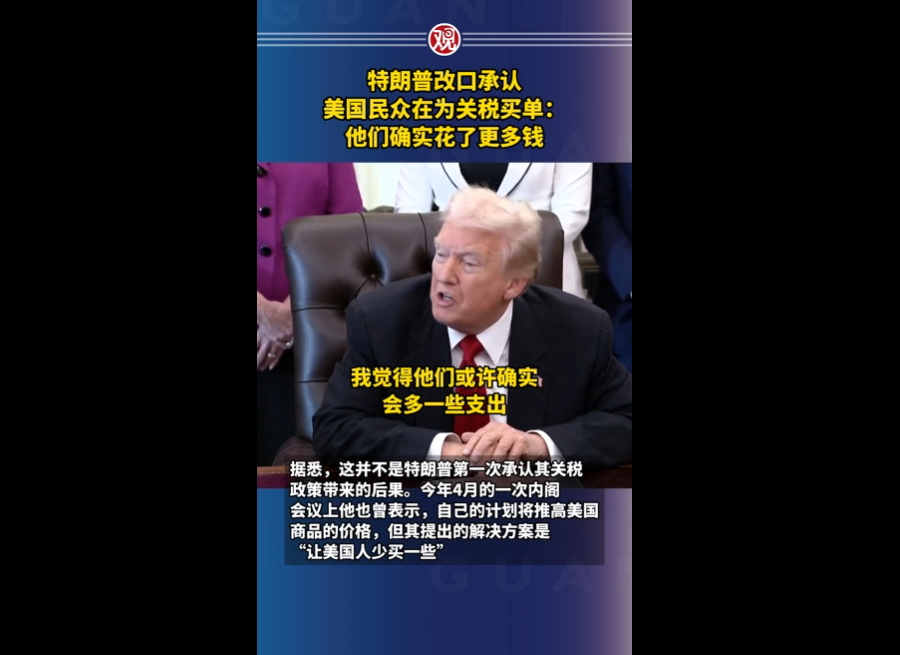
當地時間11月6日,特朗普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由於政府關税,美國消費者確實為商品支付了更高的價格。
我真心為那些勤勞、誠實、正直、值得尊敬的美國民眾感到遺憾。他們不應該承擔美國政府徵收的關税,更不該被告知關税會“讓美國再次偉大”、會帶來如此多的收入以至於“美國人不再需要繳納所得税”。美國政府至少應當誠實地告訴民眾——這些關税,是他們自己在為從中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的商品買單。不應該再提保護主義,保護主義這個詞本身就是一種誤導,因為至少就美國來説,保護主義根本沒有在保護美國民眾的正當利益。
**薩金特:**沒錯。那你剛才問我,關税是否實現了其目的?問題在於——關税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如果目的真是為了改善普通美國人的生活,那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關税只是為了保護一小部分既得利益羣體。
舉例來説,美國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税,這傷害了我和我大多數朋友的利益。但關税確實讓少數幾家鋼鐵、鋁業企業和工會受益。他們就是一個極小的利益集團。他們其實想要加徵關税,但不會在公眾面前這樣説,而是會打着“對我們有利的事也對大家有利”的旗號。其實並不是這樣。
再説到“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這兩個詞——我知道“自由貿易”是什麼意思,但每當有人説“公平貿易”時,我就有點緊張:到底對誰公平?因為貿易中永遠有贏家和輸家。
**許欽鐸:**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觀點——連諾貝爾獎得主都認為“公平貿易”的定義含糊不清(笑)。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一些單邊措施,比如對先進芯片或人工智能技術的出口限制。從被制約的一方來看,這些措施是否真的會阻礙中國高科技的發展?
**薩金特:**好問題。其實正如前幾場討論所提到的,美國的政策——不僅僅是這一屆特朗普政府,早在之前就開始了——它製造的不是風險,而是不確定性。
在統計學上,風險意味着你知道概率的分佈,雖然存在不確定性,但是正態分佈的,因為我已經見到了數據;而不確定性則意味着你根本不知道其概率分佈,也沒有穩定規則,規則隨時會變。這種不確定性會破壞投資模型和資本配置,甚至也會導致“分散風險”這種概念失效。
因此,正如很多嘉賓剛才充分闡述的——提供穩定的制度和規則的能力,是決定一個國家能否成功的關鍵。這一點我完全贊同。
**許欽鐸:**高教授,我知道您想回應,同時也請您談談一個最新的例子——荷蘭政府在華盛頓壓力下,試圖“國有化”一家中國企業。與此同時,中美剛剛達成一項暫時性的關税與出口管制“停火協議”。這讓荷蘭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所謂“去風險”策略似乎正在反噬自身,帶來更大的不安全。您怎麼看?
**高志凱:**這是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比如,我現在坐在你們面前,這把椅子隨時可能塌;我坐在舞台上,舞台也可能塌;我頭頂的天花板可能掉下來;喝水可能嗆到;游泳可能溺水;吃蘑菇可能中毒。風險無處不在。
所以,如果你在政府或企業裏聽到有人提議成立一個“去風險部門”,請立刻解僱他/她。因為“去風險”本身就是最荒謬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風險永遠存在。我們能做的不是消除風險,而是管理風險。
中國和世界上任何國家一樣,既有風險,也有機遇。把中國看作“風險的總和”是錯誤的,把中國看作“機遇與回報的總和”同樣也不對。必須辯證地看待——中國既是風險,也是機會。
第二,説到關税,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留下了一些古老的智慧。中國有句:飲鴆止渴。一個人極度口渴時,會想立刻喝水解渴;但如果手裏那瓶水其實是“毒液”,你喝下去只會害死自己。
關税就像那瓶“毒液”——短期看似能解渴,長期卻會自傷,尤其對美國這樣的超大經濟體更是如此。按最基本的金融常識,如果你希望美元繼續作為全球主導貨幣,就必須維持貿易逆差,而不是通過關税阻斷貿易。
我真心希望像薩金特教授這樣優秀的諾貝爾經濟學家,能有機會把這些最基本的常識告訴特朗普總統。
再回到荷蘭的問題。首先,我一直非常尊敬荷蘭的民眾,他們以誠信和卓越的商業口碑而聞名。但這一次荷蘭主動挑起與中國的糾紛,完全沒有道理。特別是這家中國企業,其實是荷蘭註冊公司在中國的母公司。如果你仔細看它的公司架構就會發現,其生產基地、客户和產業鏈幾乎都在中國。荷蘭若真想“收回”這樣的資產,就註定是一場打不贏的戰鬥。

荷蘭經濟事務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斯10月接受荷蘭媒體採訪,談及安世半導體事件。 視頻截圖
我必須説,作為一個向來受人尊重(尤其是受到中國民眾尊重)的國家,荷蘭做出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請允許我用這個詞。他們企圖掠奪一家中國控股企業的資產,以為能佔到便宜。這非常令人意外。幸運的是,他們的計劃最終被制止了。為什麼?因為歐洲和亞洲的汽車製造商——奔馳、寶馬、大眾等——都需要這家中國公司在大陸製造的芯片。無論荷蘭政府針對這家企業做什麼密謀,都不可能脱離中國製造。
所以,荷蘭政府的做法不僅擾亂了企業結構,更破壞了整個歐洲汽車製造業包括其他產業的供應鏈。幸好,這次荷蘭政府失敗了。否則,開了這一先例會極其危險——可能讓其他發達國家,甚至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如此效仿並掠奪中國企業的資產。
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這樣説,但我對荷蘭如此悲慘地失敗感到非常欣慰。平時我對荷蘭人是充滿敬意的。他們是偉大的民族,我十分尊重他們。
**許欽鐸:**他們其實是親手破壞了自己的安全。我們看到,中國最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其中強調的五項原則包括主權平等、尊重國際法等。也許在這樣的精神下,中美才達成了一項為期一年的“經貿停戰”,雙方將繼續保持接觸,希望最終達成更持久的協議,既促進兩國發展,也增進安全。薩金特教授,您對這樣的前景感到樂觀嗎?
**薩金特:**我並不樂觀。如果讓我預測特朗普政府接下來會怎麼做,我認為他們將無法制定出能維持幾個月以上的政策。原因很簡單——他們自己恐怕也不清楚想要什麼。
若試圖推敲他們的動機,一個理性的人會説:既然採取這些措施,他們一定有某種目標或世界觀。然而,當你聽他們闡述自己的世界觀時,會發現邏輯極其混亂。舉個例子,他們説要通過徵收關税來阻止進口,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同時還能增加財政收入。但這兩者顯然自相矛盾。那麼他們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是根本不在意?
比如,特朗普與墨西哥談好了一份貿易協議,還在和加拿大談判,然後他突然叫停了談判,因為加拿大有人播放了一段關於里根的廣告,他非常不滿意,於是叫停了談判。
你如何預測這種行為?這已經超出了“無序”的範疇,連“無序”都不足以形容。因此從這方面説,我對未來的前景並不樂觀。
不過,馬丁剛才的評論我很認同——也許這並不那麼重要。因為從數據上看,世界發展的方向已然確定。就像他提到的,到2045年的趨勢,我不會反對這種判斷。正是這些力量推動着全球格局的演變。因此,中國及其他國家推動建立不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其實是一件積極的事。這將促使美國最終不得不去適應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
**許欽鐸:**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一些更具一致性和可預期的政策。比如説,中國對來自非洲五十多個國家的商品實行零關税政策;在世貿組織談判中,中國也主動放棄了“特殊與差別待遇”地位,以推動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更好地運作。這些都是明確的方向。正如今天上午討論的那樣,中國擁抱自由貿易與自由市場——這是一條清晰、可持續的道路。
**高志凱:**謝謝欽鐸。我認為,中國將竭盡所能讓自由貿易取得勝利,讓中國和所有貿易伙伴實現共贏。舉例來説,既然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零關税政策已取得成效,為什麼加以推廣呢?為什麼不試着推動中美之間的“零關税互惠機制”呢?
設想一下,如果中國提議與美國實行雙邊零關税,也許特朗普總統會先高興一秒鐘,然後立刻跳起來反對,説“不行”“中國佔我便宜”。因為中國對美出口確實高於從美國的進口。
但這套“互惠零關税”方案的妙處在於,我們可以將美國對華出口額作為基準實施零關税——比如,美國每年向中國出口2000億美元的商品,那麼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等額商品也享受零關税。至於超出部分的中國出口,美方可自行決定徵多少關税。這樣一來,中美之間的貿易會既公平又對等。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安排不是給貿易“做減法”,而是為了進一步擴大。我們完全可以把中美貿易額從現在的近7000億美元提升到1萬億美元。至於新增的部分,也能激勵美國企業去尋找更多適合中國市場的優質、實惠商品。那樣的話,中美兩國都將變得更偉大,而世界也會因此變得更安全。
所以我認為應該對中美關係保持樂觀。中國並沒有什麼既定劇本,我堅決反對那些把中美關係套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模式的説法。中美不僅是兩大常規軍事強國,更是兩個核大國,我們需要找到保持溝通的方式。
你提到了在釜山舉行的中美元首會晤,我想説,首先,我認為中美能夠在最高層面保持接觸,是非常積極的信號。無論結果如何,能有這樣一次會晤,本身就是建設性的。
但遺憾的是,當今世界上最可預測的事情就是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他們的政策隨時可能在一夜之間翻轉。中國有句古話叫“朝令夕改”,但在特朗普政府那裏,是“朝令朝改”——早上剛決定的事,還沒等墨跡幹就變卦了。
所以我建議,中國的公眾和政府都不要對美國這位總統和政府能完全遵守承諾抱有過高的期待。事實已經證明,他們正在考慮對中國加徵更多關税,啓動更多“301調查”。這都印證了我的判斷:當今世界最大的確定性,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極端不確定性。我們必須留意他們隨時變卦的風險。
至於中國方面,我可以負責任地説:無論中國答應了什麼,都會信守承諾,絕不輕易改變——哪怕代價高昂。中國一貫言出必行,這一點是我最欽佩、也是最讓我感到自豪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