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解放初的“城市文藝接管”對於塑造新中國文藝而言有多重要?
guancha
【文/李丹】
發生於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城市文藝接管”,既意味着中國“現代—當代”的文藝轉換突破臨界狀態,也是“農村—城市”文藝轉換的關鍵性標誌。“城市文藝接管”雖然常常是軍事、政治行動的組成部分,但往往又是複雜機制和多重力量作用的共同結果。
在諸多城市的實踐中,又以上海的文藝接管最為成熟也最具代表性,其伏脈千里的長期準備、周密組織的“丹陽集訓”以及“接而管之”和“不接而管”相結合的靈活策略,都微觀而多面地呈現了文藝制度的推陳出新。通過“接管”這一界面,可以看到某些全新的內容進一步深植於中國文藝之中,如在特定條件下的文藝鬥爭需要帶有的秘密性、文藝幹部作為關鍵要素對新中國文藝的深刻參與以及“接管”作為軍事行動的組成部分對文藝的潛在影響。

解放上海,圖為解放軍向上海恆豐路橋北的殘敵衝擊
一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宣佈“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1],而新中國“城市文藝”的合法性,也往往追溯至此。中共中央對城市工作的高度關注,則可進一步上溯到此前一年的《中央工委關於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正是這一文件首先指出,“如何去收復城市,收復後又如何管理,這在黨內一般是還沒有解決的問題”[2]。
其後,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注意總結城市工作經驗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指出對城市工作經驗不予總結是“極端惡劣的習慣”,要求解放城市“凡有人口五萬以上者,逐一作出簡明扼要的工作總結,並限三至四個月內完成”[3]。
此後,隨着濟南、瀋陽、天津、北平陸續解放,中國共產黨開始持續積累接管城市的經驗,如對“關內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濟南,就將其設為“特別市”,由中共華東局直接領導,作為試點以“積累和探索接管、治理城市的經驗”[4]。在後續發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中國“城市文藝接管”的發展軌跡。
“城市文藝接管”存在着一個認識逐步深入、機制逐步完善的過程,如被視為“奪取大城市之創例”的1947年石家莊解放,其工作總結指出,“解放石(家)莊之戰,十一月十二日全部結束,領導機關及主要幹部於倉促中相繼入城,至十七日始成立‘敵偽物資管理委員會’正式進行接收工作”[5],下設“鐵路、工業、財經、銀行、軍械、電訊、文化、交通、運輸、衞生、通訊等組”[6],雖然設有文化組,但其所做的工作在經驗總結中基本沒有提及,顯然未受重視。
其後濟南解放,濟南特別市軍管會設有文教部,但無論是文教部本身關於接管城市的總結,還是軍管會副主任曾山關於接管濟南經驗的報告,都只涉及學校方面的工作,對文藝則不着一字[7]。此後,接收瀋陽的總結明確指出,“軍管會本身接收機構尚缺外交、軍事、社會、文化四個處”[8]。待天津解放時,天津“市軍管會下設辦公廳、接管部、文教部、市政接管處及塘大軍管分會、天津市糾察隊。
主要接管機構分財經、文教、市政三大部門”[9],雖然“文教”的重要性開始凸顯,但“城市文藝接管”的資源配給仍然匱乏,時任軍管會文教部文藝處處長的陳荒煤回憶,“文藝處工作人員較少,總共不到十來個人,深深感到缺乏經驗”[10]。直至北平解放,“城市文藝接管”的局面才大為改觀。
一方面,其準備工作周密嚴謹,接管人員首先在河北良鄉縣進行了一個多月的針對性集訓,甚至在進北平前,工作佈置就細緻到了提出“對大、中、小學及一般文化教育機關,不要不加分別地在沒有必要時也都派軍事代表”[11]的程度。
另一方面,接管後的組織建構更加完善,北平軍管會設置了龐大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員會”,成員包括李伯釗、艾青、光未然、田漢等著名文藝家,“下設教育、文藝、文物、新聞出版四部”,“文藝部下設戲劇音樂處(包括戲劇組、音樂組)、電影處、藝術教育處(包括藝專組、社團組)”[12],還成立了“北平市文藝工作委員會”,以在接管的同時開展新文藝的普及和舊文藝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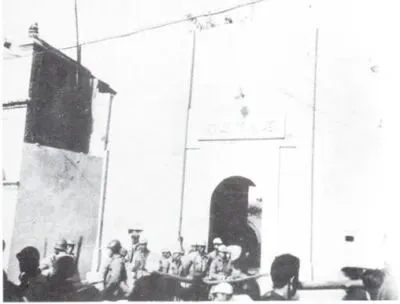
“奪取大城市之創例”的石家莊解放,圖為解放軍佔領國民黨石門市(石家莊市)政府
從石家莊、濟南到瀋陽、天津、北平,可以看出解放戰爭時期“城市文藝接管”工作在觀念、策略、組織等方面的逐步完善,也可以看出未來新中國的建設者對文藝本身的逐步重視。不過,從前期準備、實際成果和後續發展來看,“城市文藝接管”的集大成者仍是上海,正是佈局經年的淵圖遠謀、正式接管前紮實穩健的“丹陽集訓”和接管過程中對策略的靈活把握,最具代表性地彰顯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領導、治理、發展的整體邏輯。
上海的文藝接管始於1949年5月27日第三野戰軍解放上海,止於9月3日上海市政府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陳毅宣佈接管工作完成、管理建設階段正式開始。在此期間,接收單位13個,包括電影單位9個、戲院4個。但實際上藝術類高等院校亦屬文藝接管之列,如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和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即由軍管會文藝處接管。
同時,雖然依照政策,各私立學校、文藝單位不在接管之列,但文藝處仍然深刻介入到這些單位中,實際上承擔了“不接而管”的責任。另外,文藝接管是伏脈千里的長期運作,為時三個多月的接管行動只是冰山一角,解放戰爭階段長期、複雜的地下工作和解放上海前的周密準備,亦應考慮其中。
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城市文藝工作主要作為地下工作的組成部分而存在,並對日後的上海接管產生了直接影響。
抗戰勝利後,周恩來迅速對上海的文化工作進行了安排:首先是建立輿論陣地,1945年8月28日,周恩來飛抵重慶參加和平談判,甫至重慶即開始部署《新華日報》和《救亡日報》在上海的出版工作,並於9月先後派出徐邁進、劉尊棋、夏衍等駐滬,但《新華日報》始終未能出版,《救亡日報》改名為《建國日報》,僅出了12天就被封禁,後又出版了《聯合晚報》並堅持至1947年5月底;
其次是佈局戲劇戰線,1946年4月,周恩來命於伶重組上海劇藝社,推出《升官圖》《孔雀膽》,同一時期,地下黨員劉厚生、洪荒進入上海觀眾演出公司,推出《結婚進行曲》《天國春秋》等;再次,周恩來還指示建立一個民營電影據點,於是陽翰生主持成立了聯華影藝社,後改組為崑崙影業公司,推出了《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可見,當時正面的宣傳鬥爭面臨的困難很大,而以文藝創作為鬥爭武器則有更大的空間,故各文藝單位更加受到重視。
關於這些文藝單位的鬥爭策略,周恩來做出了明確指示。1946年10月,解放戰爭已經爆發,周恩來在滬接見於伶和劉厚生,對上海戲劇影視方面的工作做出了“分三線作戰”的部署,即“以上海劇藝社為第一線,高舉進步話劇運動的旗幟,只要環境允許,力爭守住這塊陣地,決不輕易放棄,但要隨時做好撤退或隱蔽的打算。
第二線由觀眾演出公司和其它一些進步劇團組成。二線劇團不宜太‘紅’,不能採用以前左翼劇團用過的名稱,更不要排演政治色彩鮮明的戲,可適當選擇一些歷史題材或外國戲劇上演,目的是團結戲劇界人士,為他們創造藝術實踐的機會,維持生活……如果第二線也難以立足,就把進步戲劇工作者分散到第三線,即電影界和地方戲劇團體”[13]。對於地方戲,袁雪芬的雪聲劇團對魯迅小説《祝福》的越劇改編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他看了《淒涼遼宮月》,説知道有越劇,不知道有這麼大的羣眾影響,應該重視地方戲,應該派人進去工作”[14]。
於是,劉厚生在1949年到雪聲劇團擔任劇務部負責人和導演,推出了《萬里長城》《李師師》等劇,錢英鬱、吳琛也被派到少壯劇團、玉蘭劇團、丹桂劇團工作,田漢還專門為雪聲劇團創作了《珊瑚引》。此外,周恩來還在1946年1月指示抗敵演劇宣傳第九隊[15]負責人呂復,要求他們“爭取留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擴大社會影響,準備迎接解放”[16]。
194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九隊地下黨支部書記呂復去上海看望於伶同志,通過他接上了上海地下黨的組織關係”,又獲得周恩來指示,“在無錫的演劇九隊在必要的時候應設法把他們調到上海來;在廣大的人民當中容易得到掩護”[17]。至1948年10月初,呂復設法將九隊調入上海。
1949年4月,上海地下黨佈置迎接上海解放的宣傳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等文告的印刷所在地即為九隊的秘密據點,並由九隊成員負責投放文告。
從解放戰爭的全局發展來看,這些安排均是為未來上海解放和接管所做的準備工作。周恩來1946年11月19日離開上海,“離滬前,他花了不少時間對於上海的堅持、疏散、隱蔽工作都一一佈置就緒”[18],10月下旬,他邀請“留在上海活動的幾位朋友——郭沫若、許廣平、馬敍倫和馬寅初等人,在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的客廳裏談話”,説“看形勢,三、五年之後回來,可能性很大;無論南京或上海,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19]。這也表明,周恩來對上海的解放和接管有着明確的預判和規劃,文藝接管至少在人員安排方面已初具模樣。
總體來説,維繫地下工作者在文藝界的穩定存在,保障幹部資源以待時局變化再圖發展,是當時中共在上海文化工作的主要戰略。雖然於伶、劉厚生等地下黨人的活動都指向未來的“解放”與“接管”,但嚴密的組織性和嚴格的紀律性又導致其行動高度收縮,以至於有進步學生回憶,“快解放那時地下黨是隱蔽的”[20]。
在1948年秋最危險的時候,周恩來更是直接要求避免“將城市中多年積聚的革命領導力量在解放軍尚未逼近、敵人尚未最後崩潰之前過早地損失掉”[21]。因此,於伶等人一度接到指示避難香港,蔡楚生、史東山、陽翰笙等重要人物亦被轉移。於伶甚至試圖將袁雪芬也轉移到香港,後者自述於伶“在香港又託人找我,要我離滬去港,我謝絕了。我的想法一直很單純,我只是個演越劇的演員,離開越劇我有何作為”[22]。

1949年,袁雪芬(左二)與程硯秋、梅蘭芳、周信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時合影
袁雪芬與於伶對離滬去港一事的分歧,體現了上海文藝界人士與黨組織親疏關係的差異以及對黨的策略、未來趨勢的不同理解。
這種親疏關係也體現於日後上海文藝接管的幹部任用以及對進步人士的安排:在“分三線作戰”部署中負責穿針引線,並且主持上海劇藝社的於伶擔任了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深入觀眾演出公司和雪聲劇團的劉厚生出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改處副處長;演劇九隊隊長兼地下黨支部書記呂復先被安排為軍管會文藝處戲音室副主任,後任華東文工二團團長;崑崙影業公司的“徐韜、張客同志等在上海軍管會文藝處領導下組織接管國民黨在上海的電影產業,在這基礎上籌建上海電影製片廠”,“1984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發文,肯定崑崙影業公司是革命團體”[23]。
被周恩來明確要求“耐心地引導她們逐步走上革命道路”[24]的袁雪芬,則成為國營華東越劇實驗劇團團長。
可以説,對上海的文藝接管,既始於解放戰爭時期高層的戰略擘畫,也基於一線工作者的長期耕耘,這些先期準備及其成功執行,幾乎直接決定了接管工作的人事安排和發展趨向。由此,也能夠清晰地看到嚴峻的革命形勢與文藝工作的深度交融。
二
1949年4—5月,上海解放近在眼前,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和北方趕來的大量幹部卻在距上海兩百餘公里的小城丹陽停留了二十多天,進行了一次重要的集中培訓。這一集訓預先解決了接管上海的思想、組織、物資等諸多問題,既是順利接管上海不可缺少的一步,也是中共成功實現“農村—城市”重心轉移的重要一環。
“丹陽集訓”的發生,首先是中共高度重視上海解放和接管的結果,1949年5月3日,中央軍委曾致電總前委[25],命令“上海在辰灰以前確定不要去佔,以便有十天時間作準備工作”(“辰灰”為5月10日),要“拖長時間至半個月或廿天或一個月再去佔領”,“過去你們在三個月準備渡江期間沒有抽出一個月時間,令軍隊學習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項,沒有作很快佔領諸城的精神準備和組織準備,吃了虧。現在只好在十天內補足此種缺點”[26]。
於是,小城丹陽就成為了解放上海的籌備中心,從1949年4月24日至5月26日,丹陽“會聚了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6人、後(候)補委員2人,會聚了總前委、華東局、華東軍區和上海局等領導機關及主要領導幹部,會聚了黨、政、軍、財、文各界精英,駐丹陽人數共有3萬多人”[27]。

江蘇丹陽總前委舊址
“丹陽集訓”的對象是戰士和幹部,於前者是“指揮”意義上的,於後者則更多是“組織”意義上的;對戰士的要求是遵守紀律,對幹部的要求則是建立秩序。“一路打到丹陽的解放軍戰士們……不但不開拔前進還在丹陽一待就是20多天……一本本學習手冊發到戰士們手中,《入城守則和紀律》《約法八章》等不僅要逐條學習領會,還要全文背誦。”[28]
在這種嚴明的紀律教育加持下,解放軍在上海入城的表現廣受讚譽,《申報》1949年5月25日報導“人民解放軍已於今晨進入上海市區”,“共軍自衡山路一帶,分隊向東徐徐推進,紀律甚佳,秩序井然”,“上海精華之區能倖免戰爭之破壞”[29]。
對幹部而言,“丹陽集訓”除必要的學習之外,更包括接管上海的機構設計、人事安排、策略議定等,這就是最終彙總形成的《上海市軍管會各接管委員會接收計劃》(即“丹陽計劃”)。也正是這些周密準備,推動了新中國文藝向着某種特定軌道行進,並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未來新中國文藝的面貌。
關於上海文藝領域的接管,中央可謂高度關心。在饒漱石向中央的報告中,即提出由陳毅任主任的上海市軍管會下轄財經、文化教育、軍事三個委員會,其中財經、軍事為“接管委員會”,而文教為“管理委員會”,“其他委員會都稱‘接管’,只有文教委員會叫‘管理’,因文教不實行軍管”[30]。
同時,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的主任由陳毅兼任,財經、軍事兩會則無此情況[31],中央的覆電亦強調“文教接管委員會規模太大,應由陳毅兼主任”,並且“分擔各部工作同時亦必須吸收一部分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接管”[32]。在1949年3月14日,鄧小平、饒漱石、陳毅在致任弼時的信中特別提出,“關於上海工作,除請調幹部外,其中如章漢夫、夏衍等,務請你注意到工作必需準其調往……夏衍在主持文化工作方面亦十分切合需要”[33]。
隨後,中央調回在香港的夏衍。1949年5月5日至15日,夏衍在北京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分別接見並予以指示。5月23日,夏衍抵達丹陽,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由其實際負責,“領導班子是於伶、黃源、陸萬美、鍾敬之、向隅”[34]。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還“成立文藝處”,“屬於管制委員會下面文教管理委員會的四個處之一,完成接管任務之後,擔負起全上海的文學藝術建設的任務”[35]。
根據黃源的回憶,“於伶同鍾敬之接管電影系統,我接管音樂、戲劇學校,文化機構”[36]。未來上海解放後的文藝接管架構,在丹陽即告完成。實際上,陸萬美因“參加籌組全國文代會華東代表團,二三個月內來不了”[37],後又於1950年底調職雲南;向隅則一直在東北魯藝工作,直至1949年10月才調任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陸、向二人對上海文藝接管工作的作用相對有限,夏衍、於伶、黃源和鍾敬之是更直接的責任人。
有學者指出:“在整個中國新舊政權交替之中,對於上海的安排明顯帶有特殊性。周恩來特地安排夏衍、於伶……負責上海文教工作,有着他的考慮。據説,周恩來交代夏衍的原話是:‘抗戰前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這之後一直在蔣管區,熟悉大後方情況,所以中央決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38]夏衍抵達丹陽時已經是5月23日晚,而5月25日接管隊伍已經進入上海。
也就是説,作為上海文藝接管的最高領導人,夏衍只接受了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並沒有完整地參加“丹陽集訓”。在中央看來,夏衍的蔣管區經驗應已覆蓋了集訓所提供的接管準備。而夏、於、黃、陸、鍾、向六人的組合,顯然有着組織上的嚴肅考慮。六人中除陸萬美外,都有在上海學習或長期活動的經歷,而陸萬美曾經活躍於北平,系北平“左聯”和學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六人皆有豐富的大城市工作經驗。
同時,除陸萬美為雲南人、向隅為湖南人,其他四人皆出身江浙,與上海在地緣和文化方面極為接近。另外,夏、於始終從事白區工作,向、鍾長期在延安工作,黃、陸則長期在華東解放區工作。也即是説,接管上海文藝工作的領導人架構為白區、延安、華東各佔三分之一,由白區地下工作者負主責。在職務方面,也“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夏衍在軍管會時期,是文教委員會的副主任、文藝處處長,但不是黨組書記;黃源是文藝處副處長,卻是黨組書記,而黨組書記則是實際領導人”[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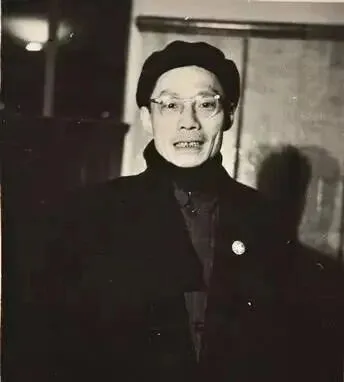
1950年,華東軍管會主要成員標準照——夏衍
於是,在這一架構下,由於出身和背景的區別,就出現了一種磨合的需要。如夏衍到上海後就回到家中探望親人,卻讓公安局局長楊帆如臨大敵,馬上給他配備了警衞員和汽車,並告誡夏衍“這是必須遵守的制度,你沒有參加丹陽的幹部集訓,可能不知道,你是‘文管會’副主任,是一個不小的目標”[40]。
而在對待接管任務的態度上,周恩來問夏衍:“中央決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全國解放後,你有什麼打算?”夏的回答是“我在大學學的是電工,還是讓我回本行吧”[41]。又如任職前於伶曾對領導過他的文委書記孫冶方説:“請組織調換個人,讓我當個副職吧!”[42]夏、於不約而同地“推脱”,顯示出地下工作者出身的知識分子的一種普遍而微妙的心態,也流露出白區工作者、知識分子身份和城市接管工作之間的某種“失調”。
黃源在後來的回顧中,曾提及“接管時有一條原則,就是以解放區、根據地裏出來的幹部為主體”[43],後來的研究者又有了更加精細的概括,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選用幹部時,常“儘可能選擇本地幹部來擔任第一把手。前提是,這些幹部必須是長期在外,經受過戰爭洗禮、土改整風等歷次運動,已經熟悉中央各項政策者”[44]。
顯然,為了接管的順利實施,上海文藝接管在人事安排上進行了較大幅度的“經”“權”調整。
如果對比“丹陽集訓”中不同系統的集訓學習情況,又會發現一些差別。如“幹部戰士學習入城政策、紀律,早在1948年解放濟南、徐州以後就開始了”,“財經幹部隊伍,在青川出發前,就開始學習入城政策、紀律,公安幹部隊伍在濟南解放後也開始學習,軍事部門的幹部、戰士學習時間可能更早,只有文教系統幹部到丹陽後才開始學習”[45]。
這就説明,無論從基層培訓實踐還是從頂層管理設計來看,上海的文藝接管都先天具有獨特性,這在中央看來是成功接管上海所必須的。
在接管城市前進行集中培訓,是中共實現“農村—城市”戰略重心轉移的重要經驗,“丹陽集訓”即其集大成者。有關文藝方面的幹部培訓則獨具特色,或者説,相對於其他方面的令行禁止,在文藝方面存在着人事配置、職責安排的微妙張力,也可以進一步發現,文藝幹部在“接收管理”乃至日後的“管理改造”中佔有關鍵地位。
三
1949年前後的城市文藝接管工作,具有一種明顯的靈活與辯證色彩。如上海接管政策,是隻接管公立和敵偽的文化機構,而對私立機構不予接管亦不實行軍管。但針對各單位的實際操作則更加複雜多樣,表現為“接而管之”和“不接而管”的結合。
根據“丹陽計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下設高等教育處、新聞出版處、市政教育處、文藝處。文藝處下設秘書室、文學室、劇音室、劇藝室、美術室、電影室,大體可劃分為文學和藝術兩類。基於二者發展的不同情況,藝術如電影、戲劇等在接管工作中相對更受重視,文藝處的直接介入更加明顯,而文學接管則更多依賴上海本地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上海分會”。
當時,有國民黨背景的文學組織“上海文藝作家協會”處於事實上的瓦解狀態,而著名的刊物如《文藝復興》亦已停刊,多數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葉聖陶等也已離開了上海,可以説“文學接管”工作不多,以至於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進駐上海一週後,工作總結中關於文學室的只有寥寥兩句“主要是和文協的同志聯繫,瞭解上海的文藝界狀況”[46],到第二、三週,甚至沒有文學室的報告[47]。故而,上海文藝接管主要是以“藝”為主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軍管會文管會文藝處進入上海
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和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是上海文藝接管的主要對象,據黃源回憶,“上海軍管會文化委員會所屬的文藝處。任務是接管文化系統,包括教育系統的藝術部分”,“文藝工作上是以我為中心的”,“我接管音專與劇專”[48]。
而接管作為“行動”常常是程序化的,即對接管對象的人員予以接收和任免,對物資財產、檔案資料予以接收,耗時並不長。對財物本來就談不上豐裕的文藝機構,接收就更加簡單。如黃源接收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也只是在1949年6月6日上午10時舉行接管儀式,下午1時即告結束,連學校財物都未接收。接管活動之所以能如此順利,又與中共長期縝密的地下工作不可分割。
在黃源主持接管兩所院校前,兩校的黨組織已經有了較深厚的組織積累。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1945年3月、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在1947年秋分別成立了黨支部。在上海解放前,由黨支部主持,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陸續發動和參加“反附逆反甄別”“新音樂”“成立上海音協”“遊行抗暴”“反飢餓、反內戰”等運動,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則發動和參加“追悼李公樸、聞一多”“護校鬥爭”“組建演劇服務隊”等活動,都形成了較成熟的組織隊伍。
但需要注意的是,1948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蔣管區鬥爭要有清醒頭腦和靈活策略》,要求共產黨“在城市方面,應堅決實行疏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尤其是上海,應實行有秩序的疏散”[49]。
因此,學校中大量地下黨員和左翼學生在解放前就已先期撤離,即“隨着三大戰役的展開,白色恐怖日益加深,劇校將近有五分之一的進步同學出走解放區”,“地下黨員的先後離開,使得劇校黨支部的工作陷於停頓”[50],後來學校內深度參與接管的學生黨組織是重建的結果。
1948年11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指示下,劇校研究班學生陳忠毅積極着手發展新黨員、重建黨組織工作”[51]。當時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學生生活極為困難,甚至不得不到街上打狗充飢,於是,黨支部將學生自治會臨時改組為“非常時期膳食委員會”,“統籌劇校學生的生活、學習、演出等各方面的活動,使之成為全校性的應變機構,依靠羣眾的集體力量來解決生活問題”[52],獲得了學校師生的廣泛支持。
在上海解放前的兩個月,學校已經無法維持正常教學秩序,為防不測,學校組織了“應變小組”,小組中的部分學生在亂中繳了一個排的十幾只槍,於是學校又擁有了自衞武裝,以近乎獨立的性質等待解放軍前來。在1949年5月27日當天,“同學們在樓頂升起了用紅色被面做的紅旗……將藏在家裏的傳單,拿出來由同學們四處散發”[53]。
可以説,在當時戰局紛亂的情境下,黨組織已經是學校重要的依靠對象,以至於有“劇校在名義上是國民黨公立學校……要有一個接管手續”[54]的説法。由此也可以理解熊佛西在1949年6月6日迎接接管時興奮地説:“我從事戲劇卅年以來,就希望有這麼一天。”[55]

1949年熊佛西在上海市立戲劇專科學校四週年校慶活動中
另外,隨解放軍入城,參加接管的中下級幹部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是此前撤離的地下黨員和左翼學生。在中共的計劃安排中,這些暫時撤離上海的骨幹本身就是未來接管上海的中堅,他們撤退後“受到首長特別是陳毅同志的很大重視和關懷;陳丕顯同志還專門為上海去的幹部舉辦訓練班或送黨校學習,予以培養和訓練。
以後這批幹部隨軍南下,大部分參加瞭解放上海後的接管工作”[56]。上海剛解放的第二天,早在1948年就奔赴解放區的丁寧回到母校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動員17人蔘加中共松江地委文工團[57]。這種運用上海文藝單位黨員和積極分子來接收單位本身的策略,無疑降低了接管的難度。
由此可見,上海文藝接管雖然從表面看遵循自上而下、由外到內的公開程序,甚至看上去是不乏軍事佔領意義的“外來掌控”,但從其內裏則可以看出,文藝接管的因勢利導,更多表現為內外結合式的複合運作。
對公私文化教育機關,依照《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執行的政策是“一律保護,不受侵犯”,“凡在這些機關供取的人員,均望照常供職”[58]。但從全國建設的角度來講,當時的指導思想是“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59]。
因此,在文藝接管實踐中,對私營文藝團體,往往是雖不接收卻要管理。而且這種管理也是公開的,如在天津接管中,軍管會就專設了一個“不管接管處”[60],以解決這種“不接而管”的問題。上海文藝接管過程中的典型案例,則是對雪聲劇團的“不接而管”。
雪聲劇團於1944年9月由袁雪芬創辦,該團“在越劇界率先建立正規的編導制,由劇務部掌握劇目選擇權和整個演出活動”,並主張“戲劇是社會和人生的反映”[61]。1946年該團演出《祥林嫂》,首次以越劇形式改編魯迅名著,受到左翼文藝界和共產黨的重視。
但在接管主持者黃源看來,“上海戲劇舞台是靠繼拜娘支撐。演員的素質、思想境界,仍停在繼拜娘需求的水平”[62],“總的藝術傾向、氣質上,卻被資產階級藝術思想蛀蝕得相當腐朽了”,在舞台呈現上甚至是“俗氣的‘服裝展覽’”[63],哪怕是進步越劇《祥林嫂》,也為了照顧越劇的傳統和迎合市民趣味而增加了祥林嫂與阿牛相戀這樣的情節。因此,軍管會文藝處對雪聲劇團雖並沒有“接”,卻有意識地、持續地予以引導支持。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對袁雪芬和雪聲劇團這樣的進步藝人和團體,存在着非常明確的引導和要求。早在1946年,周恩來就在觀看雪聲劇團的演出後指示於伶,“動員黨員從戲劇藝術入手”,“引導她們逐步走上革命道路”[64]。袁雪芬也曾回憶,上海解放後“於伶同志問我: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什麼要求”。當聽到袁雪芬“無任何要求,只要求讓我好好演戲”時,於伶説:“你應該成為一個藝術家和政治家。”[65]因此,培養袁雪芬成為“藝術家和政治家”與對雪聲劇團的“不接而管”都成了重要的內容。
1949年7月22日,軍管會文藝處舉辦了第一屆地方戲劇研究班,共計47天,後又在1950年8月、1951年7月連續辦了兩次。第一屆地方戲劇研究班尤其以越劇為重點,“其他劇種只要求編導參加,越劇界則要求編、導、演、音、美等人員都參加”[66],“課程有《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67]。
此次學習結束後,又在1949年12月將研究班的四個越劇劇目拍攝成電影,取名“越劇菁華”,袁雪芬出演了其中的《雙看相》。該片片頭序言特別説明,此片是“為了回顧越劇發展的過去,開創人民越劇廣大的道路,上海市第一屆地方戲劇研究班特將越劇發展各階段的代表性的幾個舊劇,記錄下來,以供羣眾和各地文藝工作者共同研究,在這一基礎上,推陳出新,進入科學地整理和改革的階段”。
顯然,“學習—提高”的訴求、“推陳出新”的要求都給了整個舊越劇(包括演員、劇團和劇目)明晰的方向,使其進入戲曲改革的特定軌道,而雪聲劇團也必然要接受這種管理和改革。而且,業務研討與政治提升是高度結合的,1950年1月10日,第一屆地方戲劇研究班學員畢業不久,即在軍管會文藝處大禮堂成立了中國戲曲界的第一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支部,袁雪芬等23人被批准入團。
袁雪芬在學習的同時,社會政治地位也持續提高,就在結束研究班的學習後不久,1949年9月,她作為戲曲界四位特邀代表之一,參加了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在北京數次獲得周恩來的邀請和接見。
次年10月,袁雪芬代表中國前往華沙出席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又作為列席代表參加世界青年聯合理事會,其後作為中國青年訪蘇團成員訪問蘇聯。密集的議事、參政、出訪活動無疑極大地改變了她的心態,使她愈加主動地向政治靠攏。

1978年越劇電影《祥林嫂》:袁雪芬(右一)飾祥林嫂
在“成為一個藝術家和政治家”的進程中,袁雪芬與時代進程逐漸融合在一起,雪聲劇團的改變只是這一進程中的一個環節。1950年2月,上海越劇實驗劇團成立,袁雪芬任團長,雪聲和雲華兩個劇團共36人[68]成為其主要力量。其後不到兩個月,又以上海越劇實驗劇團為基礎成立華東越劇實驗劇團,袁雪芬任團長。這是華東地區首個國營戲曲劇團,也是新中國首個國營越劇團。
而無論是這一劇團的成立,還是袁雪芬本人的不斷進步,顯然又都是“不接而管”的直接結果。實際上,通過“不接而管”,培養袁雪芬成為“藝術家和政治家”,也是中國當代文藝追求“藝術與政治相結合”的一種映射,文藝接管敏鋭地錨定了政治和藝術的結合點,始終表現為積極推動兩者的合二為一,不僅在藝術層面上引領、教導和推動其推陳出新,也在政治層面上持續鞏固藝術的基礎,這在對袁雪芬的培養方面尤為明顯。
早在1947年,浙東大戲院老闆張春帆曾迫害越劇名伶筱丹桂並致其自殺身亡,引發了越劇界的廣泛憤慨,袁雪芬曾作為代表向張春帆抗爭,並與其對簿公堂。1951年5月28日,張春帆被逮捕,其後袁雪芬多次參加座談,公開發表對張春帆的控訴,與越劇界同仇敵愾地指出:“越劇界的漢奸惡霸特務張匪春帆,他是我們越劇界的公敵,也就是人民的敵人。”[69]
7月28日,張春帆被軍管會判處死刑,袁雪芬等越劇界人士登報感謝,宣稱“要替一切受難者伸冤,只有讓迫害者的血,來祭奠被迫害者之靈”[70]。對張春帆的懲處,推動了袁雪芬在“政治家”道路上更進一步,而這也顯示出文藝接管本身堅實的政治底色,恰恰是這種在上海解放前就開始堅定貫徹的政治意志,保障了文藝接管的方向。
無論是“接而管之”還是“不接而管”,顯然都面向中共爭取全國勝利的現實目標和國家建設發展的長期目標,為實現這些目的,文藝接管在策略上就擁有了較大的彈性,也保留了相當的容錯空間。但作為一個銜接戰爭與建設的中間環節,接管仍然保留了明確的指向性,無論是對地下文藝事業的長期經營,還是對民間進步文藝的選擇和扶持,都體現了靈活性和原則性的統一。
四
作為軍事管理的一部分,“城市文藝接管”往往公開、迅捷和直接,實際上,接管行動就像水面上的冰山,易於察覺的只是表面,其背後運行的則是整個系統,這一系統長期影響了新中國文藝的發展,或者説,通過“接管”這一界面,能夠發掘出某些深度塑造新中國文藝的關鍵點。
首先,黨的領導和周密安排深度介入了文藝活動。上海文藝接管充分展示了來自解放區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為政治服務”等主張,同時,國統區文藝戰線又在黨的領導下發揮了巨大的戰鬥堡壘作用。後者的經驗相當曲折複雜,如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的黨組織對越劇的引導,使作為通俗文藝的越劇具有了革命意義。
越劇《祥林嫂》的劇本構思、演出動力乃至主創團隊造訪許廣平,都離不開丁景唐、吳康、廖臨等共產黨人的協助。在上海文藝接管完成後,越劇就憑藉對黨的工作的配合而備受重視。複雜革命形勢下文藝活動的組織實施的重要性受到廣泛認可,這對共和國文藝的影響無疑是長期和深刻的。
其次,不可忽視的是“幹部”在接管乃至整個中國文藝中的作用。在軍事勝利的保障下,城市文藝接管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幹部的培訓、調配、組織、運用,幹部成為改造舊文藝、建構新文藝的重要環節,文藝幹部也成為新中國與舊中國、現代文藝與當代文藝交接的全新樞紐,正如毛澤東所主張的:“我們的革命依靠幹部,正像斯大林所説的話:‘幹部決定一切。’”“黨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繫黨員和羣眾,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羣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71]
文藝幹部以不同的方式,在所有層面上深刻介入了舊的文藝生態,進而施加接收、管理和改造,從而建造新的文藝生態。在這一過程中,全面系統的“管理”是中國當代文藝的重要特點,因而圍繞文藝幹部的一系列操作就構成中國當代文藝的全新內容。而怎樣培養適合需求的文藝幹部和怎樣利用文藝幹部應對舊文藝及建設新文藝,在實際上構成了接管乃至接管之後最具概括力的文藝命題。文藝幹部自身的底層邏輯、經權斟酌和管理方式更影響了未來文藝發展的整體取向。
最後,需要關注的是城市文藝接管中“軍管”本身的客觀存在。作為解放戰爭與和平建設的交接階段,“軍管”使軍事行為延伸到文藝活動之中,在中國當代文藝的起點上,軍事與文藝的密切性即已產生。文藝接管的負責人對自己的軍人身份也高度認同,如於伶在前往丹陽前,自述在北京“脱下西裝穿上軍裝,以‘書生戎馬’脱胎換骨的莊嚴心情,重讀了黨中央的進軍命令”[72],夏衍則每次“填履歷表時”,“就在‘何時入伍’這一欄上,填上‘1949年5月24日,在丹陽’”[73]。
可以説,對文藝接管而言,其“軍事”成分始終是積極和有力的。雖然至1949年底,軍管會逐漸“變成了一個協調和監督的機構,其辦公室大部分沒有辦事人員,因為行政職能日益被新政府直接承擔。到1951年,它的職能基本上減少到治安和衞戍事務方面,因為地方政府這時單獨發佈命令了”[74]。到1953年底,上海軍管會基本完成歷史使命,但“軍管會”這一名稱仍然長期保留,“掛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大門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牌子,於1987年撤除”[75]。也即是説,自接管發生以來,文藝受其影響至少在名義上一直延伸到20世紀80年代。
在中國文藝由“現代”向“當代”、從“農村”到“城市”的轉折中,上海的文藝接管顯示出垂範和建制的意義。作為一種軍事、行政和文化三重性質兼具的行動,也作為中國當代文藝史初肇的一部分,文藝接管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並提供了推動力,同時也使中國當代文藝打下了接管的烙印。
另外,上海文藝接管的基本目標,是平穩地將文藝界整合到上海和平解放的政治全局之中,因此更多地依賴於接管者的白區工作經驗,一俟接管目標順利實現,當代文藝的使命就轉向了文藝制度、文藝經典乃至觀眾讀者等方面的推陳出新,可以説,文藝接管是促使當代文藝發生諸多劇烈變動的一個關鍵轉捩。
總之,歷史地看,文藝接管顯然能夠在更底層的邏輯上展現新文藝制度建構的驅動力、結構、傾向和限度,能以切片的形式展現共和國文藝的整體性,可謂同時具有現場與遠景的意義。
[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頁。
[2] 《中央工委關於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3] 《中央關於注意總結城市工作經驗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53頁。
[4] 狄井薌:《憶濟南特別市》,《城市接管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頁。
[5] 《石家莊市入城工作經驗的初步總結(初稿)》,石家莊市檔案館編:《石家莊解放》上,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頁。
[6] 《中共石家莊市委關於接收工作的報告》,《石家莊解放》上,第301頁。
[7] 參見《濟南特別市軍管會文教部接管工作初步總結(節錄)》,中共濟南市黨委黨史研究室、濟南市檔案館編:《濟南的接管與社會改造》,濟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7頁;《接管工作總結——曾山關於接管濟南經驗的報告》,《濟南的接管與社會改造》,第159—162頁。
[8] 《接收瀋陽的經驗(1948年11月28日)》,中共瀋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瀋陽卷,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頁。
[9]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頁。
[10] 陳荒煤:《回憶天津接管時期的文藝工作》,《城市接管親歷記》,第153頁。
[11] 《中共北平市委關於如何進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黨內通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頁。
[12] 劉宋斌:《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98—999頁。
[13]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頁。
[14] 劉厚生、張煉紅:《“戲改”再反思:新中國的文化理想及其實踐——“老戲改”劉厚生訪談錄》,《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5期。
[15] 演劇隊於1937年8月成立,由中共指導和組織,前身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救亡演出隊”,其中第二隊於1938年8月列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改名“抗敵演劇第二隊”;1941年3月,改名“抗敵演劇宣傳隊第九隊”;1946年1月,改名“軍委會政治部演劇第九隊”,10月改隸國防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特種勤務署,簡稱“聯勤總部演劇九隊”。演劇九隊於1938年8月建立黨支部,作為中共領導的專業文藝團隊達十二年之久。
[16] 呂復:《周總理對“演劇隊”的親切教誨》,北京師範大學編:《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第五集,1978年內部出版物,第202頁。
[17] 《演劇九隊(原抗劇二隊)大事記》,演劇九隊隊史編輯委員會編:《八千里路雲和月:演劇九隊回憶錄》,1988年內部出版物,第440頁。
[18][24]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上海革命文化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頁,第442頁。
[19] 許滌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周總理在國統區的鬥爭》,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5頁。
[20][50][51][52][53][57] 顧振輝:《凌霜傲雪巋然立——上海戲劇學院·民國校史考略》,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37頁,第316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81頁,第352頁。
[21][49] 周恩來:《蔣管區鬥爭要有清醒頭腦和靈活策略(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頁,第311頁。
[22][66] 袁雪芬:《求索人生藝術的真諦——袁雪芬自述》,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頁,第118頁。
[23] 季洪:《“你們守住這個陣地”——崑崙影業公司》,陳播主編:《季洪電影經濟文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33頁。
[25] “總前委”於1948年11月16日成立,職能為“統一指揮淮海前線作戰和領導戰區支前工作與後勤保障工作”,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劉、陳、鄧為常委,鄧為書記(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頁)。
[26] 《中央軍委關於佔領杭州、上海問題致總前委等電(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解放》上,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82—83頁。
[27] 中國共產黨丹陽市委員會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羣英會丹陽》,1989年內部出版物,第4—5頁。
[28] 上海解放紀念館:《細節決定成敗:丹陽整訓與接管上海》,《世紀》2024年第3期。
[29] 《槍炮聲昨澈夜不絕 解放軍今晨入市區》,《申報》1949年5月25日。
[30] 範征夫:《“南下”的回憶》,《人才開發》1999年第5期。
[31] 《饒漱石關於接管上海準備工作的情況致中共中央電(1949年5月10日)》,方曉升主編:《接管上海》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頁。
[32] 《中共中央關於接管上海的機構及幹部配備復饒漱石、華東局電(1949年5月20日)》,《接管上海》上,第53頁。
[33] 楊勝羣、閆建琪主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07—808頁。
[34][40][41][73] 夏衍:《懶尋舊夢錄》,《夏衍全集》第15卷,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頁,第319頁,第311頁,第315頁。
[35][37][42][72] 於伶:《四十年前隨軍進上海》,孔海珠編:《於伶研究專集》,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頁,第174頁,第175頁,第169—170頁。
[36][43][48][62] 《黃源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頁,第219頁,第221—222頁,第224頁。
[38][64] 孔海珠:《於伶傳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頁,第371頁。
[39] 吳中傑:《黃源:在文藝與政治的夾弄中》,《魯迅的抬棺人:魯迅後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頁。
[44] 楊奎松:《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談1950年代反“地方主義”的由來》,《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一輯,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45] 範征夫:《1949年丹陽集訓幾個問題的探討》,《上海黨史與黨建》2010年第8期。此處“青川”應為“青州”,南下幹部縱隊於1949年2月從山東青州出發南下。
[46] 《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一週接管工作綜合報告(1949年6月4日)》,《接管上海》上,第434頁。
[47] 參見《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第二、三週接管工作總結(1949年6月20日)》,《接管上海》上,第434—443頁。
[54] 劉厚生:《熊老在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戲劇學院熊佛西研究小組編:《現代戲劇家熊佛西》,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頁。
[55] 《接管“上海市立劇校”速寫》,《青青電影》1949年第14期。
[56] 張承宗:《解放戰爭時期上海的人民革命運動》,本社編:《紅旗飄飄》第18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48—249頁。
[58] 《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1949年4月25日)》,《接管上海》上,第15頁。
[59] 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六月六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50年6月13日。
[60] 《天津接管時期組織機構幹部名錄表(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天津市檔案館:《天津接管史錄》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頁。
[61] 盧時俊、高義龍主編:《上海越劇志》,中國戲劇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頁。
[63] 劉厚生:《漫談上海戲劇藝術的推陳出新》,《上海戲劇》1962年第4、5期合刊。
[65] 袁雪芬:《難以忘卻的往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新中國地方戲劇改革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頁。
[67] 章力揮、高義龍:《袁雪芬的藝術道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頁。
[68] 蔣中崎編著:《越劇文化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頁。
[69] 王文娟、尹桂芳、吳小樓、範瑞娟、徐天紅、徐玉蘭、袁雪芬、陸錦花、戚雅仙、傅全香、張桂鳳等上海全體越劇工作者:《控訴張匪春帆》,《亦報》1951年7月28日。
[70] 王文娟、尹桂芳、吳小樓、範瑞娟、徐天紅、徐玉蘭、袁雪芬、陸錦花、戚雅仙、傅全香、張桂鳳等上海全體越劇工作者:《感謝政府替我們復仇》,《亦報》1951年7月29日。
[71] 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羣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7頁。
[74]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謝亮生、楊品泉、黃沫、張書生、馬曉光、胡志宏、思煒譯,謝亮生校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頁。
[75] 《上海軍事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