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疫情之下,遊居文明也暴露了它的天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線”中的文明因素》,強調了這一次中國以總體戰、阻擊戰的應對方式抗擊疫情,背後有中華文明獨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認為,中華文明最大的獨特性在於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長達數千年連續不斷的定居。正是因為連續不斷的定居,這個文明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護家園並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遊居文明那樣在連續不斷的遷徙中鵲巢鳩佔他人土地,劫掠搶奪他人財富。
所以,這個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夠發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羣體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過高水平的集體行動團結一致抵禦外來威脅的能力,包括抵禦外敵入侵和對抗瘟疫流行。
此觀點似乎帶有這樣的含義:其他文明不具有這種獨特天性以及相應的獨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實很可能是這樣。
到目前為止,新冠肺炎已經發展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從中國轉移到了歐洲和美國,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區,正好可以觀察一下這個文明到底是如何應對這場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應對過程中這個文明又顯現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從疫情開始暴發一路發展到現在,在歐洲和美國已經出現了很多令中國人難以理解甚至感到震驚的現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經出現之後,民間的大型聚集活動像馬拉松、狂歡節、宗教活動等照常進行,儘管專家和政府都發出了警告,但民眾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對中國的疫情發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視而不見,提前一個多月的預警時間、震天響的警告哨聲完全不起作用,應檢盡檢、應收盡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會隔離等措施,並不及時仿效;直到意大利轉眼間成了第二個湖北省,病死率衝到了7%以上,英國、德國和瑞典等國竟然還決定以“羣體免疫”的“躺倒政策”應對,似乎準備欣然接受百萬級的歐洲人口損失。
再例如歐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確診人數開始擠兑醫療資源時,就很快出現了犧牲老年人的“選擇性治療”情況;而美國更過分,只是剛剛出現經濟停擺的徵兆,就立即出現了犧牲老年人的聲音,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採訪時公開表示,為了避免美國經濟發生崩潰,老年人羣體應該自己照顧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老年人很願意以犧牲自己做交換。
視頻/觀察者網 張逸清
在此之外,還有美聯儲以抗擊疫情名義實施的“無限量QE”,包括開放式的資產購買,將自身的“最後貸款人”角色直接換成了“最後購買人”角色,通過狂印美元託底股市、託底破產企業。這個極端舉措的含義到底是什麼?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來無限量的美元任其氾濫,到底是要幹什麼?
以上種種,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國人的常識理解。反觀中國這裏,政府不讓摘口罩,全國人民就這麼戴着,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着一起執行規定。政府説有序復工復產復市,誰也沒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負盈虧的民營企業,寧肯忍受着每日累積的成本損失,也一切行動聽指揮。至於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漢疫情最嚴重、醫療資源擠兑已經發生的那些日子裏,是否犧牲掉老年人這個問題也從未出現。確切説,對於中國人來説,這根本是一個想都不能去想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東西在決定着兩者之間這麼大的反差?其實還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觀點,既然從政府到民眾都表現出巨大反差,那麼答案就不能僅在政治制度上尋找,還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當中。
如果説歐美的“羣體免疫”和“犧牲老年人”體現的是一個社會哪怕只是為了一個並不確定的未來,就可以先犧牲掉本社會弱勢羣體這一叢林社會邏輯,那麼,中國的全民聽指揮、不以部分利益干擾全局、整個社會在統一調度之下有序運轉,體現的就是一個社會一旦看到可以確定的未來後,全民就會採取步調高度一致的集體行動這一文明社會邏輯。
疫情開始暴發時,一聲令下全國人人戴口罩,疫情開始緩解時,全國分區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這一現象,其中反映出來的集體行動水平和背後強大的文明邏輯,足以令人震驚!
遊居文明與定居文明之不同
與中華定居文明相對的,是可以籠統稱之為“遊居文明”的另一大類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書《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中,特別澄清了一個問題,即英文中與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對的Nomad不應翻譯成“遊牧”,而應該翻譯成“遊居”,與中文“定居”一詞相對。
在人類學和考古學意義上,定居的定義,可以指一種狀態,即“在一個地方長時間羣體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個過程,即“從遊居社會向永久留在一個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轉變過渡”。而Nomad這個詞本來的定義是指所有“沒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羣社團”,並不專指遊牧社會,也指沿貿易路線遊走的商隊或過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賽手藝人等,廣義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羣,所以應該是中文的“遊居”。
這個分辨,非常有助於理解中華定居農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為如果追溯人類歷史的演進,早期人類社會都是遊居的,定居才是個別的異常狀態。這就意味着,從最初那些四處遷徙、居無定所的狩獵採集遊團(Band),到草原上那些騎馬的遊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乾旱地帶那些從事長途貿易的遊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帶那些通過大遷徙強佔他人土地的遊擊民族、遊盜民族,這個長達數千年的發展構成了人類文明史的一條連續不斷的主線,就是所謂的遊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徵就是遊動,文明在不斷的遊動中演進與發展。
顯然,這些不同類型的遊居文明與中華定居文明——這種很早就開始成片地定居下來、通過在原居地大規模治水和農業革命率先轉入農耕生產生活方式、連續數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發展出的定居文明,互為鮮明對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遊居文明與定居文明的劃分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只在歷史學家的圈子裏討論,並未進入現代國際關係領域成為一種概念工具,是因為人類社會在最近的幾個世紀裏由於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權國家的先後建立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絕大部分曾經的遊居社會都紛紛轉成了定居社會,不再四處遷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與遊居文明之間的差別了。
《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中寫道:
在人類文明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定居社會並不是人類社會的主流,遊居社會的數量和總體人口規模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大大超過定居社會;人類的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都轉為定居、進入城市、成為國家的國民,是很晚近的變化。實際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遊居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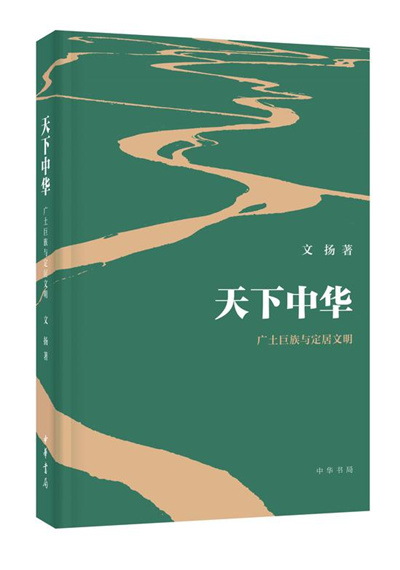
就以通常所説的西方文明為例。眾所周知,今天的美國是一個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組成的國家,建國不過才240多年,原住民被滅絕了,所有移民的古代祖先都在這片土地之外。在人類文明史的大尺度上看,這就是一個不久前從其它大陸遷徙過來剛剛才定居下來的遊居社會。
除美國外,新世界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莫不是如此,包括拉丁美洲這個由歐洲移民與原住民混雜而成的社會,作為國家的歷史,最早也早不過大航海時代的開始,都是歐洲社會大遷徙的產物。
大航海時代製造出最近的一批遊居社會,那麼,往前推到大航海之前,那個歐洲社會是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定居社會呢?歷史見證,並不是。大航海時代這一次大規模移民潮,實際上是此前500年發生的十字軍東征那一次大規模移民潮的繼續,都是被同一個永恆的動機——尋找東方的財富——刺激起來的。
那麼再往前推,十字軍東征之前的歐洲社會是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定居社會呢?歷史見證,也不是。十字軍東征的主體是歐洲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各個基督教國家,他們並不是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是此前500年發生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大規模移民潮的後代,祖先都來自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那一片巨大的日耳曼森林中的蠻族世界。
再往前推就沒必要了,無論是紙上文獻還是地下文物,都證明那裏一直是被文明之光遺忘的黑暗角落。
羅馬帝國覆滅是公元5世紀的事,從日耳曼森林裏衝出來的那一羣蠻族,首先鵲巢鳩佔了歐洲,500年後鵲巢鳩佔了東地中海世界,又500年後鵲巢鳩佔了世界海洋和所有新大陸。可以説,這一文明在最近的1500年裏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遊居”,而且是通過搶佔異族土地、掠奪異域財富的形式擴張自身,本質上就是一種“遊盜文明”,屬於遊居文明中最兇狠的一種類型。

遊居文明的集體行動特性
定居是固定的,遊居是運動的。定居的生產生活方式,決定了對秩序的重視;而遊居的生產生活方式,則決定了對運動的重視。在大多數情況下,定居社會一旦沒有了秩序就難免要發生崩潰,遊居社會一旦失去了運動也難免要發生崩潰。
為什麼會有這個根本區別?用今人的理論來看,不過就是由於資源的約束。在定居社會,因為生存空間是固定的,生存資源總量有限,生產和分配都必須在嚴格的秩序下進行。荀子所發現的“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這個規律是個鐵律,一爭一亂,生產秩序被破壞,生產力下降,一切都完。
但是在遊居社會里就不一定了,因為遊居社會的生存空間不是固定的,生存資源可以通過搶劫、勒索等方式從外部社會獲得,所以爭並不一定亂自己,很有可能是亂別人,反而大有好處。
正是從這裏開始,定居社會和遊居社會有了文明路徑的分岔。前者為了消除紛爭、尋求安定,先王制禮義,偃武修文,確立內部秩序,文明沿着“定”的路徑演化,亂了之後又回到治,一治一亂,曲折發展。而後者為了擴大羣體,增強力量,必須尚武抑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文明沿着“爭”的路徑演化,內部爭,外部爭,在競爭中獲得發展。據此,前者可以稱之為秩序主義,後者可以稱之為運動主義。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定居文明和秩序主義正是在與北方草原遊居文明的運動主義互為他者的博弈中發展起來的。《史記》載黃帝“北逐薰鬻”,薰鬻即獯粥,或葷粥,堯時曰獯粥,周曰獫狁,後世喚做匈奴。匈奴“侵盜暴虐中國”之事,時間長達七個世紀,伴隨着中華定居農耕文明早期的艱難成長。
《史記·匈奴列傳》説:(匈奴)“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如此之習俗、慣例和道德,從定居文明的角度看,與自身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為什麼是“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而不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因為整個部落隨時要快速移動,隨時要“習戰攻以侵伐”,根本顧不上照顧老幼。或者從演化論的角度看,那些試圖要追求尊老愛幼道德標準的遊居部落,早已在大草原上激烈的生存競爭中被淘汰出局了。
為什麼是“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而不是“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因為整個部落要想通過掠奪他人而獲利,就必須靠純粹戰術意義上的進攻和撤退,根本顧不上講究禮儀。同理,那些試圖要在戰爭中學習實踐“宋襄之仁”的遊居部落,也早就亡國滅種了。
草原上騎馬民族的遊牧社會是如此,海洋上海上民族的遊盜社會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總之都是遊居文明,不是定居文明,都是運動主義的,不是秩序主義的。
如此來看,也就不難理解當下的形勢了。表面上看,世界各國都是包括了政府、土地和人民的主權國家,但就其文明本質而言其實大不相同。對於那些繼承和保持了最深厚遊居文明傳統的國家,在疫情衝擊之下,政府和人民都表現出一種寧可在自由奔放的生活中染病,也不要在嚴格約束的規則中苟安的傾向,並不奇怪,因為這就是這種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衝擊之下,整個社會重新迴歸“貴壯健,賤老弱”的道德準則,選擇犧牲老年人拯救年輕人,甚至犧牲老年人拯救國家經濟,也都不奇怪,因為這也是這種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衝擊之下,社會頂層的財富精英通過“無限量QE”率先保護他們自己集團的經濟世界,捍衞自己集團的財富所得,哪怕外部世界洪水滔天也與己無關,更不奇怪,同樣是這種文明的天性。
其內在邏輯也不復雜:千百年的文明演化就是這樣進行的,集體染病就讓它染病,人口損失就讓它損失,但經濟還要保持正常的循環,精英社會還要保持完整,只要運動主義的能量還保持着,這個文明就還將繼續強大。
如前所述,運動主義和秩序主義都是從世界本原引申出來的最根本性的主義,也都成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演進,各自內在邏輯的高下和勝負,都還沒有定論。
一場全球疫情,讓不同文明再次暴露出各自的天性,也都通過各自不同的天性在抗擊疫情的應對模式中各顯神通。這讓近年來越來越熱的文明理論有了現實例證。
最近幾天很多學者都在試圖解釋為什麼東亞國家和地區整體上對於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歐美發達國家反而表現得像是“失敗國家”?從國家理論深入到文明理論當中,其實不難得到解釋。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