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恐懼是如何建設波士頓後灣的 - 彭博社
Feargus O’Sulliv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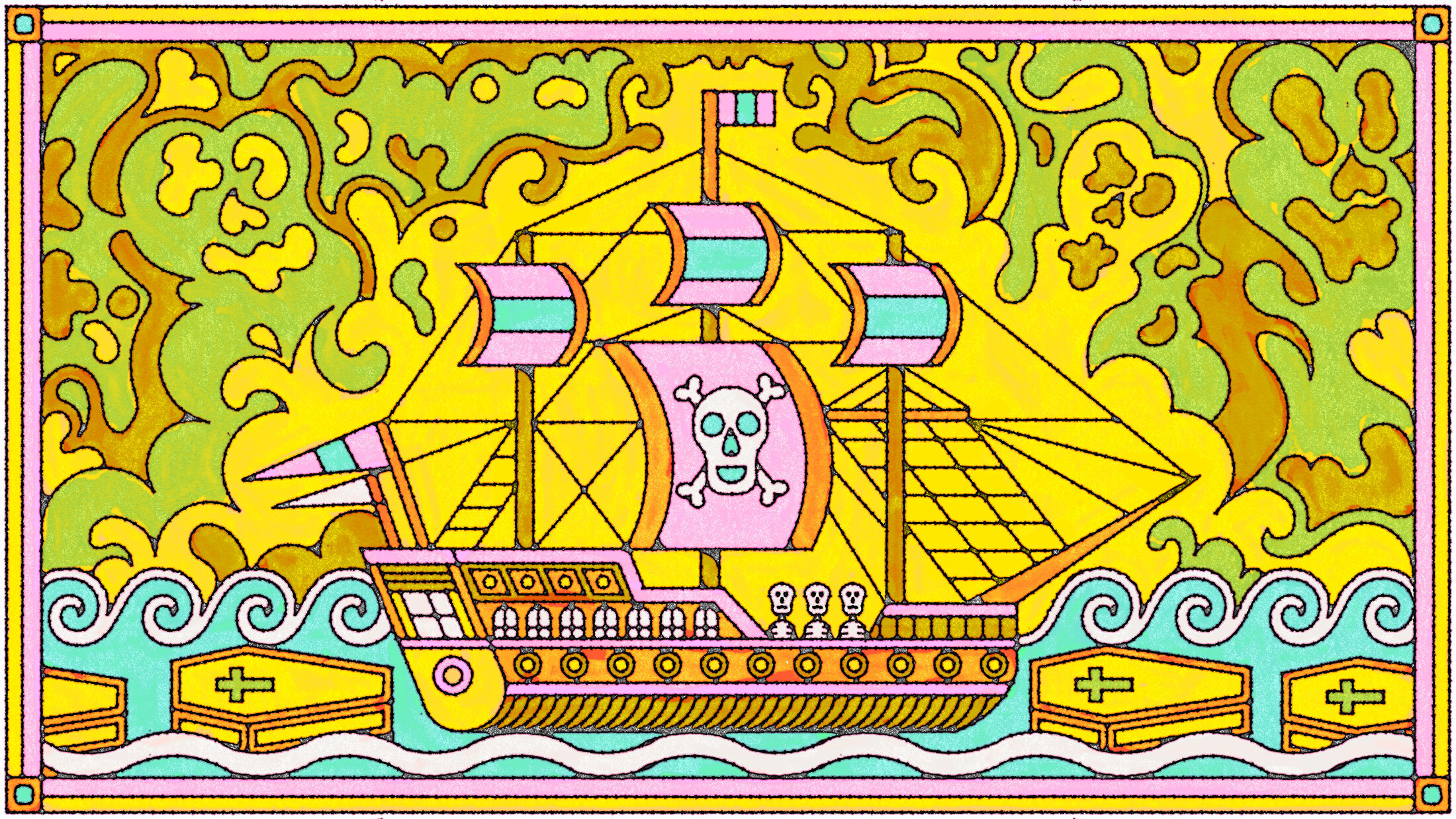 插圖:Nolan Pelletier/Bloomberg CityLab
插圖:Nolan Pelletier/Bloomberg CityLab
(這是三個關於城市及其經濟如何從歷史性流行病中恢復的故事中的第三個。您可以在這裏閲讀第一個關於阿姆斯特丹的故事這裏,以及第二個關於巴黎的故事這裏。)
對於19世紀中葉從愛爾蘭大饑荒逃往波士頓的難民來説,橫渡大西洋的旅程肯定像是從火坑跳入火海。
那些在超過40天的航程中倖存下來,乘坐所謂的“棺材船”之一抵達馬薩諸塞州的人們來到了一個水域和沼澤環繞的半島城市,那裏的建築用地稀少,他們幾乎沒有選擇,只能住在不衞生、搖搖欲墜的木質房屋中,密度明顯高於紐約或倫敦。
BloombergCityLab為什麼巴黎奧運會將成為木質建築的謙遜展示哈拉雷承諾最終修復(部分)佈滿坑窪的道路邁阿密海灘花費25萬美元告訴春假者遠離區劃改革,現在成為一個跨黨派的事業,試圖擴大一個更大的帳篷可預見的是,疾病很快爆發 — 導致霍亂的嚴重爆發。 1849年調查這場流行病的衞生委員會參觀了一些被愛爾蘭大逃亡膨脹的城市最糟糕的貧民窟。 委員會宣佈自己對這些條件感到震驚,他們驚訝地發現“在這種情況下,生命之燈如何能持續燃燒,即使只有一天。”
波士頓並不孤單。 在北美各地,城市因快速城市化和更快的旅行而受到公共衞生危機的打擊。 第三次霍亂大流行在19世紀50年代造成芝加哥人口多達5%的死亡,而斑疹傷寒摧毀了蒙特利爾,並於1847年到達紐約。 1853年黃熱病爆發造成的死亡,同時在新奧爾良造成了如此之多的死亡,以至於該城市贏得了“城市之墓”的綽號。 儘管這些爆發在其持續期間凍結了城市經濟,但它們仍然後來得到了強勁的反彈。
在波士頓,這個過程可以説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進一步,引發了美國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改造項目 — 後灣的填海和開發。 由於波士頓經濟強勁且空間有限,該項目很可能在某個時候會發生。 但它實際上採取的形式仍然受到流行病和19世紀日益主導的恐懼的影響:即城市生活在各個階層中本質上是不健康的。
隨着對通過細菌傳播疾病的更深入瞭解,人們對這種傳播方式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並意識到即使在高密度下也可以控制這種傳播。當我們回顧歷史以尋找關於當今大流行軌跡的線索時,很明顯波士頓的復甦經歷了與阿姆斯特丹和巴黎類似的道路,疾病引發了對城市規劃和建設方式的重大反思。
骯髒的舊城區
在波士頓霍亂爆發時,城市不僅被視為疫情傳播的關鍵交匯點,更被認為是感染源的工廠,這些地方的擁擠、密集和腐爛不僅促進了疾病的傳播,還促成了疾病的實際產生。19世紀中葉,城市通過產生大多數醫學觀點仍然認為是感染的主要原因的東西來實現這一點:有毒蒸氣,或瘴氣。
這種錯誤(即使不完全無益)理論的影響在微生物學家羅伯特·科赫於1876年在炭疽病上的研究證實了疾病通過微生物傳播後,仍持續了十年左右。它提出感染可以從腐爛物質如瘴氣或從糞便或腐爛動物屍體等來源升騰的惡臭氣體中自發生成。
這個想法為什麼看起來是合理的很容易理解。隨着工業化城市的增長速度超過基礎設施的跟得上速度,增加的污垢和惡臭確實造成了不健康的條件,有時甚至在嘗試改進時也是如此。例如,在紐約和波士頓,1840年代向家庭引入自來水最初使衞生狀況變得更糟,因為家庭將他們的舊雨水收集水池改建為污水池,開始滲入地下水和地下室,傳播疾病。污穢理論可能沒有揭示這些感染的真正來源,但至少它確實突出了一個真正的問題。
與此同時,霍亂似乎暗示了一個錯誤的敍事,即疾病是環境而不是基於細菌的,因為有時即使在實行嚴格隔離的地方,它也會迅速傳播。這是因為分離人們對其真正原因幾乎沒有影響,但尚未確定位置:細菌污染的飲用水。由於對污垢和擁擠的焦慮,有些美國規劃者擔心,任何人羣的密集都可能是有毒的,這只是一個小步。
“每一個生物的每一次呼吸都會產生一定量的某種氣體,”偉大的公園規劃者弗雷德裏克·奧姆斯特德在19世紀70年代寫道。“如果不被消散,[它]會使任何地方的空氣起初變得虛弱,過一段時間令人作嘔,最終致命。”
 移民到達波士頓憲法碼頭,來自《巴盧的圖畫客廳同伴》,1857年。通過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印刷### ‘污染的孩子’
移民到達波士頓憲法碼頭,來自《巴盧的圖畫客廳同伴》,1857年。通過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印刷### ‘污染的孩子’
到了19世紀50年代,波士頓的後灣似乎是生產這種有害瘴氣的理想之地。它位於肖姆特半島的後方,1814年被一座磨坊大壩封閉,形成了潮汐池,水可以在其中被引導到水磨中發電。蒸汽動力的出現減少了對這些的需求,使得灣區的水池成為了一個污水陷阱。
當城市仍在與霍亂作鬥爭時,一羣市議員警告説,這些腐爛的廢物正在污染空氣。在1850年的報告中描述了風吹過“整個城市的瘟疫性氣味”,水“像鍋中沸騰,充滿了從下面腐爛物質中爆發出來的有毒氣體。” 地形潮濕和潮濕 — 長期與不健康聯繫在一起的條件 — 使危險看起來更加嚴重。
這個委員會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城市和其周邊潮濕的工業區往往有較高的疾病率。然而,由於不完全理解污染和惡劣衞生條件如何引發疫情,城市往往會混淆疾病的來源和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人。
“有一個理論認為,解決污染的方法是稀釋,如果你把東西放進水裏再也看不見了,那就沒問題。” 《健康與疾病塑造了美國景觀的地形學》的作者Sara Jensen Carr説,該書將於2021年9月出版。 “屠宰場和其他骯髒的行業確實聚集在水域周圍,當然,污染物實際上會隨着時間在水中積累。 城市知道疾病最嚴重的爆發是在這些工業區域。 這些通常是工人居住的地方,特別是移民工人,因為他們離工作最近。 這就是你如何陷入移民和健康之間的問題關聯。”
擔心移民像瘴氣一樣有可能摧毀波士頓也是後灣地區發展的一個因素。 到1850年, 城市的人口普查 顯示,由於愛爾蘭人的定居,城市人口中“外國出生”的比例(這個類別還包括移民的美國出生的孩子)增加到46%。 加入了一個嚴重隔離的非裔美國人人口(當時佔波士頓人口的約1.3%),這種湧入使白人新教徒精英感到驚慌,他們看到自己的人口和社會統治地位受到威脅。
波士頓在以往疫情中的經驗可能為其他城市提供鼓舞,同時也提出了警告。
這些恐懼影響了當時的衞生調查,將對骯髒的厭惡與對那些不得不與之共存的人的厭惡結合在一起。在霍亂大流行之後調查貧困住房時,衞生委員會不僅注意到波士頓最骯髒的貧民窟中存在“糞臭腐爛”,還注意到了委員會認為幾乎不像人的居民。報告並沒有發現精緻,而是發現了“粗魯和庸俗。沒有禮貌,只有粗魯的行為和言語。沒有慷慨的道德和智力文化,只有酒館和妓院的教育。這裏聚集了貧困、罪惡和恥辱的孩子,受到污染的可憐孩子。”
這些“受污染的孩子”不僅在數量上增長,而且生活在距離波士頓精英居住的優雅山坡街道非常近的地方。如果這座城市不能在其範圍內創造一些高質量的、社會隔離的新區,波士頓的精英階層就有可能永遠失去這些精英——以及他們的選票。這有助於解釋接下來發生在後灣區的事情。經過排水、填土並廣泛種植樹木後,這個地方的設計不僅減少了城市衞生危機的可能性。它還讓波士頓的富人能夠擺脱與窮人危險的接近,而不必完全離開這座城市。
 波士頓後灣地區,顯示了共和大道的樹行將畫面分隔開。攝影師:Raquel Lonas/Moment Open### 查爾斯河上的巴黎
波士頓後灣地區,顯示了共和大道的樹行將畫面分隔開。攝影師:Raquel Lonas/Moment Open### 查爾斯河上的巴黎
在1857年至1880年間,這些焦慮在填海灣和隨後的發展中得到了體現,這些發展無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馬薩諸塞州規定,新填實的土地應該被規劃出來,“以防止這片領土成為污穢和疾病的棲息地”,通過廣場和大道的寬闊街道規劃,以確保良好的通風和充足的光線的矯正效果,防止瘴氣滯留。在這樣做的過程中,設計了該地區街道規劃的建築師亞瑟·吉爾曼,效仿了當時衞生改造世界領先的城市:巴黎。
效仿奧斯曼男爵在巴黎所樹立的榜樣,重新開墾的土地被規劃成了異常寬闊的大道 — 其中一些規模宏偉 — 大道兩旁種植了樹木,據信可以中和有毒蒸汽。通過將區內房屋的所有常規業務,如交付或晾曬衣物,集中到(仍然寬敞的)主房屋後面的小巷,增強了寬敞的上層階級精緻氛圍。
這種巴黎風格的影響與之前為城市高端住房提供模板的英國花園廣場模式截然不同,它幫助打造了美國任何城市中最雄心勃勃、優雅的區域之一。即使是網格規劃本身也是一種衞生措施,使排水管和水管更容易沿直線佈置。
但隨着這一地區成為波士頓富人的新客廳,得益於州計劃中規定的文化機構,波士頓較老的低窪地區的條件仍然貧困擁擠,並且仍然容易受到天花、斑疹傷寒、傷寒和猩紅熱等致命疾病的侵襲,這些疾病在貝克灣的早期年代席捲了整個城市。
這些條件最終也得到改善,儘管時間較晚,而且改善速度明顯較慢。部分歸功於貝克灣發展的影響,波士頓的南端——另一個建在填海土地上的高收入住房區——開始向社會階層下滑,因為更富裕的居民向西部遷移,這一過程使其房屋更加負擔得起。在1872年波士頓大火之後,波士頓還向新建區域擴展,這些區域專門為工人階級居民設計,通常以所謂的“三層樓”公寓的形式建造,旨在以負擔得起的價格為居民提供更多的光線和空氣。最後,在19世紀末期創建了翡翠項鍊公園系統,為城市提供了一大片對所有人開放的綠地。
隨着美國開始從當今的大流行中走出來,波士頓在以往疫情爆發中的經驗可能為其他城市提供鼓舞和警示。波士頓並沒有因19世紀的衞生危機而失去經濟勢頭,而是將危機作為推動其時期最宏偉、最受人讚譽的城市規劃的動力。它並沒有必然地減少或試圖減少不平等和惡劣條件,而這些條件正是第一位導致危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