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抗擊COVID醜聞:疫苗分發合作失敗 - 彭博社
Dayna Ev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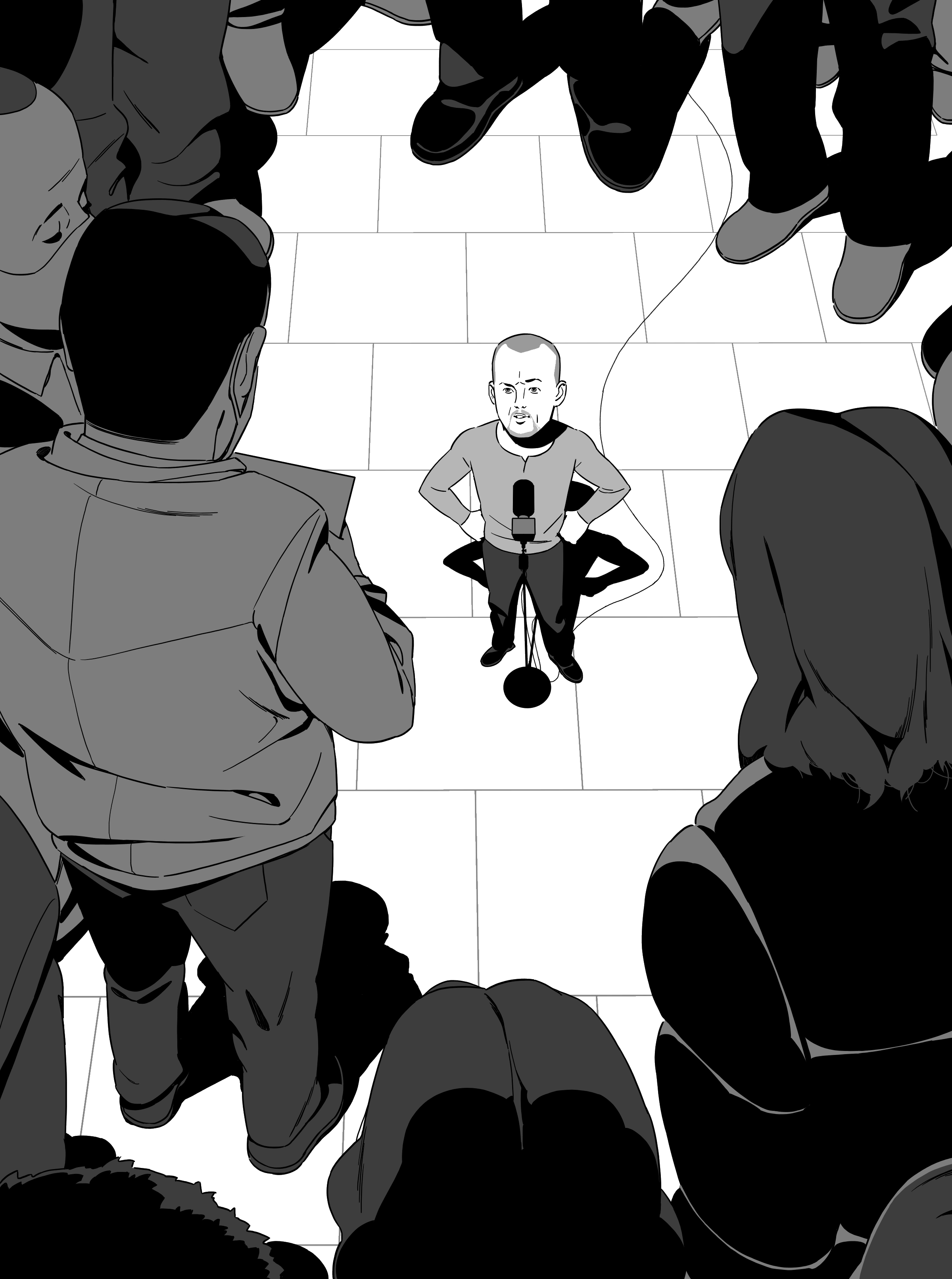 插圖:Jonathan Djob Nkondo為彭博商業週刊繪製從事費城疫苗接種計劃的22歲研究生安德烈·多羅辛看起來確實相信了自己的胡言亂語。在位於翻新過的費什敦社區的公寓大堂裏,多羅辛召開了一場新聞發佈會,就他的非營利組織費城抗擊COVID公司的失敗發表了講話。在沒有強有力、協調的努力下,這位研究生的團隊已經遠遠落後於紐約市等地的疫苗接種率,但多羅辛似乎認為這是別人的錯。“城市選擇我們是因為我們是唯一有計劃的人,”他説,聽起來很憤怒。“我被迫在這裏為自己辯護,反對費城骯髒的權力政治的又一個例子。”當一名記者要求澄清時,雙臂交叉的多羅辛打斷了她:“我也還不明白。”
插圖:Jonathan Djob Nkondo為彭博商業週刊繪製從事費城疫苗接種計劃的22歲研究生安德烈·多羅辛看起來確實相信了自己的胡言亂語。在位於翻新過的費什敦社區的公寓大堂裏,多羅辛召開了一場新聞發佈會,就他的非營利組織費城抗擊COVID公司的失敗發表了講話。在沒有強有力、協調的努力下,這位研究生的團隊已經遠遠落後於紐約市等地的疫苗接種率,但多羅辛似乎認為這是別人的錯。“城市選擇我們是因為我們是唯一有計劃的人,”他説,聽起來很憤怒。“我被迫在這裏為自己辯護,反對費城骯髒的權力政治的又一個例子。”當一名記者要求澄清時,雙臂交叉的多羅辛打斷了她:“我也還不明白。”
這場於一月底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是我家鄉的一個低谷時刻,僅次於2005年鷹隊輸給愛國者隊的超級碗和我們不得不廢除交通法庭的時刻,因為有九名法官被指控犯有刑事行為。費城是一個頑強的城市,其居民忠誠到底,但PFC醜聞讓我們感到有些暴露,某些人心目中,這也證實了唐納德·特朗普在一場總統辯論中的聲明,即這裏只發生壞事。當費城成為新聞焦點時,通常是因為真實或想象中的不端行為,而不是因為我們眾多與疫情相關的互助組織、美國民主的建立,或者賈斯敏·沙利文的歌聲等勝利。多羅辛的策略增加了不良消息的堆積。
 多羅辛在新聞發佈會上採取了一種好鬥的態度。攝影師:馬特·羅克/AP照片不過,我們來到這裏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個月前,當城市讓多羅辛負責疫苗接種工作時,他看起來更有能力,而費城需要儘可能多的幫助。在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峯期,城市每天報告超過2500例新冠病毒病例。疫苗剛剛開始運抵,對邊緣人羣的後勤挑戰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美國最貧困的大城市如何有效地為160萬市民接種疫苗呢?
多羅辛在新聞發佈會上採取了一種好鬥的態度。攝影師:馬特·羅克/AP照片不過,我們來到這裏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個月前,當城市讓多羅辛負責疫苗接種工作時,他看起來更有能力,而費城需要儘可能多的幫助。在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峯期,城市每天報告超過2500例新冠病毒病例。疫苗剛剛開始運抵,對邊緣人羣的後勤挑戰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美國最貧困的大城市如何有效地為160萬市民接種疫苗呢?
費城在這方面有自己的優勢。這座城市擁有世界一流的醫學院,以及美國殖民地第一家醫院,由本傑明·富蘭克林親自創立。然而,為了完成任務,我們委託了一個沒有接受過培訓的年輕人,他的Instagram賬號上充斥着關於大流行病是騙局的笑話。
多羅辛確實有一個優勢:他的非營利組織在疫情初期確實提供了幫助。PFC最初是一羣德雷克塞爾大學的學生志願者,為供應不足的醫院工作者製作3D打印面罩。到去年夏天,它已經發展成一個志願者團隊,在費城Fishtown音樂場所暫時關閉的停車場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市政府向該非營利組織撥款約20萬美元,以擴大運營並增加更多檢測點,特別是在檢測可能難以獲得的社區。這些成功使PFC成為多羅辛申請分發即將到來的疫苗時的一個有吸引力的候選人,儘管他在其他方面完全沒有醫學經驗。在聖誕節期間,他成為了該市的第一個疫苗提供者。
Doroshin的創業氛圍加強了他大膽的承諾,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當他開始讓人們註冊接種疫苗時,他還開始出現在全國電視上,發誓他的團隊會比受過正規培訓的醫療專業人員做得更好。
“我們把整個模式都拋到了窗外。我們説去他媽的所有那些”
但在三個殘酷的星期內,Doroshin的志願驅動非營利組織清楚地表明它無法勝任這項任務,並開始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獨特的大流行欺詐。他悄悄地把PFC變成了營利性公司,讓自己成為員工中薪水最高的人,放棄了在貧困社區的檢測點,並偷偷把疫苗送給想插隊的朋友,然後在社交媒體上炫耀。他讓費城的疫苗接種計劃在一個極其糟糕的月份裏幾乎完全失敗。到1月5日,該市僅接種了大約28,000劑疫苗。正如衞生專員托馬斯·法利當時所説,“在一個擁有160萬人口的城市,這是不夠的。”
更多關於搶劫問題的內容
在某種程度上,對安德烈·多羅辛這樣的人產生好感是很自然的。心理學家、《自信遊戲:為什麼我們每次都會上當》的作者瑪麗亞·康尼科娃説:“我們的大腦非常擅長為事情辯解。在不確定和動盪的時刻,你變得更容易被欺騙。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責任在你,要更加勤奮,因為涉及的利害關係重大。” 多羅辛沒有回應本文的評論請求。
費城是一個喜歡把其獨特人物神化的城鎮,無論是歷史人物(富蘭克林)、虛構人物(洛基·巴爾博亞)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人物(格里蒂)。在他的公寓新聞發佈會上,多羅辛堅定地結束了他加入那個神殿的努力。穿着灰色亨利衫和黑色口罩,看起來對他安排在那裏的記者和攝像組感到惱火,他似乎是那些費城標誌性人物及其仁慈的費城自豪冷靜的精神對立面。“我現在聽説城裏有傳言,有些人並不高興我們是第一個接種疫苗的,”多羅辛在新聞發佈會上説。至少在這一點上,他説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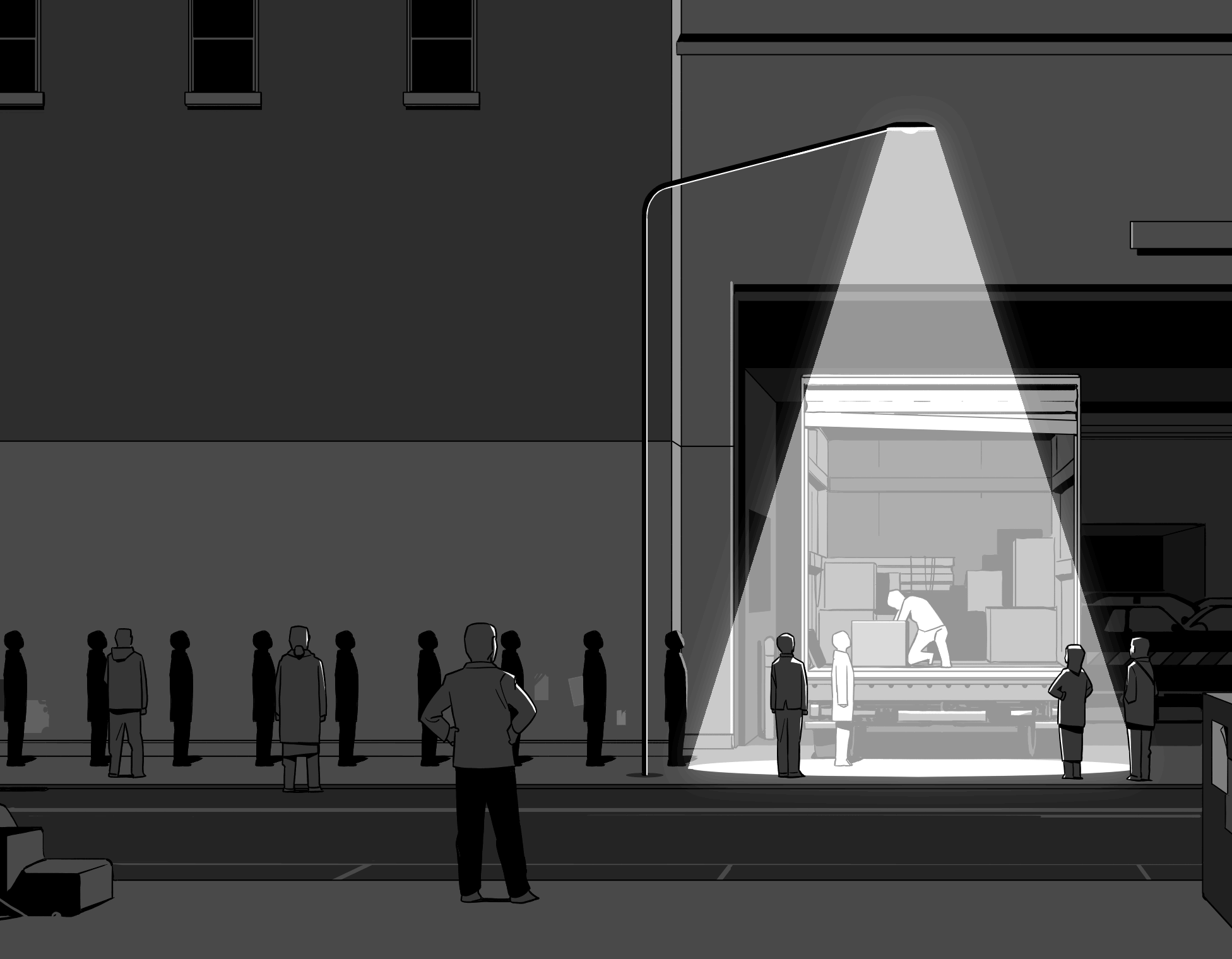 插圖:喬納森·德約布·恩孔多為彭博社繪製要寫一個關於疫情前多羅辛成就的簡要摘要很困難,因為他的簡歷是一系列不斷誇大的描述。在他的LinkedIn頁面上,他自稱是一名“企業家、科學家和慈善家”,主要工作經驗是在德雷克塞爾大學的神經影像實驗室擔任研究員和科學家。(顯著技能包括巴西柔術和“烘烤好的酸麪包。”)但直到本文發表前不久,LinkedIn頁面仍然自豪地顯示多羅辛是費城抗擊新冠病毒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MSNBC稱PFC是美國最具創新性的公司[錯別字],”上個月頁面上寫道。還刪除的內容包括:多羅辛作為Invisible Sea Inc.的首席執行官,他曾將其描述為“加利福尼亞最大的空氣質量[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應對潛在的空氣質量危機。”也許他並不特別自豪於Invisible Sea只籌集了不到700美元。
插圖:喬納森·德約布·恩孔多為彭博社繪製要寫一個關於疫情前多羅辛成就的簡要摘要很困難,因為他的簡歷是一系列不斷誇大的描述。在他的LinkedIn頁面上,他自稱是一名“企業家、科學家和慈善家”,主要工作經驗是在德雷克塞爾大學的神經影像實驗室擔任研究員和科學家。(顯著技能包括巴西柔術和“烘烤好的酸麪包。”)但直到本文發表前不久,LinkedIn頁面仍然自豪地顯示多羅辛是費城抗擊新冠病毒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MSNBC稱PFC是美國最具創新性的公司[錯別字],”上個月頁面上寫道。還刪除的內容包括:多羅辛作為Invisible Sea Inc.的首席執行官,他曾將其描述為“加利福尼亞最大的空氣質量[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應對潛在的空氣質量危機。”也許他並不特別自豪於Invisible Sea只籌集了不到700美元。
費城,像許多美國城市一樣,喜歡一個弱勢羣體。儘管沒有人可以可靠地將多羅辛描述為一個弱勢羣體,但一個沒有正式醫學經驗的研究生試圖接種整個城市對抗失控病毒的行為的純粹不可思議,使他看起來像一個弱勢羣體。他要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小—這正是我們這裏喜歡的東西。
“跳出固有思維是必須的,”副衞生專員卡羅琳·約翰遜在一月初告訴今日節目,PFC崩潰之前。“對於那些有熱情、有想法並能付諸行動的人。”NBC新聞主播斯蒂芬妮·戈斯克出現在賓夕法尼亞會議中心,目睹多羅辛的第一個疫苗接種診所。中心裏擺滿了間隔座位,其中許多座位被衞生工作者佔據,這些工作者通過工作無法獲得疫苗接種。“他們運作得井然有序,”約翰遜告訴戈斯克。
多羅辛扮演了硅谷移民的角色:剃着頭髮,穿着深藍色禮服外套搭配深灰色襯衫和牛仔褲。一方面,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這座城市信任他。在與戈斯克的採訪中,他表現得自信、冷靜,既顯得隨意又掌控一切。另一方面,令人驚訝的是,任何聽到那場全國電視採訪的人都沒有覺得有什麼極端不妥。“我們不考慮,比如説,制度。你知道,我們是工程師、科學家、計算機科學家、網絡安全專家,”多羅辛説。“我們的思維方式與醫療保健領域的人有所不同。我們把整個模型都拋到了窗外。我們説去他媽的所有那些。”
多羅辛顯然沒有考慮到機構化。正如當地新聞媒體後來報道的那樣,PFC似乎主要受到自我膨脹和金錢的驅使。通過城市獲得的測試合同,多羅辛將自己作為員工“數據記錄員”列為公司的主要支出之一。
然而,費城抗擊Covid因其在測試方面的成功而具有可信度。“看起來非常有組織性,”分享當地新聞的拉希德·阿賈穆説,他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使用Phreedom Jawn這個用户名,這是費城人喜歡將“f”變成“ph”並稱一切為“jawn”的一種方式。多羅辛表示,該團隊在秋季為大約2萬人進行了測試。
在接種疫苗方面,市政府打算與儘可能多的獲得認可的組織合作,向儘可能多的人羣分發疫苗,而不需要聯邦政府的指導或協助。與此同時,多羅辛擁有一種22歲年輕人不應有的自信。憑藉他新獲得的市政府關係,他開始將自己的組織推銷為領導疫苗接種工作的機構。他進入了一個特別由市政府組織的疫苗接種委員會,並在去年12月底,當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提供了用於提交潛在診所的文件時,PFC是第一個申請的。一週內,市政府要求多羅辛運行一個疫苗試點項目,以展示他團隊的能力。
如果多羅辛的“兄弟”小丑秀沒有分散真正專家的注意力,也許會很有趣
然而,在第一個大規模診所計劃於1月8日在會議中心開放前幾天,PFC的首席醫療官(唯一持牌醫生)辭職,並警告衞生部門,該運營已悄然將自己重新註冊為一個名為Vax Populi的盈利性組織。告發者還警告部門不要相信多羅辛或他處理疫苗的能力。當多羅辛在會議中心開設診所時,他突然退出了低收入社區的測試點。
阿賈穆立即意識到,情況並不對勁。他開始收到來自那些從費城抗擊新冠疫情組織(Philly Fighting Covid)接種第一劑疫苗的追隨者的消息和評論,稱他們沒有得到第二次預約或者沒有聽到進一步的消息。與此同時,多羅辛的團隊取消了在費爾希爾社區舉辦測試診所的計劃,這是費城最貧困的社區之一。“衞生部要求我們本週設立一個大規模疫苗接種診所,”多羅辛的現場經理維多利亞·米蘭諾告訴依賴該站點測試能力的社區領袖。“因此,繼續進行測試將不可行。”
多羅辛僱傭了他的兄弟謝爾蓋和幾個大學同學,他們曾一起製作3D打印口罩,來幫助他處理疫苗接種業務。多羅辛曾聲稱他是通過從一個家庭朋友那裏獲得的25萬美元貸款或者通過投資加密貨幣賺取的利潤來資助這項業務。當團隊的一些輕率行為曝光時,一些情況非常明顯:在他公開的Venmo賬户上,在標有“pfc payment”(費城抗擊新冠疫情組織付款)的請求之間,多羅辛列出了標有“tits”(胸部)、“boobs”(胸部)和“strippers n hoes”(脱衣舞女和妓女)的付款。
在幕後,多羅辛的事情開始出現問題。在將費城抗擊新冠疫情組織變為盈利性機構後,他更新了網站,但沒有添加隱私政策。噹噹地新聞媒體WHYY的記者詢問為什麼時,多羅辛在網站上添加了一行文字,暗示那些用敏感醫療信息註冊他們的測試診所的人可能會被出售他們的數據。與此同時,PFC疫苗接種診所的一名志願護士報告稱看到多羅辛帶着疫苗回家給他的朋友注射,幾個人向WHYY報告稱,他們看到他在Snapchat上吹噓這一點,而這些圖片在被查看後很快就消失了。
 斯坦福,一位經驗豐富的醫生,等待批准她自己的疫苗提案。攝影師:Kriston Jae Bethel在與《今日》節目記者戈斯克的第一次採訪僅三週後,多羅辛接受了一次更加敵對的跟進採訪。他承認接種了疫苗,但堅稱他的團隊先打電話詢問是否有人需要這些疫苗。最終,他選擇先給自己和朋友接種疫苗,因為“疫苗快要過期了”。當戈斯克追問多羅辛是否有資格給疫苗接種時,多羅辛羞怯地回答説沒有。
斯坦福,一位經驗豐富的醫生,等待批准她自己的疫苗提案。攝影師:Kriston Jae Bethel在與《今日》節目記者戈斯克的第一次採訪僅三週後,多羅辛接受了一次更加敵對的跟進採訪。他承認接種了疫苗,但堅稱他的團隊先打電話詢問是否有人需要這些疫苗。最終,他選擇先給自己和朋友接種疫苗,因為“疫苗快要過期了”。當戈斯克追問多羅辛是否有資格給疫苗接種時,多羅辛羞怯地回答説沒有。
幾天後,該市關閉了多羅辛的診所,並終止了PFC的合同。在一月份的新聞發佈會上,多羅辛指責衞生專員法利。他説:“我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終止合作,但我堅信應該進行調查。”多羅辛強調了多次他認為法利應該辭職。在事件發生幾天後,曾支持多羅辛努力的副衞生專員約翰遜辭職。幾個月後,法利也承認了一個無關的失誤而辭職:他處理不當了1985年MOVE爆炸案的受害者遺體,當時費城市轟炸了一座屬於黑人活動人士的房屋,造成五名兒童和六名成年人死亡,並導致隨後的火災摧毀了61棟房屋。
如果多羅辛的滑稽秀沒有讓費城分心,也許會有些好笑。在他獲得開設第一個疫苗接種診所的批准後,城市卻拖延了阿拉·斯坦福的批准。斯坦福也通過她的黑人醫生協會運行測試診所,並曾與多羅辛一起在同一個疫苗諮詢委員會任職。在城市終止與研究生合同後不久,她的團隊獲准在天普大學開始接種疫苗。阿賈穆指出:“她做醫生的時間比他做人的時間還長。斯坦福博士非常有成就,獲得了許多榮譽,並且有組織衞生活動的歷史。作為一個黑人酷兒,我覺得平庸的白人總是比黑人得到更多機會。這只是一個案例研究。”
一月份,多羅辛為自己迄今為止的慘敗提供了最好的辯護,但仍然不太好。“我們只是一羣孩子,”他告訴*《紐約時報》*。“在此之前我對法律結構一無所知。我並不在乎。我不是律師,我是個書呆子。有人試圖把我描繪成邪惡的形象。我只是想説,‘夥計,在我做這件事之前我並不知道非營利組織的所有規則。’”
直到五月,最後一次有人聽到這位前研究生的消息是在二月底,那時他給費城抗擊新冠病毒組織的原始捐贈者發送了一封他稱之為道歉的郵件。這封郵件更像是一篇針對他的仇敵的長篇演講。在感謝捐贈者“相信”費城抗擊新冠病毒組織之後,他寫道,“但首先,我要道歉。有一些次要的行政決定成為競爭對手和其他不與我們利益相同的團體關閉我們並個人抹黑我的彈草。”他説他將把運營重點轉移到償還債務和“恢復我們名譽的美好”。他在郵件結尾寫道“感謝您的關心和支持”,試圖不令人信服地暗示有人對他的幸福表示了關切,而不是對他的懲罰。
與此同時,費城基本上已經從早期的失誤中恢復過來。三月份,該市重新開放了會展中心作為大規模疫苗接種點,現在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合作。通過費城抗擊新冠病毒組織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也可以在那裏接種第二劑。到六月,超過74萬人,幾乎是該市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二,已經完成了疫苗接種。(許多當地餐館和酒吧提供持有疫苗卡的人免費甜甜圈或啤酒,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黑人醫生協會仍在為被剝奪權利的人提供診所服務,現在稱為 Philly Vax-Jawn 活動,並試圖通過向接種第二針疫苗的隨機人員提供1萬美元的彩票獎金來克服疫苗抵抗力。 Covid 限制已完全解除,人們在陽光明媚的城市裏四處走動,遛狗,喝啤酒,併為搖搖欲墜的體育隊伍加油——他們再次自豪地在這裏。